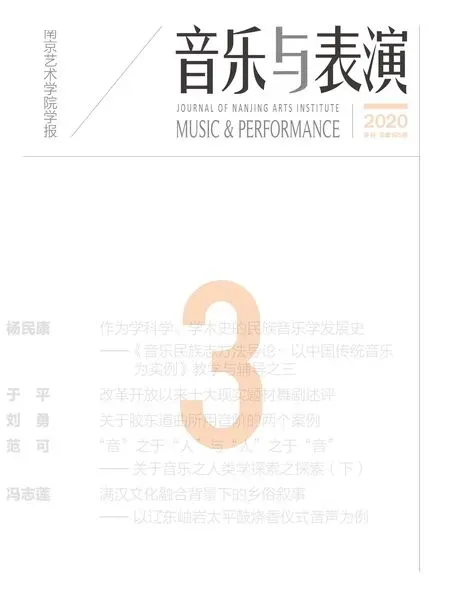乐不可妄兴也①
——《史记·乐书》中的乐论思想探究
王 维(齐齐哈尔大学 音乐与舞蹈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其体例分为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1]226但是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史记》缺十篇(“十篇缺,有录无书”[2]2724),三国时期的张晏具体指出了缺少的十篇名称,而《乐书》就在其中。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3]2509
关于《史记·乐书》亡缺情况的论述历代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唐代司马贞认为,现存的《史记·乐书》是后人取自《礼记·乐记》补写而成。[3]2509当代学者对这一问题归纳出四种观点[8]26:一、认为《乐书》亡缺,今本为后人补作。二、认为《乐书》不缺,是司马迁取自《乐记》而作。三、认为《乐书》中的序文即《乐书》全文。四、认为《乐书》的序文尚在,但正文缺失。
以上研究就《史记·乐书》的真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证,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料参考,但是学界目前对于《乐书》中所蕴含的音乐思想史问题则缺少相应的关注。鉴于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史记·乐书》的思想内容方面,以期对如下问题进行解答:《乐书》中所谈及的礼乐问题有何特殊价值?《乐书》中的乐论思想表达出哪些政治见解?这些政治见解通过司马迁的《史记》留存于世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一、“凡作乐者,所以节乐”
《史记·乐书》的结构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是序言部分,第二是以先秦以来《乐记》的原始材料作为主要叙述的部分。②“司马迁《乐书》材料不会采自毛、刘本《乐记》,而应是自有其来源。《史记·乐书》中的文字顺序与荀子《乐论》中的文字书序也有所不同,证明司马迁采集的《乐书》的材料,绝不会直接袭自荀子《乐论》。这充分证明,西汉之前乃至先秦,一定流传着很多有关‘乐’的材料”。“‘《乐记》’一名及其各篇的得名与最后成书,当在汉武帝之时,但当时关于此书的材料早有流传。”参见:孙少华.汉初《礼记·乐记》的版本材料与成书问题[J].孔子研究,2006(6):103—104.序言部分主要表达了“太史公”(即司马迁)对于“作乐”的理解,这也是本文将要重点阐述的内容。第二部分以《乐记》内容为主体,记述了音乐本体以及乐与礼的关系问题,由于此处内容与《礼记·乐记》基本相同,本文将另文探讨。
太史公在《史记·乐书》的开篇并没有从音乐话题切入,而是说起了君臣关系问题。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3]1037
太史公说自己每读到上古《虞书》中描述的如下场面就常常感叹流泪:君臣之间能够相互劝勉告诫,天下就得安宁,而辅佐之臣不良,就会导致万事堕坏。在司马迁的眼中,君臣之间的理想关系是“相敕”即相互告诫、相互劝勉,但决定天下安定的不仅仅是君主,也包括“股肱”之臣,“股肱不良,万事堕坏”,这里可以看到,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官所承负的国之安危的责任感和历史担当意识。太史公接着写道:
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3]1037
大意是说:周成王祭祀作颂,面对自己的言行充满内疚和责备,遥想先祖的遭难,心中满是悲伤和痛苦,成王以如此谦卑顺服的心态去治理国家,怎能不做到善守善终呢?[3]1037
本文通过查考《诗经·周颂》中有关成王作颂的诗篇,发现无论是“维予小子,夙夜敬止”(《闵予小子》),还是“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访落》),周成王都是通过虔诚的祈祷来表达对昊天无上旨意的敬畏和先祖生命意义的追念,成王颂诗中看不到奉天承运的自信张扬,处处充满了戒慎恐惧的敬畏谦卑,这也显露出成王作颂的意义并不是在彰显自我以善行赢得上天和先祖之灵的保佑,这种谦卑恐惧的心态恰恰说明了人靠自身的努力很难做到完善,唯有首先承认自身的不足,怀着一颗敬畏神灵的内心(“战战恐惧”),祈求上天的引领和祖先之灵的保守,才有可能“善守善终”。
太史公说:“君子不为约则修德”,张守义正义:“为,于伪反”,[3]1037“伪”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意为“诈也”,[4]263段玉裁注:“诈也,欺也。……徐锴曰,伪者,人为之,非天真也,故人为为伪是也。”[5]379伪是欺诈、人为的意思,那么“为”与“伪”相反,“为”可以理解为真实自然的意思。“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是说,君子不能真实自然地遵守约定就需要修正德行,自满就会丢弃礼仪。君子需要遵守什么约定呢?从前面成王作颂的意义阐释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成王以虔敬的心态在其生命深处与上天神灵之间达成了一种紧密而又真实的联结,因为有了这种天人关系的建立,上天才能葆有其善始善终的治国成果。可见,“君子不为约”的“约”即为君子与上天神灵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约定,君子如果不能真实无欺地按照上天的旨意(或曰天理)去行,那就要“修德”。
那么,什么是“修德”呢?“德”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意为“升也”,[4]56段玉裁注:“升当做登。辵部,曰迁登也。此当同之,德训登者。”[5]76从“德”字的本意可以看出,“德”最初的含义并不是指人自身所拥有的品质属性,而是心灵向着完善境界的转向和提升。《老子·四十九章》这样描述“德”:“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对待善良的人我也善良,这不是真正的善良;真正的善良是对待不善良的人我依然能以善良待之,这才是真正的善良(“德善”),这才是“德”之境界。人的本性可以做到“善者吾善之”,但是对于“不善者”人很难做到以善待之,正如太史公所云:“非大德谁能如斯!”这种心灵境界的提升无法来自人的努力,它需要上天之德的恩赐。君子修德不是单单依靠自身努力才能做到完善自我,他需要在心底里重新建立与神灵之“约”的关系,这是一种心灵的转向,而非行为的为善,因为“人为为伪”。
司马迁开篇举出君臣关系以及成王作颂的例子,就是想要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决定天下安定的人是能够做到相互劝谏的君臣阶层,而君臣之间要想做到彼此坦诚相见,仅仅依靠个人德行的努力是无法真正做到的,只有像成王一样本着一颗“战战恐惧”的内心,向着上天和神灵进行反省和祈祷,重建人神之间的约定关系,君臣才会得到上天之德的恩赐,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就集中体现在礼乐文化当中,“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3]1043如果人神关系断裂的话,人就会将一切的所得归功于自我努力的结果,也就失去了对于神灵的敬畏之心,这就是“满则弃礼”的原因所在。
司马迁在《乐书》开篇就描写了这样一幅“成王作颂”的理想场景,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史公眼中真正的制礼作乐其实是一种人神之间的沟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着对于自身过失的反思、对于君臣关系的熔铸、对于先祖生命的追念,最重要的是,对于昊天之命的领受与持守。圣人作乐怀揣的是一颗对于上天神灵“战战恐惧”的敬畏和“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的感恩之心。这也十分符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226的治学宗旨。
紧接着,司马迁引用了《书传》中的话:“治定功成,礼乐乃兴”,[3]1037如果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可以解释为:“治定功成”是上天的恩赐,因此礼乐的兴起是对上天的感恩。之后,司马迁从天道转向人道,“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3]1037,人性的深渊中所展示的灵魂品质并不相同,尽管上天降临在于每个人的大德是同样的,但每个人所欲满足的需要是不同的,司马迁由此提出“作乐者,所以节乐”[3]1037的核心命题,即君子所作的音乐是为了“节制”人的欲望。“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3]1037君子作乐首先要满足神灵的需要而非自身的需要,司马迁通过一段天子明堂祭祀的描写具体说明这个问题。
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协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嗷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3]1037
明堂是天子祭祀上天的场所,在礼乐仪式过程中,天子与神灵之间达成了灵魂的联结,故此神灵临在于每个人的心里,使万民之心都得到净化,“万民咸荡涤协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礼神之乐传达出的能量能够抵达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能够满足每个人的内在追求并让每个人都能感到真实、饱满、清晰而又亲切的感觉,这些取决于上天的恩典,君臣所要做的就是对于上天之理的绝对服从。而有了这个绝对的唯一标准——昊天神灵,那么任何不同国情、不同风俗都将沐浴在神灵的护佑下,“博采风俗,协比声律”,最终成就政教的推行。[3]1037
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攫取了从春秋到武帝时期几个典型的君臣论乐的例子。第一个讲了春秋时期孔子论乐的事例,孔子不满于齐国女乐见容于鲁国,作五章之歌以讽刺时事(“作五章以刺时”[3]1038),但孔子的论乐之举并没有奏效(“犹莫之化”[3]1038),由鲁国“凌迟以至六国”,[3]1038最终都没有免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3]1038的后果。既然孔子作乐无法改变现实政治,司马迁为何还要举这个例子?参考《太史公自序》中的话,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3]2491
太史公说:先人有言,从周公死后五百年出现了孔子,孔子死后至今又过了五百年,没有人能够继叙清明时代的历史,没有人能够正定《易传》、继承《春秋》、对诗书礼乐追本溯源。司马迁将时隔五百年出现一次的周公与孔子视为上天的特殊拣选,他们编写史书、传承礼乐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世间的安定,更是为了彰显超越时空的神圣价值,这是上天的旨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表达出一种天命不可违的绝对顺从。司马迁之《史记》是在代上天立言,其承载的是上天的使命。
第二个例子举出的是秦二世与李斯、赵高对于“乐”的不同理解。李斯秉承着古代乐教的传统,强调“诗书礼乐”对于王公贵族性情培养的重要性。而赵高则认为,音乐可以满足人们不同时期的不同欲望(“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3]1038),因此没必要守着古时的诗书礼乐不放(“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3]1038)。历史事实表明,秦二世仅在位三年,秦王朝便灰飞烟灭,而汉承秦制,司马迁此处以春秋笔法意有所指——汉代礼乐只有沿着传统乐教之路,才不至于重蹈覆辙,而传统礼乐所传承的是以神灵为中心的敬拜,而非以人欲之乐为目的。
其后的例子则说到汉代皇帝作乐的事情。汉高祖过沛县曾作《大风歌》,“令小儿歌之”[3]1038,高祖死后,该乐曲仅于乐府时常演习而已。但是对比当今的皇帝则不可同日而语,武帝作乐大费周章,曲子规模庞大(“作十九章”[3]1038),编曲人李延年“拜为协律都尉”,[3]1038而且诗词内容“多尔雅之文”[3]1038晦涩难懂,需要“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3]1038之后,司马迁间接解释了汉武帝作如此晦涩复杂之乐的原因,他说汉家作乐常是为了祭祀太一之神。也就是说,武帝作乐所欲呈现的是天神的旨意,所以晦涩难懂,“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3]1038。紧接着,司马迁举出了汉武帝为神马作歌的例子,其中涉及汉武帝与大臣汲黯、公孙弘对于作乐问题的不同看法。
汉武帝为所得宝马作歌,将其视为天神对于有德之君的恩赐(“天马来兮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3]1038),而大臣汲黯认为王者作乐应该有所依据,“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3]1039对于武帝为宝马作歌是否为上天的旨意,汲黯不以为然(“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3]1039),他认为真正拥有神圣意义的音乐是能够开启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并使每个人都能感到真实的感动与力量。汲黯实际上是在批评武帝以神意为己意的自我标榜,丞相公孙弘看到汲黯乐论思想背后潜藏着对于武帝政制权威的挑战,因此定其重罪:“黯诽谤圣制,当族。”[3]1039
我们看到司马迁所举的几个君臣论乐的例子都有其深刻的政治含义。孔子面对世风日下,郑音兴起的政治局面,“作五章以刺时”,也暗示了司马迁欲通过“乐论”思想的叙述,接续孔子的刺时劝谏之举,为汉室重寻德性本源。秦二世对“乐”进行了历史相对性的解释(“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3]1038),这种斩断“乐”之本源的解释,也等于弃绝了“乐”与绝对价值的联系,秦代速亡与其价值失序不无关系。武帝作乐,虽表面上本于太一神灵,(“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此以为太一之歌”[3]1039),实际上却是以己意代替神意,司马迁借助大臣汲黯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于武帝价值取向错位的忧虑。①(日)泷川资言:“结末数语(指汲黯、公孙弘之语——作者按),与平淮书烹弘羊天乃雨同一笔法,言外有无限意味。彼欲归罪于桑弘羊,此不欲显言君恶,史公妙笔,后人不可企及”。参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1651.君臣阶层对于音乐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现世政治的好坏。那么音乐的社会功用到底是什么?
二、“乐不可妄兴也”
太史公在《乐书》的第二部分以先秦以来《乐记》的原始材料为蓝本,对音乐的本质与社会功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原始材料当中也包括了荀子《乐论》以及《韩非子·十过》中的乐论思想。有关《乐记》的思想内容,学者们已经进行过众多论述,拟将另文阐述。如前所述,太史公作《史记·乐书》的目的主要针对的是君臣阶层,而“乐”恰恰关乎君臣对于世间真实价值的选择与判断(即天人关系的处理),对于“乐”的选择将直接影响一国的政治兴衰,这就涉及礼乐的社会功用问题。
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3]1078
司马迁举出舜乐的特点在于“乐与天地同意”,舜乐彰显的是天地的自然之道,所谓“生长之音”即符合生命规律的音乐,“生长之音”是上天创生旨意的彰显,它满足了每个人的生命需要,因此说,舜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纣乐之所以令其“身死国亡”,主要原因在于,这种音乐“不时也”。时间是上天的赐予,“不时也”就是与天命相违,纣乐满足的是商王自身的喜好,这种没有神圣价值的音乐只会让人心散漫疏离,最终导致“万国殊心,百姓不亲,天下畔之”。这段文字透漏出一个关键信息:音乐的本质中蕴含了“生长之音”与“不时之歌”(或曰死亡之歌)两方面的生命形式,在这样的分裂形式当中,人心只有转向超越时空的神灵,生活才会充满神圣的光照,生命才会因此而具有意义。因此说,礼乐只是天人关系的外显形式,真正决定人之生死与国之盛衰的是人的选择,而人的选择来自对于神灵主权的全然顺从,对于自我有限的清醒认知以及对于人性深渊的深刻洞察。在这里,太史公举出了《韩非子·十过》中有关“靡靡之乐”的故事。
晋平公受欲望的唆使,一再请求师旷为其演奏世间最美的音乐,最终导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期间,师旷多次提醒平公:“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师旷其实是在提示主君,美好的事物与残酷的现实往往属于一体两面,享受美好的同时也要承负生命的残酷,只有有德之人才能担此大任,因为他们来自上天的特殊拣选、是背负上天特殊使命之人,他们满足的不是个人的欲望,而是对于昊天之命的全身付出。[3]1079对于不具有这种上天恩赐和艰巨使命的普通人,司马迁给出了“乐不可妄兴”的忠告。“听者或吉或凶”体现了音乐所象征的天命与人欲的一体两面性,音乐是对人性的彻底敞开,当人心与上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的时候,这样的音乐带给人的就是上天的恩赐(“吉”),反之,就是上天的严惩(“凶”)。
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天人关系的建立,依靠的不是人的刻意为之,努力为善依然是人的自我能力的显现而非内心对于神灵的彻底顺从,由从前文成王作颂的例子可以看到,成王之所以对神灵充满了“战战恐惧”之心,就是因为他看到自身能力的有限,懂得先祖创业的艰难(“推己惩艾,悲彼家难”),怀着这样一颗敬畏之心,他的内心才会让位于神灵并成为神灵的居所。所以说人与神灵之间关系的建立,靠的不是人的努力为善,而是对于神灵的信靠,因为人性的堕落开始于心灵方向的偏差,而不是行为结果的错误。因此,司马迁强调:“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他没有说:“行正而音正”,就是因为只有在神圣的音乐之中,人们的内心才会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转向神灵,这里所摒弃的恰恰是刻意为善的追求。也就是说,只有在顺从上天旨意的前提下,神灵才会临在于人的内心并指引人做出应有的价值选择。“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3]1080这也是古代儒者一直强调礼乐传承的原因所在。
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3]1080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史记·乐书》首先在序言部分明确了该文的写作对象是君臣阶层,君臣阶层对音乐的看法既体现了他们的德性品质,也决定了一国兴衰的政治格局。司马迁看到了圣人作乐背后所体现的天人关系问题,因此指出:“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圣人作乐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喜乐,而是为了满足神灵的需要,只有这样,神灵才会降临在于人的内心,指引人的方向。作为公羊派的传人,太史公以春秋笔法叙述了从先秦到武帝时有关君臣论乐的例子,揭示了礼乐传承尽管在不同时代历经坎坷、不被人君认可,但依然有许多敢于仗义执言的史官大力推崇礼乐,因为礼乐中蕴含着人与神的联结,作为一代史官所要传达的礼乐精神正是上天的旨意,这也是史公所承载的上天使命。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言:“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3]2508
如果想要改变政治局面,必须从君臣阶层的德性品质开始改变,而君臣德性品质的改变取决于他们与上天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获得就集中于礼乐传承当中。司马迁秉承了古代乐官培养贵族道德品格与史官褒贬现实政治的文化传统,追根溯源从先秦以来的《乐记》原始资料中挖掘音乐与神灵、音乐与人性的关系。在其所引述的《韩非子·十过》有关“靡靡之音”的故事中,司马迁揭示出离开了神性的临在,至美乐音所呈现而出的残酷本相是世人无法承负的,他由此提出了“乐不可妄兴”的审慎之语。
这种神性的临在只有在礼神之乐中才能呈现,因此培养士人的礼乐文化,传承礼乐文明就成为历代儒家学者不断言及的话题。司马迁提出:“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音正的依据来源于人对神灵的敬畏、对上天之理的遵从,同时司马迁又将五音的道德属性与阴阳五行进行联结,从而确立了其乐论思想的形上理据。
从上述对《史记·乐书》的梳理中,我们发现,司马迁一直奉行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226的精神信念,即探究人性与上天的关系,考察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最终形成自身的思想见解。正因为司马迁保有着礼乐文化中对于神灵的敬畏以及作为一代史家承载上天使命的信心,才有他“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的德性涵养。在遭遇李陵之祸后,司马迁在艰难的政治处境中承担了历史和生命中的残酷,并在这种艰难时刻做出了超越生死荣辱的精神抉择(撰写《史记》)。在善恶两难的矛盾中,太史公坚守了作为一代史家的精神高度[1]226-227①,可以说司马迁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践行着他的礼乐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