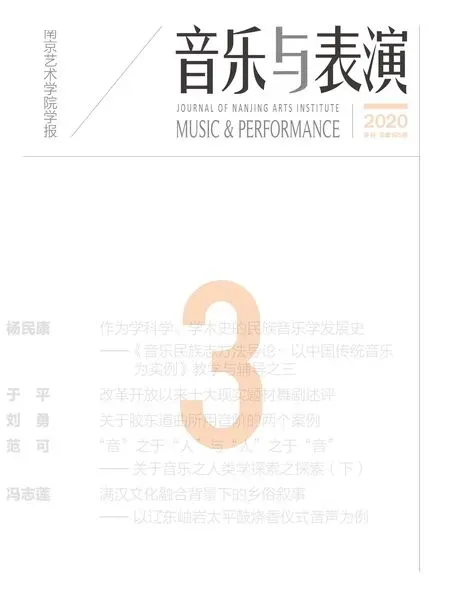唐宋宫廷对词乐的接受与传播①
彭文良(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词作兴起于民间,而大盛于文人,几成定论②胡适说得比较绝对一些,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汉魏六朝的乐府来源于民间,以后的词是起源于歌妓舞女的,元曲也是起源于歌妓舞女的,弹词起源于街上的唱鼓词的,小说起源于街上说书讲史的,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哪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白话文学史》,台南东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胡适认为文学起源于民间的关键在于新的音乐兴起。关于词体起源,比较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吴熊和的论断:“词发源于唐,而大盛于宋”,“盛唐时于民间孕育生长,中、晚唐时经过一些著名诗人之手逐步成熟和定型,这是它产生发展的大致过程。”(《唐宋词通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2页。)。相应地认为,词的创作存在民间和文人两个词坛。在众多的研究中几乎都忽略了宫廷对词乐孕育传播、词作兴盛发展的作用和意义。20世纪初,刘毓盘曾提出“小词之起,出于隋之宫中”[1]23,然此论断几乎湮没无闻;21世纪初,木斋以翔实的材料论证认为词体非源于民间,而起源于宫廷[2],虽然论证严密,因其太具颠覆性,亦不为学界普遍接受。尽管如此,唐宋宫廷确实是用乐、制乐、唱词、作词的重要场所,对词乐的接受与传播却是不争的事实。词体能兴盛发展,与宫廷对这种新兴的文艺样式的接纳、容受并推广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宫廷是与民间、文人鼎足而三的重要词坛之一。唐宋宫廷对词乐的接受与传播具体表现为:
第一,广泛采用、演奏新兴的词乐,并在各种宫廷活动中大量传唱倚声而制的词作。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词乐兴起于初盛唐之际,主要来源为胡乐,比如《旧唐书·乐志》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相传谓为法曲。”[3]1089,胡乐在初盛唐之际,即传入宫廷,如《旧唐书·舆服志》云:“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3]1958另如《新唐书》载:“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4]4295可见,胡乐在宫廷广受欢迎。唐代音乐史上,玄宗在接受、传播胡乐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据《旧唐书》载:“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3]1051玄宗以帝王之尊推广胡乐,提升了胡乐的地位。玄宗时期,宫中词乐演奏可谓彬彬盛况,这从今存的《教坊记》中可见一斑。今人李剑亮认为:“开元、天宝年间的教坊乐曲,据《教坊记》记载,共有三百余首……它们全都是由教坊妓演奏于宫廷中。”[5]25五代宫廷用乐亦极多,如蜀主王衍“曾宴于怡神亭,自执板,歌《后庭花》《思越人》曲”[6]39。宋代宫廷用乐基本沿袭唐代盛况而来,特别是南宋后期,久处承平,宫廷用乐简直到了奢华的程度,比如《武林旧事》卷一,“圣节”一条记载,理宗用乐规模前所未有,其曲目中大部分属于词乐曲调[7]17。
词乐进入唐宋宫廷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民间歌舞侍妓入内教授,传入民间所用的新兴乐曲,比如《词苑萃编》载:“张红红者,大历初随父丐食,遇将军韦青。因其善歌,乃纳为姬,颖悟绝伦。有乐工取《西河长命女》加减节奏,颇有新声。未进内庭,先歌於韦青宅第……寻诏入内庭宜春院,宠泽隆异,宫中号为记曲娘子,即拜才人。”[8]1986杨湜《古今词话》亦载:“韦庄有宠人,资质艳丽,兼善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词,强庄夺去”[8]20“政和间,京都妓之姥曾嫁伶官,常入内教舞。”[8]45总体说来,宫廷音乐是靠不断吸纳民间音乐以补充新鲜血液,正如今人曾大兴所云:“宋代的音乐,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宫廷音乐,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是市井新声,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并且不断向宫廷所属的教坊乐渗透。”[9]90
另外一种是民间和文人词作传入禁中,并在宫中演唱。最早的民间词集《云谣集》被认为:“传播之范围,可能已上达宫帏之长宵宫”[10]55。中唐文人词兴起之后,流入宫中演唱的记录则不胜枚举,比如《乐府杂录》载:“《杨柳枝》,白傅闲居洛邑时作,后入教坊。”[11]41《北梦琐言》云:“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温飞卿新撰密进之。”[12]89宋代宫中传唱文人词记录尤多,比如柳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13]49, “柳三变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14]311;宋祁词:“宋子京出知安州,以长短句咏燕子,或传入禁中,仁皇帝览之一叹,寻召还玉堂署”[15]151“子京归,作词,都下传唱,达于禁中”[16]2;苏词:“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进呈。读至‘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曰:‘苏轼终是爱君。’”[8]59总体上论,初盛唐时期宫廷对词乐的接受与传播主要表现为演奏用乐,中唐及以后由于词作的大量出现则主要表现为传唱文人词作。
第二,建立相应的制乐机构,并大量创作新曲调。
相对于演奏用乐、传唱词作,建立制乐机构并创作曲调更能体现宫廷在接受与传播词乐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唐初音乐制度沿袭隋制:“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3]1059,主要的管理机构为太常,用乐主要为雅乐。初唐时期为了更好地管理和使用新曲、俗乐、胡部音乐,太常另立乐园新院或云别教院:“俗乐,古都属乐园新院,院在太常寺内之西北也”[11]44“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3]1052玄宗对乐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首先是新设教坊,以单独管理俗乐:“(玄宗)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4]475;其次是把宫廷音乐演出队伍分为立部伎和坐部伎,玄宗尤爱坐部伎:“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特别是“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4]476,意味着胡部乐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旧唐书·乐志》云:“坐部伎有《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3]1062,《新唐书·乐志》云:“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4]477,这两则材料里提到的龟兹乐、法曲与胡部新声都是词乐的重要来源;至于天宝年间所传的《凉州》《伊州》《甘州》后来都直接转为词调。综上我们知道,词乐至少在开元、天宝间的宫廷里已经开始孕育了,相关的机构是教坊,演出队伍为坐部伎。
终唐之世,教坊及乐工都存在,但玄宗以后盛极而衰,特别是经历安史之乱及潘镇割据,宫廷经费紧张,教坊、梨园等机构被不断裁拆,乐工队伍一直在缩减。如《旧唐书·顺宗本纪》载:“(永贞)三月庚午,出宫女三百人于安国寺,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召其亲族归之”[3]406;《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宝历二年)诏教坊乐官、翰林待诏、伎术官并总监诸色职掌内冗员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并宜停废”[3]524。至晚唐再遭黄巢起义,“乐工逃散,金奏皆亡”[4]462,音乐机构再遭打击。
宋初音乐机构设置情况见于《宋史·乐志》:“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17]3348,宋初在沿袭唐制基础上主要是从地方不断吸纳乐工,以充实宫廷。整个宋代的音乐机构变化情况,《宋史·乐志》有简明勾勒:“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政和间,诏以大晟雅乐施于燕飨,御殿按试,补徵、角二调,播之教坊,颁之天下。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乾道继志述事,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17]3345简言之,宋代音乐机构的设置历程,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宋初设立教坊,但废坐部伎,这在唐制基础上,有延续,也有改革;第二阶段,徽宗时期设立大晟府,用以创制乐曲,这是宋代音乐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如夏承焘云:“(姜)白石《徵招序》云:‘徵招、角招者,政和间大晟府尝制数十曲。’今案晁次膺《闲斋琴趣》有《并蒂芙蓉》《寿星明》《黄河清》《舜韶新》诸首,即徵调曲”[18]55“新填徵调曲有《圣寿》《齐天乐》二首、《中腔》二首,《踏歌》二首,《侯新恩》《醉桃源》各一首”[18]75。仅以大晟府时期的供奉词臣晁次膺集中所见的新调新词为例,即可知大晟府创调之丰,作词之富。第三阶段,南渡以后裁拆教坊,甚至全面禁乐,宫廷用乐也只是向地方临时借用,如《都城纪胜》云:“绍兴三十一年,省废教坊之后,每遇大宴,则拨差临安府衙前乐等人充应,属修内司教乐所掌管。”[19]9
唐宋宫廷在完善音乐机构(包括俗乐机构)基础上,大量创制曲调,既丰富了词乐,也为倚声作词奠定了基础。唐宋宫廷创制曲调的形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文人创制并进献宫廷,如《唐语林》载:“于司空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20]305“韦皋镇西川,进《奉圣乐》曲,兼乐工舞人曲谱到京。于留邸按阅,教坊人潜窥,得先进之。”[20]313《碧鸡漫志》引《明皇杂录》云:“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弟兄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制《渭州曲》,特承顾遇。”[21]78秦巘《词系》引《乾淳起居注》云:“宋淳熙三年教坊保义郎都管王喜等制进会庆万年《薄媚曲破》”[22]1684此调今仅见于《乐府雅词》,原注:“大曲道宫”,并称九重传出,可见此曲在当时颇有影响。第二种是专门的制乐机构,比如大晟府创制。《能改斋漫录》载:“政和中,一中贵人使越州回,得词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撰腔,因词中语,赐名‘鱼游春水’”[23]471。《词源》载:“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24]9第三种是帝王亲自创制。唐宋历代君王基本都知音识律,是制曲的高手,各类史料记述尤多。唐代以玄宗为最,如《旧唐书》云:“玄宗又制新曲四十馀,又新制乐谱”[3]1052,《羯鼓录》云:“诸曲调如太簇曲、色俱腾、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制。”[25]3玄宗以外的其他帝王亦不遑多让,比如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溆为入内大德,上采其声制曲,曰文溆子。”[21]47宣宗:“喜吹芦管,自制此曲(指《倾杯乐》)”[11]41“宣宗妙于音律,每赐宴前,必制新曲,俾宫婢习之。教坊曲工遂写其曲,奏于外,往往传于人间”[20]656;五代帝王亦复如此,如“王衍泛舟巡阆中,舟子皆衣锦秀,自制水调银汉曲。”[21]83宋代帝王表面上看来崇雅而弃俗,实际上当他们身处承平时期,内心对俗曲新声的喜好仍是掩抑不住的,比如《宋史·乐志》:“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因旧曲造新声者五十八”[17]3351,“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17]3356南宋君王也是如此,如《词苑萃编》载:“高宗洞达音律,自制曲赐名舞杨花。停觞命小臣赋词,令内人歌之。”[8]2037
值得注意的是,宫廷所创制曲调与词调的关系极为紧密。夏承焘认为:“选调制调的几种方法,一是截取唐代法曲、大曲的一部分而成”,“一种是取各种宫调之律合成一首宫调相犯的曲子”“一种是改变旧谱的声韵来制新腔”,“一种是用琴曲作词调”。[18]10前述所引的宫廷创制曲调之方法确均包含于夏承焘所说的几种类型中。需要注意的是,宫廷创制的这些曲调后来基本都转换为词调,比如《倾杯乐》《雨霖铃》等,说明唐宋宫廷制曲成为唐宋词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即为唐宋词的创作提供了词调来源和依据。
唐宋宫廷对词乐的接受与传播对乐坛、词坛的影响是深远的,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唐宋历朝宫廷对新声、俗乐、词乐的接纳态度以及大量创制新曲,丰富了乐坛,对唐宋音乐史是极大的贡献。前述相关材料说明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对新声、俗乐、词乐是持欢迎态度的,这样的史料非常多,如《唐语林》卷四载:玄宗临轩纵击而制《春光好》,且“神气自得”“又尝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彻,纤埃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坠下,其神妙如此”[20]326,无论是玄宗的“神气自得”,还是《唐语林》作者所叹的“神妙如此”,都展现了时人对创制曲调的投入与热忱。又《乐府杂录》载:“明皇初纳太真妃,喜谓后宫曰:‘予得杨家女,如得至宝也。’遂制曲,名得宝子。”[11]40除了创制新曲之外,有的帝王也对现有曲调进行变易改革,也是对曲调的一种完善和改进,比如《续湘山野录》载:“太宗尝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太宗尝谓《不博金》《不换玉》二调之名颇俗,御改《不博金》为《楚泽涵秋》,《不换玉》为《塞门积雪》。”[26]67简言之,宫廷里无论是新制曲调,还是变易旧曲,对当时的乐坛都是一种丰富,今存的这些曲调为我们研究和还原当时的音乐生态保存了珍贵的材料。
第二,以宫廷为中心的作词实践促成唐宋词坛的繁荣。元好问曾云:“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27]1383唐宋君臣极力作词的记载很多,如《吹剑三录》载:“明皇尤所爱好者,如羯鼓曲者,夷乐也,故以戎羯名之……喧播朝野,熏染成俗,文人才士,乃依乐工拍弹之声,被以长短句,而淫词丽曲,布满天下,”[28]46只是多数词作没有保留下来。《碧鸡漫志》载:宣宗“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危髻金冠,缨络被体,号菩萨蛮队,遂制此曲。当时倡优李可及作菩萨蛮队舞,文士亦往往声其词”[21]90,这是宫廷乐工和文人合作完成曲、词的典型例子。五代时期的宫廷对词曲投入的热情更盛,如张惠言《词选·序》云:“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变新凋,词之杂流由是作矣。”[29]1宋代君臣更是如此,如《续湘山野录》载:“太宗尝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调,撰一辞。苏翰林易简探得《越江吟》。”[26]68可知此次创作至少应该有十首词,遗憾只有苏易简的作品记录下来了,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集体创作应该是唐宋宫廷里分调同作的最早记录,开启宋代词作应制、群体唱和和词社的先河。至徽宗朝这种风气最为炽烈,大晟府文人按月律制曲、作词以应制成为他们的职业,相关记载散见于各类典籍中,如《古今词话》云:“万俟雅言自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与晁次膺按月律进词,其清明应制一首尤佳。”[8]1198徽宗朝流风余韵所及,下至南宋各代君王,比如高宗“雅好文辞,奖掖才士,如康与之、张掖、吴琚之伦,皆以词受知遇。又尝自制《舞杨花》及《渔歌子》,风教所传,词人蔚起。”[30]61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唐宋宫廷作词之概貌,由于过去囿于传统观念和疏于梳理,忽略了宫廷词人群及其大量词作的存在;事实上,由于宫廷词人群体自身的文学素养普遍较高,又诱于宫廷的奖掖,所以,他们的作品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丰富和繁荣了唐宋词坛。
第三,词作经历宫廷创作环节,词体地位才真正得到肯定,词作的文体属性也才进一步确立,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按照传统说法,词起源民间而盛于文人之手,但词在民间阶段并没有确立它独立的文体属性,仅仅被视为歌曲、小调而已;即使传至文人之手,比如苏轼等人之前的相当长时间范围内仍视为末技小道。比如五代时期君臣赓和,作品很多,但很多人仍并不敢或者不愿意承认有作词,如《旧五代史·和凝传》载:“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31]1673作为“曲子相公”的和凝对自己的文字颇为得意,却悔于作词,这从与他差不多同时的孙光宪的记载可知:“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12]135无论是和凝本人“收拾焚毁不暇”的行为,还是孙光宪“士君子得不戒之”的评论都可以看出,当时士人并不认同词的地位。然而我们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宫廷对词作的态度却不同,从词作开始兴盛的盛唐时期起即高度肯定,如《明皇杂录》载:“禄山犯顺,议欲迁幸。帝置酒楼上,命作乐,有进《水调歌》者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上问谁为此曲。曰:‘李峤。’上曰:‘真才子。’”[32]56很显然,如果玄宗也只是把所进的《水调歌》当成简单的歌曲的话,只会一听了之,但明皇特意询问作者,并赞其为“真才子”,所属意的就不只是这首歌词的音乐性,而是特别属意到它的文学性。同样,到了晚唐宪宗时期,据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载:“德裕顷在内庭,伏睹宪宗皇帝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33]宪宗赏爱张志和的《渔父词》“叹不能致”,激赏的仍是该词的文学性,如果只是侧重音乐性的,宪宗在宫中完全可以听宫女演唱,已可致也。至宋代宫廷亦复如此,如沈括集中今存《开元乐》四首,据今人考证:“为春日献神宗作”[22]314,另据《侯鲭录》载:“沈存中括元丰中入翰林为学士,有《开元乐》词四首,裕陵赏爱之。”[34]170至徽宗朝对词及词臣、词才之推重达到至高程度,《挥麈三录》载:“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驻跸郡治,外祖曾空青以江南转运使来摄府事应办,忽宣至行宫,上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命乔贵妃者出焉。上回顾语乔曰:‘汝在京师,每问曾三,此即是也,特令汝一识耳。’盖外祖少年日喜作长短句,多流入中禁,故尔。取七宝杯,令乔手擎满酌,并以杯赐之,外祖拜贶而出。”[35]240靖康南奔,兵荒马乱之际,徽宗仍不忘特意召见“喜作长短句”的曾空青,“问劳勤渥”,并特别向自己的爱妃引见,足见徽宗对曾作喜爱之深。
在严肃恭敬的宫廷环境里,宴饮以外的文字应酬场合,基本采用诗赋等传统位尊的文体,但我们注意到,随着词作的兴起,宫廷里很多庄重场合也大量用词作来表达和表现,比如圣节,过去一般是献赋,但至少到宋代宫廷却大量用词,比如为徽宗生日天宁节而作,有葛胜仲的《醉蓬莱·天宁节作》、王安中《徵招调中腔·天宁节》、贺铸《天宁乐》,说明在祝贺圣节方面,词作已经跻身于诗赋等传统文体之列。又如悼亡,传统意义上除了诗外,则有铭、诔,以词悼亡始于苏轼《江城子》,继而有贺铸《半死桐》。宫廷词作则有徽宗的《醉落魄·预赏景龙门追悼明节皇后》,以帝王之尊,用词作悼亡,至少说明,在徽宗眼里,词作绝非艳科末技。所以,与民间、普通文人相比,宫廷在认可和确立词作的文体属性方面更具积极性。
简言之,从用乐唱词,建立制乐结构、创制曲调,到倚声作词,都说明唐宋宫廷是词曲孕育、词作诞生的重要场所;从具体的制曲作词实践说明唐宋宫廷对词乐的接受传播、促进词坛的繁盛是不容忽略的事实。所以,无论从音乐还是文学的角度论,词乐在宫廷中的传播接受、词作在宫廷中的创制情况都是值得深度挖掘的重要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