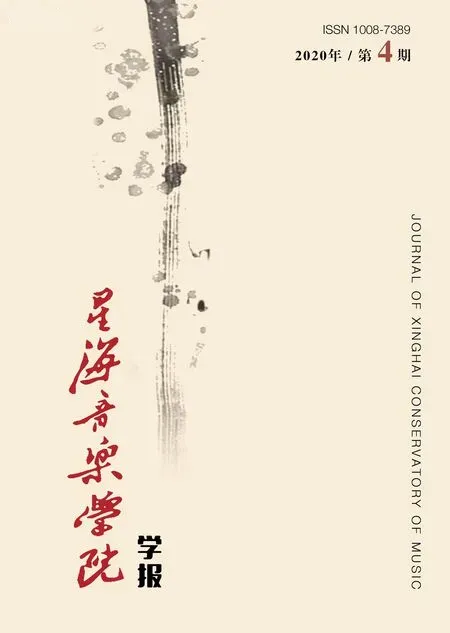民族音乐学的定义
褚 历
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国内外学界在相关著作、论文中已有大量论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关于民族音乐学的性质,除一般观点的学科外,还有研究领域或学科群(1)“ UNITARY FIELD OR CLUSTER OF DISCIPLINES? ” Philip V. Bohlman, “Ethnomusicology, III, ”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econd Edition, Stanley Sadie, ed., Oxford, New York, et 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vol. 8: 385-386.、思维(2)“音乐人类学……是一种对人类任何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洛秦:《是我们作用着音乐还是音乐作用着我们》,《民族艺术》1999年第2期,第20页;“民族音乐学也就是音乐人类学。……确切地说,民族音乐学是一种观念、一种思维和一种思想。”洛秦:《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第37页。、方法论(3)“在民族音乐学的旗号下……与其说是独立自足的学科,不如说它更多带有方法论的性质。”蒲亨强:《民族音乐学在当代中国之命运》,《艺术百家》2010 年第6 期,第77页。等不同说法。但任何学科或即使是研究领域、方法论等其他事物,都不可能是漫无边际、无法表述的,都应有个大致清晰的范围界限和定义,客观存在的多样性(例如“复数的民族音乐学”之说(4)“ Ethnomusicology ... is now well placed to take on board the diverse national ethnomusicologies represented in this dictionary which include those who recently emerged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non-European scholars and musicians untrained in the Western system. ” Carole Pegg, “Ethnomusicology, I ”,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econd Edition, Stanley Sadie, ed., Oxford, New York, et 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vol. 8: 368. 该词条中多次使用“复数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ies)的概念。)不能掩盖必然具有的统一性。面对繁杂的已有定义,研究者不宜在领域、学科群之类另换概念或“复数”的片面性表述之下就此止步,而仍应理清是怎样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学科群等,这对相关学科的理论建设和事业发展都很重要。因此,民族音乐学的定义虽已是老生常谈,但仍富有研究意义和空间。
一、以往观点梳理
民族音乐学的正式诞生以荷兰学者孔斯特(Kunst)1950年创用“民族音乐学”的概念为标志,其前身是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的比较音乐学。二者的主要研究领域都是西方传统的“音乐学”范围以外的部分——非西方音乐及西方民间音乐,但在主要研究视角上发生了由结构形态到文化内涵的性质转变,故民族音乐学与比较音乐学之间既有继承性也有很强的独立性。民族音乐学定义的模糊多变正来自其历史发展中的这种继承与独立。
以往的民族音乐学众多定义中,本文认为较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五种类型:
(一)对西方艺术音乐和流行音乐之外的人类传统音乐的研究
1959年,孔斯特提出:
民族音乐学,或者像它最初被称为的比较音乐学,其研究对象是从所谓原始人到文明国家的人类所有文化层面的传统音乐和乐器。因此,我们的科学调查所有部落和民间音乐以及每一种非西方的艺术音乐。此外,它不仅研究音乐的涵化现象,即外来音乐元素的杂交影响,还研究音乐的社会学方面。西方艺术音乐和流行(娱乐)音乐不属于它的领域。(5)“ The study-object of ethnomusicology, or, as it originally was called: comparative musicology, is the traditional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of all cultural strata of mankind, from the so-called primitive peoples to the civilized nations. Our science, therefore, investigates all tribal and folk music and every kind of non-Western art music. Besides, it studies as well the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music, as the phenomena of musical acculturation, i.e. the hybridizing influence of alien musical elements. Western art-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 music do not belong to its field. ” Jaap Kunst, Ethnomusicolog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9: 1.
其研究范围的人类传统音乐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基本部分:部落音乐、民间音乐及非西方的艺术音乐。早在1941年,格伦·海顿(Glen Haydon)已指出比较音乐学的分支领域包括非欧洲音乐(进一步分为原始音乐、高度文明的音乐)和民间音乐。(6)“Although a sharp delimitation of the various fields of comparative musicology is difficult to make, the main subdivisions of the subject are fairly clear. Non-European musical systems and folk music constitute the chief subjects of study; the songs of birds and phylogenetic-ontogenetic parallels are subordinate topics. The extra-European systems are further distinguished in terms of cultural level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music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the African Negroes, and many native peoples throughout the world may be classed as primitive if it is representative of a low degree of culture. Other musical systems studied are those of highly civilized peoples such as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Indians. Folk music is usually studied in terms of national or racial distinctions and in terms of style-species or type. ” Glen Haydon, Introduction to Musicology: A Survey of the Fields, Systematic & Historical, of Musical Knowledge & Research,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41: 218-219.孔斯特的定义在研究范围上与比较音乐学相同,其本人的实际研究也注重音乐形态而接近比较音乐学;但他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新名称,且在定义中强调研究音乐的社会学内涵,客观上体现了新的民族学学科属性和研究方向。这种新旧兼容构成了孔斯特在民族音乐学发展历史上承前启后的独特地位。
(二)对西方艺术音乐之外的传统音乐加流行音乐的研究
1956年,威拉德·罗兹(Willard Rhodes)认为:
东方艺术音乐与世界民间音乐……对于我们从过去继承的这些研究领域,应加入两种看来有充分理由属于我们学科框架之内的类别:流行音乐和舞蹈。(7)“Oriental art music and the folk music of the world, …To these fields of study which we inherit from the past should be added two categories which seem rightfully to belo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our discipline, popular music and dance. ”Willard Rhodes,“On the Subject of Ethno-Musicology ”, Ethno-musicology Newsletter, 1956, 1(7): 3-4.
这种观点比上述第一种研究范围有所扩大。舞蹈由于与音乐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在部落等简单社会中)而常被民族音乐学归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学科名称似应叫做民族音乐与舞蹈学)。在音乐方面,这种观点虽然只增加了一项流行音乐,但在现当代社会中,流行音乐作为传统音乐和西方艺术音乐之外一个重要的、文化内涵丰富的音乐种类,目前在西方已成为民族音乐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但国内这方面的观念和实践还相当滞后,仅有少量具体研究和理论阐述。
(三)对人类所有音乐的研究,民族音乐学实际上就是音乐学
1955年,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就在个人交流中提出了这种观点:
如果民族音乐学这个术语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的话,作为其领域它将包括人类的全部音乐,没有时间或空间的限制。(8)“If the term ethnomusicology were to be interpreted in its broadest sense it would include as its domain the total music of man, without limitations of time or space. This viewpoint was advanced by Charles Seeger and is supported by the semantic implications.… (Seeger …; 1955). ” Willard Rhodes,“ Toward a Definition of Ethnomusic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956, 58(3): 460, 463.
1957年,胡德(Hood)引用“音乐学”的定义作为民族音乐学定义:
(民族)音乐学是一个知识领域,以将音乐艺术作为一种物理、心理、审美和文化现象进行调查研究作为它的目标。(9)“‘[Ethno] musicology is a field of knowledge, having as its objec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rt of music as a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esthetic,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Mantle Hood,“ Train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Newsletter, 1957, 1(11): 2.
就音乐研究的基本方面而言,其中所列包含了形态、文化研究,仅缺乏明确的历史维度,这与受当时注重共时研究的人类学的影响有关。
1959年,西格指出,民族音乐学研究全世界的音乐,并且应该使用“音乐学”的名称:
我们必须把全世界音乐作为我们的领域,包括所有的欧美音乐,不仅是民间、流行和部落音乐。这包括精致艺术——我们必须也从民族学者的角度审视以往的丰碑。
显然我们必须在其自身和在文化中研究音乐,而这就是“音乐学”。所有音乐都处在文化中,因此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像“民族音乐学”那样的术语呢?原因是历史学家已经劫持了适当的术语“音乐学”,但他们仅研究世界音乐中一个很窄的频段,而且只是其部分。(10)“we must make our domain world music, including all of Euro-American music, not only folk, popular and tribal music. This includes the fine art - we must look at the monuments too from the ethnologist's viewpoint. ”“Clearly we must study music both in itself and in culture and this is ‘musicology. ’ All music is in culture so why do we need a term like ‘ethnomusicology?’ The reason is that historians have highjacked the proper term, ‘musicology.’ Yet they study a very narrow band of world music and only part of that. ” Charles Seeger, Malloy Miller, J. H. Nketia, et al.“Whither Ethnomusicology? ”, Ethnomusicology, 1959, 3(2): 102, 101.
类似的观点在民族音乐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中并不少见。如1963年,弗兰克·哈里森(Frank Harrison)认为:“所有音乐学的功能实际上就是民族音乐学。”(11)“ it is the fuction of all musicology to be in fact ethnomusicology, ” Frank Ll. Harrison, “American Musicology and the European Tradition ”,in Frank Ll. Harrison, Mantle Hood, Claude V. Palisca, Musicolog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3: 80.
1987年,赖斯(Rice)参照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文化的解释》(1973)中的论述“符号系统……是由历史建构、社会维持和个人应用的”(12)“symbol systems … are historically constructed, socially maintained, and individually applied. ”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3: 363-364. Timothy Rice, “ 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 ”, Ethnomusicology, 1987, 31(3): 473.,将梅里亚姆(Merriam)的研究模式(观念、行为、声音)分别嵌入格尔茨模式的三个部分(历史建构、社会维持、个人应用),由此阐释音乐的“形成过程”。组合产生这一带有浓厚解释人类学色彩的民族音乐学模式后,赖斯说:
这一包含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生物学成分与关注的民族音乐学模式可能成为一种统一的、而非分裂的音乐学的模式。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因为它反映了一些民族音乐学家多年来想往的方向。民族音乐学家经常拥有一种传教士般的热情,认为他们对音乐独占了最好、最恰当和最宽广的视角,认为民族音乐学实际上就是音乐学。(13)“this model of an ethnomusicology that includes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psychobiological components and concerns could be a model for a unified, rather than a divided, musicology. This is a satisfying conclusion because it reflects the direction in which some ethnomusicologists have wanted to move for years. Ethnomusicologists often possess a sort of missionary zeal that they have a corner on the best and most proper and widest perspective on music and that ethnomusicology is in fact musicology. ”Timothy Rice, Ibid.: 482.
民族音乐学家的豪情在这样的自述中可见一斑。比较音乐学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在进入民族音乐学时期后已广受批评而逐渐减弱,但谦虚稍逊、独尊排他的心态仍萦绕于胸,并成为由民族音乐学正式诞生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由西方流播到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传统。
(四)对音乐的文化内涵的研究
1956年,麦卡莱斯特(McAllester)在民族音乐学学会组织会议的报告中总结道:
普遍的共识赞成这样的观点:“民族-音乐学”绝不仅限于所谓的“原始音乐”,其定义更多地决定于学者的取向而不是任何僵化的论述界限。(14)“ The general consensus favored the view that ‘ethno-musicology’ is by no means limited to so-called ‘primitive music,’ and is defined more by the orientation of the student than by any rigid boundaries of discourse. ” David P. McAllester, “ The Organizational Meeting in Boston ” in “ Notes and News ”, Ethno-musicology Newsletter, 1956, 1(6): 5.
1957年,科林斯基(Kolinski)指出:“事实上,对于民族音乐学与普通音乐学的区别,分析的地理区域的差异不如一般研究方法的差异。”并提及民族音乐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化接触或种族关系”。(15)“In fact, it is not so much the difference in the geographical areas under analysis as the difference in the general approach which distinguishes ethnomusicology from ordinary musicology. ” “ethnomusicological theories concerning cultural contacts or racial relationships.” Mieczyslaw Kolinski, “Ethnomusicology, Its Problems and Methods ”, Ethnomusicology Newsletter, 1957, 1(10): 2, 7.
前述孔斯特的定义也包含了文化内涵研究的内容。1972年,切斯(Chase)提出“文化音乐学”的名称:
“民族音乐学”一词在其广泛的地理,时间和文化范围的背景下似乎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范围更大的术语,它将包含同样的理念,即音乐学的社会文化取向。为此,我通过与“文化人类学”类比提出“文化音乐学”这个术语。(16)“ The term ‘ethnomusicology’ seems rather restrictive in the context of its wide geographical, temporal, and cultural scope.…What we need is a term of larger scope that will contain the same idea - namely, the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musicology. For this I propose the term ‘cultural musicology’ - by analogy with ‘cultural anthropology. ’” Gilbert Chase, “American Music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 Perspectives in Musicology, Barry S. Brook, Edward Downes, Sherman Van Solkema, ed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5(1972): 220.
切斯认为,“文化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包含同样的理念“音乐学的社会文化取向”,但其涵盖范围更大而不像“民族音乐学”那样具有局限性。随后,切斯与前述胡德的做法类似,引用文化人类学的任务,加入限定词“音乐的”,即作为文化音乐学的任务,并认为这就应该是音乐学的任务。(17)“ Paraphrasing the previously quoted description of the task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vide supra, p. 208), we might describe the task of cultural musicology as being ‘to stud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musical behavior among human groups, to depict the character of the various musical cultures of the world and the processes of stability, change, and development that are characteristic to them.’” “In an ideal situation, this would simply be a description of the task of musicology tout court without any qualifier. ”Ibid.: 220. 带下划线的部分是比原文所引文化人类学的任务(第208页)多出之处,下划线为笔者所加。即用于代替“民族音乐学”称谓的“文化音乐学”实际上就是音乐学(与上述第三种类型的观点相同)。
本文认为,“文化音乐学”名称的提出虽然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巨大影响,但这一概念本身体现了不限于文化人类学的较为宽广的音乐文化内涵研究的含义。第四类型中的其他文献也常有类似特点。
2001年,《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的民族音乐学定义也属这种类型:“在地方性和全球性背景下对音乐和舞蹈的社会及文化方面的研究。”(18)“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music and dance in local and global contexts. ” Carole Pegg, et al., “ Ethnomusicology ”,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econd Edition, Stanley Sadie, ed., Oxford, New York, et 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vol. 8: 367. 该辞典的此定义至今未变,见格罗夫音乐在线(《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最新网络版):Grove Music Online: https://www.oxfordmusiconline.com/grovemusic, Ethnomusicology该条目,2020年3月4日查阅。
(五)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音乐的研究
早在1885年阿德勒(Adler)的经典论文《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标》中,对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的观念中就已包含了“民族志”的研究目的,但其实际做法属于形态研究:
比较音乐学……把自己的任务看作是出于民族志目的的考虑而比较音调产品,特别是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民歌,根据它们特征中的多样性[差异]对其进行分组和排序。(19)“comparative musicology … takes as its task the comparing of tonal products, in particular the folk songs of various peoples,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with an ethnographic purpose in mind, grouping and ordering these according to the variety of [differences] in their characteristics. ” Erica Mugglestone, “ Guido Adler's ‘ The Scope, Method, and Aim of Musicology’ (1885):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an Historico-Analytical Commentary ”,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1981, vol. 13: 13. 方括号中的文字是英文译者为使文意清晰而加入的,见该文第1页。
1956年,威拉德·罗兹指出了“民族音乐学”概念具有的“民族学”含义:“新名称中民族学与音乐学的联接强调了一个长期被认识但经常被忽视的科学方面。”(20)“ The linking of ethnology to musicology in the new name emphasizes a phase of the science that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but often neglected. ” Willard Rhodes, “ Toward a Definition of Ethnomusicology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956, 58(3): 459.
罗兹认为,有三种依时间顺序出现的研究类型,大致与比较音乐学的进化发展并行,即音乐学(指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如埃利斯(Ellis)、斯通普夫(Stumpf)(1901)、亚伯拉罕(Abraham)和霍恩波斯特尔(Hornbostel)(1909)、萨克斯(Sachs)(1914);民族志,如伯林(Burlin)(1907)、邓斯莫尔(Densmore)(1918)、罗伯茨(Roberts)(1926);民族音乐学(即先做音乐学研究然后做文化研究),如赫佐格(Herzog)(1935)、罗兹(1952)、麦卡莱斯特(1954)、梅里亚姆前文出现过(1955)、内特尔(Nettl)(1955)。(21)Ibid.: 459-460.这种归纳明确指出了比较音乐学含有的民族学成分。对于比较音乐学之后的民族音乐学,他认为:
音乐学家发展出了音乐材料分析的方法和技巧,人类学家为文化现象的解释提供了理论,民族音乐学家的任务是利用这两门学科的资源,以便为人类文化的这一重要部分赋予意义。(22)“ The musicologists have developed methods and techniques for analysis of musical material. The anthropologists have provided theori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phenomena. It is the task of the ethnomusicologist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resources of both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give meaning to this significant segment of man’s culture. ” Ibid.: 462.
西方等相关文论中,“音乐学”概念有两种含义:理论上应有的含义是指包括“音乐自身和文化”在内的音乐研究的整体;但由于音乐及其研究的特性,以及长期使用“音乐学”名称的西方艺术音乐(历史)学重视音乐形态,所以音乐学概念也常指音乐形态学研究。以往文献中音乐学与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并列时,常是倾向于指音乐形态学。本文对音乐研究的整体在必要时使用“音乐学整体”的概念加以明确。
在罗兹的主张中,结合音乐(形态)学与人类学,但更重视人类学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
1960年,梅里亚姆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著名定义:“文化中的音乐研究”。(23)“a proposal of a definition of ethnomusicology, … as ‘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 ’” Alan P. Merriam, “ Ethnomusicology: Discuss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 Ethnomusicology, 1960, 4(3): 109.此说很简洁,但含义存在不明确之处。作者对此定义论述道:
我相信我们的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文化人类学是一致的。我们的兴趣,我相信,应该指向对音乐的更宽广的理解,而不是仅作为一种结构形式,不是依据特定的地域或人群,也不是作为一种孤立的,而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人类现象,这种现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在如此定义这个领域的过程中,我已试图尽我所能表明,我绝不排除纯粹历史的、纯粹结构的、纯粹审美的同民族学相平等的考虑。关键是对历史、结构和审美的清晰理解与对这些方面运作于其中的文化背景的理解密切相关。(24)“I believe our objectives are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coincident with thos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Our interests, I believe,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 the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music, not simply as a structural form, not in terms of particular areas or peoples, and not as an isolate, but as a creative human phenomenon which functions as part of culture. In thus defining the field I have tried to make it as clear as I can that I by no means exclude the purely historic, the purely structural, the purely aesthetic from equal consideration with the ethnological. The point is that the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 structural and aesthetic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in which these aspects operate. ”Ibid.: 112-113.
以上论述的基本含义有三点:一、民族音乐学的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文化人类学一致——这反映了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密切关系;二、对纯粹历史、结构、审美的研究给予同民族学相平等的考虑——这样的民族音乐学实际上已相当于音乐学整体;三、对历史、结构和审美的清晰理解与对这些方面的文化背景的理解密切相关——这强调了文化背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历史、结构、审美等其他学科的重要意义。
这一正反合的论述过程体现了梅氏在民族音乐学的认识上音乐学整体与音乐文化人类学的二元矛盾。民族音乐学包括音乐研究的历史、结构、审美和文化背景等各个方面(等于音乐学整体)的观点是前述西格同类观点的延续和细化,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关系密切的观点则是梅氏在前人基础上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进一步明确。结合梅氏该文所述的具体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等于音乐学整体的观点是理论上或理想中的,梅氏实际主张和践行的是文化人类学的做法。
这种理论上音乐学整体而实际上音乐人类学的对立载体成为民族音乐学影响至今的一种基本观念。如前述切斯一方面认为用于代替“民族音乐学”称谓的“文化音乐学”具有音乐学的社会文化取向,另一方面又觉得它实际上就是音乐学。
又如,赖斯虽然希望融合民族音乐学与西方传统的(历史)音乐学(实为西方艺术音乐[历史]学),“创建一门统一的音乐学”,但同时又认为:
这个模式不认可对声音、认知或行为的形式描述,尽管它们可能很有趣,它要求解释我们对基本形成过程的知识的描述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提出的模式中,对音乐的分析,即对“音乐声音本身”的研究,被降到模式的较低层次,而人们在创造、体验和使用音乐时的行动成为探究的目标。(25)Timothy Rice, “ 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 ”, Ethnomusicology, 1987, 31(3): 483, 479.
可见,受其理论来源(格尔茨)的强烈影响,赖斯的格尔茨—梅里亚姆套接模式具有明显的人类学(特别是阐释人类学)倾向,理论上音乐学整体而实际上音乐人类学的矛盾二元体与梅里亚姆一脉相承。
1961年,西格对“民族音乐学”概念的“民族学”含义做了细致的说明:
当前“民族音乐学”一词有两种含义。一种将前缀“民族”等同于形容词“民族的”,意思是“野蛮的,非基督教的,异国的”;另一种的前缀“民族”与民族学中相同。前者意味着现在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仅限于学者自己音乐以外的音乐;后者则仅限于音乐的文化功能。(26)“ Two meanings of the term ‘ethnomusicology’ are current. One equates the prefix ‘ethno-’ with the adjective ‘ethnic,’ meaning ‘barbarous, non-Christian, exotic’; the other, with the prefix ‘ethno-’, as in ethnology. The former implies that the study now known as ‘ethnomusicology’ is limited to musics other than its students’ own; the latter, that it is limited to the cultural functions of music. ” Charles Seeger, “ Semantic, 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Bearing upon Research in Ethnomusicology ”, Ethnomusicology, 1961, 5(2): 77.
1962年,恩克蒂亚(Nketia)提出“音乐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方面的研究”的宏大概括。从其全文看来,其观点是与梅里亚姆等人相同的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即兼顾音乐和文化、结合音乐学与人类学的研究:
音乐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方面的研究正变得日益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的焦点。
民族音乐学……应该提供比通过音乐学(它主要关注声音复合体或一种类型的音乐)或人类学(关注文化成分)能够获得的更宽广的对音乐的理解。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既不忽视音乐也不忽视文化,既不忽视形式结构也不忽视功能,而是将两者统一在一种综合的意义表述中。(27)“ The study of music as a universal aspect of human behaviour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the focus of Ethnomusicology. ” “ Ethnomusicology …. ought to provide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music than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Musicology (where it is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the sound complex or with one type of music) or Anthropology (concerned with the cultural component). 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 ignores neither music nor culture, neither formal structure nor function but unites both in a comprehensive statement of meaning. ” J. H. Kwabena Nketia, “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African Music ”, Ethnomusicology, 1962, 6(1): 1.
1964年,梅里亚姆沿着其原有思想继续前进,在同名专著中提出了“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和“观念(概念)、行为、声音”的研究模式。(28)Alan P. Merriam,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中文版:[美]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穆谦译,陈铭道校,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他对该模式总结道:
如果我们以这个简单模式的广阔视角来看待音乐研究,我们的态度就不仅仅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文化和社会的或结构的、民间的或分析的,而是它们全部的结合。进而,它必然导致对问题的考虑,诸如象征主义、审美的存在或缺失、艺术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和通过运用音乐重建文化史的问题,以及文化变迁的问题。它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音乐研究的一个单一方面,而是使调研者能够甚至强迫他们去寻求对我们称之为音乐的人类现象的整体性理解。(29)Alan P. Merriam, Ibid.: 33-34.
其中,理论上希望综合文化、社会、结构各方面(音乐学整体)而实际强调文化内涵(音乐人类学)的基本思路与4年前如出一辙,但梅里亚姆对民族音乐学中音乐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有更加明确的说明:
民族音乐学本身蕴含着自身分化的种子,因为它总是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音乐学部分和民族学部分。也许它的主要问题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不强调任何一方,而对二者都予以重视。[Ibid.: 3. ]
这种平均结合音乐学与民族学的主张同样只是理论上的,梅氏实际看重和实施的仍然是人类学。
20世纪70年代末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大陆后,大陆学界很快就从80年代开始对民族音乐学的名称、性质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于民族音乐学的民族学(大致相当于人类学)性质,很多中国及华人学者都有明确的论述,较早的如:
1981年,俞人豪提出:
正象民族音乐学这个英文词汇(Ethnomusicology)是由民族学(Ethnology)和音乐学(Musicology)这两个词复合而成的那样,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内容也包含了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两个方面。(30)俞人豪:《民族音乐学介绍》,《音乐研究》1981年第4期,第96页。
1983年,赵如兰提出:
我们可以说“民族音乐学”中的“民族”是近乎“民族学”的定义。“民族学”是着重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之中的文化背景,从这文化背景的了解再进一步观察它的音乐特征,才是民族音乐学。(31)[美] 赵如兰:《漫谈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1983年第3期,第17页。
1984年,沈洽提出:
现代民族音乐学是一门介乎民族学与音乐学之间的边缘科学。这门学科有意识地选择民族学和音乐学的“边缘”这样一种特殊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一切音乐现象。(32)沈洽:《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当务之急——修纂民族音乐志之必要与价值》,《中国音乐》1984年第3期,第27页。
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还有对自身文化以外音乐的研究、对口头传承音乐的研究、对现存音乐的研究等,但因其对已有的民族音乐学实践(特别是当今的发展形势)缺乏概括性,故本文未将其列入民族音乐学定义的基本类型。例如,对自身文化以外音乐的研究是西方学者(尤其是早期)的特征,民族音乐学(主要是非西方学者)的研究早已超出非我音乐的范围;民族音乐学涉足很少的西方艺术音乐也有口头传承的成分,也是现在存活的音乐;而即使是在民族音乐学最为基本的传统音乐领域,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也已包含书面传承和历史传统的部分。自身文化以外的音乐、口头传承音乐、现存音乐实际都是意指西方艺术音乐以外的传统音乐或加流行音乐,只是视角和说法不同。
二、应有定义探讨
(一)五种定义评析
以上民族音乐学定义的五种基本类型,在民族音乐学产生伊始、思想活跃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致同时出现,但在思想观念上反映了由原先的比较音乐学向后来的民族音乐学逐渐发展的轨迹。
其定义的依据有三种:前三种定义主要依据音乐种类,即对某种或所有种类音乐的研究。研究某类事物中的特定(或部分)品种(如果不加限定则包括其所有方面)的学科可称为种类性学科,如红(楼梦)学、藏学、中国学。研究某类事物中的所有品种(包括其所有方面)的学科,可称为整体性学科。但从包含该类事物的更大范围看来,仍然是研究某类事物中的特定(或部分)品种的种类性学科。如音乐学、舞蹈学,既是音乐或舞蹈的整体性学科,同时也是艺术下属的种类性学科;第四种定义主要依据音乐构成元素(文化内涵)。研究某类事物整体中的特定(或部分)方面的学科可称为视角性或专题性学科,如物理学、社会学、哲学;第五种定义主要依据音乐构成元素以及研究理论和方法(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所有音乐的特定方面——文化内涵)。
五种定义的研究范围,从第一种到第三种逐步扩大,到达人类所有音乐所有方面的极限后,第四、五种又渐次缩小。
第一种定义在历史发展上体现出与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继承性;第二种定义在研究范围上具有过渡性(由第一种到第三种)及主体性(是民族音乐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第三种定义的研究目标是理想性的。民族音乐学对自己的主要研究内容——音乐的文化内涵——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而对音乐形态(使音乐之所以成其为音乐而不是其他)的意义则估值较低,由此产生了主要研究音乐文化内涵并常带有音乐形态分析的民族音乐学就是音乐学整体的观念。
如果民族音乐学等于音乐学,则对任何音乐的任何方面的任何方式的科学研究都可算作民族音乐学,显然民族音乐学没有达到这样的包容度,它在理论及实践上还是有特定内涵和所指的。
这种理想所体现的无限制的自我扩大有悖于科学研究中学科细分的基本规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发展将使民族音乐学消失在人类音乐的无边海洋和音乐学的巨大背影之中。(33)相关论述参见陈孝余:《民族音乐学的危机与后民族音乐学》,《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129—133页。
第四种定义的外延具有宽泛性。对音乐的文化内涵的研究即音乐文化学。该学科包含范围很广,概括性很强,其研究可以使用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语言学、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
第五种定义的特征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限定性。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音乐进行研究,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音乐的文化内涵。它与第四种定义的研究内容相同,但使用的理论与方法一宽一窄,也可以说这种类型是音乐文化学的下属种类。
民族音乐学定义中,前两种那样的种类性学科定义从学术理念的发展过程看来似乎早已成为历史(参见前文麦卡莱斯特的会议总结)。但由于西方艺术音乐形态复杂、乐谱等历史文献众多,而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形态常较简单但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文献缺乏,性质不同的两类音乐适于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因而民族音乐学至今向西方艺术音乐的进军成果不多,主要研究的仍然是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自1885年比较音乐学产生以来的欧洲艺术音乐与其他音乐(也是欧洲艺术音乐[历史]学与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对置的基本格局难以撼动。故在民族音乐学文论中,前两种或类似定义以“主要研究领域”的变化形式继续存在,形成定义及研究领域(第四、五种类型,即[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所有音乐的文化内涵)与“主要研究领域”(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或者口传、现存、异文化音乐等)二元并立而时显矛盾的组合。例如:
1969年,胡德提出:
民族音乐学是研究任何音乐的一种方法,不仅从它本身的角度,而且涉及其文化背景。目前,这个术语有两种广泛的应用:(1)研究欧洲艺术传统之外的所有音乐,包括欧洲和其他地方该传统早期形式的遗存;(2)研究在一个地点或地区发现的所有种类的音乐……将包括研究该区域所有类型的欧洲艺术音乐、族群飞地音乐、民间、流行和商业音乐、混合音乐等,也就是说,某一地区的人们在使用的所有音乐。(34)“Ethnomusicology i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ny music, not only in terms of itself but also in relation to its cultural context. Currently the term has two broad applications: (1) the study of all music outside the European art tradition, including survivals of earlier forms of that tradition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2) the study of all varieties of music found in one locale or region ... would comprise the study in that locality of all types of European art music, the music of ethnic enclaves, folk, popular and commercial music, musical hybrids, etc.; in other words, all music being used by the people of a given area. ” Mantle Hood, “Ethnomusicology ”,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Willi Apel, 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298.
1992年,迈尔斯(Myers)提出: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的分支,其中特别强调在其文化背景下对音乐的研究——音乐人类学。……一般而言,口头传统中的音乐和现存音乐体系是最吸引民族音乐学家的领域。通常他们研究其自身以外的文化,这使该领域区别于大多数历史音乐学。(35)Helen Myers, ed., Ethnomusic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3.
2001年,派格(Pegg)提出:
21世纪初,民族音乐学接纳了在地方性和全球性背景下对所有音乐的研究。主要关注现存音乐(包括音乐、歌曲、舞蹈和乐器),最近的研究也调查了音乐史。(36)Carole Pegg, “Ethnomusicology, I ”,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econd Edition, Stanley Sadie, ed., Oxford, New York, et 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vol. 8: 368.
2005年,内特尔提出:
我们不优待精英的曲目,我们特别关注社会经济下层、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的少数族裔的音乐。我们相信,我们最终必须研究世界上所有的音乐,来自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阶层、起源、历史时期。我们只是还没有抽出时间来顾及所有这一切。(37)“We do not privilege elite repertories, and we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musics of lower socio-economic classes, colonized peoples, oppressed minorities. We believe that we must in the end study all of the world’s music, from all peoples and nations, classes, sources, periods of history. We just haven’t yet got around to all of it. ” Bruno Nettl,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hirty-one Issues and Concepts, 2nd ed.,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5: 13.
有了第四、五种定义后,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第一、二种定义应该是统辖在第四、五种定义之下的,即并非针对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所有研究都是民族音乐学(否则会形成逻辑矛盾),确切地说,民族音乐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文化内涵。
总之,定义及研究领域与主要研究领域的明显分歧构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独特景观,理清这种二元组合的两个方面,才能对民族音乐学取得较为完整、清晰的认识。
在观念上对民族音乐学发展较有影响的是第四、五种的专题性学科定义。鉴于民族音乐学从1950年产生至今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巨大影响,包括理论(例如早先的文化背景、后来的主位客位和现在的身份认同)、研究方法(强调实地考察)及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等,第五种定义更具代表性。第四、五种定义分别体现了民族音乐学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包容性及主体性,综合这两种定义及该学科研究实践可以认为,民族音乐学是运用以人类学为主、包括音乐学在内的各种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所有音乐的文化内涵的学科。
民族音乐学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常包含实地考察、音乐资料的收集整理(包括记谱与音像摄录)以至促进该种音乐的传承发展等相关活动,但这些活动也能包含在音乐形态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实践之中,这些活动本身不能作为判断一项研究是否属于民族音乐学的依据(这些活动的具体做法则可体现出不同学科的差别);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也常包含音乐形态研究,历史研究也逐渐增多,但这些研究往往是为其主旨——文化内涵研究服务的,或者(尤其是这些研究较为独立、深入时)该研究并非纯粹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而属于多种学科的综合研究,即其中含有音乐形态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部分。
对文化内涵的研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西方艺术音乐研究中运用形态学,哲学—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揭示音乐的思想内涵、文化意义的探讨目前恐难被视为民族音乐学。对任何音乐(包括西方艺术音乐)的研究,如果文化内涵研究(并且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成分越突出,该研究的民族音乐学性质就越鲜明,反之则越淡薄。这体现了民族音乐学的人类学属性。
(二)从研究模式看民族音乐学的人类学属性
梅里亚姆1964年提出的“观念(概念)、行为、声音”模式,其对音乐的划分与人类学等学科运用的文化分类基本模式——物质文化、行为(社会)文化、观念文化——是很相似的,(38)Alan P. Merriam,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34-35. [美] 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穆谦译,陈铭道校,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第35—36页。可视为这种文化三分模式在音乐领域的反映。当时民族音乐学创新不久,离比较音乐学时代不远,梅氏虽提出了音乐人类学的新主张,但仍较多地继承了比较音乐学重视音乐形态的衣钵。
1987年的赖斯模式是将梅里亚姆模式的三维结构植入格尔茨模式的三维结构中,即“历史建构、社会维持、个人应用”的每个维度内都包含“观念、行为、声音”三种维度的分析。(39)Timothy Rice, “ 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 ”, Ethnomusicology, 1987, 31(3): 469-488. 中文版:[加] 蒂莫西·赖斯:《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汤亚汀编译,《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期,第120—126页。
梅里亚姆模式有“形式”维度,但缺乏“历史”因素;(40)伍国栋先生2014年10月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为“音乐学分析”课程举办的讲座,题目为“音乐学分析的四个维度——以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本体、行为、概念分析为例”。这种四维模式是对梅里亚姆模式的补充和发展。格尔茨模式突出了“历史”和“个人”的视角,但缺少明确的“形式”因素。赖斯将二者组合形成的格尔茨—梅里亚姆套接模式,内容虽全,而结构稍显繁琐。
2003年,赖斯又提出“音乐体验的三维空间”——时间、地点、隐喻。(41)Timothy Rice, “ Time, Place, and Metaphor in Musical Experience and Ethnography ”, Ethnomusicology, 2003, 47(2): 151-179. 中文版见蒂莫西·赖斯:《音乐体验以及音乐民族志中的时间、地点和隐喻》,张伯瑜译,载张伯瑜等编译:《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32页。其中“时间”相当于历史,“地点”相当于社会(包括各种不同范围和组织形式的社会环境空间),“隐喻”相当于思想内涵(主要指音乐的性质、功能、意义)。这个由繁转简的模式与梅里亚姆模式相比,主要区别是用“时间”取代了“声音”,这体现了格尔茨模式影响的延续。
把梅里亚姆模式、赖斯的格尔茨—梅里亚姆套接模式和三维体验模式这三个民族音乐学的常见模式对照来看,音乐形态从基本结构因素到内部(下属)结构因素再到消失不见(42)参见蒂莫西·赖斯:《音乐体验以及音乐民族志中的时间、地点和隐喻》(载伯瑜等编译:《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中的研究实例。,清晰地反映出人类学成分逐渐加重、去音乐化思维日益明显的发展线索。
这种远离音乐形态的文化研究也能揭示音乐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相关规律,对音乐研究而言也是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但它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倾向于人类学,在学科定位上离人类学更近,是一种音乐及音乐学的主体性显现较弱的研究。
(三)广义与狭义的民族音乐学
在民族音乐学产生初期的人类学转向开始不久,已有学者认识到民族音乐学包含音乐学与人类学两种性质的研究。如梅里亚姆所言:
民族音乐学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探究:人类学方向和音乐学方向。……探究民族音乐学的人类学家倾向于强调人类学方面,而音乐学家则是音乐学方面。然而,两组人都同意,终极目标是二者的融合,这被视为一种理想,且必然会经由现实加以修正。(43)Alan P. Merriam,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vii.
这种观点实际是将音乐学与人类学中相同对象(文化内涵)的研究视为一类。这种民族音乐学涵盖范围较广,可称为广义的民族音乐学,可定义为:运用以人类学为主、包括音乐学在内的各种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所有音乐的文化内涵,以解决音乐学或人类学等学科问题为研究目的的主要属于音乐学或人类学等的学科。
如美国的民族音乐学有人类学与音乐学两种基本倾向,人类学倾向的研究(音乐人类学)盛行,其民族音乐学概念即属广义。持此观点的人们认为,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虽有学科归属等方面的区别,但属细微差异,二者总体而言大致相同甚至可以互换。(44)实际运用如:“有一种音乐人类学,它处于音乐学家和人类学家双方的掌握之中。”“ There is an anthropology of music, and it is within the grasp of both musicologist and anthropologist. ” Alan P. Merriam,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viii. 结合该书书名及上一段引文;前文所引海伦·迈尔斯主编:《民族音乐学导论》;解释说明如:“ethnomusicology与其姐妹学科anthropology of music(音乐人类学)互相影响,在一些文章里,两种名称经常‘不分你我’地换用。”汤亚汀:《Ethnomusicology:释义和译名》,《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3期,第141页;“西方至今仍有‘anthropology of music’或‘musical anthropology’的提法,与‘ethnomusicology’共存。从名称上看它们似乎有所区别,但我们不能说这些名称指的就是不同的学科,而在学术研究中实际上也是难以对它们作出截然划分的。……我自己是喜欢把上述几种英文名称都译为‘音乐人类学’的,认为它们没有根本区别。”杨沐:《当代人类学与音乐研究二三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第25页。
随着研究的细化和深入,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分别主要归属于音乐学和人类学,分别探讨音乐学或人类学的问题,“研究目的的不同决定了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侧重面都有不同。”(45)杜亚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2009年第3期,第39、43页。
这种民族音乐学可称为狭义的民族音乐学,可定义为:运用以人类学为主,包括音乐学在内的各种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所有音乐的文化内涵,以解决音乐学问题为研究目的的主要属于音乐学的学科。前述民族音乐学的第四、五种定义,如果不细分主要归属于音乐学或人类学等社会人文学科,则包含二者,均为广义。
相应地,与广义民族音乐学大致相同的、主要归属兼含音乐学与人类学的音乐人类学是广义的,与狭义民族音乐学对置的、主要归属人类学而非音乐学的音乐人类学是狭义的。(46)广义如前文注释对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大致相同的观点举例,又如:“简而言之,音乐人类学是指主要运用人类学学科理论及方法去研究音乐的一种学科。”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页;狭义如:杜亚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2009年第3期。音乐社会学、音乐历史学等学科也可做此类细分。
狭义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区别明显地体现在研究中音乐属性和特征(文化内涵方面也有,但更多表现在音乐形态方面)的多寡。民族音乐学中对音乐形态的关注一般应达到一定的分量,以体现其音乐学本色;音乐人类学中音乐形态的成分往往较少甚至缺失。
对音乐的文化内涵的研究是音乐学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文化学(或称文化研究)的共同领域和交集地带。在此共同领域中,各学科除了研究目的、理论、方法和侧重的差异外,就研究基础而言,对音乐形态和人类学等文化研究都很了解是最为优越的,但学贯不同领域要求高,出现几率小;在术业有专攻、多只具其一的情况下,文化学者比音乐形态学者较为便捷;而文化学与音乐形态都不精通则更居其后。
狭义民族音乐学是介于音乐学下属的音乐形态学和人类学下属的音乐人类学之间的中间学科,是学术研究中音乐结构形态与文化内涵的连接。该学科的理论武器主要来自人类学,但在学术探索中要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音乐本身(形态学),这跟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结合更为紧密的音乐人类学相比似乎不占优势。(47)“北美的大多数学术型民族音乐学家与音乐学校和院系相关联;但许多知识领袖来自人类学。”“Most academic ethnomusicologists in North America associate themselves with music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but many of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come from anthropology. ” Bruno Nettl,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hirty-one Issues and Concepts, 2nd ed.,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5: 8.民族音乐学如何凸显音乐价值,在社会人文学界提升专业水准和学术地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外很多学者呼吁民族音乐学应加强音乐性,但民族音乐学的本质属性和主要目标是研究音乐的文化内涵而不是结构形态,如果研究重心偏向音乐形态而非文化内涵,则研究性质已更多属于音乐形态学了。
(四)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关系
在西方,民族音乐学想要取代传统的“音乐学”(实为西方艺术音乐[历史]学)并成为音乐学整体;在中国,民族音乐学不仅想取代音乐学(48)“正如2001年新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音乐学’条目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音乐学的整个功能将应该是音乐人类学的。”参见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下),《音乐艺术》2009年第2期,第107页。“我们理想中的中国‘音乐学’对‘中国文化中音乐’的研究,将是一个一体多元的汇集和融合——一个一统了的‘音乐学’。”参见曹本冶:《一统音乐学:中国视野中的“民族音乐学”》,曹本冶主编:《大音》(第二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12月,第40页。,而且也力求整合原有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或理论、学)。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关系成为中国该领域影响重大、分歧鲜明的基本问题,而答案应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和性质密切相关。
已有学者论述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交叉关系,(49)徐天祥:《多元并存 交叉融合——重审“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科关系》,《音乐艺术》2014年第3期,第107、116页。本文仅稍做补充和归纳:顾名思义,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是种类性学科,包括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所有科学研究。虽然该领域以往的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注重音乐形态,但即使将来的研究仍然注重形态,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之间也是整体与部分的包含关系而非相等关系;民族音乐学是视角性、专题性学科,今天看来,它既不是音乐学整体(西格等人的观点),也不是世界传统音乐研究(孔斯特的定义),而是主要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所有音乐的文化内涵的学科。因此,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是交叉关系。
结 语
民族音乐学的众多定义体现了不同时空环境下不同学者的思想,该学科仍然处于发展之中。近年来,具体研究中运用的理论、方法丰富多样,总体而言则有范围扩大、学科泛化,朝着音乐文化研究(即音乐文化学)演变的趋势,如《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定义。但目前此趋势的发展程度尚不明显,民族音乐学领域中人类学的影响和音乐人类学的性质仍然是显著的。
对民族音乐学这一流传广、影响大的音乐现象,如果进行学术史的研究,考察其与文化背景的关系,运用主位、客位等多视角观察方法,聚焦于主体和人,探究其观念与行为,深描其构建的身份认同及文化景观,则对其性质、发展线索与影响等基本问题应能取得较为客观、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