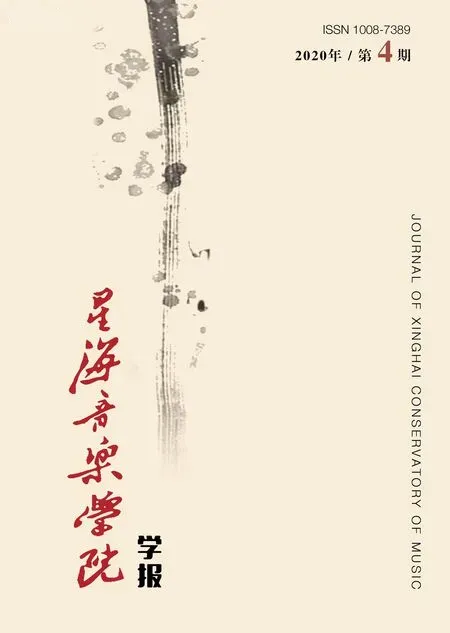“绝对音乐”词义辨析
王学佳
1846年,瓦格纳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而作的“乐曲解说”首次提及“绝对音乐”概念:“这里的音乐已几近冲破绝对音乐的界限,以刚健的雄辩之声遏制住其他乐器的喧嚣骚动,强势走向果断的决定,最终形成一个歌曲般的主题。”(1)瓦格纳:《瓦格纳文集》第二卷,第61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页。此处“绝对音乐”主要指18—19世纪器乐音乐类型。“绝对音乐”(absolute music),又称纯音乐(pure music)、纯器乐、独立音乐(2)刘经树:《独立音乐观念》,《音乐探索》2012年第2期。。“绝对音乐”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器乐形态;二是创作原则;三是美学观念。
一、“绝对音乐”之器乐形态
作为器乐音乐形态的“绝对音乐”,是一个历史中生成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指向一种音乐纯粹性的理想。首先,它不是其他艺术的附属:不从属于戏剧和舞蹈(歌剧、舞剧),不从属于歌词(歌曲),不从属于描写性意义(标题音乐)。其次,它不是达成音乐之外目的的手段:不是为了礼拜功能的宗教音乐,不是为了社交目的的宫廷音乐,不是为了舞蹈、叙事、表达情爱的世俗音乐。
人们以独立、严肃的态度对待器乐音乐形态的“绝对音乐”,是西方音乐史的晚近事件。“西方古代的‘音乐’概念是声乐的。古代的器乐作品是旋律化的。”(3)蒋一民:《音乐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音乐由和谐、节律、逻各斯构成。“和谐”指乐音之间规则的、具有理性体系的关系;“节律”指音乐时间的体系,在古代包括舞蹈和有组织的运动;“逻各斯”指作为人类理性表达的语言。(4)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页。世界各地区民歌、民间舞蹈的音乐基本由这三个要素构成。
中世纪宗教音乐承载教堂礼拜功能,世俗音乐承载叙事、舞蹈、表达情爱的功能,宫廷音乐承载王公贵族的社交礼仪功能。宗教歌曲通常是拉丁文配词的复调作品,世俗歌曲通常是方言配词的单声部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要求摆脱基督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要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这种思潮在音乐领域的表现是模仿自然、模仿感情成为音乐创作的重要原则。作曲家若斯坎的音乐创作方法“绘词法”——音乐对一个词或一个句子进行音画式的表现,在文艺复兴后期和巴洛克时期被大量采用。
巴洛克时期,作曲家蒙特威尔第旨在使用音乐构造一个“激情的相似物”,史称“激动风格”,这是“音乐模仿感情和生活”创作观念的发展。而善于理论思维的德意志民族在分析和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以音乐修辞学为具体形式的情感呈示论。该观念宣称,通过对修辞学原理的借鉴与运用,音乐表达情感的准确性与广泛性不逊于真正的语言。音乐修辞学的创作方法在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创作中普遍应用。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音乐修辞学隐含的音乐-修辞功能及其公式化作曲原则中,催生出独立的器乐音乐创作思维。
尽管巴洛克音乐在形式上有公式化倾向,但它在这方面的大量公式化探索却为突破和否定这种公式化奠定了技术基础,即为器乐的写作技法做了重要铺垫,例如模进、模仿、卡农、赋格等原先都是音乐修辞学中的写作手段,而“对比论证”则成了后来音乐中对比原则的基础。(5)蒋一民:《音乐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22页。
实际上,巴洛克时期器乐的复调作品被看作几个歌唱旋律声部的组合,在观念上仍然是“线加线”式的复调声乐的派生。“那时的器乐演奏在音乐生活中不占主导地位,毋宁被当作消遣甚至杂技性质的游艺活动,表现重大体裁并被认真对待的仍然是合唱体裁、圣剧、咏叹调等声乐形态。”(6)蒋一民:《音乐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页。器乐的观念是声乐的,这是巴洛克时期音乐历史与音乐修辞学的作曲原则、情感美学之间的鲜活互动。
二、“绝对音乐”之创作原则
除却从属于其他艺术形式和他律表现目的的情况,“绝对音乐”的意义首先指向音乐自身的形式法则。
18—19世纪,随着交响曲、弦乐四重奏的确立、成熟以及复杂的奏鸣曲式和奏鸣曲套曲模式的成熟和确定,专注于音乐形式的逻辑发展成为新兴的创作原则。古典时期“维也纳三杰”的器乐音乐创作是这种创作观念的杰出代表。此时器乐音乐逐渐占据艺术音乐主流。总体看,古典时期音乐追求旋律优美,结构方整匀称,调性明晰,和声简洁,从短小动机孕育出丰富乐思的技巧得以蓬勃发展,追求乐章中主题之间的对比变化,常用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等体裁。简言之,古典时期器乐音乐致力于追求形式逻辑结构的发展。音乐依据自身法则被创作和理解,这就是绝对音乐的创作原则。
浪漫时期,交响曲、弦乐四重奏、无标题钢琴奏鸣曲等器乐形态的绝对音乐创作降温。处于贝多芬交响曲成就的阴影下,创作之路何去何从成为有抱负的浪漫派作曲家的共同使命。从音乐形态的角度,多数浪漫派作曲家冲破音乐自身“非概念性、非具象性”的形式禁锢,不同程度地倾心于标题音乐,标题交响曲、交响诗、标题性序曲等体裁应时而生。然而,从创作原则的角度,作曲家依然专注于音乐形式逻辑的发展。也就是说,大部分浪漫派作曲家扬弃“绝对音乐”的器乐形态,但继承了“绝对音乐”的创作原则。柏辽兹的标题幻想曲、李斯特的交响诗、瓦格纳的乐剧实践,是这种观念的艺术体现。
以瓦格纳为例。1846年,瓦格纳以否定性的态度首创“绝对音乐”术语。他认为,器乐形态的绝对音乐是音乐历史发展的中间阶段,不能承载他的艺术理想:音乐反映客观世界。只有加之歌词、场面的促发,正如他后来创立的乐剧,才是未来艺术品。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声乐和器乐的恢宏融合预示了这一方向。
从音乐形态的层面,瓦格纳认为器乐音乐是音乐历史发展的反题,需要合题到综合艺术;从创作原则的层面,瓦格纳肯定维也纳三杰交响曲的创作成就,继承以音乐形式逻辑发展为主导原则的德奥创作传统:运用动机、主题及其模进、展开技术,让音乐形式本身表达人类复杂浩瀚的内心情感。正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名乐评,瓦格纳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三幕“爱之死”实际上是交响曲,除音乐之外的其他要素都是“把戏”或掩饰。
向这些真正的音乐家们,我提出如下问题:他们能否想象一个人不借助语词和舞台布景,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第三幕纯粹作为一个巨大的交响曲乐章来感知和理解,而不会因灵魂之翼骤然无可遏制地全部伸展震颤而气断身亡?(7)尼采:《三卷文集》第一卷,第117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3页。
简言之,从音乐形态的维度,瓦格纳摒弃“绝对音乐”之器乐音乐形态,创立综合艺术“乐剧”;从创作原则的维度,秉承“绝对音乐”之形式逻辑发展的创作思路,俨然贝多芬的正统继承人。二者的混淆令早期瓦格纳的“绝对音乐”态度暧昧不清,混淆终结于他的叔本华哲学接受之后。这或许是以下事实的理论佐证:1857年写作《论弗朗兹·李斯特的交响诗》之后,瓦格纳再未提及“绝对音乐”这个概念。
需要说明的是,以交响曲为代表的“绝对音乐”形态及创作原则主要兴盛于古典、浪漫时期的德奥民族。而此时的意大利走出截然不同的道路。从音乐形态的层面,前古典主义时期,意大利喜歌剧兴起。格鲁克改革正歌剧。浪漫时期意大利音乐史几乎等同于意大利歌剧史:罗西尼、贝里尼、唐尼采蒂、威尔第、普契尼的歌剧成就贯穿19世纪上、中、下叶。从创作原则的层面,意大利歌剧创作更多出自音乐形式自律之外的创作动机,而非遵循音乐结构逻辑发展的“绝对音乐”创作原则。比如格鲁克要求“音乐服从诗歌”,罗西尼的歌剧被瓦格纳嘲讽为“绝对旋律”,普契尼的歌剧更注重丰富醉人的旋律、对女性心理细腻精准的刻画、充满戏剧性的剧情、轰动的剧场效应、异国题材和情调。
综上,器乐形态和创作原则层面的“绝对音乐”盛行于古典、浪漫时期的德奥,是音乐史一时、一地作曲家的艺术追求。但是,绝对音乐创作原则对古典浪漫时期之后的德奥民族乃至其他民族的许多作曲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从音乐创作的层面,作曲家们开始专注于音乐形式的逻辑结构,如动机及其发展(瓦格纳采用主导动机)、主题及其变形(李斯特运用主题变形)、主题重复(德彪西使用主题重复)等,致力于仅仅通过器乐音乐这种纯粹的音乐形式表达作曲家的内在精神。相应地,绝对音乐创作原则重塑了听众理解音乐的方式。专业人士和音乐爱好者的聆听与鉴赏需要建立在音乐形式的基础之上,自鸣“听其所是”,所谓“懂音乐”。不能依据音乐形式的聆听与鉴赏,逐渐被边缘化了。
器乐音乐获取独立身份,且仅遵循自身形式法则,它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追求西方基督教文明下声乐艺术所蕴含的严肃性了。
三、“绝对音乐”之美学观念
美学观念层面的“绝对音乐”兴起于19世纪德国浪漫派文人让·保尔(Jean Paul)、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E.T.A.霍夫曼(E.T.A. Hoffmann)的音乐文论,史称“器乐音乐形而上学”。浪漫派文人认为,以交响曲为代表的器乐音乐既是音乐纯粹性的代表,又能够表现无限复杂的人类内心。
(一)“器乐音乐形而上学”
1800年左右,交响曲被看作器乐音乐的典型。古斯塔夫·席林(Gustav Schilling)在《音乐百科辞书》中写道:“器乐音乐公认的至高形态是交响曲”。(8)古斯塔夫·席林 (Gustav Schilling) :《音乐百科辞书》第六卷,第547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页。E.T.A.霍夫曼认为,“交响曲在器乐音乐中的地位相当于歌剧在声乐音乐中的地位。交响曲有如一部‘音乐戏剧’”。(9)E.T.A.霍夫曼 (E.T.A. Hoffmann) :《音乐文集》,第24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浪漫派文人热烈赞颂以交响曲为代表的器乐类型。这种赞颂一方面指向音乐艺术的形态独立。交响曲以纯粹的器乐形态、宏大复杂的规模,成为音乐艺术的纯正代言。赫尔德直言:“这种音乐的缓慢的艺术进程表明,音乐长期以来多么艰难地使自己摆脱姊妹艺术,摆脱语词和形象,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10)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赫尔德文集》,第15卷,第345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6页。另一方面,器乐音乐不仅是音响的形式游戏,它能够,且只有它能够,准确地表达汹涌、复杂、无限的人类内心。
人的心中有着一种从未得到满足的巨大渴望:它没有称谓,不寻求物质实存。……但我们的琴弦和乐音却道出了这一无可名状的渴望——渴望着的精神愈加痛苦地流泪,在乐音之间的狂喜呻吟中发出呼喊:没错!你们诉说的一切,即是我语竭词穷之处。(11)让·保尔(Jean Paul):《作品集》(第一卷),第776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1—62页。
作为器乐音乐的“艺术是独立自由的,自行制定属于自己的法则,天马行空地发挥想象,虽毫无企图,却实现了最高的目的,完全遵从其隐秘的冲动,以撩拨诱弄的方式表现最深刻、最神奇的东西”(12)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著述与书信集》,第254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4页。。它“引领我们走出俗世人生,进入无限之境”(13)E.T.A.霍夫曼(E.T.A.Hoffmann):《音乐文集》,第34—35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6页。。
浪漫派文人的“器乐音乐形而上学”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其一,摒弃音乐形式及精神的“平庸乏味”(prosaic),推崇“诗意”(poetic)这一艺术实质。浪漫派文人摒弃器乐音乐空洞的形式游戏,蒂克将“诗意”范畴置于浪漫主义音乐美学的核心地位。“诗意”不是指音乐对诗歌的依赖,而是指一切艺术共有的一种实质,它最纯粹地显现于器乐音乐之中。对于蒂克、让·保尔及其追随者舒曼而言,“诗意”的对立面是“平庸乏味”。“蒂克称之‘诗意’的东西也是霍夫曼关于‘浪漫’的概念。‘纯粹的浪漫性’在‘真正的音乐性’中显现自身。”(14)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第66页。
其二,催生虔敬静观的音乐接受态度。与绝对音乐及其超越语言的无限表现性相对的,是凝神静观和宗教虔敬相融合的接受态度。瓦肯罗德宣称:“啊,面对一切俗世纷争,我闭上双眼,悄然回退于音乐的王国,正如回退于信仰的国度。”(15)瓦肯罗德 (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著述与书信集》,第250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7页。蒂克宣称:“音乐无疑是信仰的终极奥秘,是神秘之物,是彻底得到揭示和显现的宗教。”(16)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论宗教》,第92—93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6页。达尔豪斯认为,“浪漫派文人眼中的音乐表现了作为宗教实质的那种对于无限的情感,这一事实足以让审美观照与宗教虔敬彼此相融”。(17)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3页。
其三,落实于实现器乐音乐的本质:理念的感性显现。青年黑格尔派学者阿道夫·伯恩哈德·马克斯(Adolf Bernhard Marx)评论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是“这样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使音乐艺术第一次独立地——即无关诗人的语词或戏剧家的戏剧动作——冲破形式的游戏,冲破不确定的冲动和情感,进入更明澈、更确切的意识领域,音乐在该领域中得以成熟并获得与姊妹艺术平等比肩的地位”(18)阿道夫·伯恩哈德·马克斯(Adolf Bernhard Marx):《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第一卷),第274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页。。马克斯认为,《英雄》交响曲首次以拒绝依附其他艺术的独立姿态,冲破音乐形式的游戏,仅凭器乐形式本身实现“明澈”“确切”的意识,或者说理念,这是贝多芬的成就。换句话说,贝多芬的艺术成就在于将理念置入器乐音乐,器乐音乐不再仅仅是形式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达尔豪斯认为,“马克思以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将浪漫主义形而上学落至实处”(19)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其四,音乐艺术的独立与地位的上升。从音乐形态的角度,器乐音乐脱离语词及其暗示的情感的制约,成为纯粹形态的音乐类型。更重要的是,器乐音乐不再仅仅是音响形式的游戏,而是能够表现无可名状、无限复杂的人类内心的“另一种语言”或“超越语言之上的语言”。至此,音乐毫无疑问地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甚至,它以形式纯粹性和表现无限性成为“艺术中的艺术”。器乐音乐非语义性、非具象性的表象特征,以往被视为缺陷——不能准确表现对象;如今被视为优势——能够表达无限复杂、无可名状的人类内心情感。以器乐音乐为典型形态的音乐一跃从艺术的最低地位上升至最高地位。
至此,理解“绝对音乐”理所当然地需要理解音乐的形式结构及其蕴含着的精神(或者说理念)。这种观念背景催生两种音乐美学:叔本华音乐意志论、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
(二)叔本华:音乐意志论
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把世界看作盲目冲动的人类意志,或者说人类诸种情感的缩影。音乐是人类意志的直接反映或情感本质的“直接写照”。这就是叔本华“音乐意志论”。这里的音乐主要指独立自为的“绝对音乐”。换言之,叔本华认为,音乐表现的情感并非附着于世界的经验性显现,而是深入至世界的哲学本质。经过意志这种非经验再现的中介,情感美学转向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哲学。音乐“从不表现表象,仅只表现内在本质,即一切显现的本质,以及意志自身。”音乐反映的“不是这种或那种个别具体的欢乐,这种或那种悲伤、痛苦、惊愕、喜悦、快乐、平静,而是欢乐、悲伤、痛苦、惊愕、喜悦、快乐、平静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它表现的是这些范畴本质的一面,缺少一切细节,因而也免去其动因。”(20)《叔本华全集》,第二卷,第258—259页。转引自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1页。
叔本华“音乐意志论”对于音乐哲学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缺少歌词不再是器乐音乐的缺陷,绝对音乐无概念性、无具象性的抽象性质,正是它得以象征世界原型的独特而优越的形态特征。其次,它彻底改变18世纪之前音乐令人愉悦的普遍观念,将器乐音乐置入深刻的哲学版图,绝对音乐成为人类意志或人类诸种情感本质之象征。叔本华从哲学视角将音乐从很低的地位提升至19世纪美艺术的最高地位。
(三)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
汉斯立克的绝对音乐观念被冠以形式-自律论,其著作《论音乐的美》(1854)的核心观念极其明确。
其一,音乐的美不受制于音乐之外的因素。音乐的美,或者说音乐的本质,应该从“只为音乐所特有的”方面去寻找。它是一种自足的形式美,首先存在于鸣响着的乐音的运动形式。“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21)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杨业治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49页。“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22)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杨业治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50页。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的科学态度源自他所处的时代背景。19世纪“器乐音乐形而上学”以及对待音乐的虔敬态度,已经让位于20世纪经验主义的科学态度。《论音乐的美》开门见山:“我们的时代,有一种推动着一切知识领域的力量,要求对于事物取得尽量客观的认识,这个要求也必然牵涉到美的探讨。”(23)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杨业治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15页。
其二,汉斯立克所谓的“音乐形式”指各部分有机统一的形式结构,即“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音乐形式的逻辑结构,正是对维也纳三杰的器乐创作,尤其是贝多芬代表性作品形式特征的精炼总结,是判断一部作品质量高下的重要指标。
其三,汉斯立克所谓的“音乐形式”不仅指外显的音响表象,还指本质性的音乐形式,即“内在形式”。汉斯立克认为,“一个完整的乐思”是音乐的“形式”,自在自为,本身具有独立的美。“至于要问,这些材料用来表达什么呢?回答是:乐思。一个完整无遗地表现出来的乐思已是独立的美,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什么用来表现情感和思想的手段和材料。”(24)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杨业治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49页。需要进一步说明,这完整独立的乐思并非仅仅是外显的鸣响形式,还满载着作曲家的内在精神。“我们一再着重音乐的美,但并不因此排斥精神上的内涵,相反地我们把它看为必要的条件。因为没有任何精神的参加,也就没有美。我们把音乐的美基本上放在形式中,同时也已指出:乐音形式与精神内涵是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的。”(25)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杨业治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51—52页。“所谓作曲,就是精神用能够接受精神的材料进行工作。”(26)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杨业治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53页。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进一步认为,音乐的意义和推论同样来自音乐形式及其内在精神,但这种意义无法通过语言翻译。
音乐也有意义和推论,但这是音乐的意义和推论;音乐是一种可以说出和可以理解的语言,但这种语言不能翻译过来。我们说乐曲中有思想,这是含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正如在语言中一样,熟练的判断力在这里也很容易区别真正的思想和空洞的语句。(27)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杨业治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52页。
简言之,汉斯立克立足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认为音乐的美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是形式自足的美。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自为的、外显的、鸣响着的乐音及其运动形式;二是有机统一的客观形式结构;三是由内而外显现着的作曲家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由作曲家注入音乐形式之中,能够被听者领会。
综上,浪漫派文人摒弃空洞的器乐音乐形式,赞颂以纯粹的形式蕴含“诗意”这一艺术实质的器乐音乐,催生虔敬静观的音乐接受态度,落实于“理念的感性显现”,提升了器乐音乐的历史地位。“器乐音乐形而上学”哲学深化于叔本华“音乐意志论”,经由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的改造与转折,至今还深刻影响着人们看待音乐的观念。
“绝对音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器乐形态,创作原则,美学观念。这三个层面的含义均生成于西方历史之中。达尔豪斯认为,“绝对音乐观念成为19世纪德意志音乐文化的审美范式。”(28)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页。考虑到19世纪德奥音乐创作及其美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极其深远的影响力,厘清“绝对音乐”概念对于深刻理解西方音乐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艺术音乐,其重要意义就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