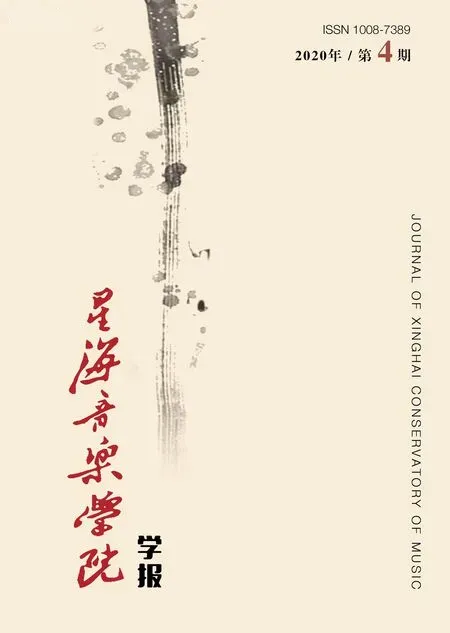广东戏剧研究所相关史料补遗
——兼及对该所历史地位和重要影响的思考
叶洁纯,向前
1929—1931年间,欧阳予倩先生在前后两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和陈铭枢的支持下,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戏剧研究所汇聚了当时戏剧界和音乐界的一流师资,开办附设戏剧学校和音乐学校培养艺术人才;以欧阳予倩、唐槐秋、严工上、吴家瑾、唐叔明等研究所人员和演剧学校学生为主体,举行戏剧公演活动十二届近百场;以马思聪、陈洪、何安东等音乐学校员工为主体创办了第一支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先后举办音乐演奏会二十余场;出版发行《戏剧》杂志十二期,编辑出刊《戏剧周刊》百余期,发表了大量创作剧本、理论文章和翻译作品,组织和引导广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展戏剧运动,在戏剧教育、戏剧研究、戏剧改革、音乐教育,以及戏剧音乐演出实践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是欧阳予倩先生艺术生涯中的重要经历,时跨三年(实际存在时间两年多)。(1)广东戏剧研究所成立时,欧阳予倩任所长,总务主任周贵菁,剧务主任唐槐秋,编纂主任胡春冰。演剧学校(后改称戏剧学校)原定由洪深任校长,洪深返沪后,先由欧阳予倩代理,后改由胡春冰负责。苏关鑫:《欧阳予倩年表(1889—1962)》,《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42页。由于存在时间较短,留存资料不多,关于该研究所的资料主要是刊载于1931年2月《戏剧》杂志、后收入《欧阳予倩全集》的《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经过情形》(以下简称《情形》)一文。(2)欧阳予倩:《欧阳予倩全集》(第六卷)“附录: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经过情形”,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35页。囿于资料缺乏,学术界关于该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不多。本文拟在进一步搜寻和补充广东戏剧研究所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延伸观察分析的时段和范围,考察其在近代中国艺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影响。
一、《广东戏剧研究所设计概略》补遗
1928年11月17日,欧阳予倩先生随同李济深和陈铭枢从上海动身,取道香港前往广州。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及其继任者陈铭枢是欧阳予倩先生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大力支持者,相关情况在《陈铭枢回忆录》(3)陈铭枢:《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和欧阳予倩先生的《粤游琐记》(4)欧阳予倩:《粤游琐记》,《南国月刊》1929年第1期,第173—185页。中均有记述。《情形》一文写道:
广东戏剧研究所,是由李任潮先生等发起,约欧阳予倩先生到广东来创办的,经费由广东省政府拨给,即归广东省政府直接管辖。此事发起于1927年的夏天,那时因为欧阳先生一时不能离开上海,直到1928年的冬天才成事实。(5)欧阳予倩:《欧阳予倩全集》(第六卷)“附录: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经过情形”,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19页。
陈铭枢对戏剧研究所的支持有诸多材料,但关于最初发起人李济深的倡议之前未曾见到确切材料。
《广东戏剧研究所设计概略》(以下简称《设计概略》,详见附录1)可以弥补这一缺失,有助于了解研究所的最初设想、组织架构和经费概算等详细情况。《设计概略》署名李济深,刊载于1928年第13期《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月刊》,该期月报出版于1928年12月31日。(6)李济深:《广东戏剧研究所设计概略》,《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月刊》1928年第13期,第144—148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是当时国民政府最高权力机构,1928年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主席,并任命各地分会主席,其中广州分会主席为李济深,指导区域为广东和广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月刊》由广州分会秘书处编辑股编辑公开出版,属政府公报性质。可以想见,《设计概略》由李济深署名,作为施政措施公开刊印于政府公报上,即便文字出自下属幕僚之手,也完全代表其本人意见。
《设计概略》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本所之事业”,包括整理国剧、介绍欧洲戏剧、创制新歌剧、组织模范剧场、组织小剧场、组织演员养成所、组织戏剧审查会、刊行戏剧杂志、设立戏剧图书室。第二部分“本所之组织”,所长和副所长之下设立杂志总编辑、小剧场主任、演员养成所主任、广东大剧场经理、文牍兼交际、编辑主任兼剧本主任、庶务、会计等8个岗位,其中广东大剧场经理岗位之下,设立舞台主任、文牍兼交际2个岗位,舞台主任之下再设立导演、美术主任(下设配光技师和工匠岗位)、演员管理(下设化装衣饰岗位)、音乐主任等。第三部分“本所经费之概算”:一是开办费18万元,包括大剧场建筑费、大剧场布置及衣装费、大剧场营业准备金、小剧场开办费和图书购买费等;二是经常费每月计4560元,包括研究所员工月薪、伙食(学生膳费在内)、电灯、房租自来水、杂志维持费、小剧场维持费等,故经常费每年共计54720元。
将《设计概略》和《情形》一文进行对比分析,具有以下差别:
第一,《设计概略》中的组织架构较为简略,研究所正式成立时有所调整和优化。《情形》一文记载:
所的组织分三股:总务,剧务,编纂,总务办理所中一切事务,庶务、会计属之;剧务办理关于戏剧上之设计及表演诸事,演员及舞台装置等等属之;编纂办理关于戏剧文学及出版诸事,编辑及剧本评判等事属之;以上三股统属于所长指挥之下。(7)《欧阳予倩全集》(第六卷)“附录: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经过情形”,载欧阳予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19页。
另外并附设演剧学校、大剧场和小剧场。(8)欧阳予倩:《欧阳予倩全集》(第六卷)“附录: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经过情形”,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19—420页。《设计概略》中,所长、副所长下辖8个岗位,事务性岗位(庶务、会计、文牍)和综合性管理岗位(杂志总编辑、小剧场主任、演员养成所主任、广东大剧场经理)并列,均直属所长和副所长,欠缺妥当。故研究所成立时,改为所长直接指挥三股,不设副所长,相关事务性工作分别归入各股,优化了组织层级和职责分工,确保研究所日常顺利运作。
第二,《设计概略》没有音乐学校和管弦乐队内容。《情形》一文记载“1930年夏季,成立管弦乐队;同年秋季,成立音乐学校”,但未说明原因。综合各方面材料,可以大致还原当时情况。此前,欧阳予倩先生在南通任“伶工学社”主任时曾组织军乐队和管弦乐队,研究所成立后希望创办管弦乐队但缺乏人才。恰好马思聪、陈洪已相继回国,欧阳予倩先生向省长陈铭枢请准成立管弦乐队让二人负责。10月,省政府同意成立乐队(见附录2),明确“本队附设于广东戏剧研究所内,即为所中歌剧系之乐队”,“马思聪当由戏剧研究所聘充歌剧系主任,乐队即归其指挥管理,其一切详细规定,均由马负责处理之”(9)《准戏剧研究所组织管弦乐队案》,《广东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36期,第16—17页。。陈洪回忆道:
于是我们招兵买马,在广州招到了几位管乐手,在上海招到了几位弦乐手,其中有原慈禧太后宫廷乐队的单簧管穆志清,他改拉中提琴。另外又去广州招到何安东、黄金槐等,一共约二十人。(10)陈洪:《忆马思聪》,载俞玉姿、李岩主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陈洪文选》,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由于经费有限,加上人才匮乏,只能把管弦乐队组织极力缩小,“把一百人缩成十八人”,虽然条件困难,但“正式成立未及三月,公开表演过六次”,第七次音乐会演奏的曲目包括俄罗斯作曲家的《序曲》、圣·桑的《骷髅之舞》、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中段、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和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选段等。(11)陈洪:《音乐革新运动的理论与实际》,载俞玉姿、李岩主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陈洪文选》,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这支管弦乐队虽然规模不大、人员编制少,但已经成为当时广州“新音乐运动”的中坚力量。
第三,《设计概略》的经费概算难以满足实际需要。《设计概略》原计划是组织演员养成所,而非戏剧学校:
招募十四至十八岁之学生四十人,授以国文,音乐,舞蹈,歌唱等课程,及戏剧之知识与经验,学习期限两年半,服务二年。不收学费,毕业后与以相当之津贴,服务期满,正式支给薪水,即为大剧场基本演员。(12)李济深:《广东戏剧研究所设计概略》,《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月刊》1928年第13期,第145—146页。
故《情形》一文中所列的戏剧学校、音乐学校和管弦乐队均为后来加办。根据《设计概略》,原计划开办费为18万元之外,研究所经常费每月4560元。对照《情形》一文,可知研究所实际创办后经费为每月4000元,与最初设想相差不大。但由于1929年5月停办,到7月再行开办时经费减半,每月仅2000元,加办戏剧学校、音乐学校和管弦乐队之后,经费更显不足,“于是重新改组,呈请省府加拨经费,每月经常费增至毫洋六千元”(13)载欧阳予倩:《欧阳予倩全集》(第六卷)“附录: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经过情形”,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35页。。可见,《设计概略》原本计划相对简单,经费预算仅包含大小剧场开办费,以及员工月薪、伙食、杂志等日常经费,戏剧学校、音乐学校和管弦乐队均不在最初计划内,尽管申请追加经费,但经费困难问题始终存在。
二、私立广州音乐院:戏剧研究所音乐教育事业的延续
1931年初,广东政局变动,陈济棠逼走省长陈铭枢,独揽广东军政大权,戏剧研究所于7月被裁撤停办。7月14日,管弦乐队举行“临别音乐会”,发表“临别宣言”称:“此次本乐队的解散,不过是机关名义的取消,而新音乐运动的阵营并不因此溃散”(14)陈洪:《四年来的广州音乐院》,载俞玉姿、李岩主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陈洪文选》,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页。。7月以后,戏剧研究所“经过种种设法,自行继续维持了四个月”(15)载欧阳予倩:《欧阳予倩全集》(第六卷)“附录: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经过情形”,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35页。,11月,广东省政府收回院址,戏剧研究所遂彻底告终。(16)康建兵:《“官办”之名,“在野”之实——欧阳予倩主持广东戏剧研究所性质考论》,《戏剧》2015年第1期,第71页。欧阳予倩先生将管弦乐队的乐器带到上海,但重组乐队未果,乐器一直保存在谭小麟处。1946年,他将这批乐器赠送给延安的中央管弦乐团,对该乐团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7)许翰如:《山沟里的火凤凰——忆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新文化史料》1999年第2期,第45页。
另一方面,戏剧研究所停办,但该所开创的教育事业仍在延续。陈洪回忆道:“在大部分的同仁星散之后,剩下三四十个流离失所的学生和两三位教员”,“东三省的炮声震动全国的时候,正是这三四十个人进行复校运动最积极的时候”。1932年春,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私立广州音乐院正式成立,马思聪任院长,陈洪任副院长。音乐院的发起人是马思聪、梁冰弦、陈伯华、胡春冰和陈洪;董事有金曾澄、许崇清、林直勉、伍大光、刘纪文、区芳浦、陈德荣、黄启明、马伯年、邝乐生、梁定慧、梁彼得、黄金槐等。(18)陈洪:《四年来的广州音乐院》,载俞玉姿、李岩主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陈洪文选》,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1页。其中,马思聪、陈洪、胡春冰、黄金槐,以及音乐院的教员何安东等均是原戏剧研究所同仁,此时共同致力于音乐院建设。
私立广州音乐院起初办学于白云路“白云楼”,开学后第二个月搬迁至惠福东路146号,开办费和第一学期的经费由各位董事捐助,拟分三期筹措10万元基金。董事中虽有金曾澄(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山大学校长等职)、许崇清(曾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广东省政府代主席、中山大学校长等职)、林直勉(曾任孙中山秘书、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委员等职)、伍大光(曾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刘纪文(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南京市长等职,时任广州市长)等多位党政要员和社会名流,但没有政府的资助,仅依靠董事捐资和学费收入难免捉襟见肘。
所筹开办费和原定计划相差太远,所以有许多地方不能将计划实现,而实际上只办了一个粗具规模的音乐学校。学生除一部分为以前戏剧研究所管弦乐队所训练的旧生,一部分则是新招的,总共不下五十人。(19)陈洪:《四年来的广州音乐院》,载俞玉姿、李岩主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陈洪文选》,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音乐院初期师资有限,尽管才5名教师,仍然开设了钢琴、声乐、小提琴、大提琴、乐理、视唱、和声、音乐史、音乐欣赏等多门课程。院长马思聪亲自教授小提琴、钢琴、视唱练耳等课程,(20)《马思聪全集》编委会编:《马思聪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42页。陈洪也担任小提琴、乐理、视唱、和声等课程教学。1933年,马思聪前往上海,陈洪代理院长。同年冬,第一届15名学生毕业,其中有钢琴专科高级(四年)3人和小提琴专科高级(四年)1人。陈洪回忆说:“回溯本院开办不过二年,四年毕业的学生是从前由戏剧研究所的音乐学校——本院的前身——转学而来的。”(21)陈洪:《四年来的广州音乐院》,载俞玉姿、李岩主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陈洪文选》,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3页。可见,在陈洪心目中,认定戏剧研究所附设音乐学校是私立广州音乐院的前身,自己从事的音乐教育是戏剧研究所音乐教育事业的延续。
1937年8月,陈洪应萧友梅之邀前往上海,就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长、教授直至抗战胜利,之后又任教于多所大学,一生专注于音乐教育事业。马思聪于1949年后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以作曲家、小提琴家和音乐教育家的身份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思聪和陈洪两位先生桃李满天下,是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而广东戏剧研究所和私立广州音乐院是他们音乐教育生涯的共同起点,在此奠定了艺术人生的基石,而后走上更加广阔的舞台。
需要强调的是,陈洪最早明确提出了“新音乐运动”的理念,(22)冯长春:《两种新音乐观与两个新音乐运动(下)——中国近代新音乐传统的历史反思》,《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第54页。而戏剧研究所附设音乐学校和私立广州音乐院阶段正是这一理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是组织研究所管弦乐队,还是创办私立广州音乐院和《广州音乐》杂志,陈洪都是身体力行践行自己所秉持的理念,有力推动了“新音乐运动”的发展。综合相关情况和资料来看,可以说陈洪提倡的“新音乐运动”理念一定程度上受到欧阳予倩“戏剧改革”思想的影响。
早在1918年10月,欧阳予倩就在《新青年》上撰文讨论“旧剧”问题,是提倡“戏剧改革”的前辈。(23)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载欧阳予倩:《欧阳予倩全集(第六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2页。该文最初发表于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4号。主持戏剧研究所期间,他先后发表《怎样完成我们的戏剧运动》《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戏剧与宣传》《民众剧的研究》《戏剧运动之今后》等文章,以“戏剧改革”为号召推动“戏剧运动”,并且《设计概略》中提出了“创制新歌剧”“制新音乐”等设想,(24)李济深:《广东戏剧研究所设计概略》,《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月刊》1928年第13期,第144页。组建戏剧研究所管弦乐队时也明确“本队以建设新音乐新歌剧为宗旨”。(25)《准戏剧研究所组织管弦乐队案》,《广东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36期,第17页。
陈洪作为晚辈,供职于戏剧研究所期间,对欧阳予倩提倡的“戏剧改革”及“建设新音乐新歌剧”的宗旨自然有所了解。材料显示,陈洪对欧阳予倩先生的五幕歌剧《荆轲》印象深刻,并对“建设新音乐新歌剧”有独到见解。五幕歌剧《荆轲》为欧阳予倩先生1927年创作,于1929年发表在戏剧研究所《戏剧》杂志上,陈洪在1937年的《中国新歌剧的创造》一文中,还以此为例,阐述关于创制新歌剧新音乐的思考,他没有明说与欧阳予倩先生商榷,但深究下去可以发现,其观点和主张均源于对欧阳予倩先生五幕歌剧《荆轲》的思考。
该文主旨在于讨论中国新歌剧的创造,基本观点脱胎于“新音乐运动”理念。第一,剧本方面。欧阳予倩创作的是五幕歌剧《荆轲》,此外也常采用《杨贵妃》《潘金莲》等为题,而陈洪认为宜作为独幕剧,且主张摒弃《荆轲刺秦王》之类为题,而用《易水之歌》或《荆轲去了》,因为“旧的、容易令人联想及旧戏的剧本,应该暂时不用,就是用历史背景重新创作,也要取一个新颖的名字才好”,“无论在外观或内容——尤其是内容——我主张彻底改造,绝不能妥协。‘改良’的办法完全不能用,那是等于自杀”。(26)陈洪:《中国新歌剧的创造》,载俞玉姿、李岩主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陈洪文选》,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页。第二,曲谱方面。陈洪的意见是:“新歌剧的音乐应该完全重新创作——根据各剧本的内容去创作——绝对不容抄袭或套用”,且应学习西洋音乐,采用独唱、二部唱、三部唱、四部唱和大合唱等形式;即便采用中国固有的旋律或调子,也“不能够把整个的旋律或调子采用,而只可取其音调,或者‘断章取义’,以求造成一种中国化的氛围”(27)陈洪:《中国新歌剧的创造》,载俞玉姿、李岩主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陈洪文选》,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页。。第三,乐队方面。陈洪强调中国新歌剧的伴奏应该采用管弦乐队,因为“乐队是一种工具,工具是没有国界的,应该选择最优良的来使用”,“无疑地现在最优良的乐队是管弦乐队”(28)陈洪:《中国新歌剧的创造》,载俞玉姿、李岩主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陈洪文选》,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后面两点意见是陈洪一直坚持的主张,并且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确与欧阳予倩先生商榷,可以作为两人曾经讨论交流的证明。1937年底,陈洪在上海观看欧阳予倩先生编导的《梁红玉》歌剧后写过一篇小文章,其中有一段话:
至于那些音乐,虽然单调,也还不至于难听。我承认唱者都有相当的技术,只是缺乏和声,给人以难堪的空虚之感!这里我又要提出我的工具无国界论,主张把西洋的管弦乐队搬过来,未知欧阳先生以为如何?(29)陈洪:《梁红玉》,载俞玉姿、李岩主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陈洪文选》,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5页。
此处一个“又”字和“未知欧阳先生以为如何?”的发问,足以说明二人应该不只一次讨论过这些问题,也充分证明“陈洪的新音乐运动理念受到欧阳予倩戏剧改革和戏剧运动思想的影响”这一推测基本成立。
总而言之,戏剧研究所附设音乐学校和私立广州音乐院阶段是陈洪“新音乐运动”理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融合了与“戏剧运动”的对比和参照。这种“音乐形态学”意义上的新音乐观得到萧友梅、青主、赵元任、黄自等音乐家们的共鸣,和以左翼音乐为代表的“音乐功能论”意义上的新音乐观一道,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思潮,由此又延伸出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两个“新音乐运动”,形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近代新音乐发展的两大潮流,(30)冯长春:《两种新音乐观与两个新音乐运动(下)——中国近代新音乐传统的历史反思》,《音乐研究》2008年第6期,第11—12页。其影响力贯穿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持续直至今天。
三、省立“民教馆”的“广东戏剧研究所”:传承戏剧教育和演剧活动的同名机构
1934年6月,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以下简称“民教馆”)成立了广东戏剧研究所,这一同名机构传承和延续了原戏剧研究所的戏剧教育和演剧活动。民教馆的目标是“以实验及推行各种民众教育事业并辅导各县民众教育之发展为宗旨”(31)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大纲》,《民众教育半月刊》1934年第1期,第13页。,隶属省教育厅第四科,馆长由教育厅长兼任。民教馆戏剧研究所由曾经留美学习戏剧和油画的李锡彭任所长,刊载于1935年第17期《民众教育半月刊》的《本馆戏剧研究所一年度工作概况》(见附录3)一文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
一是举办民众戏剧普通班,培植民众戏剧人才。研究所招收的学员以社会青年和机关、商店、工厂的青年职工居多,上课和演出活动大多在夜晚,属业余性质,到1936年为止举办了两期,共培训80余学员。“每周星期一三五下午七时至十时为上课时间;四周为一段;五段为一学期;两学期为一学年;一学年毕业。”开设课程有戏剧概论(导师李锡彭,课时26小时,下同)、戏剧史(关存英,45小时)、戏剧选读(黄凝霖,49小时)、舞台装置(吴琬,26小时)、表演术(韦碧魂,87小时)、剧本作法(谭国恥,32小时)、导演术(雷惠明,32小时)、化装术(钟启南,31小时)、文艺研究(关存英,13小时)、音乐常识(陈洪,4小时)。
二是组织戏剧演出活动。研究所以戏剧班学员为主体,常在民教馆剧场和市内的一些礼堂演出,还在广州四周及佛山的乡村设有演出点,所以每月演出的场次较多,几年间共演出了100多个剧目。(32)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文化艺术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0—301页。
三是辅导各学校及民众业余剧团演剧。成立后的一年之内,对岭南大学戏剧研究社、女青年会剧社、培正中学未明剧社、培正中学学生会、培正中学觉社、知用中学学生戏剧研究会、培道中学晔晔社、青年会中学、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青年剧社、培英中学、执信学校和努力中学等学校和青鸟剧社等民众剧团进行辅导,累计指导35个剧目,协助举办演剧活动53次,极大活跃了广州的戏剧艺术氛围。(33)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本馆戏剧研究所一年度工作概况》,《民众教育半月刊》1935年第17期,第25—26页。
四是宣传和实践“民众戏剧”理念。以民教馆主办的《民教半月刊》为平台,李锡彭、黄凝霖、关存英等人先后发表了《作为教育民众的戏剧》(34)李锡彭:《作为教育民众的戏剧》,《民众教育半月刊》1934年第2期,第8—9页。《什么才是中国的民众戏剧?》(35)黄凝霖:《什么才是中国的民众戏剧?》,《民众教育半月刊》1934年第2期,第9—11页。《民众戏剧浅说》(36)关存英:《民众戏剧浅说》,《民众教育半月刊》1934年第3期,第4—6页。《现代戏剧底社会的意义》(37)张宝树、梁之盘:《现代戏剧底社会的意义》,《民众教育半月刊》1935年第4期,第7—14页。等文章,介绍戏剧理论,讨论民众戏剧等问题。
之所以说此“广东戏剧研究所”传承了彼“广东戏剧研究所”的戏剧教育和演剧活动,原因有四点:
第一,部分授课导师来源于原戏剧研究所。除教授音乐的陈洪之外,教授化装术的钟启南曾在原戏剧研究所总务科任职,还多次参演欧阳予倩先生导演的《怒吼吧,中国!》和唐槐秋导演的《茶花女》等多个剧目。教授戏剧史的关存英是原戏剧研究所《戏剧》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第二,所设课程基本沿袭了原戏剧研究所课程编配,如戏剧概论、戏剧史、戏剧选读、戏剧写作、表演术、化装术、导演术、舞台装置、音乐等课程基本一致,只是由于学时有限缩减了课时。
第三,公演和辅导的剧目与原戏剧研究所公演剧目存在诸多重合,例如《怒吼吧,中国!》《未完成的杰作》《娜拉》《可怜的斐迦》《贼》《白茶》《熊》《女店主》《最后的拥抱》,以及欧阳予倩先生创作的《小英姑娘》等。
第四,接受辅导的各学校和民众业余剧团与原戏剧研究所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大中学校和民众业余剧团剧社的骨干正是在欧阳予倩先生在粤期间受到戏剧熏陶而投身其中,例如组织“青鸟剧社”的陈酉名就是研究所附设戏剧学校的学生。正因如此,欧阳予倩先生的广东戏剧研究所虽然停办,但戏剧的热潮和氛围并未完全消退,继起的民教馆戏剧研究所延续了广州地区的戏剧教育和演剧活动,也为日后抗日救亡戏剧运动培养了人才,集聚了力量。
四、薪火相传:广东戏剧研究所在南国播撒的艺术种子
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维持时间不长,但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出版《戏剧》杂志两卷共12期、周刊111期,发表了大量创作、翻译和理论文章,演出创作和翻译的剧本30多个,公演话剧不下10次。(38)苏关鑫:《欧阳予倩年表(1889—1962)》,《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42页。在戏剧研究所影响之下,当时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勷勤大学、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以及培正中学、培英中学、知用中学等学校学生均竞相组织剧团。广东近现代戏剧在戏剧研究所的大力推动下,逐渐完成了由文明戏阶段向现代话剧阶段的过渡。(39)张健:《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和艺术戏剧运动》,《戏剧》1998年第3期,第62页。戏剧研究所虽告结束,但播撒了艺术的种子,薪火相传,照亮未来。
前文已述,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音乐学校和私立广州音乐院是马思聪和陈洪先生音乐教育生涯的共同起点,短短几年办学仍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专业音乐人才。小提琴家、指挥家章彦(当时名为“章正凡”)先后在戏剧研究所戏剧学校和私立广州音乐院学习,1949年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音乐管弦乐团指挥、中央实验歌剧院管弦乐团指挥、中央歌舞团指挥、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等。窦立勋少年时期在私立广州音乐院随陈洪先生学习小提琴,后来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小提琴教授,是中国小提琴教学体系的奠基人之一。香港著名音乐家林声翕、凌金园等均曾在音乐院学习。(40)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文化艺术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9页。此外,歌唱家李丽莲也是在戏剧研究所拜欧阳予倩为老师的。(41)梁茂春:《中国交响乐队拾零(一)》,《福建艺术》2012年第2期,第39页。
从戏剧创作、表演和其他艺术人才方面来看,不少广州和华南地区的文艺中坚力量都来自戏剧研究所,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曾在戏剧研究所任职的胡春冰、唐叔明、钟启南等。胡春冰于1929年应欧阳予倩先生之邀任研究所编纂主任,主编《戏剧》杂志。唐叔明原系“南国社”成员,随团赴广州公演以后,便和“有约在先”的胡春冰结婚,担任戏剧学校表演教师。研究所停办之后,随欧阳予倩先生来粤人员大多返回上海,胡、唐二人则留在广州。(42)包明:《南国社的“卖花女”尚在人间》,《上海戏剧》1982年第2期,第50—51页。此后,胡春冰先后组建“前卫戏剧作者同盟”“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等进步组织,(43)周仁成:《胡春冰的戏剧人生、创作与理论》,《戏剧》2016年第4期,第86页。抗战期间在香港组织了多次戏剧公演宣传抗战。1949年以后,胡春冰定居香港,创作、改编、翻译剧本之外,着重编辑剧本选集,出版戏剧专刊,为香港剧坛播下种子,成为香港戏剧文学的拓荒者、奠基者。(44)周仁成:《胡春冰的戏剧人生、创作与理论》,《戏剧》2016年第4期,第88页。曾在研究所总务科任职的钟启南,后来成为民教馆戏剧研究所导师,继续培养戏剧人才,从事戏剧运动。
二是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和“抗战”演剧活动的戏剧学校学生,如袁文殊、吴光华(吴业琨)等。袁文殊1930年考进广东戏剧研究所文学系学习编剧,1931年和胡春冰一起组织原研究所戏剧文学系部分学生成立了“前卫戏剧作者同盟”并创办《万人杂志》(45)袁文殊:《有关“广州文总”和“广州剧联”的一些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第219—220页。,后参加“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担任分盟和下设“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领导工作,后于1934年在上海参加“左联”活动,担任执委并负责戏剧理论组的工作,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投身于抗日救亡演剧活动。1941年10月到延安以后,曾先后担任“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员、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从事电影工作,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经理、党委书记,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不仅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电影评论家和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46)《电影艺术》编辑部:《悼念袁文殊同志》,《电影艺术》1993年第2期,第4—5页。“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另一领导成员吴光华也是戏剧学校学生,抗战期间和戏剧学校的同学陈酉名(下文会详细论及)等人一起在广西创办“南宁业余剧团”(由当时中共地下党南宁中心县委属下的文化支部领导),1949年后在广西戏剧学院任教。
三是成为戏剧创作、表演和影视等专业人才的戏剧学校学生。著名粤剧导演艺术家陈酉名曾在戏剧研究所编纂股协助抄誊和校对,后来免考成为戏剧学校学生,与罗品超、黄鹤声等是歌剧班同学,卢敦、李晨风、吴回等则为同期话剧班的同学。陈酉名先后参加了“广州前卫戏剧作者同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广州分盟”,还组建了“青鸟剧团”发展校园戏剧。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以后,他和吴光华等人在广西创办“南宁业余剧团”,进行抗日戏剧宣传,南宁沦陷后,转到中共地下党桂西南特支领导的南宁战时工作团,担任第三队队长,仍继续从事剧宣活动。1949年以后,陈酉名长期从事粤剧编导工作,执导粤剧剧目百余个,成为一代名导。(47)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粤剧研究中心合编:《粤剧春秋》(《广州文史资料》第四十二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4—333页。罗品超,原名罗肇鉴,12岁进广州芳村孤儿院儿童戏班学艺,后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戏剧学校。研究所停办以后,罗品超进入八和会馆戏剧养成所学习粤剧,结业后正式成为粤剧艺人,后来更是成为“冶文武于一炉,集刚柔于一身”的粤剧泰斗。1952年,罗品超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获演员一等奖。(48)广州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广州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355—356页。当时,欧阳予倩先生主持汇演工作,眼见当年的鉴仔已经成为粤剧名角,他欣然在给罗品超的纪念本上题字:“勇敢、坚持、有恒地做戏剧改革的斗士”。此外,话剧班学生李晨风、卢敦、吴回等曾于1931年在澳门组织“时代剧团”从事演剧活动,(49)张剑桦:《澳门戏剧文学发展轨迹述略》,《艺术百家》2009年第3期,第149页。后均成为香港著名演员、编剧和导演。李晨风被誉为“粤语片导演三杰”和“五六十年代粤语文艺片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香港电影史上具有一定影响。(50)魏君子主编:《香港电影史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5页。
四是受到戏剧研究所影响的其他群体。唐叔明回忆,在戏剧研究所几年间,“由于《戏剧》杂志的出版,联系和结交了很多大学生作者,他们投稿后成了戏剧家”(51)包明:《南国社的“卖花女”尚在人间》,《上海戏剧》1982年第2期,第51页。,其中赵如琳先是热心参与戏剧研究所的活动,后正式参加编纂股工作,编辑多期《戏剧周刊》,后在抗战期间担任广东省立艺术院(后改名为“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多年。(52)曾炜:《广东战时话剧一颗星——记赵如琳》,载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广东话剧研究会编:《广东话剧运动史料集》(第二集),东莞:东莞市印刷厂印刷,1987年,第83页。张雪峰、梁寒淡、邓竹筠等人在广州期间深受戏剧研究所影响,是戏剧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39年,张雪峰、梁寒淡等与率“中国旅行剧团”南下的唐槐秋合作,组建“中国旅行剧团广东话组”并在澳门举办了多次演出。(53)胡星亮:《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澳门话剧》,《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5—16页。1942年,由张雪峰、梁寒淡、关存英、邓竹筠等发起成立了澳门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戏剧团体“艺联”,虽然活动时间仅半年左右,却对澳门戏剧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54)郑应峰:《澳门现代戏剧的文化本土意识建构过程分析》,《艺术评论》2014年第5期,第77—78页。梁寒淡是澳门戏剧运动的先驱,后来长居澳门培养了不少戏剧人才。
结 语
对于欧阳予倩先生的研究者来说,广东戏剧研究所不过是其创办的诸多机构之一,持续时间不长,故往往着墨不多。同时,由于资料有限,聚焦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研究难以拓展和深化,导致对该所历史地位和重要影响的认识不足。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不能以是否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评价成败得失。广东戏剧研究所及其附设戏剧学校和音乐学校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一时一地,放宽历史的视角,拓展观察的时段和范围,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对欧阳予倩先生和广东戏剧研究所获得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认识,更加明确意识到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持续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