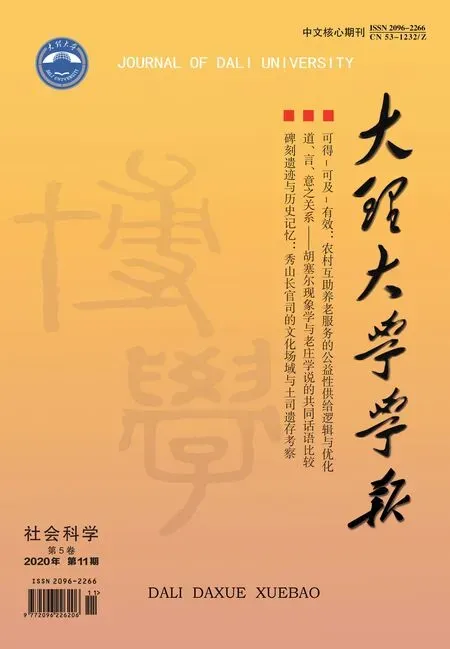抗战时期闻一多先生的民间文化观念与情怀
刘 薇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昆明 650500)
“湘黔滇旅行团”迁徙中的民歌采集活动开启了闻一多对民间的认识,沿途的采风问俗活动让他在学术上运用民间文化知识来阐释现实问题,在亲眼目睹沉重的民族灾难后,来到昆明的闻一多以自己的言行来阐释其民族情怀。
一、“湘黔滇旅行团”采风问俗活动开启民间意识
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沦陷,日军向长江流域逼近,不久武汉告急,长沙遭到空袭,为了让学校能够正常上课,“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常委会”准备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经研究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关于迁校路线,常委会事先指定军训教官雷树滋研究并提出方案。雷树滋是云南元谋人,以前经常往返于云南与京沪间,对交通、地理情况比较熟悉,他提出水陆两条路线。前者经粤汉路到广州转香港,乘海船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路经河口入昆明。后者由湘西经贵州直赴昆明。走陆路可以组织步行,沿途还可以采集标本,了解当地民俗风情,做社会调查。”〔1〕常委会接受了他的方案。参加步行入滇的人员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参加步行团的老师有11位,闻一多就是其中一员。旅行团于 1938 年 2 月 20 日出发,4 月 28 日到达昆明,历时68 天。1938 年 4 月 2 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一)民间文化理念的源泉
长沙临时大学为了鼓励师生沿途调查的积极性,为此专门发文,《长沙临时大学关于迁校步行计划的布告》规定:“本校迁滇原拟有步行计划,藉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步行队到昆明后得将沿途调查或采集所得作成旅行报告书,其成绩特佳者学校予以奖励。”〔2〕学校予以的激励,对于青年学子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参加步行团的诸位老师首先作了表率作用,在旅行团老师的带动下,学生根据自己所学专业成立了各种沿途考察的社团。
闻一多是“湘黔滇旅行团”四位教授之一,他不顾一路的疲惫,沿途与老乡攀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路途中所目睹的民众苦难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灵,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怀,是他后来学术研究具有时代感和民族责任感的源泉。“湘黔滇旅行团”在抗战史和教育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同时在文化史上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从闻一多及其指导的学生在日后的学术研究方面可见这次特殊的旅行对他们的影响。对闻一多而言,这是他首次如此近距离地与大众文化接触。他原来的学术研究是文学、诗歌,生活圈大多局限于学校,与下层劳动人民打交道的机会很少。闻一多作为教授本可以乘坐交通工具前往昆明,而他却认为“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的家族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3〕523对于当时的学者而言,大多不知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是什么样子,更谈不上对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南地区的了解。沿途中作为教授的闻一多身体力行地关注老百姓的生活,收集记录民间文化,引导学生认识到圣贤文化之外,民众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打破了“中国文化一元”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民间文化也是有价值的。
闻一多在近距离地接触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后,不但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学术上对民间文化也有了新的认识。他在《西南采风录·序》中透露,“湘黔滇旅行团”是他新生命的起点,他曾说:“我相信自己的生命是从战争之后开始的。”〔4〕当国家处于忧患时,祖国的命运时刻牵动着每个知识分子的心,促使他们从政治腐败、学术僵化等方面找原因。闻一多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被侵略,是因为“我们文明得太久了”,中国长时间把正统文化作为文化精华,人们的思想被传统文化禁锢了,没有还击的勇气和力量了,需要重新寻找中国文化整体的价值观,建构起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勇猛精神。闻一多认为那些看上去无知朴实的农民身上有不少真知灼见,特别是生活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民间文学可能成为传导新思想、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利器。可见,闻一多对民间的深刻认识是从抗战开始的,如果没有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这段经历,他就没有机会与民众广泛接触,也就不可能对普通百姓有如此深入的了解,更不会对民间文化有如此大的兴趣。当时西南联大《边疆人文》期刊编辑部的成员邢公畹也认为:“闻先生参加了部分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到达昆明。一路上见到了苗、瑶、傣等许许多多的兄弟民族,听到了广布于辽阔西南土地上的民歌、民谣和传说、神话。千里旅途的见闻和采风活动,更丰富了他对古典文学、神话、诗歌研究的内容。十年后的四十年代撰写《说鱼》一文时的思路,跟这一段经历是有关系的。”〔5〕闻一多的神话研究始于20 世纪30 年代中期,正是基于在《诗经》《楚辞》等古籍中发现了大量神话资料,开始整理、考证,并追寻神话中所包含的民族本源性。1936 年闻一多曾在清华大学开设专题课《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他所讲授的《中国文学史》也是以神话为起点开讲的,他认为神话是文学的“根苗”,这与他后来通过神话研究来探寻中华民族的源头的理念相关。如果说,30年代的神话学研究依靠的是文献典籍,那么,40 年代的神话研究更多则是运用民俗学的学科理念,探寻中国文化源头,挖掘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共同民族精神,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对现实的关怀。
(二)民间文化理念的传播
“湘黔滇旅行团”途中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生动的民间歌谣、优美的神话传说,引起了闻一多对民间文化的兴趣。一路上的长途跋涉,使他有机会亲眼目睹下层老百姓贫困的生活状态。怀着对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民众由衷的热爱和同情,他身体力行地记录民间口头文学,采集民风民俗,同时还指导“歌谣组”的学生们收集整理民歌民谣,引导他们从民歌中去感受深藏于民间的那种“原始的野蛮的力”。到昆明后“歌谣组”成员刘兆吉编辑出版了《西南采风录》;马学良写成了《湘黔夷语掇拾》一文,发表于1938年第3期的《西南边疆》期刊。
《西南采风录》是民间文学史上记录民歌的典范。“湘黔滇旅行团”途中,原南开大学心理学系学生刘兆吉积极加入了闻一多组织的民间歌谣组,一路上在闻一多支持和鼓励下采集民歌民谣,到昆明后把采集到的二千多首歌谣整理命名为《西南采风录》,于194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出版后得到了多位著名专家的肯定,被誉为“现代的三百篇”“研究西南民俗及方音的良好资料”〔6〕1。朱自清在序中写到:“他以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前无古人。他将采集的歌谣分为六类。就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这就是西南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好诗,这中间不缺少新鲜的语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读了都可以增扩我们自己。还有‘抗战歌谣’和‘民怨’两类,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看出民众的敌忾和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真可以‘观风俗’了。历来各家采集的歌谣,大概都流传已久,新唱出来的时事歌谣,非像刘先生这样亲历民间,是不容易得到的。……总之,这是一本有意义的民俗记录,刘先生的力量是不会白费的。”朱自清肯定了歌谣来自民间的重要性,内容真实地表达出民众的心声:是观风俗的一个好办法,也是一本有意义的民俗学书籍。据《闻一多全集》记载,闻一多一生中只为五本书作过序,分别是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薛沉之的《三盘鼓》、彭丽天的《晨夜诗庋》、藏克家的《烙印》和费鉴照的《现代英国诗人》,可见闻一多对《西南采风录》一书是比较满意的,而且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西南采风录》称作“新《诗经》”。序中说:“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一口。”〔7〕281抗日战争时期正需要中国人民具有“原始”“野蛮”的民间精神,而在中国正统文化中“我们文明得太久了”,闻一多深感抗战不是讲文明的时候,《西南采风录》中正好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反抗精神和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民俗学是以1918 年成立歌谣征集处为肇始,继而在刘半农主持的《北京大学日刊》开辟专栏,发表征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谣。歌谣征集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发表歌谣的《日刊》更名为由常惠主持的《歌谣周刊》。1923年成立了“风俗调查会”,自此,歌谣学的收集迅速波及到了民俗学的调查,并在知识界引起广泛的关注。《西南采风录》在当时之所以得到大师们的高度认可,与五四前期的“歌谣学运动”对知识界的影响有关,知识分子开始重新估价中国文化的整个面貌,不再仅仅把正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唯一,开始寻求民间文化应有的地位。从当时知识界对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来看,他们的目光已逐渐转向平民生活,但却少有机会真正走入民间去感受民众的生活状态,而在闻一多指导下的民歌采集活动,引导同学们认识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开启了走向田野调查的先例,并且用学术研究来反映这些现实。
迁徙的路途中采集民歌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能有毅力坚持下来的只是凤毛麟角。沿途少数民族众多,民族语言各异,“在这次采集民歌的工作中,抱着最大的希望,而结果最感失望的,就是搜集苗歌的工作,在湘黔滇三省的旅程中,自湖南晃县,一直到昆明再至蒙自,到处都看见苗家同胞,经过了许多住有苗家的城镇村落,并且在黄平的皎沙村,在炉山县城,都曾与苗家举行过联欢,请他们歌舞多次,再者一路山坡田畔间也常听到一声两声的苗歌。可是因为语言不通,不易探访采录,所以在三千多里的旅途中,仅得苗歌两首”〔6〕192。虽然路途中经过不少民族村寨,但由于语言障碍,记录下来的少数民族歌谣却很少。从采录者的调查过程来看,可见其悲喜交加的复杂心理,喜的是沿途中丰富多彩的民歌民谣,悲的是由于赶路时间紧迫和语言不通等原因,不能记录下这些民歌。能使刘兆吉坚持完成沿途的采集活动,与闻一多对他的鼓励密不可分。当时的闻一多由于自己也参与到民歌的采集活动中,因此,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并肯定民间歌谣的采集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活动。“晚上在沿途山村农舍,临时住宿地,与他观赏、讨论搜集的民歌。闻先生与学生们同样席地而坐,在如豆的菜油灯下,他忘了一天走80 多里山路的劳累,高兴地审阅我搜集的民歌”,称赞这些民歌“不但在民间文学方面有欣赏和研究价值,在语言学、社会学、民俗等方面也有参考价值。要编辑成书出版呀!不然就辜负了这些宝贵的材料”〔7〕181。正是有机会时时受到闻先生的指导和精神上的鼓励,认识到民间歌谣的重要价值,刘兆吉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完成数千首歌谣的采集。
闻一多指导下采编的《西南采风录》一书,其价值也从多次的出版中得以体现,1976 年,该书编入台湾著名民俗学家娄子匡主编的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第42册,由台湾东方文化书局出版。1991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也再版此书。在大陆,200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2003年编入《西南民族文献》第14卷,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再版。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家、民俗学家马学良先生,抗战时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也是“湘黔滇旅行团”民间歌谣组的成员之一,其调查成果为《湘黔夷语掇拾》。据他回忆:“由于民族语言的隔阂,调查时语言障碍很多。我当时是随旅行团步行的一个学生,闻先生得知我在北大中文系学语言专业,就约我同他一起去调查。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从来都是满腔热忱,诲人不倦。每次调查前,他都谆谆叮嘱我,在调查语言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宗教、民俗、民谣、神话传说方面的资料,它们与民族语言、民族文学都是息息相关的。”〔8〕闻一多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念,引导马学良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并走向探寻民族文化的学术之路。
闻一多的教导使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民间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引导他们学术研究眼光向下,关注民间文化。
二、闻一多对民间文化知识的运用
闻一多在“湘黔滇旅行团”途中搜集的民间材料,虽然没有单独的论著整理出版,但在他的神话学和民俗学领域研究中,却大量使用民间文化的材料进行论证研究。
(一)神话研究开启民族精神探源
闻一多以伏羲女娲神话开启了中国神话的研究,他认为“不管是化生万物,或创造宇宙,总归得有一个先决条件,那便是,他必须是最首先出世的一个人。而伏羲,照真正原始的传说,应该是人类历史最初一页上的最初一个人物,人皇即伏羲。那么楚人为什么祭他呢?这是因为楚地本是苗族的原住地,楚人自北方移殖到南方,征服了苗族,同时也征服了他们的宗教,因此伏羲是苗族传说中全人类共同的始祖”〔9〕。闻一多以追溯上古文学来研究神话,到从故纸堆、从书斋中走出来,对伏羲的身世进行考证,得出中华民族同源性的结论。
闻一多知识渊博,特别体现在其深厚的古文功底方面,无论参照古籍文献进行族源追溯,还是以少数民族活态神话为基础,对比较神话研究都具有开创性。朱自清先生曾说:“闻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话,是将这神话跟人们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话不是空想,不是娱乐,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现。这是生死存亡的消息,是人与自然斗争的记录,非同小可。”〔10〕闻一多力图用民俗学的眼光来研究神话,从神话资料中让中国各少数民族知其同源性,以达到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怀。
民俗能引起闻一多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具有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热情,确信从民歌、神话、民间习俗中可以找到民族精神。闻一多的神话研究不单纯是一项学术研究,更多的体现了通过神话来寻找民族共同的记忆。在研究方法上,他吸收了考古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与传统文献相结合实现对神话学研究的新突破。《伏羲考》是体现闻一多思想和运用综合研究最为典型的著述。1942 年5 月,也就是闻一多潜心写作《伏羲考》的那段日子,他应邀为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作了一场题为“神话及中国文化”的讲演。现存闻氏手稿中,有一份题为“神话与古代文化”的提纲,从内容上看,很可能与这次讲演有关〔3〕634-637。演讲题目虽然是“神话与古代文化”,但在“导言”却重点介绍了历史教育与民族意识。1942 年11 月6 日,国文学会和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文史讲座,第一讲即为闻一多《伏羲的传说》。1942 年12 月的昆明《人文科学学报》发表了《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以上这些都是闻一多对《伏羲考》前期的思考,可见闻一多通过龙图腾建构出龙与中国历史、文化、民族国家、国人之间的关联。运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外文资料、民俗调查材料,开创了神话研究的新境界,努力去实现古今材料的互证与结合。运用民俗学的学科理念,探寻中国文化源头,挖掘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共同民族精神,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对现实的关怀。
闻一多对民间文艺方面的重视不仅局限于自己的研究,并且还希望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参与到民俗学的收集整理工作中来。1941 年春季,闻一多给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文学组四年级讲授“古代神话”〔11〕。1942 年 5 月 6 日,闻一多应邀为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讲“神话及中国文化”〔3〕643,在“神话与古代文化”这一份演讲提纲中是从“历史教育与民族意识”谈起,他提出在民族意识产生的过程中认识到有共同来源,民族意识越坚固,则表现出过去无历史教育或不太重视历史教育,提出“用考古学和民俗学两种新旧材料融合的研究方法去发现事实。”最后是“神话与古代民俗”的关系,他将神话研究纳入民俗生活,从中国文化中寻求民族意识的统一性。神话是活态的文化传承,自然不能只注重古典文献而无视生活。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闻一多从神话中寻找民族记忆,希望更多的学者去发现身边的活态神话,把神话与生活中的民俗相连,从西南各少数民族神话中探求中华民族的同源性。
(二)民间歌谣对古代文学的阐释
闻一多把对民歌的兴趣进一步扩大到了民俗领域,对民俗文化的关注,使他在楚辞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在《什么是〈九歌〉》的提纲中写到“戏剧的起源∕从生活中求∕宗教生活”〔3〕623。戏剧起源于生活,宗教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对生活的体验。
1945 年,闻一多《说鱼》一文在《边疆人文》上发表,以民歌民谣中的“隐语”为论证,指出“鱼”在民众生活中的功能及流行的地域与时间。为了说明“鲤鱼”指书函,书函刻成鱼的形状,象征爱情。他列举安南情歌、黑苗情歌、昆明民歌、会泽民歌、寻甸民歌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近30多首民歌,而出现在全文中的民歌达到近60首,而且不少的民歌都是闻一多采录于昆明周边的民族和地区。闻一多引用古典文献材料和大量的近世歌谣来说明,鱼是象征配偶,这与人们的婚俗观有关。他认为“在原始人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而鱼是繁殖能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把人比作鱼是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青年男女称对方为鱼,那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现在浙东婚俗,新妇出轿门时,以铜钱撒地,谓之‘鲤鱼撒子’,便是这观念最好的说明。《寻甸民歌》‘鲤鱼摆子’,也暴露了同样的意识”〔12〕。这篇文章中对各地民俗的应用,也可见闻一多对民俗文化的认可和学术研究上的转变。虽然五四以来,在走向民间的呼声下,北京大学开展了歌谣学运动,但对古典文学顶礼膜拜的闻一多,能够对民间文学如此看重,实在是抗战时期他思想的一大转变。
闻一多对少数民族民间歌舞的热爱,也让他的学术研究有了新的突破。1946 年5 月,闻一多在昆明亲自参与指导了一台彝族歌舞演出,把不被外人所识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搬上了大众的舞台。原由是联大剧艺社负责人王松声和中山中学学生毕恒光到路南县圭山乡去服务,看到热情奔放的彝族歌舞,产生了组织彝族演出队到昆明演出的想法,二人去拜访闻一多,想得到他的支持,基于对民间文化的重视,他认真听了二人建议后大为赞同,并积极去争取文化界人士的支持。5 月19 日晚第一次招待演出在昆明,出席的有新闻、教育文化、文艺各界三千余人。演出团带来了20多个节目,有象征战争的《跳叉》《跳鳞甲》《霸王鞭》等,有表现爱情的《阿细跳月》《阿细先鸡》《大箫》《一窝蜂》等,有哀悼战士的《葫芦笙》,有反映娱乐的《架子锣》《三串花》《猴子搬包谷》《拜堂乐》等。演出完毕后闻一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24 日,正式演出时,他更是带领全家去观看。演出非常成功,昆明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演出情况,《时代评论》出版了评论专集,刊登了闻一多对演出的题词“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要用生活的折磨来消耗它?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评论专集上还刊登了楚图南的《劳动民族的健壮的乐歌和舞踊》、徐嘉瑞的《圭山的彝族歌舞》、费孝通的《让艺术在人民中成长》等。他们为彝族民间音乐舞蹈有史以来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给予热情的赞扬。演出期间,先生还参加了联大文艺社在北门书屋组织的一次文艺问题讨论会,实际上是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1029-1031。在闻一多的努力下,文化界对这台歌舞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极好的评价,起到了宣传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目的。
闻一多亲自指导中华民族土著歌舞,再一次受到了来自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滋养,并提出让这些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艺术保留下来,以丰富中华民族文化。运用民俗知识使闻一多的文献考据取得重大的突破,他从各民族的民间文艺中看到相通之处,把这种相通运用于古代神话和文学研究中。他从彝族歌舞中领悟到的是两千多年前楚国演出《九歌》的盛况,据文献考证,《九歌》是楚人祭祀天神时表演的宗教歌舞,他对《九歌》的研究早有涉及,发表了《什么是九歌》《怎样读九歌》《九歌的结构》等论文。从民俗学视角去解释民间信仰,从神话中去研究民间信仰的神,写出了《东皇太一考》《司命考》等文。之前他想把《九歌》祭天仪式还原为歌舞剧的愿望一直萦绕心头,是彝族歌舞给他带来了灵感,彝族歌舞中,闻一多看到了古人的生活习俗。在演出结束后的几天内,他就完成了《〈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的剧本,彝族民歌大多是歌唱恋情的,形式是一男一女对唱,这也是《悬解》剧本的基本结构。彝族歌舞中表现战争的《跳叉》《跳鳞甲》《霸王鞭》等歌舞场面,在《悬解》剧本中也可以找到痕迹,如为庆祝胜利并哀悼国殇,手拿着武器和钲鼓,环绕着死者尸体,举行与撒尼人跳鼓似的舞踊。在闻一多看来,少数民族艺术不仅有审美价值,还有助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总之,在抗战时期,闻一多走出书斋和故纸堆,走进广阔的田野,湘黔滇之行的采风问俗经历引起了他对民间文化的兴趣,使他的学术研究内容远远超出了一般训诂考据的陈规局限。抗战时期他对民间知识的运用是为了向国人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同源性,强调共同的血缘性,实现全民一心共同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