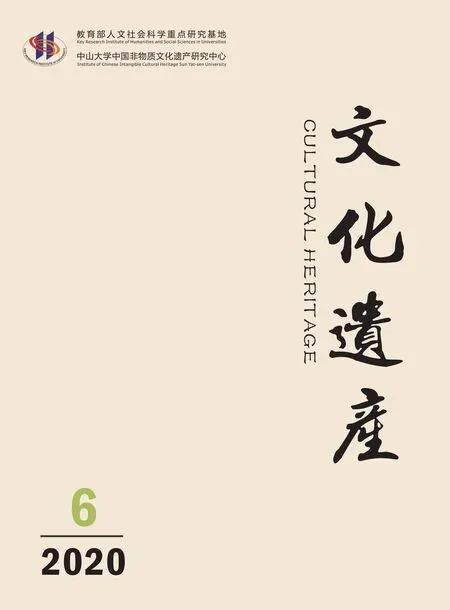唐代城隍信仰及其文化内涵*
孟子勋
唐代城隍神祭祀早先盛行于南方,牛肃《纪闻》载“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1)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三辑录此条,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400页。,李阳冰《缙云县城隍神记》言“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之,风俗水旱疾疫,必祷焉”(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461页。。可以说,中唐时期南方部分地区供奉城隍神已成风俗。咸通三年(862),刘骧作《袁州城隍庙记》,其中已见“有天下,有祠祀,有郡县,有城隍”(3)(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二,第8427页。文末言“有唐二百四十五祀壬午夏六月三日记”,是为咸通三年(862)。的记述。这种“天下郡县城隍祠祀”的迅速发展,既源于官方对于城隍神的认可,也是农业社会对城隍神功用及神格认识的体现。对于唐代城隍神信仰,前人虽有相关成果,但在城隍神功能、信仰之原因及其文化内涵上尚有不到之处。本文以唐人的文学作品和道经中关于城隍神的记载为基础,对前人较少关注的以上几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唐代城隍神之功能
唐人认为城隍神不仅可以“积阴为德,致和产物,助天育人”(4)(唐)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10页。,还能“俾夫农无水旱,人无夭札。屏绝蛮夷,阜安闾里,护乎封域”(5)(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一《城隍庙记》,第7424页。。城隍神的上述功用承载着民众对其形象的想象与塑造,是城市不断发展和民众在面对灾害、战争而寄希望于神灵的产物。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代的典籍,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祭神文关于城隍神的记载,无疑较之前代(6)按:城隍神较早显灵见记于“(北齐)慕容俨祈求城隍神冥佑”,(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二十《慕容俨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1页。较早为上层祭祀见记于南朝梁“梁武陵王纪祭城隍神”,(唐)魏征《隋书》卷二十三《五行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58页。有了更加丰富的论述,但此时城隍信仰尚处于发轫期,未能形成体系化的义理与文化,普通民众信奉城隍神也是为其经世致用的实用性所吸引。根据唐人典籍所记,归纳城隍神的现实功能如下。
(一)护国佑邦,剪恶除凶
城隍神的护国佑邦功能是其演化为自然神的首要原因。这一基本要素较早见于“(北齐)慕容俨祈求城隍神冥佑”,而唐城隍神延续了这一功能。张九龄《祭洪州城隍神(祈晴)文》提及祭祀城隍神的原因之一是此神能“懿此潜德,城池是保,民庶是依”(7)(唐)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37页。,刘骧《袁州城隍庙记》说为城隍神移建其庙并饰崇以礼的原因,也是“报其固护城池,而福及生人”(8)(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二,第8427页。。此外,唐人还把城隍神当成了军事防御神,段全纬《城隍庙记》说唐军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遭遇蛮寇突然进犯,因城隍神阴灵幽赞之能,城墙得以固若金汤完好无损,敌军撤退,段氏有感,更是祈祷城隍神能发挥“屏绝蛮夷,阜安闾里。护乎封域,富庶乎亿年”(9)(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一,第7424页。的神用。李商隐《为安平公兖州祭城隍文》针对当时五兵未息、城池武备的现状,祈请城隍神能牢记“受命上元,守职斯土”的使命,发挥“守同石堡,护等玉关”(10)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2页。的功用。唐戴孚《广异记》载开元中,当地城隍与韦秀庄共同抵御河神毁城墙(11)(唐)戴孚撰,方诗铭辑校:《广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9-60页。的民间故事更赋予城隍神具有护佑城池、军事抵御的能力。
唐人期望城隍神在护国佑邦的同时还能剪恶除凶,于是唐代城隍在自然神的基础上又演化出具有人格神的功能。如许远“眢井鸠翔,老堞龙撄”(1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百四十五,第3500页。八字《祭城隍文》,不仅是其与张巡固守城池孤立无援的写照,更是透露其希冀城隍神剪除安禄山叛军的心声;李商隐《为怀州李使君祭城隍神文》希望城隍神大发威灵与声势,祈愿“俾犯境者,望飞鸟而自遁;此滔天者,听鹤唳以嘘声”(13)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770页。,在除凶乱的基础上保城池安定,无有川竭与土崩之危。这无疑是将城隍神的职能进一步具体化。
可以说,城隍神的“护国佑邦,剪除凶恶”功能是现实生活在唐代民众意识领域内的延伸,是民众无法满足自我目的与利益时,寄托于城隍神的期盼。当这种期盼得以实现,即所谓神祇显灵时,唐人则会以不同方式予以酬谢。他们或奏请朝廷以史实方式予以记述,如德宗朝李兼被李希烈军顺风纵火袭击,李兼祷于城隍神,风向逆刮,火烧贼溃,李兼请求付史官以答神意(14)(宋)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册府元龟》卷三百九十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4514页。;或以馨香之礼酬神,如李商隐《为中丞荥阳公桂州赛城隍文》记述荥阳公在面对敌军“晦我中军之鼓,溼予下濑之师”(15)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328页。时,祈城隍神而果应,敌军溃败后以庶羞之奠答谢神助;或以重塑真身方式表达感恩之情,如刘骧《袁州城隍庙记》载大中十二年潭广宣洪,士马纷扰,乱军恣其杀戮,脍人心肝,而袁州民众认为自己能脱虎口之难“莫不由神明之阴惠”(16)(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二,第8427页。的缘故,是以大中十四年太守鲁郡颜公祭拜、重修城隍神祠。而城隍神,尤其在战争、战乱中“有灵”时,一旦以人格神方式为民众所祭祀、酬劳,无疑加剧了其自身的知名度与传播速度,筑牢了普通民众的信仰根基。
(二)干霖苏槁,应时朗霁
民以食为天,而雨水关乎农业社会粮食收成好坏。城隍神有普降甘露的下雨及应时朗霁的止雨功能,概是百姓日用功利性及生存的需要。甘霖苏槁,是指城隍能降下甘露苏活枯槁之物。唐人在面对干旱乃至大旱而束手无策时,地方长官履行祈雨职责,像李阳冰《缙云县城隍神记》中记与城隍神约定:五日不雨将焚庙,“及期大雨,合境告足”(17)(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七,第4461页。;李商隐《为中丞荥阳公赛理定县城隍神文》记荥阳公恐无雨影响秋天收成,遂“告于神,神能感我”(18)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540页。而降雨。神既有灵,祭祀者按礼应得雨报祠(19)《通典》一百二十中言“牢馔、饮福、受胙、瘗币血皆同祭社之礼”,见(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66页。,像李阳冰《缙云县城隍神记》言“具官与耆耋群吏,乃自西谷迁庙于山巅,以答神休”(20)(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七,第4461页。,白居易《祈皋亭神文》说“若四封之间,五日之内,雨泽沛足,稼穑滋稔,敢不增修设像,重荐馨香,歌舞鼓钟,备物以报”(21)(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01页。,即属报祠。唐人诗文中反映的赛城隍,如王建《酬柏侍御闻与韦处士同游灵台寺见寄》所言“赛神贺得雨”(22)(唐)王建著,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30页。,羊士谔《城隍庙赛雨二首》其一记“零雨慰斯人,斋心荐绿。山风萧鼓响,如祭敬亭神”(2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704页。,李商隐《赛灵川县城隍神文》《赛永福县城隍神文》《赛城隍文》莫不是酬谢城隍神普降甘露之雨、勿纵旱魃之虐而有丰稔的酬神馨香活动记述。
应时朗霁,是指雨水过量时地方长官通过祭祀城隍,希冀其能止雨晴天。张九龄《祭洪州城隍神(祈晴)文》因嫌雨水过大不止,恐害嘉谷,质问城隍降雨何以无有节制,祈请城隍神放晴,消水灾无令谷物失收。(24)(唐)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十七,第937页。李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记韦良宰在面对大水淹没城郭、洪水注入百川、人见忧于鱼鳖、岸不辨于牛马的现状时,怒言城隍神:若一日不停止下雨,其将要砍伐乔木以焚清祠(25)(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61页。,韦良宰希冀用此类似威胁的激进之法希望城隍止雨。韩愈《潮州祭神文五首》其三言“谨以柔毛刚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26)(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58页。,就是希冀用“柔毛刚鬣”的祭礼以乞晴于城隍神。有学者认为“(柔毛、刚鬣)两个词语在唐代官式祭神文中明显只和‘社稷’观念扣连。反之,虽然柔毛、刚鬣固属大牢、少牢祭物,但在《开元礼》《郊祀录》等礼书中——例如标志以少牢献诸太子、文宣王、岳镇、风师等祭文——都不提及柔毛、刚鬣之名”(27)(香港)冯志弘:《鬼神、祭礼与文道观念——以韩愈〈潮州祭祀城隍神文〉等祭神文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其意本在分析韩愈通过礼法仪式,把城隍神等地方神明纳入儒家体系之中,但其所述也有侧面反映用社稷礼祭祀城隍规格过高之意。实际上,城隍祭祀规格应考虑当时洪水之状况,比如李白《天长节度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中韦良宰的威胁并没有让城隍神停雨,而朝廷没有办法,遂“中使衔命,遍祈名山,广征牲牢,骤欲致祭”(28)(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1361页。,那韩愈面对“淫雨将为人灾”现状时,其使用“柔毛”“刚鬣”之属于“牢”的范畴进行祭祀亦不为过。我们说不管是李白文中提到的“广征牲牢”,还是韩愈用“柔毛”“刚鬣”,都意在体现时人在现实中已无法控制洪涝所带来的灾害,而希冀通过更高层面的祭礼体现城隍神的尊崇地位,以求打动城隍,进而达到止雨之目的。
二、唐代城隍信仰兴盛之原因
城隍神以其现实性功用为唐代民众和文人士大夫所广泛信奉、祭祀,以至开成五年(840),刺史吕述《移城隍庙记》谓城隍之神能已经达到“论功校重,冠彼神祇”(29)(清)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卷二十九,见《全唐文》,第10695页。的程度。城隍信仰在唐代迅速发展,固然与百姓赋予其经世致用的功能有关,但还与上层统治者的承认与敕封,道教对其吸纳,以及民众塑造城隍之神格,密不可分。
(一)官式祭典,尊崇有加
唐人张说首写《祭城隍文》:
维大唐开元五年,岁次丁已,四月庚午朔二十日己丑,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燕国公说,谨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城隍之神:山泽以通气为灵,城隍以积阴为德,致和产物,助天育人。人之仰恩,是关祀典。说恭承朝命,纲纪南邦,式崇荐礼,以展勤敬。庶降福四甿,登我百谷,猛兽不搏,毒虫不噬。精诚或通,昭鉴非远,尚飨。(30)(唐)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第1110页。
张说《祭城隍文》(及其他人祭城隍文)无论是在范式上,如开头的“年月日”“祭祀者”“清酌之奠”(其他祭城隍文言“清酌酺醢之尊”),结尾的“尚飨”“所飨”,还是昭告内容、达到效果的论述上,皆有典可查。唐人祭城隍的祈神典仪、祝文内容依照开元三年(715)颁布的《大唐开元礼》中“诸州祈社稷(县祈附)”“诸州禜城门(县禜附)”条,是以张说言城隍祭祀是“人之仰恩,是关祀典”。像前文牛肃《纪闻》说“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李阳冰《缙云县城隍神记》言“城隍神祀典无之,吴岳有之,风俗水旱疾疫,必祷焉”,意在针对城隍神尚未被纳入祀典之中且盛行于吴越之地的民俗而言。至于李白《天长节度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中韦良宰说城隍“此淫昏之鬼,不载祀典,若烦国礼,是荒巫风”(31)(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1361页。,当有所指。首先此句话前叙述了“中使衔命,遍祈名山,广徵牲牢,骤欲致祭”的事实,对此韦良宰是“盱衡而称”,所谓“盱衡”,注者言是“举目扬眉”或“举眉大视”,即扬眉瞪大眼睛,表恨意。其次,此句前有两句是“今皇上明圣,怀于百灵”,意即城隍神已纳入祭祀范畴。结合前语可知,“如果不载祀典而是烦了国礼”是以反语的方式意在讽刺城隍神享受祭祀却不为民服务,表示对其不满,抒发自己愤恨;而作为刺史及祭祀者,地位与城隍对等或稍高,则是用此语来彰显自我之能。
从唐人文典尤其是唐文人士大夫祭城隍文来看,城隍神涉及荆州、洪州、宣州、苏州、鄂州、宋州、广州、潮州、袁州、兖州、桂州、抚州等,但仍以南方为主,这是地域环境、社会风俗、现实需要所决定的。至咸通三年(862),刘骧《袁州城隍庙记》所述“有天下,有祠祀。有郡县,有城隍”(3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二,第8427页。,意指天下祠祀,有郡县即有城隍,说明城隍祠祀不仅多,且祭祀的规格在郡县级。所以有学者认为城隍神多是北宋时期祭祀遍布全国,由民间淫祀进入国家祀典(33)李申:《城隍神与古代政治》,《科学与无神论》2017年第6期。的论断,概商榷处有二。一是城隍神祭祀若按唐人所述晚唐已遍布天下,二是民间淫祀进入国家祀典并非一步到位,有一过渡期:即“是关祀典”。加之,晚唐帝王对城隍神的敕封,又使其地位得以尊崇,如张建《华州城隍神济安侯新庙记》记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幸华州,华州城隍厉声训叱行刺的韩建,城隍神因救驾有功,次年被封为济安侯(34)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历代碑志丛书》第七册引“(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一百五十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34-535页。,至五代陈致雍《议废淫祀状》言“准中书省札简检:诸州城隍神封为公侯,合乎典礼”(35)(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七十三,第9134页。此外,如后唐清泰元年(937)十一月,敕杭州护国庙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顺义保宁王(王溥《五代会要》卷十一《封岳渎》,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7-148页)。乾祐三年(950)八月,以蒙州城隍神为灵感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三《汉书五·隐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57页),都是城隍封神例。。可以说《大唐开元礼》的颁布,使其由地方淫祀变为官方祭神。城隍神随着祭祀地域的不断扩大,士大夫的广泛关注,加之帝王的优渥恩宠,其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直至封候进爵。如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普通民众的信仰选择。
(二)道教吸纳,神格提升
唐初,城隍神已被道教纳入其体系之中。孙思邈《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卷三十六“治疟符”有治理小儿疟方,“人窃读之曰:一切天地,山水城隍,日月五星,皆敬灶君,今有一疟鬼小儿骂灶君作黑面奴,若当不信,看文书。急急如律令”(36)(唐)孙思邈撰:《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三十五,《道藏》第2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9页。,此是道经中有关城隍最早的可靠记述,虽只是简要提及城隍,但至少证明唐初道教已将城隍神纳入其体系之中。学界考证唐道士编集的《赤松子章历》,其中“谢先亡章”有言“都谢城隍社庙神祇”(37)(唐)佚名编:《赤松子章历》卷四,《道藏》第11册,第206页。,体现了阴司城隍为阳人除去灾恐的职事与能力。晚唐杜光庭《蜀州孟驸马就衙设销灾迁拔黄箓道场词》有“城隍社庙,里域真官,密享神功,永居福地”(38)(唐)杜光庭撰:《广成集》卷五,《道藏》第11册,第256页。文辞,因黄箓斋有“拔九祖罪根”(39)(南朝宋)陆静修:《洞玄灵宝五感文》,《道藏》32册,第620页。之功用,是仅次于保镇帝王的金箓斋、保佑后妃公侯贵族的玉箓斋,此文中超拔尚需祝祷城隍,可知城隍神在晚唐道教神祇中的地位与作用。所以如张洪泽先生所言的“城隍神被纳入神灵系统,南宋时期的道经中,已经有城隍神的记载”(40)张洪泽:《城隍神及其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就显得有些不太准确了。
道教还完全吸收城隍降雨之功能,杜光庭《道门科范大全集》中祈雨雪斋仪中就是祈请城隍(41)(唐)杜光庭删定:《道门科范大全集》(卷十二至卷十五、卷十七),《道藏》31册,第787、788、791、793、796页。。丁常云认为:“杜光庭删定的《道门科范大全集》祈求雨雪斋仪中,启请神灵之一,即为城隍社令。此为道书中有关城隍的最早记载。”(42)丁常云:《道教的城隍信仰及其思想内容》,《中国道教》1997年第3期。丁先生所言大体不差,但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城隍社令”在唐代不是一个概念,“社令”是土地神,“城隍”已经从土地神中抽离出来演化为城市保护神;二是唐代道书中有关城隍的最早记载是《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再者是太玄部表奏类原题李淳风注的《金锁流珠引》。但可以肯定的是杜光庭所说“祈城隍雨雪”,为道书中有关城隍雨雪的最早记录。至宋代,道教中城隍神神位进一步上移,如“一国家祈求雨泽,或久晴不雨,或螟隍灾虫为害,……申诸天星府,五岳四渎四海九江龙神,牒本属城隍”(43)(宋)元妙宗编:《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一“祈求禳请”,《道藏》第32册,第54页。,其中“国家祈求”说明了城隍神已被纳入了国家祀典之中,“牒本属城隍”则体现了城隍神在司雨龙神之上的尊贵地位及权利。
既然城隍神被纳入了道教系统之中,亦当接受道法高超的道士乃至道教天神的监督与制约,如南唐沈汾《续神仙传》记唐道士宋玄白到抚州,逢抚州百姓天旱祈祷城隍,城隍不雨,州人请宋玄白祈城隍下雨,宋玄白却飞钉城隍神双目,此举引起了刺史的怪罪,欲要治罪宋玄白。(44)见《太平广记》卷四十七辑录此条,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十七《宋玄白》,第294页。若站在道教角度,可知晓宋玄白“飞钉城隍双目”意在通过小罚城隍神,来警诫其享受祭奠却不作为的后果。此外,唐前及唐代道书未有以道门律令方式责罚城隍,至五代宋初道士饶洞天定正、宋道士邓友功重编的《上清骨髓灵文鬼律》则有城隍有过“具奏北极取旨,三官纠察,关驱邪院施行”(45)(宋)邓有功重编:《上清骨髓灵文鬼律》卷上,《道藏》第6册,第911页。的具体措施。
应该看到,城隍神在唐代被纳入道教之中,丰富了道教神祇范畴,在信奉的人数上有所增加,扩大了道教的影响,将道教的内涵与外延扩大到都市、乡村的底层人民心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在道、佛抗衡方面亦有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唐代城隍并没有“宗教的观念与思想、情感与体验、行为与活动、组织与制度”(46)吕大吉著:《宗教学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6页。,尚未有严密的结构与理论支撑,亦无哲思与义理而言,其世俗功利化的内涵不仅冲淡了道教宗教信仰的意蕴,而且拉低了道教的整体理论水平。
(三)公忠正直,阴神宰司
唐人祭文中多处提及城隍神公忠正直的神格,张九龄《祭洪州城隍神文》赞城隍“精灵以秉,正直攸好”(47)(唐)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十七,第937页。,认为正直才是城隍神所好;赵居贞《新修春申君庙记》总结城隍神府(春申君庙)是个“宜正名于黄相,削讹议于城隍”(48)(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六,第3004页。之地,即言春申君作为城隍神能明辨是非、主持公义、消除耍赖之论;白居易《祈皋亭神文》盛赞城隍神具有“聪明正直,洁靖慈仁,无幽不通,有感必应”(49)(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十,第901页。的品性与神通,上述种种旨在通过赞美城隍神公忠正直品性以求悦神,达祭祀之目的。更有甚者,唐人在恭维城隍神同时,言语间透露出人神之间的交易,李商隐《为中丞荥阳公祭桂州城隍神祝文》希冀“(城隍)神其保兹正直,歆彼馨香。聿念前修,勿亏明鉴”(50)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552页。,刘骧《袁州城隍庙记》祝祷“惟神聪明正直,我公致力于神,神宜飨公之德”(5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二,第8427页。,无不体现时人的世俗功利性。
唐人祭文中,如前文所述,张说《祭城隍文》言城隍“积阴为德,致和产物,助天育人”, 张九龄《祭洪州城隍(祈晴)文》说人神之间“道虽隔于幽明,事或成于表里”,都意在阐述城隍神有冥佑生灵之职责。至宪宗时人段全纬,其《城隍庙记》已有“阳之理化任乎人,阴之宰司在乎神”(5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一,第7423页。记述,此虽有神道设教之意,但更多强调的是阴阳司命各有职责。唐人小说中亦有体现城隍神作为阴司公平审案的例子,如牛肃《纪闻》记载:开元末宣州司户死后见城隍神,自言平生无罪被枉录后,城隍神令其离去,司户苏醒而言之(53)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三辑录此条,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第2400页。,说明城隍神公正无私的审案能力。再如,晚唐王毂《报应录》载:唐洪州司马王简易,一夕做梦为鬼吏追拿,因修善之故不该死亡,被城隍神放回。后五年,王简易因致毙妙龄童仆事,被拘至冥界,其妻诘问僮仆地位低下怎敢诉讼城隍,王简易说“世间即有贵贱,冥司一般也”(54)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四辑录此条,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四引《王简易》,第873-874页。。作者意在指出尽管王简易修善,却致僮仆毙命,虽能逃脱世间法律,但逃脱不了阴司城隍公正的制裁。
唐代城隍最迟开元末时就具有了阴司审判的能力,概会形成类似官府式的结构,段全纬《城隍庙记》论述阴阳司命各司其职即是证明。阴司城隍既有如此体系,就要遵循官吏铨选和管理制度,如唐尉迟枢《南楚新闻》言咸通中,巫峡尔朱氏因做生意连年在当地白马神祠祷告,在一次祭祀中,神告尔朱氏:自己因为有德于三峡老百姓,被上帝升迁为湖南城隍神(55)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二辑录此条,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二引《尔朱氏》,第2469页。,这是一般神祇晋升为城隍神的故事,也侧面反映了唐城隍神的地位之尊。唐城隍神“公忠正直,阴神宰司”承载着民众对其无党无私形象的想象与塑造,是现实治理在民众意识领域之内的延伸,代表了唐人对真善美的期盼,符合老百姓善恶有报的心理预设。同时,城隍神为唐人提供了自我倾诉的途径与申诉的对象,时人希冀借用神灵的力量解决现实中的难题。
三、唐代城隍信仰之文化内涵
唐人文学典籍、道经书目对于城隍神的关注,尤其是唐代文人学士的祭城隍文,将原属于潜文化范畴的朴素民间信仰,推向了为士大夫阶层、帝王所熟知的显文化领域,期间城隍神格不断上升、地位日趋重要、内涵逐渐丰富。唐代城隍信仰,反映了唐人的生活现状、习俗文化、精神面貌,体现了唐代的世风、时风与士风,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良吏—鬼雄—城隍”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墨子说:“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也。”(56)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43页。具有人格神、社会神的城隍即是由人死而为之,唐人赵居贞《新修春申君庙记》记其游览死后已成城隍神的春申君庙时,在回顾春申君在世时烈烈功勋后,有感而重修神庙。(57)(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六,第3004页。刘骧《袁州城隍庙记》叙述灌将军庙的前世今生,盛赞灌将军死后作为城隍神的种种福德。(58)(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二,第8427页。《通典》卷一百七十七《州郡七·襄阳郡·谷城县》亦有引“梁末鲍至《南雍州记》‘城内见有萧相国庙,相传谓为城隍神’”(59)(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第五册,第4676页。的记载。春申君、灌婴、萧何莫不是在世功业卓著,死后为百姓尊崇,继而成城隍神的典例。这种“生作人杰,死亦鬼雄”的文化传统影响着唐人,如唐戴孚《广异记》“张琮”条记永徽初南阳令张琮为鬼刻铭“身殉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60)(唐)戴孚撰,方诗铭辑校:《广异记》,第67页。,即是此观念继承。唐宋时期,“良吏—鬼雄—城隍”模式,不仅数量增多,且时间大大缩短,像北宋赵与时《宾退录》中记述的唐代庞玉实、焦明、应智顼、游茂洪、白季康等人(61)(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4页。,或是以忠义著称,或是有功于民之良吏,至少在赵与时之前已成为城隍神。
从上层的角度来说,统治者将“良”“忠”的价值观念浸入城隍神格之中,已经蕴含了尘世间的道德原则,通过凝结社会群体意识,影响人们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对臣子起到劝诫、儆效之作用,对普通百姓起到安稳民心、政心之功效,甚至缓解民众心理冲突。从下层角度讲,由“良吏”到“鬼雄”,能反映老百姓善恶有报的心理追求;由“鬼雄”到“城隍”,则体现了普通民众对于生前死后公平正义的美好寄托。唐人的“造神”,加剧了城隍信仰的复杂性,城隍逐渐以道德化、礼教化的人格神取代了朴素的自然神,在将人们精神引入超自然状态后,又把神秘感落实到人格神的实体感知上。如此,更加巩固了“良吏—鬼雄—城隍”的发展及运转模式,城隍神又成为统治阶层驭官牧民的一种方式,成为皇权更加集中的一种手段。
(二)唐代士大夫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唐文人士大夫祭城隍文很难表明其对城隍神的信仰程度,有学者认为祭祀者(地方长官)“或是为了履行义务,或是为了取信于民,表明自己尽忠职守,因此官方的参与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62)郑士有、王贤淼:《中国城隍信仰》,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5页。,亦有认为“多是为祈雨而行,还不是必需的例行公务”(63)李申:《城隍神与古代政治》,《科学与无神论》2017年第6期。。实际上,文人任地方官祭祀城隍本就是其职责范围的事情,因为祈雨相较于其他公务而言,或非是一种常态化,且在人力非所及的情况下,依照儒家礼法的形式祈请城隍,于公而言是为朝廷解难,于私而论体现其履职担当,于民而说是突出其垂范表率心系苍生,这是士大夫“关心民瘼精神”及“在其位谋其政”的性质所决定的。
当干旱不雨,李阳冰与城隍神约定五日不下雨就烧其庙;当淫雨不息,韦良宰命令城隍若一日不停雨即伐乔木烧清祠。李阳冰、韦良宰所言几日不雨、不晴便要焚祠、烧庙,体现了士大夫的与神相抗的精神。韩愈在《袁州祭神文三首》(其一)质问城隍“刺史虽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无令鳏寡蒙兹滥罚”(64)(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第360页。,杜牧在《祭城隍神祈雨文》质问城隍,若自己治政不佳,可惩罚其人,为何降旱荼毒百姓?又在《祭城隍神祈雨文(第二文)》再次申辩自己虽愚钝,亦无过,纵有过,杀亦可。何苦不雨以绝民命。(65)吴在庆撰:《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02-903页。韩愈与杜牧的质问城隍之语,虽然在主观上有树立勤政爱民、安平抚慰百姓的目的,但客观上却是儒家“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的延续及帝王罪己内容(66)如唐高宗言:“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8页。的下移,体现了儒者关注生命、关注社会的政治责任与担当精神,及在将政治责任转化为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充满了儒者的批判意识。是以有学者说“说明当时人的思想中,人格是高于神格的”(67)王涛:《唐代的城隍信仰与唐中后期南方城市的发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有一定的道理。唐人的这种精神,尤其是自我罪己意识,对底层乃至整个社会稳定起到了有效作用;对神灵的批判意识,体现唐人不媚神、保持人的独立精神,这是其他朝代的文士很难与其相媲美之处。
(三)唐代文学内涵的丰富与扩充
唐代城隍信仰沟通了民间文化与士大夫阶层为主导的文化,士大夫将其所见所感录之于笔墨,见之于诗歌、祭文、小说之中。杜甫《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赐书夸父老,寿酒乐城隍”(68)(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56页。、羊士谔《城隍庙赛雨二首》“积润通千里,推诚奠一卮”(69)(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三二,第3704页。,以诗歌的方式反映报城隍神降雨之礼及得雨后人们的喜悦之情。唐士大夫根据时代发展、现实需要,以文的方式祭祀城隍文,将民众赋予的城隍神神性、功能予以记述、加工,较之原先单纯的民间信仰有了雅化,不仅反映了城隍的神迹、祭祀者的心迹、赛城隍的人迹、城隍在世为良吏的事迹,还再现了上至帝王、中至宰辅、下至百姓的社会生活风貌,展现了唐代民俗、宗教、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景象与实况。小说中对于城隍神的记述,反映了唐代民众对于城隍神的接受与信奉,及城隍神对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至于道经、小说中反映道士与城隍神之间的关系,于神化道士、抬高道教、传播道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道经,对城隍神的叙述,语言上平实朴素、不饰辞藻,内容上以反映城隍神祇功能及祈请目的为主。
城隍神的加入,拓宽了唐代文人的关注视野,丰富了文学创作祭神文的范式与内容,丰富了唐代文学内涵。唐人关于城隍神的文献记载,也侧面反映了唐代尤其是中晚唐时政、君政之艰辛,封建士大夫、官吏的勤政形象,以及民众在灾难、战乱时期心理状况。经过唐代不同样式文学对于城隍神的塑造,城隍的神格得以发展和提高,后世所具有的功用于唐代基本定型,为民服务且惩恶扬善、公平正义的实用神形象已告形成。城隍神所具有的品性是唐人社会意志、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时代特色的反映、精神烙印的体现。唐代城隍神被纳入道教范畴,增加了其为神之功用,使城隍神内涵得以彰显、定型,对后世影响深远。
结 语
唐代城隍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历史根源、社会基础、信仰之因。唐城隍“不过是超人间、超自然的异己力量的人格化”(1)荣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为中心》,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年,第339页。的显现,其所具有的“护国佑邦,剪恶除凶”“甘霖苏槁,应时朗霁”之功用,是唐人赋予其美好的寄托与希望。唐代城隍从最初的淫祀发展至“是关祀典”,地方上以官方祭祀的形式对城隍予以承认,而晚唐帝王敕封其公侯爵位,更是增加了城隍的政治地位。但是,城隍神地位虽不断尊崇,受其在过渡阶段的历史格局所影响,却始终在唐代未入国礼范畴。唐代城隍祭祀地位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发展状况及统治者的决策,力图缓解民众的心理冲突,这种民间与政府的互动无疑巩固了城隍神信仰的地位。城隍神被道教纳入系统之中,被赋予了消灾解难、延福超拔之功能,城隍神的神祇地位较之以往又有一定的提高。城隍神被百姓赋予的公忠正直、无党无私的品性更是体现唐代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和赏善罚恶、善恶有报的心理期待。统治者对城隍神的承认、道教对城隍神的吸纳、民众对其赋予的种种功能及神格,一定程度影响了百姓的信仰取向与道德价值。当城隍神的影响更大时,它也成为上层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管控普通百姓的方式之一。
唐代城隍信仰,与其说是信仰,倒不如理解为民众对于百姓日用的朴素追求,这根源于唐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苦难处境无法排遣的折中立场。无论唐代文学以何种题材记述城隍神,其最终目的是关注现实、关注民生,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玄宗朝赵居贞《新修春申君庙记》“神必依人,人兹望福,依无所据,福安来哉”(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六,第3004页。,阐述了人与城隍神之间的关系:神靠人祭祀,人靠神致福,两者互惠互利。正是此种关系,我们才会看到祭文中出现呵斥、恫吓城隍之现象,保持唐人的独立性而不谄媚于神的精神。唐人在承认城隍神的基础上,秉持着“阳人理化,阴神宰司”的理念,追求着阳政与阴司共治一方领土,希冀呈现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这在唐祭文中广泛提及(3)如刘骧《袁州城隍庙记》“甲马安而士卒和,司局宁而官僚泰,千里之内,樵童牧竖,农夫织妇,识君臣少长之礼。名儒秀士,时时间出。”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二,第8427页。,从而赋予了唐代城隍神信仰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