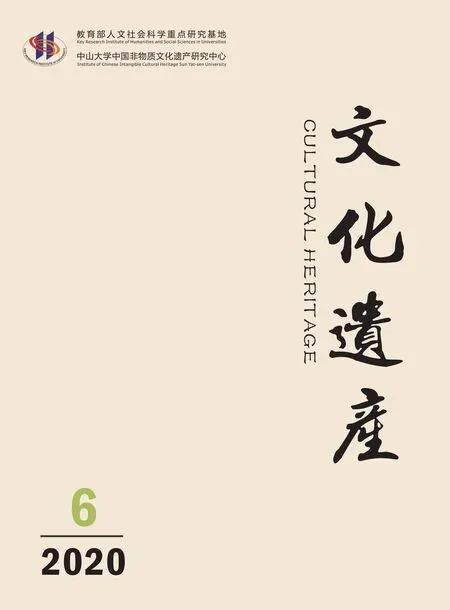在规范与认同之间:关于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标准的探讨*
王 琨
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讲述、传承的“活态”文化,集民间智慧、民俗心理、地方性知识于一身,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学术研究和生活实践意义。与其他“非遗”门类相比,民间文学的“标准化”保护似乎一直都是绕不开的难点。具体来说,因其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和变异性等特质,就意味着民间文学文本的多样化和异文的不断产生,而且它不像“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非遗那样以具体实物为依托。但其实在“非遗”介入之初,民间文学的“标准”就已经存在,比如申报项目的命名、对传承人资格的甄选与级别的认定等等,越是具体的工作,就越需要某些“标准”的介入。因此,想要解决“民间文学类”非遗申报与保护的标准制定及介入问题,就必须在具体的实践中结合学术史发展与地方性知识,实现规范化保护和“活态”传承的动态平衡。
一、不同视野中的“民间文学”
“分类,是研究者的需要。”(1)林继富主编:《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1页。当人们使用“民间文学”这个概念,就意味着对学界分类系统的某种接受与认同;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他们本来就自在地生活于“民间”,传播与传承着各种口头叙事;同时在非遗的框架下,那些被纳入评价体系、收入名录并获得官方认证的“民间文学类”非遗既源自民间,但又与学术界的分类有所差异。
(一)学术的界定与分类
我国学界对“民间文学”的学科化、系统化研究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北京大学发起的征集歌谣活动为开端,以《歌谣周刊》和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为阵地,诸多著名学者都参与其中,其中对“民间文学”的定义、分类等问题也是一直被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议题。
周作人受人类学派的影响,运用叙事与信仰相结合的视角对民间文学中的几大亚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古之时,宗教初萌……盖约言之,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为文学也。(2)周作人:《童话略论》,载《儿童文学小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页。这里的“世说”可以理解成如今学术分类中的民间传说,“童话”则更接近于“民间故事”。虽然他认为这三类民间叙事之间存在体裁上的差异性,但它们皆出于“民间”,是广大民众在信仰世界和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的产物。赵景深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三者间的生成关系,认为“神话”和“传说”是“严肃的故事”,而“童话”则是由此二者转变而来的“游戏的故事”。他也明确指出了这些“民族文学”的特点,即“由民族全体创造出来的,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并且是口述的,不是笔书的……”(3)赵景深:《童话概要》,上海:新北书局1927年,第10-12页。容肇祖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去探讨“民间的故事”,在他看来,“民间的故事”可以分为充满幻想性的给人幼年时期予以熏陶的“童话”、茶余饭后的“笑话”“其他俗传的史事及神话”(民间的掌故谈)等。(4)容肇祖:《广州民间故事序》,《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7期(原《民俗》第77期),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3-5页。。其他还有如顾均正提出将“民间故事”分为“童话(即含有神异分子的)、传说、故事、寓言、趣话、事物来因故事、地方传说等七大类”(5)顾均正:《关于民间故事的分类》,《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2期(原《民俗》第19-20合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70-71页。,实际上即是采用了类似于如今“广义的”民间故事的概念;总之,早期学者大多受到德国、英国、日本等学术成果的影响,结合搜集而来的文本资料进行研究,试图找到契合我国本土的概念范畴与研究路径。虽然当时已经有“民间文艺”“民间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说法,但还没有形成较为明晰的学科性定义与分类体系,不过毫无疑问,他们普遍认为民间口头叙事是广大民众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创作、播衍与传承的,是属于“中国民俗学”的珍贵资料,也是属于全民族的宝贵财富。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普遍采用了“民间文学”的概念,逐步确立了具体体裁分类,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提出:“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劳动生产、日常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操,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6)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页。并对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及其细类等进行了具体的划分,还特别明晰了其“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与“传承性”的基本特征。另一本较具权威性的教材是由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其中将“民间文学”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生活语境里集体创作、在漫长历史中传承发展的语言艺术。它既是该民族生活、思想与感情的自发表露,有关历史、科学、宗教及其他人生知识的总结,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也是该民族集体持有和享用的一种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生活文化。”(7)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与之前钟敬文的版本相比,这一定义强调了民间文学的“生活语境”、将其作为 “活”着的文化现象、世代传承的文化现象来看待。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使用“民间叙事”“民间叙事”“口头叙事” “口头传统”等概念,研究对象在诸如神话、传说、故事等传统文类之外,亦扩展到灵验故事、都市传说、谣言、个人叙事等领域。
(二)民众的认知
即使近些年“民俗越来越明显地被正面对待,被视为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8)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但如果询问一个普通人究竟什么是“民俗”、什么是“民间文学”,人们大多也只能给出具象的、源自日常生活的描述性说法,即使是能够讲述上百则故事的“故事家”,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或是完整的定义,很多时候他们会这么形容:“听老辈讲的故事”“看家段儿”“就是咱们平常讲的那些呗”;同时他们对自己讲述的内容和体裁也有一套自己的认知系统,比如在辽东地区人们最常讲述的是精怪故事及与之相关的灵验传闻等,这些口头叙事被大致划分为“故事”“真事儿”和“可能是真事儿”三类,实际上这是从个人、社区和集体的经验出发,反映出当地民众对日常生活和信仰实践的态度与表达。
近年来随着各种调研、考察、评比活动的介入,一些活跃的、有经验的讲述者也会总结出自己对于“民间文学”的看法。例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民间故事”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振华,作为乡里有名的“故事大王”,他不仅对自己的讲述技巧非常自信,也因为与相关研究者、非遗工作者建立了长期联系,故而更为了解非遗的相关政策。当他与辽东另一位故事家查树源同时被采录时,他曾这样评价对方:“我觉得他可能不符合你们的要求,你看他事先还整了一个大厚本,讲一讲还得瞅两眼。这要是我,别说咱们眼睛不行,就是给我我也不看。那时候省里来人,我也这么说的,你们就随便问,我能闭眼睛讲三天三夜不重样儿的。”(9)讲述人:黄振华,辽宁省抚顺市红透山镇上大卜村人;访谈人:王琨;时间:2015年7月24日;地点:黄振华家。从中不难看出,他认为作为非遗的民间叙事必须具备口头性,只有脱离文本进行讲述的故事家才可被认定为“传承人”。
(三)非遗的甄选与认定
民间文学类非遗与上述对于民间文学的定义与认识又有所区别。在学术层面上,“民间文学”包括: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谚语、俗语、谜语、歌谣、民间说唱、民间小戏等。而作为非遗保护对象,民间说唱被纳入到“曲艺”类;民间小戏则被纳入到“传统戏剧”类。具体来看,通过考察国家级非遗名录可以发现,一些项目因为自身特质兼容多种体裁,其实根本无法被划分到特定的亚类。比如“苗族谷歌”,它可以是讲述万物起源的神话,也可以是描绘族群迁徙的史诗;又比如“满族说部”,本身集合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长篇叙事诗等,并常常是韵散兼具的。而在名录中的民间文学大类下,“传说”大约占了总数的一半,这显然与实际操作者在名录申报和评审过程中所依据的一些特殊标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保护标准:在规范 与认同之间
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就是对保护对象的鉴别与甄选。具体来看,一是项目内容,需要判定该项目是否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是否具有代表性;二是针对传承人,需对其原生性、传承性、代表性等进行资格判断。由于“非遗”本身是多重力量博弈的场域,既有“自上而下”的标签,同时亦有“自下而上”的反思,所以,只有“摒除了先验的价值论之类非科学的表述,而采用中性的形态学来概述”,才“显得格外客观和通融。”(10)陈勤建:《回归生活: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页。
(一)从“民间文学”的根本属性出发
虽然“民间文学”是一个不断被归纳、总结的发展性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被无限扩大。例如冯骥才、莫言、迟子建等作家创作的小说具有深厚的乡土情节,甚至也会直接加入民间叙事,但是其创作过程和传播路径依旧不符合集体性和口头性的特质。又比如当今盛行的网络文学,当一个文本(段子、跟帖)被创作出来后可能被不断改编,从而形成类似集体化的文本再生产,这种似乎可以被纳入到“民间”的范畴,但是民众对其的真实认同感究竟如何、其原创性和传播的具体路径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1.地方认同感是关键
当谈到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和变异性等特征的同时,都不能忽略其背后还存在着一个“认同性”,即文化的持有者会对文本进行选择与判断,愿意去讲述、传播和传承某些特定的内容。就好比前面提到在非遗名录中占据大半江山的“传说”,它之所以受到如此热待,与其自身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地方民众的认同不可分割。柳田国男在对传说的界定中曾指出:“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总有个灵异的圣址,信仰的靶的……”(11)[日] 柳田国男著,连湘译:《传说论》,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在乡土社会,人们对家乡的情感往往会附着于具体的地方风物与历史名人身上,也就是那些最具有地方文化色彩的“传说核”以及“箭垛式”人物。在具体的讲述活动中,民间传说也更具有当下性与地域感,一个地方东边的这座山、西边的那条河都可能衍生出动人的传说文本,让民众产生真实亲切的感受。反过来,也因为有具体的风物存在,才在历史演进中不断推动着传说情节的发展与传承的延续。比如最早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白蛇传传说”,在其漫长的历史变异中始终离不开杭州的雷峰塔、镇江的金山寺。又比如同为“四大传说”之一的“梁祝传说”,民国时期的《民俗》周刊用了九十三至九十五期作为研究合辑,其中钱南扬、冯贞群等人皆是根据具体的地名、寺庙、墓冢等考据出其主要情节和母题的流布主要集中于宁波和宜兴等地(12)参看钱南扬:《祝英台故事绪论》,《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8期(原《民俗》第93-95合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冯贞群:《宁波历代志乘中的祝英台故事》,《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8期(原《民俗》第93-95合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206页。,时至今日,宁波在“申遗”过程中亦是将西门十里外九龙墟的梁祝庙和坟墓作为重要依据。
2.体裁是细化甄别的有力工具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叙事的体裁往往是流动的,其边界的模糊性也为具体的保护工作带来了困扰。在辽宁大学从事相关研究多年的江帆教授曾言:“很多时候你面对的材料是庞杂无序的,讲述者自己也无从分辨,比如他会给你讲东北抗联的故事,时间、地点和人物都说得特别清楚,回去一查也确实都差不多,但是要注意的是,这是属于口述史的范畴,是史料,这里面缺乏艺术化的表述。”(13)根据笔者2020年11月12日对江帆教授的视频采访整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遗就要放弃体裁,相反,在很多时候它反而能成为我们甄别叙事文本属性和价值的有力工具。以上面提到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满族说部”为例,尽管它本身融合了民间文学的多种亚类,但运用体裁分析,仍旧可以发现其与单纯的历史文本、书写文本间的差异关系。虽然对照“满文旧档”等史料可以发现,在“满族说部”中留存着许多关于重要历史事件和各类历史细节的记录,包括从女真各个部族的战争到人参的保存方法等,但其主体部分,依旧是以民间口头叙事文本为主,并充满着各种浪漫化的想象与艺术化的表述。比如其中的《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14)参看富育光《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在展现后金崛起与清王朝初建这段历史的同时,更是以唯美的爱情主线,着重刻画了一个完美又悲情的女性形象,并对诸如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帝王英雄做出了有别于正史中“高大全”形象的戏说与演绎。实际上这也正是民间文学的魅力所在,它让沉默的底层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与评价,也对所谓的“被书写的历史”进行解构与重释。
(二)保护传承人的在地性与多样化
在非遗保护中,传承人的甄选与培育是关键。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非遗传承人,学术界已有相应的共识。比如在社区内具有代表性、公信力和影响力,具有主动的交流意识和培养后继人才的能力,既能扎根传统、又能在时代变革中保持活态存续的生命力等。(15)参考刘锡诚《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方式》,《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安德明《以社区参与为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黄涛《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再具体一点,在对民间故事家的认定方面,从讲述数量上可以分为50则级、100则级、数百则级;从质量上则要求其讲述活动有较大的影响、拥有较高的讲述技巧以及较为清晰的故事来源与传承线路。(16)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83页。不过作为文化的持有者,传承人也存在着非均质化的特性,即在符合“大框架”的前提下,不同地区、年龄、族群的演述者、传承者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不能简单粗暴地进行“一刀切”式的判定与评价。
1.在地性
所谓“在地性”可以理解为传承人与其所在的地域文化间的互利共生关系,在他们的演述中离不开自己生活的“这一方水土”,他们在传统中吸收养料、锻炼技能,同时也不断展示、传承和对外输出传统的美与意义。
还是以辽宁省的黄振华为例,他大体属于“百则级”的故事家,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辽东山区,不仅擅长讲故事,还能组织节庆秧歌、主持白事(丧礼),是附近村镇中数得上的“能人”。在他的讲述中有一部分接近于经验性叙事,如以其家族成员为主角的《黄老六打熊》《黄老六救人不图报》《石磙子成精》(17)参看夏秋主编《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等等,其中都蕴含着家族史的背景。在“黄老六”系列故事中,故事的主人公虽然是其祖父,但其遭遇的事情往往具有超自然色彩,不是在下雪天遇到了鬼打墙,就是在打猎的时候被狐仙教训了一顿,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讲述的“根”依旧扎在辽东地区将萨满教、佛道教、四大门等融于一体的信仰文化中。而《石磙子成精》的男主人公——一个卖布的“老西儿”(山西人)虽然是其父母的好友,但是他在转述这件“亲身经历”时早已加入了各种各样的“插叙”,比如讲到石磙子成精是因为被滴上了中指血,他就会接着讲一段关于中指血的解释说明,比如门插成精走路、扫帚变成大姑娘等。因此这类故事的重点并不是白描个人生命史和家族史,而是在讲述精怪与人类的关系。其中所谓的“亲历”“真事”经常是一种叙述策略,将文本打上真实的标签,以此来吸引听众、增强故事的可信度与传播力度。因此非遗保护所关注的,并不只是他所讲述的内容,而且也需要尊重他这种独特的讲述风格,并注意到那些看似闲笔或细节的微末处,因为它们往往最能体现故事家、民众对区域文化以及自身生活场域的认知与认同。
2.多样化
翻开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不难发现其中对“故事家”的界定总会强调其生活在前现代社会,身上承载着“纯粹”的乡土传统,诸如“他们生活于闭塞的乡野”“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没上过学”“不识字”“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等等。不能说这是一种绝对的浪漫化想象,事实上当时发现的许多故事家、故事村等的确如此。比如辽宁沈阳朝鲜族故事家金德顺能够讲述150多则故事,她出身社会底层,还被迫当过童养媳,其传承路线主要围绕在家庭内部,且多是从母亲、祖母、外祖母、姑母等女性亲属处习得;(18)裴永镇整理:《金德顺故事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6页。又比如辽宁新民故事家谭振山能够讲述800多则故事,在被“发现”之前一直务农,小学文化,传承路线集合了家族和地缘传承。(19)江帆采录整理:《谭振山故事精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想要找到这类“典型故事家”只会越来越难,如果我们不能重新审视和制定与时俱进的标准,那么今后的很多民间文学类非遗就可能会面临消亡的命运。
难能可贵的是,近年来学术界和非遗保护部门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业已将部分原来被忽视、过滤掉的潜在传承者纳入到了保护名录中。比如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满族说部》的代表性传承人富育光,一共掌握了18部“说部”,其中既包含家传,也有他在东北各地收集整理来的。而除去讲述者、收集者的身份,他还是一名资深的“满族说部”研究者,对文本主题、地域分布、演述风格、分类体系等都有一定的研究(20)参看富育光《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富育光《满族传统说部的传承与保护》,《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如果以传统的标准来看,他带有明显的精英和学者属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多年来他不仅为收集整理满族说部材料四处奔走,还有意识地寻找和培养传承人,与相关研究者、政府工作人员都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可以说他在成为传承人之前就已经深谙非遗政策,并对非遗保护做出了积极响应,事实上,这样的传承人更具主动性,能够更透彻地理解国家的文化政策,也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在国家、地方与民众的多重力量博弈中推进保护项目本身的发展。
像富育光这样的传承人绝不是个例。辽宁省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则亭、何钧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树铮等都有较高的学历背景,兼具“口头讲述”和“笔头书写”的双重能力。对此高荷红等学者专门提出了“书写型传承人”的概念。(21)高荷红:《“书写型”传承人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4年第1期。其实不论是所谓的“精英型”也好,“书写型”也罢,只要他们没有脱离“民间”,愿意去讲述、传播和沟通,并能够得到社区内民众的认同,他们就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传承人并得到政府的认可。
总之,在对待传承人的问题上,不能死守某些“理想型”不放,特别是在这个传统与现代不断碰撞的年代,要想真正做到“活态”传承与保护,那么就要创立、使用更为具体、灵活的标准。
三、标准化与可持续发展
刘锡诚先生曾说:“民间文学是一个最与物质无缘、最与金钱疏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22)刘锡诚:《“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及其保护问题》,《民间文学论坛》2013年第5期。不过时至今日,随着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影视娱乐产业等蓬勃发展,“民间文学”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已经成为了被开发、改造、改编的重要对象。一方面想要推动民间文学类非遗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参与到地方经济开发、区域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另一方面势必会面临被过度开发、胡乱改编等诸多问题。因此民间文学类非遗并不是不需要“标准”,只是因为其与技艺类非遗不同,无法被框定到过于严谨和精细的生产性标准条文中。因此只有根据其自身特质与当下发展语境,制定具有灵活性、纲领性的实践标准。
(一)尊重叙事传统,建立伦理性标准
伦理向度一直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讲述活动中必然存在的衡量标准。比如故事家谭振山就曾明确表示自己有“三不讲”,即“女人在场不讲‘荤故事’;小孩在场不讲鬼故事;人多的场合不讲迷信故事。”(23)江帆:《民间叙事的即时性与创造性——以故事家谭振山的叙事活动为对象》,《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实际上这就是他根据故事情节和讲述情境、受众人群以及地方文化传统做出的道德和伦理标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故事家黄振华也说过:“你白天讲和晚上讲的肯定不一样,你去给人家做白事(丧礼),就不能讲结婚;你当着小辈孩子的面,就不能讲男女拉拉扯扯的那点事;跟熟人和不熟的讲法也不一样。”(24)讲述人:黄振华,辽宁省抚顺市上大卜村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民间故事”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访谈人:王琨;时间:2015年8月1日;地点:黄振华家。
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标准中的一切就都是好的,其中还会存在性别歧视、封建糟粕等。但民间文学衍续至今,无论是故事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已经对其形成了某种约定俗成的心理预判和评价标准,它一直以来都存在于源远流长的叙事传统中,可以看作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伦理性标准。而在非遗保护的标准建立过程中,就应该尊重民众的叙事传统,在其固有的伦理标准上进一步改良完善,以期对当下的文化实践起到指导规范的作用。例如在一些主题公园、文化景观中存在将民间叙事庸俗化的倾向;又如一些打着“民间故事”“传统故事”旗号的儿童读物、儿童网站根本不考虑儿童受众的特殊性,赫然将一些尺度很大的“荤故事”选入其中,不仅损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也会导致读者对“民间”和“传统”产生误解。(25)2006年《安徽商报》最先刊出一本名为《神话故事》(金建民主编,吉林摄影出版社)的儿童读物里出现了性侵、卖淫等情节;2020该作者又在多家儿童教育网站上发布了《剃黄毛丫头》等“民间故事”,随后光明日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同时豆瓣网和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自媒体也都纷纷参与讨论。
(二)尊重民族传统,建立情感性标准
不同的民族(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和表述风格,在民间文学中不仅有故事情节的铺排,更蕴含着浓郁的情感张力和价值取向。因此在定义、表述和宣扬民族精神时,“情感”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评价标准。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发现的“满族三老人”,他们能讲述上百则故事,属于那种不识字但讲述水平高的“典型的”民间故事家。不过当时也有人质疑他们完全不会满文,反而故事中还有很多汉族方言土语,这是否能符合“满族故事家”的称号。对此乌丙安先生指出:“到本世纪初(26)因为该书成书于1984年,所以此处的“本世纪初”指的是20世纪初。,除部分民间歌谣(主要是仪式歌)保持着满语演唱外,民间故事已经全部通用汉语讲述了。这是满族口头文学最重要的变化……”(27)张其卓、董明整理:《满族三老人故事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前言第4页。而“满族三老人”的讲述中还是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和口语习惯遗存。又比如国家级非遗项目“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在搜集整理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域文化,喀左地区的蒙古族是在东北民族大杂居背景下的农耕蒙古族,受汉民族影响很大,但其中像“马儿在草原上飞奔”“雄鹰翱翔在蓝天”这样的修辞比比皆是,可以从中感受到蒙古族特有的豪放浪漫的民族精神。
由此可见,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判断和探究具体语境中族群文化的真实样貌,既要挖掘传统特质,又不能忽略文化变迁中的情感维度。仅从对经典的民间文学的影视化来看,必要的艺术化处理自然无可厚非,比如2019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就是以“白蛇传传说”为蓝本进行的影视化改编,虽然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刻画上加入了很多新元素,但本质上还是体现了“真、善、美”的内核,宣扬了真挚爱情的伟大力量,这与广大民众对于该传说寄予的情感心理不谋而合,因此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相反,如果一味地追求猎奇、迎合恶俗趣味,就会使民间文学失去其特有的魅力,比如2015年演员贾玲在上海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节目中演出了一则名为《木兰从军》的小品,将花木兰塑造成为一个胆小怕事、懒惰贪吃的形象,节目播出后立即引发各界的激烈讨论,很多观众表示了抗拒和反感,最后以演员道歉、全面停播告终。而2020年上映的由迪士尼公司投资拍摄的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也在中国市场遇冷,归其原因也是因为滥用符号、“混搭”历史,没能真正理解和尊重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与民族情感。
(三)继续推进科学建档与数字化保护
虽然民间文学无法被嵌入精密而严格的标准化框架,但是对于民间文学文本的保护却可以依循一定标准化的格式。特别是“中国的‘非遗’已由初期的传承性保护向开发性利用模式转变”(28)江帆:《自在的遗产与可操作的遗产——“非遗后”时代的概念认知与实践考量》,《遗产》2020年第1期。,因此在其进入市场之前,就应以记录、建档、研究为主,建立概念体系和数字化保护的标准。
早在2012年,文化部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纳入规划,随后与之相关的“非遗普查资源的数据库”“非遗项目资源数据库”等也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同年11月,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筹建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完成了扫描、录入工作,并于2014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为了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29)宋俊华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4页。此外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和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共同开发的“中国数字故事博物馆”,以“民间故事集成”为原始数据,将故事文本、遗产地和节日等进行了分类展示;(30)参考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xy.bnu.edu.cn/xyzy/szzy/204292.html,访问日期:2020年11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库”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媒体资料库”“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影音图文档案库”等都在持续建设中。(31)参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数据库:http://cel.cssn.cn/was5/web/search?channelid=208898,访问日期:2020年11月16日。
其实从民国时期对歌谣故事的收集整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国性的“三套集成”,再到如今的各种数据库、数字博物馆的建设,都可以看到研究者对民间文学“本真性”和“整体性”的追求。而在当下语境中,数字化保护则可以最大程度上达到这样的效果,比如社科院民文所提出的“以事件为中心”的理论原则,并设计了文本、传承人、语境、演述、受众、时间、地点、责任与权利、民俗实物等16个元数据以及多达255个描述元素(32)巴莫曲布嫫等:《口头传统专业元数据标准定制:边界作业与数字共同体》,《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这都是为了实现田野采集的规范化与数字化保护所制定的标准。而对于民间文学类非遗而言,标准化采集和数字化保护能够将其更为完整直观地展演给广大民众,也为相关学者和研究者带来了便利,更重要的是它连结了历史与当下、现实与虚拟,既守住了传统的根系,又扩展了记忆的空间。
结 语
与其他门类的非遗相比,对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保护在法规、制度和具体工作层面都存在不少空白和争议。这与民间文学的精神性特征有关。当我们在探讨和实践“标准化”的时候,并不是要将其进行“一刀切”式地机械化管理,相反,应该在学术界、政府层面和民间这三者间找到平衡点,在科学有效、合情合理的界定与分类的基础上,维护保护对象的在地性和多样性;从民间文学自身特质及其在特定社区、族群和文化空间中的存续状况出发,尊重其原有的叙事传统和民族传统,制定伦理性、情感性的弹性规范标准,在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数字化保护的同时把握和展现民间文学真正的内涵与魅力;在“实现入选对象的可持续发展”(33)孔庆夫、宋俊华:《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制度”建设》,《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的同时,也让非遗普惠到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中。
—简述20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概念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