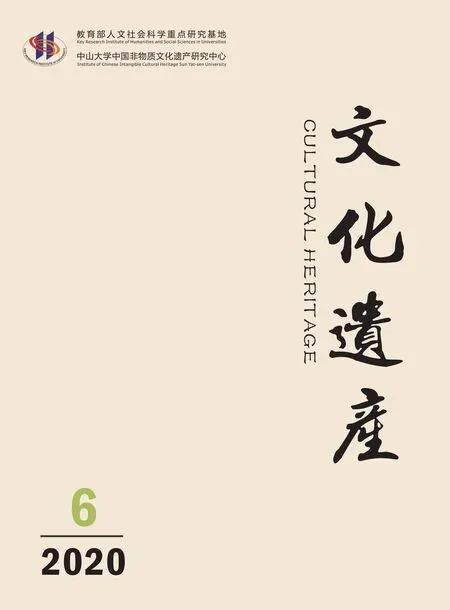“社”与海外“客家”认同的建构
——以海珠屿大伯公庙为中心的讨论*
冷剑波 [马]王琛发
“社”是中国传统社会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曾长期作为一种民间信仰、乡土制度和民俗活动而存在,与地方社会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杜正贞:《区域社会中作为信仰、制度与民俗的“社”—— 基于近十年晋东南研究的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6期。如郑振满在福建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存在以“社”为名的里社组织,其促成了“基层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进程”。(2)郑振满:《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载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52-253页。杜正贞通过晋东南的研究,阐释了社作为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的地方组织,“成为当地传统和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部分”。(3)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赵世瑜则认为,社作为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是“中国社会与文化中最具贯通性的表征”,它在“进入国家时代后在礼仪制度和民间传统中共存,而且一直存续至今”。(4)赵世瑜:《历史过程的“折叠”与“拉伸”——社的存续、变身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随着18至20世纪上半叶闽粤地区民众的“下南洋”,“社”的观念和传统也随之传入今天的东南亚各大华人聚居区。但是,与国内多年来的深入研究不同,有关社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状况,至今鲜少获得学者关注。本文以马来西亚田野考察的资料为基础,以海珠屿大伯公庙为个案,尝试分析作为祭祀组织的“社”在海外客家群体文化认同建构中的特殊意义,进而一窥“社”在海外的传承与变迁。
一、海珠屿大伯公庙与大伯公信仰
历史上的海外华人聚居区,在很大程度上并无封建王朝对于基层社会的国家权力掌控问题,因此也就不可能发展出一套如原乡般具有“建立规约、村庄管理、慈善赈济”等职能完备的以“里甲编户”为基础的“里社组织”。(5)杜正贞:《区域社会中作为信仰、制度与民俗的“社”—— 基于近十年晋东南研究的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6期。但是,以“社”作为信仰对象则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因“‘社’之本义,是指民间共同祭祀的土地之神”,(6)李玉栓:《中国古代的社、结社与文人结社》,《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是故在海外华人社区人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福德正神”“唐番地主”等,应都可以归为“社神”的范畴。除此之外,社作为一种“地缘”结合“神缘”的祭祀组织,在海外同样有较好的发展,马来西亚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中的结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地处槟城丹绒道光(Tanjung Tokong)的“海珠屿大伯公庙”,被认为是南洋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伯公信仰的发源地和祖庙。(7)[马]陈志明:《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庙中现存最老的文物为落款“乾隆壬子”的石质香炉,乾隆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该石炉也是目前所见槟榔屿全岛最早的文物。(8)[马]王琛发:《槟城客家两百年》,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98年,第16页。据庙内碑记所载,其真正建庙时间约为1799年,庙内目前有保存完好的“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重修碑记”“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庙捐册序”等碑刻3块,记载了大伯公庙的历史渊源及重修经过。此外,庙内还有匾额多幅,其中包括张弼士宣统二年(1910)以“头品顶戴”身份敬赠的“丕冒海隅”匾;另外庙前石柱刻有两幅对联,题写者为南洋著名客家先贤张煜南和张鸿南。庙后有“开山地主张公”“大埔清兆进邱公”“永定福春马府君”3座古墓。据考证,张公即祖籍大埔或永定的张理,马来西亚长期流传着他和邱兆进、马福春兄弟结义的神话,一般认为3人即是大伯公信仰的原型。(9)[马]蓝武昌、林廷侑等:《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二百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1998年,第477页。
“南洋言神,群颂大伯公。”(10)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庙内碑刻“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庙捐册序”碑文。由大伯公庙衍生出的大伯公信仰成为目前南洋华人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本土化”神明信仰之一,其作为庙宇的主神、宗祠的配祀神、家庭的护佑神,以及义山的守护神,广受华人崇拜。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地区,大伯公甚至成为其他族群所认定的华人信仰的代表。(11)徐雨村:《南洋华人民间宗教的传承与展望:以大伯公信仰为例》,[马]蔡宗贤:《砂拉越大伯公庙资料汇编》,诗巫:永安亭大伯公庙2010年,第173页。目前,海珠屿大伯公庙由槟城客家公会下辖的5个客家社团共同管理,即惠州会馆、嘉应会馆、大埔同乡会、永定同乡会和增龙会馆,合称为“客家五属”。
二、海珠屿大伯公庙中的“社”
虽然现在的海珠屿大伯公庙由客家五属共管,并通过共同组建的“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董事会负责庙的日常管理与主要祭祀活动。但据嘉应会馆、惠州会馆等各大客属会馆所藏的会议记录、纪念特刊等馆藏文献的记载,可知五属客家人很早甚至在部分会馆成立之前,就已经拥有名为“社”的祭祀组织,专门负责各属在海珠屿大伯公庙中的祭祀活动,即“惠福社”“嘉德社”“大安社”“永安社”和“增龙社”五大社。(12)[马]王琛发:《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内部的神缘结社》,《客家研究辑刊》2015年第2期。到了1889年,随着英殖民政府新的社团法令的颁行,规定凡拥有10人以上会员的组织,均需按规定流程注册并公开运作。(13)《东南亚历史词典》编辑委员会:《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因此,依现存档案资料的记载,五社重新注册成立的时间均在1889年或者之后,而实际存在和运作的时间则应远早于此,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社现存有关当时注册的档案资料,一窥这些作为祭祀组织的“社”的成立背景及概况。
通过槟城嘉应会馆所藏文献和访问可知,嘉应(今梅州)客家人所属“嘉德社”以及其他各社的成立,与历史上围绕大伯公庙产权的“客闽之争”有关。(14)访谈对象:槟城嘉应会馆会长李尧庆;访谈人:冷剑波;访谈时间:2017年3月20日;访谈地点:马来西亚槟城。据传,围绕大伯公庙产权的纷争持续了数十年,英国殖民统治者一度将这一纠纷带入英国枢密院讨论,最终经法院审理才做出裁决。(15)[马]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寺庙碑铭集录》,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13年,第44页。据槟城前辈学者刘果因的研究,最终判决约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16)[马]刘果因:《槟城嘉应会馆在马华历史上的地位》,[日]今堀诚二:《马来亚华人社会》刘果因译,槟城:嘉应会馆1974年,附录第6页。晚晴嘉应文人韩友梅写于1900年的《游海珠屿记》提及了这一纠纷:
闽侨旅人,争来奉祀,有谋畀石鼎置祠者,客人屏弗纳,构讼于公班牙(17)“公班牙”,源自英文company,指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嗣核准值年炉主归客人,始息争综。炉主五年一轮,若惠州、若嘉应、若大埔、若增城,皆粤中客人,若永定,则闽中客人也……逐年之炉主,客人率由旧章,罔敢失坠,盖不忘所自云。余游海珠屿之日顾而言曰:此所谓客人之大伯公也。王子曰:“槟城有此胜地,不可无盛会以张之”。归谋谢公塚斋,雅有同心,因联集嘉属同人结嘉德社。(18)(清)韩友梅:《游海珠屿记》,载广东暨汀州会馆:《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二百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1998年,第476页。
这份材料中提到了嘉德社成立的背景是闽客“构讼”,即为了获得庙宇的“奉祀”资格而打官司,而其最终的结果是“炉主归客人”。“炉主”又称“头家”或“头家炉主”,是19世纪马来亚华人社会中,对于庙宇、会馆等领袖的习惯称呼,一般由地方精英轮流担任,其选拔“既有民主的成分,又含有极浓的宗教色彩”。(19)[澳]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粟明鲜、陆宇生等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50页。海珠屿大伯公庙的炉主由惠州、嘉应、大埔、增城、永定“五年一轮”,基本确立了客家帮的绝对所有权,即所谓“客人之大伯公也”,此一制度也一直实行到今天。
大埔客家人的“大安社”正式注册成立的时间为19世纪末。据《大安社史略》记载:
本社为吾邑乡先达所组织,以祷神祈福,共谋同乡团结为主旨。自成立迄今,既有七十余年历史……邑中只知大伯公威灵,能保佑邑人平安及事业顺利,特订每年元宵,集合乡众,前往海珠屿大伯公庙祀神赏灯而已。嗣后及由邑众议合组祀神团体,定名为“大安社”(据闻名称为张舜卿氏所拟)。凡属邑众,均得入社为社员……初订每年农历正月十二晚祀神赏灯,并燃放鞭炮以助热闹外,十三晚复设宴联欢,籍叙乡情。董其事者为炉主,系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晚在海珠屿大伯公庙当众摇签及掷圣杯决定者,另推举协理四人,协办祀神赏灯一切事宜,任期均为一年。(20)槟榔屿大埔同乡会:《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刊》,槟城:大埔同乡会1968年,第212页。
该段材料说明了大安社这一“祀神团体”成立的简要经过,规定了入社的条件,即“凡属邑众”;同时也明确了祭祀的时间为农历正月十二至十三;作为总负责人的“炉主”则由“摇签掷圣杯”来决定。材料中提及的张舜卿又名张韶光,为19世纪末槟榔屿著名的大埔乡贤,作为张弼士在南洋产业的“信托人”,被称为张弼士的“大总管”。(21)邝国祥:《槟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8年,第58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安社成立之前,槟榔屿并无大埔人的专门社团,其所属的地缘组织为与永定人共享的“永大馆”,以及以潮州人为主导的“韩江家庙”,大安社的成立使得槟榔屿大埔人首次获得了专属的社团组织。(22)[马]王琛发:《马来西亚客家人本土信仰》,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2006年,第46页。
永定客家人的“永安社”注册成立的时间同样在19世纪末,《永安社史略》有如下记载:
本社为吾先贤所创立,以祷神祈福,共谋邑人团结为宗旨。当时鉴于邑人南来槟城者,虽人口众多,散居槟、威、吉、玻、太平、吉辇等地,平日极少联系,时感隔膜,为此先贤有必要发起组“永安社”。当初发起者为何人,兹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簿册遗失,无可稽查,惟据老前辈凭记忆所述。本社成立已近七十余年之久矣……本外埠邑人前来参加者,甚为踊跃。(23)[马]槟城永定同乡会:《槟州永定同乡会银禧纪念特刊》,槟城:永定同乡会1977年,第105页。
可见,永安社成立的目的与大安社基本相同,即“祷神祈福”和“共谋邑人团结”;而其炉主产生的方式也同样是“掷犒决定”。所不同的是,参与永安社者并非仅限于槟榔屿,而是包括从槟榔屿二次播迁到海峡对岸的威省(Province Wellesley)、吉打、玻璃市、太平等半岛地区的永定人士。材料中提到永安社的成立“已近七十余年之久矣”,可见其历史之久远。
由于资料的散佚,惠州客家人的“惠福社”和增城、龙门籍客家人的“增龙社”成立的时间已经难以考证。但据惠州会馆所藏档案资料记载,槟城惠州群体在19世纪下半叶就存在祭祀大伯公的传统,惠福社在此一时期就应该已经存在,其每年“庆灯”的时间依“历史渊源”定在正月初六;(24)[马]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180年》,槟城:惠州会馆2002年,第35-36页。增龙社每年“庆灯”时间则依传统为正月十六。(25)[马]戴邵芬:《话海珠屿说大伯公庙》,槟城:光明日报1997年4月12日。
三、“社”与客家族群认同的建构与维护
巴斯(Fredrik Barth)曾指出,客观的文化特征只能反映一个族群的一般内涵,而无法解释构成族群“边界”的重要问题,强调“形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不是语言、文化、血缘等内涵”(26)[挪]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页。;指出族群的边界并非指地理的边界,而是其“社会的边界”,族群是在“文化差异基础上的群体”经互动而建构形成,“在成员之间存在组织性互动的特点。”(27)[挪]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第3-9页。王明珂也认为,“族群边界的形成和维持,是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人们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的”,族群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源竞争与分配的工具”。(28)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页。我们认为,19世纪末叶槟城客家人族群认同意识的形成,除了方言、地缘、开拓记忆等因素之外,作为祭祀组织的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得特定时期各地客属同人统一在“客”的名称之内,更通过这样一个组织的建立,使得客家与其他华人帮群在激烈的资源竞争背景下产生“组织性互动”,由此形成建构客家认同的“社会边界”。
如前所述,在19世纪中后期围绕海珠屿大伯公庙的产权,曾爆发激烈的“客闽之争”。事实上,在庙宇产权确立归客家之前,槟城的客家人并非一个整体,一个跨地域的“客家”认同意识尚未出现。众所周知,19世纪下半叶是马来亚(Malaya)华人社会剧烈分化与动荡的时期。此时,马来半岛锡矿进入大规模开发,闽粤移民进入高潮,但同时主导各大矿区的华人会党也频繁发生争夺矿权的大规模械斗。槟榔屿作为当时主要矿家、同时也是各大华人会党领袖的聚集地,各方矛盾不可避免地由海峡对岸的矿区蔓延到岛内,不仅客家人主导的会党各自为战,福建人主导的会党也分为“大伯公会”和“义兴公司”两大派别,并出现错综复杂的相互结盟,当时的槟城华人社会处于同室操戈的境地,并最终导致了“槟榔屿大暴动”等一系列大规模械斗的发生。(29)参阅Straits Settlements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Penang Riots 1867,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55;邱格屏:《世外无桃园: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9页;[马]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第238-240页。据本文第二作者的研究,此一时期五属客家人同样长期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如惠州人和增城人分属“义兴”和“海山”两大敌对会党,大埔人则与潮州人因共奉“韩江家庙”而结盟,在雪兰莪地区嘉应人也与惠州人长期作战。(30)[马]王琛发:《马来西亚客家人本土信仰》,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2006年,第27页。此时华人社会内部的剧烈纷争,很自然地会延伸到围绕海珠屿大伯公庙,这一具有华人开拓象征意义的庙宇产权的争夺上,“神权”争夺的背后,牵涉的正是由会党所主导的华人“社会秩序”的重构。(31)张维安:《东南亚客家及其周边》,桃园:“中大”出版中心2013年,第34页。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此时的嘉应、惠州、大埔等五属人士能作为一个整体的“客家”出现。
1889年,英属马来亚殖民政府颁布《镇压危险社团法令》,要求所有华人社团组织重新注册,同时大量被认定为“危险社团”的华人会党被取缔或勒令解散。(32)L.F.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New York: J.J.Augustin Incorporated Publisher Locust Valley, 1959:255-256.由于会党的解散,以及历经多年的“客闽之争”后,面对实力更强的槟城福建人群体,原本分属于不同华人会党的五属客家人终于开始走向联合,五属随后不仅纷纷重新注册成立了各自的“社”, 而且在五大社的基础上,组建了“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作为共同的祭祀组织负责庙宇的日常管理,以及每年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大伯公神诞庆典”。(33)五属大伯公庙:《马来西亚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建庙212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2012年,第35页。作为客家人取得海珠屿大伯公庙所有权的条件之一,经协商每年最为重要的正月“请火仪式”则交由福建人的专门祭祀组织“宝福社”来主导,(34)槟城本头公巷宝福社内碑记。由此形成了客闽之间组织性互动的新模式。
自此,客家五属通过以地缘结合神缘的方式各自成立祭祀组织“社”,在一个总炉之外,各自保留香炉,除了在一年当中不同的时间举行各自的“赏灯”“庆灯”仪式之外,也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六共同举办“大伯公神诞庆典”;既维持了各自地缘小群体的认同意识,又维护了同属“客家”、共管海珠屿大伯公庙的事实。据记载,为了便于庙宇的日常管理,1899年五属客家人在海珠屿庙旁辟地建立了专门的办事地点和常设机构,命名为“槟榔屿客家五属公所”。(35)五属大伯公庙:《马来西亚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建庙212周年纪念特刊》;第35页。我们推测,“客家五属公所”很有可能是槟榔屿出现的第一个以“客家”为名称的组织机构,因作为客家五属会馆联合组织的“槟榔屿客属公会”直到1939年才宣告成立。(36)槟榔屿客属公会:《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刊》,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79年,第92页。从此,五属客家人通过祭祀组织被共同纳入“客家”的范畴,客家作为一个族群整体的形象日益显现。(37)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认为新加坡最早出现客家的自称,也与当地丹绒吧嗝大伯公庙中的祭祀组织“客社”有关,参见冷剑波、曹树基《原乡与南洋:客家的“他称”与“自称”》,《学术界》2018年第5期。
除了建构槟城客家人的族群认同之外,社对于客家人认同意识的维护与强化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与社具有的多重特殊功能存在重要关联。在英属马来亚时期,在社会机制并不完善的移民社会中,民俗信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庙宇长期作为华人主要的社会活动中心,祭祀权力的获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本。在海珠屿大伯公信仰中,我们看到嘉德社、大安社等的注册成立都离不开各属精英的推动,而在实际运作中,作为祭祀组织的社甚至发挥了超越地缘性会馆的作用,其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祭祀神明上。
首先,祭祀组织具有凝聚客家群体情感的功能。在五大社基础上形成的海珠屿大伯公庙最高祭祀组织拟定的《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章程》中,明文规定其成立宗旨和组织形式为:
宗旨:(甲)以敬奉大伯公及庆祝神诞等事;(乙)以联络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龙五属客籍人士之感情,共谋福利为宗旨。
组织:系由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龙五属客籍人士组织而成,五属会馆于每届一月中旬各自选派董事六名,共三十名组织董事会,及选派代表八名共四十名组织代表大会。(38)五属大伯公庙:《马来西亚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建庙212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2012年,第186页。
可见,除祭祀之外还有着“联络五属客籍人士之感情”“共谋福利”的功能。前文已述客家人共享的地缘性会馆——槟榔屿客属公会,直到1939年才正式成立,即便在此之后,五属大伯公庙仍然通过每年组织“大伯公神诞庆典”继续发挥着凝聚客家群体的功能。这一功能同样见于前文所引“大安社”“永安社”等祭祀组织的成立宗旨中。
其次,祭祀组织甚至成为地缘性会馆中的核心内部组织,且具有重要的金融和慈善功能。槟城嘉应会馆现存的“嘉德社档案”(39)槟城嘉应会馆藏“嘉德社档案”,感谢槟城嘉应会馆李尧庆会长无偿提供拍照和使用。,记录了自注册成立起至今超过百年的运作概况,包括自成立以来的会议记录、人员档案、收支统计和地契、典契等,从中可以窥探嘉德社特殊的组织构成和功能。我们通过系统整理该会历年的会议资料,发现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项:祭祀活动的筹备、会员的选替、资金的借贷、产业的租赁或买卖、公益慈善的投入以及其它杂项。除了作为本职的祭祀活动之外,关于资金借贷和产业部分往往成为历次会议的主要议程。
晚清嘉应诗人、曾担任海南儋州训导的王恩翔在游历槟榔屿时,曾受委撰写《海珠屿大伯公庙嘉德社序》,提及嘉德社注册成立的缘由:
兹同人佥议,醵金立社,以谋生息,俾逐年佳节应祀赀有所出,并酌立章程,用垂久远。佥曰:善!爰名其社曰“嘉德”。(40)槟城嘉应会馆:《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暨主办马来西亚嘉联会第三十六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槟城:嘉应会馆1987年,第17页。
从这段材料可知,嘉德社的成立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酬神仪式中的费用支出,即“醵金立社”,以实现“俾逐年佳节应祀赀有所出”。因此,筹措经费成为立社的首要目的。1900年重新订立的《嘉德社立社条款》,进一步详细规定了其组织构成与运作:
(一)本社之设,原为祈护佑,答神庥,亦即所以联梓谊、示亲爱也。凡我同人,虽属异姓,不啻一家,意合情投,创斯盛举,嗣后不准折回分子,不准外人添入,不准更换名字及顶替与人,以昭同德同心,永无疏间之意。
(二)本社同人共四十位。每名捐银伍元,作为社底。由众推举一人管理,以谋生息,每年定于重阳日应祀。届期各具衣冠,到坛行礼,祭毕即在坛前开筵团饮,以笃友谊。
(三)本社诸友,异日有捆载旋里转往别埠者,其子孙如有在槟,一体作为社内同人,惟不得将其父名字更改,以示不忘本源。
(四)本社开创之初,社底未厚,生息之款,仍留积储,矣社底丰厚,生息即多,方行动用公款;初三年仍由同人捐赀应祀,凡在埠者,每名出银一元,其不在埠者免。俟三年之后,视出息如何,再行酌议。
(五)本社之底,初无多款,未能置立产业,应由同人推举殷实社友一人管理,以便生息;俟积有钜款,即行置立产业,以垂永久。
(六)本社每年轮用四人为首事,周而复始。每年应祀之日,即当众结算,如有长存,多寡即交下年首事手收,但此系指余息应祀之款而言;至社底之银,社内诸友,不得生借,以杜流弊,如有呀兰契据作按者,又当别论,不在此例中。
……
(九)值年首事四人,悉皆编定年份,倘遇有轮应之年,四人皆不在埠者,即以下年首事代办,不得推展,以免参差。(41)[马]槟城嘉应会馆:《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暨主办马来西亚嘉联会第三十六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槟城:嘉应会馆1987年,第18页。
以上条款明确了结社的宗旨为“祈护佑、答神庥、联梓谊”;对于社员则做出了严苛的规定,人数被限定在40人,且“不准外人添入,不准更换名字及顶替与人”,另每年选出4人为“首事”作为负责人。据嘉德社档案记载,第一批社员40人包括谢荣光、王恩翔、古廷杰、杨铭汤、谢尚松、韩友梅、李其华、邱荣光……梁廷芳、潘祝华等,次年更替的社员包括张维栋、张煜南、张鸿南等。谢荣光、梁廷芳、张煜南、张鸿南等均为晚清槟榔屿著名的客籍领袖,前三者还曾先后担任清廷驻槟榔屿领事,其余人士也大都在《南洋名人集传》中有传,可见成为嘉德社社员的要求之高,是故嘉德社实际是由“客籍精英”所组成的会馆内的一个核心组织。这一点与大安社也颇为相似,因大安社注册成立时的主要人物,正是先后担任清廷驻槟城副领事的张弼士和戴欣然。(42)帅民风、王琛发:《马来西亚槟城大伯公文化艺术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2页。
仔细查看嘉德社的成立条款,可以发现其对于经费的筹集和使用要求甚为详细,几乎涉及所有条款。不仅设立了每人5元的“社底”,而且明确了“以谋生息”,“置立产业、以垂永久”的目标,而且如以“呀兰契据作按”还可以“生借”,可见其具有融资、投资、借贷、典押等明确的经济功能。档案显示,嘉德社也确实达成了这一目标。如1910年的会议记录显示:“宣统二年庚戍三月初七日,本社向汤荣甫君之掛沙人(43)“掛沙”又作“挂沙”,源自马来文kuasa,意为信托人、代理人,为南洋华人惯用词。买授本埠新街头门牌三十号D砖墙瓦店一间,时价一千一百大元,呀兰(44)“呀兰”,源自英语Grant,意为地契,为南洋华人惯用词。二七零号,月租三十元。”(45)槟城嘉应会馆:嘉德社档案,笔者整理。嘉德社在通过投资获得收益之后,不仅能够满足每年的大伯公祭祀支出,而且还有富余资金支持嘉应会馆的发展。如会议记录显示:“(1937年)由众通过捐助一千元,重建嘉应会馆费用”;“(1939年)是年加捐二百三十八元予嘉应会馆,充建筑费”,类似的记载非常多。此外,会议记录中也有大量“借支”和“收息”的记载。据1981年会议记录显示,嘉德社当年结余“社金共一万零五百元”,(46)槟城嘉应会馆:嘉德社档案,笔者整理。按当时汇率算是相当可观的一笔财富,可见嘉德社通过投资和借贷获得了很好的金融回报。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使得嘉德社的地位更加突出,除了满足祭祀和庙宇修缮的支出外,档案中也有不少捐资助贫的记录,即发挥了一定的慈善功能。
可见,因海珠屿大伯公庙祭祀而建立的五大社以及各社的联合,不仅成功建构起客家的族群认同,使得“客家”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自称,更通过发挥联络乡情、共谋福利、金融慈善等功能,进一步实现了客家帮内部的整合与文化认同意识的强化。直到今天,槟城客家人不仅在后裔中反复转述着“张、马、邱三公”异姓结义的神话,也通过年复一年的祭祀仪式,并在仪式中展示大量具有“客家”元素的彩旗、横幅、灯笼、海报、音乐等物质和场景,在有意无意中不断地塑造大伯公作为“客家集体祖神”的形象。(47)[马]王琛发:《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内部的神缘结社》,《客家研究辑刊》2015年第2期。可以说,对于槟城的客家人而言,大伯公已成为他们的“文化图腾”,成为凝聚群体性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结 语
近年来,国内不少研究者指出“社”是理解国家—社会关系问题的关键,主张将“社”作为理解区域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认为其是国家在基层社会管制缺失的一种替代。(48)刘永华:《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4页。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海珠屿大伯公庙中的结社,除了祭祀之外在整合华人帮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即在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中,同样曾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但是,由于国家行政、历史演进、祭祀系统、宗族势力等全然不同的时空背景,海外“社”的发展也呈现与原乡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与华南地区里社祭祀组织鲜明的“家族性”和“社区性”不同,(49)郑振满:《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50-251页。海外的社呈现明显的超宗族、跨区域特点。如嘉德社包含了嘉应五属(梅县、蕉岭、平远等5县)各姓人士,永安社的社员更来自威省、吉打、玻璃市、太平等整个马来半岛中北部地区,而作为客家五属联合的祭祀组织更是包含了所有来自粤闽两省的客家人。其次,与华南地区的社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对“国家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认同”不同,(50)郑振满:《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第253页。槟榔屿大伯公庙中的社具有极强的“组织性”,主要表现为对特定群体的整合与文化认同的凝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分裂的槟城客家人,因神明祭祀结成的“社”而重新走向团结,成为凝聚当地客家人文化认同,建构和维护族群边界的特殊工具。
田野调查发现,在东南亚各大华人聚居区,以地缘结合神缘的结社现象较为普遍。除了本文讨论的海珠屿大伯公庙之外,新加坡丹绒吧嗝(Tajung Pagar)大伯公庙中的“客社八邑”、新山柔佛古庙中的“客社”等,(51)冷剑波、曹树基:《原乡与南洋:“客家”的他称与自称》,《学术界》2018年第5期。基本都属于这一类型。随着研究个案的增多,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社”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