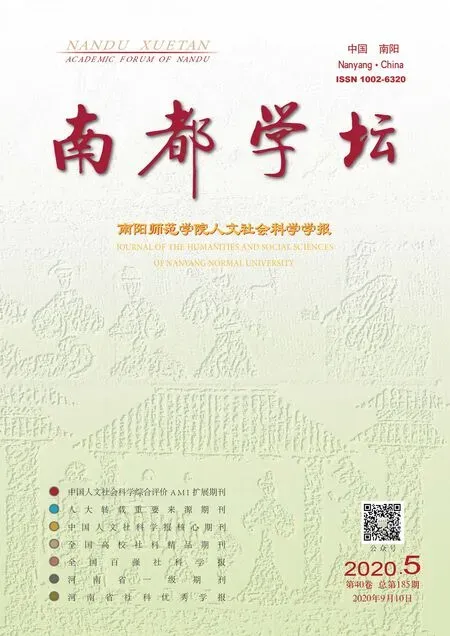余华小说的“代父”书写
黄 瀚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每逢社会转型和时代思潮迁异,文学作品对父亲形象的塑造也会有所变化,父子伦理叙事所具有的文化意涵,往往并不停留于家庭伦理层面,而是与社会结构转变、文化观念更替相关。超越血亲关系的父子伦理本身就传达出固有家庭形态的错动,因而它常常作为表达某种观念意识的手段,出现在文学作品中。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终止了自给自足的个体劳动形式,也由此动摇了附着其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个人”加入“集体”、“小家”变成“大家”成为一股书写潮流,父辈和子辈分别成为代表“旧”和“新”的文化符号,呈现出新战胜旧、子胜于父的叙事模式。柳青《创业史》里,代职父亲梁三老汉成为农业互助组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梁生宝们帮助和改造的对象,与梁三老汉并无血缘关系的梁生宝加入“集体”创业具有“先天”优越性。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们在塑造丑父、恶父的同时,开始以“爷爷”(莫言《红高粱》)、“外祖父”(张炜《逝去的人和岁月》)等代职父亲超越父辈的叙事。在这股书写潮流汇中,余华小说对父亲形象尤其对“代父”形象(1)本文所谓的“代父”形象是指余华小说中出现的履行对子辈的父职但非血亲父亲的男性人物形象。的持续塑造,构成奇特的文学景观。事实上,对余华小说父亲形象的研究已成为余华研究领域不容忽视的部分。但是,多数论者并未意识到,脱离血亲关系的父子伦理书写,才是余华小说处理父子关系的独特之处。或许,我们可以从余华小说的“代父”书写,窥探余华创作的某些特质。
一、“无心插柳”: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代父”塑造
景莹《无根之痛:余华小说中的继父现象》[1]一文,较早研究余华小说的“代父”书写。景文未注意到,余华小说的“继父现象”并非在“其后期小说创作中”才有,它甚至在余华处女作《第一宿舍》(1983)就已出现。小说中,毕建国在生命垂危之际,念兹在兹的是一盆寓示着妹妹小棠的海棠花。小棠是毕建国父亲牺牲的战友的女儿,曾受到毕父的悉心照料,在特殊历史时期,毕父接受劳动改造,小棠赶往农场看望他的途中,迷失在森林里死去。毕建国死后,复出的老干部毕父收回儿子的骨灰,把它埋在小棠失踪的地方。而那盆具有寓意的海棠花,将永远陪伴着这位“代父”。《第一宿舍》发表时,编辑的一段点评值得注意:
这篇小说长达一万多字,并无曲折的故事,读来却不觉枯燥,其秘密何在呢?除了语言流畅,富有幽默感,关键还是比较注意写人物。无论是令人忍俊不禁抑或黯然泣下之处,均为作者着力描写“命运”与“性格”的地方……[2]
也就是说,余华从事小说创作之初,在模仿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界流行的哀婉情调,但聪敏的余华懂得着力描写“人性”(人物的“命运”与“性格”),这就容易受到编辑的青睐。综观余华1985年以前的作品,作家基本上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起,这些作品多因符合当时反思历史、表现“人性”的文学成规,而受到文学编辑的重视,得以顺利发表。
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环境风云变幻,到8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普遍厌倦“伤痕”文学铺天盖地的控诉和哀怨,当代文学面临求新求变的压力而进入调整阶段。随着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的展开,西方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涌入国内,人们对“世界”的想象空间骤然拓开,作家的创作观念随之新变。除“现代派小说”外,“实验小说”“新小说”“新潮小说”“先锋小说”等名目繁多的小说实验陆续登场。这些小说实验整体上呈现出“写什么”的重要性被“如何写”所替代的趋势,由文学反映论转向文学本体论的趋势,以及“从书写的内容和表现的价值立场、艺术观念乃至叙事方式等各个方面”[3]对现实主义文学进行变革的趋势。在此文学环境中,余华为自己的创作陷入陈套而感到焦虑。
1985年,余华发表创作谈《我的“一点点”——关于〈星星〉及其它》。文中写道:“《星星》毕竟太浅”,自己“何尝不想去把握世界,去解释世界”,无奈“怎么使劲回想,也不曾有过曲折,不曾有过坎坷……于是,只有写这一点点时,我才觉得顺手,觉得亲切”[4]。焦虑之余,余华提及自己钦佩的两位作家——张承志和邓刚,因为二人写出了“男子汉文学”。那么,二人写出怎样的“男子汉文学”?从张承志《北方的河》、邓刚《迷人的海》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可推测,余华羡慕的很可能是这两部作品的某些精神特质或创作风格(2)《北方的河》出版时的内容提要说:“主人公对开创事业的决心和力量,以及他对爱情的独特选择为作品增添了一种男子汉的气魄和魅力。”(张承志:《北方的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而这两部小说的共同之处便是以象征主义手法和强悍硬朗的风格,开始了反抗“父亲”、寻求自身道路的精神之旅。《北方的河》中,“我”显然有着代表“我们这一代”与上代人对话的意识。看到奔腾的黄河,“我”觉得“这黄河像是我的父亲”,想到生父背弃自己和母亲,“我”骂道“这个狗杂种”[5]!邓刚在《迷人的海》中塑造的海碰子身材魁梧、粗犷有力,他不畏爷爷和父亲的死亡,想要潜入海底,“寻找最珍贵的,世世代代海碰子终生寻找过但始终未寻找到的东西”[6]。显然,这里的“黄河”和“终生寻找过但始终未寻找到的东西”,都喻示一种超越现实处境的精神指引。有感于自身创作的落伍,对文学环境和时代思潮极为敏感的余华,开始主动调整写作策略。
1986年春,余华偶然接触到卡夫卡小说。卡夫卡的叙述给余华很大冲击,他“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7]106。受到卡夫卡的启发,余华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解放出来,这才诞生了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小说采用“无父”的叙述,巧妙讽刺“父”对“子”的指引。叙述者“我”兴高采烈地踏上成人之旅,没想到被父亲送入一个险恶荒诞的世界。当“我”按照父亲的教诲为人处世时,非但没能阻止农户哄抢苹果,反而遭到“我”要帮助的司机的趁火打劫。小说结尾处,“我”遍体鳞伤地躺在冰凉残破的汽车上,回想起那个晴朗温和的中午父亲送“我”出门的场景。“成年”前后视差下父亲形象的重现,成为一种意义荒谬的符码。继《十八岁出门远行》塑造颇具荒谬感的父亲形象后,余华在“毕加索时期”(程光炜语)持续塑造了一系列不堪的父亲形象(3)这一时期,余华创作的《死亡叙述》《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劫数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鲜血梅花》等小说,均对父子伦理有所审视与反叛。。无论是“无父”叙述,还是“审父”“弑父”之作,其挑战锋芒直指那个似乎无处不在的菲勒斯(phallus),余华也由此写出自己的“男子汉文学”。陈晓明指出,“先锋小说一直以‘遗忘父亲’为叙事的先决条件,‘父亲’形象或者先验性空缺,或者是垂死的历史象征”[8]。这个论断确实适用于余华先锋时期的写作。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父亲”的审视与反叛已成为一股文学潮流。王蒙的《活动变人形》(1985)、《坚硬的稀粥》(1989),洪峰的《奔丧》(1986)、《瀚海》(1987),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1987)、《罂粟之家》(1988)、《南方的堕落》(1989),张炜的《远行之嘱》(1989)等作品,均对父子伦理构成不同程度的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在小说《一九八六年》里,与“遗忘父亲”相续的另一端是对“代父”的认同。这篇小说的人物没有确切名字,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个与特定历史时期告别的寓言。在疯癫的生父所象征的历史时空与女孩生活所代表的现实时空的交错中,小说四次写到女孩长大后见到生父的情景,可这四次相遇带给她的只能是恐惧与厌恶的逐步加深。直至最后,母女俩漠然地与那位疯子擦身而过,优雅离去。我们无从得知那个喊着“妹妹”的疯子是否为女孩的生父,但从叙述可知,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咖啡厅、电影院、展销会进驻小镇,流行歌曲、新潮服饰、美食佳肴带给人无尽消费快感——能够融入这个时代、也为女孩所接受的,只能是那个愉快温和的“代父”。在反抗“父亲”的文学潮流汹涌澎湃之时,余华塑造出一位无须被仰望、也无须被反叛的“代父”,这位“代父”的精神和性格是通向20世纪90年代的。
从处女作的发表到登上先锋文学场,余华一直在塑造着“代父”形象。但是,在张承志《北方的河》视黄河为“父亲”、莫言《红高粱》追认爷爷余占鳌司令为精神指引之时,余华书写“代父”的写作立场仍飘忽不定:《第一宿舍》里的“代父”塑造是与时代的“共名”(4)在陈思和看来,一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深刻地涵盖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制约。这样的文化状态称之为‘共名’”。陈思和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4页。,与官方意识形态呼应;《“威尼斯”牙齿店》里的阿王形象虽有些不堪(尿床、夸海口、亲观音),但这位“代父”的设计主要表现一种民间生活形态;《一九八六年》里的“代父”与生父形象形成反差,表现出余华知识分子立场上的社会批判意识。从其20世纪80年代“代父”书写的轨迹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余华小说的“代父”形象难以简单归于历史文化寓意上的精神性存在。我们有理由认为,余华塑造的这三位“代父”很可能是作家“无心插柳”的结果,而余华浓墨重彩地书写“代父”,则要留待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
二、回归“民间”:文化转轨中的“代父”书写
1991年,余华推出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后改题名为《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里,所有的生身之家上演的无非是一场接一场的闹剧和无法停歇的暴力,一个个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互相撕扯着陷入生命的深渊。陈晓明曾以“胜过父法”为题概括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他指出:“‘胜过’则意味着真正的超越,层次上的跃进,对原来的法规秩序的智高一筹的跨越。”[9]但陈文之谓“胜过父法”主要是指语言与写法方面的革新,陈晓明在当时并未意识到“真正的超越”在形式的内容层面也已展开,这甚至成为余华此后创作不断重复与倚重之处。
小说中,与生身父母对“我”的厌恶相比,“代父”王立强对“我”的照顾,才能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以至于“我”觉得王立强才是真正的父亲。倘若以“代父”完全取代不堪的生父,“我”的童年也许会增添更多亮色,然而血缘的隔绝成为“代父”与子辈心灵间的一道无形藩篱。上学第一天,“我”背着书包走到同学中间,正在为自己的书包比他们的大而感到自豪时,王立强当众大声提醒“我”上厕所要举手。王立强对乡下孩子的固有观念,强烈冲击了“我”敏感而脆弱的自尊心。为发泄一时的欲望,王立强不惜对“我”拳脚相加,“我”无力反抗,只能以绝食抗议。待他找到被打得鼻青脸肿而不肯回家的“我”时,小说出现一段难得的父子温情叙述:
他把我背在脊背上,双手有力地托住我的大腿,向校门走去。我的身体在他脊背上轻轻摇晃,清晨时还那么坚强的自尊,那时被一种依恋所代替。我一点也不恨王立强了,我把脸靠在他肩膀上时,所感受的是被保护的激动。[10] 258-259
如果说王立强给予“我”父爱,那多半也是出于愧疚的自责行为,然而这微乎其微的关爱,已足够让“我”铭刻心底。王立强远非完美的“代父”,与年轻女人的私情被揭发后,王立强疯狂地引爆手榴弹复仇;复仇未果,这位“代父”选择抛弃家庭,结束自己的生命。养父的毁灭与养母的离去造成“我”无家可归,来自血缘的古老召唤指引“我”回归南门,重又步入注定的深渊。这部小说里,血亲父子亲情的失落与“代父”和子辈的隔膜,是对生身之家和寄养之家的双重弃绝,也是对生父和“代父”的双重否定。
传统父子伦理轰毁之后仍存有一股重塑家庭的渴念,支撑着余华感怀父子冲突之余,继续寻觅父子温情。《活着》完成了对福贵浪子回头的叙述,这位风流成性的少爷赌博成瘾时,不惜殴打怀着身孕奉劝他的妻子,待到家产输光、父亲死去他才幡然醒悟,甘愿承受生活之苦难以自我救赎。人情冷暖与繁重劳动让福贵找到民间朴实的生存之道,他对家人的态度有了根本性扭转。我们容易读出福贵转变后对子女的爱护,却常常忽略隔膜与冲突在父子、父女关系中的延续。小说中,福贵被国军抓走再回家时,凤霞和有庆都对福贵感到陌生。由于父爱的缺席,凤霞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她高烧后失去言语能力。毋庸说福贵狠心逼迫凤霞出嫁、愤怒管教有庆,都是父子、父女矛盾的体现。只是这冲突之中饱含着父子、父女深情,苦难当中闪现着爱的光辉。通过这种戏剧性的反转,余华小说的“父亲”形象回归到严酷中有慈爱、苦难中有善良的面貌,“父亲”形象显露出民间生活的底色。值得注意的是,苦根的生父二喜意外身亡后,晚年福贵担负起赡养苦根的责任。他尽其所能给予苦根爱护,而苦根也给福贵的晚年生活带来温暖。他俩虽是外公与外孙的关系,但福贵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般对待苦根。在这层意义上,福贵也当属“代父”形象。同样,“代父”与子辈的冲突依然存在,最显在的例证是,福贵煮太多豆子给苦根吃而间接导致他的死亡。
《活着》首先借一个民间采风者的角色展开叙事,这位采风者的话语与叙事人福贵的叙述话语交织进行,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民间采风者的角色隐去,福贵成为叙述的主体。作家摒弃知识分子话语,用地地道道的农民话语讲述福贵的人生经历。待福贵讲述完自己的经历,采风者的角色再次浮现,这使得读者与福贵的叙述产生疏离感,从而使福贵的故事具有一种传奇化效果。这部小说完成了启蒙视角与民间视角并存的双重叙事,及至《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对叙述的控制,让许三观等民间小人物自己开口说话。由于叙事技巧的运用,叙述者并不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读者也跟随着这些市井人物的对话,感受他们平凡生活中的悲喜交加。
小说共叙述了许三观十二次卖血经历(最后一次未遂),情节发展的高潮是许三观为了挽救非亲生儿子一乐的生命,不顾生死、千里卖血的详尽叙述。其间他数次因失血过多晕倒,几乎丢掉性命,可他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终于把钱送到医院救治一乐。面对一次次的苦难,这位“代父”以自己生命的损耗为代价让子辈的生命得以延续,这就使得“卖血与施爱的过程超越了父与子的生命范畴, 甚至蕴含了许三观对自我生存的道德追问和伦理冲撞”[11]。作者在对许三观伟大父爱颂扬的同时,不忘他作为市井小民狡黠、市侩甚至卑劣的一面。成功迎娶许玉兰后,许三观发现一乐非亲生,他粗暴地殴打许玉兰,愤怒之余更关心的是许玉兰的初夜给了谁的问题;一乐闯祸后,许三观不肯出钱,而是怂恿许玉兰去向何小勇要钱;被方铁匠抄家后,许三观居然怂恿儿子们长大后强奸何小勇的女儿;深感吃亏的许三观,为了取得心理平衡,又去与林芬芳偷情。这样一来,许三观一副小市民的嘴脸毕现无遗,甚至还流露出流氓气。可见,小说对“代父”的审视仍在继续。由“代父”不认子到子觉得“代父”丢人,许三观与一乐的互斥持续到故事最后。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作家们塑造出越来越多的理想之父成为十分醒目的现象。张炜小说屡次追忆令人感奋的精神之父尤为值得一提。在小说《柏慧》(1994)中,与“我”对外祖父的追慕不同的是,“父亲对我而言像个陌生人,也实在是个陌生人”[12] 30。牢狱之灾彻底改变了父亲的脾性,他的遭遇给一家人带来灾难。然而当母亲为“我”找到一位“义父”时,“我”却拒绝见他。随着阅历渐长,“我”终于领悟到父亲怀着坚定的信仰投身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卷入政治斗争被捕的不幸。在此,子辈通过再次审视父亲,理解了那个虽不完美却给予自己生命的父亲。这种趋向在小说《家族》(1995)中,得到进一步确证。当“我”终于理清家族历史、体认到父亲的不易时,面对他人的逼问,“我”说出:“我认为,人世间极少有一位父亲能像我的父亲那样,让后一代感到如此自豪!”[13]404对“父亲”的体认,使得子辈能够回归到家庭伦理,完成对伟大父亲的赞颂。
肇兴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商业文化,造就了世俗化的中国社会,并改写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众文化兴起,文学生产的媒介环境发生改变,知识分子遭遇新的历史境遇,这都悄然改变着当代文学形态。由于一个经济文化趋于多元的社会图景渐次展开,文学遭受意识形态干预的压力得到空前释放,曾以启蒙者自居的作家却遭遇其身份与姿态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危机,陷入严重分化当中,先锋文学精神内核的溃散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包括余华在内的诸多作家因而改变启蒙者的写作姿态,融入民间社会,适应其赖以生存的文学市场,并开始重建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的作家普遍意识到,即便“父亲”有丑恶的一面,子辈仍然需要精神之父的引领实现自身的成长。因而,作家们在对子辈和父辈的双重审视中,开始理解父亲的生命经验,完成对父亲的体认。相比之下,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的“代父”书写,带给读者的是另类父亲想象。余华追认到的“代父”是脱离天然血亲法则同时超脱传统家庭伦理的民间之父。他们不是骑士、革命家或英雄,而是生活于民间大地上的质朴农民和小镇居民,自有其普通人的缺陷与良善。这种扎根于民间的日常化的父子伦理处理,既与其此前的“审父”“弑父”之作相异,也与20世纪90年代对“父”的重新认同有着根本疏离。
三、面向“现在”:余华小说“代父”形象构建逻辑
如前所述,尽管王立强、福贵、许三观们与子辈之间存在隔膜与冲突,但他们毕竟带给子辈依靠而得到否定中的肯定。那么,这种“肯定”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多数作家对“父”的重新认同,究竟有何不同?要解开这个矛盾之结,我们需要梳理余华小说“代父”书写的内在逻辑。
《在细雨中呼喊》里,“我”与周围人一样陷入绝境;更加不幸的是,“我”为自己身处的民间世界所排斥,只能游离于这个世界。当家人与王家兄弟为自留地发生争吵打斗时,“我”处于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位置,以致村里所有人都认为世上再找不出如“我”般坏的人。“我”长大成人后也是如此,家乡是“我”回不去的地方。与以“我”之眼观看秩序失范的世界相异,这里出现了以民间生活者之眼观看“我”的视角,而“我”是长大后考上大学的、在回叙往事时具备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这里是对知识分子身份与立场的审思。这种反观知识分子的眼光,在余华1989年8月创作的《两个人的历史》中已经出现。小说中,谭博作为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而一直生活于民间社会底层的兰花则命运稳定如一。年老的兰花身体健壮、子孙成群,谭博却在暮年忧心忡忡。这篇小说的叙述有着反思知识分子启蒙理想和革命精神的意味。而这种反思意识的获得,应当与余华的经历和感受有关。
关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亲身经历,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人民”一章有着详细记述。余华目睹了中国社会如何由启蒙狂热迅速转向经济狂潮,也见证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迅速分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余华持续塑造“恶父”,以文学实践的形式参与到社会批判潮流中。但经历过历史转折的余华,深感“一切都改变了”[14] 14,其时他的痛苦、失落和虚无感恐怕难以言尽吧!若非如此,作家也不会在时隔近20年后写下这些平静中隐含激愤的文字。这个时期,余华写下创作谈《虚伪的作品》,文中强烈拒斥生活事实的虚假,而表达出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对于写作的终极意义,余华这样写道:
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即我们为何写作?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什么?我现在所能回答的只能是——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这种传统更为接近现代,也就是说使小说这个过去的形式更为接近现在。
……我的所有创作都是针对现在成立的,虽然我叙述的所有事件都作为过去的状态出现,可是叙述进程只能在现在的层面上进行。[7] 169-170
这篇创作谈是余华对自己此前创作经验的一个总结,也是作家此后创作的一个出发点。我们之所以将之视为新的起点,是因为这篇创作谈预示着余华由一位启蒙者向一位真正文学者的转变。如果说此前的余华用极端的暴力叙事表达“对常识的怀疑”,那么从此时开始,他的形式实验要“在现在的层面上进行”。因为他意识到生活本来就是“真假杂糅和鱼目混珠”的,那么此前他对生活真实的怀疑便也并不可靠,只要生活没有脱离作家的意识,何谓真实、何谓虚假,其实是难以分明的。于是,对自身“怀疑”的怀疑产生了对生活的否定之否定,那便是肯定“现在”,因为“现在”即蕴含着“过去的经验和将来的事物”[7] 170。
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拒斥,之于余华而言,使他产生对虚无、对绝望的怀疑;对“现在”的接纳,使他获得对民间生活者建立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理解与同情——这就是余华所谓的他获得“去重新理解他们的命运的权利”[10] 1。于是可以看到,与先锋时期那些实验文本的冷漠叙事不同,《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叙事者充溢着丰富的情感体验,生活绝境里坚韧的生命力由此隐秘伸展。于作家本人而言,这是“写作磨炼的结果”[15];在我们看来,这是作家虚无世界像出现动摇进而实现超脱的端倪。对现实权力的拒斥立场是余华先锋时期就已确立的,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又遭到余华绝望后的质疑,那么余华接下来的写作只能面向“现在”。当作家将目光从高蹈的启蒙理想转回身边的现实生活时,具有包容性的“民间”(5)此处指陈思和提出的“民间”。首先,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其次,“民间文化形态”体现出“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再次,它有着“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陈思和指出,这三条定义只是就民间的文化的基本形态而言,在实际的文化研究中,“民间”所涵盖的意义要广泛得多,其中还应该包括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文化修养,等等。陈思和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的重新发现成为一种可能,毕竟余华早期创作中已经对民间生活有过艺术处理(如《“威尼斯”牙齿店》《一九八六年》)。那么,接下来作家该如何面向“现在”写作呢?
“民间”是一个包罗万象、藏污纳垢的世界,生活于其间的“代父”理应富有饱满性格。研究者多注意到余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塑造的“代父”温情的一面,却往往忽略“代父”与其他小说人物的对峙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在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已经显现。
首先,在余华塑造“代父”的作品中,多隐含“代父”与生父间的冲突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德威《伤痕即景,暴力奇观》一文已注意到:“余华不只处理叙述者父与子间的紧张关系,此父亲与他父亲间的斗争,也是死而后已。”[16]进一步说,余华在塑造“恶父”、消解“父亲”的固有权威时,同时塑造超越血亲关系的“代父”,在拆除传统父子伦理及由此产生的家国体系的可能性之后,子辈对“父”的认同才能降临到“代父”身上。“代父”与生父的冲突,自有再造父子伦理与社会伦理之深意。其次,余华小说塑造的“代父”亦不乏与子辈相冲突,表现为“代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子辈的受伤或死亡,或反之亦然。《第一宿舍》中,小棠的死是由“代父”毕建国的父亲间接造成的。《“威尼斯”牙齿店》潜藏着父女冲突关系,子辈杀死“代父”阿王,小宝和老金的结合才顺理成章。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余华笔下的子辈产生对“代父”的体认。问题在于,即便子辈能够理解和认同“代父”的感情或行为,“代父”与子辈之间的冲突仍然不断出现,从深层次上说,“代父”仍属于被审视、被质疑的对象。
余华小说“代父”书写的这两个结构性特征,决定其不同于那些简单肯定“现在”的创作。在对绝望与虚无产生怀疑而面向“现在”之后,余华对肯定“现在”进行了再次否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螺旋上升式的思维方式。在写作中,余华逐渐超脱出虚无世界像,开始浓墨重彩地书写民间中的“代父”,在对“代父”的多重否定和质疑中,构建“现在”的父子伦理关系。如同鲁迅意识到“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17]一般,余华经历一场理想主义的大溃败之后,将小说人物塑造的重心回归到民间“代父”。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并未将余华对民间“代父”的重新发现视为“转向”,而是视为“回归”。这受到竹内好鲁迅研究“回心”论的启示。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中曾比较“转向”与“回心”的区别,在此不妨摘录,以便说明:
表面上看来,回心与转向相似,然而其方向是相反的。如果说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18]
在此,我们不愿把“回心”套用在余华身上而追寻其主体逻辑构建之轨迹,毕竟余华与鲁迅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但我们将研究面向余华小说的“代父”书写时,又发现余华由塑造“恶父”到塑造“代父”的内在理路与鲁迅1926年在“多疑”中超脱虚无世界像,接续起充满现实性、战斗性的写作何其相似。回归“民间”的写作是面向“现在”的,它并不避讳“民间”的荒诞与粗鄙、谐谑与残忍,而是在对必将成为历史“中间物”的“现在”的直接书写中,展开通向过去和未来之路。
四、有常有变:余华21世纪以来的“代父”书写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产生巨大的社会差异,“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14] 181。民间生活发生异变的状况下,余华写作必然遇到如何处理当下经验的问题,余华小说对“代父”的塑造也随之发生微妙变化。
沉寂10年后,余华推出长篇小说《兄弟》。小说中,李光头的生父刘山峰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掉进粪池淹死。与这位龌龊生父迥然不同的是,李光头的“代父”宋凡平高大魁梧、才华横溢,还有着宽厚仁爱的美好品质。宋凡平以自己的开朗、乐观和强大,给家人带来自信与快乐。革命斗争中被打倒的处境没有击垮宋凡平,在宋凡平的教导下,李光头和宋钢学会了孝敬父亲,他们做好煎虾、带上黄酒、克服困难去看望关在仓库里的父亲。在极端环境下,宋凡平以最大的努力提供给家人幸福,尽管他的努力因外界的残暴扼杀而告终。
《兄弟》上部仍在处理特定历史时期父子关系,到下部,余华借由宋钢与李光头的不同命运,着力展开兄弟关系的书写。宋凡平死后,宋钢带着“父”的性格因子走到了新时代,他的善良忠厚在这个时代逐渐沦为一种迂腐懦弱,他无力改变个人境遇,又拒绝李光头的帮助,最终只能以卧轨自杀的方式结束孱弱的生命,成全弟弟和妻子的私情。而那个主要继承生父流氓性格的李光头依靠倒卖洋垃圾发家致富,依靠媒体炒作获得曝光率,依靠资本操纵丑态百出的处美人大赛,他可以在欲望横流的社会左右逢源,在黑白是非之间游刃有余地施展个人才能。然而,李光头的性格是丰富多面的,他对“代父”宋凡平的认同代表着其为人的基本良知。他落魄时未曾偷盗,生意稍有起势就偿还债务,发迹时不忘回报恩人;他重情重义,暗自帮助宋钢治病,毫不计较宋钢与其断绝往来的冷漠。只是缺少“代父”的精神指引,李光头出于本能取得的世俗意义的成功,并不能填补他精神空虚、漂泊无依的人生遗憾。如果说李光头的人生遗憾主要在于“代父”的缺失,那么宋钢的悲惨境遇则源于其“父”的精神弱化无法适应这个乱象丛生的时代,二人都断绝了为人父的可能,也意味着其精神繁衍的终止。这部小说既有对父与“代父”的审视,也有对“子”的批判,而这种审视与批判的目光又投向两个一脉相承的时代。
《第七天》延续余华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关注。小说中,身为铁道扳道工的杨金彪发现掉落在铁轨间的婴儿处于危险境地,遂把他捡回家养育。于是,杨金彪成为杨飞的“代父”。当个人婚姻与继续养育杨飞之间发生矛盾时,杨金彪并非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甚至一度把小杨飞遗弃到“孤儿院”门口。然而父子之情并不取决于血缘,已经与孩子难分难舍的杨金彪,最终还是拒绝了婚姻,选择与杨飞相依为命。杨飞长大后逐渐步入事业正轨,他忽然得知杨金彪身患绝症,遂辞掉工作照顾杨金彪,又卖掉房子为父亲筹钱治病。为不拖累儿子,杨金彪不辞而别,无声无息地离家出走。由此,父子二人阴差阳错地相互追寻,在现实世界与幽冥之境的游荡中勾连起贫富悬殊、暴力拆迁、夫妻离散、死婴遗弃、地质塌陷、黑市交易等一系列社会乱象。小说描绘的现实世界混乱、坍塌,底层人物无意义地抗争、无端地损耗生命,直至冥界方可安宁,而小说中最美好的境界乃是“死无葬身之地”。
《兄弟》和《第七天》同样存在“代父”与生父互斥、“代父”与子辈冲突的结构性特征。就前者而言,《兄弟》里的宋凡平打捞刘山峰尸体似乎是见义勇为,可他正是这场悲剧的肇事者;《第七天》里的杨金彪在得知杨飞生父是国家干部后,为让杨飞有更好的发展,忍痛鼓励杨飞回到生父身边。就后者而论,为避免孩子过早蒙上阶级身份的阴影,宋凡平把“地主”解释为“地”上的毛“主”席,但在李光头无意“揭发”出此事后,宋凡平遭到红卫兵最猛烈的殴打;而《第七天》里,杨金彪也曾放弃抚养幼小的杨飞,并且,杨飞在寻找杨金彪的过程中丧命。可见,“代父”与子辈温情脉脉的背后,仍不乏对“父”与“代父”的多重审视。
这两部小说的父子关系书写牵涉时代表象及其内在精神,体现出余华介入现实的可贵坚持。论及文艺作品的现实感时,以赛亚·伯林曾将个人及时代的经验表征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上面的、公开的、得到说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够清楚描述的表层”,这个层面易于感知和表现;而在此之下,还有深层的,“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的、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19]。两部作品中,余华选取“非常典型的符号化情节”[20]来把握时代脉搏和精神走向,诸多看似常见的表象实则渗透着不同时代,尤其是当下人们的生存体验。具体到父子关系书写,《兄弟》写出“代父”的缺失与“父”的精神弱化,造成子辈在乱世中心灵无依,处美人大赛、丰乳推销等情节触碰到这个时代欲望主体的深层经验;《第七天》则指向“拼爹”时代贫贱父子生存的困境,在权钱横行的世道,“代父”与子辈之间的父子情显得如此脆弱。余华小说对“代父”的塑造还存在一条变化的隐线,那就是:从《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在婚后发现一乐非亲生,到《兄弟》里的宋凡平以婚姻为媒介给予李光头爱护,再到《第七天》里杨金彪为了杨飞舍弃婚姻,“代父”形象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与家庭关系的冲突与超脱逐步走向神圣化。这种趋于理想化“代父”的书写,与混乱时代里人们寻求精神依托的隐秘心理息息相关。余华对具有现实感的“代父”的书写,体现出不同时代父子关系的变化,传达出深厚的民间经验,留下丰富的时代印记。
五、结语
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塑造“代父”形象时,写作立场仍飘忽不定;20世纪90年代后,超越血亲关系并逐渐超脱传统家庭关系的“代父”逐渐成为余华小说精神内核的重要支柱。从《在细雨中呼喊》对“父”与“代父”的双重否弃,到《活着》展开启蒙与民间视角的双重叙事,再到《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的丰富性格表现,余华小说塑造“代父”的叙事立场回归到“民间”坚实的大地上。进入21世纪,无论《兄弟》里的父子情深,还是《第七天》里的父子追寻,余华持续关注那些以绝望的坚持抵抗崩塌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底层人物,塑造出与现实血肉相连的“代父”形象。我们之所以未将余华的“代父”书写视为转向,而是视为“回归”,一方面由于余华早期作品已经出现民间“代父”形象;另一方面在于这是余华经历过历史转折,对国家权力中心、知识分子立场审视和抗拒后“向回看”的结果。与那些为外界左右而认同“父亲”的作品不同,余华小说塑造的是温情与残酷并存的“代父”。余华小说的“代父”书写虽随着时代而变化,但“代父”对血亲关系的否定以及由此衍生的对“父”与“代父”的多重审视,自有作家潜入时代精神而抵抗思想潮流的异质性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