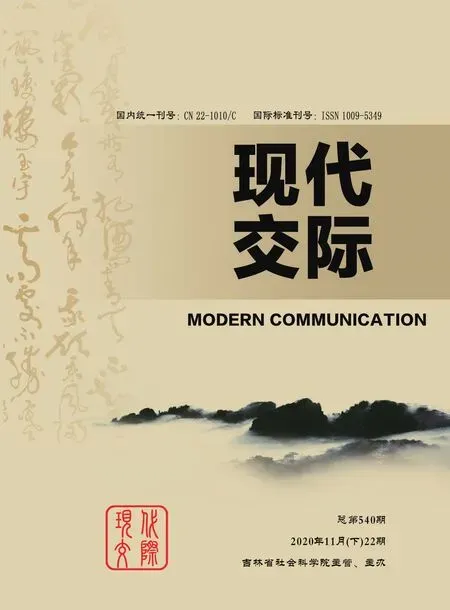理雅各《诗经》译本中女子意象的再创造
(长安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①所说,“诗歌一经翻译便丧失了诗意”,许多学者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译介学从比较文化的角度,以“创造性叛逆”为切入点,提出不同文化语境不但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还影响读者对译作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这为解决诗歌不可译性提供了借鉴。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关注现实生活,大多数诗篇抒发的是对现实生活的真情实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个里程碑,对中国文学史影响深远。《诗经》的历史价值、民俗价值和礼乐文化价值,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受到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英国的著名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就对《诗经》进行了三次重译,在1871—1879年间共创作了三个译本。
在近代中西交流的文化史上,理雅各用自己几十年的心血写下了不平凡的一页。他翻译的中国经典,不仅帮助了传教士,也帮助了西方人认识中国。他的译文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是国际汉学的重要研究资料。从译介学出发,选取理雅各1871年出版的译著《中国经典》的第四卷《诗经》,分析其中女子意象的翻译,探讨理雅各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和文化意象的跨文化变异。
一、译介学与“创造性叛逆”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20世纪提出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1]137这一概念。谢天振教授在读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一书时,与他的翻译观念产生了共鸣并表示赞赏,经过不断的撰写和阐释,于1999年出版专著《译介学》,并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作为其译介学的理论基础。《译介学》一经推出,在国内文学界和翻译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谢天振清楚地指出了译介学与普通翻译学之间的区别,并通过更深入的分析介绍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
译介学原本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探讨文化背景会大大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就中国比较文学的实践而言,文学翻译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重视。
20世纪80到90年代,对比较文学和译介学的理论探讨,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谢天振教授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曾在《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一章中分别概述了在比较文学中翻译学和译介学的学术地位,区别描述了译介学与一般翻译研究,并分析介绍了“创造性叛逆”的思想。在后来的著作《译介学》中,谢天振全面阐述了翻译研究的性质、内容及翻译文学史的编纂方法等。他提出,“译介学”是一种文学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不是在语言层面上如何从源语言转换到目的语,而是关注母语在翻译成外文时的损失、曲解、增删、延伸等问题。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实践,它与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有关。[2]1
翻译行为总是要面对和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些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信息传递,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曲解和增加。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敏锐地指出:“翻译永远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1]137他还说:“如果大家都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行为,那么翻译过程中这些恼人的问题或许就可以解决了。”[1]140事实上,他的“创造性叛逆”指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本质。文学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尤为明显,诗歌的体裁很独特,高度精练的文字与丰富的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使译者翻译的难度增加。[2]73
二、诗歌意象的文化转换
诗歌意象的文化内涵通常被忽略,因为我们往往更多地将其与典故、成语、比喻、谚语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一种修辞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意象的运用可以看作一种修辞手段,但诗歌意象包含着更广泛、更深刻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因此,诗歌意象的转换,反映了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相互碰撞、相互转化、相互沟通、相互接受。诗歌意象的转换,实际上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译者不仅要翻译原始语义信息,还要翻译文化信息。
正如谢天振所言,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译者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接近和再现原作,“叛逆”在大多数情况下反映了译者为了在翻译中实现某种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主观偏离。在诗歌翻译中,译者往往采用多种翻译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翻译目标。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保留、改造和改编。“保留”是指译者保留原有的形象,但突出一些词语,使形象更接近自己的理解。“改造”是指将原来的意象转化为另一种意象,使其能够被接受者理解和接受。“改编”是指译者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比如对原文的误解,以及其他流派思想的影响,对形象进行改编。无论译者采用哪种翻译方法,都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三、理雅各《诗经》译本中的女子意象
在《诗经》中,涉及女子意象的诗篇共101首,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因此,在《诗经》英译中,如何传承原始文本中的诗歌意象,从而重新塑造女性形象成为译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一部分的主题是讨论《诗经》中女子意象的分类及理雅各在翻译时所采用的方法。
根据不同的社会身份,《诗经》中有四种典型的女子意象:少女,未婚妻,新娘和相思的妻子。理雅各在《诗经》中使用许多方法重现女子意象,主要包括保留,改造和改编。
如有学者指出:单向的政府主导的普法模式与大众需求之间已经出现了期望与效果反差巨大的问题。一方面,政府从概念、制度和行动过程中过于强调政府主导和国家立场,鲜少顾及公民的法律需求,久而久之,这种“政府主导型”普法模式逐渐演变为“一厢情愿”的“独白”。另一方面,公民缺乏法权意识,在民间启蒙和维权活动中显然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制概念,特别是在法制建设早期,公民与政府极少有互动。
1.意象的保留
在理雅各的译本中,保留了许多女性的意象,并忠实地传达了原始形象。
Example 1:
ST: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Kai Feng,《凯风》)[3]29
TT:The genial wind from the south Blows on the heart of that jujube tree,Till that heart looks tender and beautiful.What toil and pain did our mother endure! The genial wind from the south Blows on the heart of that jujube tree,Our mother is wise and good; But among us there is none good.There is the cool spring Below (the city of) Jun.We are seven sons,And our mother is full of pain and suffering.The beautiful yellow birds Give forth their pleasant notes.We are seven sons,And cannot compose our mother’s heart.[3]29
这是一首儿子赞美母亲并且责怪自己的诗。在这首诗中,诗人感受到了夏日南风吹拂的温暖,看到了枣树在风的吹拂下渐渐长大,进而想到了母亲养育孩子的艰辛;因此写下了这样自然生动的诗句。诗人将母爱比作“凯风”和“寒泉”,将孩子比作“枣树的嫩芽”。在母亲的精心保护下,幼芽才得以健康成长。“凯风”是南方的暖风,理雅各将其翻译为“The genial wind”,突出“暖”这一词,告诉读者母亲的爱是温暖而柔和的。而他保留了“枣树”和“寒泉”的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被母亲精心保护的儿童形象。“寒泉”便成为母亲之爱的代名词。
2.意象的改造
由于中英文之间的差异,一些中文意象在英译本中不能完全等同或类似于其中文的意思。面对这种“文化缺省”,理雅各充分发挥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对意象进行了一些替换和补偿。
Example 2:
ST: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Jiu Mu,《樛木》)[3]5
TT:In the south are the trees with curved drooping branches,With the dolichos creepers clinging to them.To be rejoiced in is our princely lady:May she repose in her happiness and dignity![3]5
这是一首祝贺新婚的民歌。这首诗歌把男人比作“樛木”,把女人比作“葛藟”。在西方世界中没有“樛木”这一植物,而“樛木”是一种在中国南方生长的树木,它的树枝向下弯曲,所以理雅各在翻译时写出了樛木的特点作为补偿,也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葛藟”生在树下,能护根,藤蔓在树上攀爬生长。这种中文意象的英译很难完全等同其中文的意思,“葛藟”是野葡萄类,为了突出“累”——缠绕之意,因此,理雅各把葡萄藤改造成了“dolichos(一种木质攀缘植物)”,使葡萄藤缠绕树干的画面更加生动,诉说着情侣和恋人之间的亲密无间,情深义重。理雅各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将原来的意象改造成另一意象,用西方读者能够接受的语言最大限度地传承了诗歌意象。
3.意象的改写
受中国儒家经典的思想影响,理雅各对《诗经》中一些形象的改写是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而有的改编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是为了解释,使目标语的读者对原文有一个清晰的理解,让读者更好地接受他的译文。
Example 3:
ST: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Guan Ju,《关雎》)[3]3
TT:Guan-guan go the ospreys,On the islet in the river.The 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 lady:-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3]3
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诗,讲述了一个小伙儿对一位美丽少女的爱慕之情。诗歌以“雎鸠”开篇,其实是有意为之。据说在中国,这种水鸟是多情的;因此,“雎鸠”这个形象暗示着他们的爱情会是美好的,永恒的。理雅各将其简单地译为“鹗”——一种吃鱼的大鸟,俗称鱼鹰,失去了形象的暗示;而且“窈窕”在原文中是文静而美好的意思,理雅各将其译为“谦虚、腼腆、贤良、年轻”,这不仅拓展了“窈窕”的含义,也体现了少女的羞涩。理雅各是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四、译介学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译介学的出现,为文学翻译带来了新的方向。译介学所提出的“创造性叛逆”和“译者主体性”为中国文学翻译提供了许多新思路和新方法。
首先,翻译的目的要从文化目的转变为文化交流与文学价值相结合的目的。中国古典文学要走出去,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对文化的准确解读,这是基本要素。过度和肤浅的文化解读不能保证翻译的忠实度。二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海外是否被接受,接受度受制于翻译的文学性。[4]因此,既要保证译本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又要融入读者的本土文化特色,既要有长久的审美效果,又要有普遍的实用价值,是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的重点。
其次,译者应采取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在1871年出版的《诗经》译本中,理雅各采取了尊重源语的异化翻译策略,用无韵律的翻译——散文体②完整地阐释了《诗经》的文化内涵。由于译文中冗长的引言、大量的注释和复杂的表达方式,使得1871年版本只受中国文化研究者的推崇。在1876年的译本中,理雅各开始关注读者,采用有韵律的翻译策略——韵文体③来满足一般读者的需求。因此,译者应充分协调中外文化,利用异化策略来保证文化传播的准确性。同时,要充分利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来满足海外读者的需求。
最后,中国古典文学的外译应该由国内学者和海外译者共同完成。理雅各《诗经》的翻译和出版不是他一个人努力的结果,中国学者王韬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5]没有王韬的帮助,理雅各版本的翻译和出版很难成功。理雅各曾经说,他译本中注释的多元性和完整性主要归功于王韬的作品。可见,中外合作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有很大的帮助。
注释:
①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20 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诗人之一,被称为“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
②是一种不讲究音韵或排比的散体文章,较少用典、不尚藻饰,包括散文、杂文、随笔、游记等。
③韵文是讲究格律、大多数要求押韵的文体或文章,包括赋、诗歌、词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