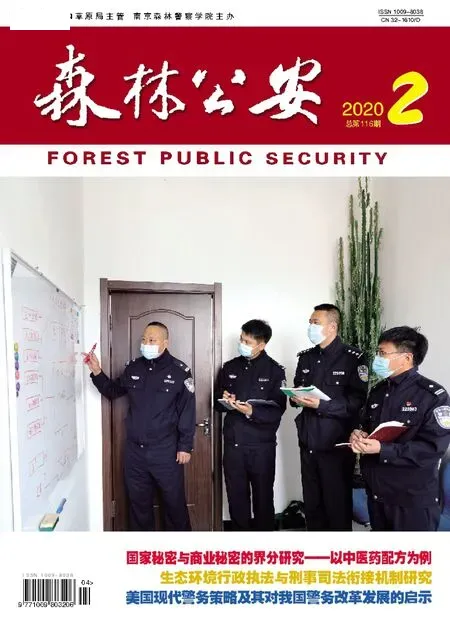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情节犯还是抽象危险犯
冯锦华
(作者系山西省森林公安局太行山分局法制科长)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虎纹蛙2只或者红腹锦鸡1只,是构成行政违法行为还是犯罪,或者说,应该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给予行为人行政处罚,还是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给予行为人刑事处罚。应当说,在2017年1月1日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施行之前,这一问题根本不难回答,但在新《野生动物保护法》施行之后,却在一些法律人当中至少在相当一部分森林公安民警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困惑。
困惑在于,《刑法》和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存在着“矛盾”。《刑法》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根据该规定,违法猎捕虎纹蛙2只或者红腹锦鸡1只,无疑构成犯罪,行为人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新《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相关自然保护区域、禁猎(渔)区、禁猎(渔)期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未按照特许猎捕证规定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条进行解读,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似乎分为两种情形:只有严重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才构成犯罪,进而承担刑事责任,而一般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只构成行政违法,只需承担行政责任。违法猎捕虎纹蛙2只或者红腹锦鸡1只,究竟属于一般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还是属于严重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却查无正条莫衷一是。
有论者出于“调和两法规定矛盾”的动机,基于检法机关对这种“违法猎捕虎纹蛙2只或者红腹锦鸡1只的行为”通常不会作为犯罪处理的作法,推测其背后的逻辑是《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换言之,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并非一律构成犯罪,只有情节较重的方可入罪,猎捕虎纹蛙2只或者红腹锦鸡1只,数量极少,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因而不构成犯罪。这一论断貌似很有道理,而且为新《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的适用留下了空间,好像颇为完满。但是,这种观点却生生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曲解为情节犯,且罔顾诸多行刑衔接规定的精神内核,以新《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为判断的出发点,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必然有失周全。
一、在犯罪成立意义上,一种犯罪属于情节犯还是抽象危险犯只应看刑法分则规范
抽象危险是立法推定的危险,不需要法官加以判断,只要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即可构成抽象危险犯。而对情节犯来说,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构成要件行为,尚不足以构成犯罪,还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程度。在犯罪成立的语境中,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于抽象危险犯,而不是情节犯。对于这一点,稍微具备些刑法理论知识的人,即使不能如数家珍般地脱口而出,但只要一看刑法条文便可知晓。《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该规定清楚地表明,只要实施了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有无猎获物、猎获物多少均在所不问),不需要再额外附加条件,即满足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不是“出罪标准”,而是“入罪限制条件”。犯罪构成要件(即罪状)是违法类型,所描述的都是值得科处刑罚的违法行为,只要行为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就应当认定为犯罪;而符合但书规定的行为原本就不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该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为由认定为不构成犯罪,而不能以行为虽然符合构成要件但情节显著轻微为理由宣告无罪。猎捕虎纹蛙2只或者红腹锦鸡1只的行为,显然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构成要件,以但书规定出罪,不仅误解了该规定的功能定位,挑战了学界对抽象危险犯意涵的共识,使该罪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法益的目的落空,而且做法武断理由粗疏,有违刑法精细化特质,实难让人信服。
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以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义务性规范为前提,《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行政处罚条款不能成为该罪的前置法
行政犯具有双重违法性,即首先需要违反有关行政法的规定,其次还要违反刑法分则的规定,而且行政违法性寓于刑事违法性之中,行政违法性是构成要件符合性中的内容。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于行政犯,毫不例外具有双重违法性。但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双重违法性的特别之处在于,根据其客观构成要件,其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完全重合的,即只要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就同时具备了刑事违法性,因而构成犯罪。需要注意的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违法”,仅限于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义务性规范(包括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该罪也只是在构成要件要素层面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义务性规范予以摄取,而不包括对有关的行政处罚条款的遵从。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有关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义务性规范一共四个,分别是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亦即《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所概括的“在相关自然保护区域、禁猎(渔)区、禁猎(渔)期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未按照特许猎捕证规定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所规定的“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不能成为判断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否成立应该考虑的因素。
三、《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理解和适用
有了前文的分析作铺垫,再看《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就很容易理解:该条没有也不能够改变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抽象危险犯属性;该条也非立法怪胎,使人陷入对其不可知的境地。《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就是对同时属于行政犯的行政违法行为设定了一个行政处罚,它没有否认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也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亦即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二者并行不悖。
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对于非法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虎纹蛙2只或者红腹锦鸡1只,构成行政违法行为还是犯罪的问题,产生困惑的原因在于受到对旧《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过度解读的影响。旧《野生动物保护法》只规定“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没有对该行为设定行政处罚,一些人因此想当然地认为,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的界限泾渭分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适用势不两立。
上述推理是非常经不起推敲的。关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并罚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下称《行政处罚法》)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下称《移送涉罪案件规定》)当中,均可找到端倪。《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该条不止规定了行政机关对行政犯的行为人先给予行政拘留、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的刑期(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和罚金,同时也肯定了行政处罚(行政拘留、罚款)的合法性。《移送涉罪案件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该条也表明行政机关对行政犯的行为人作出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是合法的。有人提出质疑,《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限于人民法院判决前,且既已折抵,何来并罚一说?《移送涉罪案件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也只限于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前作出的处罚,如何能成为普适性的规则?其实这些都很好解释。首先,法律人都知道刑法上的“数罪并罚”制度,“并罚”并不等于把对行为人各罪判处的刑罚(包括刑种和刑度)直接简单相加,而是要根据不同的刑罚分别采取吸收原则、限制加重原则或并科原则予以“并罚”。《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折抵就相当于“数罪并罚”制度的“吸收原则”。其次,《行政处罚法》虽然只规定了在人民法院判决前给予行政犯行为人行政拘留、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的刑期和罚金,但并不意味着在人民法院判决后就不能给予该行为人行政拘留、罚款处罚。至少,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仍可给予行为人行政拘留、罚款处罚:一是罚款数额高于罚金,因为折抵的数额是“相应”,相应即相等,判决前行政机关给予行为人罚款1万元,判决罚金6000元,“相应折抵”后,行为人最终还是缴纳1万元,只不过6000元属于罚金,另外4000元属于罚款,以此推理,人民法院判决后,如应罚款数额高于罚金,则仍可对行为人处以罚款,否则该制度哪有公平可言?二是人民法院对行为人不予刑事处罚后,行政机关可依法给予行为人行政拘留、罚款处罚。最后,《移送涉罪案件规定》作出上述规定,只是出于“刑事优先”的程序考量,并非否认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送后甚至判决作出后作出上述实体行政处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打个比方,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如果移送前行政机关未对行为人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仍可在之后对其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否则行为人竟可因此规定而变相获益,这一结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之所以用《行政处罚法》和《移送涉罪案件规定》的有关规定来分析《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的含义,本质上是因为《行政处罚法》和《移送涉罪案件规定》的规定是规范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关系的法源(《移送涉罪案件规定》虽然仅为行政法规,但不影响其总则性定位,正如《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属于宪法性规定一样),是关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并罚的总则性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和源自该条的《移送涉罪案件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囊括了除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之外的大部分行政处罚种类,足以为“行刑并罚”提供一般性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还是法律解释活动,都应遵循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而从单个的行政法、经济法当中“推导”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关系的一般法则的作法无异于管中窥豹。以新《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作为逻辑起点对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关系的一般性规则作出推断,起码在法律推理的方法论上犯了错误。
然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并非无懈可击。该条在规定行政处罚之后,接着写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来,在行政法或者经济法当中,此类条文既没有规定新的罪状,也没有规定应判处的刑罚,纯属注意规定或提示性规定,有没有这半截条文都无关宏旨。但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却与该提示性的刑事责任规定用分号隔离,而分号在语法上只能用于复句内部有着并列、选择或转折关系的分句之间的停顿。再结合分号前后的语义进行分析,分号前面所列的行为,应当理解为是不构成犯罪的,这也是很多人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理解为情节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一点实在是立法者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