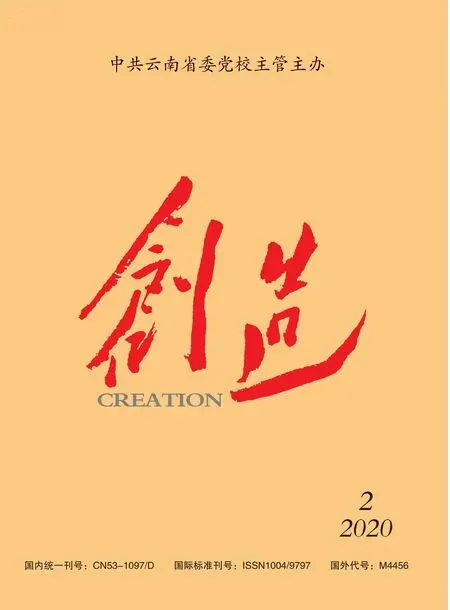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论班洪事件对班洪佤族人国家认同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1934年1月20日,英缅当局为抢占位于中国云南省班洪地区的银矿资源,利用中缅划界未定的时机,悍然派兵侵入班洪,武力夺取了炉房银矿,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班洪事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班洪事件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是以英国人D·G·E·霍尔为代表的部分外国学者,认为此地“是无主之地”、侵犯了“英国的领土”。[1]847第二种是国内主流学界高度赞扬了班洪佤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2]第三种观点认为“其之所以采取亲华抗英的举动,仅系出自一小撮部族首领的意愿,乃基于地缘因素和政治现实所作出的选择”。[3]针对这三种不同观点,本文重新梳理史料,分析对比班洪事件前后当地佤族人的国家认同情况,论证班洪事件对班洪佤族人现代国家认同意识形成的影响。
一、班洪的历史与现实
班洪地区,位于北纬23°,东经99°线交界处,在今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西南部,北邻耿马县、镇康县,东南是勐角乡、勐董乡,西南是缅甸,主要包括今沧源县班洪乡、班老乡、南腊乡,以及缅甸部分地区。整个班洪地区全部处于佧佤山区,耕地面积狭小,全区被数十万亩原始森林覆盖,山中蕴藏着丰富的金、银、铅矿,尤以班老勐弄山和南腊湖广山的银矿最为丰富。班洪地区很久以前就是佤族人民的聚居地,“直至解放时总人口约一千五百余户,共八千余人,其中佤族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四,其他为汉、傈僳、拉祜、傣族等民族”。[4]2
汉朝时,班洪即属永昌郡管辖;唐宋时期,属南诏、大理;元朝时属云南行省银沙罗甸宣慰司。明清时期,佧佤山区被称为“葫芦王地”,班洪即位于上葫芦王地,明朝时属孟定府,清朝前期属顺宁府耿马土司。乾隆年间,班老勐弄山发现银矿,石屏人吴尚贤与班老王峰筑立约盟誓,合作开矿,以勐弄谐音取名“茂隆厂”。由于经营得法,“厂例无尊卑,皆以兄弟相称”,“使各民族厂工之间团结和睦,出现了矿沙(砂)大旺,厂地人民,各守天朝法度,路不拾遗的兴旺盛况,茂隆厂的规模越办越大,人数达三万之众”。[4]4-5但由于课税被贪污,以及官方的忌惮,云贵总督以不交课银和“恐滋生事端”的罪名将吴尚贤治死于狱中,茂隆厂很快便衰败下来。吴尚贤离开前,留下木刻、信物,要峰筑保存,以便日后对证,不让他人开采。后来,茂隆厂旧址炉房由班洪、班老、永邦三部共同看守。[5]3831
明朝时,班洪部只是“葫芦王地”的一个小部落,属南板大户管辖,后来胡姓“官家”[6]势力发展,逐步征服了周边绍兴、班老、永邦、芒国、业烈、甘塞等十多个部落,脱离了耿马土司。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调停猛渗、勐角董土司争斗有功,“上葫芦王土目胡玉山,着赏给土都司衔”,[7]7-8俗称“班洪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云贵总督王文韶、藩台刘椿霖,会诏班洪王到省,赐给衣服等物,并宣示政府德政,令归故土镇守”。[8]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封胡玉山第二[9]为班洪总管。
毫无疑问,班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不是霍尔所说的“无主之地”。自乾隆征缅之后,滇缅边境保持了持久的和平,对于班洪属于中国,缅甸也从无异议。但是自英国占领缅甸后,为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打通进入中国内地的“印缅—扬子江”通道,英国殖民政府挑起了一系列边境冲突,迫使中国在划界时不断退让。其对阿佤山区的觊觎也由来已久,1886年两次派厄廖特、赫布德、布莱特等100余人潜入沧源,进行武装侦察;1900年勘界时,又挑起“黄果事件”。据邓际可记载:葫芦王地,原分上、下两部分,“下葫芦王地,在清朝中缅界约时,已允划归英缅,现所余者,仅上葫芦王地耳。”[8]
1899—1900年,中英双方对滇缅南段进行会勘,但双方对佧佤山区边界划分的分歧巨大。会勘失败后,中英双方各向对方提交了一条边界线,清政府勘界大员刘万胜、陈灿提出的边界线中方称黄线,英方称刘陈线;英方勘界委员司格德提出的边界线英方称司格德线,中方称红线。此后,双方多次就此段边界线交涉,均无结果,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中缅“南段未定界”。
根据刘万胜、陈灿的叙述:“循高山岭至猛林山,以山之东班洪所属各寨归中,山之西班况所属各寨地方归英。即顺猛林山山脊而行至帕唱山,南下至大南滚河,以帕唱山东班洪所管之永邦等寨归中,山之西班弄等寨归英。”[10]15据方国瑜调查:“班况、班洪,同宗两支,刘万胜司格德划界时所谓班洪归中,班况归英者,即指班洪一派所属之各王地归中,班况一派所属之王地归英,非仅于班洪、班况二王地也”。[7]25刘万胜、陈灿的划分方式显然是考虑到了现实因素和山川走势,按照班洪、班况两部的势力范围划分,属于相对合乎情理划线方式。这样,包括永邦、炉房、班老等地均属中国。“可问题就出在界线的文字叙述与刘、陈所绘之图不相一致。图线实际经过的不是帕唱山而是班老山,帕唱山还远在西南。”[11]永邦、炉房在刘万胜、陈灿提交的地图上被错划到了英国一侧。班洪事件发生后,英国之所以一直声称自己没有越过刘陈线,炉房是英国领土,原因即在于他们发现了这个漏洞。
事实上,英国人不但越过了刘陈线,还越过了刘万胜、陈灿在地图上错绘的线(即英国人声称的刘陈线)。1934年2月12日,英军设计偷渡南依河,用燃烧弹轰击班老寨,“顷刻间班老上下寨变成了一片火海,火光冲天”,“三月二十三日再次用燃烧弹烧毁班老,并烧了孔岩、永来、永惹、永赖、永贺、永弄等寨,打死打伤民族武装和百姓众人”。[4]16-17而当李占贤(又名李希哲)组织云南各地爱国志士成立“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即霍尔所说的土匪),支援班洪,帮助佤族人民击退英军时,英国人反诬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是土匪,“污蔑李希哲兵常越国界到缅甸烧杀抢掠,要求蒋介石政府惩治,否则要负国际责任”。[4]30
通过殖民侵略,挑起边界事件,逼迫中国退让,把中国的固有领土变成争议区,然后武力侵占,进而将中国人的抵抗说成对英国人的侵犯,这不过是殖民者惯用的伎俩罢了。霍尔所谓的“多年来,这块地方一直被视为无主之地”,“不料勘矿人员竟被佤族人和中国的‘土匪’赶了出来。他们竟进而侵入英国的领土,以致英方不得不武力对付。”[1]847很显然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上,颠倒黑白的说法。
二、与内地的脆弱联系
班洪虽然自古即属于中国领土,但国民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管理严重缺失。班洪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竟无人知晓当地情况,与英国交涉时,英国人坚称炉房位于中国声索线“黄线” (英称刘陈线)之外,属于英国领土,而国内舆论又强烈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抵制英国侵略。处境被动的国民政府遂派遣周光倬以“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的身份,前往班洪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周光倬的记载:
“汉人举家迁至班洪境内者不少,尤以镇康籍最多,皆成家立业,大有乐不思蜀之慨……且矿区附近,至今仍遗留有吴尚贤时开矿之后裔。汉人既入班洪者众,流风遗泽,影响于班洪土人之开化者甚大。经英人利诱威逼之不愿降英者,其心理之建树,即根源于此也。所谓已故之班洪老王胡玉山(第二)即懂汉话,其兄弟及子辈均通汉语,可想汉化之深入。”[12]43
在周光倬笔下,班洪俨然一派“王化之地”,“汉化”极深。但仔细对比其他史料即可发现,这一说法并不可靠。首先,周光倬入班洪是1934年10月之后,中英双方的冲突已经结束数月之久,当地各族人民在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当地人仍需国家的支持,对周光倬的到来当然是欢欣鼓舞,极力讨好。周光倬本人也是代表政府而来,其记录带有政治目的。其次,据方国瑜记载:嘉庆年间“(茂隆)厂散,必有流落于斯土者,因地僻,化为土人”。[7]15《沧源文史资料选辑》 记载的更是清楚:“茂隆厂衰败后,厂工们有的到缅甸谋生,有的就地自立为寨务农为生,与当地佤族结婚变成佤族了。”[4]5也就是说,在班洪的汉人非但没有助土人“开化”,反而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化为土人”了。第三,周光倬记载的最大破绽则是:认为已故的班洪老王胡玉山第二即懂汉话,其兄弟及子辈均通汉语。实际根据方国瑜记载:“总管胡忠汉,解余语,惟出口乞乞不能畅达,闻乃祖胡玉山时代,班洪无一人粗通汉语,有与汉官交涉,则自耿马请通事云”;“卡剌无文字,用摆夷(傣族旧称) 文,且写摆夷语,而不能拼卡剌音也,今班洪境内来往公文,悉摆夷字,而识汉字者极少,偶有汉文公事,则请孟定师爷翻译之。”[7]46-47班洪事件爆发时,班洪王的《告祖国同胞书》等文件,即皆为傣文,经人翻译才成汉语。倘若班洪各部落,有人能通汉文汉语者,又何须他人翻译?
在政治方面,班洪地区受傣族土司影响较深,初步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传至胡忠汉时,已经有四五代。“班洪之待人民,并不似沿边土司之苛征暴敛,非有所需,不向人民摊派。按例每两年始由各村上纳一次,且数额亦微,故人民极爱戴之。”[12]45在当地人的意识中,“官家是天生的官家,百姓天生就是百姓,百姓应服从官家管”;“1957年,胡中华去北京开会,停留时间较长约5个月,南板大户的群众便反映:‘我们的大官哪里去了,是不是被汉人关起来了,快回来吧!’并杀猪祈祷,盼大官快回。好像他们没有了班洪王就不能生活似的。”[13]284因此,班洪王家族在当地的统治相当稳固,对外部权威的依赖极小。清政府赐予班洪王的木印被耿马土司得到后,要求其出500两白银赎回,但班洪王并不为其所动,而是直接伪造了一颗印使用,“土人犹能道其始末焉”,[7]9却不以为意。周光倬也认为政府向来“并不采取积极经营态度,完全放任,政治上以其境土小,又于卡瓦山围内,故并未直接统治,似居于半独立性质之地位”。[12]38当地人甚至对内地朝代的变更都不清楚,只知道北方有一个“大汉朝”,班洪事件爆发后,班洪王仍有使用“大汉朝”来称呼中国。
在经济方面,班洪地区则受英国的经济渗透非常严重。据赵云岩的调查报告:“惟仅20年来,样(洋) 线洋布,多由缅甸输入”,“滇西南之各盐场税捐太重,且转运困难,以致沿边土民,尽食海盐(缅甸盐),云南盐政,大受影响,即如腾冲、永昌、龙陵、镇康、缅宁等县,亦多半食海盐”。[14]在英国的经济渗透之下,班洪地区已很少使用中国货币,而是以印度卢比为征税、储藏、送礼的手段。“班洪居民,每户年纳一卢比,或少数临时征收,年约得二千卢比”;“乃父胡玉山第二,曾以三千卢比装一罐计二十罐,私埋之”;“班洪有丧,班老、永邦各送二十五卢比以为礼”。[7]10、11、18
此外,佤族人在解放前普遍保留了一个令外人毛骨悚然的习俗——猎头祭谷。佤族的猎头祭谷的习俗由来已久,他们以人头祭祀,祈祷丰收,尤其喜欢胡须旺盛者,用以象征丰收的谷穗。为收集符合条件的人头,甚至公开买卖。民国年间,有一笔名殿生者在佤族地区调查后记载:“白人的头可以值到三百多卢比一个,汉人中的美髯公的头可值到二百卢比一个,汉人而无胡须的头可值九十多卢比一个,其他如摆夷、猓黑人(拉祜族旧称)的头很不值钱……祭祀将到而又杀不到白种人、汉人、摆夷、猓黑等的头时他们才去杀别一村卡瓦人的头……如果这村的卡瓦去杀了那村的人头,便成了仇家。”[15]成为仇家的两个村寨会经常性的展开械斗、仇杀,“因此他们除了仇家村寨互相仇杀砍头之外,比较乐意猎取外民族的人头”。[13]333周光倬在途经卡瓦山时,即对此惊恐万分,“野卡杀头之风,至今未止……故倬之由班洪入猛角董,无异置身绝域,未得解衣而卧者两昼夜……皆栗栗危惧,深恐事变之莅临”。[12]14因此,除了少数与当地头人相熟的商贩外,几乎没有外人愿意进入该地。
综上所述,在班洪事件爆发前,国民政府并不注意在班洪地区的经营管理,当地几乎处于完全放任状态。班洪的统治者自有一套管理方式,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民族地方传统的统治秩序,事实上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在经济上,班洪地区受英国的经济渗透非常严重;文化上则受傣族影响,通行傣文、傣语,通晓汉语者极少。再加上佤族的猎头祭谷习俗,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民族关系,阻碍了班洪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而根据罗之基的调查发现,班洪地区受傣族土司的影响,社会发展阶段仍处于封建领主制时代,还带有原始民主制的残余,[13]279-287赵云岩的调查报告甚至认为一些土人“尚结绳木刻记事”。[14]在这种情况下,班洪佤族人“既没有政治的概念,更没有国家的观念”,[16]75更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感。在当时的班洪,只有少数人知道在阿佤山的北方有一个汉人的大汉朝,自己属于大汉朝管,更多的人只能通过民谣和传说来回忆诸葛亮[17]、吴尚贤时期佤汉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属于相对传统的、模糊的认同方式。
三、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
国家认同是指确认自己国家归属的一种心理活动。班洪事件爆发前,由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严重缺失,班洪佤族人难以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意识。但是国家认同感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长期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具体到我国,则是近代以来我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认同意识。班洪佤族人的现代国家认同观念即是在抗击英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的。
1929年,美国矿冶工程师卓柏考察茂隆银矿后,“称茂隆银矿为‘亚洲第一富矿’,含银量高出缅甸可卜公司的波隆银矿3倍多”。[18]19探矿的结果非常喜人,但是彼时的中国却根本无力开采,反而引起了英缅殖民机构缅甸有限公司的垂涎。缅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伍波朗先是收买周边部落头人班弄马美廷(回族)、永邦王之弟小麻哈(佤族)、户板宋钟福(汉族),签订了一个“开办炉房银矿办法”,继而以重金引诱班洪王胡玉山第二、班老头人胡玉堂等人同意开矿,遭到二人的严词拒绝。钱财收买不成,英国人即开始准备武力夺取炉房银矿,“从1933年10月起,英集结上千军队,招募数千民工开挖公路,修筑工事和军事设施,进行全面备战”。[19]649
1934年1月20日,准备完毕的英军武力进占炉房,班洪事件正式爆发。炉房银矿本是班洪、班老、永邦三部共同看管,且永邦、炉房、班老均属班洪王辖地,班洪佤族人当然不能容忍英国人的侵略行为。班洪王胡玉山第二召集下辖的17个部落王开会,剽牛盟誓,约定每户出兵一人,共抗英军,并向内地发布《告急求援书》、《告祖国同胞书》,寻求支援。2月8日,战斗正式打响,班洪各部“按每户抽调一名兵员,共计约1500人,使用弩、大刀、标枪、长矛、三叉矛、铜炮枪、土药火炮等”,[19]650分三路攻向丫口、永邦、芒相,很快攻占了丫口、永邦,但在芒相受挫,被装备先进的英军逼退至南依河。
2月12日,英军越过自己声称的刘陈线,偷渡南依河,用燃烧弹轰击班老寨,整个班老寨陷入一片火海。3月23日,英军再次烧毁了班老,以及孔岩、永惹、永莱、永贺、永弄等村寨,大举进攻龙头山,危急时“上下班老9个寨子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动、妇女儿童纷纷赶上前线”,[16]10但仍然不敌占据优势的英军,被迫从班老撤退。英军则在村外路上遍撒银元,企图诱降班老寨人,班老人则回答说:“我们用的土锅、土碗都是用中国土做的,我们喝的是中国水,烧的是中国柴,活着是中国人,死了还是中国人!”[20]
3月26日,胡玉堂率领佤族人民在龙头山四面放火烧山,烧毁了龙头山英军营地,并在南滚河伏击英军溃兵,胡玉山第二也两次组织兵力进攻丫口。英军惊慌失措,慌忙向芒相方向撤退。军事失利的英军再次劝胡玉山第二投降,“胡玉山第二回答说:‘我们祖祖辈辈只知道中国,我们不想做英国人的牛马!’”[4]18为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班洪佤族人民投降,英军突袭了芒国寨,“英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芒国寨兵民死伤50余(人),寨子被夷为平地”。[19]650班洪抗英局势开始持续恶化,佤族民兵只能分散到山林中打游击,直到5月份“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的到来。
班洪事件传入内地后,舆论沸腾,各大报刊争相报道,部分爱国人士成立了“云南民众后援会”、“划界促进委员会”等爱国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帝浪潮。云南省第二殖边督办杨益谦、镇康县长纳汝珍、勐角董土司纷纷予以物质支援和慰问。景谷县爱国志士李占贤(又名李希哲)在杨益谦的支持下,把经商所得的数万元钱用于购买武器和军饷,召集汉、佤、傣、拉祜、彝等族的农民、盐工、民团、青年学生、爱国华侨、马脚,共计1400余人组成“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支援班洪。
义勇军的到来受到佤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李占贤与班洪各王盟誓:“各王永远服从中国政府,无论何时,不得退出中国投英;实行汉佧联合,以固中国边地……汉军将士有保卫佧佤人民之义务,双方立约遵守。”[21]15义勇军的军纪严格,士气高昂,“因他(李占贤)言随法行,故撤退前,纪律一直很好……我们义勇军中傣族人几乎占半数,语言流畅,平时军民相处,亲如姐妹”。[21]271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协力作战,经过丫口、炉房、南大三次战斗,击毙英军60人,[20]将英军赶到了滚弄江边。6月,战事停止,军事侵略失败的英国人,转而通过外交手段,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污蔑义勇军不识地图,越界到缅甸烧杀抢掠。在外交压力下,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被迫撤退、遣散。
在战争期间,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余户的班洪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参战。危急时刻,男女老少、妇女儿童都纷纷赶上前线,或直接参加战斗,或打草、送饭,或挖掘战壕、运送物质,或打探敌情。战斗失利,面对英军的威逼利诱,所有人均不为所动。指挥员俄潘,身负重伤仍独自坚守战壕,增援的人员要把他抬下阵地,他总是不肯,他说“为了不让乡亲们受苦,为了保卫中国,不让英国人打进来,战壕不塌完,我还不能退。只要我不死,就要接着打!”[21]472平民出身的向坎,被英军俘虏后,英军“用鞭子抽打,逼他投降,他不畏强暴,面不改色,破口大骂英国军官。英国军官又改用软办法,用金、银收买他带路,他仍大骂不止”。最后被“浇上汽油放火烧身,向坎仍骂声不绝,宁死不屈”。[21]474女英雄俄梦,号召妇女不要怕洋人炮火,发动妇女送水、送弹药、修筑工事,“深入英军营房侦察敌人内情”。[21]476整个战争期间,班洪有十多个寨子被烧毁,不计平民,民兵死伤93人。[20]可见,班洪抗英绝非“出自一小撮部族首领的意愿”。[3]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各民族的联合抗英行动,班洪佤族人民觉醒了国家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从英国人准备开采银矿之日起,就不断地用重金引诱班洪人民投靠英国,但是班洪人民从上到下,不论“官家”还是平民百姓,不论局势如何恶化,都坚决不降,始终坚持自己的中国立场。当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到来时,班洪上下热烈欢迎,和义勇军剽牛盟誓:“各王永远服从中国政府,无论何时,不得退出中国投英”,还送给义勇军大量物质。“班洪附近人民,送牛几十头,养猪不多,也送了几头,送酒、芭蕉果、牛肚子果、草烟、洋茄、笋子等,我们用盐巴作为还礼”,甚至发展到“军队常到勐角董赶街,她们(佤族姑娘)经常把几十文小洋交付代买东西”。[21]271没有深厚的情谊、充分的信任,这是绝对不可能。义勇军离开时,“沿路村寨佤族男女老幼聚道热情送行……佤族同胞送水、送茶、送酒、送水果,挥泪与我们依依惜别”。[21]327
班洪抗英的过程即是边境各族人民促进团结友爱、发展亲密关系的过程,“正是这种民族间的共同作战,消除了佤族与汉民族的长久隔阂,构建起同一地域同宗、同源的国家观念”。[16]71当地的佤族人民已经完全认识到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四、最终归属
班洪事件发生时,南京国民政府急需英美等国的支持,并不愿因此事与英国发生冲突,为避免再次发生边界冲突,于是向英国提出勘定滇缅未定边界。英国原本只是计划占领炉房银矿,也不愿扩大冲突,因此同意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边界问题。
经过双方多次交涉,1935年4月,双方同意组成“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会勘委员会”,其中,中方委员梁宇皋、尹明德,英方委员克莱规(T.Glagu)、革乐斯(F.S.Grose),国际联盟指派瑞士人伊士林(Colonel Isecin)任中立委员。勘界会议分上下两届,上届于1935年12月1日开始,共开会67次,询问英方证人12名,我方证人22名;下届于1936年12月31日开始,共开会49次,询问中方证人26名,英方无证人。
在勘界期间,英国人坚持非法的“司格德红线”,针对英国人的阴谋,班洪佤族人民广泛收集证明佧佤山属于中国的证据,严密保管各种官印木刻。1936年班洪17部落再次“剽牛盟誓”,拿出各种印鉴信物,发誓一定要归属中国,并发表了著名《告全国同胞书》,表示“我佧佤山本为本国领土,应归中国”。[21]171937年正月,由于会勘不占优势,英方委员革乐斯,突然提出休会两周,秘密派人携带礼物意图收买佤族寨头人,“但村寨寨门已闭,门外丛林中布满有毒竹钉,设立陷阱,不许英人入寨”。[21]205-2061937年春,班洪17位部落王给中立委员长伊士林递交《请愿书》,表示“敝王等以卡瓦山地为中国边土,卡瓦山民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是我卡瓦山地与中国为一体,不能分割也”。[4]24勘界时,英方为多占土地,擅自偷立界桩,伪造边界标志,“胡玉堂、保卫国又发动佤族同胞挖了英国人偷立栽的界桩。他号召佤族人说:‘石桩、铁桩都要挖,红线、黄线都要拆,‘葫芦王地’和大汉朝不可分!’”[21]460由于当地人民坚持归属中国,会勘优势均在中方,英国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勘界工作停止。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英国却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要挟中国。此时中国又急需英国协助修通滇缅铁路,运输抗战物资,国民政府被迫妥协,于1941年6月与英国划定了南段未定边界线,即1941年线。1941年线把佧佤山3/4的土地划归了英缅,班洪大部分地区被割让给了英国。但是当地佤族人民坚决不予承认,还组织了阿佤山游击支队、班洪自卫支队等游击队,协助中国远征军抗日。“一九四四年,缅官达带领六个随员到班老登记户口,第二年即来要门户钱,但班老不给,对缅官说:‘我们归中国管,不受缅甸管’。”此后缅甸政府不断逼迫当地佤族人民服从管理,甚至威胁保卫国说:“我们杀你就象(像)杀鸡一样容易,以后你不听话就杀掉你!”[4]29但是佤族人民始终不为所动。
新中国成立后,胡玉堂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受邀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胡玉堂受佤族人民所托,将祖传的木刻、信物、历代政府颁发的印件交给中央,表达了希望回归祖国的愿望。“一九六〇年,中缅在户板划界开会时,班老头人保卫国在会上仍然坚持着‘班老归中国的立场’。会后,缅官无奈地对保卫国说:‘这次算你是中国人!’”[4]29同年10月1日,中国与缅甸签署《中缅边界条约》,[22]对中缅边界进行调整,其中,第二条规定“班洪、班老部落辖区移交中国”。1961年6月5日,中缅两国发布联合公报,[23]宣布6月4日正式完成了领土交接。班洪佤族人民终于回归了祖国!
班洪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严重缺失,在班洪事件发生前,当地社会的发展阶段非常落后,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也非常脆弱。班洪佤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仍停留在传统的阶段,无法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意识。班洪事件发生后,班洪佤族人民在各民族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过程中,普遍认识到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正如云南前任教育厅长杨崇龙所说:“知道自己是中国人。”[24]可以说,班洪事件促成了班洪佤族人民现代国家认同意识的产生与形成。正是在这一强烈的国家意识的影响下,班洪虽一度被划入缅甸,但班洪人民一直坚持斗争二十余年,最终在新中国的支持下回归祖国,演奏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