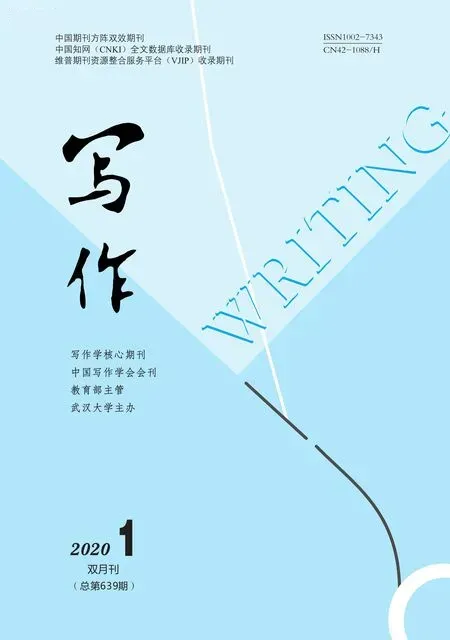文本的时空呈现
——高校写作教学改革思考之二
柳宏 王逊
20世纪以来,中国写作学研究及写作教学实践前赴后继,著述林立,观点纷呈,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多评点欣赏、批评训诫,少理性思辨、体系建构;多整体观照、模糊感悟,少具体分析、清晰透视。如重直觉体验、轻理性分析,或模糊写作学与文章学界限,将写作行为与文章成品混为一谈。如有关写作范畴、写作概念虽不乏鞭辟入里的思考和深刻新颖的见解,但零散封闭,缺少聚焦综合。另外,改革开放以后40多年的跋涉探索,高校写作教学到底教什么?究竟如何教?教学效果如何?仍然没有准确的定位、清晰的思路和满意的答案。
笔者在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写作定义中反复比较,从各种各样的创作实践中对比互勘,针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结合高校写作教学的探索历程和实际效果,提出“写作是呈现文本的行为”的新命题①柳宏、王逊:《写作即呈现——写作定义及高校写作教学改革之思考》,《写作》2018年第2期。。这一命题,突出了写作的文本目标,聚焦了写作的呈现特征,强化了写作的行为过程。该命题认为,写作行为必须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必须进入文本操作阶段方能产出物化的文本成果。“呈现”即“制作”“创造”“创制”,“呈现”一词具有宽广的包容性,能够泛指一切写作现象。“呈现”即生成“文本”,无论是主体世界丰富复杂的精神活动,还是客体世界栩栩如生的曼妙形象,都要通过笔墨键盘书写敲打,转换物化为书面语言文本。故呈现的过程就是文本形塑的过程。
“写作是呈现文本的行为”这一命题仅仅回答了“写作是什么”的问题,“写作呈现什么”是紧随其后必须追问的命题,即解决“写作写什么”的问题。放眼古今中外形形色色、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稍作抽象归纳,不外乎人和事、情和景、时与空。笔者此前曾对“情景”呈现作出了粗浅思考与探索。情感可分为普通情感与文学情感,文学情感源于普通情感、高于普通情感。文学情感在写作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它驱动了文本的生成、使文本充满生气、令文本五彩缤纷。在写景文本中,有的是较为纯粹的景观呈现,有时还寄寓了写作主体其他方面的目标和诉求,它们通常围绕着与人物、情节、主题的关系综合展开,增添了作品的形象性、生动性、感染力①柳宏、王逊:《文本的情景呈现——高校写作教学改革思考之一》,《写作》2019年第3期。。本文针对“时空”呈现予以具体阐述。
通常,文学文本有两个基本的构件,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空间。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生存的两大维度,人类以此观察和认识世界。文本世界必然包孕着丰富多彩的时间和空间,必然描述、记录、虚构形形色色的时空关系,或时空关系生成的事件、因果、意义。文本呈现处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是一个动态的时间绵延的过程,也是一个立体的空间位移转换的过程,二者互相依存,紧密勾连,共同形塑出独特的文本世界。故而,文本呈现须臾离不开时空建构。
一、时间呈现
万事万物包括人类本身,谁都无法避开时间的预设和局限。任何人、任何事总是存在于时间范畴下。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写作文本呈现,必然以时间为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一部文学文本,它必须有起始、发生、发展、高潮、结尾,经历一个时间的跨度。文本正是通过时间的流转变化来展现人物的命运,纷纭事物的现象,跌宕事件的过程,并以此表达作家对时间的体验、感悟和思考。
试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形容时间像流水一样奔腾不息地流逝,一去不复返。呈现了孔子对人生世事迅疾变化之感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其一)呈现出离家、回家时间流逝的长卷,也是生命流淌的漫漫长河。据考,贺知章37岁考中进士离开家乡,返乡时已是80多岁两鬓苍苍的老翁了。时光易逝,世事沧桑,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怎能不让他睹物伤怀呢?一个“笑”字反衬出诗人无限的感伤和悠长的苦痛。在其另一首《回乡偶书》中,此种心绪也得到透彻的彰明。诗人写道:“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回乡偶书》其二)此处,时间的远近转换衬托出内心的怅惘失落。这是一生狂放不羁的贺知章,在生命的灯火即将熄灭之时,无限惆怅、沮丧的情绪在文本中的喷涌和呈现。
电影《时间去哪儿了》是“金砖五国”多位导演分段合作共同完成的一部集锦电影。五国合作的复杂程度可以想象,如何找到一个共通的主题完成电影的表达?以《时间去哪儿了》为主题,架构起《颤抖的大地》(巴西)、《呼吸》(俄罗斯)、《孟买迷雾》(印度)、《重生》(南非)及《逢春》(中国),倚借时间概念表达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人们的共同生命感受,此种构思和表达可谓精巧。
中国短片《逢春》,通过一对生活在一座古老城市的夫妇是否生“二胎”的选择,呈现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唐代诗人王勃云:“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王勃《滕王阁序》)间接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对“时间”的一种积极昂扬的生命态度,即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人们处于哪个年龄阶段,只要拥有一种积极的生命态度,就可以改变命运、改变生活。
俄罗斯短片《呼吸》,叙述了一对隐居在深山老林里的夫妻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妻子平时很少在家,百无聊赖的丈夫以为妻子与铁路驾驶员有染。妻子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丈夫在一次追打妻子的过程中不慎失足,伤情严重,呼吸困难,危在旦夕。在大雪封山孤立无援的世界里,妻子无法向外界求助,只好将丈夫的气管外接到手风琴出风口处,通过拉动手风琴来帮助丈夫呼吸。面对丈夫的疑问:“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存活)?”妻子回答道:“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时间。”由此,当这个世界静止时,温暖的琴声和艰难的呼吸声,构成一个延续生命的动人画面。其中,有无端的猜忌,有爱情的宽容,有生命的脆弱和艰难的苟活。而时间,则不动声色凝视着这一切。
在浩如云烟的各种文本中,时间一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写作主体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呈现抗拒和超越时间的企望。如著名经典小说《百年孤独》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篱笆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岸里暖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这一开头十分简洁,只有三句话,但却把时间呈现得光芒四射,魅力十足。
第一,颠覆了时间呈现的习惯模式。常见的文本都是“从前”“很久以前”,但该本文一反常态,入笔不按常理出牌,却以“多年以后”开头。这种从倒叙向“前叙”的转变如何实施?能否实施?读罢好奇感、新鲜感、忧虑感油然而生。
第二,错位推进叙事时间和事件发生时间。叙事时间显然是当下,事件时间则花分两朵:一是多年以后一号主角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要被枪决。二是当一号主角面对行刑队慷慨就义时,他既没有害怕恐惧,也没有豪情万丈,出人意料地回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由此,叙事时间“当下”和事件时间“多年以后”“遥远的下午”三个时间线索交织一起,错位推进。马孔多小镇的百年历程就在“现在”“未来”“过去”的时间长河中史诗般地混沌展开。
第三,故意让时间来回闪烁。小说开始,叙事人为何不从当下说起?却一下子跳跃到“多年以后”。按理说,接着应该讲述多年以后一号主角如何面对行刑队、或行刑队如何处置一号主角的事。然而,小说一下子又从外部世界切入一号主角的内心,瞬间通过一号主角的回忆,闪回到“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小说就在这“未来”“过去”的腾挪闪烁中,将读者搞得晕头转向,绽放出时间呈现的摇曳多姿。
第四,在时间的来回闪烁中探究时间的奥秘。小说一开始直接切入多年以后的一件大事。本书的一号主角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即将被人枪决。这时读者急于知道:要被枪决的男主角到底是什么人?他究竟犯了什么事?他会死吗?然小说戛然而止,迅速闪回到从前那个遥远的下午。先别管他是什么人,先搁下他那些事,因为他还没死,因为人在临死时总要想些事,因为人死之前往往最容易想起童年的事。可我们的一号主角为什么偏偏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是一个“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的时代,他的父亲为什么非要带他去“见识冰块”?干点别的什么难道就不行?小说在时间闪烁中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读者在反复的咀嚼中慢慢感悟:一号主角未来处境和遥远回忆的时间闪烁,清晰昭示出:这是生跟死之间的摆动,是一个生命的起点与终结之间的过渡,是一个世界新生与毁灭之间的跳跃,是一个愚昧和文明之间的嬗变。
二、空间呈现
空间即处所,定格在时间坐标轴上的某个点。它是时间变化中出现的片段,比如场景、画面、人物的装束、衣服、帽子、肖像等,还包括戏剧性的场面等要素,都蕴含在空间的范围内。如果说历史是由相继出现的事件加以标点的,那么事件则由因果排列的画面加以组合的。相继出现的事件流淌成时间的河流,因果排列的画面点缀为空间的画廊。时空的交织构成了历史,创造了世界。文本呈现就必然以空间位移展现因环境、场面、地点、人物、事件和与此相关的要素转换引起人物情致的摇荡、命运的跌宕和结局的产生。
受意识流及柏格森的时间绵延理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在时空维度中,当代一批作家往往重视时间而忽略空间,热衷于从时间这一维度审视人类的生存境遇。其实人类所需的社会归属感、身份认同感常常是依靠空间获得的。因此,空间这一维度对人类存在的意义同样重要。特别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宇宙的时间还是那个时间,但人类生存的空间越发逼仄局促,记忆中的自然山水已荡然无存,只剩心灵的流离失所。
无论写人,还是记事,都离不开空间呈现。人只有活动在某一空间的点上才能体现人的存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人一旦彻底离开了或失去了生存空间的点,则意味着死亡,其存在空间或为坟墓,或是牌位,这些符号空间大多短暂,不太可能长久封存,终将或被遗忘、铲平,或被化为灰烬。当然有些“重于泰山”“死得光荣”的人,他们可能流芳百世,永垂不朽。但他们被人怀念、被人抒写的还是他们生前某空间画面的事迹功名。或是某地某次战役的赫赫战功,或为某郡某县的吏治美名,或是徜徉山水的著名诗篇,或是迁徙途中、归隐山林、寓居一隅写成的皇皇巨著。文本中的人无法与事实、事件脱节。
古今中外的各种文本,通过空间呈现增强了文本的生动性、形象性。
抒情文学中的空间呈现常常隽永、有力。如贺知章《回乡偶书》中家与村落、儿童和老者组成了层次分明、动静结合的乡村图画,尤其是“笑问客从何处来”中的“笑”字,既调和了回乡相遇自然诙谐的氛围,又将游子的惆怅、儿童的好奇刻画得淋漓尽致,还给静谧的乡村敲动了童话般的琴弦。
又如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乡愁》以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四个人生阶段组诗。诗歌以空间上的两地阻隔同时归纳出这四个阶段的共同特征:小时候的母子分离、长大后的夫妻分离、后来的母子死别、现在的游子与大陆的分离。十分新颖的是,诗人为这四个阶段分别找到一个表达乡愁的具有无限表现力的空间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四种空间意象,看似单纯、明朗、集中,但却丰富、开阔、博大,因为其关联着这和那、此和彼的阻隔和分离,这种阻隔和分离伴随着乡愁的蔓延不断链接和放大,这种不断升腾缥缈的乡关愁思将绵延拓展的空间距离缭绕得若有若无,最后在诗歌的结尾升华到民族情感的全新高度,有如百川奔向东海,有如千峰朝向泰山,诗人个人的悲欢与巨大的祖国之爱,民族之恋交融在一起。诗歌纵向的历史感,横向的空间感,纵横相交汇聚为礼赞祖国的现实感。全诗通过空间意象将本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乡愁”物化、具体化,增强了文本的形象性、空间感,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叙事文学中的空间呈现则更加具体可感,摇曳生姿。如《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此处描写人物,丝毫不及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全凭空间呈现:散落的芍药花、半埋的扇子、闹嚷嚷的蜂蝶、鲛帕包的花枕等,自然曼妙,栩栩如生,宛若一幅“史湘云醉卧芍药裀”美人图。
又如《百年孤独》开头的第二句话:“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篱笆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岸里暖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这个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时间的闪回顿挫,第三句话交代马孔多镇“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文明程度很低,开化程度不高,几乎处于混沌原始的状态,“宛如史前巨蛋”。这第二句则全是空间呈现:马孔多镇的村落、河岸、芦苇、篱笆,房屋沿河排开,河水清澈见底,暖石洁白光滑。自然清新,质朴鲜亮,宛如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可见,《百年孤独》的开头之所以不同凡响出人意外,除了时间的腾挪闪回把读者搞得紧张焦虑、晕头转向之外,其空间的景观呈现充满了神秘和好奇,吊足了读者前往旅游观光或阅读徜徉的胃口。
如果把时间比喻为一条河流的话,空间就是河流上的漂浮物,或者说是两岸的风景,二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在传统的文学里,空间永远是附属于时间的。然而今天情况有所变化,时空关系是和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紧密相联的。传统叙事文学关注时间流淌,今天则更多强化空间的象征寓意。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勒克莱齐奥在小说《阿丽亚娜》中呈现了少女克里斯蒂娜游荡的城市空间。这座城市“远离大海,远离大城市,远离自由,甚至远离空气——这是火葬场造成的,还远离世人,与世隔绝”。小说呈现了一座弃城:荒凉,弥漫着火葬场的烟雾,没有鸟儿没有苍蝇没有蝈蝈,只有“成千上万扇长方形窗户的高大的灰色建筑”,而穿梭其间的男男女女,像是“抓不住、找不到、眼睛无神、没有影子的幽灵”。克里斯蒂娜漫无目的地在城市中游荡,却被潜伏在这座城市中的罪恶吞噬。其遭遇流氓轮奸,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可见,勒克莱齐奥用隐喻性的笔触,将这座城市无处不在的罪恶、欲望、不幸、苦难揭示出来,原本为了保护人类免受风吹雨打的家园却在欲望的异化下成为了包藏罪恶的垃圾场。
郝景芳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呈现出北京如“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的城市”景象。在不同的空间里,分别住着不同的人:第三空间是底层工人,第二空间是中产白领,第一空间则是当权的管理者。主人公老刀为了给人送信,从第三空间到了第二空间,又来到了第一空间,之后带着第一空间的回信又回去了。小说中没有生死抉择,也没有天人交战,几乎没有科幻的“猛料”元素,都是平凡的事情,但这种平凡具有更为冷峻的现实感,甚至让人不寒而栗。显然,作者借折叠的城市空间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独立、严肃的思考,具有典型的反乌托邦设定。
三、时空呈现的辩证思考
时间、空间是抒情和叙事文学的两个重要元素。写作文本呈现之时间、空间常常紧密相联。具体的时间总是定格在具体的人物、场景等空间画面,具体的空间常常和人物活动、事件发展的时间流动依存融合。绝对的时间和空间常常是抽象的,只有与人发生关联的时空才是具体可感的。文本呈现时间、空间元素的要义和规律特点不同,分而论之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文本时间、空间呈现的联系与区别,更为立体地体悟文本时间、空间呈现的经验,更为明晰地体现文本呈现者的积极存在。
当然,文本中的时间和空间常常彼此紧密连接,互相融合渗透。文本时间是文本空间的线性流转,文本空间是文本时间的动态转换,二者相互依存,内在统一于文本本身。
孔子在川上的流水之喻,是对时间流逝的从容不迫,表面上呈现了大自然的河水在“不舍昼夜”的时间中流逝,寄寓了时事往者皆像川水,生命似流水奔腾不息,最终也会消亡,这是动态的过程。然“川上”的空间位置暗含着某种不变与恒常,象征着在连续不尽、绵延消逝中蕴含着苟日新、日日新的时机和缘分,展示了生命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密度的禅理妙悟。
《春江花月夜》全诗以月为中心,开篇以月升起,将春、江、花、月、夜逐字吐出;最后以月终结,将春、江、花、月、夜逐字收回。诗情伴随着明月的初升、高悬、西斜、下落的时间过程线性展开。同时,全诗在月升月降的推进中,又通过月光下的江流、芳甸、花林、飞霜、沙汀、白云、青枫、扁舟、高楼、玉户、闲潭、落花、海雾、江树等景观呈现,交织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春江月夜图。在这种神话般迷离优美的艺术气氛中,诗人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设问和“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哲思,揭示了时间的流动变化和空间的凝固稳定,时间在空间中流动,空间在时间中定格。人的时间的有限性通过一代代的延续获得了某种无限性,空间的稳定性又与人的生命激荡具有了某种流动性。繁花似锦的春江月夜,漂泊天涯的游子之思,长夜不眠的思妇之情,缥缈在春江夜空,升华为宇宙之思。江月年复一年,照临大地,诗人通过想象获得某种体验的存在,虽然这种存在是有限的,是要终结的,但却是可以期待的。然这种期待并没有任何回应,“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大江东去,天地静穆。诗人把深沉庄严的宇宙之思化为轻柔的“诗之时间”,把绵延的时间追问聚焦为诗意的“空间意象”。这是时间和空间完美结合的“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①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马克思说:“时间就是人类发展的空间。”②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时间本身就是空间,空间是时间的定格和聚焦,社会时间和空间不可能凝固僵化,而是互相转化的。事实上,社会时间—空间是有开端的,且也是有终结的;而自然时间—空间作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是无开端的。作为社会时间—空间,它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运动中获得现实性的,“也就是说,空间和时间在运动中才得到现实性,运动是通过空间而现实存在的时间。没有实践活动这种社会运动形式,也就没有社会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形式”③赵纯昌:《论时间与空间的社会性》,《北方论丛》1995年第2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启发学生处理时空关系时,“……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静止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观察运动也不仅要看到过去,而且要看到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④[俄]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2页。。优秀的文本,呈现出独特的社会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形式和鲜明特点;杰出的文本呈现者,总是追求社会时间和空间运动发展进程中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不断创造自由时间,形成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关系的完整概念,深刻地把握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实现自然生命时间和自由发展空间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