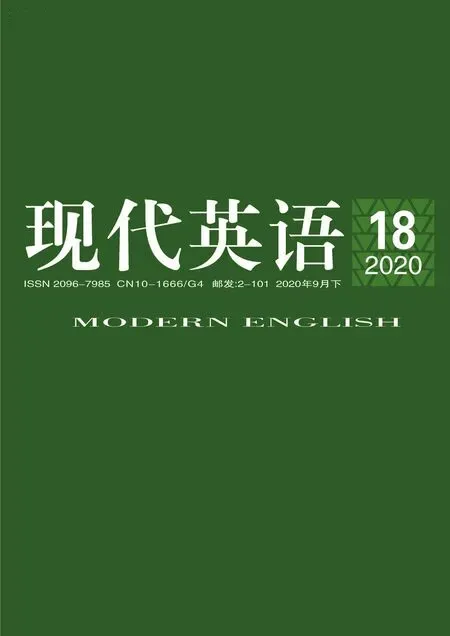从抽象和具体特质看英汉抽象名词异同
孙春媛
一、 英汉抽象名词的定义
(一)汉语抽象名词定义
目前有几种不同说法为学界接受,绍志洪的“原来可用动词、形容词短语或句子表达的概念,现在改用抽象名词来表达”;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中的“抽象名词是无形可定、无数可数的事物之名称。 不指物之实在的体质,而抽出他的性、象或功用,成为一种事体的名称”;«马氏文通»将名词分为“公名”和“本名”,其中“公名”又分为“群名”和“通名”,“通名,所以表事物之色相者,盖离乎体质以为言也”,也就是抽象名词;吕叔湘将名词分为人物、事件、物质和无形四类,无形也就是抽象名词;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对于词的定义是“语言的最小意义单位”,提到抽象名词,他认为名词所代表的物,大多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但是社会的组织,如“政府”,哲学上或科学上对于某一类事物所给予的名称,如“道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也该认为是名词。
(二)英语抽象名词定义
与汉语定义类似,伦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定义抽象名词为“Nouns like ‘difficulty’ which are ABSTRACT(typically non-observable and non-measurable)”。
可以看出,英汉两种语言都将抽象名词定义为“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这种类同,主要源于人类思维的共性。 人类的认知基于体验,而整体来看原始人类的活动都是从动作开始,为了谋生,所以在语言里首先出现的是动词,随后为了认识世界,名词和形容词也随之出现。 抽象名词应当是为了对世界产生思考的产物,而思考的特性又定义了抽象名词的特性。
二、 抽象名词的界定和分类标准
汉语中抽象名词的类别划分要比英语更复杂,主要是因为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现在还不能统一。
(一)汉语抽象名词分类
汉语中词类划分,主要有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曹爽,2015)。 «现代汉语»划分词类的依据是语法功能,词义与词的语法分类并不完全对应,不能作为划分词类的根据,“一般常说,名词表示事物,动词表示行为动作,形容词表示性质和状态,似乎词类是根据词的意义划分出来的。 但实际上汉语也不能根据意义划分词类”,原因有两个:第一,词的意义不能明确观察到;第二,词的语法性质与词的意义并不完全对应;加上汉语有着隐喻式思维,所以抽象名词的所指就成了实体物的隐喻形式,也就获得了实体物的特征。 (苏宁宁,2014)而抽象名词具有多大程度的实体物特征,要看具有多大程度的性质义和程度义。
性质义是指一个词语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所有名词都表示事物,而事物通过分属不同的类属有了不用的性质,这些性质就是名词背后的性质义。 比如说起康乃馨,人们脑海里就出现母亲的形象,那么母亲或者母爱就是它的性质义。 谭景春(1998)对名词性质义的排序:“抽象名词>指人名词>指物名词>专有名词”,抽象名词具有的性质义最强,因此中文中许多抽象名词常常能作为修饰语形成“抽象名词+名词”的搭配。两个名词之间由于性质义强弱不同构成了多层语义关系,即属性关系。 这时抽象名词由于性质义很强,成了属性定语,比如,“中产趣味”这个词的中产就形成了人们脑海里对于中产阶级的性质联想,那么中产趣味表达的含义更受中产限制。 中产本来用来修饰中心词趣味,现在语势的重点却落在了“中产”上面。
程度义指的是事物性质的语义特征。 认知语言学认为每一个词类都有自己的典型特征,名词最典型的是空间性,形容词最典型是程度性,动词最典型是过程性。 典型的名词功能稳定,但是非典型名词既具有名词性质,又游离名词外具有其他此类的性质,因此由于事物之间性质的差别,一部分名词也具有了形容词的程度性,但是程度性不是名词的主要特征。 抽象名词是名词里的非典型成员,因此具有较强的程度性。(苏宁宁,2014)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多种分类方式都围绕这两个语义特征。
目前比较受认可的有以下几种分类:黎锦熙(1992)“无形的名物、事物的性质和形态、人事动作”;王珏(2001)“知识类、度量类、消息类、策略类、疾病类、情感态度类、程度类”;刘磊(2009)“知识类、消息类、策略类、疾病类、情感类、属性类以及其他”;李英哲(1980)“领域类、度量类、消息类、策略方法类、疾病类、程度类、情感态度类”。
(二)英语抽象名词分类
张今和刘光耀在«英语抽象名词研究»中将英文抽象名词分为五类:行为性抽象名词、品质类抽象名词、状态抽象名词、固有抽象名词和复合抽象名词。 通常人们引述前四种分类,文章以行为性、品质类以及状态类抽象名词为例,探析英语抽象名词具有何特质。
1. 行为性抽象名词
按照抽象名词具体化程度,此类名词有三类:抽象化的行为抽象名词;部分具体化的行为抽象名词;具体化的行为抽象名词。
第一类指抽象名词在句子中表达完全抽象意义,并且表示泛指意义,前后不带任何修饰成分,结构独立,不可数。 比如,“Failure thwarts him again.”这一句的failure 由动词fail 转化而来,并且在此处表示抽象的“失败”概念,并不限定表示此次失败还是上一次失败,因此在此处为完全抽象化。
部分具体化的行为抽象名词,经常出现在短语中,需要和限定词一起使用,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使用部分具体化抽象名词时可以将整个名词短语视为一个部分具体化抽象名词。 比如,“Their disputes over company's development could not be addressed at this conference.”句中disputes 表达抽象概念,又表示具体已经发生的争吵,因此disputes 虽然表示抽象概念,但已经被部分具体化。
具体化的行为抽象名词要从意义上区分,它所表达的不再是摸不着看不见的概念,而是确切具体的事物。 “She is such a beauty.”在此句中beauty 不再表示美,而指有美这个特质的人。 这种抽象名词具体化的用法,有些已经太过普遍变成了抽象名词的常用用法,使它具有了具体释义。
2. 品质类抽象名词
此类抽象名词表示品质、特性、感情和状态等概念(冯树鉴,1986),主要是由形容词转化而来。 有时会和行为抽象名词相混淆,主要因为英语中许多动词和形容词是同一个词根,这种时候,也必须通过语义来分辨。
品质类抽象名词按照抽象化程度也可以划分成完全抽象化,部分具体化和完全具体化三类。
完全抽象化品质类抽象名词也是没有形容词修饰,表示泛指,没有复数。 比如,“Honest tells us the appropriate way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一句中Honest表示的是抽象的诚实这一特质,而不具体表示诚实这种行为。
部分具体化品质类抽象名词通常出现在短语中,可以搭配其他修饰语,语义上由于修饰成分限制而变得相对具体,比如,“I like our headmaster because of her kindness”一句中,kindness 指校长的和善,但是根据语义可以推出我喜欢校长更可能是因为她对我的和善态度或者和善行为,因此在这里kindness 是部分去抽象化了。
具体化品质类抽象名词则是完全表示具体的人物等,不再表示抽象的概念,因此可以以可数名词形式出现,用法同普通名词一样。 比如:“Her cuteness attracts everybody's attention though she feels embarrassed when tumbling.”这一句中,根据后半句就可以知道可爱并不是指她的特质,而是摔倒这个行为或者是她摔倒前后的反应是可爱的行为,也就是指具体的事物。
3. 状态类抽象名词
状态抽象名词很少有人研究,文章认为此类抽象名词的来源主要是由有状态含义的形容词添加词缀演变而来,也有部分表陷入某种状态含义的动词,可以通过词缀变成此类抽象名词,比如happiness, depression等。 此类抽象名词也可以根据抽象化程度划分为三类,但是通常具体化之后也就不再指抽象的状态或心情,比如depression 具体化之后往往指抑郁症这一疾病。
可以看出英汉对于抽象名词的分区别较大,这种区别也导致了英汉抽象名词在使用上的差别。 英语中即使抽象名词与动词和形容词同源,具有部分动词和形容词的特征,但是绝可能原原本本、不加处理地作为动词或者形容词使用;而汉语中抽象名词可以直接拿来修饰名词,比如,哲学常识、常识的来源、西方科学、西方的科学等。
三、 英汉抽象名词差异原因
英汉抽象名词有差异主要是因为英汉分属不同语系,具有不同的语义特征。 文章认为差异来自两部分:第一,英汉语言使用形式上的不同;第二,英汉民族的思维差异。
(一)英汉语言使用习惯不同
文章认为抽象名词使用上的差异主要来自:第一,英语比汉语更善用介词;第二,英语中名物化现象突出。
1. 介词差异
英语介词丰富且使用频繁。 在形式上有简单和复杂之分。 简单介词就有70 个左右,而汉语中介词总共不过七八十个。 (沈家煊,1984)英语中的介词不仅能和名词构成名词短语,引出动词相关的对象、处所、时间等,也有许多介词可以兼做副词。
英语中介词除前置外,也有一些情况允许后置。而现代汉语中介词只能前置,位置上不能改变,否则语义不通。 比如,“He is whom I going to work with.”和“我将与他共事”两句中,根据语义可以推出work with him 才是句意,但是由于表语从句要求,介词后面的宾语前置,介词与对象分离,但是语义通顺。 而汉语中介词必须跟在对象前面,否则句意不通。
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英语抽象名词的最典型结构是“N1+介词+N2”,抽象名词即使不是语义重点,但是在结构上也处于中心位置,并且抽象名词和第二名词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依赖介词来表达。 但是汉语中抽象名词的搭配形式较为广泛,做中心语时为NP 结构,作定语时既可以出现在NP 中,也可以表示为“N 的N”,比如“爱情的苦”“哲学的法则”等。 这既是汉语意合的表现,也是汉语介词较少的结果。
2. 名物化现象
名物化既是语法范畴,又是语义范畴。 语法上,有词性和级阶的变换,语义上有从一致式走向非一致式的变化。 (王振华,王冬燕,2020)语言本身具有能指功能,名词更是具有指物的功能,在英语中动词的述谓义在语义层面转化为名词的指物义,这一转变也就是“名物化”。
英语中出于语法要求,动词和形容词要作主语或者宾语,必须改变为具有名词性质的词。 英文表达中,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比较普遍,而汉语中则几乎没有名物化现象,或者说汉语的语言事实完全不支持名物化的说法(朱德熙,1961)。 汉语的实词天然地带有名词性,无论动词还是形容词,因为缺少屈折变化,都可以做主语,因此名词性或者灵活性相比英语中的实词天然地更为突出。
系统功能学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人类思维的隐喻化,也就是说英语的静态名物化指出了英语的发展趋势,是不断从动词性转向指物性的,英语这一转变将缩小英汉动静和抽象具体之间的差异。 可以说在语言不断变化的过程,英汉表达在今天的抽象与具体的差异,也有可能会随着两种语言的不断变化而渐趋同一。
(二)英汉语言背后的民族思维差异
英汉语言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比如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抽象汉语具体、英语动态汉英静态等。 文章探讨的英汉抽象名词间的差异根本原因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思维存在差异:英语使用者是抽象思维,汉语母语者是具象思维。
汉语的具象思维主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历来强调抒情要借物,必须有象才有意。 这样的具象思维不重视逻辑性,注重情感性,更擅长将表达具象化。 因此在汉语的表达中为了使表达更形象,往往借助有力的动词,比如汉语偏爱的四字结构,往往都是包含动词连用,精炼且生动。
英语代表的抽象思维可以追究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一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科学的理性使英语的表达更为冷静。 这种表达要求英语多使用名词,而抽象名词又是英语名词中的重点,并且抽象名词表达的含义更为广泛,这样也就使得英语表达更强调口吻要客观冷静。
四、 结语
英汉抽象名词之间既有着相似的定义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 英汉对于抽象名词的定义基本类似,体现出两种语言背后的人类思维共性。 至于抽象名词的区别,目前普遍认为是由于英语表达抽象而汉语表达具体这一差别,文章认为根本还是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思维存在差异。
英语使用者是抽象思维,而汉语为母语者则是具象思维。 汉语的具象思维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强调抒情要借物的意象。 这样的具象思维使语言更形象化,更倾向于使用有力的动词。
而英语是抽象思维,这主要由于西方哲学更为繁盛。 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开始,西方的哲学发展不曾断流,一直追求科学和理性,这就使得英语的表达口吻更偏向冷静和严谨。 这种表达要求英语多使用名词,因此相较汉语,也更多地使用抽象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