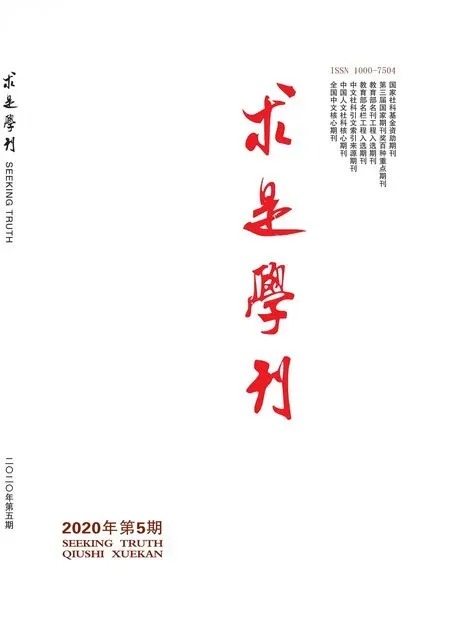作为物质型人格权之“基因权”的理论证立与法律保护
郭少飞
生物科技突飞猛进,推动基因分子水平的人体研究利用快速发展,人体生理结构及运行机理逐步得以揭示。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命的操控愈加深入纯熟,如2000 年美国诞生全球首个“救命宝宝”,①See Susan M.Wolf et al.,“Using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to Create a Stem Cell Donor:Issues,Guidelines &Limits”,in Journal of Law,Medicine and Ethics,2003,Vol.31,No.3,pp.327-335.2016年4月世界首例“三亲婴儿”出生,2018年11月我国诞生世界首位“基因编辑婴儿”,引发巨大的伦理争议。在基因映射下,作为生命高阶形式的人类与其他生命形态同质化,人类生命的神秘性、崇高性及魅人光辉正在消解,“人的自然体在迄今无法想象的程度上变成了可以通过技术加以支配的东西”。②库尔特.拜尔茨:《基因伦理学——人的繁殖技术化带来的问题》,马怀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我们需要构造基因权利制度,重塑其伦理性,发现并强化其人格价值。学界主张的人类基因权利保护进路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传统身体权、健康权保护基因,由于局限明显,仅为少数学者主张;二是,新设权利,单独保护基因,为众多学者所采,亦为本文赞同。后者存在“基因人格权”“基因财产权”及混合权利说,而人格权又分出“基因隐私权”“基因信息权”等。现有基因权利说概念用语芜杂,理论体系不一,尤其对作为物质的基因保护不周。对此,本文主张创设以物态基因为客体的新型物质型人格权“基因权”,详论权利确立的正当性基础,并结合我国《民法典》基因法律制度,阐述后民法典时代“基因权”法律保护的理念及进路。
一、“基因权”的提出及理据
“基因权”的提出奠基于对基因物质性的科学认知,但是否足以作为独立单一的权利存在,尚须从科技、伦理、制度等多个层面予以论证。
(一)基于物态基因之“基因权”提出
基因作为一种物质,不仅分布在人体及与人体分离的组织器官中,而且存在于复制的人体细胞中。由于科技发展,物态基因已经在分子层面自人体析出,自然人对其基因的占有支配已非现有权利可以保障,需要一种以基因为客体的新型权利。
在生物意义上,基因(gene)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通常由编码蛋白质或核糖核酸(RNA)链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片段组成。但特殊情况下,基因可能以RNA 形式存在。基因组(genome)是生物体携带的全套遗传信息,包含蛋白质编码基因、非蛋白质编码基因、基因调节区域及功能未知的DNA 序列。①参见悉达多·穆克吉:《基因传:众生之源》,马向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42—544页。基因主要分布于细胞核与线粒体上,呈线性排列。基因可经由精子、卵子传递给胚胎,然后由胚胎进入生物体的每个细胞。人类基因组共编码约20 687 个基因。编码基因的序列在基因组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基因组序列的98%是由大量散布在基因之间或基因内部的DNA 片段组成,它们不编码RNA或蛋白质。
基因是“承载着肌体的信息、生命的蓝图、运行程序的生命终极因子”。②张春美:《DNA的伦理地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7页。人类基因与个人生理发育、心理健康、生命状态关系密切。基因变异可能导致生长迟缓,器官组织不健全,健康状况恶化,甚至死亡。基因与人的生命进程有关,但并非生命本身;基因关系人的生长发育,与人肉身的完整度相关,但身体无法涵盖基因,只是基因表达的结果之一;基因影响身体器官的功能发挥,致病基因或基因变异会导致不健康。生命、身体、健康受基因形塑,但无法等同。尤其与人体脱离的组织器官或人体生成物中的基因,非属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客体范畴。
总之,基因作为一种化学物质,关乎人的生老病死、人的身心状态,意义显著;且已非人体可涵盖,成为一种新型独立的主体利益,有必要从基本的物质层面对其赋权保护。仿照民事权利“客体+权利”的惯常命名方式,应称为“基因权”,即权利人直接支配基因,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乃绝对权的一种。
(二)“基因权”提出的正当性基础
承认“基因权”不仅在于基因生物性或物质性,还在于基因对人的价值与意义重大。“基因权”确立具有显著的科技、伦理、制度等综合基础,作为独立权利条件成熟。
其一,基因技术深度进阶,基因物质需要单独权利保护。基因技术令人类能够从分子水平认知自身生命现象。通过基因技术,人类开始掌握本体命运,不再完全受制于生物人生命规律。至今,基因筛查、检测、诊断、治疗等已广泛运用;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后,个人基因测序简便易行,成本大幅下降;基因优化、增强、编辑、克隆等技术逐渐成熟,虽然存在潜在的伦理风险、社会风险,一旦法令准许,大规模应用可期。无论如何,当下深度进阶之基因技术对个人、族群乃至整个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而所有基因技术皆系作用于基因之手段方法,须取得、占有、利用基因。为此,就基因本体,应取得有关主体的同意或授权。当发生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有关主体享有法定权利防御或主张侵权救济。这些均需赋权于个人,承认个人占有支配其基因的权利。独立的“基因权”能够充分发挥上述功用,实现良好保护效果。
其二,基因获得独立权利保障,有利于强化人类尊严保护。技术理性的张扬、现代性的深化及结构化,使得人的客体化趋势加剧。基因技术在分子层级解构人,预测人,试图把人的生理心理状况与基因勾连起来,①参见威廉·赖特:《基因的力量:人是天生的还是造就的》,郭本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0页。归结为基因,导致身心俱在之人降解为物质之人。在社会认知层面,基因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人们普遍认为“基因关乎人类自身,与个人的自我意识深度关联”,②Sonia M.Suter,“The Allure and Peril of Genetics Exceptionalism:Do We Need Special Genetics Legislation?”in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2001,Vol.79,p.669.相信基因决定人的样态、特征,能够解释人的差异。这也带来了基因歧视。而人们追求以基因技术设计、改造、转换生命。生命不再神圣,只是不同的基因组合,可人为操控。人物质化、原子化,引发人的异化,人的尊严自由不断消解。对此,应认识到,基因为生命提供了自然基础,蕴含生命潜能,道德意义显著,应赋予道德权利。在法学视阈中,面对人被基因技术透析之境地,考量基因盗取或掠夺、基因标签、基因歧视、基因商业利用等现状,应将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明晰个人在基因分子层级自我决定、自我控制的地位,赋予个人对基因本体的权利,即“基因权”,从而凸显基因的法律地位、之于个人的本体意义,强化基因之上人类尊严保护。
其三,国际宣言及域外立法实践为承认“基因权”提供制度镜鉴。1997 年《世界人类基因与人权宣言》第1章“人的尊严与人类基因组”第2条规定,(a)每个人都有权使其尊严和权利受到尊重,不管其具有什么样的遗传特征。(b)这种尊严要求不能把个人简单地归结为其遗传特征,并要求尊重其独一无二的特点和多样性。这表明基因之上存在人格利益,应受权利保障。第2 章“有关人员的权利”第5 条规定,(b)在各种情况下,均应得到有关人员的事先、自愿和明确同意。(c)每个人均有权决定是否要知道一项遗传学检查的结果及其影响,这种权利应受到尊重。《法国民法典》③《法国民法典》,罗洁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1994 年新订第三章“对人之特征的遗传学研究以及通过遗传特征对人进行鉴别”第16-10条规定,对人之特征进行遗传学研究,仅限于医疗与科学研究之目的。在实施此种研究之前,应当征得当事人的同意。第16-11条规定通过遗传特征对人进行鉴别,明确“鉴别之前,应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上述国际宣言及立法均要求,对基因进行研究、鉴别前应取得当事人同意,实则承认个人的基因权利。基因研究、鉴别皆需获得基因,当事人同意至少包含提取占有基因之许可,此乃个人支配控制其基因的权利的彰显,即本文主张的“基因权”。国际社会及有关国家立法表明,“基因权”有其存在的制度空间。
综上,基因技术蓬勃发展,在基因分子层面透析利用人,超越过往以器官组织细胞为对象的超分子认知范畴。作为人的生物身份证,基因可揭示个人生物特征,在社会系统中颇具独特的社会文化意涵,关乎人的尊严自由,利害关系重大。当下,基因已然成为一种新型主体利益,当配之以独立的“基因权”,保障权利人对其基因的自我控制、自主支配。
二、“基因权”作为物质型人格权的学理分析
基因具有物质与信息双重属性,“基因权”指向物质性基因,以物态基因为客体。现有研究就基因权利数量、性质争议较大,存在明显不足,缺乏对基因物质性这一根本属性的聚焦。本文立足物态基因,基于权利特性及实证法,厘定“基因权”性质。
(一)现有基因权利说难敷物态基因保护之需
1.现有基因权利主要学说
就基因权利种类、属性等,存在各种学说。按所主张的基因权利数量及权利之间是否彼此独立,分为单一权利说、二元权利说与权利束说;按权利性质,可概括为财产权、人格权及混合权利说。
(1)单一权利说
该说认为,基因之上仅存在一元权利,按单一权利属性,分为人格权说与财产权说。前者主张,人类基因是一种信息或隐私,应以基因隐私权进行保护。①See Guido Pennings,“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One’s Genetic Origins”,in Medicine and Law,2001,Vol.20,pp.1-15;Graeme Laurie, Genetic Privacy:A Challenge to Medico-Legal Nor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42-50.还有大量英文文献可参考。美国大多数州制定了个人基因隐私保护法。联邦层面,2008 年颁行《基因信息反歧视法》。而承认基因财产权的趋势渐强。有些州如马萨诸塞、南达科他、得克萨斯、阿拉巴马,立法议案要求把基因信息、DNA 或DNA 样本等界定为专有财产(exclusive property)或独占财产(sole property),赋予财产权。实践中,个人基因财产权为基因公司承认,在服务条款或声明中包含“财产权放弃”或“DNA 和DNA 数据所有权”之类的表述。学界也有基因财产权专论。②See J.W.Harris,Property Problems:From Genes to Pension Fund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Ltd.,1997,pp.92-114;Jessica L.Roberts,“Progressive Genetic Ownership”,in Notre Dame Law Review,2018,Vol.93,p.3.
(2)二元权利说
该说主张,基因之上并存两种单一权利,即基因人格权与基因财产权。我国有学者论道,基因上人格法益与财产法益交融共存,应区分基因财产权和基因人格权,前者包括承认基因资料提供者捐赠、转让基因和获取相关回报的权利,知情同意、利益分享等权能。③参见刘红臻:《人体基因财产权研究——“人格性财产权”的证成与施用》,《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 年第2 期,第22—23 页。基于两种权利进路,有学者认为,“人对其基因享有人格权,包括对尚在人体内的基因的身体权、对与人体脱离的基因的自己决定权及对基因信息的隐私权。其次,人对其基因享有财产权,包括对其基因物质的所有权及决定对基因的研究与商业化运用并获得财产利益的权利”。④李燕:《论人对其基因的民事权利》,《东岳论丛》2008年第4期,第171页。还有学者主张,基因无形财产权加上隐私权,赋予个人自主控制领域,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合理排除政府或社会对私人空间的侵入。⑤See Adam D.Moore,“Owning Genetic Information and Gene Enhancement Techniques:Why Privacy and Property Rights May Undermine Social Control of The Human Genome”,in Bioethics,2000,Vol.14,p.2.
(3)权利束说
该说认为,基因权不是单一权利,而是多项权利的集合,包含各种性质的权利。这种观点在我国较为普遍。颜厥安教授认为,人对于他的基因拥有:基因隐私权或基因资讯自主权、基因人格权(知情权、自主决定权)、基因财产权一(与身体分离之基因物质的所有权)、基因财产权二(与基因专利相关的财产权利)、基因保育责任。⑥参见颜厥安:《鼠肝与虫臂的管制——法理学与生命伦理探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4—135页。张小罗教授主张,“基因权利是一束权利”,“是一项综合性权利,主要包括基因平等权、基因隐私权、基因人格权、基因财产权、基因知情权等内容”。⑦张小罗:《宪法上的基因权利及其保护机制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0—71页。王康教授认为,在私法意义上,“基因权是指自然人基于自己的特定基因而享有的人格权利”,包含基因平等权、基因自主权、基因隐私权、基因公开权等子权利。它是一个积极的、新生的、兼顾财产性的具体人格权。⑧参见王康:《基因权的私法规范》,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132—133、136—138页。
2.物态基因视域下基因权利定性检讨
自作为物质的基因本体角度,现有基因权利说对基因的定位模糊,在物质与信息之间摇摆,导致定性失准,与物态基因保护不适配,与我国主流理论不符,学说自身的理论自洽性亦不足。
其一,基因财产权应当否弃。该说在英美法系国家较为流行,亦符合其法治传统。但与我国遵循的大陆法系人格权理论存在违和之处。基因首先是人体组成部分,蕴含生命潜能,标识个人身份,关乎人的尊严。基因本体直接作为财产,乃人的客体化商品化,有损人格尊严,不合我国主流理论。当然,基因之上附有财产利益,但依据我国《民法典》以人格权一并保护人格财产利益的规范方式,并不承认独立的人格财产权。①参见郭少飞:《新型人格财产权确立及制度构造》,《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48—49页。基于此,物态基因尤其体内基因在我国不宜界定为财产,有关权利亦非财产权。
其二,基因隐私权或信息权偏重基因信息保护。隐私权涉及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信息权乃个人对其信息享有的自主控制决定的权利。基因隐私权或信息权,指向基因的信息形态,即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对个人生物样本检测分析获取的,与该个人先天或后天的遗传特征有关的信息。基因信息来自物态基因,是后者的信息表达。基因隐私权或信息权无法涵盖、也无法周全保护作为物质的基因本体,如第三人取得基因(材料),但不提取基因信息。何况,基因信息提取后,可与基因本体分离,自由流动。此种分离性决定了基因精神人格权难以一体保护物态基因与基因信息。
其三,混合权利类型混杂,缺乏统一理论基础。权利束说承认基因多元利益,试图以多元属性权利构成的一束权利保护基因,但权利范畴不清,各种主张差异较大;权利关系混乱,非同一层级、上下位权利并列,如基因隐私权与基因人格权;未能建构翔实的基因权利体系。而如基因平等权,到底是私法权利或宪法权利,值得斟酌。
(二)“基因权”应定性为物质型人格权
基因是个人生物身份证,能够用于识别个体身份,预测身心健康状况,揭示家族、种族等社会关系,蕴含生命潜能,与人的尊严关系重大。“基因权”无疑应归入人格权,并因符合物质型人格权的本质特性,且具有法律基础,应定性为物质型人格权。
1.物质型人格权的本质特性
物质型人格权的概念用语有别,如物质性人格权、人身的人格权、身体的人格权,但内涵基本一致。主流理论认为,物质型人格权与精神的人格权相对而在,“是自然人对于物质性人格要素的不可转让的支配权”,②张俊浩:《民法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是指对具有人的身体属性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拥有的权利”,③五十岚清:《人格权法》,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页。旨在保护存在于人身的人格法益。④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9页。就物质性人格权要素的范围,张俊浩教授认为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劳动能力;王泽鉴教授主张包含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及贞操。综合而言,生命、身体、健康作为物质性人格要素乃共识。
物质型人格权与精神的人格权类型划分奠基于人作为物质实体与精神存在的双重属性。人当然并非纯粹的肉身之物,还具有心灵、意志、意向性等精神能力及活动,应当说是“身”与“心”、“肉”与“灵”的统合。物质型人格权指向人的物质属性,精神的人格权关涉人的精神属性。人活的状态,肉体的完整度,人生命过程功能的正常健全,均系人身物质层面的重大人格利益,关系人的生存、尊严,在法制史上也最先得到承认与保护。而精神的人格权注重保护人的心理利益、精神利益,“是人的正当心理利益在法律上的定型化”。⑤张俊浩:《民法学原理》,第146页。
与精神的人格权相较,物质型人格权特性鲜明。其一,客体的物质性。物质型人格权以物质性人格要素为对象,通说包括生命、身体、健康。以实体论,即以人体或身体为基础的物质性存在。此类实在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或认知为转移。无论权利人或他人的认识能力如何,其生命、身体、健康等物质性人格要素皆在。而精神的人格权客体乃心理性或精神性要素,如名誉、荣誉、隐私等,均与人的精神心理活动直接相关,具有典型的主观性。其二,与身体直接关联性。物质型人格权以身体或人身为载体。生命是人身活的状态,身体指向肉体的完整,健康注重人体功能健全正常,无不与身体直接密切相关。这也是被称为人身的或身体的人格权的重要原因。精神的人格权也与身体有关,毕竟心理精神活动基于人体及器官,但精神的人格权主要涉及人体精神活动而生的精神性人格利益,而不直接指向精神活动所依赖的物质条件,即人体及组织器官,它与身体仅有间接相关性。其三,侵害后果的客观性。物质型人格权遭受侵害,在客观世界中表现为物质变动,人们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测量或一般经验观察获悉。如权利人死亡、身体完整性被破坏等,皆可在客观意义上呈现与感知。而精神的人格权侵权后果主观性强,缺少客观化计量方法,标准富有弹性,当事人易生争端。
2.“基因权”契合物质型人格权
“基因权”是权利人支配控制其基因本体的权利,符合物质型人格权本质特性,应定性为物质型人格权。这在我国也有相应的实证法基础。
(1)“基因权”符合物质型人格权特性
第一,就客体物质性而言,基因是人体中的DNA 分子片段、一种化学物质,其物质属性毋庸置疑。基因作为实在物,存续于客观世界中。虽然在“心”“灵”层面,基因与个人心灵塑造,与个人智力、性格、精神状况、行为倾向等有一定联系,但深受教育、文化、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应当说,基因功能主要表现为遗传特征的表达,控制个体性状,与人身、人体等物质性人格要素关联更加直接紧密,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基因权”客体物态基因具有显著的客观性、物质性。
第二,“基因权”与人体直接密切相关。物态基因通常分布于人体各个角落,也蕴含在与人体分离的组织、器官或细胞中,如脱落的人体毛发、皮肤碎屑、指甲。基因此种遍在性特点虽然不同于完全以人体为边界的传统物质型人格权,但与人体分离部分仍然是人体的生成物,与人体关系密切。“基因权”旨在分子水平保护人,但基因与人体的分离性高于超分子的器官、组织,为周全保护考量,权利客体势必扩展到与人体分离的物质中的基因。无论处于体内抑或体外,物态基因来自人体,“基因权”与身体直接关联。
第三,“基因权”遭受侵害,主要表现为未经权利人同意非法取得、利用权利人基因等。从后果状态看,加害人占有控制权利人的物态基因,显然可以通过技术方式予以检测,客观化地确定受侵害物态基因的种类、范围、用途等。
(2)《民法典》为“基因权”作为物质型人格权奠定法律基础
《民法典》人格权编第2章“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中,第1006条规定可无偿捐赠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等;第1007条规定禁止买卖。禁止人体细胞买卖在于细胞中的基因,可用于器官再生、组织再造甚至人类克隆等,关涉人格尊严,伦理风险、社会风险非常高。第1008条规定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开展人体试验的规则。其中,必须经受试者或其监护人书面同意。该条也指向基因药物、基因疗法以及人体基因试验。在此意义上,为试验而收集利用受试者基因,当经其同意。第1009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该条直接规定人体基因,未能言明基因所属主体的权利,但从守法要求、禁止性规定分析,取得基因主体同意乃基本前提。
《民法典》虽未明确规定自然人对基因本体的权利,实则承认主体对其基因享有某种权利,否则自然人如何处分(捐赠)其基因,基因的取得占有利用也不必其同意授权。可以说,《民法典》为人体基因保护留下了巨大的制度空间。再者,四个法条处于“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这三项典型物质型人格权的规范部分,依体系解释方法,人体基因规定在以物质性人格要素为调整对象的规范中,至少表明人体基因的物质性得到立法者认可,进而经法典解释,基于上述条文,可构造出以物态基因为客体的“基因权”。
概言之,“基因权”符合物质型人格权的本质特性。客体物态基因具有物质性,关乎人的尊严,乃物质性人格要素;指向处于人体内外的基因,与身体直接关联;损害后果印刻于客观世界,可以一定方法测量。而《民法典》物质型人格权条文,直接或间接指涉人体基因,明确承认基因的物质性,隐含自然人基因权利,为解释明定“基因权”留有制度空间。
三、后民法典时代“基因权”的法律保护
《民法典》基因立法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但也存在笼统间接、过于原则、体系化不足等问题,亟待补充完善。后民法典时代,“基因权”私法保护需要法典解释与特别立法并重,秉持特定理念,遵循相应进路,周全保护物态基因。
(一)《民法典》基因制度特色及不足
《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以少量条文对人体基因做出原则规定,系我国首度基因民事基本立法,具有显著的制度特色。其一,较之前草案视野限于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等,《民法典》更加贴近基因技术前沿及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感更强。其二,统合法律与伦理。包括基因在内的人体不得买卖的禁令深植道德伦理,关系人性尊严。人体试验需同时由主管部门批准与伦理委员会同意,共同发挥法律与伦理作用。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或科研活动,既要守法,也要遵守道德伦理。其三,发挥私法公法协同作用。转介条款如第1009 条“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指向公法规范及特别法。在人体基因等领域,共时涉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必将是私法公法协同调整的规范格局。
此外,基因制度尚有明显缺憾。其一,因循固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框架,不足以应对基因社会实践发展。如上文所述,物态基因权利,非现有物质型人格权所能涵盖。至于第1009 条,与基因直接相关,却语焉不详,完全交由公法及特别法调整,而未言明私权基础,难谓完满。其二,制度体系不周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可捐赠,不许买卖,但未解决与身体分离后,在基因层面被他人利用侵权问题。如术后抛弃之人体分离物,无身体权、健康权适用,亦无物权适用,个人没有提起侵权之诉的有名基因权利基础。若纯粹科研之用,难言违反伦理道德,极易陷入争议。其三,未能直面基因技术挑战。基因之上人性尊严、物质性人格利益需周全保护。临床试验局限于人体试验,而人体分离部分、人体基因试验等,涉及诸多法律及伦理问题,亦需规制。《民法典》未能直接明定自然人基因权利,面对基因技术对人的冲击,回应力度不够。
《民法典》刚刚颁行,作为民事基本法须保持权威性及稳定性,短期内不会修改,“基因权”目前难以在法典中具名化。后民法典时代,人格权编成为现实后,应从立法论迈向解释论,①参见姚辉:《当理想照进现实:从立法论迈向解释论》,《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第46页。一方面可通过法律解释,构造“基因权”;另一方面亟需特别立法,在《民法典》统领下,遵循特定理念,建构基因权利及保护体系。
(二)当下“基因权”法律保护理念
迄今,基因技术迅猛前进,产业不断拓展,伦理风险日益剧增,社会影响巨大,纷争激烈。“基因权”法律保护,必须立足基因技术现状,直面复杂的社会实践,发挥多种主体、多元力量、多样规范作用,此需秉持如下理念。
第一,自由与管制并重。“基因权”乃私权,在法律保护时仍应遵循权利本位,尊重权利人的意思自治及行为自由。但同时,“基因权”涉及家族成员的合法权益,关系特定群体利益,甚至对人类基因资源亦有重大影响。为保护他人权益、公共利益,预防各类风险,平衡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社会安全的关系,须与赋予“基因权”同步,实施相较于传统私权更加严格的管制,约束权利人的自治范围,限定行为类型,特别要严格管理“基因权”许可利用行为或生命潜能开发行为,“坚持在全面立法模式下的严格规制、法定许可的立场,保持行业主管和审查机构的中立性,提高机构伦理委员会的独立性,实行个案审批制度”。①王康:《人类基因编辑实验的法律规制——兼论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的法律议题》,《东方法学》2019 年第1 期,第19页。
第二,伦理与法律共治。基因技术确能助益人类,但也蕴含巨大风险,面临深重的伦理困境。现行技术已经开始超越人类的预测能力,很难确切认识其未来社会影响及后果,不确定性加剧。我们需要新的技术伦理保障技术不会偏离为人类服务之根旨;须以法律来规范技术开发运用,防范不当后果。这样“一种旨在控制不可预测的后果的、预防性的伦理与法律”,“必须偕行:法律提供控制与遏制的主要客观手段,而伦理则提供这样做的内在道德理由”。②何怀宏:《构建一种预防性的伦理与法律:后果控制与动机遏制》,《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第11页。此种伦理与法律并置的规范格局在基因领域已然生成。国际社会基本达成基因技术伦理共识与规则;许多国家立法规制基因技术或保护基因权利。而伦理在引导基因技术发展过程中必然具有不确定性与软弱性,单纯依赖伦理无法确保技术的安全性,无法确保该技术不会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③参见刘长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与生命法学之证成》,《东方法学》2019年第1期,第26页。“基因权”伦理与法律共治,根植于伦理,重在明晰基因权利的法律规则,发挥法律调整作用。
第三,私法规制应审慎必要。面对蓬勃发展、尚不稳定、风险未知的基因技术,保持审慎的态度并不为过。立法者非全知全能,其理性也有限。故“基因权”法律保护,除了明确基因权属规则外,基因积极利用尤其生命潜能开发高度依赖基因技术,伦理及安全风险高,应当更加审慎,既不能完全由当事人自治,也不宜过于严格,影响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为此,在私法领域,首先在于建构完整的“基因权”制度,为物态基因提供系统的私权保护;在利用方面,私法供给底线规则,而制度细节尤其基因技术规制,可容让于公法。同时,为自律留下制度空间,细节性、体系性的技术标准、行为规则,可由基因技术研发团体、所属行业在法律框架下自给,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最终实现他律与自律统合。
(三)后法典时期“基因权”法律保护进路
基因权法律保护分为公法进路与私法进路,前者注重规制基因技术,间接保护基因权利;后者直接明定基因权利。我国现行法侧重以技术规制为中心的公法模式,存在立法层级低、伦理准则薄弱、权利视角缺失、行政管理中心、调整效果不佳等弊端。基因技术涉及多元主体甚至未来世代,多重利益交错,多样风险叠加。此种挑战已超越单一法律部门、特定法律制度,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构建。为此,在法律层面,公私法应协力,既要供给基因权利制度,也要国家监管,公法干预。
在私法层面,长远来看,适宜采取《民法典》规定一般条款、特别法构建制度细节的协同立法体例。《民法典》体系庞大,具有抽象性、权威性,不宜随时修订。那些指涉重大价值、规范形态稳定的条文适宜纳入民法典。特别法主要调整鲜活、生动、变化快的事务领域。“基因权”一般条款旨在确认自然人控制支配其基因的物质型人格权,以法典宣示其重要性。如上述,“基因权”在短期内于法典中难以有名化,可通过法律解释,典外构造“基因权”。本文引述有关条文论证“基因权”作为物质型人格权时即已开展此类活动。
在具体领域或特定基因技术条件下“基因权”的享有、行使等需要特别立法,系统规定“基因权”的基本结构、得丧变更等运行规则、保护制度。建议以《基因权利法》规定以物态基因为客体的“基因权”以及以基因信息为客体的基因隐私权或信息权等基因权利体系,明确各种基因权利要素、行使、运行、救济等基本规则。同时,单立《基因技术法》,与《基因权利法》并列,协同调整基因科研、医疗等技术事务。或者,融合基因权利与基因技术,构造公私法混合属性的《基因权利保护法》或《基因法》。
还应开展框架式、实验立法。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及潜在风险,令制度构造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对此,必须深入了解新技术,全面掌握新型社会关系,做好立法预测。鉴于立法者能力有限,在未成熟领域,应采取指引性框架式立法,以简约规则化约复杂世界,为社会进步保留弹性制度空间,为技术和产业发展提供导引。框架式立法时,应实行实验立法。“实验法”应设定期限并伴有评估措施,用于风险治理。①参见王贵松:《风险社会与作为学习过程的法——读贝克的〈风险社会〉》,《交大法学》2013年第4期,第175页。可制定临时性、开放性条款,根据新技术、新领域具体状况,随时检讨立法成效,针对存在的问题,适时调整修订法律,进行动态规制。尤其基因特别立法时,面对技术、伦理、安全等诸多风险,在特定领域、小范围内开展实验立法最为妥当,可把风险后果降至最低,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各方权益。
结语
基因科技令人类对自身的认知进入分子水平,围绕基因的医学、科研、商业利用等活动已蔚为大观。基因是个人的生物身份证,关乎人的尊严。基因之上存在独立的人格利益,已非传统民法物权、物质型人格权所能涵盖。创设“基因权”有利于加强人的尊严保护,维护伦理道德,平衡技术变革、产业发展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最终深度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而在后法典时代,在《民法典》现有规范格局下,应发挥法律解释作用,构造“基因权”;同时,开展特别立法,以特别法系统规定“基因权”,建构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此一过程应注意私法与公法协同、伦理与法律共治、自律与他律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