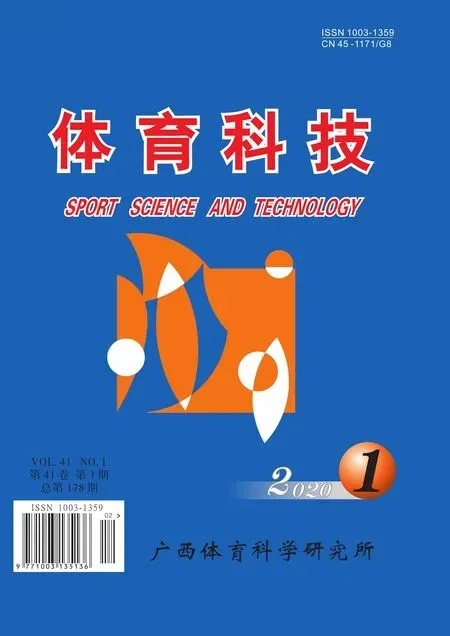神话·仪式·景观
——壮族民俗体育“蚂拐舞”现代转化人类学阐释*
黎年茂
(1.广西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2.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任何一种文化的缘起必定有其缘起与发展的自然和社会根基,并且在其滋润的文化“土壤”里成长成熟。其“土壤”里营养成份,决定了这种文化的意蕴与内涵。壮族“蚂拐”既“蛙”,“蚂拐节”就是蛙图腾文化的典型代表,蚂拐舞作为主要活动内容,是早期壮族社会原始记忆,是在壮族文明这块土壤里发育而成的文化奇葩,它是壮族稻作文明的结晶。2006年,蚂拐节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名录,归属民俗类(编号463,X-15)。据文物资料显示,唐朝《岭表录异》记载铜鼓以蛙为配饰乃壮族先民蛙图腾崇拜的缘由。关于蛙图腾《韩非子·内储说》《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河池县志》均有类似记载,民国《河池县志》中记载壮族正月有祭祀蚂拐习俗。笔者查阅权威文献中发现与蚂拐舞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蚂拐舞是千百年来壮族人民的伟大创造,凝聚了壮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理解诉求,是研究壮族文明的“活化石”,是壮族祖先世界观,反映了人类的思想历程。因此本研究对壮族蚂拐舞进行实地考察,进一步挖掘“蚂拐舞”的起源文化,探索其仪式象征隐喻,剖析象征功能的现代转化形式,对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壮民族地区民俗文化资源发生、发展和现代转化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1 走进蚂拐舞文化传承基地
一个地方拥有特色,才能吸引眼球,一个地方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将更加富于韵味。广西天峨县六排镇纳洞村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以壮族聚居为主,地处被人誉为百里画廊的红水河峡谷沿岸,群峰林立,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暖夏凉,四季分明。纳洞屯以山高水长而闻名于世,山峻拔,水秀逸,洞神奇,石精美,景色如画,风光旖旎,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神奇的民间故事。
纳洞壮族主要以农业耕种为主要生计方式,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期,晚可能早于阶级社会,由于交通闭塞,经济水平、文化观念相对落后,与外界交往相对缺乏,长期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世代延续,稻作农业在当地生产生活中占据着绝对的地位,历史悠久,并对当地民族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民族经济特征可称之为稻作民族。从文化特征上来看,纳洞壮族地区是以壮族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综合体,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相互吸收和同化,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呈现出多元一体、求同存异的局面。例如,壮、汉、瑶等民族间打“老同”“老庚”的现象比比皆是。从地理上看,纳洞地处高原向丘陵过渡带,依山傍水,红水河自古以来作为四川经贵州进入广西的水上通道,将高原旱作文化和丘陵文化融通和整合,成为神秘的区域民族文化,呈现出开放性、包容性、坚韧性和滞后性的特征。而壮民族自古以来均有好歌善舞的兴趣爱好和人文特点,以壮家歌仙刘三姐为代表,从而孕育出许多壮族民俗庆典习惯而衍生成为民俗节日,为民族信仰与动作艺术相结合提供平台,如蚂拐舞正是依附民俗节日而存在,仪式即神圣的身体表达(舞蹈类),是通过肢体展演实现象征、功能现代转化的存在形式。近十多年来,纳洞地区定期举办“蚂拐节”,且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因此对其进行实地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实际意义。
2 神话:蚂拐舞起源口述文本重构
传说与神话、民间故事是围绕特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风俗习惯以及地方风物而展开的口头叙事,通常对其依附物进行描述或者解释,情节带有传奇性特征,通常被视为民众对其社会生活的一种记忆和充满意象的反映[1]。追溯蚂拐舞文化的源流,研究壮民族地区民间有关蛙崇拜神话传说,探索壮族民族民俗文化衍生内在逻辑与功能延伸。据史料记载,古越人对蛙崇拜源于原始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与晴雨气候密切相关,蛙的生活习性恰与自然气候相吻合,因此有“青蛙叫,大雨到”的民间谚语。在壮族地区蛙出没、鸣叫等生活习性与晴雨、旱涝气候变化相吻合,稻作农耕作为壮族先民仅有的生计方式,晴雨就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由此衍生出许多壮民族与蛙之间的神话传说,深刻影响着壮族民间社会生产生活,进而演变成为民族文化,表现为宗教意识和祭祀行为。蛙图腾是早期壮族社会文化和文明程度的展现,归属宗教意识范畴,是氏族制度时期的产物,是人与动物、植物之间超自然关系下的“禁忌”或“祭拜”形式的社会文化现象。诸如汉族敬龙、回族敬猪、土家族敬狗、高山族敬蛇等一样崇拜与敬畏。蚂拐舞作为蚂拐节的主要仪式活动,其历史悠久,且没有足够的依据和文字记载,主要以口述形式留存,迄今为止无法考究它起源具体年代。关于壮族蚂拐舞源起口述文本可归纳如下:
龙王宝杀敌救国:英雄崇拜。广西天峨县主要流传的以崇拜蚂拐神父、蚂拐将军,因杀敌救国的神话故事,流传至今,敬奉的是男性“龙王宝”来构建神话和集体记忆。壮族英雄崇拜主义浓厚,敬仰蚂拐神父、蚂拐将军,典型男性崇拜。相传历史上红水河沿岸连年遭遇旱灾,人们束手无策。上天为了拯救黎民百姓,把一只小青蛙变成一个英俊的小青年,并由村寨中的韦姓人家收作养子,取名“龙王宝”,托“龙王宝”之福,红水河一带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好景不长,富足的生活遭到外族的艳羡,外族举兵入侵,生死存亡之时,龙王宝带领兵马,英勇杀敌,潜入红水河挫败敌军。龙王宝因战功赫赫,被封为驸马,却在成婚前,因天意而随之死去。人们为纪念他对壮族社会所做伟大贡献,定下“蚂拐节”[2]。“龙王宝”作为蛙神后代,男性代表,蕴含着对原始壮民族婚俗习惯抵触意识和较强的英雄崇拜、男性崇拜。
东林浇蚂拐尽孝的传说:蛙婆崇拜。东林浇蚂拐尽孝的神话反映壮族先民对社会压迫和野蛮意识的绝地反抗和对女性的敬畏崇拜。传说远古人吃人年代,出了个东林,阻止天下吃人事。那年他母亲逝世,夜守亡灵,心烦意乱中用沸水把屋外呱呱鸣叫的青蛙烧死,由此引来几年旱灾大祸。最后找到始母解答为:青蛙为天女,掌管风雨和人间福祸。需陪她三十天,拜它为恩婆。由此产生了崇拜思想和敬祭习俗。东林民间故事保留着某些母系社会的痕迹。现在“蚂拐舞”民俗文化展演亦存留原始隐喻,舞场最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两个大鼓, 由两个带姑娘面具的男青年扮女装表演。妇女击大鼓这是在广西各民族舞蹈中极为罕见的, 她们自始至终击鼓伴奏, 事实上成了整场蚂拐舞的指挥者。
传统文化中壮民族心理帷幕:雷神崇拜。雷神崇拜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雷神敬畏和崇拜历经了长期的演变过程,反映传统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状态、思维模式认知水平[3]。这种心理帷幕为壮族蛙图腾文化创造了神秘空间,是祭祀仪式发生的重要源泉和依据,通过“仪式”重述历史神话故事,传递仪式社会功能和象征隐喻。正如詹姆斯·凯瑞认为“仪式”转变、修改和创造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和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4]。纳洞壮族地区世代以农耕为主要生计,雨水事关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问题,雷雨作为天气描述的复合词,是宇宙自然规律的表现。因此,壮族先民总结出蛙、雷和雨水三者之间的发生有一定的自然规律,蛙的出现能预测风调雨顺,甚至原始壮民常把蛙和雷神联系在一起,认为蛙是人与神联系和沟通的载体,通过对蛙的祭拜和敬畏可以传达人间的疾苦和诉求而得以庇护和保佑,这种意识对壮族民族文化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使蛙神叙事口述史有源可溯,也为“蚂拐舞”起源文本构建创造神圣文化空间。
3 仪式:“蚂拐舞”象征功能转化的载体
仪式不仅是对社会诉求的积极响应,更是人类赋予内涵与价值的特殊行为[5]。民俗文化中仪式的作用及仪式中肢体媒介均用来传递文化信息,满足人们生理需要、心理和社会的需求,进而形成了带有礼仪性和规范性的仪式行为举动。壮族蚂拐舞从历史跨越到现代,在仪式中具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性,传达着壮民族某些习俗、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反映仪式主体的社会功能以及象征意义。
3.1 壮民族地区群众社会秩序、道德规范
宗教信仰体系象征的本质在于维持族群内部的安定,是族群的价值观展现[6]。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仪式的本体行为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展现。蚂拐舞仪式正是以形象化的叙事方式间接表达对原始生活的记忆性重述,通过祭祀仪式规范,潜移默化地发挥着诉求认知与表达、愿景寄托和道德行为规范等功能,为激发文化认同、情感交融创造集体空间,这些集体记忆被认为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现实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具有回归历史的当下感。蚂拐舞作为中国式的文化象征,是探索壮族传统社会民族思想世界的重要依据,其起源神话象征伴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对善恶、福祸、正邪、是非等观念的认知,这些观念构建了民族神圣的文化空间,维持旧社会的社会秩序。英雄崇拜、蛙婆崇拜和雷神崇拜作为壮族民间叙事文本,是壮族蛙图腾起源的神话空间。反映出早期壮族先民对自然的认知水平及由此产生的宗教意识,是壮族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蚂拐舞作为壮族“蚂拐节”民俗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它是系列民俗舞蹈的总称,既包含有反映壮族先民宗教意识的舞蹈类型,也有反映壮族原始生计方式农耕劳作技能的“捞虾舞”“插秧舞”“耙田舞” 的舞蹈类型。无论哪一种舞蹈类型,其原始的象征和意义终将回归于通过取悦于拟人化的“蛙神”获得认同,祈求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古代壮民族反抗人与自然压迫的一种潜在意识,记叙了在落后生产力背景下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水平,通过模拟生产生活技能的舞蹈,呈现出原始壮族社会生活面貌生动再现和农业文明真实写照。蚂拐舞祭祀文化由神话传说演变成为祭祀仪式,也是壮族先民生产生活实践需要,其象征隐喻和功能在维系壮族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
3.2 传说与社会记忆构建的符号象征
神话资源现代转化的成功之处在于是否发掘其代表性符号,是否能够激活其文化认同。蚂拐舞作为远古时期壮族先民祭祀信仰中最重要的仪式活动,色彩庄严神秘,富有生活习俗化特点,现已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壮族先民把“蚂拐”当成民族的保护神,通过各种仪式性献祭表达对神的崇敬和虔诚之心,取悦神灵,并把自己内心的诉求传递给神灵,祈求除祛人间灾祸,人畜平安,五谷丰登,隐喻着渴望摆脱对自然和不可预知的心理恐惧和焦虑含义。壮族蚂拐舞民俗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唯心主义思想,反映和记载的是原始人的世界观。而蚂拐舞活动内容里的各种舞蹈几乎均为模仿先民劳作活动技能创编而来,是壮族民族典型的文化符号之一,无论是仪式过程,还是舞者的道具和各种肢体动作都有其特殊的象征和诉求模型,如舞者头戴面具,模仿劳作技能,常伴随着蹲、跳、撂等蟹行状和蛙跳状,运行路线一般为曲折不定,展现的内容主要是先民劳动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场景,这些舞蹈活动表现为祭蛙仪式形式,宗教特征明显,神圣敬畏而庄重,融入了一定的鬼神元素,是早期壮族社会的记忆和原始文明的展现。而蚂拐舞文化同样重在仪式象征和社会功能,其肢体动作均为特定的“仪式”服务。原始“蚂拐”神化文本演变成为蚂拐舞身体仪式性文化符号,是古代壮民族反抗压迫的一种潜在意识,记叙了在落后生产力背景下解决生产生活实践中社会矛盾的需要,是一种迷茫和无奈的精神转换与寄托,为神话传说创造和民族记忆建构提供神秘空间和传承工具,是壮族特有文化符号。
3.3 民俗体育文化行为传承的纽带
在人类学视野中,祭祀仪式和衍生出来的肢体文化作为人们对虚拟世界中叙事文本的选择、加工和创新的行为举动。壮族社会至今延续着许多传统的民风民俗,这些民俗习惯主要是依靠长辈们生活中的以口述和示范的方式言传身教而得以传承,而程序化的肢体动作表演应属于口述和示范传承范式之一。正如理查德·舒斯特曼认为,身体也是有意识的,他把身体的意识分为四个层次: 无意识层次、意识层次、深刻意识层次及反思意识层次[7]。而基于蚂拐舞仪式中,肢体行为意识应处于第四个意识层次。现代蚂拐舞仪式的参与者无论所处社会环境及生活方式从本质上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民族的宗教意识和民族认同依然能从原生态“蚂拐”民俗旅游节日中流露出来,参与者体验到原始祖先的生活场景,促生其敬畏和崇拜的意识,这就是壮族 “蚂拐舞”仪式中肢体文化的魅力。正所谓:“仪式中的范式具有一种促成欲望的功能,它既可以促使人们去思考,同样也可以驱使他们去行为”[8]。壮族蚂拐舞就是通过民俗节日(蚂拐节)祭祀仪式凝聚民族精神,促成民族认同,通过蚂拐舞祭祀仪式中演示轨迹传递民族信仰和动作技能,使参与者在体验民俗文化的同时不自觉地接受民族文化洗礼。蚂拐舞作为壮族特殊的文化符号,其仪式作为壮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和变迁的重要载体,伴随着社会变迁而积极的自我调适、创新发展,不断发挥其社会和象征功能意义。恰如柳倩月教授所言:过去的历史渐行渐远,新的历史由今人创造,而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就是联系古今、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纽带[9]。
4 景观:民俗体育文化现代转化的表现形式
神话文本、仪式行为和景观图片叙事作为神话资源现代转化主要途径和范式。利奇认为:神话乃是一则语言形式的表白,而仪式乃是一则行为形式的表白。也就是说,我们大可将蚂拐舞仪式作为神圣范畴的宗教意识,固然是凝聚民族精神的场所,是壮族社会的集体记忆和行为表达。蚂拐舞由神话到仪式正是促使语言表白向行为表白转化的过程,以肢体表演为媒介,呈现出来的祭祀场景,可以满足现代人的观赏和心理需求,属于仪式性叙述和景观叙事范畴。“蚂拐”神话作为民间口头叙事,而祭祀仪式则是叙事性景观呈现,是关于“蚂拐”神话的社会表现形式。因此,蚂拐舞祭祀文化展演应属于仪式性叙事和景观叙事的综合体,可将蚂拐舞肢体动作表述为祭祀仪式和表演景观。人类学家弗雷泽等人也提出:仪式是神话的展演形式。由神话转化而来的蚂拐舞仪式是壮族人们创造最重要的表达文化之一,用以解释壮族民俗文化的源起及现阶段的社会文明,是壮族人们远古时期的世界观、宇宙观和人生观。蚂拐舞祭祀仪式是纳洞壮族民间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信仰,是蚂拐节最主要的活动内容,记录着远古壮族社会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近年来蚂拐舞如期举办,热闹非凡,车水马龙,人潮涌动,受当地人民积极参与和重视,这些与壮民族信仰有关的节庆和活动正是纳洞壮族人民以肢体动作为媒介,民俗信仰和文化习得为内容的表演性景观叙事形式,而表演者赤膊纹有各种蛙型图案,也可认定为图像景观叙事范畴,其核心是满足国家治理和地方经济发展、创建乡村文明和现代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重述难忘的人文历史,传承民族精神,维护地方民族信仰和文化传统,从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现代转化。伴随着神话和仪式主体诉求的流变,壮族蚂拐舞民俗体育文化也积极地进行着自我调适,仪式象征作用的客体由娱神到娱人的转变、隐喻的功能由凝聚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传承逐渐升华成为国家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主要抓手。场域变迁促使现代蚂拐舞仪式由早期“蚂拐”神话传说演变成为现代的表演景观,从而依靠肢体动作媒介、祭蛙仪式为表象对原始神话传说的再表达,由此,转化生成现代性仪式象征和社会功能,呈现出民俗体育现代转化的主要模式。
5 结语
如何实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一直作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伴随着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如何实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成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就是其中重要议题之一,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意义。美国心理学派神话学家坎贝尔认为,现代人之所以焦虑,是因为缺少神话,应该用神话来抚慰人类的心灵[10]。因此,壮族蚂拐舞文化作为重要的民俗文化资源,在壮族原始民族信仰和人文精神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是国家提倡和加强文化自信建设的要素之一。蚂拐舞文化展演是现代壮族人民以新的方式重述历史、构建集体记忆和凝聚文化认同,是加强壮族社会教育、文化、经济和旅游发展的关键点。壮族民俗体育文化在远古世纪里正发挥着宗教信仰体系中的某些功能和价值,凝聚民族集体,规范社会行为,是原始壮族社会文明的真实写照。作为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蛙婆”神话,通过肢体动作展示成为的壮族民俗文化表演,是一种以神话为母体,仪式为媒介,肢体动作为桥梁,表演景观和图像景观为外在呈现形式的神话资源现代转化典型案例,凝聚民族精神和仪式象征社会功能逐渐升华成为国家治理和地方经济发展及创建乡村文明的重要抓手,是民俗文化象征隐喻和社会功能的升华,是壮族社会现代文明的展现。因此,我们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工具性价值的同时,更应注重其人文功能和作用保护和传承,促使民俗文化资源现代转化更充分,更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