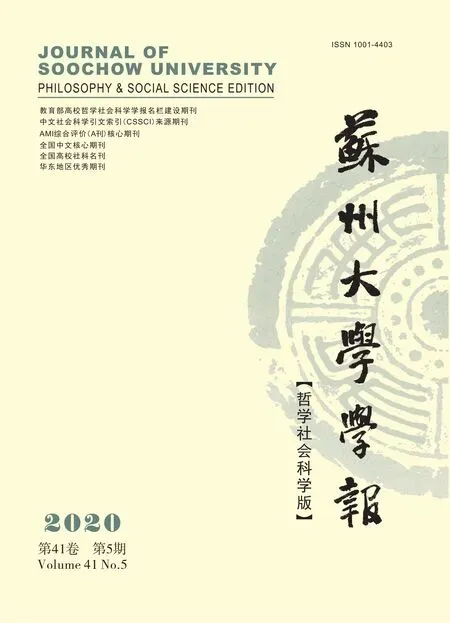论中国式 “心”的内涵
张再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随着科学主义的风靡,人们对“心”的解读日趋认识化、知性化。然而,当我们步入中国传统哲学的领域发现,其中虽有对“心”的同样的解读(例如荀子学说就是其代表),但更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占主流地位的却是一种与之迥然异趣的“心”,一种堪称中国式的“心”。
一、身心一体之心
当代哲学最根本的变革,莫过于现象学的出现了。这种现象学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现象与本质关系的完全改观,而且还导致了人们对身心关系的全新理解。也就是说,对于现象学而言,身心关系已不再停留在笛卡尔所坚持的心是心、身是身,身心是判然有别、彼此对立的二元,而是转变为心中有身、身中有心,身心相互交织、有机联系的一元整体观。用梅洛-庞蒂的表述,即真正意义上的心,与其说是一种笛卡尔所谓的“我思”,不如说是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之间的一种织体。这里所谓的“不可见的”也即通常所谓的内在心灵,而这里所谓的“可见的”也即通常所谓的外在身体;或者说,“意识本身是一种为己的原呈现,这种原呈现被呈现为为他的非原呈现”[1]304。换言之,“思想不是依据自身,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2]序言19。其情况,恰如画家用色彩、音乐家用音响、作家用感性形象表达自己的心灵那样而显而易见。故对于梅洛-庞蒂来说,人类的艺术创作无疑可视为这种全新的身心一体观至为生动、也至为有力的体现和彰显。

道家的身心一体思想,既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又成为连接中国文化与佛学文化不可或缺的桥梁。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谈到中国佛学中法相宗思想,也即唯识宗思想;因为按倪梁康先生的说法,“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某种形式的法相宗”[3]。换言之,就其方法论而言,一如现象学坚持本质即现象、不可见的亦为可见的那样,法相宗亦以“非因迷而求真,则真无可求之路”这一“真俗不二”为其方法大纲。据此,法相宗坚持心外无独立的客体存在,把世界一切现象都视为内心所变现。所谓“外境随情而施设故非有如识,内识必依因缘生故非无如境”(《成唯识论》卷一),意指诸法随人的情识设置而有、识依因缘而生故非无。故对法相宗来说,真正的世界乃是处于有与无、真与幻之间,这种“之间”恰恰可视为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的“交织”。用佛学术语来表述,这种“之间”也恰恰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这一“互为因果”的“之间”。也许正是受这种“互为因果”思想的影响,晚明思想巨人刘宗周才为我们推出了“仁复藏果,果复藏仁”这一哲学上伟大而深刻的洞见,而把中国传统的“身心一体”思想在理论上推向了一个全新而更高的阶段,使其不再像前人那样仅仅停留为一种前思的独断。
值得注意的是,道家的“身心一体”思想为禅宗在中国的风靡做好了重要铺垫,也即“在吸收了道家思想之后,禅宗才在中国传播开来”[4]。如果说法相宗以其繁缛的理论推演往往给人以舶来之嫌的话,那么禅宗则以其“简易功夫”更为中国人喜闻乐见。故在中国思想史上,与其说是法相宗,不如说是禅宗为中国传统的身心一体思想建设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正是禅宗提出“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提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提出“烦恼即是菩提”,“淤泥定生红莲”。在禅宗学说里,心与身是如此的密切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举手投足、扬眉瞬目都有佛性,以至于我的心走在哪里,我的身亦走在哪里,心的界限即身的界限。正像梅洛-庞蒂表述的那样,一如我的心灵可遨游太空,“我的身体亦可达到星星”[1]75,故禅宗身心思想实开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之先声。也正是禅宗,从这种身心一体思想出发,主张真正的修行并非要求你“沉寂守空”地一味耽于心灵的冥想里,而是要求你“正念式”地也即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地投身于生活和工作之中。此即禅宗所谓的“饥餐困眠”,而非“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景德传灯录》卷六);也即铃木俊隆所谓的“一切作为都是修行”[5]132。从中不仅使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儒家的“执事敬”的传统,还为我们开出了并非假道于“新教伦理”的东亚自身的敬业、精工精神。
实际上,这种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地投身于生活和工作之中,就是禅所谓的“活在当下”。而这种“活在当下”既是一种身心一体的活动,又是一种对不可见的本心的“智的直观”的直接经验活动。更严格、更准确地说,这种“智的直观”与其说更多地像康德、牟宗三所认为的那样,表现为一种心思的认知,不如说更多地像梅洛-庞蒂现象学所认为的那样,表现为一种“用身体知道”,也即一种其所谓“我走向世界”的“我走”。[1]285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禅宗何以从纯粹“冥想”最终走向“念念若行,是名真有”,走向由禅僧所推进的“行脚运动”,从“观念禅”“文字禅”走向借助于种种身体行为的“以势示禅”,甚至走向“是欲见性,必先强身”(达摩语)的少林武功。而中国画论、中国武术的“得心应手”之说也正是以这种禅的主张为其发端。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王阳明何以受禅学影响,以所谓的“致良知”取代了传统的“良知”;而“致良知”之所以有别于“良知”,乃在于前者更为强调的是“事上磨炼”,强调我们应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也即强调不是在纯粹的“知”中,而是在“元来只是一个功夫”的“知行合一”中来把握“心之性”“心之理”。故阳明的良知说不仅与康德的“智的直观”说大异其趣,亦为我们暴露了牟宗三基于“智的直观”的“心性说”中所难以遮掩的“唯知主义”的理论嫌疑。
耐人寻味的是,一种现象学精神除了表现在禅的“活在当下”的内容上,还表现在如何通达这种“活在当下”的途径上。也就是说,正如现象学认为为了“回到事物本身”,也即回到彻底直觉的经验,就必须实行对所有先入之见的“现象学的悬置”那样,禅宗亦认为为了回到“活在当下”,就必须做到对种种物我两执的“一切放下”。故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佛学“不许因果,不许本质,唯以现所感触为征”的前语言的“现量”思想的体现,还看到了佛学对中国传统源远流长的“减法功夫”的归返。这种“减法功夫”可见于老子的“为道日损”,庄子的“无待”“坐忘”;可见于孔子对“性相近,习相远”的自觉,孟子的心“勿忘勿助”和力反“揠苗助长”的主张;可见于张载的不萌见闻的“德性之知”的首创;可见于阳明的关于祛“习心”之蔽的思想;可见于宋明儒对“戒慎恐惧”的修身功夫的高扬。而蕺山对所谓“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等“五过”的“讼过”和“改过”的力倡,以及从中推出的他的“过”“妄”不二的思想(1)刘蕺山称“有过而后有不及,虽不及,亦过也。过也而妄乘之,为厥心病矣”。《刘宗周全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第17页。,则可视为代表了中国心性现象学的“减法功夫”的最终的绝唱;尽管他对禅学始终坚持着毫无妥协的批评立场,甚至把“流于禅”视为阳明心学难以克服的硬伤。
这里所涉的“现象学的悬置”也即“现象学的还原”。但按梅洛-庞蒂的说法,“最重要的关于还原的说明是完全的还原的不可能性”[6]17。也就是说,一种“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的交织、一种“身心一体”的现象学决定了,对一切先入之见的彻底“悬置”是如此的难以实现,以致于这种实现犹如我们的解释要脱离“前理解”那般的困难,犹如我们要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球上拔起那般困难。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之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玉洁的世界,一个则为红尘滚滚、前缘难了的世界。因此,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哲学中,“回归本心”与“反求诸身”实际上走着同一条道路。故“知恻隐”的“心”也即“识痛痒”的“身”,而阳明心学之所以流于具身化的禅,心学之所以出现后心学的身学转向,心学之所以从阳明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其心”一变为刘蕺山的“直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的“大身子”,这与其说是对中国式的“心”背叛,不如说恰恰是中国式的“心”的现象学逻辑的使然,恰恰是中国式的“心”的身心一体内涵的极其忠实的理论体现。最后,这还意味着,正如禅宗告诉我们的那样,一种“活在当下”的彻底实现,不仅要求我们从所谓“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走向所谓“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而且也要求我们进而从所谓“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重回所谓“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五灯会元》卷17),也即我们唯有通过破除执念上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之“圆圈”,才能真正解决禅的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不可还原之间那难以克服的两难。
二、生命可能之心
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心”,既是一种“身心一体”之“心”,又为一种“生命可能”之心。现象学坚持“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之间的“显微无间”的原因,就在于它把“微”与“显”不是看作两种实体,而是视为事物由微及显、由潜在到呈现的过程,即一种事物可能性之不断展开、展现的过程。在胡塞尔那里,它使其宣称“‘可能性’的知识必须优先于现实性的知识这种古老的本体论学说,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真理”[7]201,并把从意识视域意向中发现的这种可能性视为我们每个人的绝对存在根据的一种“根本可能性”[7]111;在海德格尔那里,它使其把“此在”之“在世存在”称为“去存在”(Zu-sein),而这种“去存在”就是作为“此在”最重要属性的可能的存在;在梅洛-庞蒂那里,它使其认为身心一体即“我走向世界”的“我走”,而这种“我走”涉及的是一种我“能够”[1]285,进而指出“意识最初并不是‘我思……’,而是‘我能(I can)……’”[6]183,并认为这种“我能”是“将我的经验向世界和存在开放的那种可能性”,那种“更加根本的可能性”。[1]137
既然这种可能性是一种由微及显、由潜在到呈现的过程,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体现了事物动态的发生、生成,从而它就不外为一种生命之可能性。故对于胡塞尔来说,把握住了这种可能性就把握住了“生命的纯粹主体”,乃至使他推出了“我思,故我在,故这个生命在,故我生活着”这一命题[7]111。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可能性必然导致所谓的“生存”(Existenz),而他的后期哲学重要概念的所谓“缘构发生”(Ereignis),则正是对这种生态化的可能性的进一步深入阐明。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这种可能性恰恰就是其所谓的“生命意向性”,并且从这种生命意向性出发,使他明确宣称“感觉体验是一种生命过程,也是生殖、呼吸或成长”[6]31;而他的生命意向有赖于“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的交织,不正可视为一种现代版的“阴阳化生”吗?
这意味着,一旦现象学同时被理解为一种生命之可能性的学说,我们发现,中国式的“心”的学说与现象学又一次默契相通了。也就是说,中国式的“心”既是一种即“身”见“心”之“心”,又为一种以“生”训“心”之心。在中国思想史上,论及这种以“生”训“心”之心,就不能不使我们首先提到孟子。众所周知,孟子为我们开创性地推出“尽心知性”的命题,而这里所谓的“性”,与其理解为人性的性,不如说一如《说文》“从心,生声”,一如古人“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所指,乃为人生的“生”。故“尽心知性”意指,一俟我们扩充了自己的心,我们就会认知到自己生命的生。无独有偶,这种理解的忠实性还可援之于孟子的“四心即四端说”。孟子“四端”的“端”字本作“耑”,《说文》解耑云:“耑,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易言之,“端”即事物之萌芽、之端倪,也即我们所谓的生命之可能。
人们看到,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孟子这种以“生”训“心”的极其珍贵的思想,除了可见于《中庸》、郭店竹简(如竹简提出的“心,志并举”,提出的“有性有生”,提出的“机然忘塞”的“流体”,等等[8])外,实际上成为日渐湮没无闻的历史绝响。只是殆至道家重新发现与佛学的一度大昌,以及援道于儒、援佛于儒的宋明新儒学的崛起,这种以“生”训“心”的思想才又一次得以光大发扬。
先看道家。一如许慎《说文》“一达谓之道”、桂馥《义证》以“导”训道所示,道家之“道”的目的性特征显而易见。但以康德的术语来表述,这种“目的”并不是一种“外在目的”,而为一种“内在目的”,也即一种“生命目的”。这使道家的学说不能不打上鲜明的“生命哲学”的印迹,使道家之道最终是以“生之道”为归依。这种道家的“生之道”除了表现为老子所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一关于道明确表述外,还表现为他对“玄牝之门”的强调,对“物壮则志”的强调,对“婴儿”“赤子”的强调;而其对“以屈求伸”“持满戒盈”“势”的提撕,则体现了对生命的潜能的无上高标。从老子的“生之道”中,不仅产生了庄子的“保身全生”的主张,对“残生伤性”的“以身为殉”的人类危机的大力声讨,还滥觞出了道教旨在“夺造化”“窃天地之机”和开发人自身能源的修炼之道。而在解老释老基础上的魏晋玄学“以无为本”的“无”,与其说是一种实在论意义上的“无”,不如说恰恰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无”,也即一种有别于“现成性”的“潜在性”“可能性”之“无”,它同样是以老子的“生之道”为其坐标、为其机奥。
再看佛学。如果说道家更多是在“天道”的名义下为我们谈论“生”的话,那么中国佛学则以强调“万法唯识”“三界唯心”,而使我们可直接切入人心之“生”。先以法相宗为例。对法相宗来说,一如章太炎所说,“言自然规则者,则谬于自性,不知万物皆展转缘生,即此展转缘生之法,亦由心量转缘生”(《四惑论》);或更具体地说,法相宗的人心即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种子和现行循环往复,恒转如瀑流之所在。这不正是海德格尔所谓在相互之中的“缘构发生”、梅洛-庞蒂所谓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交织中的无限的“生命意向性”吗?再以禅学为例。禅的学说虽然众说纷纭、林林总总,但其根本要旨则是祛除妄心,显现与佛性合一的本心,以开发其固有的无限生命能;或一言以蔽之,即“明心见性”。这里所谓的“性”,也即孟子的“尽心知性”之“性”,亦即人生之生,故禅学同样恰恰为一种以“生”训“心”的理论。职是之故,才使禅学在肯定“三界唯心”的同时反对“实体化”的心:“问曰,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师曰在心内。藏曰,行脚人着什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五灯会元》卷十)。职是之故,才使禅学所谓的“心”是“无所住心”之心,并且从这种“无所住心”之“心”出发,使禅学力辟心的种种一成不变的执见、执念,为我们得出所谓“念头死,则法身活”的观点。职是之故,才使禅学有了“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春来草自青”(《五灯会元》卷一五)这一答语,使禅宗不是在文字、概念和理论里,而是在大化自然的诸如流水落叶、花开草长、鸢飞鱼跃里为我们隐喻出心灵无穷的勃勃禅机,从而才诞生了苏轼“惟江上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前赤壁赋》)的千古名句。职是之故,才使禅宗从佛学的不生不灭永恒转向转瞬即逝的当下、瞬间,提出“永恒在瞬刻”“万古长空,一朝风云”,在可直接把握的“现在”“当前”里,领悟不分昼夜、奔流不息的时间,并借以不仅使我们参破了世人似乎永难洞破的生死机关,而且也为我们开出了宋明人“千万年只是当下”这一中国式的现象学的时间观念。
作为援道于儒、援佛于儒的宋明新儒学,则使这种道、释以“生”训“心”的心学观点得以空前彰显,代表了中国古人对心的理解发展的最高阶段。例如,宋明心学的“种子论”的观点。程子“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这一说法人们耳熟能详。此外,我们还看到上蔡的杏仁、桃仁的隐喻,朱子茄籽粒的隐喻,以及真德秀的莲实的隐喻。[9]285显然,如此众多的思想家之所以都指向了“种子隐喻”,不能不使我们追溯到法相宗的观点,不能不使我们从中感到宋明人对心的理解与法相宗的“种子生现行”的思想有着某种不解之缘。例如,宋明心学的“灵根论”的观点。王阳明谓“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10]101,不难看出,无论是“种子”的隐喻,还是“灵根”的隐喻,都为我们指向了生命的生生不息。但二者的理论来源是不同的,前者更多出自法相宗的“种子生现行”之说,后者则更多可直溯于孟子的“四心”即“四端”、老子的“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之论。再如,宋明心学的“心几论”的观点。刘蕺山是这种“心几论”的最具代表性人物,他称“未有是心,先有是意,曰‘心几’”[11]434,并言“只此一点几微,为生生立命之本,俄而根荄矣,俄而干矣,俄而枝矣,俄而花果矣。果复藏仁,仁复藏果。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是故知死生之说,是故知无死无生之说”[11]469。这里的“心几”的“几”,也即周子“动而未形,有无之间为几”之“几”,就其为一种潜在的生命可能性而言,它与上述的“种子”“灵根”完全同义。但是,就其触探到“果复藏仁,仁复藏果”这一生命可能性的可逆性的“互为因果”而言,它则是对这种生命可能性更为淋漓尽致地领悟的体现。这意味着,蕺山的“心几论”的观点,既师承了与道家生命哲学可以互发的《周易》“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辞上》)的思想,又深得法相宗“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这一种现不二观点之真传,从而使其以“生”训“生”思想实际上屹立于宋明心学理论的真正前沿。
这一切,就把我们带到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的心学观。也即牟宗三先生认为,就心学系统而言,中国哲学可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以“格物致知”为宗并成就于朱子的横摄性的心的系统;一种则为以“尽心知性”为宗并成就于王阳明、刘蕺山纵贯性的心的系统。换言之,一种是“以知训心”之心,一种则为“以生训心”之心。同时,牟宗三先生还指出,如果说前者是所谓“别子为宗”的话,那么唯有后者才以其忠实于中国哲学的大本达道乃不失为中国心的理论之真正正宗。至此,经由牟宗三先生的甄别鉴定,一种中国式的心的本来面目业已大明。
这不仅是中国式的心本来面目的大明,而且也是中国式的道德本来面目的大明。也就是说,中国道德之所以坚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之所以坚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之所以坚持“极天下之色,不足眩吾之目;极天下之声,不足淆吾之耳;极天下之艳富贵,不足动吾之心”[12]686,以及之所以与西方的“幸福不许诺德行”一致而坚持“为富不仁”,恰恰在于“在心为德”(《周礼·地官》注);而心的生命可能性决定了,它以其生生不已的性质乃是对一切生物性的既有规定(尤其是生物性的趋利避害规定)的超越,并正是在这种超越中使中国心学一跃为“道德形上学”。因此,这意味着,正如中国式的心是生命之心那样,中国式的道德亦是生命之德。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何以中国式道德始终是和布种、研几须臾不可分,才能理解何以中国式道德总是为我们指向了“如婴儿之未孩”的“赤子之心”,才能理解何以中国式道德乃以“和实生物”的“和”而非“同则不继”的“同”为实质规定,才能理解何以中国式道德是通过“感应之几”来把握所谓“一体之仁”,才能理解何以中国式道德具有“敬宗收族”“天亲合一”的突出特征,才能理解何以中国式道德为我们打上了有机体与环境互动的“处境伦理”“时机伦理”的鲜明烙印。无疑,在生物技术已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命面貌的今天,在诸如人工堕胎、克隆人、器官移植、安乐死、代孕母亲、同性婚恋的风靡使人无所适从的今天,对中国这种既根深蒂固又不守固常的开放性生命道德伦理的重新揭示,必将为走出举步维艰人类生命伦理的困境提供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
“知几其神乎”(《系辞下》)!其实,一旦我们了解了生命可能之心,我们就不仅了解了中国的生生不已的“德”,而且还同时了解了中国的生而不测的“神”。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步入与神圣相连的中华民族的信仰领域。
三、民族信仰之心
还是让我们首先从现象学谈起。一种不假中介的现象学,既是一种之于对象至为直觉的学说,又是一种以其我在直觉而为真正切己的“我”的学说。故对于胡塞尔来说,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完全一致,我思之“我”是最无可置疑、最具明证性的东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本体的“此在”之所以为“此在”,乃在于它以其“在世性”的此时此地性质而为一种“属我性质”(Mineness)的存在,而他后期推出的所谓“缘构发生”(Ereignis)的eigen,同样也具有“自己的”“切合自身的”的意蕴。对于梅洛-庞蒂来说,他所谓的意识最初的“我能”,意指“这种可能性就是我,我就是这种可能性”[1]74。故无论是他的“我能”还是他的“我走”(“我走”是对“我能”的另一表述形式),实际上都与“我”难解难分。
这样,正如现象学的“心”不外乎为一种“我之心”一样,中国式的现象学化的“心”实际上亦是一种“我之心”。而这种“我之心”的揭示无疑为中国哲学迎来一场石破天惊的发现。也就是说,既然我之心是一种“身心一体”之心,既然这种“身心一体”之身同时又是一种“走向世界之身”,那么,这意味着,“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陆九渊集》卷三十五),意味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六),意味着“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下)》)。于是,与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一致,穷尽了我之心,不仅可知人的生之性,进而还可知天道的生生之规定,从而吾心已不再仅仅停留在伦理端倪之心,而同时是在人“上下与天地同流”中直接成为“天地生物之心”,也即宇宙根源之心。换言之,“鸢飞鱼跃,其机在我”,那种看似不可诘致的大化宇宙之终极、大化宇宙之根本并非异己于人的东西,而是它就亲切体己并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心中。
这就把我们导向了章太炎所力推的“依自不依他”这一中国哲学的至胜命题。章太炎写道“要之,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答铁铮》),写道“孔氏而后,儒、道、名、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一语”(《答铁铮》)。这里反复申说的“依自不依他”,也即他所谓的“厚自尊贵”,所谓的“自贵其心,不依他力”,所谓的“自贵其心,不以鬼神为奥主”。在章太炎看来,也正是在这一点,以一种点睛之语使中国哲学成之为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民族哲学;尽管他的这一命题的产生显然也受启迪于西方后来的叔本华哲学、尼采哲学。而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如诗如歌的人生,不正是对“依自不依他”的生动践行吗?
显然,考之中国思想史,章氏的这种“依自不依他”的确是揆之百世的不易之谈。就儒家而言,它可见于孔子的“为仁由己”、孟子的“万物皆备 于我”之说。就道家而言,它可见于老子备极推崇的自然而然的“自然”,即一种生命的“自组织”的自然而非无生命的“他组织”的自然。就中国佛学而言,它可见于法相宗的为“心”所依的“心王”,禅宗的“佛是自性作”主张以及其对“自家宝藏”的无上尊尚。而后来王阳明的“心学”,则可视为是对中国古代的“依自不依他”精神的进一步明彰。他所谓“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所谓“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同上),以及“个个人心有仲尼”和“满街都是圣人”,不仅将“依自不依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峻极之境,而且以其“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但不可取尼采贵族之说)”(《答铁铮》),为我们实开中国近现代“主体性”精神之先声。
其实,这种“依自不依他”既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精神的真正声明,又为中国文化“不以鬼神为奥主”的“无神论”精神的真正声明。在这方面,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实际上都无一例外。按章太炎所说,尽管孔子亦有天视、天丧、天厌、获罪于天等语,似非拨除无神论者,然而孔子又曰:鬼神之为德,体物而不可遗。此即明谓万物本体即是鬼神,无有一物而非鬼神者,是即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之说。泛神论者,即无神论之逊词耳,也即客客气气的无神论说。此外,孔子之祛神还见于他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却明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而“如在者,明其本不在也”(《答铁铮》)。儒家是如此,道家亦不出其右。如老子言象帝之先,即谓有先上帝而存者,如庄子云道在屎溺、无乎逃物,则正所谓孔子体物而不可遗者,也正与孔子的泛神论之说相合。再加上“孔子学说,受自老聃”(同上),这足见中国无神论思想流长源远。最后,中国无神论思想还可以中国佛教为坚定之援。佛教行于中国,宗派十数,却独以禅宗为盛,究其故端,恰恰在于其“以自贵其心,不援鬼神,与中国心理相合”(《答铁铮》)。而禅宗推见本原,实以法相宗为其根核。较之易简工夫的禅,法相虽多迂缓,然而,“至于自贵其心,不依他力,其术可用于艰难危急之时,则一也”(《答铁铮》)。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中国思想广持“无神”之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像一些矮化中国文化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信仰上缺乏神圣的超越性,而是相反,其和其他民族思想一样同具神圣的超越性,因为但凡伟大民族的思想文化都须臾不可离于这种超越性,因为正是这种超越性,才使我们生命从有限走向无限,从生灭走向永恒,从而也最终使人猿揖别,使一种大写的人成为真正的可能。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其他域外民族所持的超越性是一种“外在超越性”(如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出世间法”)的话,那么中华民族所持的超越性则为一种“内在超越性”。对这种“内在超越性”研究最为精深的牟宗三对之写道:
有“心性之学”之教,则可迎接神明于自己之生命内而引发自己生命中神明以成为润身之德,“从根上超化一切非理性反理性者”(唐先生语),如是,吾人之生命可以恒常如理顺性,调适上遂,而直通于超越之神明,此为彻上彻下,既超越而又内在,一理贯之而不隔也。[13]
易言之,对于牟宗三来说,这种“内在超越性”之“内在”,是指内在于我们自己作为生命可能的心之中,内在于我们自己顺人性达天命的“纵贯系统”的心之中,也即内在于他所谓的“自由无限心”之中。然而,遗憾的是,当人们进而追问这种超越性之内在如何可能时,牟宗三先生却将之归结为康德经验主义所不认可的人所具有的“智的直观”这一心的特殊功能。于是,在牟宗三那里,一种不无吊诡的自相矛盾出现了:本是合内外、一身心的心,又重新回到纯内在、纯思知、纯观念之心;本是后康德主义的心,又重新回到康德主义之心。其结果必然使牟宗三“内在超越”的把握看似唾手可得,实则却仍犹如天地之隔。也就是说,牟宗三先生并不理解,对“内在超越”的真正把握与其说是一种康德式的特殊心知的产物,不如说其恰恰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交织的身心一体的结果。正是在这种身心一体之中,其既使不无神秘的“智的直观”得以证成[14],又使那种既内在又超越、既形下又形上的“内在超越”成为真正可能。
因此,在通向“内在超越”的道路上,“回归本心”与“反求诸身”以一种内生外成、互为表里的方式携手并行,心的端倪的无限扩充与身的机体的无限伸展体现为同一过程。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哲学既讲“万化根源总在心”(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又讲“万化生于身”(李贽《九正易因·乾》),既讲“心藏神”(《内经·素问·宣明五气篇》)又讲“有神自在身”(《管子·内业》)。以至于中国哲学愈强调心的神化,也就愈强调身的神化;以至于它使提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的张载不得不趣向“天亲合一”,使力倡“赤子之心”的罗近溪必然以“直竖起来,便成上下古今,横亘将去,便作家国天下”[15]951这一“无限身”为皈依,并最终使他们都由之跻入“死而不亡”这一至极的生命化域。无独有偶,该思想恰恰又与古文中“身”通“伸”(申)、“申”又通“神”这一《说文》中的以“身”训“神”解释完全妙契合一了。
故在这里,我们不仅发现了中国哲学如何超越世俗之道,同时也揭晓了今人如何超越牟宗三之道。换言之,唯有从康德式的“心体”走向梅洛-庞蒂式的“身心一体”,我们才能揭示牟氏终极性“自由无限心”的真正隐秘,从而才能为中国哲学形上研究迎来全新的“后牟宗三时代”,并最终使中国本土哲学步入当今世界的前台。
——兼论现象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