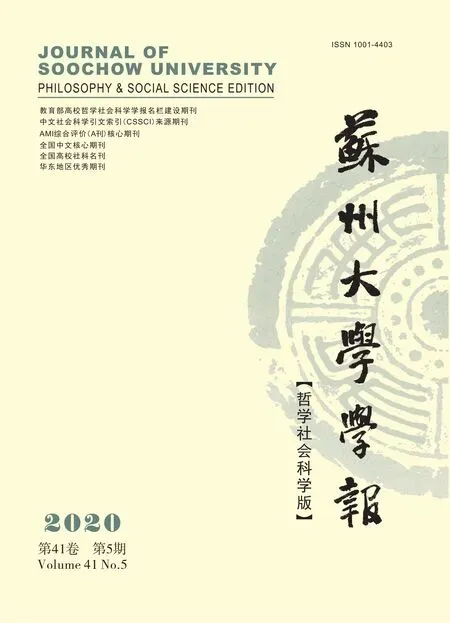唐代刺史与州郡的文学关联
李德辉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唐刘禹锡诗云:“苏州刺史例能诗,西掖今来替左司”[1]卷三六○,《白舍人曹长寄新诗有游宴之盛因以戏酬》,4060,此诗揭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唐代刺史和州郡的文学关联。照理说,多数唐代刺史都是能文的,在任数年,必有文学作为,从而对当地文学有所贡献。但这只是一般状态,不在讨论范围,我们感兴趣的是唐代刺史影响州郡文学的方式、途径、效果,二者结合的具体状况,意欲从这些方面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1)近年相关成果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刘勇《唐代刺史与文学》,但其研究对象、路径、角度都与本文不同。本文意在探讨刺史是怎样与州郡文学结合的,并不讨论刺史的文学成就。,避免论述的浮泛。
一、刺史与州郡文学关联的两个基础
刺史为一州最高长官,在古代使用过郡守、太守、刺史、知州等不同名称。唐之刺史,通称“使持节某州诸军事守某州刺史”,集一州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样的人到任,关系到一地文学的全局,因而刺史与州郡的文学关联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唐代国祚绵长,通计五代长达342年,名刺史多,文学名家也多,文学业绩突出,刺史与州郡的关系,在唐代尤为密切。这种关联,建立在两个基础上:
一是刺史的水平能力。刺史人数多,分布广,构成复杂,各有等差。刺史个人能力水平的高下,决定了对当地文学发展所起作用大小。刺史的能力水平,可以有政事、文学两个衡量标准。政事、文学都突出的刺史,本人既能写出好作品,行政能力也强,对地方文学能起更大作用。能力水平一般的刺史,可能写不出很多好作品,但他可以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因而其与州郡的文学关联亦不可忽。考虑到优秀刺史人数不多,数量更大、能力一般的刺史才是基本面,对于这类人物与州郡的文学关联,尤当给予足够的注意。
二是州郡的等级层次。唐代358州(2)此据《旧唐书·地理志一》统计。《旧唐书》根据的是《贞观十三年大簿》,此时唐代地理版图已经确定,可作依据。唐代羁縻州虽多达856个(此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但不纳贡赋,不上户部,仅仅表明其是唐代的“声教所暨”,非实际管辖范围,且素无名郡,故不在统计范围。,因为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的关系,分为不同等级。这种等级看似不好把握,但仍有明确的判断标准,那就是两《唐书·地理志》分出的上中下州。唐朝政府分出的这些等级,正是基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总体水平所做出的判断,是有科学依据的,行政层次高下也反映出一地文学水平的高下。基于此,行政上的上中下州,大体上也就是下文将要论述的名郡、一般州郡和无名州郡。上州政治地位高,地理位置好,经济文化资源优厚,是一地的行政中心,知名度高,影响大,多数属于名郡。中州的地理位置不是特别偏远,政治地位和经济文化水平不上不下,文学上也居于中位。下州位置最偏远,等级最低下。中原地区及交通便利的州郡,名郡较多。南方偏远地区,无名州郡最多。对应于具体州郡,以江南道为例,则润、昇、苏、杭、湖州为名郡,睦、明、衢、处、温、台等州为一般州郡,最偏远的汀、漳二州为无名州郡。再以湖南为例,则潭州为名郡,衡、郴、道州为一般州郡,位置最偏僻,条件最差的连州为无名州郡。像这样,以行政等级为依据,参考地理位置及社会知名度,就可分出上中下。
刺史与州郡的文学关联,视州郡的层次高下而变化。名郡文学传统悠久,资源优厚,对名家名作的需求并不强烈。一般州郡没有很多优势,刺史的带动作用显得突出。下州各种优势全无,发展文学的需求最迫切,刺史对当地文学发展所起作用最大。
以上两个方面,分别从人与地两个角度影响着唐代刺史与州郡文学关联,构成这对关系的两个基点。
二、刺史与名郡:增强地方文化吸引力
唐代众多州郡中,分量最重的是名郡。唐代的名郡有三种:首先是一个政区的行政中心——开元十五道治所,如河东、剑南、江南东道治所太原、成都、苏州,此为顶级名郡。其次是至德以后分出的四十七个方镇治所,其名具《旧唐书·地理志一》及《元和郡县图志》,除开少数不知名的外,其馀皆要冲大郡,如荆南、浙西、浙东治所江陵、润州、越州,也有一定知名度。第三,还有一种名郡,不是政区治所,但因位置适中,境内有名山名水而历来有名。如魏、徐、江、湖州,这样的州郡,文学上也颇有分量。
唐代出名的州郡集中在地理位置好的江南、淮南道,唐代租税所出的“东南四十三州地”,因为经济分量增加而政治地位抬升,吸引士子前往。为了保障租赋来源稳定,地方经济繁荣,唐廷往往派遣重臣出镇方面,精择能臣担任刺史。而治才高的刺史,文学上往往也是名手,能够写出更多的名篇。即使本人文才较弱,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发展文学。因而对于名郡来说,刺史和名宦就是同义词,二者等价,刺史与州郡的文学关联,在名郡这里,体现为州郡-名宦-名篇的联系。
名宦一词南北朝就有,指名位、官宦,此为古义。本文则取宋以后所起新义,指德行、政事、文学出名的地方官。宋代地志多设有名宦门,收录各地著名官员,而以刺史为主,故名宦一词,多指刺史。中唐以下,出于唐朝政府有意的制度安排,文学名家多被指派到名郡去任刺史。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以名手、能臣配善地,犯官配丑地,平庸者配一般之地的用人方略和惯例,相沿不改。由于这一制度,很多著名官员在其仕宦顺畅阶段,所历皆善地,在任多佳作。
文学上的名宦,条件很高。本人既是政坛能臣,诗坛名人,而所在州郡也位置较好,众人向往。在这样的地方做官不仅十分荣耀,更有信心,创作也更有激情,会进入持续高涨状态。作为行政主官,在任两到三年(3)唐代刺史,一般以三或四年为一任期,但除去赴任路上行走数月,实际在任不到三年。,会在文学事业上有建树,比如写作诗文、培育新人等。时间一久,名宦-名郡-名篇之间,就形成一种稳定、明晰的连带关系。名宦本来就是依靠名气和地位来吸引人的,而州郡又会因为名宦的到来而更知名;善地的美名本来就有助于提高为官者的美誉度和自信心,而名郡地位声名的维持和扩大,也有赖于名家的到来和艺术创造,二者之间,形成一种稳定而明确的依存关系。名宦本人虽然任满以后徙任他所,但他在当地的那些施为,却长存于历史的时空,成为一种遗迹、传说和声名,增强一个地方的文化吸引力。
但拿开这些东西,这个地方也不见得就会降低地位,减损声名。由于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它的优越地位始终不会改变。优秀作品只能给当地添彩,此外并无更多意义。至于一般作品,更只是一种量的增加。例如唐杭、越、鄂州,写西湖、镜湖、黄鹤楼的诗文就成百上千。然而这些东西,对当地却无决定意义,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可见对于名郡而言,优秀作品的作用是第二位的。刺史和名郡的文学关联,只能是“地因文增重”,即因为大量书写当地的文学作品而扩大本地影响,增强地方文化分量,而不能是其他。

从这些人名、诗文的罗列可知,名宦对于当地固然是锦上添花,但他们留下的那些名作更不可忽,是文学上的“千秋万岁名”,一个地方对外宣传的最好资料。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创作的《钱塘湖春行》《杭州春望》就是杭州重要的文学资源。岑参的嘉州刺史经历及其留下的数十首巴蜀诗文,更是嘉州宝贵的文学资源,不仅能促进当地文学发展,还影响到外地人才成长。陆游诗风的形成,就与其乾道中知嘉州的经历有关,正是这段仕历加深了他对岑参的认同。其《剑南诗稿》卷四《夜读岑嘉州诗集》自叙文学渊源云:“汉嘉山水邦,岑公昔所寓。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常想从军时,气无玉关路。至今蠧简传,多昔横槊赋。零落财百篇,崔嵬多杰句。”[2]《剑南诗稿校注》卷四,332《跋岑嘉州诗集》:“予自少时,绝好岑嘉州诗……今年自唐安别驾来摄犍为,既画公像斋壁,又杂取世所传公遗诗八十馀篇,刻之以传知诗律者,不独备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意也。”[3]卷二六从中可见名家诗文的影响之大。文中提到的刻印文集,传播名篇的“此邦故事”,越出了纯文学范围,而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部分。嘉州不过是唐剑南西川名气稍大的州郡,但在例证上却有代表性。从明清古籍中可以看到,岑参是巴蜀除了李杜之外最著名的诗人,在《蜀中广记》《成都文类》《四川通志》中出现频率较高,作者多在宋以下。可见一个地方如果有著名文学家任刺史,那他的影响不仅在当代,更在后来。嘉州地区文学在宋以后的发展,就与岑参这样的名家到来很有关系。
再以唐苏、杭、越三州而言,《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搜罗的数以百计诗文,就是当地文学的代表作。《会稽掇英总集》录唐五代北宋诗文805篇。虽然作者来源各异,但刺史所占分量较重。特别是名宦,本来就是诗坛名家,出镇名郡,创作热情更高,文学活动更密集,号召力也更大。以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所列为例,唐苏州刺史中,政事、文学知名的就有韦夏卿、齐抗、崔衍、韦应物、范传正、白居易、刘禹锡、杨汉公。杭州的名宦有魏玄同、宋璟、刘幽求、韦凑、崔希逸、刘晏、元载、崔涣、房孺复、于邵、韩皋、白居易、裴弘泰、姚合、李宗闵、李远。越州名宦有李大亮、胡元礼、姚崇、吕延之、杜鸿渐、杨於陵、阎济美、薛苹、孟简、元稹、李绅、杨汉公、沈询、郑处诲。唐苏、杭、越三州诗文,有很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这些作家作品的存在,清晰地呈现出名宦诗文能给名郡在文学上添彩的事实。
以上是从人的角度说的,从楼阁、碑记的角度来看,亦不乏实例。鄂州南楼,唐宋间叠经修建,名气极大,名士题诗极多,其中刺史诗也有不少,能给当地增重。碑记方面,《舆地碑记目》卷二有《鄂州南楼磨崖记》。诗文方面,有范成大、陆游的游记,黄庭坚的《鄂州南楼书事四首》及登临诗一首。陆游《入蜀记》云:“南楼在仪门之南石城上,一曰黄鹤山,制度闳伟,登望尤胜。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山谷所谓‘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是也。下阚南湖,荷叶弥望,中为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但以卖酒不可住。”[4]第1册,卷五,612从中不难想见风景之嘉胜。宋以下地志,诗文、景物、古迹、四六、碑记诸门,罗列的都是历代名贤诗文,而其历史渊源,则是唐宋刺史的创建楼阁和诗文题咏。这种名家名作的罗列,彰显了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以上名郡都有名家、名篇匹配,结合较好。但诗篇终究不及州郡的名气大。对于这些顶级名郡而言,决定其自身价值的是州郡多方面的优势,文学仅是其中一项,虽也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例如杭州,《明一统志》卷三八所列门目,有建置、形胜、风俗、山川、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释等十八个,每个门目都是一种优势资源,都能对当地有所贡献。优势因素一多,就掩盖了文学的光彩,文学在这里也就不具有独特价值和突出地位。可见对于顶级名郡来说,文学的吸引力并不大,文学之外的山川、园林、楼阁、寺庙、学校更吸引人,湖山之胜、古迹之多才是这里出名的关键,郡守及其文学对当地的贡献只能是增重、增价,而不是决定性的提高地位。
三、刺史与普通州郡:造就名家,兴建楼阁,带动创作
相对全国来说,名郡毕竟只是少数,占多数还是那些名气不大不小,地位不高不低的普通州郡。这类州郡,由于政治经济上分量不够,刺史除了少数为名人外,其馀多非名家,而是才能、名望一般的官员。翻阅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要是再继续去翻阅史籍、地志,得到的证据会更多。这类州郡刺史虽有一部分不以文学见长,但并不妨碍其在文学上起作用,比如主修楼阁,吸引文人,带动创作,这些行为,都可以让本地更知名。这是一般州郡刺史促进地方文学的独特点之一。
另一不同在于,名郡刺史及其作品只能增大州郡影响,不能决定地位升降。但普通州郡刺史的到来及其在任创作,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决定性的,是该地能否知名的关键因素。唐连、夔、和州出名,就是因为刘禹锡的到来及其出色的创作。黄、睦、湖、随四州之所以出名,也与杜牧、刘长卿的到来大有关系。
以上是从地对人的关系角度看问题。立场转过来,再从人对地的关系言,也是如此。相较于著名州郡,一般州郡及无名州郡更能造就文学名家,使其不朽。一则因为一般州郡数量更多,文人在此出名的可能性更大,唐代三分之二州郡属于此类。二则从地方文学角度而言,名气不大不小的一般州郡也关注、书写不够,更有创造空间。因而文人一旦出京刺郡,就等于在文学上找到了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刘禹锡之所以能够成为唐诗名家,就与他二十三年的谪放大有关系,其中连、夔、和州刺史这一段尤为关键。刘禹锡以怀古咏史诗及竹枝词著名,这两类题材主要就创作于连州到和州期间。同样的例子有杜牧。促使他成为名家的,不是他在两京任郎官、御史、中书舍人的经历,而是他的江西、宣歙、淮南的幕僚生涯,及黄、睦、湖州刺史经历。特别是黄州刺史任上的创作,使得这里成为文学名郡,可见灵秀山川也是文学家成名的关键之一。而山川风物作为文学题材,也特别需要有才力的人去表现。“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1]卷二二六杜甫《后游》,P2442山川的奇伟瑰丽,特别有待于优秀作家的书写,只有经过了名家题咏,才会变成有灵气,有活性的文化产品。江山风物,园亭山林,幽鸟晴花,游客皆可得而见之,而无所私,唯独唐代诗人得见,能够写出气象不凡的篇章,天真挺拔之句,直可与造化争衡。这一现象,深刻表明了作家对于地域的依赖性,这是问题的另一面。
同样的例子又有元结、阳城及道州。道州本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州。使它出名的,是唐人元结、阳城两位刺史及其诗文。元结在代宗朝,两次出任道州刺史,写下一批诗文,播于人口。其中《大唐中兴颂》一文,天下知名,是元结文章的代表作,早在代宗朝就刻石祁阳浯溪。加上文章还涉及玄、肃父子恩怨和唐室中兴等大问题,名气就更大了。早在南宋初,刻石的摩崖碑上,就“唐以来名士题名无间隙”[5]《骖鸾录》,57。元结是道州刺史,尽管碑刻在祁阳,文学成就却归道州。元结在道州,又有新乐府《舂陵行》《贼退后示官吏作》,均被杜甫赞誉为有“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的佳作。因为有杜甫的宣扬,极为有名。从地域言,也是最早的中唐前期湖南政事、民生的写实讽谕诗,值得珍视。此外,元结两次道州任内留下的诸多衡州永州道州景物杂记,也是唐代山水文中较有特色的,成为唐湖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文学家对当地文学及知名度贡献较大,当时之人,即习惯性地将刺史姓氏和所刺州郡结合起来,形成对他的简称、别称,多数后来还成为文集名称。常见的有岑嘉州、刘随州、元道州、阳道州、戴容州、韦江州、韦苏州、独孤常州、令狐华州、陆歙州(陆亻参)、韦简州(韦勋)、吕衡州、柳柳州、薛许州(薛能)、林邵州(林蕴)等,大大小小二十多个,都集中于天宝以后到晚唐的普通州郡,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深刻表明了刺史对州郡的依赖性,以及州郡对刺史文学的帮助之大,表明了刺史与州郡之间“人地两相须”“人地两相待”的规律性,说明并不仅仅是地方特别需要刺史来扬名,刺史同样也有待于地域。对于唐人来说,地域才是让他成名和立足的关键,京城的仕宦并不足以使他成名成家。特别是那些声闻不彰的诗人,刺史的任职经历更是他成名的关键,是他以文学或政事知名的起点,具有重要意义。以州名来称举文学家,说明该州刺史的任官经历是他在文学上知名的因素之一,这种做法,就跟以郎官、御史、尚书、侍郎、常侍等京官来称举文人一样,都是一种文学上的美誉和标举。虽然名郡也有此类例子,例如韦苏州之类,但并不普遍,数量过少,并不构成一种创作中的人地关系,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尽管无名州郡这类现象也有,但一部分简称指郡佐,不是指刺史,越出了本文的论题范围,所以仍不妨碍这一结论的成立。
以上说的是著名文学家和著名诗文结合的情况——名家以其出色创作贡献于当地,给本来一般的州郡带来文誉,造成影响,也让自己成为名家,地与人两相依赖,互相促进,这是理想状态。但若有名臣刺郡,即使他不以文学名世,只要本人事迹突出,对一般州郡的帮助也大。例如阳城与道州,就是如此。阳城在唐代以极谏闻名,贞元十四年上疏论裴延龄奸佞,陆贽无罪,触怒德宗,出贬道州。后竟卒于道州,时号阳道州、阳谏议。此事大大提高了道州的知名度。在唐代,影响甚至比韩愈贬潮州还要大。卒后,柳宗元为撰《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事迹载入《唐国史·卓行传》,两《唐书》亦为之立传。唐商於驿路有阳城驿。元稹元和中南迁过此,以为驿站名与阳道州同,当避其讳,遂改为避贤邮,并作《阳城驿》诗纪其事,以五言长诗数十韵,将阳城平生的风义气节表彰出来。白居易在长安,闻知此事,亦作《和阳城驿》以和之。晚唐杜牧过此,为赋《商山富水驿》诗以记。宋初王禹偁过此,又作《不见阳城驿》以继之。阳城的事迹,借助诸位名士及其诗文,到处传扬,道州一地也因此天下知名。类似这种州郡名声的传播、影响的扩大,是通过名臣-名篇的聚合效应产生的,这也是刺史和州郡结合的一种状态。所举诗文虽不作于道州,内容也不专写道州,但所咏则为道州刺史,所以对道州的影响扩大仍大有好处。
中国疆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也不一样,因而论刺史和普通州郡的文学关联,还需要考虑到区域及时代因素。至德以后天下大乱,北方荒残,“避地衣冠尽向南”[1]卷二四八郎士元《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2787,文人南向,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唐文人和和南方州郡的关系日益密切,变成文学上的大问题。特别是唐文人和江南列郡的关系,甚至构成中晚唐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自孟浩然、王昌龄以下,文学家活动的主要区域就在南方,作品的产出地也多在南方,而此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北方却日益荒残没落。因而对于多数北方州郡而言,并不存在“地因文始重”的问题。“地因文始重”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秦岭-淮河以南州郡。例如淮南道宣、池、黄州,江南西道江、饶二州,这方面的表现就相当突出。这五州,初盛唐以前本土文学素无名家,外来的名家也没有几个。是刺史制度、迁谪制度、使府制度让大批外地文人进入当地,改变这里长期低落的局面,文学开始有分量。
一个州郡想要在文学上出名,有时候,单靠刺史还不行,还需借助名楼、名作的力量。但三者齐备的并不多,常见状态是刺史无名但楼阁有名,因楼兴文,以文知名。名楼作为当地人文景观,郁然孤起于平地,吸引文人。本地人既经常聚集,把它当成文学活动的中心;外地人到来,首先想到的也会是它。登临纵目,感慨古今,必然会产生一批名作。
楼阁之中,有一部分是当地的郡楼,多为刺史主修,在此理政、待客,创作活动也发生于此,因而郡楼诗文也是考察对象。郡楼诗文的重要作者是刺史。白居易在杭、苏二州,就有《郡楼夜宴留客》《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羊士谔在资州,也有《郡楼晴望》《九月十日郡楼独酌》。韦应物在滁、江二州,有《郡楼春燕》《登郡楼寄京师诸季淮南子弟》,这些作品也是能给当地文学增重的。
很多普通州郡文名的获得,都是通过楼阁。唐岳州、滁州就是典型。此二州在张说、韦应物、李德裕到来以前,并不为人知。即使有一二名臣出任刺史,也是自迁谪量移而来,到任以后不久即调离,没有对该州文学做出多大贡献。比如滁州,最著名的刺史是李德裕,但他在任三月即回京。据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李德裕开成元年三月,自袁州长史改任滁州刺史。四月到任,七月即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真正在任只有三个月[6]251-254。很显然,滁州刺史对他而言,只是一个过渡。真正使它全国知名的,是韦应物《滁州西涧》诗,及李德裕主修的怀嵩楼。后人来此,往往登临赋咏,从而对当地文学有所贡献。岳州的情况也类似。该州在开元初,虽有张说这样的名臣到任,《新唐书》也说他“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7]卷一二五《张说传》,4410,但实际上他的岳州诗很一般。真正使岳州天下知名的,是李白、孟浩然、杜甫的登临诗,而产生这些诗文的关键,又是张说之前多位岳州刺史对岳阳楼的兴建和维修,楼阁修成以后,就成了当地著名景观,吸引游人,引发创作,形成一地文学景观,可见刺史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唐代南北各地州郡,普遍流行郡守到任,修造楼阁的做法。以郡守和楼阁为中心,就能形成文学活动中心,建立地方文采风流。多个楼阁都是这一文化的产物。例如宣州叠嶂楼,创建者为刺史独孤霖,此后随即产生登临诗文。池州九峰楼、萧相楼,名刺史为萧复,名家为杜牧等,杜牧有《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登九峰楼》《池州重起萧相楼记》。郢州白雪楼,创建者为某位无名刺史,名作为白居易《登郢州白雪楼》。刺史-楼阁-诗文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以上均为名气、地位都很一般的州郡。这样的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优势都不突出,反倒是楼阁和诗文的名气大。表明对于这类州郡而言,著名楼阁和重要作品对当地文学地位的提升起着关键作用。当古迹和山川不能使它知名的时候,就得靠名人、名楼和名作。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类州郡,刺史、楼阁、诗文不能很好地匹配,往往此强彼弱。一般面相就是楼阁有名而州郡无名,或是郡守、楼阁有名而诗文一般。例如岳阳楼,在唐代,文名就不如滕王阁盛大,岳州刺史张说也不为人知。韩愈就说:“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8]卷八一○《新修滕王阁记》,4282他的话很能代表唐人的看法。又如叠嶂楼、九峰楼、消暑楼、齐云楼,虽然在唐宋间号称“名与天壤齐”[9]卷四,滕宗谅《上范希文诗序》,80,但时至今日,早已堙灭,作品也无人提及,属于古代有名而现代无名的例子。此外如八咏楼、越王楼、白雪楼,楼阁和州郡也都表现一般,文学上也只是一度有声有色。
刺史在其中所起作用,令人玩味。刺史不仅作为文人创作诗文,还作为地方首长举行宴会,发动唱和,从不同层面参与当地文学建设。其中修造楼阁一事,尤其值得单独提出。滕王阁如果没有刺史李元婴的主修,如果没有那次“都督阎公”(阎伯玙)的召集宴会,就不会有王勃名满天下的《滕王阁序》及诗。岳阳楼如果没有唐初某位刺史的修建,也就没有孟浩然、杜甫、李白、刘长卿、韩愈、吕温、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诗文,就不会有滕宗谅编的载于《宋史·艺文志八》的《岳阳楼诗》二卷,可见郡守的创建之功不可忽。
这种创建之功,有时甚至能够对一地文学发展起到奠基作用。中晚唐巴蜀就有数个州郡都是刺史筑楼,因楼兴文,烜赫一时,刺史-楼阁-文学之间,形成密切关联,构成当地文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刺史张某之于巴州击瓯楼,越王李贞之于绵州越王楼,就是如此。此二州在唐人赋诗以前,不为人知,是唐人修楼赋咏提高了知名度,当地文学亦起于此。相关记载代代流传,成为当地文学的宝贵资源,更是《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四川通志》等总集、目录、地志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击瓯楼在巴州东,晚唐张曙有《击瓯楼赋》,另一晚唐文士冯介诗,有“座上击瓯清似玉”之句,因此得名。楼下有唐中和四年张袆《击瓯楼记》《击瓯楼赋》,州内紫极宫天王堂,有唐大中元年军事判官萧珦记,皆当地文学遗产。据《方舆胜览》卷五四绵州,越王楼在城西北,显庆中,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贞为绵州刺史日建。楼成以后,中唐之初就产生了文学业绩。杜甫避难蜀中,代宗初至此,有诗二首,一曰《越王楼歌》,二曰《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均宝应元年至绵州时作。此后,代宗朝绵州刺史乔琳,有《绵州越王楼即事》。大历中王铤为绵州刺史,有《登越王楼见乔公诗偶题》。另一绵州刺史樊宗师,有《蜀绵州越王楼诗并序》。到大中年间,已形成一个以越王楼登临唱和诗为中心的创作高潮,发起人正是大历刺史乔琳。《唐诗纪事》卷五三将这些诗汇于一卷,为我们考察刺史、楼阁、诗歌提供了绝佳材料。内收乔琳、王铤、于兴宗、李朋、杨牢、李商隐、刘得仁等二十四人诗。其中前三人为绵州刺史,后面二十一位为台省官员、使府僚佐、布衣文士。乔琳《绵州越王楼即事》云:“三蜀澄清郡政闲,登楼携酌日跻攀。顿觉胸怀无俗事,回看掌握是人寰。滩声曲折涪州水,云影低衔富乐山。行雁南飞似乡信,忽然西笑向秦关。”小传记乔琳事迹云:“琳为郭子仪朔方掌书记,与联舍毕曜相掉讦,贬巴州司户参军。历果、绵、遂、怀四州刺史。”[10]卷五三,802可见乔琳为绵州刺史,夏日登临,赋诗创作是一个关键,越王贞创建楼阁则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二者结合,即可诗歌唱和,登临题咏。表明对于一般州郡的文学事业来说,刺史起着引领作用,刺史与楼阁、诗文的关系不是平行并列、同等重要的关系,而是主从关系、领属关系。
四、刺史与无名州郡:以名臣到远地,带动地方文学发展
名郡和普通州郡之外,就是无名州郡了。这类州郡,没有很多的名楼、名家、名作,却有众多的大臣贬放,以此闻名,这是其特色所在。其刺史和文学的关联,也正建立在以名臣到远地为刺史这个基点上。尽管贬谪至此的刺史多为政治名人,不以文学见长,但毕竟生于唐代,照样赋诗作文,留下题咏、碑刻、四六,甚至建筑、石刻、古迹,提携当地文学人才,厚殖当地文化资源。这类人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集中出现于多个州郡,原来无名的也变得有名。其对当地文学的贡献,或是通过有特色的地域书写,以迁谪文学、流寓文学的形式直接体现出来;或者通过间接途径,以其他方式体现出来。其诗文产生于当时,影响则在后代。唐代刺史在这里的创作,作为一个历史起点或中介环节,引导后来的创作,这是其另一意义。
唐朝遵循古来惯例,常将文官贬降到偏远州郡为官,这一政策贯穿全唐。显庆二年,贬韩瑗、来济、褚遂良为远州刺史。韩瑗振州,来济台州,褚遂良爱州,柳奭象州。永贞元年,柳宗元与韩泰、韩晔、陈谦、刘禹锡以附王叔文,贬远州司马。元和十年,五人又皆出为远州刺史。柳宗元柳州,韩泰漳州,韩晔汀州,陈谦封州,刘禹锡连州。龙纪二年,贬孔纬、张濬为远州刺史,孔纬授均州刺史,张濬授连州刺史。开元中,张九龄为相,建言放臣不宜处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因而盛唐以来,出现了更多的远州刺史。其在文学上的直接结果,是逐臣文学的快速发展,各种体裁、题材的逐臣诗文、碑记大量涌现。经过盛中晚唐持续二百年的积累,唐代逐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与被贬逐到这里的郡佐,共同组成唐代迁谪文学的主力军,具有经典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其在刺史任上创作,以写当地,赋愁心为中心。符(苻)载《愁赋》云:“愁之为物也,亲贱贫,傲富贵……愁兮愁,春与秋兮登临,放臣寓目,游子开襟。枫江千里,青壁万寻。微波荡漾,灌木萧森。香杂花而覆水,见槁叶之乱林。起宋玉之沉思,伤屈平之远心。”[8]卷九一,415所说虽不为迁谪而发,却把唐代以远州刺史、郡佐为代表的放臣逐客文学的哀怨基调及感伤特征做了精练概括,这两类作者诗文确实兴微托远,属思千里,感人至深。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11]卷四,138。
远州知名度最低,其出名完全是因外力的推动。比如汀州,是福建偏远州县。《方舆胜览》卷一三《汀州·事要》云:“在闽山之穷处……复嶂重峦,亘数百里”[9]卷一三,229,其出名,是德宗朝以来张滂、苏弁、韩晔、蒋防、张又新的陆续贬放。封州是岭南偏僻州县,使它出名的,是刘幽求、陈谏、李宗闵、李甘、张裼的贬官。连州是湖南偏远州县,韩愈《送区册序》称为“天下之穷处”,刘禹锡诗《赴连州途经洛阳诸公置酒相送张员外贾以诗见赠率尔酬之》称为“三湘最远州”。虽然条件最差,但名家和题咏使它在文学上知名,韩愈、刘禹锡诗文即连州出名的关键,时至今日影响仍在。
以上事例,特点是以名臣到远地,带动地方文化和文学发展。唐剑南、黔中、江西、湖南、福建都存在这种情况,而以岭南道最突出。据《舆地纪胜》可知很多这样的事例。潮州是因曹王皋、常衮、韩愈、李德裕、郑馀庆而知名的;桂州是因褚遂良、张九龄、齐映、常衮、马总、李渤而知名的;柳州是因柳宗元和刘蕡而知名的;贺州是因李回、杨凭、韦保衡而知名的。而且这个知名,主要是指先以文学出名,然后再扩大到其他方面。大凡一个边远州郡想要知名,主要得靠贬官流放;另外才是通过正常途径派遣刺史、设置方镇,其出名与该州名宦有很大的关系。类似情况,有端州之于该州名宦李绅、杨收、崔嘏,康州之于该州名宦程知节、李涉,容州之于该州名宦韦丹、杜佑、戴叔伦。
由于刺史、迁谪制度的作用,不少名家出任刺史,文学家和州郡的关系变成一种稳定的政治关系,一种常态化的促进地域文学发展的手段。唐代最有名的范例,有柳宗元和柳州,韩愈和潮州,常衮和福州,吕温、令狐楚和衡州,李绅和端州,李德裕和潮州。每位刺史都对当地文学做出了贡献。这几位到任以前,这些州郡都毫无名气。自从这几位名人到来以后,就名声鹊起,情况反过来。通过迁谪制度,来自北方的多位名家,连同他们的凌云才笔,都度越万里关山,来到偏远的湖南岭南,树立起文学的丰碑。他们在当地留下的不朽文字,连同他们的生平事迹、故事传闻,感染和教育无数后人,成为天壤间的永恒存在。
而以人和文两个因素比照,人的因素显然居于首位。以韩柳而论,其对潮、柳二州的贡献就是多方面的,不仅在文学上,还在文化上。即使以文学而论,作品也仅是其中显著一项,此外还有人才培养、风气带动等。常衮、韩愈、李德裕、郑馀庆曾贬潮州,作有多篇重要诗文。褚遂良、张九龄、齐映、马总、李渤曾贬桂州,也都有可称道的诗文。但以文衡人,文显然不及人的分量重,人对当地带来了更多的东西。
无名州郡文化居于弱势,对外地缺乏吸引力。这样的地方想要发展,就只能借助外力。对唐代而言,就是借助制度强力来引入人才。刺史和无名州郡的文学关联,主要靠迁谪制度实现。迁谪制度将罪臣放逐到远地,并加以职务、任期和活动范围的限制。以唐代来看,惯例是以名臣、重臣贬远地,无名官员因为分量不够,只能发配到次要州郡。唐崖州、潮州、端州、新州,就是著名宰相和文学名家的迁谪之地。行贬之际,先要看地图,定贬所。一般做法是根据《十道图》《十道志》等唐代各个年份流行的地理总志,再结合罪状轻重去确定贬所,一般规律是罪越重的地方越远。罪重的又多是名望、地位高的宰相、尚书、侍郎,连郎中以下的中层官员都少见。身为远地、远官而能为善地,用名臣的,大概也只有广、韶、桂州了。这几个地方倒是风土不恶,刺史多为正常任命。但相对于大多数无名州郡而言,这只是少数,不具代表性。
排除掉这个情况,我们的眼光就又聚焦到 名臣-远地的文学关联这个主题上来。在唐代,名臣-远地-优秀诗文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固、恒久的联系。从本质上说,唐代推行的迁谪量移制度,乃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生产机制,带有强制性,潜存于政治制度的夹缝,对全体官员都起作用,因而会屡屡看到荒远州郡每多名家,产生名作的现象。由于官场险恶,斗争激烈,那种长期在京任官而不出问题的人已非常少见,半数以上的唐代文学名家都有过流贬经历。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偏僻之地名臣特多的现象。这种强制措施,固化了创作中的人地关系,将一个有声望、有能力的文学家限定在偏远无名之地,让他们去在文学上经营这片弃地。这样一来,位置较差,本来无名的州郡,也可以因为名家的到来而提高知名度。虽非真正的名郡,文学上却十分知名。
五、结语
唐代刺史与州郡的关系,反映了创作中的人地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州郡对刺史有较大的依赖,因为这类人物的到来,能给当地增重添彩。另一方面,刺史也有赖于州郡这个场地来完成文学伟业,建立文学声名。一定程度上,是州郡而不是京城成就了众多名家。但以人与地相较,地对人的依赖性更强,而其中也有等差。大体而言,越是著名州郡,对名家名作的依赖就越小;反之亦然。基于此,刺史与名郡的文学关联,只能是给名郡增添光彩。而一般州郡刺史的作用则在于兴修楼阁,创作诗文,让当地出名。无名州郡,刺史的作用在于以名臣而到远地,带动地方文学发展。以上三个类型,概括出古代刺史和州郡文学关联的三种情形,有助于认识刺史与州郡在文学上的相互关系及其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