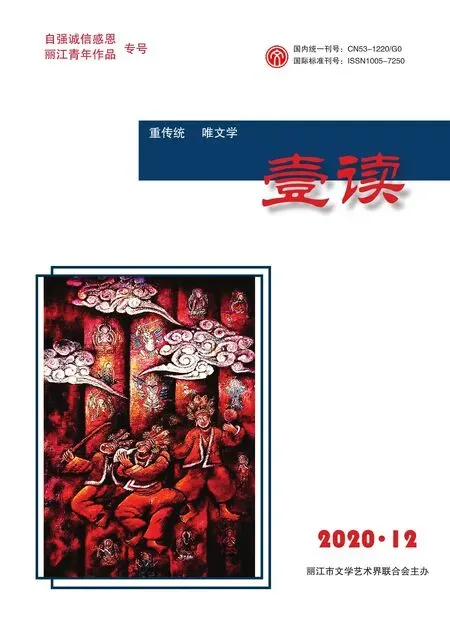箱子
◆包成秀
又是周末,天气晴好,细碎的阳光透过树叶,照进窗户大开的屋内,落在窗前的软塌上,斑驳的光点晕成一片。院里桂花的香气隐隐约约地从窗户飘进来,让人心旷神怡。在为家人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我随着音乐声开始整理家里杂乱的东西,收拾到公婆住的房间时,突然发现一个陈旧的木头箱子,上面红色的漆已经脱落,斑驳的表面呈现出浓浓的年代感,锁扣和锁头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样子,点点红锈好像在跟人诉说它曾经的辉煌。
这样的红漆箱子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家中应该都有,那是它独领风骚的年代。记得小时候我的家里也有两口这样的红漆箱子,是妈妈的嫁妆。妈妈嫁给爸爸时,外公外婆请木工给她做了一个漆着绿色漆的柜子,和两口红漆箱子。在我们小的时候,箱子上面的漆还比较完整,那时整个社会的生产条件都比较落后,物资匮乏,爸妈作为地道的农民,每天的工钱只有一块到两块钱,有时甚至难以满足温饱需求,能匀出来给我们兄妹俩买零嘴的钱基本没有。每次买了红糖,妈妈就会把它锁在其中一口红漆箱子里,隔两三天拿出来给我和哥哥每人切一块。我一般吃得很慢,想要让那甜美的味道在嘴里多留一会儿,让我能在接下来吃不到零嘴的日子里感受它留下的余味。而哥哥却狼吞虎咽,很快把他的那份吃完了,之后就会来哄我手里面的……现在时代变好了,生活也好了,有太多各种各样美味的糖果摆在面前任由我们吃,但却再也找不到那时候那样的味道了!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时候吧,那年我还没出生,哥哥也只有三个月大,爸妈被爷爷分出了家门。爷爷奶奶生了八个孩子,大家庭里本来就一贫如洗,什么东西都分成八份的话基本也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爸妈分家出去爷爷奶奶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他们,他们就只能带着外公外婆给的两口红漆箱子和绿漆柜子出了那个大家庭的门。他俩在外公家不远处的一块地里划了地基,建了一所土木结构的正房,里面没有条件做更多的装饰,只孤零零的摆着两张木床,墙上贴着不知是哪里找来的泛黄的报纸,两张床的外面用白色的塑料薄膜遮风,也没有大门,家里其他的物件也就那两口红漆箱子和绿漆柜子,当然,院子里还有几根新砍来准备建造圈房的木料。这些微薄的财产就由外公家借来的一只大黄狗来看守。
后来我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我们家那时住的那个屋子,凹凸不平的墙面,泛黄的报纸,素色大花的床褥,院子里摆放着一口石头打的水缸,水缸表面有绿色的青苔,偶尔缸底还会趴着一两只蚂蝗……我还记得那晚,外婆举着火把大声呼喊“来帮忙抓贼啊”的声音,幼小的我当时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外公,舅舅们和爸爸都不在家,而外婆的呼喊声惊慌又凄厉,院子里大黄狗亢奋地跳跃、扑腾、狂吠,妈妈和小姨脸上的神色惶恐不安,但又有着想要保护自己仅有财产的决绝。
多年以后我跟妈妈打听记忆里的这件事,妈妈总是语焉不详,她总是跟我说,对悲伤的痛苦的过往不要心存埋怨,只有自己不去记那些苦难,苦难才会走远;要多看阳光、多看远方、多看未来。我又向当时的亲历者小姨打听这件事情,小姨跟我说,那晚的小偷是趁着我们家里没有男人在家,来偷院子里那几根木料的。我很惊讶,老家四面环山,那个时候也没有禁止乱砍乱伐这一规定,整个农村热气腾腾地忙着大兴土木,建造房子,出门就能砍到的木料,为什么还会来偷?小姨回答我说,即使背靠着山,但能够用来建房的木料,要去到山里仔细挑选,选好以后才能剥皮拖回家,这些都是需要人力物力的。任何时候都会有想要不劳而获的人,即使是在我们那个民风相对淳朴的老家。那件事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我外婆这位勇敢的女人,跟全天下的母亲一样护犊子。那时候村子里还没通电,一到晚上,到处一片漆黑。在那个长风呼啸的夜晚,她半夜起来上厕所时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她的大女儿(也就是我妈)家的方向,就瞟到了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地在那里摸索,所以就爆发出了我记忆里的那声惊天大吼。吓走了小偷,也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
后来外出务工的爸爸回家了,他出去务工时看到下面坝区里土地多又平坦,医院、学校都在那里,看病、读书都很方便。坝区人多,还可以做点小买卖什么的,就动了搬到坝子里生活的念头。政府当时也鼓励在山里居住的人搬到坝子里,还会给一部分宅基地作为政策扶持。爸爸回到家就跟家里人商量,想要搬到坝子里去,可外公和爷爷都不同意,认为去不熟悉的地方生活太过冒险。外公还提起一件事,当时老家有一户人家也在前两年搬到了坝子里,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生存下去,两个人双双跳进了水库留下他们的一双孩子成为了孤儿。至于另一个原因,那自然是因为家里太穷了,除了那两口箱子和柜子什么都没有,而箱子和柜子除了放东西好像在搬家建房子这样的大事里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外公和爷爷,两个人都不赞同爸爸的观点,觉得他是活腻歪了,想要去步跳了水库那家人的后尘。妈妈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就像夜晚归家的人想要看到的那盏灯,虽然不亮,却很温暖。她身材高大,眼睛清亮,让人看到就觉得有生生不息的希望。她想着,反正日子已经艰苦成这样,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了,她也迫切地想要改变,想要让她的下一代不要再这样辛苦。所以爸爸搬家的这个想法,她想了想也就接受了,并且愿意与他一起奋斗。两个年轻人,借了外公家养的一匹马,开始了人背马驮,一天两头跑,谋划建房。
那时的他们其实也就二十三四岁。现在二十三四岁的我们总还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很多还在求学,都不想也担不起太多责任。但在那个年代,我年轻的父母肩上担负的已经是一家四口的未来。每天早上从老家出发,要走一个小时左右的崎岖山路,才能到达新建房子的坝子里,然后在那什么都没有的贫瘠又荒凉的土地上,要一砖一瓦新建土木。当时政府给的宅基地大概有六分左右,恰好爸爸有一个朋友会建土墙房,爸爸就把他的这位朋友请来做建房的大师傅,妈妈和他当小工。爸爸妈妈去附近的石场拉来石头打成地基,之后就在划给我们家的那块宅基地里,用水将泥土浸透湿润后再挖出来,用撮箕一撮撮地抬起来倒在篮子里,背到舂墙师傅的那里,倒在他们搭好的模具上,慢慢的舂成型,一点一滴的汗水汇入,变成了一个能遮挡风雨的简陋的家。
后面我还了解到当时生活在坝子里的原住民在那时候大多有排外思想,不想爸妈他们这些外来户能顺利在他们的地盘上生存,经常会把水源阻断,让他们没有水喝,也没有水用来浸泥建房。但爸妈他们终究克服了这些困难,在坝子里扎了根,把哥哥和我也带了下来。他们把哥哥送进了学校去上学,当时还有从其它山头搬家下来坝区建房的人家,他们家跟我年龄相近的孩子们也成了我的伙伴,各家建房的区域成了我们挥洒汗水的游乐场所,我们尽情地在那里玩泥巴、躲猫猫……大多数时候爸妈会把我留在老家,让外婆或者小姨帮忙带着我。听妈妈说,当时的我就像个黏人精,每天在他们要出门前,我都抱着妈妈的大腿哭闹着要跟着去,我太小,走不了几步就走不动了,爸爸只好把我放在马背上,我在马背上坐几分钟又开始耍赖说腿磨得疼,妈妈只好抱着我走。那时妈妈留着很长的头发,编成麻花辫,干活的时候辫子在后面一甩一甩的,非常精神。她抱着我的同时后面还要背着一篮很重的东西。现在我再来听我那时候干的事,总是觉得羞愧难当。
在爸妈每天忙着大兴土木,建造房子的那个时候,家里就更加没有了经济来源,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苦了。山里有一种红色的野草莓,妈妈去山里砍柴或者挖药材的时候会把它扎成一小捆,然后拿回家放到袋子里,跟哥哥和我说是买回来的。每天拿一些给哥哥我俩吃,余下的就放到箱子里收起来。放这些零嘴的红漆箱子成了哥哥我俩心目中的藏宝箱,每当看到妈妈打开锁,就觉得有一股香甜的气味扑面而来。不开箱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紧盯着箱子上那把小锁,希望我们的视线能把这锁射开,我们想要的零嘴能从里面飞出来。
直到后来慢慢长大,街上家具店里开始有了更加新奇精巧的家具。衣柜、书柜、鞋柜、梳妆台等等,妈妈的红漆嫁妆箱子也开始从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慢慢地被移到了阁楼里,以前总被擦得崭新干净的箱子慢慢蒙上了灰尘,越来越陈旧……
二十多年后,爸妈和哥哥嫂子又在另一块地里建了时下流行的钢筋混泥土的楼房。承载了我们童年、少年回忆的老房子也卖给了刚从山上搬下来的人家。新楼房明亮干净,摆放的家具都是这几年流行的新款式,而我的妈妈,身材略微佝偻,有着一张农村妇女都神似的沧桑脸庞,皱纹如白桦树的斑驳树皮,记录着春夏秋冬的寒暖。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过妈妈的红漆箱子了,外公外婆也在前几年相继离世,箱子是他们留给妈妈的唯一念想了,她应该把它们收起来了吧!
也是无奈,这些年辗转在每一个城市高楼大厦间的格子里穿行,早已忘记那些年守着妈妈的红漆箱子等零嘴儿的心境。今早又突然看到这样的箱子,此情此景,一别数载,那时驰骋在风雨里固若金汤的意志,就这样在心间铺天盖地地重现。我发现尽管天大地大,时移世迁,原来有些往事竟从未随风而去,呆板老旧的家具们在角落里伏首呼吸,有一种被时代遗忘的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