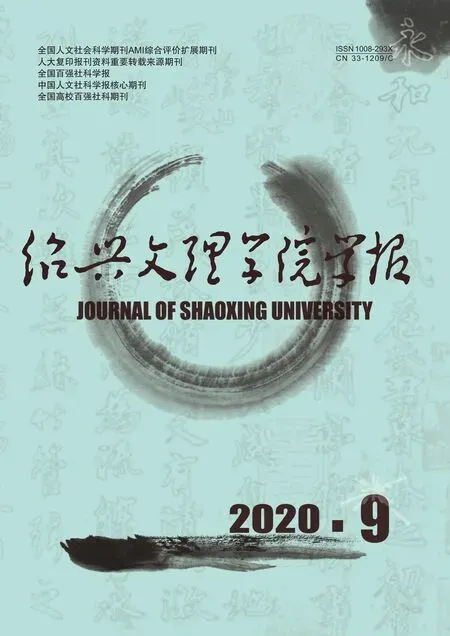梁社乾与《阿Q正传》的首次英译
季淑凤
(1.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2.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引言
《阿Q正传》是鲁迅于192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以其深邃的思想、娴熟的技巧、独特的风格赢得世人的喜爱和赞赏,小说刚一问世就产生了巨大反响,在文坛上刮起了一股“阿Q旋风”。连鲁迅的“宿敌”对《阿Q正传》的深刻笔法、艺术成就也不得不折服,倍加推崇。评论家郑振铎曾预言“《阿Q正传》在中国近来文坛上的地位却是无比的;将来恐也将成为世界最熟知的中国现代的代表作了”[1]。小说中所反映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其英译历经百年而不衰的魅力所在。《阿Q正传》自面世以来,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其中,敬隐渔(1926年)的法译本《阿Q正传》是外文世界的首译本,而英语世界的首译本则是同年出版的美籍华人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的英译本,此后便拉开了英译《阿Q正传》的序幕,比较有名的译本如表1所示。
后面四个译本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论著颇丰,而对英语世界的第一个极为重要的译本——梁译本讨论较少。鲁迅在1926年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评价“《阿Q正传》的英译本已经出版了,译得似乎并不坏,但也有几个小错误”[2]。接着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又说:“英文似乎译的很恳切。”[3]西谛(郑振铎) 在1926年写的论《呐喊》的文章中对梁的英译本评论道“他(梁社乾)的译本颇不坏;只可惜《阿Q正传》是太难译了, 所以有许多特殊的口语及最

表1 主要《阿Q正传》英译本信息表
好的几节,俱未能同样美好的在英文中传达出”[1]。1927年,署名“甘人”的赞同鲁迅评价梁译本译得很恳切的观点,进一步评论道:“唯其因为太恳切,反见得译文有些僵硬与不自然了。这原是直译的通病,只能怪译者不该为便利对读起见,就墨守了直译法,拘住了自己的笔头,使文章有了逊色,因为对读并不是翻译的目的。”[4]1977年,戈宝权首次详细考察了梁社乾英译《阿Q正传》的过程及前人对此译本的评价,并简单介绍了《阿Q正传》的其他几种英译本[5]。此后学界对此译本的定位一直不高,基本上延续该时期定下的“直译”“僵硬”“不自然”“误译”等基调。近年来,汪宝荣(2015a)[6]、(2015b)[7]、Wang(2017、2018)[8-9]主要以梁社乾英译《阿Q正传》的个案研究,来验证其提出的“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的理论。然而正如作者自己意识到的那样,这种阐释难免有套理论之嫌疑。鉴于此,本文拟对该译本的作者生平、著作及英译策略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
二、梁社乾其人其著
梁社乾,英文名George Kin Leung,1897年出生于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祖籍广东新会,在美国接受教育,熟练掌握中英双语,大学时即热心戏剧和音乐。后因家庭变故,决心回国发展,谋求个人事业。梁社乾循着个人的兴趣爱好,致力于中国传统戏剧的英译与研究,一生勤于著作,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翻译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欧美本土的学术性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曾出版发行戏剧方面的英文单行本7本,国内外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38篇,另外,还有英文讲学和演说21次。除了撰写文章之外,还曾参与梅兰芳访美访苏剧目的选定与翻译,并曾担任梅兰芳的英文老师。众多归国华裔中,梁社乾能得到梅兰芳如此信任,一方面自然源于其通晓中西两种语言,又比一般的所谓的“中国通”更具有中国视野和戏曲视野,更多也是因为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欧美人士和海外学术界评论“梁社乾是传统中国戏剧艺术及其现代典范的权威。有多部专著,也是在中外期刊中论述戏剧的多产作者”[10]。也正因其能够在中西之间自由、灵活出入,真正具备中西对话的能力,在第一次访美演出这样重要的时刻,齐如山和梅兰芳才会如此倚重梁社乾。与梁社乾在戏曲界的权威名声相比,其在小说界的译者身份几乎被遮蔽了。20世纪20年代,梁社乾回国后,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译成英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销量不错,很快便再版,在此鼓舞下,1926年,又将鲁迅的《阿Q正传》进行英译,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被柳无忌赞誉为“英译中国现代小说第一人”[11],该书颇有影响,于1927年便出第二版,1929年出第三版,1933年在听取包括鲁迅等人的意见对书目进行修订后,又出第四版,在此版本基础上,于1936、1946年重印。正是凭借这两本书的英译,梁社乾在国内站稳了脚跟。2002年,离《阿Q正传》首次出版发行接近80年后,该译本由美国一直致力于出版成名作家作品的Wildside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可见,该译本即使在当代社会依然有着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对于梁社乾翻译《阿Q正传》的缘由,囿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通过细读梁社乾于1925年在上海撰写的“自序”与“附录”可窥见一斑。在前言中,梁社乾开头便写道“《阿Q正传》是用白话文写成,该种语言形式极具口语化风格……这种语言流畅自然,通俗易懂,与传统文言文相比更加简洁、文雅、优美,然而也更难学……虽然文言文有自己的优势,但是白话文更容易被大众学会,而且比文言文更能体现民主精神。”[12]v-vi作者在此表达了对白话文这种语言形式的喜爱,同时还表达了译者对该作品主题的理解——“口语化的白话文旨在帮助目不识丁的普通大众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而《阿Q正传》则代表几千年来被精英文学所忽视的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呼声……原作的语言风格独特、幽默,但是每个字都发出受压迫受剥削的百姓的呼喊以及作者本人对社会不公的批判”[12]v-vi。这种选材取向一方面由于梁社乾自幼出生于美国受教育于美国,所以难免受到西方国家的民主、科学思想熏陶。另一方面,当时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文化。顺应当时国内的文学思潮,自然也会选择翻译该类体现民主思想的作品。至于选择英译鲁迅作品的原因,译者在“附录”中写道“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现代作家”[12]101,显然与鲁迅的地位和影响不无相关。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蜚声世界文坛,被誉为“20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因此,正是鲁迅的盛誉及作品的主题、语言风格等促成了梁社乾对《阿Q正传》的首次译介。
三、梁社乾《阿Q正传》的翻译策略
(一)“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
梁社乾在“前言”中明确说明“只要中英双语之间的差异不是大到非要大动干戈不可,他总是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12]v。细读译本之后可以发现,除了与原著主题关系不密切的几处有所增删,译文“恳切”几乎与原著“亦步亦趋”。还原到译文发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语境中,这种翻译方法也无可厚非。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可能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译者的文化身份的选择。梁社乾作为美籍华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国发展,自然是怀着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深深的热爱。希望将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介绍给外国读者,因此翻译时会“忠实”于原文,尽量实现译作与原作的对等关系。第二,原作作者的威望与理念。鲁迅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有着“白话小说之父”的美誉,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生产场域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其作品也颇有影响力。再者,在进行英译之前,梁社乾首先征得了鲁迅的授权,翻译过程中也多次向鲁迅请教咨询,付梓后又把译稿寄给鲁迅审阅,这种外部压力也促使其“忠实”于原文,而这也与鲁迅当时提倡的“直译”“宁信不顺”的翻译理念相吻合。第三,目标读者的定位。梁译本在国内出版,目标读者主要为外国在华的华侨以及致力于学习英语的中国人,读者很容易将原作与译作进行对比,以此来检验译文是否忠实可靠。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初回国内发展,力图在国内站稳脚跟的梁社乾来说,这个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第四,赞助商的影响。1923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规定,从中学开始开设英语课,一时掀起了一股“英语学习热潮”[13],此时发展起来的负责出版发行梁译本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以编写、出版教科书为主要业务,而梁译本作为英语学习的辅助材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体方针政策及翻译规范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
总体而言,译者自身的文化身份、原作作者的声望、目标读者以及赞助商等综合因素促成了“直译”的翻译策略。梁社乾在翻译时,力求“密合原文”不仅无可厚非,反而显现出译者高超的汉语水平。而同年出版的法译本,就因难度太大,而将第一章删除不译。
具体而言,人名、地名及一些文化负载词等采取直译的策略,以尽量保留这类词汇的文化异质性。
1.音译
对于一些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词的专有名词,为了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忠实传达出源语文化内涵,对原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或文化负载词英译时一般直接音译,如,阿Q(Ah Q)、王胡(Wang-hu)、妲己(Ta-chi)、褒姒(Pao-szu)、董卓(Tung-cho)、貂蝉(Tiao-ch‘an)、邹七嫂(Tsou Ch‘i-sao)、赵司晨(Chao Sze-ch‘ên’s)等人名。地名也是直接音译,如未庄(Weichuang)、湖北(Hupeh)。
文化负载词,如阿弥陀佛(O-mi-t‘o-Fu)、麻酱(Mah-jong)、观音(Kuanyin)也采取音译的方式。
2.音译+注释
有些文化负载词因其自身所包含的深厚的文化背景,仅仅采用音译的翻译策略不能比较充分和完整地表达清楚其文化内涵,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添加注释,从而有利于译入语读者更深入了解中国的民族文化背景。如,秀才(Hsiu-ts‘ai)、翰林(Hanlin)、举人(Chü-jen)等。其中“秀才”一词,梁译本音译为“Hsiu-ts‘ai”+“A Hsiu-ts‘ai is a scholar who has qualified for the governmental examinations in his district”,“举人”音译为“Chü-jen”+“Chü-jen is the scholarly rank above hsiu-ts‘ai and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of a province”[12]99。
3.直译
《阿Q正传》包含了成语典故、谚语等蕴含独特的语言、文化特征的话语元素,成为翻译中不容忽视却又颇具挑战性的难点。对于这类词的英译,因目的语文化中没有对应词,梁译本主要采用直译的方式,尽量保留原作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下面将梁译本(以下简称梁译)和被认为《阿Q正传》英译比较成功的莱尔译本(以下简称莱译)做对比分析。
原文:惩一儆百
梁译:Punish one to subjugate a hundred.[12]84
莱译:Make an example of only one/And a hundred crimes will go undone.[14]168
“惩一儆百”出自《汉书·翁归传》:“其有所取也,以一儆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通过对比发现梁社乾和莱尔总体都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梁译本无论内容和形式都贴近原文,而莱尔的英译语言更加灵活,考虑英语读者的阅读需求,符合英美国家表达的习惯。直译策略降低了文化负载词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元素的损失,能够让译入语读者感受到地地道道的源语文化色彩。
原文:仇人相见分外眼明。
梁译:When enemies meet, their eyes glitter more brightly.[12]40
莱译:When met by chance, foe sports foe at one fell glance.[14]133
“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是一个汉语成语,意思是指当敌对的双方相逢时,彼此对对方都格外警觉和敏感。对于这一成语梁氏亦采用直译法,旨在将原文中原汁原味的文化内涵传达出来,同时也保留了原文的简洁与连贯。莱尔的译文采取了替代法,就是用目的语中与之相对应的词汇直接来替换源语中的词汇,从而更好地为读者所了解,从而达到语用功能对等的目的。
4.梁译本除了词汇上采取直译的策略外,在句法形式及结构上也遵循汉语表达的习惯,紧贴原文进行翻译。
原文:他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时常留心看,然而伊并不对他笑。
梁译:The women who without a doubt desired to lure on“loose”men,he always watched closely. But they had never so much as smiled at him.[12]31
莱译:He constantly keep an eye out for women who were“trying to seduce a man or two”, but none of them so much as smiled at him.[14]126
将原文与译文两相对照即可看出两个译本各有特色。梁译本紧贴原文的形式、结构、词序进行一一对译,几乎是逐词翻译,尽可能地展现白话文的表达习惯,保留原作形式上的艺术元素,体现了译者以源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倾向。与之对比鲜明的莱尔译本没有拘泥于原文语序及表达习惯等束缚,而是尽可能贴近读者的文化背景,采用符合英语国家读者习惯的表达,语言简练、流畅,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体现了译者以译入语国家读者为导向的立场。
原文:“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地说,一面赶快走。
梁译:“Why do you molest me?”cried the little nun, her face crushed crimson, as she hastily stepped along.[12]25
莱译:“What’s gotten into you? Get your filthy paws off me!”Her face flushing scarlet,the nun hurried onward.[14]121
该句子中,梁译本无论是形式还是用词上都紧扣原文,将“你怎么动手动脚……”直译为“Why do you molest me?”趋向于保留原作的形式之美,语言简洁凝练。而莱尔译本没有受制于原文形式的限制,用一个英语中常见的口语句式“What’s gotten into you? ”自由地将原句译出,并擅长挖掘形式与语词背后的元素,进一步增译了一句“Get your filthy paws off me!”将说话者的潜台词明示出来,也将小尼姑内心对阿Q这一动作(摸头皮)的嫌弃和厌恶淋漓尽致地突显出来。这一举措让译入语读者读懂字面意思的同时,也读懂了人物内心的心理,从而更好地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也体现了译者对原作的深度理解。
(二)灵活性的翻译策略
梁译本固然以直译见长,却又并非全部如先前论者所评价的那样,是僵硬、蹩脚、呆板之作。换言之,梁译本虽然以直译策略为主,却又不乏巧妙灵活的变通之法,颇有出彩之处。《阿Q正传》的一大语言艺术特色是人物对话中包含了大量的口语和方言土语,其中不少是带有强烈鄙视意味的侮辱性贬义词或粗俗詈辞,“忠实”翻译出去可能会给西方读者留下粗俗不堪的不良印象。梁社乾作为美籍华裔,家境富裕,衣食无忧,大学毕业后却选择从美国回中国发展自己的事业,自然是对中华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从其业余喜爱音乐、戏剧等高雅艺术可见品味、格调不俗。加之,梁译本英语学习辅助材料的定位,对这类词的处理,都是其翻译过程中需要谨慎对待的内容。
原文:“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来说。
梁译:“Remember this, you-”spurted Ah Q, turning back his head.
“You——remember this and it will be all right,” sputtered little D, also turning back his head.[12]42
莱译:“Let that be a lesson, you fucker!” said Ah, Q, turning his head back to Young D.
“Let that be a lesson,you fucker!”said Young D, also turning his head back to Ah Q.[14]135
小D和阿Q之间原本有过节,这是二人一次相遇打斗之后的对话,他们同样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处的社会地位、身份、语言都相同。梁译本和莱尔译本在这一句上的翻译差异较大。梁译本采用直译的方式,遵照原文的语序,把“记着罢”译为“Remember this”。而莱尔翻译时照顾到英语表达的习惯,将原文语序完全相反的两句翻译为一样的语序,译为“Let that be a lesson”,属于意译,形式更加灵活,并且将这句话所隐含的潜台词明晰化;而对原文中“妈妈的”一词的翻译,二人采取风格迥异的翻译策略。“妈妈的”是一个极具文化特色的辱骂性方言口语词,是被鲁迅称之为“国骂”的詈辞“他妈的”在小说中的变体,梁译本在这里采取“净化”的翻译方法,直接将其隐匿不译,仅译为“you-”,体现了译者使用“净化”翻译方法的良苦用心。莱尔译本采用了同样带有侮辱性的对应词“you fucker”进行翻译,并采用了“!”来表达说话人内心的强烈感情,将原文中“妈妈的”所蕴含的愤恨、仇视与诅咒传递出来,实现了文化功能对等。
《阿Q正传》主要刻画底层百姓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像阿Q这样的平头百姓,因此语言中不乏粗俗色情成分。梁社乾对色情方面的猥亵之词倾向于进行委婉化处理。
原文:“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梁译:“Will you...will you...?”suddenly cried Ah Q,advancing quickly and kneeling before her.[12]32
莱译:Now Ah Q moved directly in front of her and knelt at her feet.“Sleep with me!Sleep with me!”For a brief instant you could have heard a pin drop.[14]127
这是第四章《恋爱的悲剧》中,阿Q突然跪下向吴妈表达爱意时所说的话,语言粗俗直白。对照原文与梁社乾、莱尔的译本,显见二者的差异。莱尔将下层百姓的粗俗之语视为《阿Q正传》语言艺术特色的一部分进行直译,“Sleep with me!Sleep with me!”让读者直接体味到原文中此类小人物的地道语言。且对原文的语序进行了调整,将阿Q说话时的动作调整到其对话之前,意在突出强调阿Q的突兀行为。而梁社乾译为“Will you...will you...?”,原文中表达阿Q强烈感情的标点符号“!”被改为“?”用一个文雅体面的场景来代替原文中粗俗的求爱场面。因此无论从语词还是标点符号的使用上,梁译本的表达更委婉含蓄,更体面。可见译者使用改译的翻译策略刻意回避《阿Q正传》的粗俗表达,为英语语言学习者提供较为洁净的语言学习文本。
四、余论
梁社乾回中国后,选择鲁迅的《阿Q正传》进行英译。一经出版,很快售罄,第二年便第二次印刷,可见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证明了其过硬的双语素质。当然对于《阿Q正传》这样一部“并不是一本很容易译成外文的书”[5]67,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误译。如“而立之年”误译“the late age of forty”,“三十而立”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常识,译者这里错译为四十“forty”。“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误译成“If the seventh child cuffed the eighth child,or perhaps,the fourth Li child struck the third Zhang child”[12]19,“阿七”“阿八”这里指成年人之间的打斗,作者用“the seventh child”“the eighth child”进行对译,显然比较滑稽。推其出现误读误译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来梁社乾生于美国,归国时间未久,对中国下层百姓生活、语言、风俗等的知识储备不足,从敢于着手翻译《阿Q正传》这样一部翻译难度较大的书而言,已属勇气可嘉。众所周知《阿Q正传》是一部极富民族特色的小说,文中包含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及地方文化特色及习俗,加上鲁迅语言独特、文白夹杂,翻译中难免出现误译。二来关于误译,谢天振教授曾谈到“尽管人们认识到,翻译应尽可能准确、忠实地传达原文,但误译的情况仍比比皆是。甚至一些大家、名家在他们的译作中也无法避免误译”。中外大家都有不少类似的情况。鲁迅曾把《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女主人公谢赫拉扎台的名字误解为一座城市[15]。1990年出版的,被誉为《阿Q正传》成功译本之一的莱尔译本在大量前人译本可供参照的情况下,依然有着不少误译。如,邹七嫂,误译为“Seventh sister Zou”(邹家的第七个孩子)。注释中“赵匡胤”误译为“Zhao Guangyin”。在梁立乾翻译的20世纪20年代,在毫无前人资料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进行英译,已然实属不易,不可求全责备。
因此,无论从原著的难度、译者的身份及误译出现的概率,误读误译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日本学者河盛好藏断言“没有误译的译文是根本不存在的”[15]。所以,此类误译不能遮蔽梁社乾英译本《阿Q正传》的成就和影响。从该版本多次再版、重印以及梁社乾靠着翻译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和鲁迅的《阿Q正传》这两本小说在国内站稳了脚跟的事实,便可窥见该译本的成就和影响。他的《阿Q正传》翻译策略的选择适应时代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忠实而又不失灵活,尤其对文中人物对话的一些粗俗、猥亵语言采取的“净化”“委婉化”翻译方法的运用,契合该译本作为语言学习材料的功能以及目标读者和赞助商对其的期待。何况梁社乾作为《阿Q正传》的首个英译本,仅此一端,也是厥功至伟的。笔者衷心希望梁译本的文献学及文学翻译史价值和意义不再被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