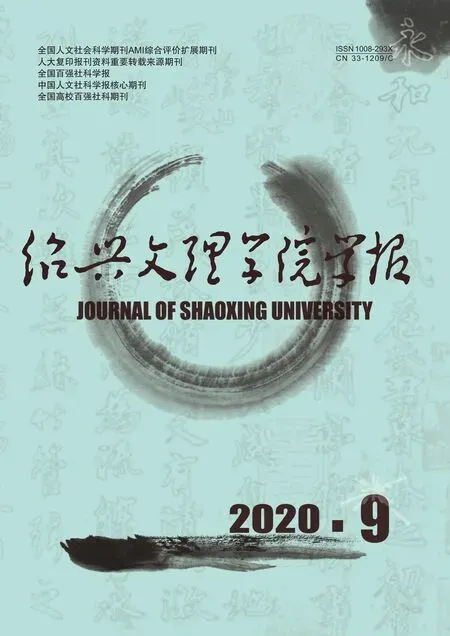论“愁”字诗意的生成
曹诣珍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中国古典诗词素有言愁之传统,故陆放翁《读唐人愁诗戏作》曰:“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1]102虽为戏语,却将诗与愁之间的紧密联系明确肯定下来。古诗写愁篇什众多,内涵各异,喻象纷呈,愁情之表现自非必待“愁”字而彰显。然“愁”之一字,实乃愁情最直接、最明晰的语言载体,故深得文人骚客青睐。据统计,唐诗中大约4000多首诗含有“愁”字[2];《全宋词》中,“愁”字出现了3845次[3]。金岳霖指出,中国文字在情感上的寄托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哲意的、诗意的和普通的[4]259-265。“愁”字在古典诗词中的反复出现、层层皴染,显然已使它蕴含了浓郁的诗意,能够轻易地触发读者的联想与美感,引领人进入诗情与画意的境界。
然纵观学界成果,学者们对于古典诗词中的愁情虽已甚为关注,但多着眼于某一具体作家作品,如万静《试论东山词写“愁”的艺术》、向梅林《论李清照词中“愁”的文化内涵》、谷利平《论船山词中的“闲愁”》等。作较全面关照者,又多局限于唐宋时期,其中以张仲谋《论唐宋词的“闲愁”主题》一文最为精深,其它如葛琦《论唐宋词中的愁情》、曹瑞娟《宋代思想文化与宋词的“闲愁”主题》等。而对于一个较为本源性的问题,即自先秦以还,唐宋之前,愁情的主要文字载体“愁”字所依附的诗意如何生成,又如何从“忧”“悲”“哀”等与之近义的情感词中脱颖而出、秀然而立,成为最受诗人青睐、最富诗意者,则较少涉及,未见详论,甚至存在一定的误识。因此,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作系统的梳理,以期有助于更深切地体认中国古典诗词言愁传统的发生与发展。
一
然而,考察汉语中以“秋”为声符孳乳繁衍的一系列同源词,可发现,“秋”作声符兼有表义功能时,所包涵的语义特征并非“秋天”,而是与秋天密切相关的“聚收”“收缩”。如《左传·昭公元年》杜预注:“湫,集也”[9]1199;《后汉书·马融传》李贤注:“揫,聚也”[10]1959;应劭《风俗通义》:“甃,聚砖修井也”[11]123。再如“”,谓居丧者头饰或古代男子束发用的巾,其功用为束聚头发;“鬏”,指脑后头发盘聚而成的髻;“”,谓车轮中凑集于中心毂上的直木;“”“鞦”,指驾车时络于牛、马尾下的革带,引申为收紧;“”,同“縬”,指绉缩;“”,同“绉”,谓衣不伸……相关字词,均含“聚收”“收缩”之义。诚然,“秋”之本义当如《说文·禾部》所云“禾谷熟也”,与其直接相关的标志性行为就是“聚收”。正如《管子·四时》曰:“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12]37《礼记·月令》也记载当秋之季,须“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13]591。又因秋是一个万物收敛成熟的季节,故前人亦以为“秋”字本身包含“收缩”义,如《汉书·律历志》云:“秋,也。物敛,乃成孰。”[14]971(《说文·韦部》:“,收束也。”)显然,对尚处于早期农耕时代、以食为天的先民而言,秋天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草木摇落、白露凝霜等景物的萧瑟,而就在于万物成熟、收获庄稼。故在造字之初,以“秋”为声符兼表义时,取“聚收”“收缩”之义,当在情理之中。
由此可进一步推断,在先秦时期就已生成、同样以“秋”为声符兼表义的“愁”字,其义源当为“心绪聚积”,由此生成忧愁义。事实上,正因“愁”字本身就包含“聚”义,故“愁”可与“揫”通,释为“敛束、聚敛”。如《礼记·乡饮酒义》:“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郑玄注:“愁,读为揫。揫,敛也。”[13]2284又可与“梄”通,释为“聚”,《集韵·尤韵》:“梄,《说文》:‘聚也。’或作愁。”也就是说,“愁”字的义源中,并不包涵“触景生情”的成分,其诗意并不像很多人以为或希望的那样为造字之初就天然赋与;以“触景生情”解之者,实是忽略了对它的同源词的系统考察,且囿于后来文学之“悲秋”印象,将其诗化了。
二
从目前所能依据的先秦典籍看,“愁”字最早当见于《周易·晋》:“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15]124其后亦散见于《墨子》《管子》《庄子》等诸子之文,以及《左传》《晏子春秋》等史家之文,然皆为一般叙述性文字,体察不到诗意的美感。欲探寻“愁”字诗意之生成,还得求诸《诗》《骚》等诗歌作品。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不乏愁情之抒写。无论是《周南·关雎》《陈风·月出》等的思慕之愁,还是《邶风·击鼓》《小雅·采薇》等的离别之思,抑或《鄘风·载驰》《王风·黍离》等的家国之悲,以及《唐风·蟋蟀》《曹风·蜉蝣》等的忧生之叹,都已远开后世诗词言愁之先河。故陆放翁《读唐人愁诗戏作》又曰:“三百篇中半是愁。”[1]103而《秦风·蒹葭》一篇,更以其意境的飘渺深远、用笔的郁伊惝怳、风格的翛然自异,被视为言愁之典范。程俊英评曰:“全诗不着一个思字、愁字,然而读者却可以体会到诗人那种深深的企慕和求之不得的惆怅。”[16]346然不着“愁”字,正是《诗经》言愁之总特征:遍览三百篇,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尽管《诗经》中已多愁情,却无一个“愁”字!而与之语义相近的“忧”字则多达83个,此外“哀”字28个、“伤”字16个、“悲”字11个……“愁”字在《诗经》中的缺失,是单纯的巧合?抑或是语言的地域特征的显现?令人费解。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7]35《诗》《骚》之间,或仅偶有古谣谚传世。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记载:“梧桐宫,在句容县。传云吴别馆,有楸梧成林焉,梧子可食。”并引《古乐府》云:“梧宫秋,吴王愁。”[17]6沈德潜《古诗源》名之为《吴夫差时童谣》,评曰:“国家愁惨之状,尽于六字中,不啻闻雍门之弹矣。秋,隐语也。”[18]19倘若此谣谚确为吴王夫差时作,则当为目前所能见之文献中包含“愁”字的最早韵语。而其中“愁”字诗意的生成,显然与梧宫秋色浓重、梧叶飘零的景象密切相关。前文论及:“愁”字的义源当为心绪聚积,与秋天景物之趋于凋敝并无必然关联。这主要是从词源学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去推断的。然而,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以美为旨归,并以跳跃性的联想为主要思维方式。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个体意识的觉醒,对天然拥有“宇宙间一种生命的共感”[8]14的诗人而言,物之枯荣与心之悲喜,便因其有类似之处,易引起一种见物起兴的感发。秋景与愁情之间的关联,在《诗经》中已现滥觞。《小雅·四月》:“秋日凄凄,百卉具腓”[16]638写出秋日草木零落对乱离之人内心凄情的触发。《秦风·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16]346的一唱三叹,更是将满目秋光与迷离惝怳的愁绪交融合一,达臻天籁之境。故在诗人的心目中,“秋”的意义恐怕早已与“聚收”渐行渐远,而更多地与萧瑟、凋敝、衰败等秋日景物的印象关联在一起。正如史达祖《临江仙·闺思》所畅想的:“愁与西风应有约,年年同赴清秋。”[6]3380“愁”字诗意的生成与秋光秋色秋容秋韵相融汇更像是一种约定,是或早或迟的必然。虽然,因文献的缺失,我们已经难以判断“愁”字最初入诗是否就与秋景关联,但是,像“梧宫秋,吴王愁”这样的谣谚能够动人情、摇人心,久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显然得益于“秋”与“愁”的情景交融。二者字形关联,音读相类,在诗歌的国度里交融汇聚,确有恍若天成之感。
然“秋”与“愁”的关联,更为鲜明、直接的体现当是在《楚辞》中。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以奇思椽笔,抒写了美人迟暮、命运多舛的悲叹与家国飘荡、美政无门的忧戚。其《离骚》一篇,为“忧心烦乱”“中心愁思”而作[19]2;《九歌》诸首,缘于“怀忧苦毒,愁思沸郁”[19]55;《天问》之创,由于“忧心愁悴”[19]86;《九章》之作,则因“思君念国,忧心罔极”[19]121……故屈赋诸篇,皆悲愤抑郁,愁情积聚,荡溢其中的是“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19]136(《九章·哀郢》)的情感基调。其后宋玉等,或悲感己身之遭际,或追慕屈子之洁操,所作之文,大抵类此。而在愁情的表现上,与《诗经》不着“愁”字相反,《楚辞》中的“愁”却是触目可及、随处可摭。据笔者统计,《楚辞》中“愁”字多达35例,其中屈赋用及11例,见于《九歌》者4,见于《九章》者7,多用以抒写诗人不为世俗所容的悲郁心境。如《九章·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19]132《九章·悲回风》:“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娱”[19]160。最具典型性的,当属《九歌·湘夫人》开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19]65此一“愁”字,于《楚辞》中,不仅为首见之例,且又是最动人心、最使人遐想无限、最具诗意者。其诗意的生成,显然与秋风疾而草木摇、湘水波则树叶落的洞庭秋色的描写有首要关联,至于愁情的具体所指,——或是人神相恋的怨望,或是悲岁徂尽的哀叹,或是思贤不得的怨尤,或是不值尧舜的感伤——倒反退居其次了。故明胡应麟誉之为“千古言秋之祖”[20]5,清贺贻孙评曰“可敌宋玉悲秋一篇”[21]9。如此秋景,恁般愁情,真正实现了情与景的水乳交融,正如明人陆时雍所评:“风流萧瑟,袅袅秋风,水波木下,愁绪当与湖水相量耳。”[22]428相较而言,前文所举“梧宫秋,吴王愁”的意境与手法虽与之均有近似之处,然任昉《述异记》的创作年代为南朝梁,与吴王夫差之时相距已近千年,其所记谣谚为历史真实抑或后人附会,已难确考,且其于中国诗歌史的影响力毕竟微渺。故《楚辞·九歌·湘夫人》这起首数句,实堪称“愁”字诗意的真正发端。
继屈赋之后,宋玉《九辩》抒写喟叹“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进一步确立了愁情与秋景间的关联。其文亦用及3例“愁”字:“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独悲愁其伤人兮,冯郁郁其何极”,“邅翼翼而无终兮,忳惽惽而愁约”[19]185-199。后人概言“屈原(平)愁”“宋玉愁”,指向的虽然是其作品中整体的愁意,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屈宋诸赋中“愁”字的频繁运用,使其愁情的表现更为直接明晰酣畅了;而“愁”字的诗意,也就在其中酝酿、发酵,渐次生成。
三
“愁”为情感词。情感词的特点,是意义抽象,相互间的差别微妙,既模糊又容易混同,故字书亦难为之作解[23]148。以释“愁”而论,《说文·心部》:“愁,忧也。”《广雅·释诂三》:“愁者,悲也。”《广韵·尤韵》:“愁,忧也,悲也,苦也。”诸字之间,意义近同,时为互训,不易作严格区分。此一特点,在《楚辞》等早期诗歌作品中,主要表现为“愁”与他字多以一种联合混同的形式出现:就词而言,有“愁苦、愁凄、悲愁、愁悴、愁戚、愁哀哀”等;就句而言,有《九叹·惜贤》“忧心展转,愁怫郁兮”[19]302,《九叹·思古》“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于山陆”[19]310,《九思·逢尤》“悲兮愁,哀兮忧”[19]318等。据笔者统计,《楚辞》中“愁”字固然多达35个,而“忧”字亦有37个,“悲”字55个,“哀”字57个……在这样的语词背景下,“愁”字的诗意虽已生成,但显然独立性不强,难以突显,尚不足以从一干近义词中脱颖而出。而《骚》之后,唐之前,以“愁”字入诗赋者虽不乏名篇警言,如汉乐府《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18]80王粲《七哀诗》:“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18]128潘岳《秋兴赋》:“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24]991……然若论以浓墨重笔皴染“愁”字之诗意、令其终秀于林者,当数张衡《四愁诗》、曹植《释愁文》与庾信《愁赋》。
张衡之《四愁诗》,其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霑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二思“在桂林”,三思“在汉阳”,四思“在雁门”[18]54-55。《文选》此诗前有小序,言张衡效法屈原,以香草美人为比兴,抒写己志。前人评价《四愁诗》,多点出一个“情”字。如胡应麟曰“百代情语,独畅此篇”[20]40,沈德潜云此诗“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18]55,都指出深情委婉是这首诗的最大特点。而诗中所抒之情的中心内容,正如诗之标题所揭示的,乃是“愁”。全诗由四组意象组成,诗人由“东望”而到“南望”“西望”“北望”,表现了一种由“理想”(有所思)→“实践”→“阻遏”→“感伤”→“希望”→“无奈”→“忧怀”→“哀怨”“失望”“惆怅”构成的心灵历程[25]。这一历程完整而曲折,然终归于一个“愁”字。故将此诗置于整个中国古典诗词的言愁传统中看,会发现它的意义不同寻常:首先,这首诗应是最早直接以“愁”字名篇的诗歌(2)或以为西汉武帝时刘细君有“吾家嫁我兮天一方”之歌,其名为《悲愁歌》,乃在张衡之前。然考之《汉书·西域传》,仅云:“公主悲愁,自为作歌。”并未有歌名。其后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皆同。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唐《艺文类聚》、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元左克明《古乐府》等录此诗均名之为《乌孙公主歌》。及至明冯惟讷《古诗纪》,方称为《悲愁歌》。其后明梅鼎祚《古乐苑》、陆时雍《古诗镜》,清杜文澜《古谣谚》、沈德潜《古诗源》等因之。可见,《悲愁歌》之称当为后人所加。而张衡《四愁诗》之名则应是诗人自己所命。晋时傅玄有《拟四愁诗》,其《序》即云“张平子作《四愁诗》”。。《楚辞》之中,已多用情感词名篇,如《离骚》《悲回风》《哀郢》《悯上》《伤时》等。而直接以“愁”字名篇者,当为张衡此诗。这意味着“愁”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完整的意象,被独立观照。其次,此诗承继《诗经》之《关雎》《汉广》《月出》《蒹葭》等篇,尤其是《楚辞》的《九歌·湘夫人》等,进一步以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人形象,明确了“愁”的核心内涵为“求而不得”。后人言愁,具体所指虽各有异,“有缱绻情愁、黯然离愁、款款思愁、乡梦迷愁,有羁旅行役之愁、风物兴发之愁、怀古咏史之愁、节序习俗之愁,有济世怀抱与扼腕叹息之愁、壮怀激烈与家国沦落之愁、内心返视与世间沧桑之愁”[26]……然究其根本,终是因为“一方面既对彼高远之理想境界常怀有热切追求之渴望,一方面又对此丑陋、罪恶而且无常之现实常怀有空虚不满之悲哀”[27]217,由此“陷入一种永远追求与不断失望相交错的心理困境”[28]。概而言之,即“求而不得”。曹植《洛神赋》:“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遗情想像,顾望怀愁”[29]284-285,阮籍《咏怀》“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18]139,李白《长相思》“美人如花隔云端,……长相思,摧心肝”[30]244等等,皆如是。再次,张衡此诗以其情感的深挚、风格的婉丽、音节的清新,在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甚或被誉为“千古绝唱”[31]118,这使得愁情在诗歌中的表现更为人们所关注。后人多以“张衡愁”或“平子愁”(张衡字平子)为常语,也可以说是从侧面反映了张衡在以诗言愁传统中的地位和影响。
张衡《四愁诗》之后,乃有曹植《释愁文》。曹植工愁善病,其作品喜以“愁”字名篇,如《九愁赋》《叙愁赋》《愁霖赋》等。而《释愁文》一篇,最具特色,尤可重视。其前半部分云:
予以愁惨,行吟路边。形容枯悴,忧心如醉。有玄灵先生见而问之曰:“子将何疾,以至于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为物,惟恍惟惚。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情爽。其来也难退,其去也易追。临餐困于哽咽,烦冤毒于酸嘶。加之以粉饰不泽,饮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麾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悦,乐之以丝竹增悲。医和绝思而无措,先生岂能为我蓍龟乎?”[29]467-468
后半部分则借玄灵先生之口,谓“愁”惟以老庄道术解之,“于是精骇魂散,改心回趣。愿纳至言,仰崇玄旨。众愁忽然不辞而去”[29]468。此文从形式上看,显系仿照《楚辞·渔父》,故虽未冠之以“赋”称,实为赋体之作。而此文之一大意义,在于它当是赋体文学中最早完全以“愁”为表现对象的作品(3)卞东波《庾信〈愁赋〉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2期)一文以为,赋体文学中,庾信《愁赋》最早完全以“愁”为表现对象。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因为对曹植《释愁文》等这一类虽未冠以赋称但实为赋体的作品失于考察。。文中着重描摹了“愁”这种情感的特征:恍惚莫名,缠绵顽固,低落弥久,无可排遣。其中“愁是何物”一问,尤为高妙,启后代无数情思:“愁”分明是一种情感、一种心绪,是抽象的,难以形状的,而诗人却采用化虚为实之法,以其为具体之“物”,欲推欲握,欲退欲追。在诗人笔下,“愁”已经“由一种抽象的内在的情绪变成一个独立于人的外在客体”[2],不仅有形态,甚至似乎还有了独立的意识,能自来自去,缠人磨人。后世写愁,手法各异,然举其要,大致不出“化虚为实”四字。李白的“远海动风色,吹愁落天涯”[30]600(《早秋赠裴十七仲堪》),李煜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32]85(《乌夜啼》),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6]931(《武陵春》)等,都以“愁”为可吹、可剪、可理、可载之实物,或皆当以曹植此文为滥觞。
曹植《释愁文》后,又有庾信《愁赋》。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述及庾信《愁赋》对唐宋诗词言愁之影响,并提醒人们注意一句话,即“‘庾郎愁’字乃是宋人常语”[33]1531。庾信《愁赋》今已散佚,在宋人的类书和注释中尚存片言只句,主要有以下两段:
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34]431
攻许愁城终不破,荡许愁门终不开。何物煮愁能得熟?何物烧愁能得然?闭门欲驱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34]431-432
虽为残篇,但在艺术手法上,依稀可辨主要延续的是曹植《释愁文》中的“化虚为实”之法,故言无形之愁可用容器“斛”来承载,且难煮难烧,不熟不燃;欲驱不去,欲藏已知。而又有进一步的发挥,直接采用了比的手法,谓愁如城如门,不破不开,以喻愁之顽固烦人。后之诗词抒写愁情,最大的特点就是喻象纷呈:一江春水,千丈白发,万点落红,满城风絮……无不可喻愁;愁可“似天来大”[6]1968(辛弃疾《丑奴儿》),“似月明多”[6]930(李清照,失调名),“似春山碧”[6]1681(沈端节《菩萨蛮》),“似鳏鱼知夜永”[35]194(张先《和苏诗》)……凡此种种,皆可视为是在庾赋基础上的求新求变。
就风格而言,曹植《释愁文》飘忽玄奇,庾信《愁赋》则略显“狂易可怪”[36]448,而其共同之处,在于不仅都明确以“愁”名篇,且充分发挥了赋体文学的优势,淋漓尽致地铺叙了愁情的特征,并将“愁”客体化、形象化,令人耳目一新!故后世多有追摹仿效之作,如唐符载《愁赋》:“愁之为物也,亲贱贫,傲富贵。……其去也若缘云之难,其来也类走丸之易。”[37]2055释真观《愁赋》:“尔其愁之为状也,言非物而是物,谓无像而有像。……或起或伏,时来时往,不种而生,无根而长。”[38]396终不出曹文庾赋之范围。曹、庾二人,论其才情,均高华爽俊;视其命运,则跌宕多舛,又皆有言愁典范之作,故后人喜以“才八斗”“愁万斛”合而言之,如:“便如前哲亦非敌,八斗才当万斛愁”[39]13737(晁说之《惜春》),“明窗净几风日暖,有愁万斛才八斗”[40]113(陈师道《古墨行》),“有愁万斛,有才八斗,慷慨时惊俗眼”[6]2537(黄机《鹊桥仙·次韵湖上》)……“才八斗”与“愁万斛”就其典故出处而言分指二人,实当视为互文,意指曹植、庾信皆怀才不遇,有才八斗有愁万斛。
总言之,“平子诗中,庾生赋里,满目江山无限愁”[6]3083(陈人杰《沁园春·次韵林南金赋愁》)。继《楚辞》之后,张衡《四愁诗》、曹植《释愁文》与庾信《愁赋》均以其新奇高妙的艺术手法,对“愁”的情感内涵或特征作了形象生动的描摹,从而使“愁”字进一步突破了“忧也”这样一种单调、模糊的概念义的束缚,更多地拥有了能够触发人联想和美感的诗性的涵义或附属义;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和“忧”“悲”“哀”等近义词的混同局面,更趋独立和鲜明。“愁”之一字,由此更能激发后世诗人的共鸣,更为他们所青睐,不仅频繁入诗,且通变化用,喻象万千,内涵更深,外延更广,终成为最富诗意的情感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