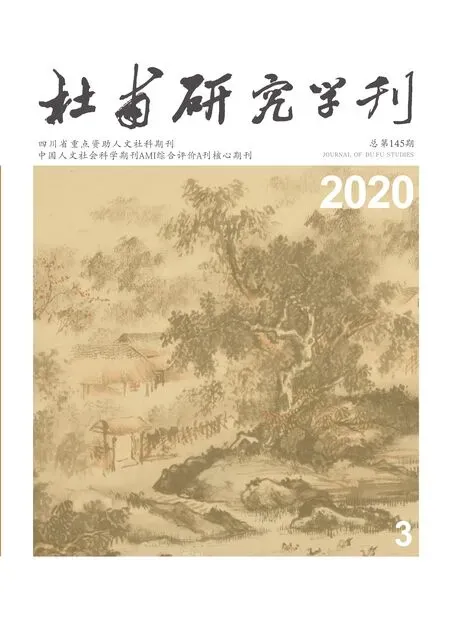唐代清乐“三十二曲”考
——曲目辨析与文献批判
林晓光
一、问题的提出
东晋南朝的俗乐,包括汉魏旧曲和江左新声,在隋平陈后被纳入清商署,成为隋唐九部乐中的清乐。关于清乐在唐代的存亡状况,以下史料常常被学者引用,《乐府诗集》卷四四“清商曲辞一”解题:
至武后时,犹有六十三曲。其后歌辞在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凤将雏》《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及欢闻》《团扇》《懊憹》《长史变》《丁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伴》《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声无辞,《上柱》《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①
其大意是说清乐至武后时尚存六十三曲,而到杜佑写《通典》之时则仅存四十四曲了。其中以曲目为单位来数的话,三十二曲存有歌辞;而以歌辞为单位来数的话,则有三十七曲。另有七曲则仅有音乐而无歌辞。不过,这段话实际上应是抄自《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
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凤将雏》《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及《欢闻》《团扇》《懊憹》《长史》《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伴》《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声无辞,《上林》《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②
而《旧唐书》的史源,显然又来自《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六》“清乐”节,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典》相应段落是:
大唐武太后之时,犹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欢闻》《团扇》《懊憹》《长史变》《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叛》《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共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曲。(其《吴声四时歌》《杂歌》《春江花月夜》并未详所起,余具前歌舞杂曲之篇。)又七曲有声无辞:《上林》《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③
三种文献之间的承袭关系一目了然,只是有抄书的巧拙之别。例如《通典》所谓“今其辞存者”,显然就是指唐人杜佑自己所知道的当代情形;而《旧唐书》作为五代时编撰的有唐一代史书,却连这句话也照抄不误,令读者茫然不知“今”为何时;《乐府诗集》抄得则要聪明一些,将“今”改为“其后”,虽然还是含糊其辞,但总算维持了文脉的稳妥。而曲目上最大的分别,则在于从《旧唐书》开始,在《明君》和《明之君》二曲之间多出了一曲《凤将雏》。这不言而喻会使看似数目相同的“三十二曲”发生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再加上各书整理者的理解差异,结果便导致三种文献的点校本对这一同源史料作出了差异颇大的点断,不免对读者认识南朝至唐期间的清商乐曲造成混乱。下面列表以示三书点校本对具体曲目理解存在差异之处(以数字表示该处的曲数):

其结果,尽管《通典》和《乐府诗集》都分别凑合了“三十二曲”的总数要求,但却是貌合神离;而《旧唐书》更是离谱,号称三十二曲,实际上却点出了三十五曲之多!
因此这段材料看似简单,但由于文献的承袭改造、曲目的古老难辨,却发生了颇费思量的棘手问题。学者过去已对此有所探讨,王运熙先生曾针对《通典》中的这段文字,精辟地指出:
《通典》:“《三洲歌》者,诸商客数由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又因《三洲曲》而作《采桑》。”似将二曲并而为一,否则总数应为三十三曲。
《旧唐书》《唐会要》于《明君》《明之君》二曲中间,增入《凤将雏曲》,与下文《凤雏》分为二曲,非。④
王先生对《三洲采桑》的意见与《通典》点校本是一致的,但他的行文也反映出这同样是“凑数”思维所得到的结论,即在曲目稍多或稍少于正确数目时,对其中可以调整的部分做出微调,以求吻合。对于这一史料,这种思考方式无疑是最切实可行的,但在学理上则恐尚可商,这一点下文再论。同时,王先生更已敏锐地意识到了《通典》《旧唐书》《乐府诗集》这一系列文献之间先后承袭的文本生成关系,指明《凤将雏》乃是从《旧唐书》以后才被增入的,因此当然就不可能是《通典》所说“三十二曲”之一。
关于中华书局本《乐府诗集》的点校失误,学者也已多所指摘。孙尚勇正确地指出《阿子及欢闻》应点为“《阿子》及《欢闻》”⑤,《雅歌骁壶》也应分为两曲⑥。不过这样一来,《乐府诗集》的曲目却不免要变成了三十四曲。即使将《凤将雏》除去,也还有三十三曲,显然不合,这一点则似未见论及。而且,点校本《通典》同样将《阿子欢闻》点为一曲,如果将其拆开,也要变成三十三曲了。值得注意的是,据《通典》校记,可知这其实是根据“北宋本”、《旧唐书·音乐志》等校改的结果;而在其据为底本的“浙江书局本”中,“阿子欢闻”原是作“阿子歌”的。王运熙先生所据的恐怕也是这个本子,因此其标点刚好符合“三十二曲”之数,并不发生问题。为什么《通典》不同的版本之间会发生这种出入呢?说不定也就是因为校刻者意识到了其中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将字形相近的“欢”改成“歌”,又从而脱去了“闻”字。
无论如何,我们综合上述讨论,可知这段记载了唐代清乐至杜佑时尚存“三十二曲”的史料,所载曲目却无论怎样数也至少有三十三曲之多,因此也就意味着至今对其的理解必定还存在着未曾被意识到的错误之处。而这些相关曲目为何会在不同的文献整理中出现不同的理解?则与乐府文献史料之间纠缠复杂的生成关系有关。本文即拟通过对这段史料进行文本构造分析和文献生成批判,厘清其书写脉络,考订清乐“三十二曲”究竟是哪些曲目?
二、“三十二曲”的文本构造
前文提及,王运熙先生已经指出《凤将雏》是《旧唐书》误增入的。不过王先生并未详细说明理据,似乎只是凭常理判断。然则从理论上说,我们并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现存《通典》脱漏了《凤将雏》这一曲,反而赖有《旧唐书》才保存了这一较原始的面貌。这两种可能性在文献流传上都不乏其例,那么究竟哪一种才是事实呢?实际上,如果结合《旧唐书》此曲目之后的一大段文字,仔细观察这“三十二曲”的叙述次序,便会发现其并非随意杂凑,而是井然有序地分为五个层次。这让我们看到杜佑撰写这一节时,无论是出于自己的观察归纳抑或别有所本(例如清商署的档案),其书写背后都有着清晰的体系意识,反映出唐人对清乐构成的理解方式。而《凤将雏》必为后人羼入,正可从中得到证明。下文就此稍作申论补充,关于各曲源起本事的说明,则引据现存史源最早的文献。
首先,排在第一位的《白雪》,是独一无二的周代古琴曲。《通典·乐典五》:“《白雪》,周曲也……按张华《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弦琴曲名。’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者。”⑦
第二层次,则《通典》所记《公莫》以下七曲,都是汉魏时代的古舞曲。其次序是:《公莫》《巴渝》《明君》《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当时主要的舞曲类型有所谓鞞、铎、巾、拂四舞⑧,均在其中。“《公莫舞》,今之巾舞也”,其源起于项伯与项庄舞剑护卫刘邦之事,见《宋书》卷十九《乐志一》⑨。《明之君》是鼙舞曲(见下)。《铎舞》,《通典·乐典五》:“汉曲也。”⑩。《白鸠篇》则是拂舞歌诗五篇之一,《南齐书》卷十一《乐志》:“出江南,吴人所造”。除此四舞之外,《白纻舞》歌诗三篇,也“宜是吴舞”。“《巴渝舞》,汉高帝所作也。”源起于高祖出汉中定三秦时充当前锋的阆中賨人之舞,见《乐府诗集》卷五三“舞曲歌辞二”王粲《魏俞儿舞歌》解题引《晋书·乐志》。
在这七曲中,唯一存在疑问的是《明君》。从标题上说,此语本身就含有两种歧义,一是指王昭君,二就是等同于“明之君”。《通典·乐典五》和《旧唐书·乐志二》的解释,都取前者,认为是汉人为昭君远嫁作歌(不过《通典》并未直接将这一解释与《乐典六》所载“三十二曲”中的《明君》挂钩),而石崇妓绿珠善舞,故崇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也就是著名的《明君辞》)。
但是,《明君》也可能为《鼙舞曲》中的一篇。《乐府诗集》卷五三“舞曲歌辞二”“晋鼙舞歌五首”解题引《古今乐录》:“晋鼙舞歌五篇……五曰《明君篇》,当魏曲《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树》。”南北朝《鼙舞曲》均继承了此篇题。齐鼙舞曲有《明君辞》二首、《圣主曲辞》一首,《魏书》卷一百九《乐志》所载“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云云,其中的中原旧曲“《明君》《圣主》”显然就是齐鼙舞曲的这两篇——曲为汉魏旧曲,辞则为南朝新造。而周舍所造梁鼙舞曲三首更是同时包括《明君》和《明之君》在内。《通典·乐典五》:“《明之君》,汉代《鞞舞曲》也。梁武帝时,改其曲词以歌君德也。”故对《明之君》而言,曲旧辞新的逻辑也正是一样。考虑到《通典》“三十二曲”中“《明君》《明之君》”次序相连,毋宁说从这一角度理解《明君》一曲,更有说服力。
当然,即使认为《明君》是汉晋人为王昭君之歌,其为舞曲的性质也并不受到影响。《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明言隋代清乐“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而石崇由于绿珠善舞而教以此曲,也正反映出此曲乃是舞曲。
第三层次,则是《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欢闻》《团扇》《懊憹》《长史变》《丁督护》《读曲》。这十曲无一例外,都是吴歌。
关于吴歌的曲目,《乐府诗集》卷四四“清商曲辞一”“吴声歌曲”解题:
《古今乐录》曰:“吴声歌……其曲有《命啸》吴声游曲半折、六变、八解,《命啸》十解。存者有《乌噪林》《浮云驱》《雁归湖》《马让》,余皆不传。吴声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凤将雏》,四曰《上声》,五曰《欢闻》,六曰《欢闻变》,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丁督护》,十曰《团扇郎》,并梁所用曲。《凤将雏》以上三曲,古有歌,自汉至梁不改,今不传。上声以下七曲,内人包明月制舞《前溪》一曲,余并王金珠所制也。游曲六曲《子夜四时歌》、《警歌》、《变歌》,并十曲中间游曲也。半折、六变、八解,汉世已来有之。八解者,古弹、上柱古弹、郑干、新蔡、大治、小治、当男、盛当,梁太清中犹有得者,今不传。又有《七日夜》《女歌》《长史变》《黄鹄》《碧玉》《桃叶》《长乐佳》《欢好》《懊恼》《读曲》,亦皆吴声歌曲也。
这段史料也有严重的点校错误。“其曲有《命啸》吴声游曲半折、六变、八解,《命啸》十解。存者有”,明显应该点作“其曲有《命啸》《吴声》《游曲》《半折》《六变》《八解》。《命啸》十解,存者有”。其实从这段材料本身就可以知道,《命啸》有十解,《吴声》有十曲,《游曲》有六曲;而《半折》《六变》《八解》都是曲名。还有“《七日夜》《女歌》”,从《乐府诗集》卷四五所录曲辞可知显然就是《七日夜女郎歌》,所以应当标点为“《七日夜女歌》”才对。此外,《通典》所录这七曲中,《平折》《命啸》都是吴歌,《平折》当然就是《半折》,二者只是形近而讹;《上林》和《上柱》显然也是形讹关系(但不知到底是《吴声》十曲中的《上柱》,还是《八解》中的《上柱古弹》)。此曲现存《通典》和《旧唐书》都作“上林”,而《乐府诗集》在不同的地方都作“上柱”,维持了内部的统一。
了解这一基本情况后,便可知在这十曲中,《子夜》《前溪》《阿子》《欢闻》《丁督护》《读曲》都是《吴声》十曲中的曲目,《团扇》也是《吴声》十曲中的《团扇郎》无疑。因此其中有七曲都出自《吴声》。而《游曲》六曲,亦即从《子夜歌》演变的六首歌曲,包括《子夜四时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吴声四时歌》显然就是其中的《子夜四时歌》,因为《子夜歌》本身就是《吴声》十曲之一,所以《子夜四时歌》当然也就不妨称为《吴声四时歌》。换言之,如果《通典》原文写成“吴声子夜四时歌”,那么应当理解为一曲;但既然写作“子夜吴声四时歌”,那就只能理解为《子夜歌》及其变歌《子夜四时歌》了。另外《懊憹》《长史变》两种则是单独的吴歌曲目。
排在吴歌之后的第四层次,包括《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伴》《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这批曲子,除了《骁壶》以外,全都是西曲,其曲目均见于《乐府诗集》卷四七至卷四九的“西曲歌”解题及歌辞部分。其中《栖乌夜飞》在点校本中虽似未见录,但从题目及本事(沈攸之作)看,其实就是卷四九所录《西乌夜飞》。事实上,宋本《乐府诗集》原本正作《西乌夜飞》,《乐府诗集》解题和歌辞本身是自洽的;点校者想必是依据《通典》《旧唐书》迳改,反而导致《乐府诗集》内部出现了裂痕。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上柱》和这里的《西乌夜飞》,情形完全一致,都是《通典》《旧唐书》相同,而《乐府诗集》尽管内容承袭二书,文字细节上却自己维持了内部的一贯性。
需要略加讨论的是《雅歌》。孙尚勇已经考得这应当就是《乐府诗集》卷五一所录梁武帝造《雅歌》五曲,而《骁壶》则是隋炀帝命白明达所造《投壶乐》。这里可以再补充一点证据。《通典》这段文字的小注说:“其《吴声四时歌》《杂歌》《春江花月夜》并未详所起,余具前歌舞杂曲之篇。”然而在前文的曲目中却并未提到《杂歌》,这个《杂歌》当然只能是《雅歌》的形讹。杜佑说除了这三曲源起不明外,其他诸曲均在《乐典五》的“歌舞杂曲篇”中已经提到,而检此篇中正有“《骁壶》者,盖是投壶乐也。隋炀帝所造”云云,可知《骁壶》当然就不是“未详所起”的三曲,因而也就不可能和《雅歌》是同一曲。
尽管杜佑已经说《雅歌》所起不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文献线索作出一些推断。在《乐府诗集》收录西曲的相关卷次中,卷四七至四九先录“西曲(上、下)”,紧接其后,卷五十、五十一收录的则是梁代的三类歌曲:《江南弄》《上云乐》和《梁雅歌》。其中《江南弄》和《上云乐》都明言为梁武帝“改西曲”“以代西曲”(分别见二曲解题),也就是西曲歌的变体,不妨说也就是如上述《子夜游曲》一类的变歌。而《梁雅歌》无论从编排位置上还是内容上,都与之紧密相连,其性质一致的可能性很高,同样应可纳入西曲歌的谱系中理解。我们都知道梁武帝曾对乐府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革,《隋书·音乐志上》称“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爰诏凡百,各陈所闻。帝又自纠擿前违,裁成一代”。而从梁代乐府的实践看,其裁断正以西曲为一个重要的基础,这恐怕与萧衍自建武五年(29)以后便以襄阳为根据地发展势力,最终从雍州刺史任上起兵得天下有关。
最后的第五层次,则是陈隋时期的曲子,包括《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四曲。
三、相关曲目的文献批判
如上分析以后,这段材料的文本构成便清晰地呈现出来:在时代次序上,先排列周代的《白雪》古曲,其次是汉曲,其次是东晋南朝曲,最后是离唐代最近的陈隋曲。在类型上,则先排列周代琴曲,其次是汉代舞曲,其次是吴歌,再次是西曲,最后是新造曲。这实在是一套十分严整的文本秩序,绝非泛泛随手可以杂抄出来的。而在这样严格的文本秩序中,却存在着两个不合秩序之处:
一是如《旧唐书》那样将《凤将雏》插入《明君》和《明之君》中间。关于《凤将雏》,尽管《旧唐书》说是“汉世旧歌曲也”,但这一简短的说明文字背后同样存在着文本层累生成过程中的指向偏移,有必要作详细的析论。其所承袭的《通典·乐典五》原文是:
《凤将雏》,汉代旧歌曲也。应璩《百一诗》云:“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然则《凤将雏》其来久矣。特由声曲讹变,以至于此矣。
而《通典》所承袭的《宋书·乐志一》原文则是:
《凤将雏歌》者,旧曲也。应璩《百一诗》云:“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然则《凤将雏》其来久矣,将由讹变以至于此乎?
可以看到《宋书》只说是“旧曲”,以推测的语气猜想其应该发生过讹变;《通典》则凿实了这种猜测语气,并根据其所引应璩诗落实这是“汉代”旧曲。而《旧唐书》则将后半部分全部省去,仅保留了“汉世旧歌曲”这一句。然而在《宋书》的原文语境中,《凤将雏》却是作为“吴歌杂曲”中的一曲来叙述的。体味沈约的叙述脉络,他实际上是基于“吴歌”的认识立场,对其中有点特别的一曲做了一个小考证,借助应璩此诗推断其应为旧曲。换言之,“旧曲”并不是沈约本来就有的知识,而是他的个人判断。可知在江左人物对乐府的一般认知里,《凤将雏》乃是不折不扣的吴歌。正是为了调和这种“常识”和“新知”之间的矛盾,沈约才猜想其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发生过讹变。
而这一文脉到了《通典》中,却开始发生扭曲,引导读者往“汉曲”的方向理解这一曲。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宋书·乐志》和《通典·乐典五》的叙事结构有所了解。《宋书·乐志一》先分为歌、舞、乐三大块总述音乐史,接下去的《乐志》二至四才抄录郊祀宗庙、相和、舞曲等各种曲辞。因此,《宋书》虽然在《宋志一》中就抄录了吴歌曲目,但却并未录其曲辞;相对地,相和歌辞则是放在《乐志三》中抄录的,两者清楚区隔。而《通典·乐典五》则是专题性地论述歌、舞,不另立抄录歌辞的章节,故在歌的部分将《宋志》中对相和歌和吴歌的说明文字抄在了一起,随后再抄录吴歌、西曲的各种曲目。不论杜佑本人对古歌曲的理解如何,这种处理方式都非常容易模糊各种歌曲的种类边界。然而杜佑却调整了叙述的结构,将《宋书》叙述相和歌和吴歌的两段抄在了一起,然后再列举各种曲目。在列举的曲目中,尽管先“吴歌”而后“西曲”,但两者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分割说明。这么一来,不论杜佑本人的理解如何,读者都很容易模糊所抄各种曲子的边界。在《宋书》所述吴歌十一曲中,《凤将雏》排在《子夜歌》后面,居第二位;而在《通典》中,《凤将雏》却排到了首位,然后才是晋代的《碧玉歌》《懊侬歌》《子夜歌》等,这种排列也有着强调《凤将雏》时代更早的效果。在这样书写调整后,《凤将雏》作为“吴歌”的存在感就大为削弱,而作为汉曲的一面则得到强调。《旧唐书》编者会因而只抄《凤将雏》为“汉世旧歌曲”的部分,而将后面部分全部省略,是不难理解的(或许他们也就是在这种认知下,将这一“汉曲”放进了“三十二曲”的汉曲序列中)。然而在作为隋唐清乐前身的江南乐府中,《凤将雏》却是吴歌而非汉曲,这种混入就导致在高度一致的秩序中忽然出现了无序的现象,从而露出破绽了。当然,《凤将雏》不是舞曲,这一点本身也是与文本层次格格不入的。而如果将《明君》和《明之君》理解为《鼙舞歌》的两篇,那么就更没有理由在中间插入一个其他曲目了。王运熙先生的判断,由此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确证。
违背秩序的第二点,则在于《骁壶》进入了文本的第四层次亦即西曲序列中。如前所言,杜佑将《骁壶》解释为隋炀帝所造《投壶乐》,当然应该属于第五层次的陈隋新曲才对。这一点,还无法得到妥善的解释,只能推测可能存在文本次序的颠乱。不过,《乐典五》在列举曲目时,遵循的是与“三十二曲”文本相同的次序:先抄吴歌,次抄西曲,最后抄陈隋曲。这暗示着他在撰写这两个部分时,可能根据的是相同来源的资料。而《骁壶》正位居陈后主所造“《玉树后庭花》《堂堂》《黄鹂留》《金钗两臂垂》”和隋炀帝所造“《泛龙舟》”等之间,完美地符合文本秩序。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在“三十二曲”中,《骁壶》的位置原本可能也是在《泛龙舟》之前,位居倒数第二的。
四、“三十二曲”的曲目考定
以上我们已经借助对“三十二曲”的文本分析,厘清了各种文献间差异形成的脉络,并论定其是非。那么现在就应该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了:究竟这“三十二曲”是哪些曲目呢?
在认定《凤将雏》为羼入,应予排除;《子夜》《吴声四时歌》《阿子》《欢闻》《雅歌》《骁壶》应当分为六曲后,还剩下的一个问题是:“三洲采桑”究竟应点为一曲还是二曲?如果是一曲,那么我们按照现有的标点方式,将会点出三十三曲,这也就意味着,必定还有一种曲目被我们错误地分割成两曲。而如果是两曲,那么被错误分割的曲目就多达两种。然而如前所论,文献所载各曲的源流已经条分缕析,一清二楚,又哪里还存在这样的误解可能呢?
前引王运熙先生关于“三洲采桑”可能合为一曲的意见,正给了我们通往最终答案的重要线索。尽管王先生和《通典》点校者可能都只是基于“凑数”才这样处理,但选择“三洲采桑”而非其他曲目进行“凑数”,却也有其理路,即《通典·乐典五》:
《三洲歌》者,诸商客数由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又因《三洲》曲而作《采桑》。
遗憾的是如前所述,王先生因为所据的《通典》版本将“阿子欢闻”误刻为“阿子歌”,于是在合并《三洲采桑》后便满足了“三十二曲”之数,故不再继续推求了。其实顺着这个思路,我们立刻便能发现另一组完全相同的关系:
《石城乐》,宋臧质所作也。……《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谣,且《石城乐》中有“忘愁”声,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
答案可谓呼之欲出。如果承认“三洲”“采桑”因为含有衍生关系而应该点为一曲,那么同构的“石城”“莫愁”又焉能独外呢?——由此我们还可以对这类问题提出一点方法论上的思考:尽管凑数字是一个必然的方法,但仅仅将数目凑得巧并不足够,而且还要理路通贯,消解内在矛盾,我们才可确信已寻找到了真正的答案。
关于这两组乐曲的同构关系,还可以补充提出另一个佐证。《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中有一段记载,虽未明言曲数,但文意则与此高度对应:
隋亡,清乐散缺,存者才六十三曲。其后传者:《平调》《清调》,周《房中乐》遗声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汉舞也;《巴渝》,汉高帝命工人作也;《明君》,汉元帝时作也;《明之君》,汉《鞞舞》曲也;《铎舞》,汉曲也;《白鸠》,吴《拂舞》曲也;《白纻》,吴舞也;《子夜》,晋曲也;《前溪》,晋车骑将军沈珫作也;《团扇》,晋王珉歌也;《懊侬》,晋隆安初谣也;《长史变》,晋司徒左长史王廞作也;《丁督护》,晋、宋间曲也;《读曲》,宋人为彭城王义康作也;《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作也;《石城》,宋臧质作也;《莫愁》,《石城乐》所出也;《襄阳》,宋随王诞作也;《乌夜飞》,宋沈攸之作也;《估客乐》,齐武帝作也;《杨叛》,北齐歌也;《骁壶》,投壶乐也;《常林欢》,宋、梁间曲也;《三洲》,商人歌也;《采桑》,《三洲曲》所出也;《玉树后庭花》《堂堂》,陈后主作也;《泛龙舟》,随炀帝作也。又有《吴声四时歌》《雅歌》《上林》《凤雏》《平折》《命啸》等曲,其声与其辞皆讹失,十不传其一二。
总体来说,《新唐书》的这份材料是无法用作依据的,因为尽管这份曲目看起来和《旧唐书》十分相似,包括前列三十余曲,后列“又”数曲的结构都高度一致;然而其内部却有着显著的差异——丢掉了“阿子及欢闻”,又把《吴声四时歌》和《雅歌》放到“又有”后面,反而将《平调》《清调》挪到了前头,实际上是对原始材料进行了颠三倒四的改造。但是,作为宋人的编撰产物,其中又显然保留了一些珍贵的正确信息,有助于考证。例如在“三十二曲”的对应部分就没有收录羼入的《凤将雏》,又如《前溪歌》的作者,早期文献包括《宋书·乐志一》、北宋本《通典·乐典五》等都已讹为“沈玩”,而此处仍为正确的“沈珫”。可见史料的价值不可一言以概之,即使劣质材料亦可披沙拣金。而其中关于《石城》等几曲的部分,正作:
《石城》,宋臧质作也;《莫愁》,《石城乐》所出也……《三洲》,商人歌也;《采桑》,《三洲曲》所出也……
这种完全一致的表述方式,就比其他文献更清楚地传达出这两组乐曲之间的同构性。与前论合观,《莫愁》和《采桑》在这批曲目中的特殊性可谓凸显无遗。
综上考论,本文的最终结论是:清乐在唐代杜佑时所存的“三十二曲”当为《白雪》《公莫》《巴渝》《明君》《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欢闻》《团扇》《懊憹》《长史变》《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叛》《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
注释:
④王运熙:《乐府诗述论》,《王运熙文集》(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
⑤按这个“及”字十分突兀,恐怕是从《宋书·乐志一》“阿子及欢闻歌者”云云的行文中粘连过来的。
⑥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0-421页。
⑧《乐府诗集》卷五三“舞曲歌辞二”“杂舞一”解题:“汉、魏已后,并以鞞、铎、巾、拂四舞,用之宴飨。”(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