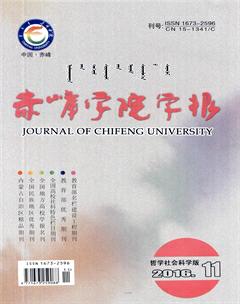论《嘹歌·日歌》与《圣经·雅歌》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覃丹
摘 要:中国壮族的《嘹歌·日歌》和犹太民族的《圣经·雅歌》都因其对爱情的出色描写而成为各自民族文苑中灿然绽放的奇葩。通过对这两首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两位女主角都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她们对“他者”地位的打破和自我幸福的勇敢追求。
关键词:《日歌》;《雅歌》;女性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42-03
《日歌》是壮族民间歌谣精品“嘹歌”的重要作品,它描述的是一对分别被父母包办婚姻的壮族男女为了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而勇敢抗争,历经艰难后终成眷属。《雅歌》(The Song of Solomon)是《圣经·旧约》中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经卷,它由民间流传的数十首情歌汇集而成,生动地描述了一对希伯来年轻男女对爱情和幸福的大胆而执着的追求。千百年来,这两首民歌都因其对爱情的出色描写而成为各自民族文苑中灿然绽放的奇葩,成为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汲取不尽的甘泉。
《日歌》全歌共1458首5832行,《雅歌》共8首117行,都是男女对唱的方式,《日歌》是男女平分秋色各唱一半,而《雅歌》则是女子唱17次,男子唱10次,还有众人唱5次。显而易见,无论是《日歌》还是《雅歌》,女性在其中都是绝对的主角,她们用自己的声音和言语抒发着自己的情感和追求。因此,这两首歌中的女性主体意识都是不容忽视的。
一、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者”地位的打破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主体性是主体意识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主体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观念表现[1]。在此意义上,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表现出的是女性独立自主、自强自重的精神气质。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主体意识一直被有目的地压抑和遮蔽,就如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艾琳·希苏所言,父权社会消音了女性的话语,女性被剥夺了表达的能力,处于失语状态,她们没有表达自我的能动性,没有自己真正的话语权,是被言说的“他者”[2]。
所谓“他者”,西蒙娜·波伏娃对其的界定采纳了黑格尔的观点:“他者意识是一种依附意识,对于他来说,本质的现实就是那种动物型的生命;就是说,是另一种存在所给予的一种生存模式。”[3]而女性的他者或客体地位就表现在对男性的依附上,这种依附性就是女性并未高扬其主体意识,进行自我设计,而是受传统对于男性女性地位的界定。但在《雅歌》里,这种格局明显被打破了。女主角书拉密女在整首诗中一直处于主体地位,她有血有肉、有胆有识、热情奔放,勇敢地表达着自己的欲求,是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主动者。她对自己充满自信:“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①基达的帐篷是用黑山羊毛编织而成,所罗门王的幔子自然也是高级布料制成,她把自己比喻为“基达的帐篷”“所罗门的幔子”,说明她认为自己虽然黑,可却仍然是高贵美丽而有着独特的风采。在与男主角的爱情中也是积极主动,一开始就主动表达了她渴望男主角的亲吻和爱情:“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然后主动追求男主角,请他告诉自己在何处放羊,以便她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去找他约会:“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还直率而骄傲跟男主角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葡萄园”比喻她自己,“狐狸”比喻其他追求她的人,在这里,她聪明地运用古老格言鼓励男主角守护他们之间的爱情,因为爱情不是这样理所当然的,是需要他花心力去培植的,而且还有其他的竞争者在,所以他更要关注这爱情的发展。直至她发出“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简直就是她在这场爱情中主体地位的宣告:她和男主角一样都是生活的主体,没有主客体之分,他们之间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的互相隶属的关系。
相对于《雅歌》书拉密女的热情奔放,《日歌》中的女子似乎含蓄内敛许多,但在选择生活道路的主动性上,她却丝毫不逊色于书拉密女。在与男主角邂逅后,她即试探男主角对自己是否仍然有感情:“想跨定能跨,胆大就有路;路有刺就有,有条能通妹”;“爬山去岩洞,跨洞去找菲;菲不如姜辣,哥不恋我就难堪”;“哥想去套鸟,不怕碰寒旦;寒旦鸟也飞,你爱就来玩”[4]。在试探明白双方彼此恋情依旧、爱心依然之后,她做了大胆表白,“古时不造泉,泉四路不通;拿刀去砍路,就能通情哥”;“古时不造渠,水引不到此;用溪水灌田,不恋就枉过”;“从小学交友,不怕成叫花;哪天过铜桥,②跟兄一起过”[5]。两人决定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而重拾旧爱后,她又主动赠送定情物:“送给哥件衣,不是当寿衣;送给哥双鞋,想跟你一辈”;“送给哥条裤,让你永不忘;送给哥条裙,想快乐一辈”[6];“送哥这张巾,拧绞成墨线;墨线弹板上,誓言永不悔”[7];这样的主动大胆可说是和书拉密女如出一辙,完全颠覆了父权社会的规范,大大有别于性别社会化中女性被动的、压抑的、服从的角色特征,已经不再只是被男性支配的客体、“他者”。
二、爱情如死亡之坚强:自我幸福的追求
女性主体意识的内涵包含两方面:一是女性处在主体的地位上,她是选择生活道路的主动者;二是肯定女性主体意识和欲望的存在[8]。换句话说,女性主体意识既是女性对其生存环境的探求与思考,也是对其人格尊严之平等与女性自由解放之个性的追求。在《日歌》和《雅歌》中,为了实现自我幸福,具有主体意识的两位女主角对爱情的追求不可不谓执着而勇敢。
中国壮族的婚姻形式基本实行的是自由恋爱和父母包办的双轨制,男女青年在婚前是有社交自由的,但双方即便情投意合,也需征求得父母同意后才能结婚,也就是所谓的“恋爱比较自由,婚姻并不自主”[9]。《日歌》中的女子年轻时与男主角在歌圩上认识并倾心相爱,最后却由于父母包办而被迫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对于那个男人,诗歌中并没有直接的描写,但从男女主角的对唱中可以知道该男子家庭是比较富裕的,“他家多富裕,当高兴才是”[10],在女子很小的时候就来提亲,“女刚刚落地,娘嚼果来喂;还在月子里,就有人来提”[11],而且八字跟女主角很相配,因为女主角因被迫跟他结婚而不能跟自己意中人结婚而发出“恨古创世人,要八字来合”[12]的愤恨。按照世俗的眼光,八字相配且男方家庭富裕可以保证女性的下半辈子过得温饱不愁、安康和睦,结这么一门亲对女性来说那绝对是完美的结局。但对于女主角来说,这个婚姻是父母强加给她的,她心中始终惦念着那个在歌圩上相恋的情哥,“不落夫家”的壮族婚姻习俗使得她可以常住娘家,可终究是要去婆家的,每次去婆家对她来说都是煎熬:“头回去婆家,扁担丢给娘;娘送女下楼,想到哥就回”;“二回去婆家,似断尾蜻蜓;频频展翅去,想念哥就回”;“三回去婆家,柑树下梳头;饭不吃一口,站门口叹气”;“四回去婆家,日哭四五回;回回都昏死,问卜才知是为哥”;“五回去婆家,抛把秧下田;每想念到哥,泪水没过秧”;“六回去婆家,到竹林去坐;自坐自叹息,趁圩盼遇哥”[13]。她执着的思念终于等来了他们歌圩上的重遇,两人互表心迹并决定重合后,为了追求爱情,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敢:“人说由他说,我们照样住;照样住安稳,怕他做什么”;“人论由他论,咱照往田里运肥;使坏由他使,咱仍相好一辈子”[14]。尤其在他们的恋情受到众人非议,遭到家人辱骂,甚至被村人送官问罪,戴枷游街示众后,她为了爱情视死如归的勇气更是令人震撼,“说当场发觉,捉拿去游街;官连声说杀,刀架脖不怕”;“越骂越不怕,像蜘蛛淌水;父母砍手脚,死了也无怨”;“越骂越不悔,刀割耳朵也不听;舍命跟你去,没有哪样舍不下”[15]。这种为了爱情决然的勇气最终给她带来了她想要的幸福生活,“沙棘丛连丛,错节又盘根;咱得配夫妻,心似牡丹花”;“咱得配夫妻,喝茶相递瓢;你递给我我给你,有说又有笑”;“咱相恋结合,稳固像山岗;像满山茅草,相爱到永远”[16]。
犹太民族认为婚姻的意义既在于生儿育女,也在于满足爱情和性生活欲望的理想途径,因而非常重视婚姻中的夫妇之爱[17]。也因此,与《日歌》中的女主角相比,《雅歌》中的书拉密女从一开始就能执着地追求她心中所爱,并表达了与男主角长相厮守的愿望:“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哪哒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常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我的哪哒香膏指的是男主角,没药和凤仙花都是香料,隐基底葡萄园则比喻她自己,在这里,她用香气来暗示了他们两人相依相伴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大胆说出她的爱,并从心里发出对对方的召唤,其中不乏赤裸裸的性暗示:“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我的良人哪,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椽子”;“北风阿,兴起。南风阿,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尤为可贵的是,为了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她敢于蔑视权贵,反抗强权,面对拥有无上权力的所罗门王花团锦簇的轿子、豪华气派的婚礼以及数不尽的钱财的诱惑,她无动于衷,可为了寻找自己的平民爱人却不惜冒着名誉受损、生命受到威胁的危险:“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她的执着勇敢终究也给她带来了她想要的幸福生活,还有男主角甜蜜的爱情:“我妹子,我新妇,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炼,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新妇,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過一切香品!我新妇,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
由上可见,《日歌》中的女主角和《雅歌》中的书拉密女在爱情的追求上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勇敢无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而书拉密女最后发出的“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爱情誓言可以说既是爱情的千古绝唱,也是对她们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的颂歌。
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男性和女性之间基本上表现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在主体与客体、塑造者与被塑者、观看者与被看者、再现者与被现者等对立的双方中,男性永远代表着前者,女性则永远代表着后者。但在《日歌》和《雅歌》中,两位女主角能够站在主体的位置,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坚决、果敢,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得不说她们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使她们摆脱了充当男性凝视的客体对象的地位,不再物化为男性观看的对象,而是与男性一起成为掌握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体。
注 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圣经·雅歌》内容均出自和合本。
②铜桥:传说中人死以后其灵魂赴阴间途中必需经过的十二座铜质桥梁。
参考文献:
〔1〕金炳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186.
〔2〕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4.
〔3〕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60.
〔4〕〔5〕〔6〕〔7〕〔10〕〔11〕〔12〕〔13〕〔14〕〔15〕〔16〕罗汉田.平果壮族嘹歌·日歌篇[M].谭绍明歌书抄本提供.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8〕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0.
〔9〕罗志发.壮族的性别平等[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35.
〔17〕贺璋瑢.历史与性别——儒家经典与《圣经》的历史与性别视域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2.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美国雅歌全球总裁Mark R upert先生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