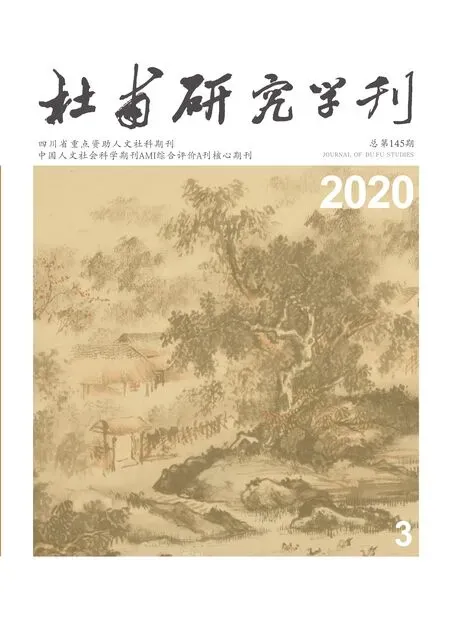唐人的乐府观与中唐诗人的乐府
[日]增田清秀 撰 樊昕 译
说到唐代的乐府,中唐是极其重要的时代,在讨论中唐乐府之前,先考察一下唐人一般所持有的乐府观。
一、唐人的乐府观
基本上,大部分的唐代诗人对乐府都有所关心,不存在不是诗人的乐府作家。正因为这样,首先,就有了他们到底是如何区别诗和乐府,并进行创作的问题。然而实际上,唐人并没有把乐府和诗之间加以特殊对待的意识。他们中除了仅有的少数诗人外①,即使同样的作者,也很少考虑音律而制作乐府,而是把乐府和诗视作一体,从和诗同一立场来制作乐府。因此,对于他们的作品,诗题自不用说,想要从体裁和内容方面来把握诗和乐府两者的区别,是很困难的。例如,在编纂唐人乐府总集时,就没有那种直观的、权宜的选择方法。这种选法有多暧昧呢?现以孟郊的作品为例证:
长安羁旅行
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三巡酒过饮②,每食唯旧贫。万物皆及时,独余不觉春。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直木有恬翼,静流无躁鳞。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野策藤竹轻,山蔬薇蕨新。潜歌归去来,事外风景真。
长安羁旅
听乐别离中,声声入幽肠。晓泪滴楚瑟,夜魂绕吴乡。几回羁旅情,梦觉残烛光。
前首是孟郊四十二岁时作为乡贡士从湖州上京城应进士试失败所作③,后首由于没有使用透露出应试的语句,虽不能断定为同时期所作,但有描写回归吴地故乡的归心这一共同点。然而,宋、元、明、清的乐府总集或孟郊别集的编者将前者取作乐府,与后者的诗相区别,理由可能就是前者的题目《长安羁旅行》,有“行”字附着其上。说起来,因为乐府就是具有将乐章与乐器伴奏歌唱性质的东西,除了作者不明的民歌之外,作家取材于人事和时事,从纯客观的立场来描写,其原则是要回避根深于作者的个人环境的主观叙述。职此之故,像孟郊《长安羁旅行》这样取材于个人世界的作品,如果进入乐府范畴的话,不得不说是一种无视乐府的本来性质的选择方法。但由于唐人并没有严密区别乐府和诗,所谓仅仅用是否有主观的理由来作判定,除此之外也不稳妥。那么,关于孟郊的这两首作品,还想再说一点就是,同样是古体诗,从形式上也难以辨别其差异,但这也不仅仅限于孟郊的诗。尽管唐人在形式方面没有对诗和乐府作实质性的区别,古体诗不用说,更多创作的是律诗和绝句这样的新形式,以及古乐府或者新乐府。从编选者的立场来看,除了选择暧昧的方法以外,就再没有适当的方法了。然而,据孟郊作品之例,尽管很暧昧,但从题目上也有选择的可能,但就《长安羁旅行》这首作品而言,却是完全无法判别其是否为乐府。另一个情况是“古意”。“古意”本来是六朝的宋、齐诗人所命名的,大概由于多用汉魏以来的乐府或古诗的形制和典故,才产生了这一名字。梁代刘孝威就有以“古体杂意”为题的作品,这一题名,应该就相当于“古体”之意吧。唐人的“古意”作品,可知有着这样的两分:即大致区别于描写作者私生活和感怀世事的所谓的一般的诗,和取材于古乐府的诗。然而,唐人有着很强烈的汉曲《燕歌行》的意识,所以在创作这类古题乐府的时候,内容就基本局限于闺怨的题材④。乔知之、吴少微、沈佺期、崔国辅、王昌龄、祖咏、李颀、崔曙、李白、阎宽、毕耀、蒋冽、耿湋、戎昱、刘商、杨巨源、陈羽、孟郊、张碧、鲍溶、段成式、李频、于濆、陆龟蒙等人乐府性质的“古意”之作,都歌咏了闺怨。所以,为了将这种“古意”之作与一般的诗歌相区别,将其改题为“怨歌行”应该没有障碍吧。唐代还有“歌行”这一术语。在选择作品的时候,是将其作为诗歌类呢,还是新题乐府呢?其归属都令人困惑。关于“歌行”的语源,历代乐府的解题者或诗歌的评论家众说纷纭。例如,有些人指出乐府题的“短歌行”“长歌行”“伤歌行”“燕歌行”这些,“歌行”都是六朝以前已经产生的语词。但此说并不正确。这些乐府题并非是短的“歌行”、长的“歌行”、燕的“歌行”、伤的“歌行”的意思,短歌之行、长歌之行,“歌”和“行”应该是截然分判的东西,尽管两者语义的差异,后世不再能说得清,但它们本来应该具有不同的意义。与此相反,唐代的“歌行”则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习语,也就是说,唐代歌行的作品,指的是在形制上限于七言长篇,且并不用拟古的乐府题来创作的诗歌。因此,即使诗题和内容相似,由于异体的原因,脱离了歌行的范畴。明人冯班在《钝吟杂录》中有一篇题为《古今乐府论》,其中所考述的歌行说,在历代诸家的说法中,我认为是比较简明又适当的,兹取如下:
至唐有七言长歌,不用乐题,直作七言,亦谓之歌行。故《文苑英华》歌行与乐府,又分两类。
照上文的理解,七言长篇是不用原题乐府歌唱的歌行。那么,这种歌行和一般的诗歌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从作者方面而言,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考虑乐章的用途,也并不期待它们能为广大的士人所歌唱。又其与乐府的关系是,在盛唐以后的诗人们创作的许多新题乐府中,把七言长篇的作品,都称为“歌行”或“乐府”这一点是相同的。
以上所揭示的唐人的乐府观中,包括以下内容,即本文所探讨的中唐诗人的乐府观,题名上的“古意”暂且不说,因形制上有“歌行”一体,内容上则侧重于个人的、主观的东西,与今天的总集或别集的编撰者一样,采用直观的、权宜的立场选出乐府的诗作,以求读者的谅解。
二、中唐的乐府作家
有唐二百八十九年,多姿多彩的乐府作家辈出,是在中唐时代的德宗贞元至宪宗元和的三十五年间。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中记述了三百九十七位诗人的逸事以及著作存佚的记述中,以卓越的乐府创作才能驰名于世的,几乎都是贞元、元和时代在世的人,即武元衡、刘商、庄南杰、姚系、张仲素、雍裕之、权德舆、长孙佐辅、鲍溶、韦楚老、李贺、李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等。这些作家中,武元衡虽然并不是勤于制作乐府的人,但他的五言诗却被好事者谱为乐章,用丝竹伴奏歌唱。刘商的乐府被称为高雅殊绝,其与董庭兰原作同题的《胡笳十八拍》为全天下的儿童妇女所传唱。庄南杰现存的乐府虽只有《湘弦曲》《黄雀行》《雁门太守行》《阳春曲》《伤歌行》五篇,但当时他的歌体却被认为和早逝的前辈李贺有着相似的特色。姚系虽然也仅残存有一篇《古别离》,当时他以鼓琴名手而知名,巧于制作古调的诗歌。张仲素燃烧创作热情,协和宫商乐律,发挥古人都难以企及的才能。雍裕之和权德舆都作有情趣丰厚的乐府。对长孙佐辅,《唐才子传》有着“每见其拟古乐府数篇,极怨慕伤感之心,如水中月,如镜中相,言可尽而理无穷也”的评价,现存有《拟古咏河边枯树》《古宫怨》《关山月》《陇西行》《对镜吟》五篇。鲍溶以古诗和乐府独步于世,在《陇头水》中歌咏有“陇头水,千古不堪闻。生归苏属国,死别李将军。细响风凋草,清哀雁入云”的秀句。韦楚老是稍迟于元和时期的作家,创作了很多好的古乐府,但只残存有《祖陇行》一篇。以上根据《唐才子传》,对从武元衡到韦楚老,虽只作了极为简单的介绍,但可判断出作为那个时代的风潮,诗人间制作乐府十分旺盛的事实。因此如果无视这些人的话,就无法讨论当时的乐府。但遗憾的是,由于他们中的多数行迹不详的原因,除了权德舆外,其他残存的乐府作品也很少,尝试对其公正评价并不容易。不得已只好省略他们,而特别揭出一般被认为是做出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的李贺、李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六人,以及柳宗元、韩愈二人,试图揭示他们各自的乐府作品,取得了怎样独一无二的成绩。
三、李贺与李益
自李贺出生的德宗贞元七年(791)的四五十年以前,进行宫廷音乐改革的玄宗,为了成立立、坐二部伎和太常四部乐,偏重的是胡曲这种新曲,而不顾魏晋以来的清商曲也就是古乐府。因此,与宫廷音乐绝缘了的古乐府,便被李白等民间诗人重新拾起,选取其诗题而在文坛产生出的新诗体,但这种诗体并不一定成为歌唱的对象,仅仅是为了满足诗人创作的欲望而产生的作品⑤。然而由于李贺的出现,某类古乐府得到了卷土重来到音乐界的机会。因此在乐府史上,不得不给予李贺的业绩以很高的评价。据新、旧《唐书》本传,李贺制作数十篇的乐府,被云韶也就是内教坊的乐工们采用,伴以管弦讽诵。李贺的音乐才能得到了上司的认可,短期担任过太常寺协律郎一职。但这一工作,与他的作品被广为传唱的事实相比,在音乐业绩这一点上,简直有着云泥之别。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记载李贺七岁时创作的长短句的歌辞,其名声已传扬到都城长安。若是如此,直到二十七岁时死去,他的作歌生涯恰好有二十年。这期间,他所制作的乐府中,为内教坊乐工所演奏的作品的数量,或许太少了些。尽管如此,在任协律郎或奉礼郎的下级官吏时,有相当数量的歌辞经伶人之手而作曲,沐浴着为天子所知的光荣这样的事例,限于史书传记,李贺和他的宗族李益以外,还没有见到其他的人。往日著名的诗人中,魏时曹植创作的乐府,今天可知的歌题已超过了七十曲,晋代陆机也有三十五曲。即便如此,除了曹植的《箜篌引》《怨诗行》《鼙舞歌》以外,两者的乐府很可能都没有被歌唱。《文心雕龙·乐府篇》中云:
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
没有被伶人用丝管伴奏的曹植、陆机的乐府,就被俗称作“乖调”。乖调就是和笛律、弦律以及钟律不相协和之意,即使曹植、陆机的歌辞技法如何显著,如果不适合器乐和声乐的话,那可能就丧失了作歌的意义。然而对于李贺,也有否认其作被歌唱的事实的唐人,他就是在李贺去世的两年前,即元和十年(815)及第的沈亚之。他在《送李膠秀才序》一文中,批评李贺作歌说:“故友李贺,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亦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终亦不备声弦唱。贺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后学争效贺,相与缀裁其字句,以媒取价。”对李贺的乐府没有用声乐和器乐来付予声歌弦唱表示了惋惜。然而宋代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一中对沈文提出了疑问,认为史书中李贺的传记也好,李益的传记也罢,都重复记载了李贺的乐府被声乐歌唱的事情,因此否认了沈的说法,认为其说不符合事实。沈亚之和李贺是同时代的人,李贺元和七年(812)作有《送沈亚之歌》,尽管他们是诗友,相比于七岁就已经歌名在外的李贺,沈亚之的说法大概是不正确的。又沈亚之所说的“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也可能不对。李贺残存的二百四十四首——据《唐才子传》,这个数字只是实际作品数量的十分之四,虽不过五成,但也要比能见到的南北朝,更不用说是汉魏的乐府故题的古曲要多了。
李贺的作品中,今天能够确认有被歌唱事实的是《申胡子觱篥歌》《花游曲》和琴曲《渌水词》三首。《申胡子觱篥歌》据自序,乃是在长安崇义里与朔北客李氏痛饮时创作的即兴之歌。“申胡子”是叫李氏的苍头,以“颜热感君酒,含嚼芦中声”开头的这首五言十六句的歌诗,按歌题,描写的是苍头申胡子在酒席上吹奏觱篥的场面。明代唐顺之《荆川稗编》卷四十二云“《申胡子觱篥歌》亦五言,当时工师,尚能于席间裁为平调奏之”,这虽是明代人的记录,但可能写的就是唐代当时乐人们在酒席间,为了与平调协和,吹奏了这首歌诗。《花游曲》据自序,也是即兴之歌。这首歌曲是在寒食之日,作者与诸王的家妓在游宴席中,和家妓一同弦歌创作的。五言八句的歌辞中,由于歌咏“烟湿愁车重,红油覆画衣。舞裙香不暖,酒色上来迟”,可能写的是在微寒的细雨中歌舞饮酒的愉快。琴曲《渌水》本来是汉曲《蔡氏五弄》中的一首名曲,其旋律在唐代尚能弹奏。李贺新作的歌辞也被后世的琴曲家所选取,明代谢琳的《太古遗音》、黄士达的《太古遗音》及朱厚爝的《风宣玄品》等琴书也都著录有明代演奏的一段宫调:
今宵好风月,阿侯在何处。为有倾人色⑥,翻成足愁苦。东湖采莲叶,南湖拔蒲根。未持寄小姑,且持感愁魂。
据以上歌辞,写的是在美好的风月下,其人漂泊湖边,用采莲和拔蒲根来慰藉心中不堪忍受的愁苦。沈亚之所谓的“怨郁凄艳之句多”,大概指的就是这首《渌水词》中的歌句吧。
李贺在世时,内教坊伴以弦管讽诵的数十篇乐府,指的是他作品中的哪几篇呢?现存作品中比较多的是以古乐府为主题的,诗友沈亚之所说的“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我对此也没有犹豫,也作出了他以古乐府为主题的作品比较多的类似判断。即以汉短篇铙歌主题的有《艾如张》《上之回》《巫山高》《将进酒》《有所思》,作品在语句构成方面凝聚了功夫,借用了这些古乐府的题目,歌唱的正是北周以来的事件。还有来自汉魏歌曲的《箜篌引》《江南曲》《日出行》《蜀国弦》《铜雀妓》《长歌续短歌》《猛虎行》《难忘曲》《塘上行》《安乐宫》《雁门太守行》,来自六朝歌曲的《神弦曲》《莫愁曲》《大堤曲》《江南弄》《上云乐》《夜坐吟》《摩多楼子》《堂堂》《苏小小歌》,以古琴曲主题的有《湘妃》《走马引》《渌水词》,《公莫舞歌》《拂舞歌》《浩歌》《神仙曲》《少年乐》这些也是古曲名。他刻意从《拂舞歌》的古辞中寻找并为自己的作品命名的《后园凿井歌》,又从魏鼙舞歌中挑出了《章和二年中》为自己作品的题目,或者袭用《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公莫舞歌》这些古谣古歌,可见他对于古乐府的执着心是何等强烈。这其中,《公莫舞歌》据序文,因是“《公莫舞歌》者,咏项伯翼蔽刘沛公也。……且南北乐府率有歌引,贺陋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大概是期望在唐代复活这一古舞吧。李贺既是诗人同时也是歌手。七岁时就作有长短句的歌辞博得声名的他,一定对音律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觉。他每创作一篇歌辞时,都要考虑其是否能协和音律,即注意应该避免陷入所谓的“乖调”。他古乐府的歌辞与新题的歌辞相比,长短错杂,多有律动变化的句子。他的古乐府创作,表现的是完全为想要再一次赋予音乐以生命的意识所强烈地驱动吧。
李益在贞元末年,与李贺一样声名驰著,他每作一篇歌辞,便被教坊乐工采购去,享有上闻德宗的荣誉。新、旧《唐书》本传记载了他的事迹。然而他的被歌唱的作品,相比于乐府的诗歌,基本都是在行军露营场合下制作的。他亲手编辑了从建中到贞元的十八年间创作的《从军诗》五十首,赠送给了左补阙卢景亮,添加了“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或因军中酒酣,时或塞上兵寝,拔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乎慷慨意气,武毅犷厉”一段序文⑦,吐露了作诗的心境。又《唐才子传》载其“二十三受策秩,从军十年,运筹决胜,尤其所长。往往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故多抑扬激厉悲离之作,高适、岑参之流也”。但他的作品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一诗传唱满天下,《征人早行篇》诗被喜爱的好事者们竟然画在了屏风上⑧。那么为当时人如此好尚的理由是什么呢?换言之,李益的作品究竟在哪些方面捕获了时人的心呢?我举两点意见。第一,李益发挥了作为诗人的本领,所写的从军诗完全是自己的体验。他在军营中度过了自己最好的壮年时代,诗中洋溢着横槊握剑、感怀军事。因此,他耳濡目染的风物,主要就是边塞的风月和鸣响在沙漠中的鼓、角、笛、笳的军乐声。这种环境自然和他所采用的手法,即富于紧迫感和生动性的表现,博得了当时人们的共鸣,以至于被歌唱。这一点,可从当时传闻李贺、李益两人的歌诗,每作成一篇就被人广为传唱所推论出来。李贺的歌诗喜欢描写富于超现实的怪奇的场景,追求的是极端的梦幻和浪漫。与之相对,李益则予现实以冷静的凝视,重视的是将彻底的亲身体验用平淡的笔调写出。他们这种两极的、截然相反的作品,不正大大唤起了时人心中的兴味吗?前揭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征人早行篇》都是军中体验之诗。
李益被时人喜爱的第二个理由是他的从军诗,与其他诗人相比,难道不是因为他具备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的缘故吗?这种风格,就是他所说的慷慨、意气、武毅、犷厉。他绝不写悲观的战况,也不流露出退缩保守的感情。被全天下传唱的《夜上受降城闻笛》歌咏“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此诗和同一旨趣的《从军北征》中的“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都写笛声引起了征人的归乡之心和哀伤之情,这些诗,并不要误会他对从军很是憎恶,实则暗示的是他的反战意识。在他的从军诗中,洋溢的是男子汉的精神。《赴邠宁留别》歌咏“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侠少何相问,从来事不平。黄云断朔吹,白雪拥沙城。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束发即成人后就口不离谈兵的他,燃烧的是横戈朔野、一心博取功名的欲望。现存的作品中,没有一篇是他用旁观或回顾的角度来直叙悲惨的战场的。基本上,他的从军诗都是心情开朗的,没有那种阴暗的倾向。以下所举同题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之作,由于恼人的边地归乡之心而毫不隐瞒地抒发出沉溺于胸中的哀愁,我认为不是李益的作品。一说为戎昱所作,或较为妥当。
入夜思归⑨切,笛声清更哀。愁人不愿听,自到枕前来。风起寒云断,夜深关月开。平明独惆怅,落尽一庭梅。
以上我关于李益的作品投合时人好尚的理由的论述,除此以外,我认为当时还有欢迎从军诗的社会事件,但这一点并不清楚。那么,尽管李益和李贺并称,但他并没有李贺那样的音乐才能,而他大半作品也没有以古乐府为题,只是记录了从军体验的诗,然而,他的从军诗变成了乐章,以至于为宫廷声歌弦唱这一点,应该也大受过欢迎吧。
四、白居易与元稹
白居易与元稹也制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即白的新乐府五十首及元的新题乐府二十首、古题乐府十九首。而这些作品的每一首都诱发了相和并制作当时流行的乐府的风潮,而且,这一风潮是仅见于元和时代的特殊现象。这里将不限元、白二人,考述相和乐府的实际状况。在乐府史上,引起相和风潮的时代有两次,先于贞元、元和时代的,是六朝的齐代永明年间到梁朝之世。限于文献所见,乐府的相和始于齐武帝永明八年(490),出仕随郡王子隆的谢朓,大约在转任镇西功曹文学一职时,滞留京师,与沈约、范云、王融、刘绘等人会聚一堂,制作《芳树》《将进酒》《临高台》《巫山高》《有所思》等鼓吹诸曲各一首。那么,在这种多数人同席制作的场合,会使用“同”这一词。然而,齐永明年间的作品中,因在熟人之间相和的同样的歌题,除了用“同”外,同时还使用“和”这一词,所以这两个词完全是一样的。如谢朓的《同谢咨议咏铜爵台》《同王主簿有所思》,王融的《和南海王殿下咏秋胡妻》也是如此。梁代君臣间的乐府相和,在梁简文帝、元帝、刘孝威、江洪等相和的歌曲中,今天可知其歌题的仅有《折杨柳》《洛阳道》《紫骝马》《从军行》《爱妾换马》《采菱曲》《渌水曲》《秋风曲》《胡笳曲》《燕歌行》《婕妤怨》《班婕妤》等。但是,相和的两曲中,除了原为梁臣的王褒的《燕歌行》及元帝的《班婕妤》及其相和的梁人之作外,仅有一方的曲辞残存。
贞元、元和时代的乐府同好者在相和之时,会受到当时诗坛所流行的和韵,即依韵、用韵、次韵等押韵上的影响。但作者却不受这些约束。而且,虽然和韵之诗多少夹杂了触及两者之间境遇的语句,或者插入有表达抒情的句子,但在相和乐府的场合,基本很少言及私生活,只是在熟人之间相和同题的歌曲,除了共同爱好的歌曲以外,也不再去互相求得什么。然而,从这个时代多数留存的诗人作品中,挑选出相和的曲辞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歌曲的序和歌题中,没有能够实际证明其是相和歌辞的记载,那么就无法判定了。例如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二十首,不管是否是对李绅所作的作品的相和,白的《新乐府》之序也没有记载过这一旨意。又,相和作品虽然也有歌题,但不能将其看作是新题乐府,让人迷惑不已是否应该与诗区别开来,古乐府和新题乐府有着识别上的暧昧的情况。比如元稹的古题乐府十九篇中,十首相和刘猛⑩之作中,有《梦上天》《采珠行》《忆远曲》《夫远征》《织妇词》《田家词》六首是新题乐府;又相和李馀之作的九首中,有《君莫非》《田野狐兔行》《人道短》《捉捕歌》《苦乐相倚曲》五首也是新题乐府。尽管如此,却不见元稹自己作有古乐府:
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馀,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元稹《乐府古题序》)
目前列举能够确定是相和的作品,代宗之世有独孤及《太行苦热行》和作一首、卢纶《塞上曲》和作六首,贞元之后,有羊士谔相和李经的《宫人斜》。此歌可能是悲痛于当时死去的有名的宫女而作。羊之外,权德舆、王建、雍裕之等也有和作。当时,权德舆相和张某有《朝天行》,他自己所作的《离合诗》,张荐、崔邠、杨於陵、许孟容、冯伉、潘孟阳、武少仪等人都有相和。“离合诗”,唐人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云“起汉孔融,离合其字以成文”,即所谓的离合体,是一种文字上的游戏。杨巨源在当时也作有相和练某的《折杨柳》,孟郊也作《湘弦怨》赠送给卢虔,时因收到卢虔寄来的和作,再次酬作《楚竹吟》,歌题即作“楚竹吟 酬卢虔端公见和湘弦怨”。孟郊还与丁某相和,作有《塞上吟》。然而以上所举的这些作品,在相和的两方中,另一方的作品已不存。幸运的是,皇甫冉和李端的相和、孟郊和陆长源的相和,双方的两篇歌辞都见存,可以一窥相和作品的内容,兹列举供参考:
巫山高
皇甫冉
巫峡见巴东,(平,东韵)迢迢半出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
巫山高和皇甫拾遗
李端
巫山十二峰,(平,东韵)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过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望,清秋见楚宫。
乐府戏赠陆大夫十二丈(三首之一)
孟郊
绿萍与荷叶,同此一水中。(平,东韵)风吹荷叶在,绿萍复西东。
乐府答孟东野戏赠
陆长源
芙蓉初出水,菡萏露中花。(平,东韵)风吹着枯木,无奈值空槎。
以上孟、陆之作,不算戏赠作品的佳例,但皇甫、李之作则应当做相和曲的范例予以关注,即李端所作的语句与和韵(首句的“峰”与其后“中”“风”“空”“宫”同韵),内容上更是对皇甫冉先作的追和。当时像皇甫冉、李端这样相和乐府的人可能还很多吧。但是,元稹和白居易没有偏重于原作,元稹从刘猛和李馀的数十首古乐府中挑选出十九首,在和作时“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是也。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词》先蝼蚁之类是也”,夸示他的和作表现了刘、李原作所没有的新奇的设想和手法。元稹在制作此新题乐府以及白居易制作新乐府时,都袭用了李绅的原作,歌题就表现了讽刺。李绅的新题乐府二十首已全部亡佚,但都是为了讽刺时事而作的,可由元稹作品《立部伎》的题注,以及《缚戎人》的题注中得知。
受到当时相和乐府风潮的诱发,相对于从比较自由的立场来制作的元、白各乐府,我们应该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我大概的看法是,白居易的新乐府给予了新题乐府应该具备的条件。即新题乐府不止名作乐府,可以说也具有了乐章的性格,这就是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所说的“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但是,元、白二人在同一年即元和四年(809)所创作的新题乐府,这一点却表现的不是很明显。虽然如此,他晚八年制作的古题乐府十九篇,实际上过半都是新题的乐府,从这些作品的序和语句构成上就能承认,他们也具有乐章的性格。大约有意将时事作为素材进行讽刺,尤其是用诅咒的口吻批判实行恶政的官吏,这是盛唐以来普遍的倾向。但是,很少有诗人在元、白之前赋予歌辞以乐章的性格。元稹自己在《乐府古题序》中,把杜甫说成像是新乐府的创始者,在序中举出他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是否也期待杜甫将制作出的乐章付予歌唱呢?这一点是很可怀疑的。根据前揭所谓的唐人并没有严密区分诗歌和乐府的观点,我虽未必要否认这个见解,但在元、白之前,如果要找寻在制作时便期待付予歌唱,尝试讽刺时事的人,与其说是杜甫,不如说是元结吧,那就是元结的《系乐府》十二首。然而,元结此作乃是他无官位且在商馀山中隐居时候所作,由于缺乏对世事的体验,《颂东夷》《寿翁兴》等计十二首歌题,虽也下了功夫,但在歌辞中表现的感慨很浅薄,讽刺的效果也失于贫弱,因此才被元稹无视吧!从以上的见解来看,可以断言,赋予新题乐府与古乐府同样乐章性格的人,就是元稹和白居易。然而,在上述史料评价之外,元、白乐府与当时张籍、王建的乐府相比,可指出的不同点是,元稹制作的是只可诵读而不能成为歌唱对象的乐府,从中也可见出和白居易一样的讽刺态度。元稹的这一作品指的是人道无穷说的《人道短》,关于以“古道天道长,人道短,我道天道短,人道长”之句开头的长篇乐府,近人陈寅恪已在《古题乐府》中,考述乃是受到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的影响。辞中“留得孝顺语,千年万岁父子不敢相灭亡。没后千余载,唐家天子封作文宣王。老君留得五千字,子孙万万称圣唐,谥作玄元帝,魂魄坐天堂”,引出孔子、老子来论证之所以长久,是乐府史上稀见的尝试。又白居易在为《新乐府》五十首的总结《采诗官》中说“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从谏官的立场上讲诉了作歌的意图。但当时他将自己置于与为政者同等的地位,是向天下万民垂示训诫。例如《天可度》憎恨时人之口多虚言,《盐商妇》表达了对通过不正当的利益所得而过上奢华生活的盐商之妻的厌恶,《井底引银瓶》对妄想与异性私奔的妇女提出劝诫,《古冢狐》讥刺了迷惑于美女姿色的世人,《时世妆》警告追逐流行的轻薄妇女,《青石》则褒奖了臣子的忠烈。这些作品由于都有着垂示训诫的意味,像白居易这样用警世的态度作歌的诗人,大概是史上稀有的吧。
五、柳宗元与韩愈
尽管柳宗元和韩愈都没有展示对古乐府有多么的关心,但在乐府史上,也留存有应该特别记载的作品,就是柳宗元的《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韩愈的《琴操》十首。不言而喻,铙歌鼓吹曲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武乐中最被重视的,每个王朝更迭必有改作的歌曲。为了让天下万民周知新王者的功德,又让祖宗的遗训仍能垂示百代之后,因此利用这些歌曲可以得到最佳的效果。但是,柳宗元的《唐铙歌鼓吹曲》与历代的习惯不同,他不是应王室的公共的要求而制作的,或者说,也不仅仅是满足诗人的创作欲望的案头玩物。根据曲序,柳宗元因记述了高祖、太宗的功勋,可知王室在统一天下时经历的劳苦,以及武将在指挥军队及每次在有兵事发生时练兵的艰难,出于颂歌的目的而制作了这一曲辞。然而,柳宗元在序中说汉曲有十二篇,魏曲有十四篇,晋曲有十六篇,自己现在用汉曲的篇数来制作了《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但是,各个时代的曲数,为什么与事实不符呢?大概是因为古书字句常有夺漏,才知道所说的应该是不符合事实的吧。那么为了附会自己所作的篇数,才特意作出了汉曲还有魏晋曲数有变化的判断。柳宗元的十二篇名为《晋阳武》《兽之穷》《战武牢》《泾水黄》《奔鲸沛》《苞枿》《河右平》《铁山碎》《靖本邦》《吐谷浑》《高昌》《东蛮》。这其中,《吐谷浑》以下三篇,看上去取材似乎稍有贫乏。即《晋阳武》歌颂唐王室起义兵于晋阳,欲使天下归一于仁德的事迹;《兽之穷》写李密来归,《战武牢》写讨伐郑王王世充,《泾水黄》写讨伐西秦霸王之子薛仁杲,《奔鲸沛》写讨伐辅公祏,《苞枿》写讨伐梁王萧铣,《河右平》写讨伐河西大凉王李轨,每篇都取材于僭位者;《铁山碎》则写讨伐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靖本邦》写讨灭刘武周的事迹。以上九篇都是歌颂高祖及太宗的功勋,在篇名上下了功夫。但《吐谷浑》三篇,并不适合前九篇的取材。这三篇中,《吐谷浑》和《高昌》篇的主人公是臣子李靖,《东蛮》写率群臣来朝的东蛮酋长谢元深应太宗之要求被画像一事。那么对这三篇,我批判为取材贫乏,不适合入鼓吹的理由是,如前记的鼓吹曲,本来是将对天子及其祖宗的功德作为取材对象,而每个朝廷基本没有直接将臣子的武勋及行动作为歌辞取材的。
柳宗元的十二篇歌辞,并不像前记那样是应王室要求制作的,而是从顺宗永贞元年(805)十一月到宪宗元和十年(815)十二月这么长的时间他在永州司马任上,闲暇时自己私下创作的。但可能一直没有被世人传唱的机会。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的解题说“此诸曲,史书不载,疑宗元私作而未尝奏,或虽奏而未尝用,故不被于歌,如何承天之造宋曲”,这应该是正确的吧。可以思考的是,即便柳宗元上奏了这些曲辞,但已经历了自唐开国以来一百九十年的元和之世,政府要员感到将这些取材于祖宗二代功勋的曲辞当作颂歌是没有必要的。为了当下能接受,希望扩大取材的范围,准备歌颂现在天子的仁德。元和十二年(817)十月,朝廷捕缚了叛将吴元济,平定了淮水一带,柳宗元即刻上奉《平淮雅夷》二篇。如果从是否合时宜这一点来看,不得不说,《铙歌古曲》十二篇要比此曲逊色一筹。
柳宗元这十二篇的用语,可以说大致是他自己窃取了古书中,即魏晋以来的鼓吹曲辞的辞句。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辩》卷八评价为“(曲)词太严密,(语)气亦促迫,而乏优游之韵。唯《兽之穷》一篇,词义若差胜云”。兹从十二篇中摘录其曲辞一篇:
兽之穷,奔大麓。天厚黄德,狙犷服。甲之櫜,弓弭矢箙。皇旅靖,敌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贙猛,虔栗栗。縻以尺组,噉以秩。黎之阳,土茫茫。富兵戎,盈仓箱。乏者德,莫能享。驱豺兕,授我疆。
但徐氏所谓的“词太严密,气亦促迫”这点,因是曹魏以来鼓吹曲辞所共有的,柳宗元的作品也难免受此限制。
对于柳宗元的十二篇曲辞,不像前记那样看不出在用语上有什么特色。但他是如何发挥其才能的呢?我认为,在历代鼓吹曲的作家中,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对音律有如此重视的程度。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流传的是汉鼓吹铙歌的旋律,尽管它们在长年间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变调,但在用旧有的旋律填合新辞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其数,鼓吹曲的制作是比较容易的。因此,辞作家便没有必要从音律上深加考虑。但柳宗元却相反,他制作曲辞,不可能依据的是北周宣帝之世以来灭绝已久的旋律。他在新作铙歌鼓吹曲时,就有了倾注苦心的必要。他的各作品的语句构成便可明白揭示出这番苦心。每一篇都有独特的系统,而全部的十二篇,又好像形成了一首完整的曲子,极具变化之妙,他绝对不会漫不经心地使用错杂的长短句。
晋阳武 26句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兽之穷 22句 3343343343334333333333
战武牢 18句 333333334343333333
泾水黄 24句 333343434433433344434333
奔鲸沛 18句 334343434343434343
苞枿 28句 4445544533444343444343434343
河右平 18句 445444544554434345
铁山碎 22句 3333334454334343435444
靖本邦 14句 44444444444444
吐谷浑 26句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高昌 22句 5555555555555555555555
东蛮 22句 5555555555555555555555
首先,《晋阳武》反复用轻快激急的三拍子;从《兽之穷》到《奔鲸沛》间,依次混用缓慢的四言调;《苞枿》和《河右平》则加入了流畅的五言韵律,缓急自在;到了《铁山碎》又再度以急切的三言调为主;《靖本邦》则一变,始终是单调的四言;《吐谷浑》三篇又始终重复着五言韵。最后的三篇在用同一韵律构成这一点上,稍有技穷的嫌疑。然而这十二篇在能够单独演奏之外,也可连续演奏为全篇,发挥其转变的妙趣,而让人不觉得有些倦怠,这就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单独一曲也好,组曲也罢,它们都独具特色。因此,我认为,即便此曲实际上是不能合唱的,与魏晋南北朝的鼓吹曲相比,都可推许为独具特色的佳品。
韩愈的十首琴操中,《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三首的原作者是孔子;《越裳操》《岐山操》乃周公原作;《拘幽操》是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时作;《履霜操》乃周宣王之世,尹吉甫之子伯牙遭受继母虐待所作的悲歌;《雉朝飞操》乃齐宣王之世,孤独的七十岁的犊牧子控诉不遇之歌;《别鹄操》(同《别鹤操》)写的是商陵牧子因无子嗣,被迫与妻子离婚的悲叹;《残行操》据说取材于曾子在梦中遇见无首之狸;以上十首原作者和作歌的缘由,每一首都在东汉蔡邕的《琴操》中有说明,韩愈信凭其说,取材于这些故事。可是韩愈为何要取材故事并且制作歌辞呢?我试做如下推测。说起来,这些原作的歌辞实际上都是假托也就是伪作,尽管如此,也被东汉的琴曲家珍视为来源纯正的名曲。经过六朝,十曲中大半都不能弹奏。可知韩愈当时的琴书也没有著录这些琴曲的实际状况,才想要试图复原名曲吧。可知著录唐代能实际弹奏的琴曲名的资料,有隋代丘公的《碣石调幽兰》、唐或唐前所撰的《琴历》、宋代郑樵的《通志》卷四十九。其中,《碣石调幽兰》记有六十曲,《琴历》记有四十二曲,《通志》记有四十曲的曲名。除了《猗兰操》别名为《幽兰操》、《别鹄操》又名《别鹤操》这二曲外,剩余八曲也不见著录。我认为,这八曲从隋末到唐已经亡佚了。然而,韩愈所作的八曲,也无法确证其在唐代实际弹奏。但在宋代以后所附的曲谱,很长时间在琴曲家间可以弹奏,却是事实。下表即记有明、清间演奏的音阶和段数。

表一
表一中的九曲,都是演奏时间较短的一段。韩愈所作辞中,没有混入他人新作的语句,可能就是将短篇的原作原班不动付予弦歌。然而,《猗兰操》是绵亘千古弹奏不绝的名曲,韩愈并不偏重于作辞,与由琴曲家弹奏的曲谱和歌辞也不相同。此外,还有相信韩愈的歌辞就是孔子所作之辞的人,在引用其语句的同时,也制作了新的曲辞。
近世以后,对韩愈琴操的批评者渐多。如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吾谓西汉后独《敕勒歌》及韩退之十《琴操》近古”,又《沧浪诗话》所谓“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诸贤所及”,被明清诸家聚焦批评,主要从用语、体裁、内容等方面,与古曲相比较。然而,韩愈惋惜《将归操》《龟山操》等名曲在唐代就已经亡佚,为其制作的歌辞,被宋以后的琴曲家所重视而实际弹奏。其不论是被动的,还是再生于现实的功绩,不应该先于近世的批评家们而得到称赞吗?
六、张籍与王建
最初评论张籍乐府的人是他的诗友白居易。白氏在元和十年(815)所作的《读张籍古乐府》诗中说张籍“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在给予张籍乐府很高的评价后,触及到作家的精神是“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认识到张籍乐府的真正价值是以六义,即美刺褒贬的精神为准则。近人徐澄宇氏把当时和张籍并称的王建的乐府也加入到张籍的乐府中,撰写了名为《张王乐府》一书,在此书的导言中,分析了两人乐府所展现的作家精神,列举了“反对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攻击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讽刺特权阶级的骄横强暴”等八项,引用了符合这八项的作品并论证之。但我认为,白居易的张籍乐府体现了古代《诗经》精神的说法,和现代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学批评式的说法之间,归根结底是没有差别的,都可以说是一种对时事批判的说法。但时事批判这一问题,从关于作歌的立场来看,不限于张、王两人。当时见于乐府作家的一般的倾向,无论是白居易的意见,还是徐氏列举的八项(此八项稍有重复之嫌),其他作家也多少都有言及,只是有批判意味表现得强弱的差别而已,作家之间并没有认识到有那种个人差别。因此我认为,徐氏所引证的作品,未必是他人所无而仅是张、王特有的作家精神的反映。我的观点和徐氏的完全不同。我认为,张王乐府的特色,正在于其作品取材于庶民生活的实态。这是因为,两人都仔细观察庶民阶层的生活,并深刻描写其生活实态这一点,遥遥领先于其他唐人。所以无论是否从批判现实的立场制作歌词,也不管他们是否有用徐氏八项中所说的“歌颂人民的坚强意志和劳动活力”的歌颂的态度来制作歌词,其作品本身在歌咏庶民生活的实态这一点上,便有巨大的意义。现存作品有取材于耕作、养蚕、牧牛的《江村行》《赛神曲》《簇蚕辞》《田家行》《田家留客》《牧童词》,捕捉林中采薪场面的《樵客吟》,有描写江南渔村风景的《江南曲》,有描写采莲和捕鱼场面的《采莲曲》《塞塘曲》,直叙从事水运者和商人船上生活的《贾客乐》《水夫谣》《水运行》等,接触到采珠者和织工劳动的《海人谣》《织锦曲》。这些作品用平淡的语言写出庶民平时努力于生计的行为,作者的观察极其绵密,使得这些作品带有了风俗画的色彩。张、王作品中,徐氏把《江村行》《采莲曲》指为民歌,这是不正确的。基本上,民歌不用说就是指民众的歌声,从古老的《诗经》,到汉魏南北朝之世,上流阶层歌唱的作品,是平民共有的各种生活感情的歌曲,或者也多是歌咏一些市井事件。但在民歌的世界,作者几乎没有客观照原样来描写庶民生活状况的作品。张、王也不是打算要制作民歌,仅仅是向平民阶层的生活求得素材而已。他们观察了平民生活的状况,《牧童词》“远牧牛,绕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饥鸟啄牛背,令我不得戏垄头”,捕捉到在某个农村郊外追赶鸟儿的牧童的身姿;《贾客乐》“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聚焦于深夜船中商人数钱的行为;《水夫谣》“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描写的是纤夫在雪夜这样的恶劣天气中劳动的样子。现在我再列举取材养蚕的《江村行》《赛神曲》《簇蚕辞》《田家留客》四篇如次:
江村行
张籍
南塘水深芦笋齐,下田种稻不作畦。耕场磷磷在水底,短衣半染芦中泥。田头刈莎结为屋,归来系牛还独宿。水淹手足尽有疮,山蝱绕身飞扬扬。桑林椹黑蚕再眠,妇姑采桑不向田。江南热旱天气毒,雨中移秧颜色鲜。一年耕种长苦辛,田熟家家将赛神。
上诗描写的是农家在水田地带的农事活动,即到了耕种期,通过农夫动作对从灌溉、整地、结屋、移植旱苗等作业的刻画描写。此诗末句歌咏了等待收获期,将举行赛神的仪式。直到那一日的到来,举家狂喜乱舞,结果是深刻描绘出路人举杯庆祝的动作,见《赛神曲》:
赛神曲
王建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听神语。新妇上酒勿辞勤,使尔舅姑无所苦。椒浆湛湛桂座新,一双长箭系红巾。但愿牛羊满家宅,十月报赛南山神。青天无风水复碧,龙马上鞍牛服轭。纷纷醉舞踏衣裳,把酒路傍劝行客。
写的是在稻田收获后举行的赛神风俗。当蚕经过三眠而上簇,也把它们当作神来祭祀:
簇蚕辞
王建
蚕欲老,箔头作茧丝皓皓。场宽地高风日多,不向中庭㬠蒿草。神蚕急作莫悠扬,年来为尔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无苍蝇下无鼠。新妇拜簇愿茧稠,女洒桃浆男打鼓。三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后两句略)
除以上三曲外,王建的《田家行》取材麦秋期的农事状况与农民生活实态,张、王通过其笔力,首次用乐府详加介绍。那么再举一首王建的《田家留客》,此篇歌句由农民的独自言语所构成,农民朴素的感情溢于言外,作品中的“客”恐怕是作者自己,因被农民纯粹的情感深深打动,我认为这种即兴歌咏,恰巧速记的手法颇富生动性。
田家留客
王建
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浆马有粟。远行僮仆应苦饥,新妇厨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门户,蚕房新泥无风土。行人但饮莫畏贫,明府上来可苦辛。丁宁回语房中妻,有客勿令儿夜啼。双冢直西有县路,我教丁男送君去。
唐人取材于田园的乐府作品很少,而仔细观察农民的生计、直叙生活实态的作品更是几乎没有。可见,我所例举的张、王乐府,不得不说是乐府史上了解农民生活实状的重要资料。
在乐府史上,自从汉武帝创设上林乐府以来,宫廷音乐就由大别于雅乐的,用民歌来粉饰的俗乐所构成。俗乐粉饰的民歌,除了少许取材于市井事件外,尽管也照样歌颂庶民的生活情感,但写出他们生活实态的几乎没有。此外,历代的诗人,被创作欲所驱使,尽管也向民歌寻求素材,但也没有着眼于平民生活的实际状况。到了唐代的贞元、元和时期,张、王首次在歌辞中细致刻画描摹了平民的生活,之所以说他们乐府的特色,就是因为在作品中发挥并展现了这些内容。
(本文原载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文学研究室《中国文学报》第21 册,1966 年4 月;译自〔日〕增田清秀《乐府的历史性研究》第十五章,创文社,1975年)
注释:
①这里指元结、皮日休等。他们都希望把诗付予乐章歌唱,虽然元结创作有《系乐府》《补乐歌》,皮日休创作有《正乐府》《补九夏歌》,但除此以外,也似乎没有再制作古乐府。
②大概是在酒肆饮酒之意。
③据华忱之氏《孟郊年谱》,民国二十九年(1940)版。
④用“古意”一题歌咏闺怨,是六朝人的想法。刘宋的颜竣、吴迈远、王融,萧梁的武帝、简文帝、元帝、沈约、吴均、刘孝绰、何子朗等都歌咏过闺怨。
⑤宋王灼《碧鸡漫志》:“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
⑥“人色”一作“城人”,下句“拔蒲根”一作“折蒲耳”,“愁魂”一作“秋风”。
⑦《从军诗序》,载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之《李益集》。
⑧据新、旧《唐书》所记。但宋王谠《唐语林》所举篇名有《征人歌且行》,并不是同一首诗。《征人早行篇》,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云“今集有从军诗五十篇,而无此诗,惜其放逸多矣”,此诗宋代已亡佚。然《唐语林》所举的《征人歌且行》现存,作《送辽阳使还军》:“征人歌且行,北上辽阳歌。二月戎马息,悠悠边草生。青山出塞断,代地入云平。昔者匈奴战,多闻杀汉兵。平生报国愤,日夜角弓鸣。勉君万里去,勿使虏尘惊。”
⑨“思归”一作“归思”,第八句“落”一作“飞”。
⑩关于刘孟的行迹,为梁州进士,元稹《酬刘猛见送》中有“持此慰远道,此之为旧交”,除了为元稹旧交外再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