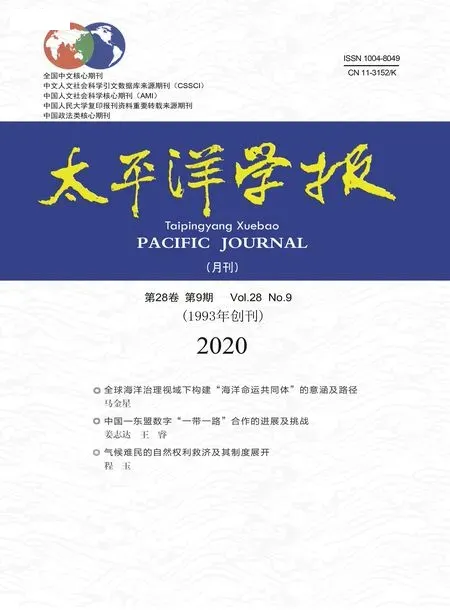气候难民的自然权利救济及其制度展开
程 玉
(1.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2.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权威气候科学证据已经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确定性的增加给自然环境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例如,海洋洋流流向发生变化,全球海洋风暴持续时间延长、强度增加,海平面不断上升;许多陆生、淡水和海洋物种改变了分布范围、迁徙模式、丰度和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很多区域的小麦和玉米产量大幅减少;极端天气在全球肆虐,荒漠化加剧,干旱、洪涝频发,气候日益极端无常。(1)Se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of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2015,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5/SYR_AR5_FINAL_full_wcover.pdf.预计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升幅将超过3摄氏度,届时冰川体积将减少85%,全世界70%的海岸线会发生20%以内幅度的海平面变化,海水酸化程度将达109%;而当全球平均温度上升2摄氏度时,全球粮食产量可能会减少25%。(2)Se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53.在此背景下,很多国家的领土或因气候条件极端而不再适宜人类居住,或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其国民开始主动或者被动向外迁徙。根据是否跨越国界,迁徙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在一国范围内从某地区被迫迁徙至其他地区的国内流离失所者(Internal Displacement);(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国内流离失所监察中心(IDMC)已经确认洪水和干旱等气象灾害是造成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主要原因,并对气候变化导致流离失所者进行了跟踪报告。据报告,仅2010年,亚洲地区流离失所者数量达到了2945万人,占全球的77%。Se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53. 2017年,自然灾难所致国内流离失所者数量虽有所下降,但全球135个国家或领地范围内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仍高达1880万人,其中,气象灾害引发的国内流离失所者达到1800万人。Se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NRC/IDMC), “2018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May 16, 2018, https://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grid2018/downloads/2018-GRID.pdf.二是跨国界迁徙的移民或者难民(Migrants or Refugees)。对此,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会导致特定时间和地区的人口迁徙,给迁徙者及其原籍国和东道国带来不均衡的风险和收益。”(4)同①, p.1060。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也将气候变化列为移民的诱因之一,并列举了不同生态区域的气候移民实例。(5)S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0”, November 2019,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20.pdf.对于低洼环礁、资源有限的小岛屿国家而言,自然地质属性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缺乏资金和技术资源)使它们的脆弱性更甚、更易遭受损害。(6)参见张晨阳:“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所致小岛屿国家损失和损害研究”,《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9期,第11页。联合国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UNU-EHS)对图瓦卢、瑙鲁等太平洋小岛屿国家国民因气候变化导致跨国迁徙行为的评估证明了前述观点。(7)Se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curity (UNU-EHS), “Tuvalu: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November 2016, https://collections.unu.edu/eserv/UNU:5856/Online_No_18_Tuvalu_Report_161207_.pdf.
相较于“气候移民”这一术语,当我们使用“气候难民”概念时所要强调的是个人或群体被迫迁徙,他们会面临更大的生存风险,需要更多和更优先的权利保障。世界银行2017年做出的一份最为悲观的前景预测显示,在未来30年内,全球可能超过1.43亿人被迫成为气候难民。(8)See Kanta Kumari Rigaud, “Groundswell: Preparing for Internal Climate Migration”, World Bank, 2018,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9461.而南太平洋小岛屿国家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有限,经济水平不高,其国民沦为气候难民的风险更大。气候难民问题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它对新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提出了挑战,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法难题:气候难民是否可以归为传统难民?气候难民的哪些基本权利遭受了侵害,可否归因于气候变化?在既有实在国际法框架中,(9)实在国际法和自然国际法相对,有关实在国际法概念的内容,请参见罗国强著:《国际法本体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304-313页。气候难民是否有权主张损失与损害救济?不再占有领土的气候难民原籍国是否可以继续保持其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资格,抑或成为“特殊的国际法律实体”?如何建立由原籍国、东道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分担的气候难民责任机制?本文试图对这些焦点问题作出初步解答。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议题:气候难民权利救济困境
气候难民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可能源于环境、文化、经济和家庭因素的综合交织),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气候难民概念。学界关于气候难民的概念定义众说纷纭,包括气候移民、气候变化所致流离失所者、气候迁徙者、气候难民、环境难民、生态难民、环境移民等。国际移民组织(IOM)为避免概念混乱,将环境难民涵盖在环境移民概念之中,并将后者界定为,“因环境突然或缓慢变化对人们生活或生存条件产生不利影响而被迫或主动、暂时或永久离开家园的个体或人群,既可以是国内迁徙,也可以是国际迁徙。”(10)参见郑艳:“环境移民:概念辨析、理论基础及政策含义”,《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4期,第96页。有学者沿用此种实用主义方法,将气候难民定义为,“因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环境发生突发性或者渐进性变化而不得不立即或者在不远的将来离开原居住地的人或人群。”(11)See Frank Biermann and Ingrid Boas, “Preparing for a Warmer World: Towards a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o Protect Climate Refugee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10, No.1, 2010, pp.60-88.贝诺伊特·梅尔(Benoit Mayer)将气候难民概念的构成要件分解为:气候变化是造成人口被迫逃离的主导性原因,气候变化引发的是一种永久性迁徙,且气候难民必须跨越国境。(12)See Benoit Mayer,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Challenges of Climate-Induced Migration: Proposal for an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Vol. 22, No.3, 2011, pp.13-14.邦尼·多彻蒂(Bonnie Docherty)和泰勒·詹尼尼(Tyler Giannini)将气候难民概念的构成要素归纳为六个方面:(1)发生被迫迁徙行为;(2)暂时性或者永久性迁徙;(3)跨越国境的迁徙;(4)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环境损害;(5)突发性或者渐进性的环境损害;(6)人类迁徙行为与前述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3)Bonnie Docherty and Tyler Giannini, “Confronting a Rising Tide: A Proposal for a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Refugees”, 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33, No.2, 2009, p.372.这些概念或交织重叠或指向单一,但基本内涵相对一致。本文基于上述概念的共性,将气候难民定义为,“因气候变化导致的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类环境损害而被迫离开本国进行临时或永久性跨国界迁徙的人(个体或者群体)。”(14)环境损害与气候变化具有高度的因果关联性,可由专门科学专家机构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出具的报告确认。
气候难民问题的本质是权利的侵害与救济。人类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导致的气候变化不仅影响了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加剧了特定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还对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在内的各项基本人权的享有和实现构成了严重威胁。2003年,极地63名因纽特人直接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起诉讼,要求委员会确认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行为所致气候变暖直接侵犯了其应享有的多项基本人权,包括文化权、财产权、生命健康权、人身权、居住权以及自由迁徙权等。(15)See Sheila Watt-Cloutier, “Petition to the Inter 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Seeking Relief from Violations Resulting from Global Warming Caused by Acts and Omiss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Houston Law Center, December 7, 2005, http://law.uh.edu/faculty/thester/courses/ICC_Petition_7Dec05.pdf.尽管该案诉求最终被驳回,但其为国际社会探讨气候变化与人权关系提供了契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其2008年和2011年的决议中指出,气候变化对基本人权构成影响。(16)See Rana Balesh, “Submerging Islands: Tuvalu and Kiribati as Case Studies Illustrating the Need for a Climate Refugee Treaty”, Environmental and Earth Law Journal, Vol. 5, No.1, 2015, p.100.2017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组织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深入讨论了“人权、气候变化和跨国界移民、流离失所者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气候变化影响到数百万人享有的广泛人权,包括食物权、饮水权和卫生权、健康权和适足住房权。” 2018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生命权的一般性意见中,首次阐述了气候变化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项下生命权的一般关系,它指出,“环境损害、气候变化以及非可持续性发展构成对人类享有生命权之能力的最为紧迫、严重的威胁。”(17)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36, Article 6: Right to Life”, CCPR/C/GC/36, October 30, 2018, para. 62.可以说,逃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难民并不是出于自主选择,而是迫于逃离连最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的生存危机。事实上,气候难民在迁徙中也并非一路坦途,他们始终遭受着仇外敌对心理,难以获得食物、水、保健和住房,以及面临随时可能出现的任意拘留、人口贩运、暴力袭击、强奸和酷刑等威胁。(18)Se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UNHCR), “Summary of the Panel Discussion on Human Rights, Climate Change, Migrants and Persons Displaced across International Borders”, U.N. Doc. A/HRC/37/35, November 14, 2017, https://undocs.org/A/HRC/37/35.在面临自然灾难或公共卫生事件时,气候难民的权利更难获得保障。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气候难民因较难获得检测或医疗服务而特别容易受到COVID-19爆发的威胁。(19)See Carly A. Phillips, Astrid Caldas, Rachel Cleetus, et al, “Compound Climate Risk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Nature Climate Change, Vol.10, No.1, 2020, pp.586-588.
气候难民问题不仅是重大的权利危机,也给全球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其一,气候难民全球迁徙行为可能导致疾病的全球传播。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与伦敦卫生学和热带医学学院于2003年做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暖已经造成每年16万人死于疟疾和营养不良,到202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翻倍。(20)李文杰:“论气候难民国际立法保护的困境和出路”,《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67页。如果缺乏有效控制,气候难民迁徙行为极有可能造成疟疾等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传染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传播,诱发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可以预见,气候难民的无序迁徙,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其二,争夺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例如水和食物)易引发各种敌对与冲突,造成局部地区的战争不断。例如,气候变化使得非洲地区适宜耕种土地的1/2遭受沙漠化和土地退化的风险,导致达尔富尔等地区持续爆发水和草原等自然资源的争夺,造成当地社群之间频繁发生武装冲突;极端自然灾害事件也加剧了美洲地区的土壤退化,使得墨西哥每年都有70万~80万左右的人口寻求进入美国,美国政府为避免难民进入一直致力于在美墨边界加筑高墙以实现边界安全与稳定。(21)Benoit Mayer,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Challenges of Climate-Induced Migration: Proposal for an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Vol. 22, No.3, 2011, pp.11-12.此外,气候难民潮还会对东道国(即气候难民迁徙目的地)的资源分配和治理秩序带来冲击,如果缺乏稳妥的秩序调节机制,东道国国民和气候难民之间将爆发诸如种族歧视等不可避免的争端,扰乱社会治安。
为救济气候难民遭受的权利侵害,并消除或减缓气候难民给全球治理带来的挑战,国际社会不仅有必要想方设法从源头减少气候难民,还要考虑如何在制度层面确立气候难民的权利保障机制,毕竟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后果无法完全消除——气候难民也就无法完全消弭。从应对思路来看,既然气候难民问题的本质是权利侵害与救济,其应对方案自然也应从权利角度进行设计。无权利即无救济,是极为简明的法理。仔细研究后发现,尽管气候难民议题已被纳入国际政策和法律议程,但气候难民的权利在实在国际法框架下尚难获得保障。
首先,国际人权法在应对气候难民问题时存在制度局限。目前,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成功经验的国际人权法并不能为气候难民提供充分的基本权利保障。这是因为,国际人权法的适用以人权遭受直接侵犯为前提(要么侵犯本身是国家行为造成,要么国家在职权范围内未采取行动保障人权免于遭受侵犯),而气候变化对气候难民人权的侵犯具有间接性——温室气体累积排放导致各类突发性或者渐进性环境损害对气候难民享有的基本人权构成限制。(22)Se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UNHRC), “Report of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Rights”, U.N. Doc. A/HRC/10/61, Januray 15, 2009,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98811532.html.事实上,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具有典型的跨界性、累积性和集体性特征,要在法律层面证明一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直接侵犯了特定人群的具体人权,具有相当大的困难。(23)参见龚宇:“人权法语境下的气候变化损害责任:虚幻或现实”,《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第75-85页。更何况,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积极态度应对气候变化,导致国际人权法中补充性保护机制(Complementary Protection)(24)国际人权法将国家保护义务范围从难民扩展到处于被任意剥夺生命、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危险中的人。这通常被称为“补充性保护”,这种保护是对《难民公约》所提供保护的补充,源自国际人权公约体系,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以及一些区域人权公约,例如《欧洲人权公约》。的适用条件(例如,保护免受任意剥夺生命、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难以满足。(25)参见[澳]简·麦克亚当:“新西兰在气候变化、灾害及流离失所问题上的新判例”,《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2016年第1期,第75页。从国际人权法的保护对象来看,国际人权公约遵循国家视角,其确立的成员国人权保护机制以成员国本国难民为适用前提。虽然近年来国际法在一国对另一国国民所负人权保护义务的问题上有所“松动”,但“有效控制”黄金法则(即一国仅对其能有效控制之国民负有人权保护义务)始终成立,致使国家一般对其领土或管辖范围外的人不负有人权保护义务。2019年底,荷兰最高法院在“乌尔根达案”(Urgenda)终审判决中认定,“气候变化对国民生命与生活造成了切实且紧迫的威胁,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生命权)以及第8条(个人及家庭生活权),成员国有义务采取减排及适应措施”。(26)See Supreme Court of the Netherlands, The State of the Netherlands v. Stiching Urgenda, Judgment, December 20, 2019.2020年初,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泰提奥塔案”(Ioane Teitiota v. New Zealand)中第一次确认气候移民获得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护的法律可能性,成员国依据该公约所载之人权义务应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27)Se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of Human Rights Office, “Historic UN Human Rights Case Opens Door to Climate Change Asylum Claims”, January 21, 2020,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UniversalHumanRightsInstruments.aspx.两起司法案例都只认可了气候难民原籍国对其本国居民的人权保护义务。
其次,作为国际人权法特殊组成部分的难民法——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也无法适用于气候难民问题。这是因为,其一,通过法律解释将气候难民归为公约难民的做法始终存在着难以突破的理论局限和道德困境。(28)气候难民不同于政治难民,其起因并非政治迫害理由,并且气候难民与逃离所谓迫害者的传统难民不同,其会向作为“迫害者”(原籍国)的工业化国家寻求庇护;主权国家对公约难民资格条件享有任意解释权,往往会基于国家利益采取更为严格的庇护/难民审核程序,以限制申请者的数量;气候难民纳入公约难民的保护范围,会引发气候难民原籍国的道德风险,气候难民原籍国有可能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消极,不积极采取减缓和适应措施。See Tony George Puthucherril, “Rising Seas, Receding Coastlines and Vanishing Maritime Estates and Territories: Possible Solutions and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 Vol.16, 2014, p.108.其二,即使通过文义扩张解释或者条约修订方式将气候难民归为传统公约难民,既有难民公约机制也仅能提供一种有限保护。(29)《难民公约》项下难民保护存在二元困境:难民原籍国倾向于以道德和人道主义的方式进行讨价还价,以扩大对寻求避难者的保护,而其他国家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那些尚未迁徙至原籍国之外的气候难民难以满足流亡(在原籍国之外)要求;传统国际难民法并未规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分担原则,同时它也缺乏全球环境基金等类似资金机制的规定;各国在实践中习惯于采用个体意义上的甄别措施,通过个案裁决来判断申请者是否符合难民的身份资格,不利于气候难民的集体救济;联合国难民署每年预算已不足以支撑其开展保护日益增加的政治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援助任务。See Stellina Jolly and Nafees Ahmad, “Climate Refugees under International Climate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Towards Addressing the Protection Gaps and Exploring the Legal Alternatives for Criminal Justice”, ISIL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nd Refugee Law, Vol.14, 2014-2015, p.237.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和2018年《全球难民契约》已经明确纳入“突发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可能导致的跨界流离失所者”,这就为国际社会依托国际难民法应对气候难民问题提供了可能性。(30)《全球难民契约》很多条款规定了有关气候难民问题的解决办法。例如,“减少灾害风险”(第九条)、“备灾措施”(第五十二、五十三条)、“全球、区域和国家的早期预警和早期行动机制”(第五十三条),以及“基于科学证据对未来人口迁徙的预测”和“将难民纳入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第七十九条)。但《全球难民契约》仅仅是一种国际倡议,并不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31)参见武文扬:“应对难民和移民的大规模流动:《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及其执行困境”,《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7期,第42-53页。其规定的气候难民权利保障规则仅有指导意义,各主权国家有权只采取契约项下难民人权保障措施中的部分内容。
最后,规制气候难民问题产生原因(温室气体排放所致气候变化)的国际气候法也无法充分救济气候难民的权利侵害。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并未使用与气候难民或者气候流离失所相关的概念,(32)See Ruth Gord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oorest Nations: Further Reflections on Global Inequality”,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Vol. 78, No.4, 2007, p.1583.但该公约第4条第1款b项承诺中的“适应”,(33)所有缔约方应采取充分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第四款规定,附件二所列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帮助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支付适应这些不利影响的费用。为理解气候流离失所(包括气候难民)预留了解释空间。随着气候流离失所问题日益严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s)开始关注此议题(有关共识参见表1)。起初缔约方大会对气候流离失所问题的关注较少。《巴黎协定》是自2007年巴厘岛行动计划之后首次详细阐释气候变化所致人口迁徙和流离失所问题的协议。但总体上看,《巴黎协定》在气候流离失所问题上的规定仍有诸多不足。其一,协定并未明确使用气候难民概念,导致气候难民与国内流离失所者混同,一定程度上分散和弱化了国际社会在解决气候难民问题方面的焦点和信心。其二,虽然协定多处提及气候流离失所,(34)《巴黎协定》序言要求各缔约方尊重、促进和考虑气候迁徙者的权利;《巴黎协定》多次提及解决气候流离失所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护人民、社区的复原力和生计的重要性,为其提供水、粮食、能源以及谋生机会;《巴黎协定》第8条要求华沙损失与损害机制执行委员会在损失与损害方面加强理解、行动和支持,以应对属于非经济损失的气候流离失所问题,第50条敦请该机制设立专门的气候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为避免、尽量减少和解决气候流离失所问题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但其规范内容仅要求各缔约方尊重、促进和适当考虑它们在应对气候流离失所问题方面的责任。从责任配置来看,协定鼓励原籍国通过灾害风险管理框架解决气候流离失所问题,与《巴黎协定》确立的自下而上式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不谋而合,即原籍国而非国际社会对气候流离失所者负主要责任。其三,协定设立的气候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TFD)仅负责科学研究和技术支持,不具有政策制定权。其四,从随后的历次气候协议来看,《巴黎协定》序言规定的“气候正义”和“迁徙者的权利”,(35)《巴黎协定》序言规定,“缔约方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时,应当尊重、促进和考虑它们各自对……迁徙者权利……等义务。”仍然仅停留在原则性规定中,因缺乏细化条款而无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表1 历届缔约方大会有关气候流离失所问题(包括气候难民)达成的共识
虽然国际政策和法律议程已经开始探讨气候难民问题,但截至目前,进展有限,既有实在国际法无法为气候难民的权利救济提供法律规范依据。实践中,2005年因纽特人起诉被驳回,2014年基里巴斯公民以海平面上升导致土地丧失为由向新西兰申请气候难民身份被拒绝,这些都是明证。国际社会之所以无法就气候难民问题达成一致的国际法解决方案,既和气候难民权利救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相关,也和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危机挑战密不可分。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低迷、难民危机加剧等为特点的新全球化席卷全球,民族主义重新崛起,一体化与多样性的竞争、合作与冲突的博弈此起彼伏。新全球化浪潮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气候变化领域也不例外,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体系日益呈现碎片化和多中心的特征,导致全球治理整体性方案难以落到实处,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不确定性。(36)参见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36页。2015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2017年美国退出《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加剧了全球气候难民治理的不确定性。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治理的时代情境中,现实主义主导着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不仅导致各国各自为政、未能建立有效的联防联控机制,(37)苏云婷:“新冠肺炎疫情背后: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回溯”,《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60页。也为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可以预期,包括气候难民在内的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受到限制。
二、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气候难民权利救济方案选择
气候难民在当前实在国际法框架中不享有救济权,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也不享有自然国际法意义上的救济权。在国际法二分为实在国际法和自然国际法的背景下,自然权利和实在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互动特征。(38)一般而言,自然权利和实在权利(法律权利)的互动关系包括:其一,自然权利是自然国际法的核心概念,对具体自然权利的保护需要依赖于自然国际法内的一般法律原则或强行法规则,而法律权利是实在国际法的核心概念,权利人可以直接援引实在国际法中的一些保护规范;其二,实在权利来源于自然权利的转化,因此自然权利规则可以被用来评价、指导有效的实在权利规则,甚至在实在权利规则出现空白或不当时,对其进行相应的补正、完善。此外,实在权利保护规则不能对自然权利构成严重违背、侵蚀;其三,自然权利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实在权利的形式实现,实在权利的保护程度反向制约着自然权利的发现和实现程度。在当前实在权利规则无法保障气候难民权利救济需求的背景下,国际立法者应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可以对实在权利加以补充的自然权利。结合既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气候难民的救济可以从两项自然权利入手。其一,个体性自然权利,即由地球集体所有权衍生出的地球资源再分配请求权和紧急避难权;其二,集体性自然权利,即其他国家负有消极不干涉和积极支持义务的气候难民集体自决权。
2.1 地球集体所有权:地球资源再分配请求权和紧急避难权
地球集体所有权这一概念由格劳秀斯首倡,(39)参见[荷]格老秀斯著,马呈元、谭睿译:《战争与和平法(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其作用是服务于西方社会16—17世纪由格老秀斯、普芬道夫等人推动、展开的与“紧急避险权利”(Necessity Right)或“宾客权”(Hospitality Right)有关的讨论。康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新定居权利”,即基于地球集体所有权推论得出个体享有因受到风险而在其他国家重新定居的权利。(40)参见[德]康德著,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24-25页。地球集体所有权是一种非平均主义的“平等主义所有权”,并非指每个个体均对地球的某一具体资源/空间享有平均化的个体权利,而是所有人均对地球资源/空间享有一种对称性权利要求。(41)See Mathias Risee, “The Right to Relocation: Disappearing Islands Nations and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Earth”,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3, No.3, 2009, pp.283-294.依据霍菲尔德权利分析法学理论,为实现人类个体的自我保存,原初状态中的地球资源集体所有权应至少包括两项基本要素:(1)特权(Privilege),每个地球资源所有权人都可以自由地占有、使用地球上的资源/空间,而其他所有权人没有权利(No Right)要求其不占有、使用;(2)权利(Right/Claim),每个人均有权利为维持生存而占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源,而其他所有权人负有不干涉的义务(Duty)。(42)See Pauline Kleingeld, “Kant’s Cosmopolitan Law: World Citizenship for a Global Order”, Kantian Review, Vol.998, No.2, 1998, pp.72-90.特权对应一种消极义务,即其他地球资源集体所有权人负有义务不干涉某个人占有、使用维持其基本生存所需的地球资源/空间;而权利对应的既可能是消极义务,也可能是积极义务,即地球集体所有权人在他人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且在自身资源/空间有富余之时,负有转让资源的义务。因此,在紧急情况下接受和救济他国公民,可理解为对权利积极义务的履行。申言之,对于其他任何地球公民而言,作为地球集体所有权人的气候难民享有“权利”的结果是各国负有维持气候难民生存的两项自然法义务:其一,消极义务,即不干涉气候难民为维持基本生存而占有、使用资源/空间的义务;其二,在发生极端紧迫情形时,为气候难民提供维持基本生存所需之资源/空间的义务。
从权利的角度来看,上述从地球资源集体所有权推导出来的紧迫情形下资源/空间转让义务对应的是气候难民的紧急避难权,该权利可以作为气候难民权利救济的规范依据。(43)有学者曾对其适用条件做过总结:(1)国家对受有风险的个体而非集体负有救济义务;(2)受有风险的个体必须满足特定标准,且其必须向另一国而非本国主张救济;(3)另一国并非基于矫正正义对受有风险的个体负有救济义务,即负有救济义务的是所有国家而非特定国家;(4)另一国所负义务是永久接纳部分或全部符合特定资格的个体。See Katrina Miriam Wyman, “Sinking Islands”, in Daniel H. Cole and Elinor Ostrom, eds., Property in Land and Other Resources, Puritan Press, 2012, pp.449-450.事实上,气候难民享有的紧急避难权直接来源于地球资源集体所有权,也可以在人类社会制度的演进史中得到验证。设想一下早期的人类社会状态,人类开采自然资源的有限能力和自然资源的变幻莫测和不稳定,使得自然资源开发主要以社群(洛克的早期政治社会)为基础,但共同社群开发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群体在干旱、饥荒时对自然资源的享用;随后,随着人类利用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财产私有(如牲畜)、自然共同所有(如水、河流),再到自然为不同社群完全私有的制度演进。(44)Maurice Godelier, “Territory and Property in Primitive Societ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17, No.3, 1978, p.417.此时人类为实现自我保存,就需要确保其身处生存威胁的困境时能拥有最低限度的应对能力——一种紧急避险权利。根据适用范围不同,紧急避险权利有两种。其一,在本社群内成员之间适用的紧急避险权利;其二,在社群之间适用的紧急避险权利。而随着原始社群通过社会契约转化为现代国家,作为一项“制度前自然权利”(即社会制度被建构出来之前的权利)的紧急避险权利也发生了演变。(45)具言之,社群内紧急避险权利完全转化为国内法意义上的实在法权利;而针对其他社群之紧急避险权利,在国际关系演变过程中,仅实现了自然权利的部分制度化、法定化转变(例如,国际人权法仅赋予政治难民以寻求庇护的权利)。一项自然权利并不会由于未及时或者未完全转化为法定权利而导致法律效力的递减或消失,紧急避险权在现代政治社会中也包含两方面内容:(1)一国范围内不同公民个体间的紧急避险权利,这种权利的义务指向也可以是国家,由国家在个体无法维持生存时提供救济(国内法中的国家救助义务);(2)一国公民在无法维持生存时,可以主张其他国家对其负担一定的救济义务,它来源于原初社会中特定社群成员向其他社群主张的紧急避险权利。
可以说,在人类社会通过先占将地球集体资源转变为私人财产权(或者主权国家在本国主权范围内享有的自然资源“财产权”)的过程中,财产权的构造中隐含着一项先天的自然义务(“生存需要”构成限制甚至排除财产权的条件),该义务在原初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过程中被暂时“封印”。换言之,“保留对原初地球资源集体所有权利的尊重”是人类同意建构政治社会、通过契约制定财产规则的前提条件。(46)参见[荷]格老秀斯著,马呈元等译:《战争与和平法(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对国际关系而言亦是如此,即一国公民(作为个体或集体)享有的自然资源财产权并非绝对不受约束,相反,对他国公民紧急避难权的尊重始终是该财产权的隐含条件。(47)诺齐克曾以“沙漠中的泉眼”为例进行了形象说明。发生气候难民悲剧时,隐含的自然义务便被触发,地球上各种自然资源将再次恢复至原初共有状态(以维持所有人类基本生存为限),(48)参见王铁雄著:《美国财产法的自然法基础》,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气候难民为实现自我保存,可以依据地球资源集体所有权主张分享已经为他国占有的资源。
从地球集体资源所有权还可以推导出另外一种气候难民权利救济方案。既然地球资源为集体所有,在分配不均时,资源分配中的弱势群体在道德上有权要求再分配。以地球集体资源所有权为基础,有些学者主张在全球分配正义框架内对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现状进行调整,通过自然资源再分配制度对已为各国所占有的自然资源进行再分配,将其他国家富余的自然资源转给气候难民,以维持其生存。贝尔尝试引入罗尔斯和贝茨的国际自由正义思想(“人民的世界社会”和“世界主义方法”),经过比较分析,贝尔认为贝茨基于罗氏“社会公平正义分配原则”提出的“全球资源再分配原则”(用于自然资源)和“全球差异原则”(用于利用自然资源而产生之收入、财富等),相较于罗尔斯的“人民的世界社会”理论更利于解决气候难民问题。但是,为了修正贝茨仅将自然资源视为工具价值的不足,贝尔认为应确保气候难民享有平等分配自然资源和财富的权利。(49)See Derek R. Bell, “Environmental Refugees: What Rights? Which Duties?” Res Publica, Vol.10, No.2, 2004, pp.135-152.斯基林顿进一步主张,应构建出一套更加科学和合理的全球自然资源再分配、合作协议。(50)See Tracey Skillinton, “Reconfiguring the Contours of Statehood and the Rights of Peoples of Disappearing States in the A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Social Sciences, Vol.5, No.3, 2016, p.54.玛格丽特·摩尔的分析尽管未直接指向气候难民,但其关于自然资源控制和收益权二分,以及个体生命权对集体自决权行使之限制的观点,亦可间接适用于气候难民问题。(51)See Margaret Moore, “Natural Resources, Territorial Right, and Global Distributive Justice”, Political Theory, Vol.40, No.1, 2012, pp.86-107.因此,如果将气候难民亟须的土地资源归入这些学者所谓的自然资源范畴中,气候难民将有权主张重新分配全球土地资源。
2.2 集体自决权:绝对化的救济方案和相对化的救济方案
长期以来,集体自决权在由自然权利向实在权利转化的过程中,仅实现了部分转化,以至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作为一项实在权利的集体自决权的内涵仅限于民族分离、民族独立范畴,(52)参见杨泽伟:“论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与国家主权”,《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第40页。其对应的义务也仅限于其他国家对某一民族是否独立、如何对待各种基本权利等自决事项的消极尊重义务。这种狭义理解忽略了自然法意义上集体自决权的积极义务内涵——要求其他国家为其提供必要条件以确保自决权得以实现。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是,在既有实在国际法框架中,对于气候难民要求其他国家提供一块新领土以确保其集体自决权得以维系的权利主张(很多学者认为独立的领土是确保集体自决权的必备条件),其他国家并无相应的履行义务。为破解困局,有学者开始回归自然权利,扩展集体自决权的应有内涵(积极尊重义务),并将领土权利和集体自决权联系起来(集体自决权以领土存在为前提),进而主张气候难民有权向其他国家寻求领土救济——要求加害国提供新的领土,以保障集体自决权的实现。(53)Cara Nine, “A Lockean Theory of Territory”, Political Studies, Vol.56, No.10, 2008, pp.148-165; Avery Kolers, “Floating Provisos and Sinking Islands”,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29, No.4, 2012, pp.332-343; Frank Dietrichand Joachim Wundisch, “Territory Lost-Climate Change and the Viol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Rights”, Mor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Vol.2, No.1, 2015, pp.83-105.换言之,集体自决权遭受损害的气候难民,有权要求其他国家提供一块新的领土,以确保其可以继续作为“自治”“独立”的国际法律实体。
前述观点的一个逻辑前提是将领土权利作为集体自决权的基础。但该前提并不必然为真。这是因为,虽然集体自决权利和领土权利从自然权利转向实在权利都依赖于同一种程序性自然权利,即自然联合权利,(54)为确保个体自我保存,人类必须在享有占有、使用地球资源权利的同时,具有可彼此自由联合的自然权利。自然联合权利是一项自然权利,强调人与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权利,这是由人类的现实处境决定的。“人类的境况似乎比畜类更糟糕,因为很少有其他动物像人这样生下来就如此脆弱”,人类要相互帮助、联合以提高应付生存威胁的能力。参见[德]塞缪尔·普芬道夫著,鞠成伟译:《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0-83页。但二者的基础来源不同。自然联合权利是具有工具属性的程序性权利,其作用仅在于实现个体间的联合,本身并非自然状态中个体应享有的(内在价值型)实体性权利。自然状态中的个体要实现自我保存的自然法义务,在逻辑上应至少享有三项内在价值型自然权利:第一,地球集体资源所有权及其衍生的紧急避难权;第二,自由处置个体发展诸事项的自决权利(个体自由);第三,在自然权利受他人干涉或者妨碍时,原初状态中的个体还享有相应的自然法执行权。因此,我们需要回答自然状态中的个体在行使自然联合权利进入政治社会后,三种自然权利将如何变化。实际上,第一种自然权利作为义务附加于财产权中,而个体自决权和自然法执行权,分别经由社会契约转化为“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自决权利”,以及“国家”的“领土权利”。一方面,个体自然联合成“命运共同体”,提高了自我保存能力,实现了从自然状态向现代政治社会的蜕变,并因自然法执行权的让渡催生了领土权利。(55)See Bas Van der Vossen, “Locke on Territorial Rights”, Political Studies, Vol.63, No.3, 2015, pp.713-728.另一方面,个体进入现代国家后,其个体自决权也因所涉事项的相似性和效率原则而发生自然聚合,由集体决定诸事项,进而衍生出集体的“自治”和“独立”。(56)See Cara Nine, “Ecological Refugees, State Borders, and Lockean Proviso”,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27, No.4, 2010, pp.359-375.可见,集体自决权的价值基础在于个体自决权(自然权利)的自然聚合,而领土权利的价值基础则是个体自然法执行权(自然权利)的让渡,尽管两者均通过自然联合权利生成,但前者不宜直接理解为后者的价值来源或道德根据。二者的唯一关联在于权利客体或者说权利行使的结果都会指向土地等自然资源。因此,对领土权利的损害不一定导致对集体自决权的损害,相应地,对集体自决权损害的救济也并不必然要以恢复领土权利的方式来实现。
以此为基础,有些学者尝试重新解读集体自决权和领土权利之间的关系。例如,乌达伦采用了布坎南式的较弱意义上的自决概念,即自决是一个渐进的光谱式概念,完全领土权利的享有仅是实现自决的一个特例。(57)See Jorgen Odalen, “Underwater Self-determination: Sea-level Rise and Deterritorialized Small Islands States”, Ethics, Policy and Environment, Vol.17, No.2, 2014, pp.225-237.在现实国际社会中,各国可能仅能实现一定程度而非完全程度的自决。在重新理解集体自决权和领土权利关系的基础上,乌达伦提出了一种相对意义上的集体自决权救济方案,(58)在此意义上,不同于直接由其他国际社会为气候难民提供一块新领土的绝对意义上的集体自决权损害救济方案,“去领土化的国家方案”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集体自决权恢复方案。即“去领土化国家方案”。根据该方案,气候难民可以以集体文化社群或民族身份在东道国聚居,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独立的国际法律实体身份(保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包括语言习惯、文化传统等自治权利),并对气候难民原有领土上“被遗弃”的陆地、水底或者相应海洋区域继续行使领土主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乌氏方案成立的两项基本前提:其一,该方案承认集体自决权和领土权利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利,对集体自决权损害的救济并不一定要求领土转让式赔偿,即气候难民可以在不享有领土权利的情况下保有集体自决权,保留国际独立政治法律实体的身份;其二,该方案承认了领土权利的财产权维度,气候难民原籍国虽然已经丧失了在原有领土上建立正义秩序的能力,但其对原有领土上的自然资源仍享有独立的控制权。但乌氏并未就该方案的具体落实路径展开论述。
总之,以集体自决权作为气候难民的权利基础,可在逻辑上导出两种权利救济方案:其一,绝对化集体自决权方案;其二,相对化集体自决权方案,即“去领土化国家方案”。
三、去领土化国家方案在国际气候法框架中的制度展开
气候难民问题是奥尔森第一定律失效引发的一种“公地悲剧”,依赖利益诉求多元、行动能力差异较大的主权国家的个体理性行为不仅实现不了气候难民的权利救济目标,还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效应。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借助于国际社会的干预和适当的制度安排。(59)奥尔森第一定律提出,当集体中人数很少时,尽管个体仅仅寻求自我利益,集体的共同利益也会自动实现。而第二定律是指,当集体人数众多或缺乏强制、激励等特殊手段时,第一定律会失效,即不论个体如何精明地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由于他们不会自愿采取行动实现集体共同的利益,社会的集体理性结果便不能产生。对于国际关系,奥尔森定律同样适用。See 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4.从自然权利的角度来看,气候难民的权利救济方案有四种可能选择:由地球集体所有权衍生的个体紧急避难权方案和地球资源再分配请求权方案(“全球分配正义方案”),以及由集体自决权导出的“绝对化集体自决权方案”(“领土赔偿方案”)和“相对化集体自决权方案”(“去领土化国家方案”)。国际社会宜采用何种方案,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综合考虑。理论上,需要探讨四种方案各自的优缺点,并择出最佳方案;实践层面要考虑最佳方案和既有国际法律制度框架是否兼容,以及如何进行具体制度的构建。
3.1 “去领土化国家方案”是最优权利救济方案
全球气候治理始终面临着公平性和可行性的争论。各主权国家在国家利益和全球公共利益之间不断考量、平衡,力求通过谈判寻找出最公平、最可行的气候公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方案。(60)参见郑艳、梁帆:“气候公平原则与国际气候制度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第1-22页。但气候领域所涉利益的复杂性、动态性、交互性等特征,使奥尔森第一定律失效,各国气候治理立场呈现出不确定性——在气候谈判政治场域中不断进行着利益的分化和重组。(61)《巴黎协定》之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呈现出新动态。发达国家内部出现裂痕,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在美国政策影响下发达国家的立场集体退化,加拿大、新西兰开始与欧盟立场趋同;而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结成强有力的联盟(公约将其从非附件一发展中国家中分离出来),基础四国的内部立场也进一步分化,以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出现退缩。这一客观现实决定了最优气候难民权利救济方案的形成,必然会在公平性和可行性两个层面引起国际社会的激烈争论,最终择出的救济方案也必然是公平性和可行性程度最高的方案。公平性是指,救济方案可以充分救济气候难民的权利侵害,并且不同主权国家间的责任分配合乎气候实质正义;可行性是指,在当下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哪种救济方案最易为各国采纳、接受。主权国家对各种方案的理解和接受不仅取决于方案背后的公平正义理念,还取决于该方案给本国利益带来的影响、各国现实发展条件的差异以及国内政治决策机制的影响等。(62)参见庄贵阳、陈迎著:《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本文以救济方案是否对东道国产生治理挑战作为可行性的衡量指标。
对于紧急避难权方案,其导向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个体化救济方案,即气候难民作为个体有权向其他主权国家请求庇护(主张难民资格)。该方案并未要求转让领土,而是由各国自由决定是否接纳气候难民,实际上可以避免大规模的集体难民潮涌入,遭受的国家抵制相对更少。但国家对气候难民资格的任意解释权会严重制约气候难民能够获得的救济。即使个体有权在东道国以难民身份进行生存,其也仅享有部分公民资格。此外,在该方案中,气候难民遭受的权利损害也无法全部获得救济。(63)例如,政治身份、语言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对社群的集体身份认同等。而对于全球分配正义方案,其意图在全球自然资源分配领域中引入公平原则进行再分配,以促进自然资源财富的平等化。但在奉行“自然资源主权至上”且平权结构特征明显的国际社会现实中,(64)参见李慧明:“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128页。该方案同样无法突破公平性难题。全球分配正义方案强调对国家富余资源的转移,但何谓“富余”很难界定(有极强的价值属性),这就为各国有意规避或减轻责任提供了理由(自身资源稀缺),导致最终被用以救济气候难民的资源极少,很难实现充分救济气候难民所遭受全部权利损害的制度目标。
从气候正义的角度来看,个体紧急避难权方案和全球分配正义方案,均奉行的是单纯的气候分配正义理念,其实质是一种“资源平等观”,强调“一人一份”的地球资源分配方式,这种正义观念对气候难民相关具体责任分配而言过于简单、粗糙,忽略了各国温室气体历史和现实排放程度不同的社会现实,与气候实质正义相悖。(65)事实上,单纯的矫正正义也与气候实质正义相背离,因其仅侧重于在过错方(温室气体排放国)和受害方(气候难民原籍国)之间分配责任,而忽略了气候正义本应涉及的所有主权国家。而集体自决权救济方案旨在融合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理念,更具公平性。集体自决权救济方案在认可各国应当就气候变化承担普遍共同责任的基础上(“分配正义”),强调有区别的责任(“矫正正义”),通过特定的归责原则和标准,将气候难民的权利损害与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联结,为特定国家(“气候加害国”,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而非地球集体所有权救济方案中的任何国家设定具体责任。此外,从充分救济气候难民权利损害的角度来看,集体自决权救济方案是对气候难民的一种集体化救济,可以在救济个体受害者时,赔偿气候难民作为民族集体遭受的集体自决权损害,以维持其民族共同体的存续。因此可以说,集体自决权方案更具公平性。
在集体自决权救济方案内部,“去领土化国家方案”更具政治可行性。这是因为,绝对化集体自决权救济方案需要重新划定国家边界并转让领土,以确保气候难民作为集体有新土地可以安置,此方法容易引起主权国家的抵制。而“去领土化国家方案”具有较高的政治可行性,其承认一种多元化救济方案——国际社会无需向气候难民转让领土,气候难民可以作为独立政治法律实体居留于他国领土范围内,同时保有诸项自治权利。事实上,“去领土化国家方案”主张通过“手段式替代补偿”措施增强气候难民保持自决地位所必需的制度资源和经济资源。(66)经济资源是指开采原领土内自然资源的经济资源,制度资源是用来有效分配自然资源租金的资源。See Maxine Burkett, “The Nation Ex-situ: on Climate Change,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hood and the Post-climate Era”, Climate Law, Vol.2, No.3, 2011, p.345.这一方案可以弱化气候难民与东道国在领土权利方面的直接冲突。

表2 四种气候难民权利损害救济方案的比较分析
3.2 去领土化国家方案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为契合
对最优气候难民权利救济方案的选择还要考虑方案与既有国际法律制度的兼容性。一般而言,兼容性更高的方案是相对更优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更低的制度生成成本。相较于在既有国际法框架中对已有法律的修订,推倒重来的开创式立法(创设一项新公约)需要耗费更多的制度成本,且更易受到主权国家的抵制。考察既有国际法,本文认为,“去领土化国家方案”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间的兼容性最佳。理由有三:其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序言载有“不得造成他国环境损害”,有助于国际社会未来在该公约框架中就“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实现谈判回归。(67)参见程玉:“论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国际法规则”,《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1期,第12-22页。该公约第18届缔约方大会已将“人口迁徙”和“气候流离失所”界定为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中的“非经济损失”,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谈判理论上应当涵盖气候难民问题。其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创设的专家机制、财政支持机制、能力技术合作机制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分担机制,以及该公约广泛的成员国基础等,对于解决气候难民问题具有有利的制度优势。(68)Bonnie Docherty and Tyler Giannini, “Confronting a Rising Tide: A Proposal for a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Refugees”, 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33, No.2, 2009, p.394.其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倡导的气候正义原则与“去领土化国家方案”秉持的气候正义理念相符合。该公约第3条及随后诸气候协议一贯秉承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分配正义基础上的矫正正义,与集体自决权方案兼容。
此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气候流离失所议题上已经取得的制度成果,为进一步落实“去领土化国家方案”奠定了制度构建的基础。但诚如前文所述,既有制度成果过于原则和零散,并且《巴黎协定》进一步加强了国际气候法的软法化。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相关气候协定(主要是《巴黎协定》)暂时均无法为气候难民的权利损害提供周全救济。然而,它们可以为气候难民权利救济问题在国际气候法框架中的“生根”提供初步依据,并为“去领土化国家方案”的制度化奠定规则基础。
3.3 去领土化国家方案在国际气候法框架中的制度构建
《巴黎协定》标志着国际社会打开了为气候难民提供权利救济的缺口,但“去领土化国家方案”要想发挥效力,仍需在国际气候法的既有制度框架中展开具体的制度设计。
首先,国际立法者应以《巴黎协定》序言所载的“气候正义”和“人权保障”为出发点,在未来气候协议中专设气候难民条款或者制定专门的气候难民协议,并建立信息、资金、技术的共享和互助机制,通过综合性风险管理机制提高原籍国和气候难民的适应能力。协定序言提到的“气候正义”,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所蕴含气候正义理念(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融合)的高度提炼,可以为建构气候难民权利救济方案提供正义观念基础。协定序言所涉“人权保障”条款明确列举了迁徙者的权利,为设定气候难民最低权利待遇提供了可能。专门的气候难民条款或协议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有关气候难民的灾害风险管理措施,气候难民的集体自决权,重新安置土地的选择和实施程序,以及国际社会就气候难民重新安置和维持生存所需成本的责任分担机制。
其次,气候难民权利保障的核心要素是对集体自决权的损害赔偿。按照“去领土化国家方案”,这种赔偿形式并非要求国际社会为其提供一块新领土,而是要确保气候难民可以在新的土地上维持生存,至于新土地的领土主权可以仍然归属于东道国。(69)在东道国同意的情况下,气候难民集体和东道国可以达成“嵌入式主权权利安排”或“共享主权权利组合安排”。See Cara Nine, “Ecological Refugees, State Borders, and Lockean Proviso”,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27, No.4, 2010, pp.374-375; Avery Kolers, “Floating Provisos and Sinking Islands”,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29, No.4, 2012, pp.341-342.本文建议,国际社会应考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制度框架内设立“全球土地委员会”,(70)Tracey Skillinton, “Reconfiguring the Contours of Statehood and the Rights of Peoples of Disappearing States in the A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Social Sciences, Vol.5, No.3, 2016, p.55.由其联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机构负责研究不同区域气候难民的迁徙模式和可能路径,并在全球范围内研究推行一种公平可行的“土地拍卖机制”或“土地长期租借机制”,为气候难民选择可能的定居土地。但气候难民原籍国往往是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和自然资源并不富裕的“小岛屿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无法筹集足够资金来支付土地的租金或使用费。加之,按照气候正义的原则,气候难民遭受的损失理应由国际社会共担。因此,国际社会还有必要确立一种公平合理的资金分担机制。本文建议,资金分担机制的具体责任分配标准应同时兼顾气候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理念,重点考量以下几组核心指标:第一,“过错指标”,以污染者付费为原则,考量199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科学报告发布之后各国人均历史累积的非生存排放量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比例;第二,“能力指标”,以能力支付为原则,考察各国自然资源的富裕程度(例如,土地利用情况/人口密度、各国未来的碳汇资源实力)、收入财富水平(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三,“衡平指标”,针对特殊情况的“衡平处理”,例如:(1)基于“隐含碳”原理,扣除转移排放对“生产者责任”的影响;(2)免除或减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对气候难民问题的责任承担等。(71)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第29-48页。至于具体目标的最终选择和多元目标间的组合方式,与国际社会在减缓和适应领域面临的责任分担争议相同,需要经过多轮气候谈判方可实现。(72)基于不同利益和立场,各主权国家持有不同的责任分摊观念。参见张丽华、李雪婷:“利益认知与责任分摊:中美气候谈判的战略选择”,《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34页。
有人可能会质疑,这种自上而下式的责任分担机制似乎与《巴黎协定》确立的自下而上式的全球治理新路径发生冲突。事实上,本文提出的“去领土化国家方案”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混合的模式。一方面,该方案提倡一种自愿的土地租赁机制,鼓励各国探索灵活的主权结构,体现了“自下而上”;另一方面,该方案要求各国承担公平的资金责任,为气候难民重新定居提供财务保障,东道国需为气候难民确立最基本的权利待遇,体现了“自上而下”。这种混合机制和《巴黎协定》确立的顶层管控和自由灵活特征相结合的规则模式相契合。(73)参见于宏源:“自上而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模式调整:动力、特点与趋势”,《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0页。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届缔约方大会以后,《巴黎协定》的“自上而下”色彩不断增强,旨在就协定实施细则进行磋商的卡托维兹气候大会最终通过统一规则为“自下而上”的松散协定注入了更多强制性色彩,提升了协定的法律地位。(74)参见朱松丽:“从巴黎到卡托维兹: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统一和分裂”,《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9年第2期,第209页。
最后,为确保气候难民权利保障机制的落实,相应国际法规则需要修正。其一,修订有关国际法主体的成立、承认标准。根据1933年《蒙得维的亚公约》第1条规定,国家成立必须以领土作为必备要素。(75)参见《蒙得维的亚公约》第1条,根据该条规定,作为国际法上的主体的国家需须具备4个条件,即永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政府(有效控制)、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的能力。对于“去领土化国家方案”而言,这会构成障碍。因此,本文赞同托马斯·格兰特(Thomas D. Grant)对《蒙得维的亚公约》项下“领土”要素标准的重新解读——领土对国家资格来说并不是必须要素,《蒙得维的亚公约》第1条标准的含义主要是表明一个主体能否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要表明一个主体如何终止其国家资格。(76)See Thomas D. Grant, “Defining Statehood: The Montevideo Conven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37, No.2, 1998, p.435.一旦特定的民族集体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便不再会因为失去领土或失去对领土的有效控制而失去国家资格。(77)参见何志鹏、谢深情:“领土被海水完全淹没国家的国际法资格探究”,《东方法学》,2014年第4期,第92页。这就意味着,集体居留于东道国的气候难民仍可保留其国际法主体资格,有权代表国民主张集体自决权损害赔偿。其二,修订国际海洋法。为确保集体自决权的充分赔偿,要对现行国际海洋法规则进行修订,允许冻结当前海域的外部界限,以保留气候难民对原海域的领土主权,尤其是对海域自然资源的主权。(78)See Sarra Sefrioui, “Adapting to Sea Level Rise: A Law of the Sea Perspective”, in Gemma Andreone, ed., The Future of the Law of the Sea,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 2017, pp.3-22.其三,为促进气候难民集体自决权救济方案在国际气候法框架中的制度展开,后巴黎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还应关注气候程序公平目标的落实,努力构建一套更加公平的气候谈判程序规则。只有保障利益相关方的全方位参与,平等表达意愿,才能避免制度实施中的“搭便车”和“外部性”等问题。
四、结 语
有关气候难民问题的国内研究刚刚起步,在“实在国际法”盛行的当下,以自然权利为视角来研究气候难民问题更是“人迹罕至”之径,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价值所在。在国际法碎片化的背景下,气候难民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使得自然灾害法、人权法、难民法、环境法、移民法等部门国际法在理论上均可适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有国际法律保障机制均是基于温室气体浓度控制、自然灾害救济、难民和移民保护等特定目标而创设的国际法律规范。它们在创设之初并未考虑到气候难民问题,使得气候难民救济权利在实在国际法框架中存在规范缺位。但从自然权利和实在权利二分互动的观点来看,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和部分自然权利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导致了自然权利向实在权利的转化具有不完全性。那些暂时未能转化的自然权利并非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其法律效力在道义上并非必然低于法律权利。因此,尽管气候难民不享有实在救济权利,但其仍享有自然救济权利。本文认为,个体紧急避难权和集体自决权可作为气候难民寻求救济的权利基础。在综合比较分析之后,相对化集体自决权方案(“去领土化国家方案”)是最优选择。该方案可与国际气候法框架良好兼容,并且《巴黎协定》为该方案的制度构建奠定了理念和规则基础。未来国际立法者应着重考虑如何在国际气候法的框架中将“去领土化国家方案”展开为具体的实在法制度体系。
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其在气候谈判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在始终坚持集体自决权方案的基础上,尽量规避发达国家最抵触的领土转让赔偿,支持“去领土化国家方案”,同时将损害责任转化为资金义务,进一步弱化责任刚性。在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由双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向三元(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其余发展中国家)且不同利益集团气候立场分裂的格局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集体的代表之一,必须警惕发达国家和更弱发展中国家可能就气候难民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多责任。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宜采取拒绝承担责任的简单策略,这不仅会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让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脱离”发展中国家阵营。因此,为确保未来中国不至处于不利地位,中国政府应积极推进气候难民国际议题的谈判工作,尤其应通过科学研究强调气候难民问题对自己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自身在应对气候难民问题上的可能贡献。在气候谈判中,中国政府应在强调自身责任、能力的同时,努力敦促发达国家按照气候正义原则承担责任,并在实践中以“南南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在气候难民问题方面加强与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开展合作行动。
——聚焦各国难民儿童生存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