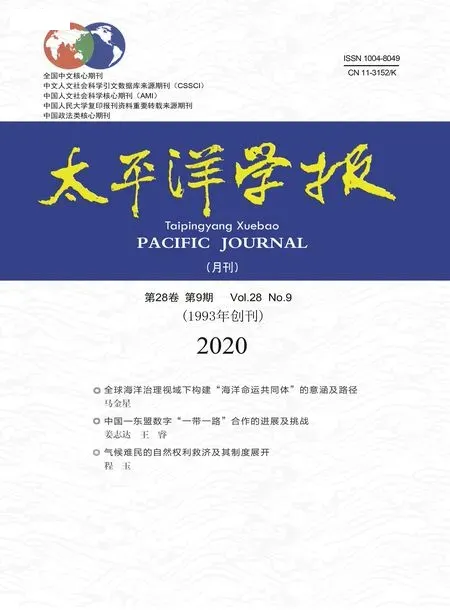崛起国缘何陷入战略迷思
——基于一战前德国海权战略决策的实证研究
徐若杰
(1.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历史一再证明,战略缺失或失当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1)本文所使用的战略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大战略。根据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的经典阐释,“大战略的任务为协调和指导一切国家资源(或若干国家的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则由基本政策决定”;此后,大战略的内涵在二战后逐步拓展,战略工具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手段,政治、经济、外交等被囊括其中。中国学者周丕启对比考察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大战略做出了折中的界定,“所谓大战略,是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运用自身实力,主要是战略实力来维护自身安全的科学和艺术,是对战略实力调动、分配、投送和运用过程的筹划和指导。”参见B.H. Liddell Hart, Strategy, Plume, 1991, pp.335-336;周丕启著:《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对处于崛起关键期的国家而言,战略决策是否符合理性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2)在西方政治理论中,理性通常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实质理性,目标偏好选择是否合理且能够带来增进生存或产生其他方面的意义;其二是工具理性,选择的战略工具与目标是否匹配。本文重点考察工具理性层面。关于理性问题的讨论参见Sidney Verba, “Assumptions of Rationality and Non-Rationality in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Vol.14, No.1, 1961, pp.93-117;董柞壮:“国际冲突研究的理性范式:争论及启示”,《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2期,第93-107页。虽然国际竞争的烈度和性质由互动双方的战略选择决定,理论上可以实现有效管控,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良性大国竞争,(3)这里的良性大国竞争主要是指烈度得到有效管控,竞争双方没有爆发直接冲突。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两国在埃及、英美在委内瑞拉、英俄在中亚和波斯的殖民利益争夺、1947—1991年间的美苏竞争等。然而,更多的图景却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频繁的竞争失控,乃至爆发大战,(4)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团队考察了近500年崛起大国与守成霸权国之间的权势博弈,在其选取的16个案例中只有4个没有爆发战争,参见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双方似乎难逃“修昔底德陷阱”的悲剧宿命。崛起国的决策精英基于某种战略迷思所做出的非理性战略决策与实践,是这种悲剧反复上演的重要原因。(5)需要强调的是,导致霸权国—崛起国冲突的因素极为复杂,“战略迷思”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是一种用于分析的抽象微观视角,并不代表此类冲突的背后都隐含着这一因素的作用。
全文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学界关于一战前德国海权战略决策成因的已有研究,重在讨论既有解释的不足;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的解释视角——战略迷思,梳理了其中蕴含的理论机制,构建了分析框架;第三部分运用前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对一战前德国海权战略决策进行过程追踪,对理论机制的有效性进行深度检验。力求依托一战前德国海权战略决策与实践的历史,(6)海权战略指一国所采取的以海军发展和建设为核心内容,以谋求海权为最终目标的发展战略,主要涉及海上力量的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军事学说等具体方面。关注崛起国的决策精英何以形成战略迷思这一理论问题。
一、关于德国海权战略决策成因的解释
作为崛起国与霸权国竞争失控的经典案例,一战前的英德海军竞赛是一个广受学者关注的议题。其中有关德国战略决策成因的已有解释,在分析层次上涉及了体系和国内政治层面的多种变量。依据理论范式和分析视角不同,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类。
1.1 权力转移解释
权力转移被视作英德海军竞赛研究的“正统范式”。(7)Matthew S. Seligmann, The Royal Navy and the German Threat 1901-1914: Admiralty Plans to Protect British Trade in a War Against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36.基本逻辑是一战前德国海权战略决策根源于双方霸权国—崛起国二元对立的结构属性。在这种范式下,英德两国在体系中的不同排序和身份决定了双方利益的根本性对立,除了对抗别无选择。亚瑟·马德尔(Arthur Marder)将英德海军竞赛的成因解释为结构性的安全困境;(8)See Arthur J.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Volume I: The Road to War 1904-19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霍尔格·赫维希(Holger H. Herwig)认为作为崛起国,德国在战列舰数量上单方面挑战英国海上主导权的行为,摧毁了德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空间,塑造了英德敌对。(9)See 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Routledge, 2014. 采用这一视角的研究还有很多,在此不做赘述。See Peter Padfield, The Great Naval Race: Anglo-German Naval Rivalry 1900-1914, Thistle Publishing, 2013; John Charmley, Splendid Isolation? Britain,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Faber and Faber, 2009;吴征宇:“《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的起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2期,第44-55页;顾全著:《大陆强国与海上制衡:1888—1914年德国的海军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该范式带有一种宿命论色彩,似乎大国竞争难逃对抗和冲突的悲剧,崛起国与霸权国的互动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生存博弈,但国际政治并非一个机械的系统,国家间互动的结果是由政策选择而非某种客观规律支配。这类研究相对忽略了战略互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未能充分解释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决策精英,其主观认知和选择对于国际政治互动结果的影响。
1.2 大战略解释
一些学者倾向于将德国海权战略决策作为大战略缺失的表现进行研究。由于大战略范围颇为宽泛,因而这类研究几乎囊括了物质和心理方面的所有变量。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指出,德国混乱、反复无常、恃强凌弱的对外战略,最终迫使英国建立反德联盟以寻求安全;(10)See Jonathan Steinberg, Yesterday’s Deterrent: Tirpitz and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Battle Fleet,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6.徐弃郁认为,“单骑突进”式的“大海军”建设是威廉二世等德国决策精英缺乏大战略远见的直观体现,并造成了德国大战略的瓦解,(11)参见徐弃郁著:《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梅然也持类似观点;(12)参见梅然著:《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姜鹏则从德国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地缘政治特征入手,分析了德国海权战略失败的原因。大战略分析着眼更为宏大的战略图景,从作为整体的大战略入手,对作为大战略从属之一的海权战略进行解释。存在的不足是,部分研究过度关注事后分析评判的“客观合理性”,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果导向”问题,即因为德国在一战中遭遇了失败,所以德国的很多战略必然存在严重缺陷,结论有失偏颇。(13)参见[德]弗里茨·费舍尔著,何江、李世隆等译:《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的战争目标政策》,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3 军事战略解释
这种解释视角将德国海军建设的悲剧性后果归结为军事战略方面的错误。德国退役海军军官魏格纳(Wolfgang Wegener)对一战前德国的海权战略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未能充分把握英德地理位置差异是德国海权战略设计的最大败笔;(14)See Wolfgang Wegener,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指出,德国海权战略的失败之处在于误解了制海权的真正含义;(15)参见[美]赫伯特·罗辛斯基著,吕贤臣等译:《海军思想的演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霍尔格·赫维希认为,德国海权战略失败的根源是违反了马汉的海权六原则。(16)Holger H. Herwig, “The Failure of German Sea Power, 1914-1945: Mahan, Tirpitz and Raeder Reconsidere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10, No.1, 1988, pp.68-105.海军是一战前德国海权战略中最主要的内容,上述文献有助于深入理解德国海权战略选择的军事考虑。但此类研究往往倾向于将海军战略作为独立对象,而非国家整体战略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将海军战略的错误视作导致海权战略彻底失败的根源,以海军战略设计是否科学代替了视野更为宏大的国际关系理解,这客观上夸大了军事战略在国家整体战略体系中的地位。
1.4 国内政治解释
国内政治解释考察的是一战前德国政治体系中的决策精英、各类官僚组织和社会力量,围绕权力和资源分配展开的政治行为,以及此类行为对于海权战略的影响。既有文献可以依据侧重点差异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涉及部门利益,将塑造德国海权战略选择结果的主因,归结为以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为首的海军官僚组织,基于对部门利益的追求,有意识地施加政策影响。(17)See Carl-Axel Gemzell, Organization, Conflict and Innovation: A Study of German Naval Strategic Planning 1888-1940, Esselte Stadium, 1973, pp.50-137; Gary E. Weir, Building the Kaiser’s Navy: The Imperial Navy Office and German Industry in the Tirpitz Era, 1890-1919, Naval Institute Press,1992; Jonathan Steinberg, “The Copenhagen Complex”,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1, No.3, 1966, pp.23-46.第二类涉及战略认知,将参与海权战略决策过程的决策精英作为关注对象,认为他们基于自身经验和价值选择形成的战略认知,是影响海权战略选择的关键因素。(18)See Ivo Nikolai Lambi, The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1862-1914, Allen & Unwin, 1984; Michelle Murray, “Identity, Insecurity,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The Tragedy of German Naval Ambition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4, 2010, pp.656-688 ; [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盖之珉译:《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三类则关注社会力量,一些学者讨论了社会团体、媒体等社会力量对德国海权战略选择的影响。(19)See Oron James Hale, Publicity and Diplomac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and and Germany, 1890-1914, Peter Smith, 1964; Rolf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the Ideology of Sea Power, and the Tirpitz Plan, 1875-1914, Brill, 2002.此类文献在解释范围上几乎囊括了全方位的国内政治变量,但是对各层次变量之间的抽象因果机制考察相对欠缺,尤其是尚未形成一个简约的科学化理论框架。
总体而言,上述四种既有研究成果虽然数量充分,但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德国决策精英会执意选择一个在理论上就存在不足,而且事后被证明为错误的海权战略”。本文认为需要转换研究思维,更多地关注“为什么决策精英认为这种战略选择是合理的”,而不是“以今人眼光来看,这种战略选择错在哪”。另一方面,既有成果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方法,注重细节的梳理和史实的考证,理论化的思考存在不足。将具体的历史分析考察嵌入抽象的中层理论框架,是国际战略研究的新趋势,(20)美国《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杂志在1997年第1期将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作为当期专题进行了系统讨论。有助于厘清战略过程诸环节及其中变量的相互作用机制,实现知识积累和创新。
二、战略迷思的成因:理论机制及分析框架
战略迷思是指一种非科学、属幻想的,无法结合现实的主观价值,是战略行为体在战略决策与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偏执的错误认知倾向。(21)涉及战略迷思的理论讨论参见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tion in the Periphe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ao Resende-Santos, Neorealism, States, and the Modern Mass Ar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美]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等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简化、机械、偏执的战略认知模式。陷入其中的决策精英普遍基于某种战略冲动的非理性认知偏差,而非对具体战略环境的审慎体察进行战略谋划和运作。(22)时殷弘:“关于中国对外战略优化和战略审慎问题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第1-5页。通常表现为将复杂的大国博弈简单理解为,“如果获取了霸权国拥有的某种权力,安全和国际地位均可获得,否则将危及生存”。这种认知偏差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决策精英对标霸权国的“学习”倾向,即崛起国的决策精英以体系霸权国的能力为参照,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倾向。(23)唐世平、王凯主编:《历史中的战略行为:一个战略思维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另一方面,则与精英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有关。其负面影响是选择不足以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甚至将某种战略工具当作战略目标本身,忽视自身客观真实的利益需求。(24)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第36-42页。
本文聚焦的是崛起国内外部的环境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决策精英—社会双向认知互动与非理性战略认知—战略迷思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在这一理论机制中,居于中心的主体是决策精英。体系压力和社会心理焦虑是其形成机制中的两个核心自变量,而基于历史传统所形成的战略文化则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常量,(25)Jeffrey S. Lantis, “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 No.3, 2002, pp.87-113.发挥结构性的约束作用。国内政治博弈则是决策精英与社会进行认知互动的中间变量。组织利益和行为反映的是,组织内部“路线斗争”博弈胜出的决策精英群体对整体利益的认知与偏好。(26)王鸣鸣著:《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因此,本文排除了组织的内部分歧,关注的是已经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占据主导地位且对战略决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认知结果。本文也未对组织文化因素的影响作单独测量,因为这一因素主要在组织内部“路线斗争”中发挥作用。而在国内政治博弈中,组织行为已包含了组织文化作用的结果。
第一,体系压力改变战略决策的外部环境。所谓体系压力,是指因大国竞争引发国际结构变化而带来的体系层面的外部安全压力。这种安全压力的来源可细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伴随崛起进程而来的实力增加,引发霸权国的制衡性竞争行为,由此加大崛起国的外部安全压力;其二,在与霸权国的竞争互动中遭遇外交挫折。作为决策精英,需要对体系压力做出及时感知、评估和回应。当现有政策工具无法满足安全需求时,体系压力的增加促使崛起国的决策精英通过增强实力进行必要的应对,包括弥补与霸权国之间的物质实力鸿沟,尤其是军事实力,以及强化面向社会的战略动员,如通过舆论宣传和引导向社会传递国家处于生死攸关状态的威胁认知、(27)[美]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等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1页。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培育民众的国家荣誉感。(28)梁雪村:“‘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为什么没有衰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第97-112页。而实力的增加必然加剧竞争烈度,遭遇霸权国更为激烈的制衡。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体系压力持续增加容易导致决策精英群体的“安全感缺失”,他们的上述心理状态会通过战略动员传递给社会,并受到社会的反向作用,由此形成一个循环过程。
第二,崛起进程中的社会心理焦虑改变战略决策与实施的内部环境。社会心理焦虑包括社会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对更高国际地位的追求,以及与此相关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等多个方面。其来源主要包括社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感知,以及决策精英出于应对外部竞争的需求进行的战略动员。这种来自国内社会的压力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改变社会环境,限制决策精英的战略选择。当某种权力类型被标志化为国家地位,强大的社会压力会对战略决策形成巨大干扰。而对社会心理焦虑回应不足,容易引起决策精英集团的分裂,降低精英凝聚力,增加政权脆弱性,而这种状况也阻碍了战略决策中科学、理性和审慎评估的展开。出于对社会稳定和自身政治利益的理性考量,决策精英通常倾向于迎合大众诉求,很难依时据势调适国际行为。狂热的社会情绪将推动其选择激烈和强硬的国际竞争,最终陷入与霸权国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其二,社会心理焦虑反向作用于决策精英的战略认知。在大众政治时代,发达的传播体系与网络、多元的意见表达渠道和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团体等保障了决策精英与社会之间畅通的联系。社会心理焦虑通过彼此之间的联系机制,借助国内政治博弈反向回输给决策精英,对其战略认知产生塑造作用。
第三,战略文化作用下的战略决策路径依赖。战略文化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类似于一种结构,反映的是基于历史传统所形成的文化因素,如历史记忆、社会规范、军事学说等对战略缔造的影响。(29)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战略文化的价值已为学界普遍公认,但是其测量难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目前通行的方法仍然是经验性的定性研究,依据对历史与现实关联性的联想获得,需要发挥社会科学的想象力。通常体现为某种建立在特殊战略理念基础上的认知和行为路径依赖,其作用客体涵盖政府、政治决策精英群体和军事统帅等。本文重点关注战略文化如何通过影响决策精英应对内外部压力的战略认知,以及工具偏好,最终对战略决策和运行产生影响。战略文化具有鲜明的保守性特征,据此形成的路径依赖限制了改善崛起困境的创新性战略路线的选择,(30)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第4-33页。导致决策精英的认知和行为难以根据形势的快速变化进行调适。
第四,国内政治博弈是战略迷思形成机制的中间变量,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中间现象而存在,(31)[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是决策精英—社会认知互动的重要连接点。一方面,国内政治博弈事关资源分配。在大众政治时代,不同部门的决策精英出于各自的组织利益,需要通过动员来有效整合社会力量,进而影响国内政治结果。另一方面,组织化的社会团体,如利益集团、新闻媒体等也通过国内政治平台产生内部压力,促使决策精英群体回应其利益诉求,反向作用于精英群体战略认知。由于凝聚社会共识有利于在国内政治博弈中获得有利地位、充分汲取战略资源、实现官僚机构部门利益,崛起国的决策精英需要同时引导社会舆论以支持其政策主张,以及回应社会大众的心理诉求,巩固这种支持,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图1 战略迷思的形成机制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海权迷思”与德国海权战略
在一战前德国的海权战略选择中,决策精英群体表现出一种高度神化海权的战略迷思——本文称之为“海权迷思”。需要强调的是,本案例所指的决策精英,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在海权战略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的德皇本人和海军部高层,而非德国全部军政决策精英。1897年至1914年,由于威廉二世的鼎力支持和干预、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卓越的个人能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大海军主义”势力在德国海权战略决策中处于统治地位。(32)See 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Routledge, 2014; Rolf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 Naval Strategic Thought,the Ideology of Sea Power and the Tirpitz Plan 1875-1914, Brill and Academic Publisher, 2002.其他决策精英,或难以介入海军事务并影响决策,如1912年之前的德国陆军军官团;(33)徐弃郁著:《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46-256页。或被内外政治形势变化所“说服”,如一直对海军建设持怀疑态度的时任德国首相霍亨洛厄(Hohenlohe),他在美西战争后开始转而支持提尔皮茨的计划;(34)[美]诺曼·里奇著,吴征宇、范菊华译:《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5页。或未能左右海权战略的走向,如1909年“海军恐慌”期间,接替毕洛夫(Bernhard Bulow)担任首相的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也不支持“大海军主义”,而是主张通过与英国谈判签订政治协议和海军协议,缓和并最终结束海军竞赛,(35)Arthur J.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Volume I: The Road to War 1904-19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171-177.但由于提尔皮茨的反对和英国态度的冷淡无果而终。而海军部内部的反对声音,则遭遇了提尔皮茨的政治打压和言论“屏蔽”,难以形成影响,如提尔皮茨在德皇授权下,实施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反对其海权战略的书籍和文章很难面世。(36)Ivo Nikolai Lambi, The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1862-1914, Allen & Unwin, 1984, p.166.1900年,德国驻英大使哈兹菲尔德(Hatzfeldt)给外交部的一封信,间接反映了提尔皮茨强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的对外政策取决于提尔皮茨的看法,那我们在世界上绝不会有太大发展”。(37)Norman Rich, Friedrich Von Holstein: Policies and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Bismarck and Wilhelm II,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598.
“海权迷思”的基本逻辑可以简单概括为,“德国的安全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必须获得与英国接近的海权”。(38)Jonathan Steinberg, “The Copenhagen Complex”,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1, No.3, 1966, pp.23-46.这种战略理念的突出特征是将控制海洋等同于国家发展,以军事战略思考替代了大战略考量,认为夺取制海权即可实现国家强盛。原本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内容的海权被等同于军事意义上的制海权,海权战略从大战略的层次下降到了军事战略层次。
3.1 体系压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面临的三大体系压力决定其海权战略决策始终缺乏一个持续稳定的外部环境。一是,在“海军至上主义”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大国竞争内容的转变带来的压力;二是,回应英国制衡不断升级的压力;三是,在多次外交受挫后,如何维护国家荣誉的压力。三者既独立作用,也相互促进,其中的逻辑关系简要概况为:“海军至上主义”时代背景,既增加了德国发展海权的现实需要,又刺激了其发展海权的欲望;德国海权的不断增强导致了英国制衡力度的持续升级,增加了德国的外交挫折频次;结果进一步刺激了决策精英群体获得更高海权地位的意愿,特别是建设“大海军”的决心。
第一,“海军至上主义”时代激烈的大国竞争。德国的“海洋转型”发生于“海军至上主义”的大环境之下,受马汉海权思想、帝国主义扩张思潮和日趋激烈的海外利益争夺的共同影响,英国、法国、美国等世界主要强国纷纷热衷于海军扩建,国际事务的走向和基调常常由他们的战舰数量决定。(39)Lisle A. Rose, The Age of Navalism 1890-1918,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7, p.xi.这种大范围的“海军狂热”深刻改变了德国战略决策的外部环境,增加了德国决策精英对自身安全的担忧。(40)Rolf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the Ideology of Sea Power and the Tirpitz Plan 1875-1914, Brill and Academic Publisher, 2002, pp.154-177.在这种背景下,竞逐海权成为威廉二世时代德国最为重要甚至唯一的目标。毕洛夫在回忆录中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当时的对外政策,是受到军备问题制约的,不得不在一种非正常条件下推行”。(41)Bernhard Bulow, Imperial Germany, Cassell and Company, 1914, p.93.1897年,霍亨洛厄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我们要奉行一种和平的政策,必须要使舰队足够强大……在涉及海洋的问题上,能够说一种温和的、但纯粹德国的语言”。(42)Jonathan Steinberg, Yesterday’s Deterrent: Tirpitz and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Battle Fleet,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 p.164.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对马汉的学说深信不疑,认为发展海权是德国保证自身安全、避免在大国竞争中掉队、谋求“世界强国”地位的必由之路。在1894年给友人的信中,威廉二世写到,“我不是在读,而是在吞咽马汉上校的书。我努力要把它背下来”。(43)Ivo Nikolai Lambi, The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1862-1914, Allen & Unwin,1984, p.34.1897年法绍达危机后,威廉二世充满讽刺地说,“可怜的法国人……他们没能理解马汉”。(44)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Allen Lane, 1976, p.206.德皇还在1908年表示,“我不希望以德国海军的发展为代价换取英国的友谊,这是对德国的羞辱与冒犯……海军法案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英国人喜不喜欢都随它去。如果英国人企图发动战争,德国也绝不退缩”;(45)Johannes Lepsius, 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a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1925, p.104.提尔皮茨在一战后的回忆录中夸耀自己的海权战略设计是马汉海权思想的完美实践。(46)Alfred von Tirpitz, My Memories,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19, p.72.
第二,来自英国的制衡压力。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后,英国逐渐将德国而非法俄同盟作为制衡的首要对手,通过《英法协约》《英俄协约》等战略部署调整、大规模增加海军建设投入等方式对德国进行强力制衡。(47)胡杰著:《海洋战略与不列颠帝国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226页战略环境的恶化增加了德国决策精英的恐惧与愤怒,促使其做出更加激进的战略决策,使得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日益结构化。例如,1906年第二次海牙会议前夕,英国曾提议将限制海军竞赛作为会议期间英德谈判的主要内容,德皇将此看作英国企图欺骗德国放弃海军发展的阴谋,明确指出“每个国家都必须按照保护自身利益和维持国际地位的需要来决定它所需军事力量的规模”,(48)Arthur J.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Volume I: The Road to War 1904-19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30.因而拒绝了这一建议;提尔皮茨的态度更加直接地反映出德国决策精英的不安全感,“英国已经比德国强大四倍了,并且与日本和法国结盟。这样一个巨人却要求德国这样的侏儒削减军备……我们已经决定要拥有一支舰队,而且要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建造和维持这样的舰队”。(49)同⑦, pp.130-131。马德尔指出,“海军竞赛被英国视为德国试图称霸欧洲的有力证据。德国海军发展构成了英国自由施展政治影响的最大障碍,这是两个国家相互仇视的焦点。海军竞赛并没有引发战争,但它保证一旦战争爆发,英国必然处于德国的敌对方”。(50)同⑦, pp.431-432。
第三,1896年“克鲁格电报事件”以来的多次外交受挫,使德皇与提尔皮茨等德国决策精英坚信:必须迅速发展一支足够强大并能够对英国构成有效威慑的舰队,才能避免继续在外交中遭受侮辱。“大舰队”被视作大国地位和国家荣誉的一种标志。1899年12月,英国在非洲海域扣押了德国邮轮“班德罗斯号”,理由是怀疑该邮轮经葡属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奎斯港给布尔人运输违禁物资。依仗海军优势,英国在海上的霸道行为在德国国内掀起了巨大的反英浪潮。(51)Ivo Nikolai Lambi, The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1862-1914, Allen & Unwin, 1984, p.156.提尔皮茨认为这一事件唤醒了德国上下对海军羸弱现实的清醒认识,是德国海军大规模扩建的“东风”。(52)[美]诺曼·里奇著,吴征宇、范菊华译:《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页。此后在1901年,威廉二世将萨摩亚纠纷中德国未能实现预期利益目标,也归结于德国海军实力的羸弱。(53)Paul M. Kennedy, “German World Policy and Alliance Negotiation with England”,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5, No.4, 1973, pp. 605-625.
3.2 社会心理焦虑和国内政治博弈
部分与海军发展利益相关的决策精英进行的社会动员活动,推动民众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身份认同,即将海权作为实现国家安全与追求更高国家荣誉的唯一要旨,并反向作用于德国决策精英的战略认知。强大的舆论压力压缩了决策精英的战略选择空间,使其更加倾向于选择一种“对标”霸权国能力,带有强权政治逻辑的国家崛起方式,客观上促进了战略迷思的形成。例如,在1898年至1901年间,英德两国曾经进行过三次结盟谈判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皇和毕洛夫认为,英德结盟一旦形成,会使德国丧失建造“大舰队”的理由,同时招致国内“大海军主义”、殖民主义等社会势力的反对,因而在谈判中采取了消极的态度。(54)See Eckart Koch, “The Anglo-German Alliance Negotiations: Missed Opportunity or Myth?”, History, Vol.54, No.182, 1969, pp. 378-392; Paul M. Kennedy, “German World Policy and Alliance Negotiation with England”,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5, No.4, 1973, pp.605-625.而1908年8月11日,英国外交部次官哈丁(Hardinge)希望德皇以两国关系全局为重,接受英国限制军备的建议,但德皇认为这是英国利用海军优势对德国的又一次威胁性侮辱,愤然表示德国海军建设事关国家荣誉,任何国家都无权对此说三道四。英国的海军实力已经超出了两强标准,德国如果接受建议,将引发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满,影响政治稳定,德国因此必须完成海军建设计划。德国宁可走向战争,也不愿屈服于这种霸权。(55)George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Vol.VI,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28, pp.185-186.
第一,国际权力上升引发社会焦虑。1871年的统一是德国作为大国崛起于欧洲的重要标志,此后直至1914年一战爆发,高速崛起是德国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56)以年均经济增长率数据为例,1880—1890年,英国、德国分别为2.2%、2.9%,1890—1900年均为3.4%,1900—1913年英国为1.5%,德国则达到了3.0%;保罗·肯尼迪将1900年的英国工业潜力赋值为100,作为参照指标研究了主要大国的工业潜力。在选取的1890年、1900年和1913年这三个年份中,英国得分为 73.3、100和127.2,德国为27.4、71.2和137.7;在1890年、1899年和1913年,德国在国际贸易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9.3%、22.2%和26.4%。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Unwin and Hyman, 1987, p.201.达到了“自1815年以来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达到过的发展速度”。(57)F.H. Hinskey, Power and Pursuit of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300.一方面,综合国力的日新月异,对于德国人的世界观和身份认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塑造作用。这突出表现为一种“国际地位焦虑”,即实力的迅速增加,强化了德国社会对更高国际地位的追求,希冀“世界大国”地位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和尊重。德国想要的是影响力,而不是某种需要通过外交谈判讨价还价的具体物质利益,“是别人的肯定,是权利的平等,是一套加载了复杂情感和心理宣泄的目标……德国人想要的是他们认为英国人已经拥有的东西”。(58)Jonathan Steinberg, “The Copenhagen Complex”,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1, No. 3, 1966, pp. 23-46.另一方面,大国竞争增加了体系压力,使得社会不安全感增加。“克鲁格电报事件”后的每一次英德外交摩擦,即便是很小的问题,都会引发德国社会对于自身安全的深度担忧。例如1907年,“费舍尔(Fisher)来了”(59)费舍尔(时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要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海上打击。的传闻在德国基尔港引发了大规模社会恐慌,很多家长持续两天不敢让孩子去学校;(60)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Routledge, 2014, p.51.1911年,在英德关系高度恶化的背景下,德军将领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出版了《德国与下一场战争》,鼓吹德国如无法通过征服新领土成为“世界强国”,则只能被毁灭。(61)See Friedrich 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General Books, 2010.
第二,决策精英的战略动员助长了民众的社会心理焦虑。提尔皮茨为了筹集更多战略资源用以实现“大海军”建设目标,降低帝国议会的阻力,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以获取支持。采用的方式包括把海军主管的出版物从技术性刊物转变为大众读物,在海军办公室增设新闻署,支持成立民间组织“海军协会”,以及拉拢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知名学者组成“舰队教授”群体等,以此增加宣传效果。其结果是进一步激发了德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广阔的海外殖民地被德国社会视作英国全球性影响力的象征,海权成为一种民族主义虚荣心的满足,一种国际政治地位宣示信号,一种在大众政治时代通过精英说服和动员民众力量、增进民族忠诚的政治宣传艺术。保罗·肯尼迪(Paul M. Kennedy)指出,“鼓吹自己君主受欢迎的程度,将整个民族凝聚在一起,以从事极具冒险性的海军扩张和对外政策来抑制国内反对意见,便成为那些受德皇保护的随从们不可动摇的决心”。(62)Paul M. Kennedy, “German World Policy and Alliance Negotiation with England”,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5, No.4, 1973, pp. 605-625.
第三,国内政治博弈的影响。在一国政治体系中,鉴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不同官僚组织借助政治博弈竞争资源在所难免,(63)郝诗楠:“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军政关系:趋势、议题与未来议程”,《比较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辑,第74-96页。这一问题对于新生的德国海军来说更为重要。在一个容克地主阶层占据统治地位,陆权被长期作为立国之本的大陆国家,海军这样一个以新兴中产阶级平民出身的官兵为主的军种,面临着汲取战略资源的巨大困难。因此,利用国内政治机制获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以社会力量压制帝国议会的反对势力,实现部门利益的最大化,是海军决策精英的一种理性选择。除了上文提到的社会动员,提尔皮茨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争取支持。(64)历史学家斯坦博格(Steinberg)将提尔皮茨称为“在俾斯麦时代与斯特莱斯曼之间最成功的德国政治家”。在动荡与躁动不安的威廉时代,他的人事协调能力、公共舆论操纵能力、行政管理能力,以及政治沟通与协调能力超越同时代的所有德国政客。Jonathan Steinberg, Yesterday’s Deterrent: Tirpitz and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Battle Fleet,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 pp.204, 206.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利用威廉二世对海军事务的抱负争取支持,通过建立和维持私人关系获取有影响力的政客支持,与议会中的天主教中央党结盟,以及在德皇支持下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65)Ivo Nikolai Lambi, The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1862-1914, Allen & Unwin ,1984, p.166.打压国内反对声音等。(66)提尔皮茨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策略参见Jonathan Steinberg, Yesterday’s Deterrent: Tirpitz and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Battle Fleet,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 pp.201-224; Gary E. Weir, Building the Kaiser’s Navy: The Imperial Navy Office and German Industry in the Tirpitz Era, 1890-1919,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2, pp.9-35; Peter Padfield, The Great Naval Race: Anglo-German Naval Rivalry 1900-1914, Thistle Publishing, 2013, pp.17-28.1898年2月,提尔皮茨在向德皇的一次汇报中指出,他的工作主要是“消除帝国议会对陛下海军发展意图令人不安的影响”。(67)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Routledge, 2014, p.35.
3.3 “陆权式海权思维”——战略文化的影响
德国决策精英的“陆权式海权思维”是普鲁士战略文化的鲜明体现,来源于德国深厚的陆权战略传统和在历史上成功的领土扩张记忆,本质上是一种试图汲取和复制历史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68)路径依赖是国家战略选择存在的普遍问题,当因面临新问题和状况需要做出新的战略选择时,决策精英往往倾向于从历史记忆中“学习”成功经验,并试图将其进行复制。唐世平:“国家的学习能力和中国的赶超战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42-48页。通过海上决战击毁敌国舰队并占领海洋,变成了德国海军所有理论和思想的最终结果与目的。“控制”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纯军事优势下的情形,类似于陆军在陆战中夺得的控制权,而不是海战中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这个最终目标的必要前提和手段。“陆权式海权思维”透视出的是,以德国陆地作战为特征的战略文化对于海军发展的影响。尽管提尔皮茨等海军决策精英与陆军军官团在阶级出身方面差异明显,海陆两大军种在组织文化和军事学说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别,但是新生的德国海军很难不受传统战略文化的影响:其一,战略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凌驾于组织、制度和个体行为之上的抽象社会结构,(69)Jeffrey S.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3, 2002, pp. 87-113.虽然精确测量存在难度,却可以凭借过程追踪,在社会事件的具体现实中发现战略文化的作用。(70)[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作为结构中的组织与个体,海军及其决策精英很难超越基于自身所处社会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形成的战略文化束缚。这也可以解释在付出了一战的沉重代价后,纳粹德国的海军发展为何依然没有领会马汉海权理论的精髓所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马汉的理论是基于海洋国家实践进行的总结。(71)Holger H. Herwig, “The Failure of German Sea Power,1914-1945: Mahan Tirpitz and Raeder Reconsidere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10, No.1, 1988, pp.68-105.其二,德国海军决策精英群体大都成长于海军独立性与地位相对较弱的历史时期,在早年的军事素质养成中,都曾接受过陆军背景的将领领导,难免受到影响。例如1872年至1888年,德国前后两位海军最高长官阿尔布雷希特·冯·斯托施(Albrecht Von Stosch)和后来担任宰相的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都出自陆军军官团。(72)David H. Olivier, German Naval Strategy: 1856-1888, Frank Cass, 1988, pp.186-192.德国海军直到提尔皮茨主事后,才拥有了与陆军平等的地位和独立性,而现代化海军教育体系的建立健全则是更晚的事。
这种罔顾不同类型地缘权力的做法,最致命的错误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每种类型的地缘权力背后都存在基于地理位置、技术条件和战略传统的截然不同的逻辑,(73)吴征宇:“地理战略论的分析范畴与核心命题”,《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期,第28-39页。混淆了发展海权与陆权的巨大差异,而是简单地以发展陆权的思维和经验指导海权发展,将获得海权等同于通过武力控制海洋,将海洋理解为如陆地一样,可以通过大规模决战的方式进行排他性占有和控制。(74)同①。但是“与陆地不同,海洋不能被占领和拥有,军队也不能像依赖陆地那样依赖海洋而存在。几个世纪以来,海洋唯一的积极作用是充当交通路径”。(75)[德]赫伯特·罗辛斯基著,吕贤臣等译:《海军思想的演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对海洋的控制并不是指占领某片海域……这里的控制指的是不受任何阻碍和约束地穿越海洋的能力,同时还要阻止敌方以同样的方式利用海洋。(76)同⑤。此外,延续性是海洋的重要自然属性之一,即全球性的海洋表面是延续的。(77)[英]普雷斯科特著,王铁崖、邵津译:《海洋政治地理》,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页。海权的发展与武力和影响力的投射密切相连,一支主要由主力战舰构成的远洋舰队必然与控制海洋和争夺海上主导权高度相关,这是存在于海洋霸权国与后发海军强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无论该国宣称的海权目标多么有限。
3.4 “海权迷思”的影响
“海权迷思”对德国海权战略选择的最大影响在于:它使德国海权发展处于一种“战略无序”的混乱状态。海权不再是一种战略工具,而成为战略目标本身,德国的海权战略内容只剩下发展用于海上决战、争夺制海权的主力舰,全然不顾盲目追求进攻性海上力量的潜在恶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德国海权战略依据的是“马汉主义”海权学说,但是并没有遵照马汉的深刻告诫,“海军的每项规划,如不考虑大国关系,又不考虑本国资源所提供的物质程度,就会立足于一个虚弱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外交政策和战略是被一条不可割裂的链条紧紧地联结在一起”。(78)[美]阿尔弗雷德·马汉著,蔡鸿干、田常吉译:《海军战略》,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页。
第一,造成海权战略规划缺乏对自身海权禀赋的审慎考量。德国地处北海深处,虽有赫尔果兰岛这一战略屏障和部分良港,但德国出海口方向非常单一,“英吉利海峡是德国在获得海权的道路上必须能够自由穿越的两条主要通道之一,英国一旦封锁了这条通往大西洋的入口,将会把德国舰队的主要战区(北海)变成‘死海’”(79)同③。英国的地缘位置和占据绝对优势的海军力量使其可以有效实现这一目标。一战期间德国海军的碌碌无为正是因为其始终难以突破英国海军从斯卡珀湾实施的远距离封锁。此外,德国的地缘政治属性是陆海复合型国家,(80)陆海复合型国家是一个从美国学者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地理政治概念,主要是指濒临开放性海洋,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一类地区。这类国家多处在海陆势力的联合夹击之下,面临两个方向的战略压力和吸引,因而资源、力量配置分散,这是造成欧洲陆海复合型国家在近代竞争中不敌英美等海洋强国的主要原因。其战略资源投入相较于海洋国家英国更为分散,资源压力更大。
第二,非理性的海权战略折射出决策层大战略思考的缺失,推动了德国大战略的进一步瓦解。德国决策精英强调要拥有一支“大海军”,但是对于发展海军的原因、对这支海上力量的战略定位,以及要据此实现的具体政策目标都缺乏大战略层面的考量和指导,没有从大战略视角认真思考和审视“为什么—一定要”这个问题,进而将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政策目标。通过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不再是一种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军事途径,海权也不再是一种特定的战略工具,而成为大战略目标本身。“世界政策”及发展海军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而非具体的国家利益诉求。时任德军总参谋长瓦德西(Waldersee)曾表示,“我们常被认为在执行一种所谓的世界政策,但是它究竟有什么内容,却无人知晓”。(81)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Routledge, 2014, p.20.
第三,安全焦虑主观臆造英德敌对。德国海军在扩展伊始便深深地陷入对英国“哥本哈根化”,(82)“哥本哈根情结”源于德国对1807年英国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突袭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举扣押了全部丹麦舰队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观诠释,代表了一种现实的恐惧。即重蹈丹麦海军历史覆辙的恐惧之中。这种情结也是德国“海权迷思”影响的一个缩影,其中包含三个假定:一是,英国是一个“非道德”的国家,为了维护政治权力,英国“对采取武力没有任何顾忌”。1807年的突袭哥本哈根事件暴露出英国“强权的真正本质和隐藏在人道主义背后的绝对无情”。(83)Jonathan Steinberg, “The Copenhagen Complex”,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1, No.3, 1966, pp.23-46.二是,德国正在快速崛起为一个欧洲超级强国,因此,英国人冷酷的“商业利己主义”肯定会促使英国试图摧毁德国,对深谙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的那代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84)同③。三是,实现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快海军建设,抛弃英国可以容忍德国海权的战略幻想。快速、大规模建造战列舰确实很危险,但只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才能有效威慑英国,确保德国的国家安全。(85)Alfred von Tirpitz, My Memories,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19, p.198.被“哥本哈根化”的恐惧成为德国对外部世界印象的死结(86)同③。。来自英国的威胁和英德海上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被先入为主地植入德国外交决策层的思想中,主观想象变成了事实本身。这种情况对德国外交处境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尤为促使德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的一系列国际危机中,始终以应对英国的预防性打击为外交要务,造成了战略灵活性和回旋空间的日渐丧失。
3.5 德国海权战略对英德关系的影响
德国的海权战略不可逆地恶化了崛起所需的外部战略环境,(87)徐弃郁著:《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页。对英德关系产生了致命的破坏。正如战后一位德国外交官做出的反思,“战前在英国多年的政治活动使我深信,德国作战舰队的迅速扩建乃是使英国站到我们的敌人方面的最主要原因”。(88)[美]科佩尔·S·平森著,范德一等译:《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08页。
这一历史结果的产生存在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英德的地缘政治关系。作为隔北海相望的近邻,德国海军在北海的大规模聚集直接威胁了英国的本土安全,故不难理解海军竞赛开始后,英国在短时间内对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光荣孤立”和海外殖民扩张两大对外战略进行了颠覆性修改。第二,英国的霸权属性。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主导性海洋国家。“殖民地、商贸和海军是构成英国霸权秩序且相互促进的三个互联要素”,(89)Gerald S. 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 Studies in British Maritime Ascendan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112-113.是构成英国霸权基础的“相互促进的三角”。(90)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Allen Lane, 1976, p.155.借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势,德国已经具备了竞逐世界霸权的经济、资源和工业实力,加之拥有一支一流的陆军,一旦德国通过极速扩张海权成为兼具陆权与海权优势的海陆双缘大国,英国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霸权地位,而是对自身生存和命运的掌控能力。1907年的《克劳备忘录》已经发出了警告:如果德国试图通过寻求更大的物质权力优势、更广阔的领土范围、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疆,以及海上的绝对优势来实现其凌驾于国际体系之上的“世界强国”抱负,英国将与其他国家一道予以坚决制衡。(91)吴征宇:“《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的起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2期,第44-55页。
四、结 语
本文依托一战前德国海权战略决策及实践的战略史,构建了一个理论化的战略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崛起国决策精英战略迷思的成因,并透过大量实证材料进行了有效性检验。这段历史折射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作为崛起国,如何在高速崛起中保持必要的战略定力,避免因决策环境快速变化陷入战略迷思,延展自身战略空间的同时,有效管控大国竞争。德国决策精英陷入“海权迷思”的历史教训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启发:首先,应明确具体领域战略与大战略之间的关系,防止本末倒置。具体领域的战略只是服务于国家整体大战略的工具,不仅不能取代大战略本身,而且需要在其指导下进行系统规划。尤其要避免对某种权力类型的盲目崇拜与无限度追求,始终在大国关系与周边安全的框架内进行战略思考和规划。其次,要正视自身战略禀赋的有限性,审慎选择战略方向及配置战略资源。最后,要重视社会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在大国竞争压力增加的情况下,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对社会舆论进行积极引导,适时降低社会心理情绪,为科学审慎的战略决策与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