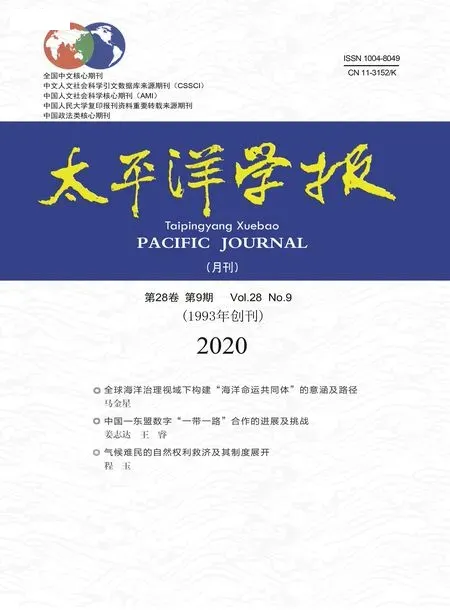美国对华民意的转变及其政策影响
付随鑫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 100005)
近两三年,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明显增强,这不仅体现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精英的对华认知方面,也表现在美国普通民众的对华态度上,而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并加剧了这一趋势。美国对华民意的迅速转变既是受精英影响的结果,也会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约束或支撑作用。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关于近年来美国政府、战略界等精英群体对华认知变化的研究成果,(1)参见何汉理:“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与中美关系未来”,《美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1-9页;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19-28页;李海东:“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美国研究》,2016年第4期,第9-36页;滕建群:“特朗普‘美国第一’安全战略与中美博弈”,《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第18-24页;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80-93页;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真的形成共识了吗?——基于当前对华政策辩论的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3期,第3-21页。但尚缺乏关于美国民众对华态度转变的研究成果。尽管国内已有少量关于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所持观点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所依据的都是多年前的民调数据,不能反映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民意的转变,同时,也较少分析影响美国对华民意的原因,更少探讨民意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2)参见熊志勇:“美国民意看中国六十年——变与不变的趋势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85-96页;袁征:“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第9-33页;[美]理查德·K.赫尔曼:“美国公众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认知”,《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3年第6期,第54-76页。本文将考察近年来美国对华民意的变化趋势和主要特征,分析对华民意转变的原因,并探讨这种转变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潜在影响。
一、美国对华民意的变化趋势和主要特征
民意在构成上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浅层的、短期的和易变的公共舆论,另一种是深层的、长期的和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前者很容易受到重大事件的冲击和意见领袖的操控,而对于后者,个体层面通常在个人社会化的初期就形成,并在一生中保持相对稳定,在社会层面则可能持续数十年或更久。对此,长期跟踪的民意调查数据通常既能反映民意的短期变化,也能展现长期趋势。
最近两年,美国民众中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明显上升。在美国的民意调查中,负面看法是指对被调查对象持不赞成、不认同、不支持或缺乏好感的态度。对华负面看法通常指不赞成中国的某些言论或举措,不承认中国的行为对美国有利,将中国视为美国的“竞争者、对手、威胁、敌手或敌人”,而非利益攸关方、伙伴、友邦或盟国。盖洛普公司(Gallup, Inc.)2020年初的民调显示,67%的受访者对中国“没有好感”,这比2018年增加了22个百分点,比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最高值高出11个百分点。(3)Jeffrey M. Jones, “Fewer in U.S. Regard China Favorably or as Leading Economy”, Gallup, March 2, 2020, https://news.gallup.com/poll/287108/fewer-regard-china-favorably-leading-economy.aspx.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反映了类似趋势:在2020年7月的受访者中,对华持负面看法的比例达到73%,比2018年高出26个百分点,比金融危机期间的最高值多出18个百分点。(4)Kat Devlin, Laura Silver and Christine Huang, “Americans Fault China for Its Role in the Spread of COVID-19”,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30,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7/30/americans-fault-china-for-its-role-in-the-spread-of-covid-19/.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数据同样严峻:在2019年的受访者中,将中国视为“对手”而非伙伴的比例高达63%,比2018年的数据高出14个百分点,比金融危机期间至少高出12个百分点。(5)Craig Kafura, “Public and Opinion Leaders’ Views on US-China Trade War”,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June 27, 2019,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publication/lcc/public-and-opinion-leaders-views-us-china-trade-war.这些长期民调数据都表明,在过去两三年里,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民众激增,逆转了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美国民众对华持负面态度比例显著下降的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态度。截至目前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相对迟缓和无力的情况下,美国受访者主要指责的不是特朗普政府,而是将矛头指向中国。7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为新冠病毒的传播负责”,而且77%的共和党人持这种观点。相比之下,仅有43%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该对病毒的传播负责,而共和党人中持此观点的只有28%。(6)Yusra Murad, “Most U.S. Adults Practice Some Degree of Social Distancing amid Coronavirus Spread”, Morning Consult, March 20, 2020, https://morningconsult.com/2020/03/20/coronavirus-social-distancing-poll/.拉斯姆森报告的民调显示,42%的受访者表示中国“至少应当承担世界抗击疫情的部分费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中各有54%和37%支持这种要求;有28%的受访者认为,“一旦中国断供美国的重要药物,美国就应当考虑跟中国开战”。(7)“42% Say China Should Pay Some of World’s Coronavirus Costs”, Rasmussen Reports, March 17, 2020 https://www.rasmussenreports.com/public_content/politics/current_events/china/42_say_china_should_pay_some_of_world_s_coronavirus_costs.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7月的民调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对华持负面看法的美国民众比例从2019年的60%上升到2020年的73%。(8)同②。虽然疫情尚属偶然的负面冲击,但这些加剧趋势也说明美国对华民意目前很难朝好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美国民众当前对华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已经上升到过去三四十年以来的最高点。其中,盖洛普公司的美国人对华态度民调始于1979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没有好感”的美国民众比例基本维持在50%左右,而目前67%的比例是1979年以来的最高值。(9)“China: Gallup Historical Trends”, Gallup, February 2020, https://news.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皮尤研究中心的对华民调始于2005年,其调查结果显示,直到2011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基本保持在40%以下,只有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增至55%左右,但都比当前73%的比例要低。(10)Kat Devlin, Laura Silver and Christine Huang, “Americans Fault China for Its Role in the Spread of COVID-19”,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30,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7/30/americans-fault-china-for-its-role-in-the-spread-of-covid-19/.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对华民调始于2006年,直至2018年,将中国视为“对手”而非伙伴的受访者比例在50%左右波动,2019年才突然增至63%。(11)Craig Kafura, “Public and Opinion Leaders’ Views on US-China Trade War”,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June 27, 2019,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publication/lcc/public-and-opinion-leaders-views-us-china-trade-war.从长期趋势看,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相对稳定,对华持负面态度的比例基本维持在50%左右,而且这个比例的总体趋势是缓慢上升的。但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容易受到短期事件的冲击,导致持负面态度的比例出现峰值,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威胁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近两年来美国对华民意的恶化意味着另一个峰值的出现,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是其中的主要冲击性事件。同时,这种恶化可能预示美国对华民意进入一种“新常态”,即使今后有所回落也不大可能下降到先前的平均水平之下。
最近两年,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的受访者比例明显上升。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调查显示,23%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对手”,5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个“严重的问题”,持这两种观点的比例均比2018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12)“China”, Polling Report, https://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访问时间:2020年9月5日。盖洛普公司2020年的民调显示,22%的受访者将中国看作美国的“头号敌人”,比2018年增加了11个百分点。同时,23%的受访者将俄罗斯视作美国的“头号敌人”,比前一年下降9个百分点;另外,分别有19%和12%的受访者将朝鲜和伊朗视为“头号敌人”。(13)“China: Gallup Historical Trends”, Gallup, February 2020, https://news.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不过,美国人眼中的“头号敌人”一直在变化,容易受到短期重大事件的影响。在2012年,只有2%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头号敌人”,但这个比例在克里米亚事件后激增至18%;朝鲜、伊朗和伊拉克等国也曾处于首位。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或将很快取代俄罗斯,成为多数美国人眼中的“头号敌人”。
美国民众普遍担心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增长。8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力的增长对美国是“坏事”,8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力将在未来10年里对美国的关键利益构成“重大威胁”。8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将在未来10年里对美国的关键利益构成“重大威胁”。(14)同⑤。不过,相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人对本国的信心近年在增强,更少有人认为“中国会很快超越美国”。在2013年,4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只有39%认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但到2020年,59%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将中国视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比例下降到30%;8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比2016年增加了11个百分点,而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军力最强的国家”。(15)Kat Devlin, Laura Silver and Christine Huang, “U.S. Views of China Increasingly Negative Amid Coronavirus Outbreak”,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0/04/PG_2020.04.21_U.S.-Views-China_FINAL.pdf.总的来说,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在增强,但依然认为中国并不是需要紧急应对的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党派、年龄和教育方面的差异。共和党人一直比民主党人更可能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7月的民调,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共和党人比例高达83%,比2018年增长了32个百分点;而民主党人的比例为68%,比2018年增加了21个百分点。(16)Kat Devlin, Laura Silver and Christine Huang, “Americans Fault China for Its Role in the Spread of COVID-19”,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30,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7/30/americans-fault-china-for-its-role-in-the-spread-of-covid-19/.当前,共和党人更担心来自中国的“威胁”,民主党人更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68%的共和党人和62%的民主党人将中国视为美国的“重大威胁”,相比之下,46%的共和党人和68%的民主党人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重大威胁”。(17)Jacob Poushter and Moira Fagan, “Americans See Spread of Disease as Top International Threat, along with Terrorism, Nuclear Weapons, Cyberattacks”,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13,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4/13/americans-see-spread-of-disease-as-top-international-threat-along-with-terrorism-nuclear-weapons-cyberattacks/.其中,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越强:超过50岁的受访者中有71%对中国持负面看法,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大约53%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教育程度较高的美国人更可能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美国人中,大约68%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在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中,64%对中国持负面看法。(18)Kat Devlin, Laura Silver and Christine Huang, “U.S. Views of China Increasingly Negative amid Coronavirus Outbreak”,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0/04/PG_2020.04.21_U.S.-Views-China_FINAL.pdf.
虽然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在增强,但在对华具体政策上仍然相对温和,且内部存在不少分歧。2019年,6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跟中国进行友好的合作和接触,该比例比2016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只有31%的受访者主张美国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58%的共和党人和74%的民主党人都支持对华合作和接触,说明两党在这方面有较强的共识。不仅如此,59%的受访者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助于增强美国的安全,79%支持两国通过谈判达成控制军备协议,72%支持在国际发展援助项目上与中国进行合作。即便两国的贸易关系变得比以前更紧张,仍有74%的受访者支持跟中国进行贸易,而且64%的受访者相信中美贸易能够增强而非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这一问题上,受访者存在严重分歧:47%支持加征关税,51%表示反对。在关税问题上的党派分歧更加显著:72%的共和党人支持加征关税,但71%的民主党人反对加征关税。美国人对限制两国学术交流的看法也存在分歧:49%的受访者支持限制中美之间的科研交流,其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支持率分别为63%和41%;40%的受访者支持限制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支持率分别为57%和28%。(19)Craig Kafura, “Public and Opinion Leaders’ Views on US-China Trade War”,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June 27, 2019,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publication/lcc/public-and-opinion-leaders-views-us-china-trade-war.
总之,众多民意调查数据都显示,美国对华民意近年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对华持负面看法的比例显著上升,更多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并“担忧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增长”。同时应当看到,目前美国人对华看法的恶化仍主要表现在个人态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政策层面还相对温和并充满分歧。
二、 美国对华民意发生转变的原因
美国民众对外交事务的看法主要来自国内精英的见解和媒体的报道。约翰·R.扎勒(John R. Zaller)的经典研究表明:美国普通民众对外交事务的了解甚少,也不太关心,而且民众缺少独立思考能力,因而他们只是从精英提供的观点中进行选择;精英对民意变化的刺激基本是或完全是外生的,极少量的“创新型精英”发明新的政治观念,然后由政治意识强的人逐渐向普通民众中传播,从而形塑公共舆论和意识形态。(20)John R. Zaller,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 113, 327.因此,美国民意变化的一般过程是:精英创造了新的政治观念,媒体对其进行报道,而民众要么被动地接受精英的观点,要么根据其自身偏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挑选。
当精英内部达成共识并传播能与民众既有意识形态发生共振的新政治观念时,精英对民意的主导作用最为显著。精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议题上都能主导民意,其首要因素是精英内部要先达成共识。如果精英在某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主流媒体的报道就会提供大致相同的说法,从而产生“精英共识”和“主流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反应将是默许或支持精英的看法。如果精英达不成一致,媒体的观点就会呈现较大差异,从而导致持不同观点的精英带动与他们观点一致的民众造成公共舆论的分歧。影响精英主导舆论的另一因素是,精英创造的新政治观念是否跟接受者既有的或潜在的意识形态相协调。两者差距越小,民众就越容易接受精英的新观念。
在最近两年美国对华民意的变化中,精英对民意的主导作用表现得非常显著。过去10年,美国经济整体向好,民众对国家发展的满意度在提升,因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在2015年至2017年明显出现缓解,在此期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是上升的。虽然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曾大打“中国牌”,将美国人的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在这一年实际处于最近十年里的最低水平。如果没有精英和媒体的引导,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不太可能在最近两年里突然明显增加。特朗普执政以来,一方面,美国精英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更加负面的新共识,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也越来越多。在精英一致和媒体关注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民意也随之发生新的转变。另一方面,精英内部的对华具体政策仍存在不少分歧,这导致民众支持的美国对华政策也缺乏一致立场。但无论如何,在对华看法上,美国战略界、政府官员、利益集团这三个精英群体正在形成的新共识,为美国民众对华看法的转变提供了思想资源,发挥了引导作用。此外,重要媒体人士也是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本身就是意见领袖,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能为公共舆论设定议程。
2.1 美国战略界大体上形成了更加负面的对华新共识
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快速变化,美国战略界在过去五年里针对美国对华政策发起了一场全方位的大辩论,目前基本上形成了新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过去40年采取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受到严厉质疑和批评。美国战略界曾认为对华接触政策能将中国纳入既有国际体系,并促使中国向美国期望的方向转变,但现在他们认为这个初衷和目标已经归于失败,甚至批评对华接触战略是“过去70年来美国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误”。(21)Robert Blackwill, “Trump’s Foreign Policies Are Better than They See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2019, https://www.cfr.org/report/trumps-foreign-policies-are-better-they-seem.2018年11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曾举行关于对华政策的专家辩论会,在专家辩论之前和之后,认为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听众分别占听会人数的65%和62%;认为中国按照自己的模式寻求重塑国际体系的听众比例分别为63%和68%。(22)“China’s Power: Up for Debat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29, 2018, https://www.csis.org/events/chinas-power-debate-1.这表明,质疑对华接触政策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的主流意见。其二,美国战略界对待中国的看法日趋负面和强硬。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还曾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G2”等具有一定正能量的理念,但现在美国战略界却弥漫着“战略竞争”“头号对手”“中美脱钩”等对抗性概念。当前,美国战略界的对华负面看法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不仅超越了白宫和国会的分歧,更弥合了全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分歧,在对华问题上,两党内的国家安全鹰派、经济民族主义者、人权积极分子、大战略派都联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华盛顿共识”。(23)Zack Cooper, “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December 21, 2018, https://www.aei.org/articles/the-new-washington-consensus/.
不可否认,美国战略界内部在对华看法上仍有不少争议,特别是在对华政策调整的方向和力度上还有很大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新的共识。《华盛顿邮报》曾发表100余位亚洲事务专家的公开信,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并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24)M. Taylor Fravel, et al., “China Is Not an Enemy”, Washington Post, July 2, 2019.但这些人同时对中国提出了不少批评,也不否认美国对华政策需要调整,他们反对的主要是特朗普政府极端和草率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开提出异议的人,要么已经不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要么已经放弃在政界的发展,而很多过去对华相对温和友好的专家要么转变观点,要么保持沉默。这种对华态度的转变和新共识的形成虽然经过了长期酝酿,但在过去一两年里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正如曾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Joseph Biden, Jr)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所言:“一年前,我和其他一些人谈到这个可能的现象(中美“脱钩”)时,(大家的)反应是,这永远不会发生……但我们今天看到,在某种程度上,这至少是部分现实……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事实。”(25)Ely Ratner etc., “Conscious Decoupling: A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arting Ways?”,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14, 2019,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video/conscious-decoupling-are-the-united-states-and-china-parting-ways.总之,目前美国战略界与普通民众的对华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过去的对华政策已经失效,现在的对华态度变得更加负面,但关于未来具体怎么做还存在分歧。
2.2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和认知发生彻底转变
与前几届政府的政策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明显的转变,对中国进行了更加负面和对抗性的定位,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并首次强调要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竞争”。(26)“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比前任政府更极端、更单边主义的手段。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发起了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贸易冲突,还想单方面迫使中国改变知识产权、市场准入、金融和产业等方面的政策。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试图与中国“脱钩”。美国政府已封杀大批中国高科技企业,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限制,强化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减少国防产业链对中国的依赖。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建立了印太司令部,增加了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在人文交流方面,特朗普政府加紧审查中国学生和学者的赴美签证,要求美国的大学终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27)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15页。总之,目前美国已发起全政府、全方位的对华竞争。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表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最为优先的任务,为此需要将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执法及军事等国家权力在内的要素整合起来,以保护和巩固国家安全。”(28)“United States Strategy on China”, U.S. Congress, August 13, 2018,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515/text.
2.3 许多美国政客和利益集团将中国作为“替罪羊”
美国部分民众看待外国事务时,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种族主义、本土主义或保护主义偏见,许多政客竭力迎合和蓄意利用这些偏见,为自己谋取政治支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众多美国政客和媒体立即乘机掀起反华浪潮。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反复在媒体上宣扬阴谋论,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福克斯新闻等保守派政客和媒体频繁使用歧视性表述,特朗普曾连续多天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发布会上污名化中国。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既是趁机反华,更主要的是推卸国内对其抗疫不力的指责,同时通过挑起种族矛盾来巩固基本盘对他的支持。(29)Adam Serwer, “Trump Is Inciting a Coronavirus Culture War to Save Himself”, The Atlantic, March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trump-is-the-chinese-governments-most-useful-idiot/608638/.在美国疫情恶化后,特朗普和共和党都面临巨大的竞选压力,他们蓄意向中国推卸责任和转嫁矛盾,这严重恶化了中美关系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共和党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了三大竞选策略:“一是,批评中国掩盖疫情;二是,指责民主党对华软弱;三是,强调当选后会要求中国对疫情的传播负责”。它还建议共和党各级候选人“不要为特朗普辩护,而要把矛头指向中国”。(30)Alex Isenstadt, “GOP Memo Urges Anti-China Assault over Coronavirus”, Politico, April 24,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4/24/gop-memo-anti-china-coronavirus-207244.与此同时,美国政客每次公开使用新冠肺炎的歧视性表述后,美国社交媒体上针对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论就会激增,(31)Hanna Kozlowska,“How Anti-Chinese Sentiment Is Spreading on Social Media”, Quartz, March 25, 2020, https://qz.com/1823608/how-anti-china-sentiment-is-spreading-on-social-media/.这说明美国政客的反华言行能有效激发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而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手段则是顺应并利用民意,但在公众不关心或忽略的空隙处着手。(32)[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蓄意煽动和利用反华情绪来谋取私利,将贸易保护具体化为保护钢铁、农业和化石能源等特定行业的利益。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的白人蓝领是支持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获胜的一群关键选民,集中在该地带的钢铁产业从业者强烈支持其贸易保护主张。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当选后竭力迎合该群体的诉求,妄称中国“窃取”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将其对制造业衰败和经济困境的愤怒导向中国。这群“关键少数”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发挥着远超出其人数比例的影响力。保护美国工人,正是特朗普政府庇护衰落产业、对华发动贸易冲突的一个重要口号。美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很大程度上要么是特定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要么是回应美国选民中部分有影响力的群体的诉求,并不能反映民众对保护主义的支持高涨。事实上,盖洛普公司的民调显示,到2020年,79%以上的受访者仍认为贸易给美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机会,而且该比例是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33)Lydia Saad, “Americans’ Vanishing Fear of Foreign Trade”, Gallup, February 26, 2020, https://news.gallup.com/poll/286730/americans-vanishing-fear-foreign-trade.aspx保护主义仍然是一个经典的公共选择案例:集中的利益和分散的成本,被自利的利益集团和政客用来推行实际上为大多数选民反对的政策。只要经济发展足够顺利,直接损失不太严重,大多数选民就不会发现和追究利益集团和政客的做法。(34)Scott Lincicome, “The Protectionist Moment that Wasn’t American Views on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Cato Institute, November 2, 2018, https://www.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ftb-72.pdf.
2.4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推动精英的新共识向民众扩散
至今,仍只有很少一部分美国人到过中国,绝大部分美国人仍需要通过媒体来了解中国。虽然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选题非常广泛,但它们的报道主要关注中国的内外矛盾,包括中国的各种社会事件及与外国的纠纷。对于中国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它们往往视而不见,或者竭力从中寻找可做负面解读的内容。美国媒体虽然表面上独立于政府,但政府经常通过“媒体吹风会”的方式,主动提供信息,引导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已完成对外传播的战略整合,建立了一个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导,涉及外交、军事、情报、对外援助、媒体等各方的跨部门联动机制。在这一协调整合过程中,作为战略传播导向主体的是美国政府,其并非让媒体充当喉舌,而是以提供新闻的方式,通过媒体来左右舆论,影响公众。
同时,美国在媒体技术上的优势使其很容易限制中国发声,抹黑中国,误导美国民众。美国社交媒体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有绝对优势,它们不仅以公正和中立为借口,放任不利于中国的信息广泛传播,而且阻挠中国人在这些平台上发声,删除有利于中国的信息。2019年8月,个别美国社交媒体以“官方散布假新闻”为由,关闭了近千个揭露香港暴徒行径的内地账号。12月,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出的新疆反恐纪录片被个别视频社交网站以“涉嫌违规”为由下架停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民众很难获得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而只能接受美国媒体对中国的间接报道。
由于价值认同和利益驱动,美国媒体会受制于“政治正确”,配合美国政府的外交话语。对于中国新闻的解读,美国媒体主要采用自由民主体制对“威权体制”、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话语。从最近两三年美国对中国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出,美国主流媒体接受并传播着当前美国精英对中国的一套新看法、新共识。精英的共识加上媒体的报道,导致对中国不甚了解或漠不关心的美国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中国看法的转变。
2.5 美国精英的对华新共识与美国民众既有的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发生共振
精英发明和传播的新政治观念只有与民众既有的意识形态发生共振,才能使精英对民意的主导作用产生最大效果。美国民众的对华负面看法主要基于意识形态,其次是物质利益。他们大多清楚自动化和经济结构转型才是其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并非主要原因,但他们仍然将中国作为情绪的发泄口,支持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极端打压政策。(35)Mariana Rambaldi, “China, Immigrants or Robots: Who Is ‘Stealing’Jobs in the US?”,Univision News, https://www.univision.com/univision-news/united-states/china-immigrants-or-robots-who-is-stealing-jobs-in-the-us,访问时间:2020年9月5日。当前,多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疑虑和不满具有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根源,因为“从中国清朝末年与中国直接交往至今,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一直都是二元性的:一方面,将中国视为美国人改造和拯救的对象;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的文明是异质的、落后的和压迫性的。当中国看起来要接受美国价值观的时候,美国人就会欢欣鼓舞;当中国与美国关系疏远的时候,美国人就伤心或愤怒。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的性格中有一种传教士冲动,希望看到别国人变得更像自己,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36)崔存明:“美国的中国观——新乐观主义和一些历史性的考察”, 《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第51页。这种现象既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经常被情感和价值判断所主导,也反映了美国人的优越感和种族中心主义观念。美国人对中国文明异质性的不信任是长期存在的,他们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人权等方面抱有近乎本能的偏见。总之,优越感、异质性、“重建论”和“吃亏论”等观念意味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疑虑和不满是根深蒂固的。美国民众这些既有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存在,意味着他们很容易接受精英近年来达成的对华新共识。
总之,近两年来美国对华民意的负面转向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原因。直接原因是美国精英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反华新共识,进而将这种共识“灌输”给普通民众。这些创造新共识的精英主要是美国战略界和政府高官,而利益集团和主流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深层原因是,美国民众一直对中国抱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这使得精英的反华新共识很容易被民众接受,从而形成新的对华民意。近两年来,美国对华民意的转变可以作为政治传播过程的经典案例:首先精英的旧共识走向瓦解,随后新共识逐步形成,这种新共识被传播给普通民众,并与民众的既有意识形态发生共振,新的民意最终形成并取代旧的民意。
三、 美国对华民意转变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浅层的公共舆论和深层的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不同的影响力。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等早期研究公共舆论的学者认为,公共舆论是易变的、混乱的和无关紧要的,民众对美国的外交既缺乏了解也没有重大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由精英主导,而民众的无知和易受影响给精英操纵外交政策留下了很大空间。(37)Jerel A. Rosati and James M. Scott, The Politic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13, p. 329.但越南战争之后,研究者们重新评估了民意对外交的影响。新的研究认为,虽然公众很少了解外交政策,但他们拥有相对稳定的态度,并能对外交事务进行理性的回应。(38)Robert Y. Shapiro and Lawrence R. Jacob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Me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60.美国民众通常具有相当稳定的意识形态,对特定外交政策或理念的支持可能在几十年或更长时间里保持稳定。例如,在二战前,美国民众长期存在着孤立主义共识;在冷战期间,美国民众维持了几十年的国际主义共识,这两种深层意识形态都曾对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过强大的约束或支撑作用。
即使是浅层的公共舆论也能对特定外交议题产生巨大影响。近来的许多研究仍然表明,相对于利益集团和政策专家,普通民众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很小的;总统通常不太回应民众的偏好,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来限制民众的影响或者操纵舆论为其政策服务。(39)Lawrence R. Jacobs and Benjamin I. Page, “Who Influences US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1, 2005, p. 107.然而,在三种情况下,外交政策可能会受到公共舆论的显著影响。第一,如果公众特别关注某个外交议题,则公共舆论可能对政策制定产生即时和直接的限制。例如,美国民众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政府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转圜空间。第二,如果民众对国家的发展感到满意,他们通常会支持现状,并更能容忍总统在外交领域自由发挥;如果民众感觉国家发展出了问题,公共舆论可能短期内发生明显变化,总统支持度的下降将迫使其在外交事务上谨慎行事。(40)Dino P. Christenson and Douglas L. Kriner, “Does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 Presidential Unilater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3, No. 4, 2019, p. 1071.第三,当精英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时,公共舆论存在的争论会被激活,公众的支持对官员来说将变得十分重要,政府政策可能受到公共舆论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例如,在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后期,精英内部的分裂扩散到公共舆论中,美国政府不得不回应民众要求撤军的请求。
至于深层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精英,都无法摆脱它的强大束缚。相对于公共舆论而言,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取向是非常稳定的。美国人一直具有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二元倾向。美国精英在外交上更容易遵从道德原则、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但普通民众实际上更加偏好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41)Daniel W. Drezner,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6, No. 1, 2008, p. 51.但冷战结束后,冷战共识消退,美国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变得碎片化和缺乏连贯性,容易被民粹主义所吸引。由于反恐战争旷日持久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民众对全球化和国际主义的质疑更加强烈,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倾向明显上升。
美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华“脱钩”和“激烈对抗”的民意,这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向具有一定的阻滞作用。虽然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决心跟中国“激烈对抗”或“脱钩”。第一,当前美对外民意的大背景仍然倾向于孤立主义,既不想再次卷入海外战争,也不想承担既有的国际责任,而是希望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解决经济、医保、移民、教育等国内问题。(42)Sam Hananel, “Release: New CAP Poll Reveals What American Voters Really Want in U.S. Foreign Policy Debate”,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May 6, 2019,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press/release/2019/05/06/469430/release-new-cap-poll-reveals-american-voters-really-want-u-s-foreign-policy-debate/.现阶段美国民众对海外干预具有高度敏感性,特朗普在这一重要外交议题上受到民意的强烈限制。在叙利亚、朝鲜、委内瑞拉和伊朗等问题上,特朗普虽然屡次发出严厉的威胁,但从来没有派兵卷入。特朗普之所以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确反对美国过去十余年的全球反恐战争,并“承诺不再卷入愚蠢和昂贵的海外战争”。(43)Douglas L. Kriner and Francis X. Shen, “Battlefield Casualties and Ballot Box Defeat: Did the Bush-Obama Wars Cost Clinton the White Hous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53, No.2, 2020, p. 248即使遭到共和党内盟友的激烈反对,他也竭力让美国从阿富汗、叙利亚等地抽身。第二,尽管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喜欢通过“攻击中国”来发泄情绪和获得利益,但他们不一定愿意承受中美关系恶化带来的严重损失。贸易摩擦升级对美国农民的冲击甚大,特朗普很关注这群关键支持者在2020年大选中的倾向,这种不甚稳固的民意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特朗普对华要价的筹码。(44)Keith Bradsher and Ana Swanson, “For Both Trump and Xi, Trade Deal Comes amid Growing Pressures at Hom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2019.特朗普虽然威胁对中国全部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但先期加征的关税仍主要集中在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上,没有轻易扩大至全部进口消费品。(45)Chad P. Bown, Euijin Jung and Zhiyao (Lucy) Lu, “Trump and China Formalize Tariffs on $260 Billion of Imports and Look Ahead to Next Phase”,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eptember 20, 2018,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trump-and-china-formalize-tariffs-260-billion-imports-and-look.贸易摩擦升级对美国经济增长和特朗普连任的潜在负面影响,也是他不得不与中国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重要原因。第三,美国精英和民众并未认真思考与中国“对抗”或“脱钩”的严重后果,也未进行充分准备和动员。中美是深度相互依赖的两个大国,“脱钩”必将让美国民众付出极大的经济代价,“全面竞争”也将导致两败俱伤。美国从其他地区抽身并不意味着立即全力投入与中国的“对抗”。美国当前的国防支出虽然绝对数值很大,但相对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财政支出,其比例显著低于历史峰值,增长速度也比较缓慢。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在2024年之前,美国的国防支出还会持续地小幅度下降,(46)“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the 2020 Future Years Defense Program”,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August 2019,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19-08/55500-CBO-2020-FYDP_0.pdf.两党内部对于国防支出的总量和财政支出的优先事项仍有很大分歧。
但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民意很可能为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强硬提供支撑。美国精英清楚中美在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可以预见美国精英对中国的态度整体上将越来越趋于负面。美国公共舆论的重大转向往往快速发生,如二战前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在“珍珠港事件”后迅速销声匿迹,再如美苏在二战期间形成的同盟友谊在两三年内就被冷战意识所取代。如果中美两国在未来发生更激烈的冲突,当前在对华政策上仍相对温和与充满分歧的美国民意也可能发生类似的迅速转变。同时,在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社会矛盾丛生、国家治理失灵的情况下,美国精英也需要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外部假想敌”,转移国内矛盾并增强国家凝聚力。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和全球暴发,当前的全球化趋势或将进入加速衰退期。美国政府很可能趁机加快推进产业链的调整及中美经济和技术的“脱钩”,美国的民粹—民族主义势力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力度将进一步高涨,(47)Philippe Legrain, “The Coronavirus Is Killing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 Foreign Policy, March 12,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12/coronavirus-killing-globalization-nationalism-protectionism-trump/.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民众的对华看法在精英的影响下必将变得更消极。反过来,这种对华民意的负面趋势也将为美国政府对华强硬政策提供更大的支撑力量。
总之,短期来看,美国对华民意仍将限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升级为“对抗”或“脱钩”,但长期来看,当前的民意束缚将很可能减弱,因为中美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将使美国对华民意变得更加负面,并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进一步强硬提供支撑。
四、 结 语
最近两年来,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人比例显著上升,达到过去三四十年以来的最高点,而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中国实力的增长,将中国看成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态度在增强,但在对华政策上仍然比较温和且存在分歧,远不像特朗普政府和对华鹰派那样强硬和极端。美国对华民意的转变主要受美国精英对华看法和媒体报道的影响,也与美国民众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深层意识形态相适应,这很可能预示着美国对华民意将继续向恶化的方向发展。虽然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整体上日趋负面,但并不意味他们已决心与中国“对抗”或“脱钩”,这对美国政府实施更极端的对华政策有一定的阻滞作用。从长期来看,由于中美之间存在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差异,美国民众的对华态度很可能在精英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这将为美国政府推行更加极端和强硬的政策提供支撑。
面对美国政府对华日渐强硬的政策和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应当充分考察和评估美国对华民意,并通过跟踪其走向来研判美国对华政策的限度和韧性。目前,美国民众的孤立主义情绪仍然强烈,对经济形势变化很敏感。这种民意让美国政府不会轻易卷入海外军事冲突,不易跟中国进行激烈“对抗”或“脱钩”,但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很可能成为美国政客炒作“中国威胁”、谋求政治利益的契机。如果美国民众被精英进一步煽动起来反对中国,美国政府则可能对华实施更极端的单边行动。
改变美国对华民意的关键是影响美国精英和媒体的看法。相对于通过在美进行传播或促进民间交流来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民意,更有效的方式可能是通过影响精英和媒体,进而间接影响民众。但总体上看,由于两国的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存在根本性分歧,上述技术性手段将很难显著改善美国精英的对华态度,只有更多的大国博弈才能使其更加理性。
中国也需要改进国际话语,提升对他国民众的说服力。美国拥有国际话语霸权,且掌握着主要传播渠道。中国当前的国际话语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旨在捍卫自身正确性与反驳对方污蔑,同时,主要基于民族主义和自身特殊性,缺乏普世性。而更有影响力的国际话语的建构应当基于国内的成功治理经验,尤其是国家能力建设和治理手段创新这两个优势。为了展现并发挥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并针对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构建国际话语可面向以下三个目标:缓解各国都面临的经济不平等和族群矛盾;改善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的不公正和治理失灵问题;补充或超越西方主导的现代性。如果能够应对这些普遍的难题并超越西方的话语,中国对他国民众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必将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