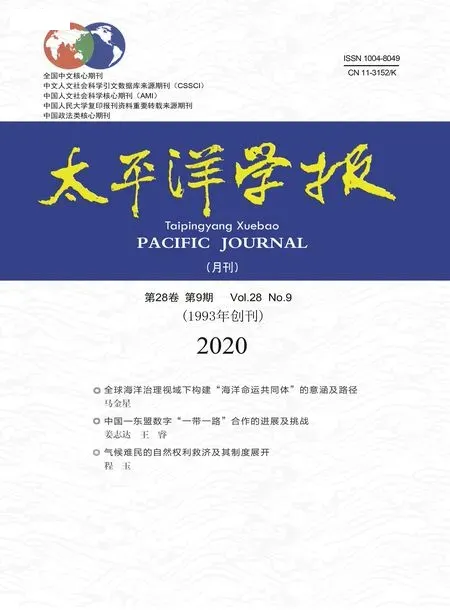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进展及挑战
姜志达 王 睿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 100005;2. 重庆大学,重庆400044)
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驱动下,第四次工业革命快速发展。数字经济(1)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2016年9月29日,http://www.cac.gov.cn/2016-09/29/c_1119648520.htm。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正在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2)《数字经济治理白皮书(2019)》,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9年版,第1页。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带来的全球危机进一步推进了数字经济发展,并将在全球经济复苏后产生持久影响。
数字“一带一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结合。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建设,就是要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和效应,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抓住数字化发展机遇,促进数字要素资源创新集聚和高效配置,带动产业融合发展,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提升信息化水平,积累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7年5月,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在论坛上正式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3)“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年5月14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514/c64094-29273979.html。自该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相关合作进展迅速,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亮点。但是,数字“一带一路”处于发展初期,许多方面还属于探索阶段,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发展完善。作为中国的近邻,东盟既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区域,深化与东盟的数字“一带一路”合作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考察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基础,梳理其成果,力求剖析这一合作面临的挑战,提出应对思路,并展望合作前景。
一、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基础
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除了双方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外,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具备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展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1.1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数字化进程加快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活跃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4)“习近平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8年5月28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5/28/content_5294268.htm。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显著特征,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全球竞争格局正加速调整。对中国而言,其已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同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及环境压力增大,中国经济亟需产业转型升级,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重大机遇。(5)王皖君:“找准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经济日报》,2019年7月25日。对东盟国家而言,新一轮科技革命也使东盟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原有的依靠低廉劳动力降低制造业成本的模式将受到冲击,需要抓住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历史机遇,通过大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以此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并推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6)Badri Veeraghanta,“Digitalisation Key to ASEAN Attracting China Trade War Exodus”, The Business Times, October 23, 2019.但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世界经济原有的产业链、价值链受到较大冲击,亚洲出口导向型国家大受其害。(7)“‘恐怖陷阱’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人民日报》,2018年7月15日。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重构。因此,借助数字“一带一路”合作,双方可在数字经济和高科技产业领域深化交流合作,促进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整合与高效配置,通过建立更为紧密的产业分工和区域价值链体系,缓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1.2 中国—东盟关系制度化程度较高
东盟与中国毗邻而居,邻居大国的身份定位是双方关系中最基本且最本质的部分。(8)聂文娟:“东盟对华的身份定位与战略分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第21页。基于这种身份定位,一方面,东盟重视与中国发展全方位关系和全面合作,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东盟又担心中国的不断强大可能会制约自身的地区影响力,故而在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实行平衡外交。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大国,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互信得以加深。在实践中,东盟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为本地区提供了重要机遇,由此坚定支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随着双方政治互信加深,2003年10月8日,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签署并发表《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9)“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6—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3月3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344899.shtml。双方正式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此外,东盟所有成员国与中国之间都已建立了伙伴关系。就中国—东盟合作而言,中国作为地区大国,以实际行动回应东盟国家的期待,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提供制度性的区域合作公共产品。在中国的倡导下,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等方面建立了诸多合作制度,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自2002年中国和东盟启动自由贸易区进程以来,双方贸易额由2002年的548亿美元提高至2019年的6 415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8年双向投资158亿美元,累计达到2 057亿美元。(10)“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全面生效”,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2019年10月23日,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1910/41659_1.html。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双方在产业园区、港口、铁路等领域的合作取得多项积极成果。(11)“中国—东盟国际产能合作初具规模”,新华网,2016年9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13/c_1119559123.htm。中国与东盟已经构建起以文化产业合作、教育交流和合作、青少年交流,以及国际旅游合作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文交流机制。双方互访由2003年的387万人次增至2018年的近5 700万人次。截至2019年10月,每周有近4 000个航班往返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互派留学生达20万人。(12)“东盟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释放哪些信号?”,新华网,2019年10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0/10/c_1125086882.htm。
这些制度安排既发挥了合作渠道的功能,促进了双方的务实合作,又增强了双方关系的韧性,使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关系并未因东盟部分成员国与中国的某些权益争端而受到冲击。在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公开表示: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必须容纳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也必须接受,阻挡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美国必须与中国寻求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在经济上互相依存的关系。(13)“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美须接受阻挡中国崛起是不可能的”,中新网,2019年8月19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8-19/8930896.shtml。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与东盟互通疫情信息,加强抗疫合作。中国先后向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并向老挝、柬埔寨、菲律宾派出医疗队,谱写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3 双方新的发展战略契合度较高
为抓住数字经济革命带来的机遇,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先后出台《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等指导性文件,不断完善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的顶层设计,以期达到经济发展制高点。
冷战结束后,东盟将互联互通作为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内容,而信息互联互通是其建设的重要一环。为此,东盟除了在《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2025》《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等政策文件中强调信息互联互通外,还专门制定了《电子东盟框架协议》等政策措施和框架,希望借助数字“一带一路”促进东盟国家市场紧密联合,提升数字互联互通,力争使东盟成为数字经济领先型地区集团。(14)“Digital ASEAN”,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digital-asean,访问时间:2020年2月3日。为更好地实现区域数字化转型,东盟在已有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正抓紧制定“第四次工业革命综合战略”,旨在解决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治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基于本国国情和发展目标,东盟各国亦推出各自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参见表1)。目前,中国与东盟已在电信、电子商务和智慧城市发展等共同关注的领域探讨科技创新合作,力求抓住数字经济和技术的创新机遇,实现创新驱动发展。(15)“中国与东盟共享数字经济合作机遇”,《中国报道》,2020年第6期,第71页。2020年6月,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正式启动,双方在数字化防疫抗疫、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展开密切合作,进一步推动了双方战略的契合和深化。

表1 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1.4 双方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较强互补性
中国与东盟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合作前景广阔。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持续深化为双方数字“一带一路”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中国在跨境贸易、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支付等数字产业化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等产业数字化领域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全球竞争力随着自身数字经济“迭代升级”而不断增强。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开展的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中国的排名在2019年跃升至22位。(16)“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19”,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https://www.imd.org/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digital-competitiveness-rankings-2019/,访问时间:2020年2月8日。而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还处于早期阶段,数字经济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仅为7%,但东盟发展数字经济的潜力很大,主要表现在:劳动适龄人口数量超过4.3亿,拥有庞大的数字经济潜在群体;互联网活跃用户数量达到3.3亿,是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速最快的地区;到2025年,东盟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3 000亿美元,约占东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17)“E-Conomy SEA 2019”, Bain & Company, https://www.bain.com/globalassets/noindex/2019/google_temasek_bain_e_conomy_sea_2019_report.pdf,访问时间:2020年3月3日。东盟数字消费者预计突破3亿人,(18)“聚焦东盟数字经济发展(三):东南亚数字消费前景广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0年8月19日,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ztdy/202008/20200802993956.shtml。一个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好成长性的消费市场正在形成。
二、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进展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不断加强政策沟通与对接,创新合作机制,推动双方数字“一带一路”合作进入全方位发展新阶段。数字“一带一路”合作为中国与东盟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拓展了新空间,注入了新动力,也为打造中国—东盟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实践探索。
2.1 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推进
数字经济政策对数字经济发展极为重要,中国与东盟开展“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需加强双方的政策协调与对接。(19)“The Digital Economy in Southeast Asia: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s for Future Growth”, World Bank, January 1, 2019, p.17,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2894155870 8267736/The-Digital-Economy-in-Southeast-Asia-Strengthening-the-Foundations-for-Future-Growth.2020年,中国提出“深化数字丝绸之路、‘丝路电商’建设合作,在智慧城市、电子商务、数据跨境等方面推动国际对话和务实合作”等八项举措,进一步明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顶层设计和合作框架。(20)“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20年6月1日,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006/t20200601_1229648.html。东盟成员国则于2019年1月签署了《东盟电子商务协议》和《东盟数字融合框架》,为“数字丝绸之路”与东盟建立整体性政策对接奠定了基础。在合作进程方面,2017年12月,中国与老挝、泰国等国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致力于实现互联互通的“数字丝绸之路”。(21)“多国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光明日报》,2017年12月4日。2018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1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双方通过《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对接《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并且促进数字创新领域的战略对接。在2019年7月底召开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双方确定2020年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在电子商务、科技创新、5G网络、智慧城市等领域加强合作。(22)“确定!2020年: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网站,2019年8月1日,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20&id=236772。2019年11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发表了《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国—东盟智慧城市合作倡议领导人声明》《深化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的联合声明》等三份合作文件,(23)“李克强在第22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9年11月4日,http://www.gov.cn/premier/2019-11/04/content_5448249.htm。进一步深化和明确了双方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重点和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阶段有所差异,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政策对接的重点领域也不尽相同,如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其对接重点在数字技术、智慧城市等领域;而对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国家,则侧重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合作。这种差异性的战略对接,既体现了双方合作的灵活性和务实性,更体现了双方开展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迫切愿望。
2.2 合作范围日益扩大
随着东盟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增加,中国—东盟“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由先前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拓展至智慧城市、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涵盖了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市场拓展和数字内容等方面,合作领域越来越多,合作规模越来越大。仅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科技领域的投资达到25亿美元,超过2017年全年投资额。(24)“Digital Economy Is Becoming the Tie Connecting the Destinies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Haixun, August 23, 2019, https://haixunpr.org/info/19082373936.在基础设施方面,华为和中兴承担了东盟多个国家的5G项目,中国电信运营商和通信企业已与部分东盟国家合作建成数条跨境光缆和国际海缆。中国设计的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海底光缆系统已于2015年开始建设。(25)方芳:“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国际环境与路径选择”,《国际论坛》,2019年2期,第67页。中新(重庆)国际数据互联互通专用通道已于2019年正式开通,通道以新加坡为枢纽,推动东盟国家共同参与通道运营和使用,更好地服务于东盟国际通信网络体系。在平台建设方面,以基础设施、信息共享、技术合作、经贸服务和人文交流五大平台为建设重点的中国—东盟信息港,已经成为面向东盟的国际通信网络体系和信息服务枢纽。在市场拓展方面,广西南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于2018年12月正式运营,具有东盟区域特色的跨境电商产业带及集聚地正式形成。(26)“中国—东盟跨境电商‘逆风飞翔’”,《中国报道》,2020年5月28日。与此同时,中国数字经济领域龙头企业通过股权投资与并购等方式加速布局东盟数字经济市场,以电子商务平台为特征的跨境贸易发展迅速。中国企业入股印度尼西亚电商,并在马来西亚启动了首个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海外“试验区”——马来西亚数字自由贸易区。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大量应急救援物资通过该平台运送到全球各地,该平台成为全球抗疫救援和恢复生产的关键通道。中国企业投资的数字支付平台已覆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等6个东南亚主要市场,其中11个平台已服务超1.5亿用户。(27)“阿里、腾讯投资的11个东南亚数字支付平台已成当地巨头 服务超1.5亿用户”,移动支付网,2020年7月1日,https://www.mpaypass.com.cn/news/202007/01111703.html。在数字内容方面,中国企业的数字内容服务平台已在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可以预期,随着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进程的持续,双方合作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展,合作的成果将更加丰富多元。
2.3 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机制是未来扩大双方在数字经济领域深度合作的重要保障。在现有的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一带一路”倡议、澜湄合作等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基础上,双方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和中国—东盟电信部长会议两大政府间对话机制为重点,以中国与东盟各国、行业组织、企业、智库的合作机制为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机制体系。中国与新加坡在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基础上,已形成副总理级、部长级和地方级不同层级,信息技术、数字贸易等不同领域较为完善的沟通协作机制。另外,中国还与泰国建立了“数字经济合作部级对话机制”,与越南、柬埔寨分别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与马来西亚启动双边跨境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商签进程,推动双边合作机制建立。(28)“中国东盟共建数字经济之路潜力巨大”,《经济日报》,2019年4月24日。中国还充分发挥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联盟、广西—东盟智慧城市博览会等平台的作用,以南宁、厦门、杭州、济南、昆明、深圳、南京、成都等城市为载体,加强与东盟各城市间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与交流。(29)“中国—东盟智慧城市合作倡议领导人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19年11月8日,https://www.ndrc.gov.cn/fggz/cxhgjsfz/dfjz/201911/t20191108_1201879.html。除了政府部级对话机制外,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等行业组织、企业、智库间多层次和多渠道的合作机制也正加快建立和完善。需要强调的是,除了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建立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外,中国还创新其他合作机制,如2018年5月,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其中大部分项目均布局在东盟地区。中日已将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简称EEC)确定为两国第三方合作的发轫之地。(30)王竞超:“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日本的考量与阻力”,《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84-85页。
三、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因得益于合作双方的互补性和发展潜力,数字“一带一路”在东盟及其成员国两个层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且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尽管如此,数字“一带一路”合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影响了合作绩效和未来发展。
3.1 数字合作顶层设计有待完善
数字“一带一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技术支撑。自2017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数字“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就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一是,通过虚拟空间的打造,支持五大领域互联互通;二是,通过开放中国的巨大市场,用“轻资产”方式促进沿线国家传统产业转型、促进创新就业;三是,整体利用中国已经形成的数字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主动优化产业布局,形成区域经济利益共同体基础。(31)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数字“一带一路”蓝皮书课题组:“激发数字化企业潜力 共同打造数字‘一带一路’”,《光明日报》,2019年4月22日,https://news.gmw.cn/2019-04/22/content_32761743.htm。
但相较于物理层面“一带一路”合作的实际操作,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缺少制度性安排固化实际推进的合作进程。同时,数字“一带一路”的倡议目标、合作机制、优先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也不明确,导致合作各方在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协同、数据资源共享和市场开放等领域缺乏必要的协同。这显然既与建设数字“一带一路”的初衷相背离,也与该地区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特殊重要性不相符合。
在东盟内部,虽然各成员国相继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但相互之间缺乏相通性,特别是涉及跨区域、跨领域的项目难以衔接。如前文表1所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悬殊,各国发展数字经济的起点不同,目标相差较大,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数字经济呈现碎片化特征。还要指出的是,东盟作为地区组织在整合各国数字经济战略方面的作用不太明显,这显然与目前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建设缺乏战略性安排有关。与此同时,由于东盟地区存在“合作机制拥堵”的现象,其他域内外大国也通过现有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了与东盟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换言之,在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方面,东盟同样沿袭了在其他领域所使用的“大国平衡”这一对冲策略,对与中国合作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持既欢迎又防范的立场,这也成为中国在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中与东盟在政策协调上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从微观层面上看,参与数字“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方企业是私营企业和少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参与合作更多是出于商业利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合作规划的统筹协调。
3.2 数字治理滞后于合作需要
数字经济依托技术快速迭代带来各种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数字治理挑战,涉及安全、标准规则和治理机制诸方面。在安全方面,数字经济对国家主权、社会稳定、网络安全的影响日趋深入,一些项目涉及东盟国家之间能源、交通、水利、民航等领域的重大合作,这些合作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具有很大关联性,因而包含诸多敏感信息,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系统和数据暴露在开放的互联网上,原有的网络安全防范措施受到新的挑战。(32)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编著:《数字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在社会经济方面,数字经济带来了跨境电子商务的征税困境,导致国家税源流失,并引发国家间的经济纠纷。(33)Richard Rubin,“Italy Follows France in Levying a Digital Tax”,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5, 2019.在标准和规则方面,商业和技术的快速变革使东盟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亟待完善。(34)Heejin Kim, “Glob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Change: The Interplay of Laws and Technologies in E-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Vol.35,No.5,2019,pp.1-20.例如,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拟筹划征收电商税,保证电商与实体零售商的公平竞争,但各国税收制度不一致,容易产生各类纠纷。在数字监管方面,东盟各国面临监管思路和监管手段的制约,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监管制度、措施建设还存在滞后、空白等问题。这些治理困境不仅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制约着数字经济合作的进程。
其中,中国—东盟“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存在的数字治理滞后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数据收集、个人隐私、数据安全、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物流、海关等诸多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在治理机制方面,现阶段中国—东盟“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协调工作主要由电信部门牵头,但由于部委主要侧重单一业务板块,在诸如网络空间安全、征收“数字税”、缩小“数字鸿沟“等社会、经济与安全方面缺乏整体协调能力。与此同时,由于东盟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重点不相一致,其数字治理也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
3.3 东盟国家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
数字经济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高度相关。除新加坡是发达国家外,东盟其他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初期的发展阶段,各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信息化支持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形成东盟成员国之间巨大的“数字鸿沟”。例如,2019年新加坡在全球63个国家数字竞争力的排名中位列第二,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数字竞争力排名靠后。(35)“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19”,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https://www.imd.org/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digital-competitiveness-rankings-2019/,访问日期: 2020年3月2日。在印度尼西亚的网购消费中,网银和电子钱包等支付方式只占10%左右。(36)“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扎堆‘出海’ 印尼缘何受青睐?”中新网,2018年4月25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8/04-25/8499437.shtml。根据环球金融创新公司统计,90%的菲律宾人没有信用记录,66%的菲律宾人没有任何银行账户。(37)张信宇:“目标东南亚 蚂蚁金服境外本地化战略”,移动支付网,2018年9月14日,http://www.mpaypass.com.cn/news/201809/14092210.html。此外,受资金短缺的限制,大部分东盟国家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导致信息化程度较低,宽带服务网络使用成本居高不下。特别是东盟各国之间互联互通的数字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跨国跨区域通信网络不完善,缺乏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体系及完备的物流供应链基础,这些都使中国企业难以获取一体化的规模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东盟国家的“数字鸿沟”还表现在数字人才资源匮乏。大部分东盟国家在推动数字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的人才资源短缺困境,东盟国家的人才结构和素质与中国—东盟“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要求并不适应,面临数字技术和产业经验的跨界人才及初级数字技能型人才的“双重缺失”。目前,东盟国家主要采取吸引对外融资和国外数字科技公司等方式,引导国外人才参与本国数字经济建设,其中包括吸引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作的东盟人才回流。由于数字经济具有资本密集性、技术密集性和数据密集性相互叠加的特征,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培训系统尚无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这种变化,(38)James Manyika, Susan Lund, Jacques Bughin, Jonathan Woetzel, Kalin Stamenov, and Dhruv Dhingra,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February 24, 2016,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digital/our-insights/digital-globalization-the-new-era-of-global-flows.这也导致中国企业难以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员工,企业的生存与获益空间被大大压缩。

表2 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
3.4 面临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
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强化了与东盟的基础设施合作。(39)刘飞涛:“美国‘印太’基础设施投资竞争策略”,《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第1-20页。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印度尼西亚发表公开演讲,提出美国要在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等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美国国会拨款600亿美元组建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推动美国企业加强对东盟的投资。(40)陈菲:“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建立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26-30页。美国还宣布建立美国—东盟智能城市伙伴关系,旨在促进美国对东盟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增长和发展,“加强东南亚的安全”。(41)Kaewkamol Pitakdumrongkit,“Pence in Southeast Asia: Ways forward for U.S.-ASEAN Cooperation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Brookings Institution,November 27, 2018,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11/27/pence-in-southeast-asia-ways-forward-for-u-s-asean-cooperation-on-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美国还通过夸大华为5G网络安全问题阻扰东盟国家使用华为设备,逼迫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42)Brian Harding,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and Southeast Asi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February 15, 2019,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digital-silk-road-and-southeast-asia.与此同时,日本、澳大利亚更是在美国的战略框架内推进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与东盟的合作。(43)“The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nounce Trilateral Partnership 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the Indo-Pacific”, U.S Embassy and Consulates in Australia, July 30, 2018, https://au.usembassy.gov/the-u-s-australia-and-japan-announce-trilateral-partnership-o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in-the-indopacific.其中,日本战后一直深耕东南亚地区,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与援助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日本为保持和巩固其在东盟的经济利益与战略优势,也进一步加大了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投资和援助力度。尽管中日两国于2018年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共同开展了关于智慧城市项目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但中日间在东盟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关系不会得到根本改观。加之,美日在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场合倡导“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试图谋求在数字经济征税、数据流动标准等方面的主导权,削弱中国数字“一带一路”的先发优势,加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阻力。(44)王凯、倪建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路径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0期,第31页。域内外国家加强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既有经济收益的因素,也有同中国竞争数字标准制定权,以平衡中国在东盟地区影响力的考量。美日等国的竞争对中国推进与东盟的数字“一带一路”合作造成了较大干扰和破坏。(45)赵明昊:“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态势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4页。
四、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未来路径
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双方应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2020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为契机,将搭建政策对接机制与平台、制定发展规划、加强人才培养、推动区域数字治理建设等作为未来数字“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与优先方向,推进各领域合作提质升级。
4.1 加快各方政策深度对接
中国与东盟需加强双方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高层沟通,促进战略对接,共同确定发展合作的方向,提升双方合作的战略协调性与契合度,通过设立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等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政治互信,促进双方合作共识,为双方的合作提供更加适宜的政治基础。针对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中国可采取灵活务实的对接策略,进一步明确各国发展定位,特别是数字技术创新的定位,在此基础上形成差别化的协调发展格局。具体而言,针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在强化和巩固现有对接的基础上,中国可在科技金融、智慧城市、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数字治理等方面与其建立全方位对接机制。对于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中国可以进一步挖掘这些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机制的广度和深度,拓展新的合作机制。在区域层面,中国与东盟可进一步增加创新性制度设计与供给,通过深化政策对接机制,强化数字经济合作机制的有效性,积极搭建更多战略合作平台,将数字经济合作纳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10+1”合作及澜湄合作等机制性会议议题,推动建立新的数字经济合作机制与合作框架。在具体操作层面,中国可积极引导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实施更多的双边、多边、第三方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示范项目。在规则方面,双方需加快完善跨境电子商务、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的国际规则、法律规范、技术标准,以及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际税收政策。
4.2 共商数字经济合作规划
中国需加快完善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布局,做好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整体设计与目标定位,提升规划设计的系统性和前瞻性,通过强化中国与东盟各国数字经济的合作与联系,促进区域资源要素高效汇聚与流动。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共同制定“数字‘一带一路’与东盟合作发展规划”,将其纳入国家外交、科技、商务等国家间合作框架协议。围绕东盟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数字娱乐、在线旅游等数字经济重点领域,(46)Jeff Desjardins, “Southeast Asia: An Emerging Market with Booming Digital Growth”, Visual Capitalist, February 26, 2018,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southeast-asia-digital-growth-potential/。中国需加快制定相关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明确双方合作的路线图、实施路径及政府职责和企业规范,注重各项政策措施衔接配合与项目落地,为企业“走出去”、开展重点领域合作提供指导。同时,可进一步突出中国与东盟各国以数字链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发展,形成“数字链、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四链融合协同发展,将数字经济规划编制融入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合作的各个环节,加快推动双方产业升级。中国需根据东盟各国国情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准确评估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现实需求,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共同制定并实施差别化、精准化的数字经济行动路径,推进政策创新与精准施策。中国需聚焦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国家,有针对性地推进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其中,可进一步加大对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周边国家数字经济规划编制的援助力度。此外,基于参与数字经济行为体呈现多元化的现状,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要积极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金砖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东盟共同开展数字经济相关规划编制和项目设计工作。
4.3 创新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与东盟可将人才培养作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优先议题,共同建立数字经济和相关治理的知识体系,(47)Zhai Kun and Yang Xueying,“Empowe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China Daily, November 25, 2019.强化中国与东盟人才结构和数字产业的合理匹配,推进人才链与数字链、创新链协同配合。中国可根据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特点,推动构建深度融合的科教互利合作共同体,加强中国高校与东盟各国高校和教育机构联建数字经济特色学科、专业和培教基地,搭建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平台载体,在课程研发、教师培训、人才认证、职业服务等方面为东盟各国提供优质教育服务。中国可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各类教育服务机构的联系,推动其参与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人才教育合作,搭建多层次专业化培训体系,联合当地华人科技公司共同开办培训机构,开发适应东盟各国语言、宗教文化的网络教程和课程体系,提升数字素养和应用技能。同时,进一步创新合作培养人才新模式,以在东盟地区开展数字经济业务的重点企业作为依托,在重点国家设立数字经济海外办学机构和职业培训基地。通过市场化力量为东盟国家提供数字经济培训项目,强化技能实训环节设计,为相关培训企业提供信贷优惠、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提高企业参与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为进一步强化东盟数字经济高端人才支撑,中国与东盟可考虑共建跨境科技园区、数字经济小镇、技术研发和转移中心等平台,积极引导中国科研机构与东盟国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领域开展技术交流和项目合作,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创新研发和技术合作等,推动其成为高端人才集聚地和龙头企业研发策源地。双方可探索建立中国与东盟各国数字经济人才跨境交流机制,推动与相关国家开展双边或多边学历学位、技术职业资格的关联互认,放宽东盟数字经济人才在中国开展相关行业市场准入的执业限制。中国政府可加大对东盟数字人才培养的政府援助力度,在“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下设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专项。
4.4 推进区域数字治理
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建设要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治理老路,突出“边发展边治理”理念,推动数字技术与治理理念深度融合。中国可凭借在民生服务、社会安全、灾害预测、应急管理等领域数字技术应用的优势,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东盟各国的示范与应用。在治理框架和治理模式上,双方尽快建立中国—东盟数字治理框架,提升数据治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与协同性,共同探索政府、企业、平台和个人等多方参与及多元治理的区域数字经济治理新模式。双方可建立双边、多边综合性协调机构负责数字经济治理问题,将数字治理融入现有双边和多边法律法规、贸易协定,以及条约与全球标准之中。在网络空间治理上,双方可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完善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机制,提升数据流通安全性,努力开创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治理新格局。(48)张耀军、宋佳芸:“数字‘一带一路’的挑战与应对”,《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38页。在数字冲突管控上,中国与东盟各国可进一步增强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加大管控数字冲突力度,妥善处理数字贸易摩擦、个人隐私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打击网络犯罪等问题。(49)“大力发展‘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光明日报》,2018年4月26日。由于技术的快速迭代,数字经济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治理热点和难点,需要中国与东盟加快缩小技术与政策之间的差距。(50)“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Digitalisation, Southeast Asia Needs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Technology 4.0 and Policy 1.0”, OECD, August 24, 2017, https://www.oecd.org/newsroom/to-seize-the-opportunities-of-digitalisation-southeast-asia-needs-to-close-the-gap-between-technology-4-0-and-policy-1-0.htm.在治理主体上,双方可充分发挥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作用,推动数字治理建设,促进国家间相关标准的互换互认,联合东盟国家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完善数字经济国际标准体系。在治理规则上,中国与东盟各国可共同参与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共同提升发展中国家对数字治理问题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4.5 防范和对冲其他国家的干扰
中国需继续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各国的关系,积极回应东盟的安全诉求和合作信号,防范和避免“场外因素”影响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需采取对冲措施,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蓝点网络”计划、打压华为公司、渲染网络安全等对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产生的干扰。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尽相同,各方在与东盟数字经济开展合作时存在竞争,但很多方面是互补的,甚至是可以合作的。针对其他国家的干扰,中国可创新沟通与合作方式,采取灵活有效的差异化策略。例如,对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中国可就数字“一带一路”倡议与其数字经济战略进行战略调适,协调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利益冲突,弱化“对抗”意图,避免在东盟地区形成战略对抗,争取形成由竞争向竞合转变的良性互动。而对于韩国和俄罗斯等国,中国可寻求多方共赢和最大利益契合点,共同建立良好的产业生态,鼓励数字企业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与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参与数字“一带一路”合作进程。
五、结 语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是促进东盟乃至东亚地区发展的最佳路径。(51)张群:“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东盟合作”,《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5期,第44页。数字“一带一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中国与东盟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新实践。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进展迅速,合作领域和层次不断深化与丰富,现有合作的基础也更加牢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催生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进入关键时期,面对双方在当前合作中的现实挑战,加强与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全方位对接和合作,促进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产业培育、稳妥应对美日等大国竞争方面进行合作,可作为未来的重点方向。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进程加快推进,双方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