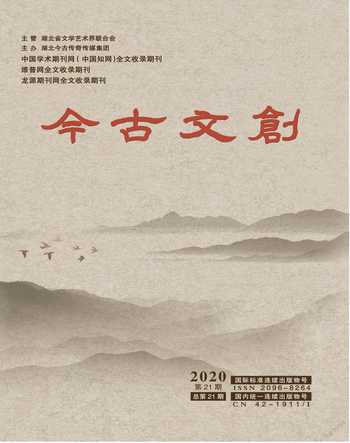《黑人开心屋》中的白脸表征
【摘要】肯尼迪的《黑人开心屋》是表现和批判种族化现象和白人性的代表性戏剧。该剧运用白脸表演,把穆拉托莎拉的自我表现为两个高贵白人女性和两个黑人男性,从而揭示了黑白对抗给她造成的分裂人格。肯尼迪的这种白脸表演戏剧策略艺术旨在质疑和批判理想化的白人性。
【关键词】白脸;人格分裂;白人性;艺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J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1-0071-02
一、引言
跨种族表演一直是美国戏剧的话题之一,其中白人模仿黑人的黑脸杂戏是美国白人戏剧中永恒的表现形式,一种戴上黑色面具或涂成黑脸,以夸张的形式讽刺、贬损黑人的表演形式。白人的这种面具仪式合法化了结构暴力,理性化了体制暴力,它以残忍的、可恶的方式攻击那些被奴役的人们,催生了一种长久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叙述,加剧了黑人刻板形象,影响了黑人自我身份认同。[1]对此,许多非裔美国女性剧作家感到他们必须直面并直接回击白人在他们的戏剧中塑造的消极刻板印象。上世纪60年代非裔美国剧作家肯尼迪的《黑人开心屋》是表现和批判种族化现象和白人性方面最具代表性戏剧。虽然剧中的主人公莎拉诋毁她的黑人性而崇拜白人性,但该剧本身却在通过她的分裂人格,通过“白脸”表演来反击这种价值观,质疑和批判理想化的白人性权威。
二、分裂的人格
莎拉是黑白混血“穆拉托”女性,一个种族和性别歧视阶级自我憎恨造就的牺牲品。该戏剧以公爵夫人和维多利亚女王谈话和贯穿戏剧始终的敲门声为开端,来表现她对黑人父亲的恐惧。敲门声预示着黑人父亲再次到来和她的梦魇。她一直认为是黑人父亲强暴了她的白人母亲,所以,她视父亲为魔鬼,威胁着白人女性身份,就像她母亲一样,也把自己的黑人身份归罪于他。对父亲的恐惧和她迫切希望成为白人的愿望使得她的自我身份分裂成维多利亚女王、哈布斯堡公爵夫人、耶稣、帕特里斯·卢蒙巴四个历史人物。两个女性历史人物代表她所渴望的白人性和母系身份及传统,而两个黑人历史人物则象征她憎恶的黑人性和父系身份及传统。相互对立的人格和文化力量存于她一身,每一个自我都与另外三个相互冲突、相互侵蚀,都想取得对对方的统治权,把对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2]莎拉极力调和这四种冲突的自我,然而,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力下,她绝望地自杀了。
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是国家和一个时代的象征。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她集权力与荣誉于一身,同时也是高贵白人的象征。但剧中的女王与历史上的女王完全不一样,此时的女王已经丧失了应有的气质和风度。这个女王就是莎拉。尽管面具把她伪装成一个白人,但她的头发不停掉落,预示着她的权力在慢慢消失。女王本是莎拉的母系偶像,她羡慕女王的白皮肤和权力,在她的床头矗立着女王的雕像,可能是希望雕像带给她力量,或者她可以借此满足自己心理上的需要。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雕像并没有给她带来能量,反而让她的人格自我更加破碎。
哈布斯堡公爵夫人是女王的表妹,一个非常勇敢、聪明和雄心勃勃的女性。像女王一样,她是欧洲殖民主义的象征,也是莎拉的母系偶像和她渴望的王室白人女性。剧中的公爵夫人表现出一种对自己肤色厌弃和黑人父亲的恐惧。她声称他是世界上最黑的,是魔鬼,而她的母亲却是白人,是天使。这表明公爵夫人是莎拉的一个分裂自我。她这种分裂的身份让她变得胆小、懦弱、自私、残忍。公爵夫人沒能给莎拉带来力量和勇气,相反,莎拉用一张面具来掩饰自己的黑人面孔,面具之下依然是那个穆拉托女孩。
这个角色支离破碎的人格在剧中逐渐瓦解,最终她无法融合的自我表明。在否定黑人身份的同时,她也否定了自己、母亲和父亲,否定了她与黑人家族史在更大的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相关性。[3]因为“穆拉托”身份依然不被白人社会认可而导致她自我憎恨,将自己转化为白人刽子手耶稣和黑人领袖卢蒙巴。
耶稣是充满爱、宽容、和平、力量和幸福的基督教灵魂人物,受人膜拜。剧中的耶稣也由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黑人扮演,但他变成了莎拉是另一个自我,“一个驼背、黄皮肤的侏儒,穿着白色的破衣和凉鞋”[4],矮小好色、心理残缺,完全是怯懦和畸形的形象。他不是救世主的化身,不是回到非洲拯救整个黑人民族,而是轻视和厌弃他们,一心想脱离黑人身份。
卢蒙巴曾是刚果的缔造者之一,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他与新老殖民主义和分裂势力做斗争,但最后他却被同胞杀害。剧中的卢蒙巴是莎拉的黑人父系,代表她的另一个自我,他同样不愿接受自己的黑人身份。他本应拯救他的人民和国家,反对殖民统治,然而舞台上的他却是一个病态和畸形形象,他的头好像被分成两半,两眼无神,头发也像其他人物一样不停脱落。
三、白脸戏剧策略的艺术价值
四个历史人物这种复合体角色表征了莎拉人格的分裂。显然,肯尼迪反击和解构这种白人性的最直接方法是白脸戏剧策略的使用。舞台说明提到维多利亚女王和哈布斯堡公爵夫人的特征:穿着廉价料子的白色长外套,帽子是白色的,帽子下面却是乱蓬蓬的卷发;戴上面具或者化妆后她们的脸白中带黄,颧骨隆起,眼睛大而黑,额头高耸,头发卷曲,“如果没有戴面具,那么脸上必须是涂了厚厚的白粉,有一种僵硬呆滞的表情和死人脸一样的沉静。”[4]肯尼迪对两位皇室女性的描述完全是对白人性的批判:白人性不仅仅被当作一种已建构的身份呈现出来,而且过度可见、奇怪,甚至骇人恐怖。
肯尼迪也给戏剧导演提供了两种白脸人物表征方法来表现白人性:使用有形的面具或涂厚厚的白色化妆品。无论哪种情形,人物高度可见的乱蓬蓬的卷发变得异常突出从而达到视觉冲击效果。通过提供面具之下真实黑人身体特征的永恒提示物“卷发”,肯尼迪提醒受众这是黑人与白人的集成现实。面具或化装的掩饰功能把注意力引向她们的身份建构和种族身份伪造的性质。剧中的白脸意指策略是通过采用跨越种族的戏仿同时,实施白人表征而不是黑人表征但又修正它的含义;该剧“暗含了种族歧视的黑脸秀主要修辞,质疑基本的社会、哲学、本体论问题:种族是什么,是怎样体现的,黑与白不可调和的绝对性怎样得到内化甚至自然化我们的皮肤,进而移植到我们的身体。”[3] 显然,肯尼迪的白脸参考了黑脸秀策略,她的白脸是对严格划定的黑与白的对抗。
肯尼迪具有讽刺效果的白脸戏仿专注于偶像式的以欧洲为中的人物。因此,肯尼迪的过分装饰的场景和描写使得白人性修辞充满活力,她的白脸主题的选择要求受众人物的象征意义。维多利亚女王和哈布斯堡公爵夫人是权力承载的形象,她们“作为权力轨迹融合在一起,这种权利轨迹由当代全球性的父权制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经验提供。她们是占统治地位的白人人物形象,叠加在黑人性之上,象征欧洲强权政治。”[4]当女王和公爵夫人充当殖民主义和白人统治的象征符号时,也应该注意肯尼迪所选人物特点也对这些历史人物特定的和个人的叙事做出的批评,这样进一步消解了对理想化的白人性的认知。
维多利亚女王象征英国殖民统治的顶峰,但同时象征王室人物缺乏政治影响力和乏力的个人生活。她也是一位女性,在位期間遭受家庭不幸和轻度抑郁症不断发作的折磨,必须严重依赖她的首相和重臣才有可能确保权力不断缩小的君主政体的延续,因而她只是一个象征性而不是真正政治上的领袖。因此,女王象征着另一种形式的面具:权力面具,它掩盖了君主制本质上的虚弱和无能。同样,哈布斯堡公爵夫人代表与高贵相关的名望和权力,但她个人历史与主人公莎拉飘摇不定的精神状态遥相呼应。为了挽救丈夫,她拖着病身返回欧洲向拿破仑三世和教皇寻求援助,失败后丈夫被处死,自己则最终演变成精神分裂症而发疯。因此,肯尼迪并没有崇拜英国君主政体中的人物女王和公爵夫人,而是把她们戏剧化,成为她批判白人性的戏剧策略,通过恰当的人物角色来质疑理想化的白人性权威和地位。
就像用女王和公爵夫人祛除对理想化的白人性认知的浪漫主义色彩,肯尼迪的驼背和黄皮肤耶稣也是如此。通过进一步把耶稣描述为穿着白色破旧衣服和拖鞋的侏儒,肯尼迪斥责一个美化了的白人耶稣的现代表征,同时也挑战基督教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畸形丑陋和种族上模糊不清的耶稣亵渎了如善恶、黑白、正常与反常这样的二元建构观点。剧作家让卢蒙巴戴着乌木面具则强调了种族间和种族内冲突,也强调了摆脱不掉的黑人身份。肯尼迪似乎在这里暗示,像公爵夫人和女王这样的欧洲女性权力人物占据了莎拉的身份,为莎拉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力量来对抗她黑人父亲的威胁,对抗她对黑人种族和黑人男性身体的恐惧和厌恶。这种复合体角色表征了莎拉人格的分裂。身份的冲突导致她自我人格分裂,分裂又加剧种族憎恨和自我身份定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能性。分裂的根源在于她憎恨黑人身份,崇尚神话化了的白人性,想努力获得白人社会认可,然而结果却是她既不属于黑人社会,又不被白人社会所接受。
四、结语
肯尼迪显然是通过表征四个历史人物的弱点来呈现莎拉的分裂人格,但整个剧中白色面具或白脸戏剧策略始终用来质疑广为接受的神话化了的白人性,破坏和动摇它的稳定性。甚至主人公莎拉收集的各种物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试图掩盖和逃离她黑人性的证据,否定其身份与黑人家族史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相关性。戏剧对白脸面具的持续展示,莎拉过分装饰的空间和华丽的物件都在视觉上相互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卓.黑与白的“变脸”——论“黑脸喜剧”的历史嬗变及文化悖论[J].外国文学,2016,(5).
[2]白锡汉.艾德里安娜·肯尼迪戏剧中的私刑历史叙事[J].戏剧之家,2015,(11).
[3]Wood, J. Weight of the Mask: Parody and the Heritage of Minstrelsy in Adrienne Kennedy’s Funnyhouse of a Negro[J]. Journal of Dramatic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3(1).
[4]Kennedy, A. Funnyhouse of a Negro[M]. NY: Samuel French, 1969.
作者简介:
白锡汉,男,陕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非裔美国女性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