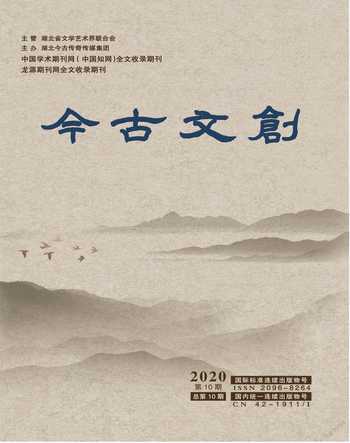《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双重叙事声音
【摘要】 《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叙事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式叙述者的双重叙事声音。作者安排第一人称回顾型叙事者将自己的话语融入“我”的思考轨迹之中,而母亲与老干部的精神上的爱恋作为主要故事情节部分,则在女儿“我”和笔记本上母亲不在场的叙事声音共同完成,其本质是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珊珊)与隐含作者间的潜在对话关系,为文本增添了一种复调的美。同时,作为女性“成长”主题的短篇小说,叙事者的双重叙事声音建构以女性视角探讨了女性的真实存在及对“自我”的构建。
【关键词】 《爱,是不能忘记的》;双重叙事声音;复调审美;儿童视角;女性成长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0-0023-02
叙述者是每部小说的主体和关键,“他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这个行为通过对一定叙述话语的操作与铺垫最终创造了一个叙事文本”。《爱,是不能忘记的》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有限性是第一人称叙事的特点。而张洁运用双重叙事者,使作品中的“我”成为能够全知世界的上帝,小说显现出复调的叙事特点,引导出双重叙事声音。
一、双重主题结构与双重叙事声音
文本中不难发现作家在小说中安排了“双重主题”的结构,即“爱情”的主题和“女性成长”的主题。我与母亲钟雨共同组成了“双( 女)主人公”的设置。女儿珊珊通过回忆、阅读和分析母亲的爱情日记,自己潜在的意愿与理想也已暗中塑形,完成了自我的爱情成长宣言。小说总体上采用的是两个故事嵌套的结构,充当叙述主体的“我”在叙述文本中具有的独立身份,即其本身是小说中的人物,“我”参与到了故事中来,“我”是作品中的虚构人物,而作者不过籍“我”之口来实现其叙事目的和意图。但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受到主人公身份的约束,不能述说本角色之外的具体内容,这就导致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场面的有限性”和“主观性”。因为“我”无法将我不在场的场面呈现给读者,叙述上它偏于主观。
而隐含作者的出现则彰显了叙述者的显在性和权威性。韦恩·布斯在其《小说修辞学》把隐含作者视为依赖于文本里的创作者的“第二自我”。也就是说,某个叙事文本展现出来的形态,正是隐含作者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等注入其中的结果。隐含作者是在读者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产生和建立起来的。
《爱,是不能忘记》中的隐含作者是介于第一人称的“我”与文本的中介者,存在于文本之中,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在故事被陈述的同时起到解释和评论的作用。叙述者是“表达出构成文本语言符号的那个行为者”,其体现自己的方式就是叙述声音。据此,《爱是不能忘记》中存在两种叙事声音,分别为个人型叙事声音和作者型叙事声音。
个人型叙事声音,即第一人称写作手法,通过“我”的记忆与母亲的日记来叙述“母亲”对于爱情的执著。第一人称内聚焦的表现手法让小说更为切合人物形象的内在感受,珊珊的心理变化与焦虑都可以自由地以接近独白的方式表现出来。小说开头就是叙述者“我”作为三十多岁面对婚姻困惑的单身女青年,对婚姻充满疑惑,紧接着随着“我”的回忆跳入母亲临终前与“我”对话的情景:“准是我那没心没肺,凡事都不大有所谓的派头让她感到了悬心。她忽然冒出了一句:‘珊珊,要是你吃不准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
作者这样的叙述方式可以方便控制叙事流引导读者进入母亲的故事。“我”主要是讲述母亲的故事,但同时也展示“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拉进了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共鸣效果。
作者型叙事声音,即隐含读者藏匿在文本中的声音。按苏珊。兰瑟的定义,它是指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且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隐含作者虽没有直接公开,但以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姿态存在着。在《爱,是不能忘记》中:“她就会揪心地想到为什么他离她那么近而又那么遥远?他呢,为了看见她一眼天天从小车的小窗里,眼巴巴地瞧着自行车道上流水一样的自行车辆,闹得眼花缭乱,……他在百忙中也不会忘记注意着各种报刊,为的是看一看有没有我母亲发表的作品。”
作者在此处引入的是万能视角,“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却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出现,因此可见,这里并非与前文中的第一人称视角产生了冲突,而是隐含作者隐身在幕后,传达出声音。
在小说的结尾处,叙述者的人称又发生了转换,“我”换成了“我们”,作者把文本的潜在读者拉出来,描述了“你”对爱情或婚姻的多种困境,“……我为什么要钻牛角尖呢?说到底,这悲哀也许该由我们自己负责。谁知道呢?也说不定还得由过去的生活所遗留下来的那种意识的一种挑战。有人就会说你的神经出了毛病或者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这里作者以“隐含作者”的身份引出了隐含读者,隐含作者在客观叙述中隐身在幕后,为广大女性发声。
二、双重叙事声音的复调特征
“复调”本是音乐专有名词,巴赫金转用该词来解释小说文本中的“多声部”现象,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认为复调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换句话说,小说中的“复调”主要指文本中几种类型的叙事声音、几种思想观念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主要表现为多个独立意识的交响乐曲和对话特性。
在小说中,双重叙事声音的复调特征主要体现为对话性特征。对话性是复调小说的本质特征,“巴赫金所构建的话语体系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开放性的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里,各种表述平等共存但他们并不彼此独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阐明的。他们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
小说中母亲的“精神日记”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袒露出母亲内心对至爱的深沉、挂念和遗憾。母亲笔记本上的倾诉与女儿珊珊的观察与推测相互交织,形成了两种交互显现、相互呼应的叙事声音。如:“要是他不愛她,为什么笔记本里会有这样一段记载呢?‘这礼物太厚重了。不过您怎么知道我喜好契诃夫呢?’‘你说过的!’‘我不记得了。’‘我记得。’原来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是他送给母亲的。对于她,那几乎就是爱情信物。”
“我”与日记本里的母亲的故事叙述横向交织,由“我”所叙述的日记,并不是单个叙事声音,而是双重叙述声音的相互作用。即“个人型叙事声音”与“作者型叙事声音”相互渗透、相互阐明,引语间的自由转换,不断对话产生了情绪效果。
此外,小说“我”的故事符合成长小说的一般标准,儿童聚焦者与隐含作者的成人身份间存在潜在对话关系,“我”被一分为二,分割成了成年的叙述者和儿童回忆的我,并以一种独特的文本张力达到文学阅读的陌生化效果。在讲故事中,“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儿童,说话幼稚,对成人世界充满新奇。母亲与老干部偶遇那段,作为儿童的珊珊尚不能理解成人世界的言语行为,由此,“我”看着老干部被民警呵斥,只是觉得有趣。转头却看到母亲好像一个小女孩。追忆结束后叙述者又转回到成年的珊珊,“现在回想起来,他准是以他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动了母亲的心……”显然,这种成年的态度与儿童时的懵懂之间形成了一个巧妙的呼应,隐含作者则是艺术精湛的指挥者,从而促成了叙事文本复调审美显现。
三、双重边缘中“自我”身份的确认与文化反思
双重叙事声音既是女性文学自觉发展的结果,也是张洁融入自己对爱情的幻想不自觉的创作结果,女性的叙述声音中隐含的是一种自我本色的独立意识。张结在写作时,她把这种女性意识放在幼年珊珊、成年珊珊和母亲钟雨的交替叙述中,用双重声音对外呼吁女性要摆脱无爱的婚姻,自由选择自己的伴侣。
此外,结合当时社会与历史深厚意蕴,她将女性觉醒与文化反思结合起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男权话语社会,长期以来,女性都处于“失语”的状态,这种创作模式必然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反叛成为潮流,但对女性书写的内容、形式却没有真正自由。张洁小说中的双重叙事声音实质上是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探索和思考,这一探索和思考并没有出现与男性话语相斥的局面。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作品里塑造了一位至善至美的“老干部”男性形象,而为了柏拉图之恋终其一生也未再婚的钟雨也是男性眼中优雅的女性。这些人物形象的创造也表现出张洁追求一种以女性独立人格为前提的自由、平等、真挚的两性关系。
张洁以充满问题的眼光看待社会和人生,在如何看待婚姻价值的问题上,小说的结尾,作者借珊珊之口批判社会积习和旧有意识对个人的压迫:“别管人家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以来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
面对多数人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现状,张洁作为新时期的女性,她开始大胆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鼓吹女性解放,探索纯真爱情与文明婚姻。张洁戏称这部作品是一篇读书笔记,她说:“这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问题的小说。是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试图用文学形式写的读书笔记。”以“我”为主角,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批评那个禁欲的社会的不满。
小说中双重叙事声音的复调特征瓦解了情节的复杂性,是作者及女性心灵复调的反应,具有相当高的美学意义和人文意义,使张洁“女性成长”主题更加深刻和流畅,由觉醒所带来的成长更是对女性要争取人格平等,追求自我的一次宣告。
参考文献:
[1]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8.
[2]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
作者簡介:
刘利娟,女,湖北人,中南民族大学201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