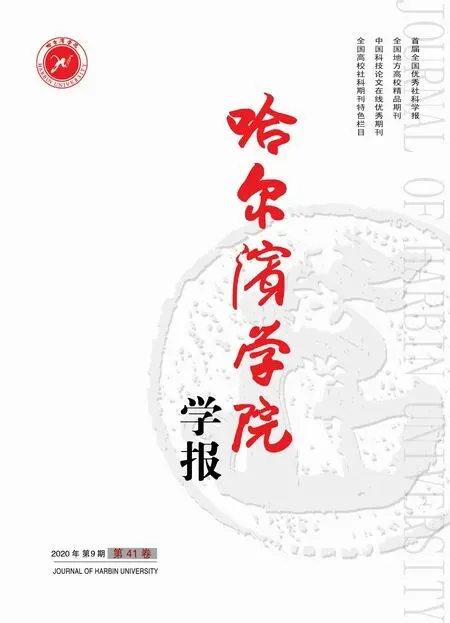以胡塞尔现象学视角看奥古斯丁时间虚无性问题
——以《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为基础
王 芸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时间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大难题。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开篇就引用了奥古斯丁对于时间问题的描述:“没人问我,我还知道,若有人问我,我想向他说明时,便又茫然不知了。”[1](P37-38)可见时间问题之晦涩。然而胡塞尔与奥古斯丁的关系并不止于引用其文字作为文学修饰,他还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开篇称赞了奥古斯丁对时间的分析。不少研究者认为,奥古斯丁的时间分析与胡塞尔的分析存在一定相似之处。然而,本文将表明,两者的时间观念存在根本的分歧,奥古斯丁走向了将时间理解为全然的虚无这一路径。当然,这与他的神学立场是不可分的。本文试图以胡塞尔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一回应。
一、奥古斯丁论时间
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忏悔录》第十一卷。在第十一卷中,奥古斯丁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其论述:上帝作为创造者,其意愿不能从受造物中来,因此上帝的意愿在其自身之中。如果上帝创造世界这个意愿是全新的,那么上帝就不是永恒的;如果这个意愿是永恒的,那么为什么受造物不是永恒的而是无中生有呢?在这个问题中,人们将永恒理解为一种时间中的持存,即对生成变化的否定。奥古斯丁认为,这种理解误解了永恒的真正意义。时间乃是受造物,作为创造者的上帝超越了时间,因此不存在“创世前后”这种说法。这种超越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超越,而是指“在永恒现在的永恒高峰上超越一切过去,也超越一切将来”。[2](P241)永恒是对一切时间的超越,它完全对立于时间。而这种永恒被具体描述为“永恒的现在”。“永恒的现在”不同于时间性的现在,奥古斯丁如是描述道:“你的日子,没有每天,只有今天,因为你的今天既不递嬗与明天,也不继承着昨天。你的今天即是永恒。”[2](P241)与“递嬗与明天”“继承着昨天”的现在相对,“永恒的现在”与将来和过去无关,它是不动的现在。同时,时间性的现在的含义也浮现出来了:它是将将来递送给过去的一个“枢纽”。
然而,作为枢纽,现在却是一个虚无的点。奥古斯丁认为,过去已经不“是”,未来尚且不“是”。因此,不能用“是”来描述过去与未来,而只能说“曾是”和“将是”。唯有现在,才能“是”,才是存在。但是,如果现在永久“是”,那就不是时间而是永恒。因此,现在之所以“是”,乃是由于它是未来与过去的交界点。这就意味着,“现在所以在的原因是即将不在”。[2](P242)作为这一交界点的现在是没有延展的,因为一有延展,就区分出了过去和现在。于是,在此便出现了一个悖谬的结论:现在作为一个虚无的点而“是”或者说存在,而现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走向不存在。
现在是一个没有丝毫延展的纯粹虚无之点,过去与未来不“是”。因此,作为三个维度之统一的时间便不能说“是”。但人们也不能说时间不“是”。准确的说法是:“除非时间走向不存在,否则我们便不能正确地说时间不存在。”[2](P242)在介于“是”与不“是”之间有一种张力,时间便在此运作,这种张力显然来自于从未来流向过去的流动性力量。未来之所以可能流向过去,是因为未来与过去之间具有某种亲和性,这种亲和性的表现就是作为递送之“枢纽”的现在。同时,现在又使未来与过去保持区分。因此,现在是使过去与未来既统一又分离的力量。
现在何以具备这种力量?从《忏悔录》的文本来看,时间性的现在所拥有的力量来自于“永恒的现在”:“谁能把定人的思想,使它驻足谛观无古往今来的永恒怎样屹立着调遣将来和过去的时间?”[2](P240)黑尔德在《时间现象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指出,这种将时间性的现在视角归结于永恒的做法,来源于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时间是永恒的影像,永恒是持守于一的当下,具备存在。而时间不存在,它仅仅是一个发生进程。在柏拉图的时间观念中,作为当下存在的“esist”是不能进入时间的。在尘世的时间性中,现在无非是指过渡性,它并不是永恒的存在。[3]在此,奥古斯丁似乎弱化了这种极端性,他认为在现在之中有一种张力,现在“是”,但这是因为它走向不“是”。
当然,除了求助于永恒,奥古斯丁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以说明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理解。人们会说:时间具有长短。这一段时间长一些,那一段短一些——时间可以度量。但是过去已经不“是”,未来尚未“是”,现在是无延展的纯粹的点,那么对时间的度量是如何可能的?在此奥古斯丁引入心灵的力量。心灵具有三个基本功能:记忆、印象和期待。尽管过去已经流逝,将来尚未到来,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将来的期待始终在场。因此,日常生活中所谓的对时间的度量实际上是对记忆、期待的度量。期待通过注意进入记忆,这类似于未来通过现在被递送至过去。就单独地看来,注意仍是一个用于递送的点,这个点必然是无延展,因为一旦拥有延展,便区分出记忆与期待。因此,注意是虚无的点。这个点“向两面展开”,[2](P256)展开为一个有三个维度的统一体。问题在于,如果记忆与期待在现在(或者说作为纯粹过渡点的注意)在场,而现在是一个纯粹虚无的点,那么,期待与记忆同样是虚无的。因此,这里再次引发了时间的虚无性问题。
对奥古斯丁而言,尘世是纯粹的虚无。时间作为受造物也是虚无的,这种虚无通过一个虚无的现在点而支撑出一个双面的统一体。黑尔德如是总结道:“人类的时间是彻头彻尾的虚无;未来尚未存在,而过去已不在,那流逝着的现在作为两者之间的界限同样不具有存在。但在一定程度上使之有所平衡的是,它的受过这种虚无性浸染的整体性中,人类的全体时间在每一个‘现在’中都在场。”[3](P25)问题在于,时间是虚无的吗?
二、以胡塞尔的角度探讨奥古斯丁的时间虚无性问题
(一)问题的澄清
时间是虚无的吗?在此要追问的并不是自然态度下时间的实存性问题,而是指经过还原后,就直接被给予的现象而言,时间是否是彻底的不在场?以直观性的原则来看,时间显然是在场的。那么应该如何回应奥古斯丁的分析呢?以下将从胡塞尔的视角出发,通过对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分析,对这一问题作一回应。鉴于篇幅与笔力,本文的探讨将集中于《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这一文本。
(二)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结构
时间客体是如何被构造的?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在这里涉及前摄—原印象—滞留三重统一的内时间意识结构。滞留、原印象、前摄都是指意识方式。一个材料虽然在现在序列中过去了,但它以滞留的方式在当下被意识到。同样,一个材料虽然在现在序列中尚未到来,但它以前摄的方式在当下被意识到。例如在图1中,横坐标轴绝对的现在点的序列,A和B是已经过去的绝对现在点,C是当下的绝对现在点,D和E是尚未到来的绝对现在点。所谓绝对的现在点,即在抽象的目光下那个转瞬即逝的现在,即奥古斯丁所说的那个将未来递送给过去的绝对虚无而无延展的现在。这个无延展的现在是不能被把握的。但是在当下时刻,除了对C的原印象,还有对A、B的滞留A”和B’,以及对D、E的前摄D’和E”。在这里字母表示内容,上下标则代表意识方式的不同。这意味着滞留A”与当初的原印象A的内容是一致的,二者的区别在于意识方式。因此,滞留A”是对当初被给予的A本身的滞留,在其中A是被直观到的。与之相对,前摄D’中D本身被直观到。前摄—原印象—滞留构成了纵坐标轴的序列。胡塞尔认为,这个纵坐标轴才是被直观到的现在。因此,现在是一个具有宽度的晕圈。

图1
就以上论述而言,胡塞尔的结构与奥古斯丁是相似的。在奥古斯丁那里,同样存在着一个三重一体的结构:期待—注意—记忆。同样的,奥古斯丁认为这三者统合于一个现在之中:“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待”,[2](P247)期待通过注意而进入记忆之中。这种从期待流向记忆的能力是心灵的能力,而这种结构是由一个现在点支撑起来的。由于现在本身是一个无延展的空虚之点,这一结构就出现了一个吊诡的悖谬:期待与记忆的双面延展是由一个无延展的虚无之点支撑起来的。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奥古斯丁将此归结为时间本身之虚无性。期待作为对不存在的未来的期待,通过一个纯粹虚无的注意,而成为对不存在的过去的记忆;时间本身“从尚未存在的将来出现,通过没有体积的现在,进入不再存在的过去”。[2](P248)于是,这种双面延展也被归结为彻底的虚无。
前摄、原印象、滞留三个要素与奥古斯丁的结构之间是可以对应起来的。前摄是对尚未到来之物的前摄,滞留是对已经过去之物的滞留,二者相当于奥古斯丁的期待与记忆。原印象则对应于注意、印象。在胡塞尔那里,三个要素之间也构成一个延展。那么,胡塞尔的结构与奥古斯丁究竟有何不同之处?对于作为虚无之点的现在如何支撑起一个延展的问题,如果不求助于将时间整体归结为虚无,以胡塞尔的视角又该如何解决?
(三)对时间理解的区别——基于对“现在”的不同理解
应当注意到,奥古斯丁所说的双面延展与胡塞尔的延展有着区别。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以唱一首娴熟的歌曲为例,对期待—注意—记忆的结构进行分析:“在开始前,我的期望集中于整个歌曲;开始唱后,凡从我的期望抛进过去的,记忆都加以接受,因此我的活动向两面展开:对已经唱出来的讲是属于记忆,对未唱出来的讲是属于期望;当前则有我的记忆力,通过注意把将来引入过去。”[2](P255)这里的关键是,从将来到过去是通过注意而发生的。换而言之,期待—注意—记忆这一结构的支撑点乃是注意。在这个结构中,期待通过注意这一过渡点而成为记忆。
如图2所示,O点是作为过渡性的现在点,左边是对过去的回忆,右边是对未来的期待。点N原本是期待,通过点O,它成为记忆。这里所说的双面延展指以点O为边界的过去与未来两个视角的延展。这种延展的基点是作为界限之区分的现在点,这个现在点在区分两个视角的同时使从过去向未来的过渡得以可能。因此,延展之所以可能,在于一个无延展的现在点。这种延展是从未来到过去的不断转化。

图2
胡塞尔同样承认无延展的绝对的现在之点不能被直观:“各个立义在这里连续地相互过渡,它们限定在一个立义中,这个立义构造着现在。但这个立义只是一个观念的界限。”[4](P101)在此,胡塞尔认为,绝对的现在之点是一个边界,即滞留与前摄的边界。这一边界只是观念上的极限,或者说,是一个理念。在胡塞尔这里,这一理念不能独立自为地存在。“这只是一个观念的界限,是某种抽象的东西,它不能自为存在。此外还要坚持一点,即使这个观念的现在也并不是与非—现在有天壤之别,而是连续地与之相联接的。”[4](P101)因此,就事情本身而言,不能抽象地谈论原印象点,必须要在前摄—原印象—滞留这一整体结构中来讨论。在这一整体中,本原的构造发生了,它能够被直观到。
因此,在胡塞尔这里,除了从未来向过去的不断转化这种意义上的延展,还存在着另一种延展,即前摄—原印象—滞留构成的晕圈。这一晕圈进行着本原的构造。唯有在前摄—原印象—滞留之统一体的语境下,谈论原印象才是有意义的。换而言之,不是虚无的、无延展的绝对现在之点支撑起一个三重一体的时间结构;而是在三重一体的时间结构中,通过理念化的行为,一个无延展的现在点才可能被把捉。
在此,奥古斯丁的分析中存在的问题“一个无延展的现在点如何可能支撑出双面的延展”已经被消解了。在奥古斯丁那里,时间的现在视角具有一个根基性的地位,以现在为基点,过去与未来之区分、统一及其流动才可能发生。然而在胡塞尔这里,绝对的现在只是一个理念,尽管它占据了前摄—原印象—滞留这一结构的内核位置。绝对的现在本身唯有在前摄—原印象—滞留的统一中才可能区分出来。胡塞尔倒转了奥古斯丁的层次:绝对的现在点恰恰以时间的三重统一视角为基础。
以这种对现在的理解为基础,奥古斯丁进而推论出整个时间的虚无性:不存在的未来通过虚无的现在被递送至不存在的过去。这一推论的层次是从分散的三个视角到其聚合与联系。然而问题是,绝对的现在之点,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发生的过去与将来,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在胡塞尔那里,应当是先有本原性的构造之发生为其基础,而后对这一构造分析,并进行理念化,才能得到独立的原印象。这种本原性的构造是能够被直观到的,在此意义上,作为前摄—原印象—滞留之三重统一的时间并非是虚无的。
三、总结与反思
本文尝试对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作一分析,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无延展的现在点如何可能支撑出一个延展?如果将延展也归入虚无性,那么时间就是彻底的虚无。奥古斯丁便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就实事本身来看,人们确实能够体验到时间。
在奥古斯丁那里,虚无的现在点处于基点的位置,而胡塞尔倒转了这一层次,将绝对现在点置于整体的视域之中来考量。于是,奥古斯丁以无延展的现在点支撑延展的可能性问题本身就被消解了。恰恰是在延展本身之中,无延展的现在点才能在理念化的目光中出现。同时,基于这一理解,时间不再是不可把握的虚无,因为虚无性是从现在点的虚无之中推论而来的。以胡塞尔的视角来看,前摄—原印象—滞留的时间整体可以被直观到,它不是虚无。恰恰在这一整体性中,理念化的行为才构造出了抽象的虚无性——一个无延展的现在点。
本文仅以《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为基础进行了分析。事实上,在《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中,胡塞尔对原印象进行了更详尽的分析,并将其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位置完全倒转过来了。此外,关于理念化的问题,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也有大量论述。鉴于篇幅与笔力,本文缺少对这一部分的分析,实属遗憾。
——专栏导语
——兼论现象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