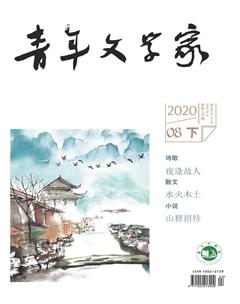布莱德自我缺失背后的创伤解读
摘 要:从《最蓝的眼睛》到《孩子的愤怒》,创伤一直是当代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她塑造的人物在创伤中“努力理解人类生存环境的各个方面:善良、邪恶、爱情、友情、美丽、丑陋、生存以及死亡”[1]。《孩子的愤怒》通过多重叙事视角以及魔幻叙事手法,讲述了奴隶制废除之后依旧笼罩于美国当代黑人的创伤阴霾。基于肤色主义的种族创伤以及不幸童年的家庭创伤是造成女主人公布莱德自我缺失根本因素。
关键词:《孩子的愤怒》;托妮·莫里森;创伤;自我
作者简介:郭晓睿(1999.9-),女,汉族,山东肥城人,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17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外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2
前言:
从最初的《最蓝的眼睛》到如今的《孩子的愤怒》,基于肤色主义的种族歧视一直是托妮·莫里森的写作主题。她尤其关注出生于美国的黑人女性的命运,注重刻画黑人女性基于种族、历史与性别的创伤历程,表达对种族历史的深切思考。莫里森曾在创作《最蓝的眼睛》时提到“我一直在书写美丽、奇迹及自我形象,书写人们彼此伤害的方式,书写一个人是否美丽”[2],而《孩子的愤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美丽”故事的再现于改写。小说采用“复调叙事”的结构,以多重叙述视角讲述了女主人公布莱德基于肤色主义的种族创伤以及不幸童年的家庭创伤。
一、家庭创伤
因为生下来便“黑得要命,像午夜,像苏丹人”①。布莱德自出生起便遭受其父母的嫌弃。“她飞快地变深了。她在我眼皮底下变成黑得发蓝的颜色时,我想我要疯了”(5)。可以说,布莱德从出生那刻起,就因为其天生的黑皮肤而背负了永远摆脱不掉的十字架。母亲难以接受并厌恶深肤色女儿的一切,布莱德的出生直接导致了父母婚姻的破裂,父亲一口咬定布莱德的母亲“跟其他任何男人鬼混”,母亲驳斥道“她那么黑,一定是他家那边的问题,跟我家这边没关系”(6)。
在抚养教育孩子上,甜心显然缺乏对布莱德的情感投入和情感交流,割裂了与她的亲密关系,而“依恋是儿童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开端和组成部分。研究表明,早期安全的依恋关系不仅有利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化的顺利进行,而且直接影响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人格完善”[3]。母亲的逃避回应进一步加剧了布莱德的不安全感,赫曼认为“与照顾者的联系所产生的安全感,是个体人格发展的基础。当这种联系粉碎时,受害者就会丧失基本的自我感”[4]。基于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又缺乏与母亲的依恋关系,布莱德内心孤独、恐惧、才有故意犯错让母亲扇自己耳光的怪癖。“母亲原本尽一切可能避免与她有任何身体接触,却触碰了她,伸手推她,由此带来的满足感缓和了她受到的惊吓”(88)。母爱极度缺失引起的价值观的扭曲和受虐倾向,严重伤害了儿童正常的自我构建,导致儿童人格的不完善性。
从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到绝笔之作《孩子的愤怒》,莫里森的作品在自我的探寻上具有连续性,其作品探寻自卑心理导致自我意识的严重受创,即自我的缺失。因为奴隶制的历史过去,黑人始终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丑陋不堪。在白人文化霸权中,美国黑人的“童年的创伤更加严重些,因为他们产生在心智发育不完整的时期,更容易导致创伤”[5]。
二、种族创伤
创伤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一种被社会建构的事物。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已经谈及肤色主义,而在《孩子的愤怒》中将此主题再次深化。布莱德出生于九十年代,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黑人奴隶制度早已被废除,但肤色越浅越高贵的思想根深蒂固,白人统治者构建了文化创伤,继续在精神上奴役获得自由之身的黑人后代,白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扭曲黑人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将自己定义为社会边缘人物,他们必须屈服于白人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才能换取相对平等自由的生活。黑人女佣“就是不能和他们碰同一本《圣经》”,“在俱乐部、教堂、联谊会甚至黑人专属学校里按照肤色来分类”(4),侮辱谩骂更是家常便饭。对黑人的歧视行为不仅来源于白人,还有装成白种人、与自己深肤色的孩子断绝关系的浅色混血儿,“哪怕渴得要死,他们也绝不会去‘有色人种专用的饮水处”(5)。布莱德的父母同样也是浅色人种,所以有幸能在百货商店试帽子而不被拦下,他们深知布莱德柏油一般的皮肤会将她困在哪一社会阶层,因此认为布莱德出生便是一个错误,她的肤色是她背上永远也摆脱不掉的十字架。
三、自我的缺失
创伤对受害者产生的心理影响解释了布莱德的创伤症状,黑人成年女性会因为白人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异化的审美观、家庭观等,儿童在白人强势文化中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自我厌恶感、嫉妒感以及仇恨等消极因素。布莱德从小就清楚自己的深肤色意味着什么,在社会和家庭灌输的肤色认知下,她不得不学会顺从、听话和懦弱,儿童时期的布莱德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创伤症状。
儿童无法健康成长,因为历史遗留的和父母传递的创伤使他们缺乏安全感,心理产生自卑感和嫉妒感。“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仅有助于引导孩子的成长,而且会修补孩子与生俱来的不足,相反,不良的家庭关系则无疑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6]。父爱缺失、母爱畸形的原生家庭導致了布莱德恐惧、孤独、无助、自卑的产生,懦弱和讨好型人格的形成。“我让她喊我‘甜心,而不是‘母亲或是‘妈妈。这听起来比较保险”(7)。“甜心”从来不喜欢触碰布莱德,从不亲自喂奶,不得不给她洗澡时满脸带着厌恶嫌弃的神情,母亲面对布莱德的一系列反应正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种族歧视深入黑人骨髓的表现,也是“甜心”将肤色认知深深嵌入布莱德脑海的过程。“甜心”教育布莱德最重要的一课是懦弱,她必须服从、讨好白人主导的世界而获得尊重和认可,比如“在大街上见到白人男孩要躲避”。幼年的布莱德将学着逃避,逃避作为一种消极的创伤复原方式,虽然可以使黑人暂时挣脱精神桎梏、寻求心理平静,但是这种压抑、逃避似的生活让布莱德严重影响了其自我的正常构建。
四、假性自我身体空间构建
根据角色扮演理论的观点,“自我的发展经过游戏阶段和竞赛阶段这两个阶段……在游戏阶段,儿童挨个扮演以各种方式进入他生活的人或动物……而在竞赛中,他扮演参与共同活动的任何一个他人的角色”[7]。布莱德童年时期一直处于角色扮演阶段,“黑人孩子”布莱德遭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创伤,片面地将母亲压抑式的保护解读为对自己的伤害,经过时间积累就形成了怨恨。同样出于对白人强势社会的不理解,加以内心对尊重的渴望,布莱德在双重复杂情感的交织下选择诬告白人教师索菲亚。通过对别人的攻击,儿童内心的失落和痛苦才能得以宣泄。她的诬告是对白人社会的报复,也是对母亲的讨好和对白人社会认可的渴望:在审判结束之后,负责疏导他们的社工和心理专家“谁也没有拥抱我,但他们朝我微笑了”,“我做得很棒,我知道,因为在审判结束后,甜心对待我的方式像个妈妈一样”(34-35)而这看似成功的角色扮演,实则是布莱德缺失自我的假性构建,她始终还是那个企图获取自己母亲怜爱的不幸儿。
大众“黑即是美”审美观念的突然转变、新历史语境让布莱德似乎获得了能够容纳她的空间,黑皮肤成了布莱德事业的一大卖点。“真我女孩”的系列化妆品被布莱德定义为“真正的自己”。这一“适用于一切肤色”产品似乎是布莱德基于大众对“身体美”理解的再创造,这一隐喻象征“真我”和“女孩”的结合,她以白人的评价衡量自我价值,“真我女孩”系列产品并非是布莱德积极进行自我构建的创造物,而仍是消极接受白人主流世界审美和价值观而生的衍生品。外貌作为布莱德身体的一个标识,是衡量身体重要魅力的一项特殊标尺,布莱德黑得发亮的眼睛为她赢得无数倾慕。服饰不单单是作为包裹身体的工具,它还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装点着布莱德的身体,使她借由身体的姿态,塑造了一个“真我女孩”形象,构建了一个虚拟的自我身体空间。
结语:
莫里森创作的人物都囿于基于肤色主义的文化和心理创伤,人物创伤的治愈紧紧围绕自我角色的追寻和救赎展开。从儿童时期“黑人女孩”的角色扮演阶段到“真我女孩”自我的角色塑造,从“白即是美”到“黑即是美”肤色认知的转变,布莱德经历一系列波折,最终摆脱来自家庭、社会的双重创伤,追寻真正的自我。莫里森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揭开现代种族歧视下黑人女性的文化、心理创伤,她认为“黑即是美”这一口号是对黑人的精神奴役,质疑了黑人种族之美被公众认可的原因,描写了“像妖魔化的种族一样的荒诞的东西如何在社会最脆弱的个体——小女孩——心中扎根,如何在社会最容易受伤的个体——女性——心中存在”[8]。
注释:
①[美]托妮·莫里森:《孩子的愤怒》,刘昱含译,南海出版公司2017版,P.3.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参考文献:
[1]王丽丽:《走出创伤的阴霾:托妮·莫里森小说的黑人女性创伤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p.8.
[2]Taylor-Guthrie(ed.).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1994, p.40.
[3]宋海荣,陈国鹏:《关于儿童依恋影响因素的研究述评》,载《心理科学》2003年第1期,p.172.
[4][美]朱蒂斯·赫曼:《创伤与复原》,扬大和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p.52.
[5]傅婵妮:《文化创伤的言说与愈合——解读盖尔·琼斯的小说<科里基多拉>》,载《安徽文學》2009年第3期,p.158-159.
[6]丁玫:《艾·辛·巴格小说中的创伤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p.95.
[7][美]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3.
[8]Morrison, Toni. The Bluest Eye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