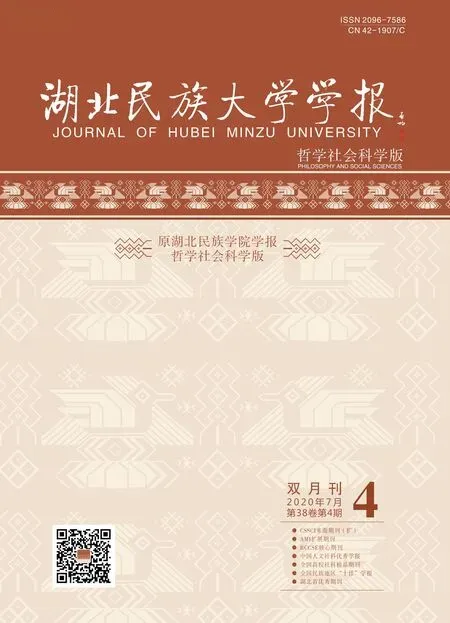跨国网络与中亚离散群体的认同建构
——以新疆乌孜别克族的跨国实践为基线
唐淑娴
“Diaspora”(离散)作为移民研究的一种视角和理论框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物质、信息和资本随着行为个体的流动超越领土疆界和文化疆界,离散移民群体的跨国网络逐渐形成。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宏观理论视域下,跨国离散群体的文化再生产和流动中建构的复杂、多元的族群关系,以及异域社群文化建构为跨国网络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文本。“离散”一词,因描述犹太人受特定历史事件影响被迫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文化现象,而被赋予了一定程度上的宗教意涵,后来逐渐发展到对特殊移民族群,如美籍非裔、巴勒斯坦人和海外华人的相同情景研究中。其中将巴勒斯坦人视作“Diaspora”,是因为在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人为躲避巴以冲突造成的影响辗转移民散居在中东和世界各地的历史镜像。将华人视作“Diaspora”是基于对华人在特殊历史时期向全球移民、散居过程的研究。
其中,对离散群体研究的重心大多关注离散群体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与定居国的社会融合和文化涵化等内容,但最终落在对离散群体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国族认同的讨论中。总结起来,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离散群体在所在国的群体认同中更多强调集体记忆,但大多经历了国民身份的确认或国民意识的重构,并主动做出所在国的国家认同选择。比如,生活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达曼人作为尼泊尔的离散族裔,他们构建“想象的故国”这一集体记忆,但主动加入中国国籍,并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模范遵守法律法规。(1)周建新、杨静:《族群离散与认同重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再如,生活在海外的离散群体——中亚的回族在所在国既保持了文化杂糅的特征,又通过“热爱祖籍国的同时忠于所在国”来表达国家认同。(2)马强:《离散族群与文化杂糅:中亚回族文化反思》,《世界民族》2015年第5期。另外,王赓武梳理了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坐标内,从中原地区走向海洋的部分移民群体,在海外通过“再华化”和“分享精英地位”等方式获得身份认同的路径,参见王赓武:《越洋寻求空间——中国的移民》,《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创刊号)》2009年,第3-50页。另一种观点认为,离散群体中有双重认同和多元认同,有些离散族群由于对祖籍国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甚至发起或参与远距离的跨国政治活动,学界将其称之为“远距离的民族主义”,但只有当离散群体人口中的政治流亡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远距离的民族主义才会出现。(3)梁茂春:《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段颖论述了泰国清迈省北部的原国民党军队及后裔通过调适,完成了从孤军到华人族群的认同建构和历史变迁,他们宣誓效忠泰国、泰皇,同时和台湾保持密切联系,既认同“泰”,也认同“华”。(4)段颖:《异域、孤军、华人族群——泰国北部原国民党军队及其后裔的社会变迁与认同建构》,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新加坡:华裔馆,2007年,第150-172页。
生活在中国的乌孜别克族是中亚的离散群体,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逐渐形成的一个跨国群体。早期的移民体现了更多的“寓居”“流动”和“跨国关联”特征,为了突破生存困境,早期乌孜别克族移民主动加入中国国籍,通过“阿吾勒”游牧组织实现文化嵌入,并以社团组织的制度化表达主动融入主流文化的诉求。本文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原乌孜别克族街道萨拉霍加家族八代人的代际职业传承为个案,结合汉文和维吾尔文两种史料文献记载,以乌孜别克族的跨国实践为基线,讨论乌孜别克族在不同情境下的族群建构和国家认同。
一、离散族裔与跨国网络建构
日本学者羽田亨将包括广大不通外海的河水流经的相当于亚细亚大陆的中央部分,称为中央亚细亚。从纯粹的地理角度来说,西域是大中亚的一部分,它包含苏联学者定义的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和中国新疆地区。由于中亚定居地区的绿洲规模都很小,彼此间被大漠戈壁所隔开,形成了空间意义上的破碎性,继而呈现出一种“源初自由”,它又恰恰符合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5)施展:《枢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3页。由于中亚地区的特殊地理区位和各类庞大的商人群体所从事的跨境商业贸易,造就了中亚自由贸易通道的世界历史命运。
实际上,中亚乌孜别克人的世界性移民活动从14世纪就开始了,移民群体涵盖了参战军官、士兵,逃难的百姓,逐利的商人以及参政的宗教人士等。经过几个世纪的流动迁徙后,逐渐形成辐射东南西北的移民跨国网络。比如在历史上,现在的俄罗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都出现了乌孜别克人寓居的现象,继而形成世界性的同源跨国离散族群,阿富汗甚至成为乌孜别克人口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另外,澳大利亚、土耳其、乌克兰、白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等地也有一定数量的乌孜别克族离散群体,其中中国的乌孜别克族人口大约有1.4万人,其人口分布体现了“大分散、小聚居”特征。
追溯中亚—中国的跨国网络,可能要回溯到公元10世纪喀喇汗王朝时期或更早的时候,因为汉朝时大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第四代国王迦腻色迦在位时期,其疆域已北至花剌子模、西南扩大到恒河上游马土腊,东至新疆塔里木盆地。(6)赵小刚:《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7页。至喀喇汗王朝时期,新疆的喀什噶尔作为王朝的正都,是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7)邹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6页。14世纪初期,成吉思汗的后裔在新疆地区建立的封建游牧政权即“东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东抵哈密与明朝接壤,西至费尔干纳,北抵额尔齐斯河,南到喀喇昆仑山。其统治者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后,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先后征服新疆于阗、龟兹、高昌等三大佛教圣地和东部的吐鲁番、哈密。乌孜别克族向中国大规模迁徙可能与当时欧洲弥漫的瘟疫有关。据称,黑死病大约在1331-1332年发源于亚洲西伯利亚一带的大草原,在中亚爆发后向南传播到中国和印度,向西袭击了金帐汗国的城市,此后很快降临到了主要的商路要塞……似乎是首先通过陆路到达了克里米亚半岛,并随后从热那亚设在黑海沿岸的商业中心,通过海路传播到了意大利。(8)Horrox, Rosemary Herlihy, David Cohn, Samuel K., The Black Death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刊载在《中国乌孜别克族长诗》中的一首“亚迪卡尔”(乌孜别克语,意“纪念”)用长诗的形式也记录和反映了金帐汗国的乌孜别克人在 14-15世纪有组织地迁徙到中国的艰辛过程。
明朝初期,准噶尔部与中亚地区贸易多由“布哈拉”商人通过水路进行贩运,沿着托博尔河口周围出现了“布哈拉”商人的聚居地。当时中亚撒马尔罕作为许多国家的货物集散地,来自不同国家的绢、缎、麝香、钻石、珍珠等都能在撒马尔罕的市场上自由买卖,甚至撒马尔罕的东门也被称为“中国门”。在中国的新疆、青海、北京等地不断出现乌孜别克族的商队,他们将中国的大黄、茶叶、丝绸、瓷器等运往中亚的安集延、浩罕、塔什干等城市及哈萨克、柯尔克孜人的游牧区,再将珠宝、牲口、皮张等运往新疆各商业城市。(9)赵小刚:《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47页。进入18世纪中期,清政府和中亚浩罕汗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乌孜别克人的移民人数和批次达到了史上高潮,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据清史料记载,19世纪20年代“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贸易之人络绎不绝”“安集延商贾亦云集往返,行旅众多”“其(浩罕)人善于商贩,轻家重利,时往他部贩易土物,来喀什噶尔等处易布帛、瓷器、贩运别部逐利……现在新疆等处贸易者,常数十百人往来络绎”。(10)潘志平:《浩罕汗国与西域政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页。20世纪初,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社会运动,又有一批乌孜别克人移民至中国,但是伴随着移民或寓居后的政局变化,中间存在着零散的回流和至少两次大规模回流的情况。
根据约·弗·巴德利的著述,乌孜别克族人选择的陆路交通一般会采用以下两个通道。第一条通道是从阿斯特拉罕出发,途径撒马尔罕、吐鲁番、哈密来到中国,但有时也经过拉萨,一直到达肃州。在肃州收购大黄,然后销往欧洲。第二条通道是从托博尔斯克乘平底船到盐湖,后改行旱路,通过喀尔木克(11)喀尔木克人即卡尔梅克人,是蒙古卫拉特人的后裔,笔者注。和蒙古地区,再走两个礼拜后到达北京。(12)约·弗巴德利:《俄国 ·蒙古 ·中国》(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94-1295页。
目前生活在新疆南北的乌孜别克族其实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18-19世纪被清政府编入回籍的中亚人,另一部分为20世纪30年代俄籍人口返苏后剩余的加入中国国籍的中亚人后裔。当时他们大多以来源国的区域自称,比如“安集延人”“布哈拉人”或“玛尔噶朗人”等。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民族识别后,乌孜别克族被确定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拥有了独立的民族称谓。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乌孜别克族主要在新疆的不同区域间流动,也有个别家庭向中国内地和海外流动。国家统计局官网显示,2015年伊犁市乌孜别克族人口比重较大的都来提巴格街道的乌孜别克人数量较2000年减少了439人,堪称乌孜别克街道的托特克瑞克社区的乌孜别克族只剩下115人。
纵观历史,早期乌孜别克族的跨国网络是以亲属为纽带的,同时通过不同国家的乌孜别克族之间的联系和再移民建立跨国网络,因此,不同国家离散族裔的亲属网络在更大范围产生了。早期的许多乌孜别克族商人娶2~4位妻子,她们大多是塔什干人、玛尔噶朗人、撒马尔罕人或者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也有个别是中国内地的回族女性。20世纪90年代,新疆乌孜别克族的跨国探亲活动非常活跃,2003年,具有美国国籍的乌孜别克人塔伊尔江·纳斯尔江·肉孜哈吉(1921-2012年)出资重建了位于伊宁市的乌孜别克族清真寺的宣礼塔。(13)来源于2015年田野调查的口述资料。可见,乌孜别克族的跨国网络一直通过贸易或亲属纽带在全世界范围内维系和互动。只是,进入21世纪以后,乌孜别克族的跨国网络越来越多受到全球化的商机、求学、就业等因素影响呈现向国际更大范围的再移民趋势。
二、跨国网络解构与秩序再造
乌孜别克族的跨国网络是始于族内血缘和地缘关系,成熟于跨民族跨文化地缘关系的一种时空网络。其早期建构源于亲属间代际传承的商业贸易网络,体现了部分宗族特征。从纵向看,商业贸易是乌孜别克族跨国网络的媒介,载体即为具有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亲属或朋友;从横向看,它连接了家庭类型的代际结构、婚姻状况和亲属关系三要素。它承载的不仅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功能,同时反映了其寓居并成为离散族裔的历史截面,以及跨越地理边界和文化边界过程中的族群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安东尼·吉登斯在阐释结构化理论时,引入了“横向的组合向度”和“纵向的聚合向度”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社会关系中的模式化,包含具体情境中的实践再生产,后者指体现这种模式的虚拟化秩序。无论是短期的旅居者,还是长期的海外移民,不同时空的社会关系会因个体行为动机、社会进化方向及互动情境的变化发生一系列改变,而社会关系的改变不仅影响到个体的“身体定位过程”,同时也会成为文化模式分解或重组的一种关键性因素,从而导致文化特征在重新排列和组合过程中,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结构。(1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页。乌孜别克族的跨国网络形成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结构上的逻辑,如图1所示个案。
为便于表述,本个案中A-H分别代表不同的代际,奇数代表男性,偶数代表女性,比如,第一代男性成员为A-1,两个妻子分别A-2、A-4,以此类推。本个案中,跨国贸易是始于该家族内男性成员的,大多为父子、兄弟或者近姻亲关系。随着贸易类型和范围的扩大,以及跨国流动性增加,乌孜别克族族内通婚和近亲婚姻被解构,跨民族、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增加,亲属关系向跨地域、跨文化的更广范围拓展,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出现多样化趋势。纳曼干系的谱系中,纵向的商业贸易职业代际传承达五代,除了父子联合、兄弟联合外,近姻亲关系也在该个案中表现突出,比如哈姆什·哈里派(1817-1900年)是C-3的岳丈,曾出资参与伊宁市乌孜别克街道的早期建设,C-3的跨国贸易也主要依赖他的儿子。关于C-3的“家族式”跨国贸易中的血缘联合,纳曼干系第六代后裔(F-5)回忆如下。
萨拉霍加(A-1)在中国新疆的尼勒克购买的牧场,并拥有难以计数的马、牛、羊,还有伊犁河附近购买了好几个果园,以及好几个大库房(现伊犁市卫校背面)。伊玛目霍加(C-3)(1859-1936年),是萨拉霍加的女儿的儿子,他于1881年和儿子玉山霍加用5个骆驼,装着日用品和布料来到新疆伊犁,与生活在塔什干的二儿子阿肉普霍加一起联手做贸易,即将新疆伊犁收购的畜产品交给阿肉普霍加,阿肉普霍加把畜产品转卖给俄国的大商人后,从俄国购买日用品再运到伊犁出售。将畜产品3%的利润作为税金上交地方政府。他还在新疆修建了土木结构清真寺。1933年和“费尔干纳”公司联合,在特克斯河到昆仑山的“卡布奇海”的河面上修筑了一座桥,为当地牧民的出行提供了便利。(15)受访人:热黑木·艾合买提江;访谈时间:2015年5月27日;访谈地点:伊宁市果园街6号;使用语言:汉语。
可见,从第三代开始,宗族式贸易模式的跨国性特征逐渐消解,个体成员的社会身份出现转型,职业代际结构发生改变。至第五代,其生产方式的宗族特征已经不复存在,大多数个体商人开始选择公私合营,或进入国家政府部门工作,第六代以后,宗族贸易逐渐淡出乌孜别克族的生活。此外,该家族内成员流动性几乎可以作为观察当前新疆乌孜别克族人口流动性的缩影,在该家族目前在世的所有成员中,从第四代开始有34人迁出中国,一部分人回归中亚,另一部分人向其他国家再移民,目前主要生活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等国。其余18人因婚嫁、求学或就业等因素迁出原居住地。随着人口流动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该家族的家庭类型也被解组,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家庭类型逐渐转变为直系家庭或者核心家庭。
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流通和积累加速了社会生态系统之间能量的流通以及文化脉冲和信息流通的速度,中国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顶层设计,为个体或族群的发展愿景和交往准则提供了多种现实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具有宗族特征的贸易形式开始局部重组,个案中塔什干系的第五代后裔E-11,男,1975年生,他的创业经历了父子联合、兄弟联合向更广的社会关系推演的过程。目前他的合伙人中既有汉族也有回族,既有新疆人也有内地人。
我从7岁开始便和两个哥哥一起做生意了,17岁时开始在乌鲁木齐做生意,等生意好起来后,便和哥哥们分开经营了。后来,和汉族人做生意的机会多了,我逐渐学会了用汉语交流。 2002年我在乌鲁木齐注册成立了“一帮达”彩印公司,我的合伙人中有新疆人也有内地人,有汉族也有回族,比如2名分别来自湖南和西安的汉族人,另外的2名是来自西安和乌鲁木齐的回族人。公司主营糖纸包装印制,销往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市场。除此之外,我还兼作手机配件生意,主要发往中国内地。两个哥哥也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和伊宁市有了自己的生意。(16)受访人:艾克买依力霍加;访谈时间:2015年6月8日;访谈地点:伊宁市前进街53号;使用语言:汉语。
奇台县、木垒县从事牧业的乌孜别克族则通过交换和赎买等手段拥有了自己的牲畜和牧场,逐渐融入到哈萨克族的游牧组织,并产生一种嵌入式的社会组织——“阿吾勒”,在中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其个体职业身份从商人转变为牧人,传统的“阿吾勒”被拆分在不同的牧业队,在经历了地方社会的双向认同和文化涵化后走向了“土著化”和“合法化”的过程。(17)解志伟:《嵌入、生成与解组——乌孜别克族游牧组织阿吾勒变迁的人类学解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无疑,乌孜别克族经历了脱离母体社会进行了落地生根的地方化进程。从目前外在的文化表征看,中国乌孜别克族的风俗礼仪和交往规范已经与其混居的主要民族高度趋同。比如城镇居民的文化大多与维吾尔族文化相似,牧区居民则与哈萨克族文化趋同。可见,这个过程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族群空间的想象与现实
李明欢在解读当代欧洲华人社团时总结,对于生活在异族人群中的跨境移民而言,组建社团是相关人员自觉不自觉地尝试关系纽带制度化的实践。(18)李明欢:《欧洲华人华侨史》,北京: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672页。诚然,乌孜别克族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也成立了类似的社团。迄今,在新疆曾出现过两个乌孜别克族社团,但实质上第二个社团是第一个社团的延续。第一个社团为1938年成立的乌鲁木齐文化建设联合会,它是新疆“四·一二”事件后,盛世才鼓励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以获取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及当地进步人士支持的直接产物。该社团成立后的运作表明,当时被法律正式承认的中亚离散族群,准备在动荡的政治生活中检验其新的身份认同。当时鼓励多元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向中国展示忠诚的路径。他们开始以社团为依托,积极弘扬乌孜别克族的文学和歌舞艺术、培养了一批乌孜别克族艺人,比如歌手米日吾买尔、阿布杜力·艾尼再木、米日阿尼亚提等,舞蹈演员艾尼帕、赛里麦、热尔萨、木合泰百尔等。更重要的是,为了响应抗日战争,乌孜别克族剧作家许库尔·亚里坤创作的舞台剧《上海之夜》《尼来甫的牺牲》和《沙尔特兰》被搬上了舞台,为乌孜别克族融入主流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称,后来许库尔·亚里坤接受了中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的建议,在《上海之夜》中增加了有阶级指向的汉族家庭的“奶妈”形象,使得作品更加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除此之外,该社团还创办了“反对帝国主义扫盲学校”,开设语言课程;还向乌孜别克族群体内部发起了捐款捐物活动,以支持当时的革命。许多乌孜别克族妇女捐献了自己的手镯、戒指、珍珠等贵重首饰。也是在这一时期,乌孜别克族街道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发展,现坐落在伊宁市托特科瑞克社区的伊宁市第五中学的前身为乌孜别克族学校,被称为当时的“模范学校”。可见,这一过程不仅带动了乌孜别克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深刻激发了新的法律意义上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意识。
抗日战争和三区革命之后,乌孜别克族的血缘和宗族贸易进一步解组,乌孜别克族文化社团的相关活动进入休眠状态。社团组建者之一艾尼瓦尔·汗巴巴参与了土地改革工作和新疆南北疆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建设工作,与同族的巴哈尔、马合木提江·卡斯木等人组织团队,开展了维吾尔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的翻译工作,艾尼瓦尔·汗巴巴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
三区革命期间,我从事教育工作,直到1946年7月与国民党方面签订合约。当时,赛福鼎·艾则孜负责新疆教育厅的工作,我负责教育厅的学校部、干部部、教师培训等工作。因为要消除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腐朽教育,展开新式教育制度,所以不仅需要组建新的机构,制定教育方针、程序、规章制度,还要培训老师、修理学校的教学楼和设施,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很繁忙。(1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编:《新疆文史资料(维吾尔文版)》(第40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3页。
20世纪80年代后期,乌孜别克族的第二个社团“乌孜别克文化研究委员会”以新的宗旨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下。该社团由时任新疆大学副校长的艾尼瓦尔·汗巴巴牵头,于1986年先期组建了“乌孜别克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委员会预备会”,1988年5月修改社团名称为“乌孜别克语言文字委员会”, 1993年召开了乌孜别克族代表大会,将社团名称正式确定为“乌孜别克文化研究委员会”,同时确立了相关规则和章程以及1988-1990年度的工作计划。研究会下设常委、理事和委员,其中乌鲁木齐的常委29名,其余区(县市)的常委14名。委员的人数至2015年已经发展到200人左右,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昌吉、伊犁、奇台、吉木萨尔、大南沟、喀什、莎车、叶城等地。委员中除了退休干部外,还有大、中、小学教师,党政军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民族企业家和个体户。
可见,乌孜别克族通过对唯一社团的制度化努力,维持和壮大队伍组成,通过一直以来与官方的正面互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乌孜别克族文化研究会成为离散在新疆各市镇的乌孜别克族活动的公共组织和城市的族群活动空间。在一年一度的奴鲁孜节上聚会、商议相关事宜,安排翻译文学作品以及配合政府做相应的宣传,并通过歌舞表演等形式进行庆祝。一方面,该社团的组织和运作体现出了新疆乌孜别克族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与能动的调适;另一方面将离散在中国各地的乌孜别克族带入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族群生境与想象的空间。
四、情景式身份选择与认同建构
虽然在大多数人眼中,新疆乌孜别克族往往被视为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的同类群体,因为从其体貌特征和风俗礼仪中,都很难辨别出具体的差异。但是,就乌孜别克族自身而言,其差异因其根基性情感的不同而体现。根基性的情感除了“因生长在某一社会中而获得的语言、宗教、风俗与宣称的血统”(20)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p. 56.外,也包括“社会人群经常集体选择、活化并强化特定的社会记忆。”(2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5页。在上述的个案中,第一代移民和第七代移民所体现的“隐性的源文化、源意识和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22)邹威华:《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以斯图亚特·霍尔为研究对象》,《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明显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它反应了不同代际离散族裔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着离散族裔在异文化中能动适应的过程和结果。因为族群特征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现象,族群的形成、维系及改变与社会地位及环境的变更、政治权利与经济资源的分配竞争策略是息息相关的。
在上述个案中,讲述人F-5,74岁,他为了寻根,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从塔什干、阿拉木图、伊犁州市等地搜集祖辈的照片和相关口述史。2014年,他花了4000元钱请专业人士拍摄了祖辈七代人传承的视频,并配有解说,视频时长大约1个小时,首先呈现了其太爷爷C-3和子嗣的照片,然后顺着代际一一开始讲解他们的生平事迹,每一个事迹的讲解中配有可以证明历史事件的建筑物照片和采访的镜头。从F-5的讲述中可以看到,其祖辈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的主要社会身份是商人,但第三代中有一位名叫“伊玛目霍加”。“伊玛目”系阿拉伯语词汇,兼有“众人礼拜的引导者”之意。为了强调宗族的显赫身份,讲述人特意使用了代表宗族身份的符码——“霍加”。并特意强调它“不仅指穆圣后裔,也有掌管财政之意”。(23)唐淑娴、苟晓霞:《解构与建构:跨国民族文化适应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以新疆乌孜别克族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在他的叙述中,有意在所有男性成员的名字后加上了“霍加”称谓。
然而,“霍加”称号在乌孜别克族适应新疆本土文化过程中早已丢失,命名方式也被新疆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的命名礼俗所替代。“霍加”封号的宗教身份显然在乌孜别克族的集体记忆中被淡化。相比之下,似乎“掌管财政”之意更值得去记忆。诸如“逃难的军士”“躲避黑死病的难民”等相关的记忆,也表现为“结构性失忆”或“选择性遗忘”。个案中第七代开始,3/4的男性成员的职业是教师,没有一人从事商贸活动。他们认为“教师”是有文化的象征,在当今这个时代仍然是被公众悦纳的社会角色之一。伊犁、奇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莎车、喀什、叶城等地的乌孜别克族,同样表示对“有文化”这一身份标签的接纳和认同。奇台县的一名乌孜别克族大叔,甚至将自己收藏的几页关于乌孜别克族的文化构成的资料复印后“郑重地”送给笔者。显然,“较高的文化水平”是乌孜别克族整体选择性记忆的结果。这个内容来自《乌孜别克族文化志》,原文如下。
乌孜别克族是我国各民族中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之一,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每千人中的文化人口为742.9,位居第7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98.1人,其中,大中专学历的比例为9.34%,在校就读的学生占22.54%。(24)何星亮:《中华文化通志——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俄罗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0-341页。其中的比例是笔者根据文中罗列的“1990年乌孜别克族人口的文化构成统计表”和“1990年乌孜别克族在校学生的构成统计表”换算的结果。
另外,讲述人F-5还对收录在《新疆文史资料》第三辑的“《援助公司》及其十件大事”中的“赛提瓦尔得巴依”的族属问题提出质疑。他称“赛提瓦尔得巴依”是名副其实的“安集延人”,因为他的弟弟是F-5的姐夫,而《新疆文史资料》中只用“富商”指称,忽略了他的族属和乌孜别克族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他求证了该公司的历史事迹,“援助学校”最早的名称是“帕尔尕那公司”,而“帕尔尕那”是维吾尔语对“费尔干纳”一词的音译。此外,门楣上悬挂了由“帕夏霍加”题写的维、汉、俄三种文字的牌匾,“帕夏霍加”是当时有名的乌孜别克族富商。
可见,乌孜别克族的认同建构是随着情景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的,随着宗族式生产方式的解构和代际职业转型以及频繁的人口流动,早期呈现的“安集延”风格的街道和村落早已被多元文化所稀释,在极具竞争的市场经济和全国统一的教育体制下,具有大分散、小聚居、强流动的乌孜别克族群体的离散特征所蕴含的竞争劣势逐渐显现。除了少量掌握社会优势资源的乌孜别克族将孩子送往国外或选择再移民外,部分乌孜别克族一改过去几十年重视“纯正血统”的传统,通过变更民族称谓克服面临的困境。在F-5所在的社区,受访的36户乌孜别克族家庭中,80%以上的家庭中都有体制内工作者。纯商人家庭或纯体制内职业的家庭只占到1%~2%。在关于该问题的统计中,“身份证上的民族称谓”是乌孜别克族的有93人,维吾尔族的有8人,哈萨克族的有2人(见下表)。他们认为,在社会竞争中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占有比较优势。

表1 身份证上的民族称谓调查表
实际上,乌孜别克族在不同情境中的认同建构本身包含了“由变化中的国家和资本的逻辑所激发、促成和调节所表现出来的横向的、相互的和直线的当代行为与想象。”(25)尹晓煌、何成洲:《全球化与跨国民族主义经典文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特定语境下的时代特征,因为它的建构和解构无不与制度和市场的变迁与资本的流动息息相关。具体来说,其社会身份经历了从以地域指称的商人,比如“布哈拉人”“安集延人”等,到拥有“回籍”“中国国籍”到确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过程,其职业身份也从世代传承的商人逐渐向多元职业身份转变,在不同的情景中建构认同并进行自我身份定位,也就是说,它是经过与国家资本关系深刻互动后,产生一系列“合理性调适”的结果。
五、结论和反思
纵观乌孜别克族的跨国实践,其族群认同和身份建构始终受到综合因素的影响,且贯穿了脱离母体后在中国落地生根并“本土化”的全过程。当族内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跨国网络遭解构后,乌孜别克族通过表达忠诚在更广的范围内获得自我身份的建构和族群生存空间。一方面,生活在牧区的乌孜别克族借助“阿吾勒”这一游牧组织嵌入到新疆的哈萨克族中,并通过对木垒县乌孜别克族乡的文化重建等方式,表达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以艾尼瓦尔汗·巴巴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及其后裔通过创作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作品、对社团组织的制度化以及翻译《毛泽东选集》等形式表达国家认同,完成了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并在新的多元文化环境中实现了情景化的身份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乌孜别克族的认同建构和国家认同经历了不同情境中被定义、被塑造的过程,且大多数是随着生计转型得以确立的,这也是本文以田野调查的资料为基础,以家族代际职业传承为切入点,讨论离散群体在不同情境中认同建构和国家认同形成过程的一个主要原因。总体来说,乌孜别克族的跨国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离散在中国的乌孜别克族的认同既体现了离散群体的普遍特征,也保留了其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生计转型是乌孜别克族认同建构的核心要素。乌孜别克族的族名最早来源于术赤兀鲁斯汗室的乌孜别克汗,在《元史》中他被称为 “月即别”或“月祖伯”,他是成吉思汗的六世孙、金帐汗国的第九代大汗。乌孜别克族正是在“月即别”建立的金帐汗国的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其生活的场域围绕着中央亚细亚的广阔土地发生着变化,但是起初都是在阿姆河和锡尔河等流域附近水草丰美的地方进行游牧生产。自从南下迁入河中地区以后,与当地土著部落的融合加速了走向了定居的步伐,完成了第一次生计转型。随着中西交通线上商贸活动的兴盛,乌兹别克族开始向第二次生计方式转型,即逐渐向商业贸易为主的经济方式转型,尤其是浩罕汗国与清政府建交后,这种贸易往来几乎成了乌孜别克的一个文化符号。早期离散在中国的乌孜别克族群体中游牧群体的生产方式“阿吾勒”,在民国时期因现代地方行政机构在哈萨克游牧区的设置而受到了生存空间上的挤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些全新的地方组织形式及其话语体系渗透到乌孜别克族的游牧社会,阿吾勒、阿塔等传统组织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已经解体。(26)解志伟:《游牧、流动与变迁——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的人类学考察》,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228页。以血缘为基础的商业代际传承也逐渐被新的生计方式所取代。因此,生计方式的转型促成了乌孜别克族认同情景的改变,认同情景的改变又促使他们寻找更大的族群空间,选择主动融入生境便成为认同建构的普遍路径。
其二,血缘为纽带的跨国网络消解促进了国家认同的进程。以中国乌孜别克族为视角观察整个乌孜别克族的跨国网络时,不难发现,中国乌孜别克族体现了离散群体的概念所能涵盖的大多数内涵和外延,自经历了20世纪40-60年代大规模俄籍人口回流事件后,中国的乌孜别克族人口分布特征中的“大分散,小聚居”体现了新特征,即大分散的范围更大,小聚居的范围更小,新疆许多以乌孜别克族命名的街道早已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散居特征更具代表性。另外,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属商贸网络也被新的就业、务工、求学的移民方式所代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的这段时期,乌孜别克族与其迁出国之间的联系几乎处于中断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90年代虽然是乌孜别克族海外关系的重新弥合和维系的阶段,但是,除了个别从事跨国贸易的乌孜别克族与海外亲属的往来中掺杂着探亲和合作贸易的事项外,大多数乌孜别克族的海外关系维系仅仅存留在某些代际之间的探亲和互访,子孙后代之间的往来逐渐减少。可见,乌孜别克族精英阶层通过社团组织的制度化融入主流文化的智慧,是做出国家认同选择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