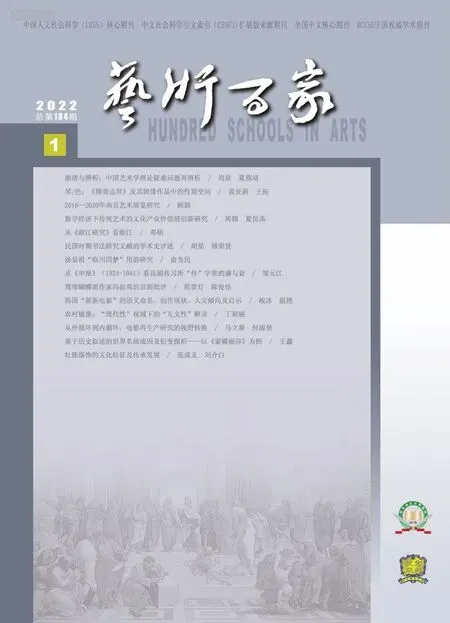当代灾难片的声音美学创作论析*
峻 冰
(四川大学 影视艺术系,四川 成都 610064)
一、语义与声音元素
(一)语义与类属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类型化进程的加速,以前国内很少摄制的灾难片(Disaster Film)数量不断增加,并展现出不凡的视听审美魅力。灾难片肇始于20世纪初期,默片时期的英国电影《火灾》(詹姆斯·威廉逊,1902)、美国电影《一个美国消防员的生活》(埃德温·鲍特,1903)便可算是最早的以灾难为题材的故事片。“这种电影类型在三十年代十分流行,如《旧金山》(SanFrancisco,1936)和《在古老的芝加哥城》(InOldChicago,1938)。”[1]71有声电影时期,随着声音技术的革新拓进,题材多样、以灾难为背景的电影逐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成为好莱坞诸多电影类型中的一种。一如弗兰克·毕佛所说,“以《飞机场》(Airport,1970)和《波塞冬历险记》(ThePoseidonAdventur,1972)为开端,灾难片在七十年代再次风行起来”[1]71。也正因如此,灾难片作为一个描述一种特定电影类型的专有名词日渐进入众多研究者的视野,有学者指出“灾难片……这一词语是在70年代开始盛行的”[2]333。
灾难片以对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事件为题材,惊心动魄的情节和逼真的场景氛围设计贯穿其中。由于灾难题材不一而足,我们把灾难片分为四类:(1)自然灾难片,即展现自然界对人类造成灾难的电影,可以是对本来已有的灾难(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的再现,也可以是对将来可能发生或一定会发生的灾难(天塌地陷、世界末日等)的想象,如《泰坦尼克号》(詹姆斯·卡梅隆,1997)、《日本沉没》(樋口真嗣,2006)、《2012世界末日》(罗兰·艾默里奇,2009)、《唐山大地震》(冯小刚,2010)、《海啸奇迹》(胡安·安东尼奥·巴亚纳,2012)、《太平轮》(上、下,吴宇森,2014、2015)等;(2)社会灾难片,即描写人为破坏导致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突变的灾难题材影片,如《新干线大爆炸》(佐藤纯弥,1975)、《卡桑德拉大桥》(乔治·克斯马图斯,1976)、《后天》(罗兰·艾默里奇,2004)、《海云台》(尹齐均,2009)、《釜山行》(延相昊,2016)等;(3)怪物灾难片,即描述因基因突变等原因而产生的具有强大攻击力的怪物对人和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的电影(其中大多融合了一定的科幻元素),如《大白鲨》(斯皮尔伯格,1975)、《哥斯拉怪兽》(罗兰·艾默里奇,1998)、《汉江怪物》(奉俊昊,2007)、《环太平洋》(吉尔莫·德尔·托罗,2013)等;(4)科幻灾难片,即讲述失去控制的科学技术或科学幻想给人和社会带来重大灾难的电影,如《恐怖地带》(沃尔夫冈·彼得森,1995)、《生化危机》(保罗·安德森,2002)、《我是传奇》(弗朗西斯·劳伦斯,2007)、《神秘代码》(亚历克斯·普罗亚斯,2009)等。
作为好莱坞的一种电影类型,灾难片真正成熟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显然,灾难片是类型电影多样化发展的产物,它明显受到恐怖片、惊险片、科幻片等类型元素的影响。但在严格意义上,灾难片则是指专门借助声、光、色等现代科技来展现自然灾难的电影,因为在词典学的范畴,“灾难”一词意指自然力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损害。其他诸如战争灾难可在战争电影中研究,科幻灾难可在科幻片中研究。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描述自然界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的灾难片。
(二)声音元素
1927年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王》(阿兰·克劳斯兰德)的问世,宣告了影像与声音共存时代的来临。其实,之于电影,“单诉之于眼睛,耳朵将会不耐烦;而单诉之于耳朵,眼睛也会不耐烦。必须好好地利用这些不耐烦”[3]28。然而,早期电影因不懂声音技术而滥用声音,故也没有实现它应有的审美效果。一如安德烈·巴赞在论及声音技术的发展与人类自然性要求之间的关系时所说,“支配着电影发明的神话就是实现隐隐约约地左右着从照相术到留声机的发明、左右着出现于十九世纪的一切机械复现现实的技术的神话。这是完整的写实主义的神话,这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影像上不再出现艺术家随意处理的痕迹,影像也不再受时间的不可逆性的影响。如果说,电影在自己的摇篮时期还没有未来‘完整电影’的一切特征,这也是出于无奈,只因为它的守护女神在技术上还力不从心”[4]21。巴拉兹·贝拉表示:“我们的反感(有声片当中让我们感到像是一堆滑稽可笑、不堪逼视的赝品——笔者注)代表一种迫不及待的要求,而不是反对……有声电影不应当仅仅给无声电影添些声音,使之更加逼真,它应当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表现现实生活……在艺术里,只有当它(声音——笔者注)发现并展示了我们的眼睛或耳朵迄未看到或听到过的某些东西时,这才算是一桩壮举。”[5]207显见,从声音参与电影这一门新艺术的那一刻起,它就沿着更为真实也即“现实主义”的创作美学道路往前迈进。
灾难片之所以在电影史上出现得较晚,是因为欠发达的声音技术难以配合画面在银幕上展现那些可怕的灾难(如地震、火山爆发、飓风、海啸、空难、海难等),而“节奏、旋律、和声和乐器能够相当大地影响观众的情绪反应”[6]315。近些年来,随着声音数字技术的发展、成熟,不少灾难奇观仰仗声音元素的良好表现而得以在银幕上呈现。在某种意义上,对声音更为真实、更为细腻、更为全面的模拟,即创造性地发展出更具有质感、原态感、情理性的声音,成为声音美学创作的方向。
诚然,声音数字技术的发展、革新成果并非为灾难片所独享,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较晚出现的一种电影类型,灾难片比其他类型电影更需要声音数字技术的支持。也正因创作主体在多个声音范畴(尤其是音乐和音响)中的出色表现,灾难片才取得了今天的声音美学成就。
二、声音创作及美学效果
(一)叙事
毋庸置疑,对电影这门叙事艺术(同时也是视觉艺术、综合艺术、大众艺术)[7]126来说,叙事主要是由运动画面来完成的。但进步了的声音技术也增强了电影的叙事效果,有时甚至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尤其是在戏剧性和深度感方面)。当然,灾难片亦不例外。
叙事者缓慢、滞重、伤感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对灾难片的情节和氛围起到暗示和强调的作用。在《泰坦尼克号》中,片首老年萝丝对那一号称“不沉之船”的巨轮沉没前后深情而富有沧桑感的讲述(在舒缓的稍带感伤的钢琴曲的伴奏下)——“已经八十四年了,我仿佛还闻得到油漆的味道。船上的瓷器都是新的,床单也没人用过。泰坦尼克号被称为‘梦幻之船’,名副其实,果然名副其实”——显然暗示了已经发生的海难既可怕,又那么令人难以接受(这无疑契合叙事目的,并激起了观影者对事件本来面目的心理期待)。在《太平轮》(下)中,女主人公周蕴芬(宋慧乔饰)在得知丈夫罹难后那一段对女人命运的感伤独白(在低沉幽怨的管弦乐的伴奏下)——“这就是我的家!这个时代的女人,为了维持一个家,似乎注定要……辗转奔逃。你是,你是,我母亲是,我认为我也是。义方曾跟我说,我就是他的家。只要我在,他永远找得到路回家”——显然也较为恰当地暗示了已经发生以及仍然可能发生的可怕灾难(当然,这既包括自然灾难,又包括人为因素)。在这一意义上,马赛尔·马尔丹所言“画外音又为电影开拓了心灵深处的丰富领域,使许多最隐秘的思想外在化”[8]90,于今仍有启示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声音是画面的辅助性元素。“只有以视觉效果为前提,有声电影才能实践其作为媒介的精神。”[9]103然而,特殊的声效演变往往能够使画面的灾难性效果得以加强。在《泰坦尼克号》的结尾部分,轮船撞击冰山(配以水流撞击船体的破裂声、惊慌失措的人们四处奔跑的呼喊声以及急促的小提琴演奏声)、人们决定弃船后,于嘈杂的人声氛围中,舒缓低沉的小提琴演奏向急促的交响乐陡转,便强化了即将到来的沉船灾难的可怕性——显然,这是具有叙事功能的。
借助缓慢、抒情的音乐逆向暗示出剧中人物不便言说的令人难以承受的灾难是灾难片的惯用技巧,它不仅能有效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人物情感呈现和人物性格塑造方面也能起到较大的作用。一如马赛尔·马尔丹所说,“音乐也可以用来有力地加强某段时间或某场戏的戏剧作用和深度,使前者具有一种只有音乐才能产生的抒情内容”[8]102。《太平轮》(上)中,男主人公严泽坤(金城武饰)作为日本军医被师长雷义方(黄晓明饰)带领的中国军队俘虏,他在目睹了战争对生命的大规模屠戮后仰望苍天、感伤下跪,这时在高亢感伤的管弦乐伴奏下响起的舒缓、伤感的女高音吟唱,也暗示了严泽坤对自我、他人悲惨命运的绝望——命运不可把握,也不可言说。主人公的沉默(当然这也是一种声音表现,“在声音的领域里,静音拥有一种新的表达功能”[6]308,“如果用得巧妙,悄无声息可以比金鼓齐鸣更有感染力”[10]109),有力地渲染了当时的紧张气氛。在《太平轮》(下)中,造访海边别墅的严泽坤进屋看到美丽祥和的周蕴芬正在弹奏怀旧抒情的钢琴曲,便回忆起与女友雅子(长泽雅美饰)共度的美好时光(周蕴芬弹琴的画面也化为雅子在芒草地上弹奏钢琴的画面)。由舒缓而富有真挚情感的钢琴曲所烘托的现实场景与回忆场景,无疑也暗示出那两场刚刚过去的不仅仅指向生命个体的灾难(战争导致了周蕴芬丈夫的死亡与严泽坤女友的投海自杀)显然是不便言说的,也是现实中的他们所难以承受的。显然,此处的沉默已“升格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表现,作为死亡、缺席、危险、不安或孤独的象征,沉默能发挥巨大的戏剧作用”[8]90。
(二)环境
在某种程度上,之于电影的环境氛围,声音尤其是音乐加诸观众的感染力要比运动画面更快速且有效;自然,其对形成影片整体节奏、风格、韵味等,也至关重要。其实,如L.R.波布克所说,“从为无声片伴奏而在蹩脚钢琴上敲出第一个音符时起,音乐就一直是电影影像的一个忠实伴侣。音乐大半是被用来直接烘托银幕动作,提供情调和速度”[10]103。马赛尔·马尔丹则明确指出:“音乐应当细致入微地去参与创造作品在美学与戏剧方面的总格调(当音乐愈是让观众去感受,而不是听到时,它的作用就愈成功、愈有效果)。”[8]102
灾难片的音乐风格往往是缓慢、低沉、伤感的,显然,这是对片中灾难环境氛围的暗示与衬托。在《太平轮》(下)中,严泽坤念女朋友雅子留给自己的日记时,清脆而稍显刺耳的风铃声与低沉幽怨的管弦乐,则暗示出经历苦难的雅子投海自杀的灾难;之后严泽坤拼读雅子的来信时,感伤幽怨的管弦乐也烘托出令人伤感的悲剧氛围;而撞船事故发生后,影片一直回响着的低沉哀伤的交响乐,在于真(章子怡饰)、佟大庆(佟大为饰)落水时急转,一度显得高亢强烈,而后又舒缓感伤,这无疑是对悲剧性海难的直接衬托;在落入海中且被歹徒刺伤的严泽坤即将死去时,高亢感伤的女高音吟唱也把影片的悲剧氛围推向高潮。在本质意义上,正如埃·苏里奥在《论电影世界》中所说,“电影世界始终拥有一种音乐,这种音乐从气氛上替电影世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幅度,它不断地丰富电影世界,解释这个世界,有时还校正甚至指挥它。总之,它的结构同延续时间很相近”[8]97。
灾难片在模拟环境时,往往需要用超载的音响效果(多音轨立体声效)对灾难环境氛围予以强化、烘托。唯有如此,才能使坐在舒适的电影院里的观影主体(也是手脚能力受限只有视觉能力在起作用的,很容易陷入混淆现实与想象的镜式情境的做梦主体[11]494—495)体会到灾难的恐怖,并得到某种启示。《海啸奇迹》片首对海啸突袭的声音效果(鸟群惊飞的啼鸣声,小动物的尖叫声,波涛汹涌、滚滚袭来的洪水的轰鸣声,房舍玻璃的脆裂声相交织)的模拟,《唐山大地震》片首对地震突然发生的声音效果(轰隆隆的房屋破裂声,电杆、吊车、大楼哗啦啦的倒塌声,房屋玻璃的碎裂声,电火花的嗞嗞声,水管的破裂声相混合)的模拟,《泰坦尼克号》片尾对轮船断裂、倾覆时的声音效果(轰隆隆的水流撞击声,桅杆、舱房的倒塌声,玻璃的破裂声,电火花的嗞嗞声,水管、气管的破裂声,碗盘的碎裂声相混杂)的模拟,《太平轮》(下)片尾对台风突袭周蕴芬所住的海边房屋的声音效果(屋顶窗户的破裂声与急促的风声、雨声相交织)的模拟,《2012世界末日》对世界末日来临时的声音效果(地面的陷裂声,房屋、树木倒塌的声音,高速公路垮塌的声音,整个城市落入洪水之中的声音,洪水拍岸的声音,车辆互相撞击的声音等相混杂)的模拟,对于影院的有限空间和观众的听觉接受能力来说明显是超载的。而此时影片又多配以感伤幽怨的管弦乐,夹杂着四散奔逃的人们撕心裂肺的呐喊声、哭叫声等,这无疑又使声音的感染效果得到加强。
(三)人物
巴拉兹·贝拉认为“一切样式的影片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电影是一种有声的演出,是活动的画面,也是一种当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动作”[5]265。诚然,人物在特定环境中有缘由的行动构成了故事情节,因而对叙事电影来说,人物的行为动作与言语动作表现显然是重点着墨之处。而之于非常注重灾难性情节叙述的灾难片,对人物言行的展示,则显得尤为重要。
灾难片往往对人们遭遇灾难时发出的惊恐哭叫声进行逼真展示。在《唐山大地震》《泰坦尼克号》《海啸奇迹》《2012世界末日》等影片中,当地震、轮船倾覆、海啸等灾难来临时,伴随着低沉幽怨的背景音乐,人们哭爹喊娘、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惊呼声、惨叫声、哭喊声(童声、女声较多——这也契合妇女、儿童容易受到伤害的情理逻辑,当然,也易激起观众的同情心,强化接受效果)不绝于耳。很明显,对人声的着力刻画强力烘托了灾难氛围;同时,借助不同的人物声音表现,影片也恰当地塑造了不同的人物性格。
有时,灾难片也用与恶劣的灾难效果相反的音乐效果去抚慰显梦中的遇难人们和在似梦情境中经历灾难的观影者的心灵,同时巧妙地刻画人物形象或暗示人物性格,因为“声音和画面的对比是极其强烈的,从而又加强了这两个元素的力量”[10]99。在谈及音响问题时,马赛尔·马尔丹曾说:“音响显然并不永远是画面的简单补充,我们可以通过蒙太奇手法对音响进行最大胆的处理,尤其是使用普多夫金极为重视的‘音画对立’。”[8]92—93音响如此,音乐亦然,创作者可以大胆使用“音画对立”,这已经被证实,也必将继续得到印证。在那部风靡全球(2D和3D版在全球共赢得高达18亿美金的票房)的影片《泰坦尼克号》中,面对慌乱奔跑的人群,三位视死如归的乐师平静演奏出的悠扬的小提琴声,显然起到了抚慰即将死难之人(走进驾驶舱的船长、沉默注视着泰坦尼克号竣工标牌的轮船设计师、相偎躺在包厢床上的老年夫妇、给孩子喂了安眠药的妈妈)的心灵的作用,同时,优雅动听的琴声也彰显了演奏者的高尚品格和浓郁的人道情怀。当然,琴师们处乱不惊的演奏,无疑也反衬出面对灾难慌不择路、不择手段、损人利己者的丑陋内心。
(四)画外空间
“由于背景有了音响,画面就恢复了它真正的现实主义价值,声带重现了许多主观效果……”[8]89“对音响的直接使用……通常是旨在使观众相信自然环境的真实性”,而且“音响效果声带也能用来延伸可见影像的范围”。[10]99—100当然,声音不仅能与画面同步,直接提升运动画面的视觉效果,而且能补充、完善画面的情节叙述,从而使影片的视听效果达至佳境。
灾难片对灾难突发时复杂的声音状态的数字化仿真(多是以剧中人物的主观镜头来展现,即剧中人物和观众都能听到,声源在画外),多能较为逼真地暗示出画外的灾难性场景。《唐山大地震》《海啸奇迹》等片中,被突发的灾难瞬间惊呆了的人们即时所听到的各种声音,都真实生动地暗示出画外空间的可怕状态。显然,这种超载的声音处理,一方面能够非常讨巧(既能减少拍摄难度,又能节约拍摄成本)地让剧中人物(其实是让观众)感受到灾难的惨烈恐怖,达到叙事和抒情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让观影者透过剧中人物面对突发灾难时的各种直观表现,把握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品质风貌,从而有效达成与导演的双向交流。
另外,灾难片中令人惊奇的声音效果(当然它是被特写镜头所注视着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被主观化了的),往往有效地暗示出灾难的即将来临。《海啸奇迹》中水下低沉的闷响声、蜥蜴等小动物的惊叫声、棕榈树树梢莫名的断裂声等,都对海啸的即将来临进行了恰当预示和叙事铺垫;《2012世界末日》中地面莫名其妙的陷裂声、墙壁突然晃动破裂的噼啪声、汽车无缘无故的报警声、成群鸽子惊慌高飞的悲鸣声、火山突然爆发的轰隆声、猪狗等动物的狂叫声等,也对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作了不无幻想色彩但又合乎情理逻辑的成功预示。
(五)声音特技展现
毋庸置疑,电影运动画面对叙事(尤其是奇观化叙事)的日益有效传达,也得益于声音科技(特别是数字化的声音特技)在当代的逐渐进步。这无疑也充分印证了马赛尔·马尔丹不无预见性的论述,他认为“音响增加了画面的逼真程度,画面的可信性(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而且也是美学方面的)几乎是大幅度地增长:观众事实上是重新找到了感觉的多面性,恢复了所有感觉印象的相互渗透性,正是这一切使我们看到了现实世界不可割裂的实际表现”[8]89。这一点,在灾难片中得到充分体现。可以说,声音特技的发展进步,使灾难片的叙事效果得到大大提升,也使其叙事场域得到无限扩展,还必将继续推进灾难片的创新性发展。
在灾难片中,声音科技的发展使数字化声音能够较为成功地模拟灾难(地震、火山、海啸、台风等)爆发时的复杂声响效果,《太平轮》(下)、《唐山大地震》、《2012世界末日》、《海啸奇迹》等影片已经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在灾难片中,日益精进的数字化声音对现实当中难以把握的或不可知的伴随灾难发生的特殊声响效果的模拟,能够达到出人意料或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泰坦尼克号》对船尾和船身在电火花的嗞嗞声和低沉幽怨的管弦乐背景声中凸显出的整体断裂声的模拟(这种令人惊奇的声音效果被随后落水的和已经登上救生艇的人们的惊叫声衬托得更具有感染力),以及《侏罗纪公园》对再生的巨大史前动物恐龙的吼叫声的模拟(混合了狮子、大象、鲸鱼等动物的叫声),显然都是数字声音技术发展进步的结果。
三、声音技术数字化发展的效果及影响
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明确写道:“不管是否意识到,声音始终是一种强有力的电影技术。……它利用了一种特殊的感觉模式。……能有效地影响我们对影像的领悟和理解。……能够相当明确地引导我们在影像中的注意力。……引导着我们形成期待。”[6]306声音数字技术在当代的突飞猛进,使一些以往电影难以展现的声音效果得以有效呈现。也正因声音技术数字化的发展进步,加之运动画面的科技创新(尤其是数字动画技术、3D技术的成熟),世界电影才有了今天类型多样、题材广泛、形式新奇、效果感人的精彩态势。当然,非常仰仗声音科技效果的灾难片更是受益匪浅。
(一)从模拟到数字
声音科技的发展使声音在当代由机械模拟声向数字立体声、3D环绕立体声发展,这使灾难片的声音效果愈加逼真。如《海啸奇迹》对海啸的声音效果的模拟,《2012世界末日》对公路连续裂陷、洪水奔流、火山喷发的声音效果的模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这大大增强了灾难片的艺术感染力。
(二)从平面到立体
声音科技的进步使声音在当代从单声道(单音轨)向立体声(多音轨)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立体声迅速向杜比音效效果(在多音轨的基础上,降噪并实现立体环绕效果)发展,并日臻成熟。这使灾难片的声音效果更为生动、逼真,也强烈震撼了观影主体。
(三)数字技术中艺术的脱魅与重建
灾难片中的不少声音(如地震的声音、海啸的声音、恐龙怪兽的声音等)是罕见而令人惊奇的,这为灾难片的声音美学创作提供了大有可为的空间。也正因如此,声音数字化技术对新奇声音效果的模拟便极为必要。但灾难片的声音美学创作切忌陷入为新奇而新奇的误区,对任何新奇声音效果的想象和实践必须建立在真实可信或合情合理的基础上。创作者必须遵循马赛尔·马尔丹在谈及“音响对电影带来的作用”时所提出的“现实主义”原则——“现实主义,更准确地说,便是真实感”[8]89。也就是说,在更宽泛的语境中,任何声音效果都要合乎情理逻辑,如《侏罗纪公园》中恐龙的声音融合了狮子、大象、鲸鱼等动物的声音元素,便完全合乎人们对远古食人猛兽或巨型动物声音的合理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