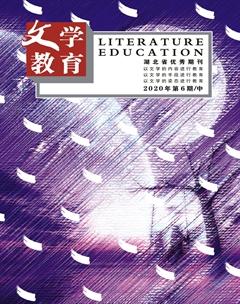论《呼兰河传》创作中的精神展现
夏玉溪

内容摘要:《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生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大多数观点认为《呼兰河传》是萧红与鲁迅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对国民性的批评,但萧红的批判与鲁迅是有所不同的。借鲁迅的《呐喊》与《呼兰河传》中相似的部分进行比较,笔者意在挖掘了《呼兰河传》中展现出的与《呐喊》不同的批判精神存在。《呼兰河传》不仅仅停留在批判国民性上的,它更是一本萧红在离别世界之前给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了重构,寄托了萧红的自由、坚韧与爱的小说。
关键词:《呼兰河传》 《呐喊》 萧红 精神世界
《呼兰河传》是萧红生前所写下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但我们在阅读萧红与鲁迅的作品时,能够清楚的感受到这种“国民性批判”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具体体现在哪里?萧红创作《呼兰河传》的动机是批判国民还是别的?以下,借用批判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保守、庸俗等社会特点的鲁迅先生的作品之一《呐喊》与《呼兰河传》相对比,阐述该问题。
一.从看客阶层看国民劣根性
在提及萧红文章中对麻木看客的批判之时,笔者认为将萧红文章里展现的百姓和他们的行为与“看客”是有所不同的,提及看客我们会想到鲁迅,但萧红笔下的“看客”与鲁迅笔下的“看客”是有所不同的。萧红笔下的呼兰河镇的人民是更为善良的。
我们从鲁迅《阿Q正传》的一个片段入手阐释,在阿Q被王胡辱打之后,他不断骂骂咧咧走向酒馆,路途看到了“晦气”转移对象小尼姑后他不仅摸了她的头,还变本加厉地侮辱了小尼姑。在这一段里群众的反应是哄堂大笑,没有人对阿Q的行为予以阻止,也没有正义的发声,他们只是狼狈为奸,九分得意地笑。鲁迅笔下的“看客”群体不止是冷漠、不作为,他们推波助澜,没有一个是好人,更像是一群无赖、流氓。
萧红笔下对虚伪旁观的“看客”批判与鲁迅笔下的主体是不同的,鲁迅笔下的看客包含了“下层人民”,而萧红笔下的“看客”更多是绅乡阶层,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明确的批判。
其次,萧红笔下也是有下层人民群体组成的看客。但他们做出的事的出发点更多是因为迷信和根深蒂固观念的束缚,比如马没有死却要说马死了是因为怕泥坑的威风没了,校长的儿子掉进泥坑是因为学校传播的新知识违抗了龙王的意识,小团圆的死亡是源自“治病”和对王大姐的恶意是因为门当不户对、未婚先孕等,这些嚼舌根的群众是愚蠢的、迷信的、无聊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本身不是“坏人”,萧红笔下的他们做这些事更似在整个社会的封建思想影响下自然而然形成的,她并没有去着墨过多地批判他们,下层人民在萧红的笔下是作为受害者一方出现的,而阿Q和酒馆里的百姓们对比他们更弱小的人施加威风、欺负他们等,他们是站在加害者立场上的,萧红的百姓不是刻意地做狼狈为奸的事,他们本质上是善的。虽然是他们嚼舌根,但他们也会去想方设法把泥坑里的马拉出来。他们身上包含着萧红多种多样的情感,其中是有爱的,这一点我们很难在鲁迅的文章里看到。
萧红对国民性的批判没有鲁迅的那么狠绝,它即使是含着萧红隐喻讽刺的意思在里面,但对呼兰城,萧红始终是充满了爱意和眷念的。当一个人年老并且预料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很难不怀念生自己养自己的土地,呼兰城是萧红的故土,是萧红临走前的最后的精神家园,在她独居香港的时候,想象里的童年就是她孤寂敏感缺乏安全感的心的归宿地,也是她理想的长眠之地。她对于呼兰河这座小城的爱包容了呼兰河人民存在的缺点,包容了新旧文化冲突之下的差异。她向我们传达的情感其实很简单:呼兰小城是自然的,无论是“生老病死”还是存在其中的迷信愚蠢。
二.从有二伯与孔乙己的比较中析精神家园
有二伯作为《呼蘭河传》里塑造的一个复杂的形象,常有学者将其与阿Q联系起来,在比较中阐明鲁迅对萧红的影响。笔者认为其实有二伯身上其实还有另一个角色的影子,即孔乙己。
从他们的共同点来看,有二伯和孔乙己说话都是有一股文绉绉的范儿,他们穷但也有属于自己的自尊,都在称呼上被开过玩笑,没有固定的居宿地,穿长衫,形象滑稽,同时都会用借口来遮掩自己偷盗的小毛病,都是作者笔下创造出来的典型的重要角色。萧红在描写众人嘲讽有二伯的偷盗时甚至用的笔调色彩和情景都与鲁迅的一样,旁人都会笑话起来。
从他们的不同点来看:首先,孔乙己在《孔乙己》一文中是孜身一人的,他没有朋友,遭遇也只是被偶然知道,生活里有他没他不值得旁人的注意,甚至是死了也没人会惦记,孔乙己是孤独的,就连想向店小二卖弄一下自己的知识也不被赏识,他是被时代抛弃的产物,他与社会脱节,与旁人没有关系网络,他是没有任何存在于世上的价值的。而这一点上,有二伯是不同的,有二伯有朋友老厨子,第六章的开题便提到“我家的有二伯”,虽然有二伯没有睡觉的地方,但他是有一个归属地的。他与老厨子的相伴模式虽然有嘲讽和矛盾,但他们也有能相处的时候,老厨子是有二伯与外界的联系点,有二伯与社会是连接的,他拥有自己作为社会人这一身份的价值所在,同时文中的“我”与有二伯也是有联系的,即使很多小孩子会在身后说有二伯的笑话,取笑他,但“我”是会去请教问题的,有二伯拥有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百姓价值。同样在有二伯对我的态度“你这孩子,远点儿去吧……”能看得出来萧红给予了有二伯选择权、话语权和主动权,不像孔乙己只有自己去找别人然后被拒绝看不起,没有主动权。从这一点上,萧红对有二伯这一人物的情感是有爱的,尽管他古怪有盗窃的癖好,但萧红给予了有二伯尊重,萧红对于作为底层劳动人民之一的有二伯是有主观上的偏好倾向的,没有做一味的批判,尤其是在她对有二伯某些细节处的描写更是如此,如给自己缝枕头、缝鞋等,在滑稽的笔调里隐藏着劳动人民生活的辛酸苦楚。
其次,有二伯与“我”的“友谊”建立的切入点也很有意思,都是盗窃。“我”因为太饿了,偷黑枣吃,有二伯因为眼馋贫穷,偷各种东西,“我”与有二伯进行更亲密的接触就是因为“我”偷东西的时候他也在偷东西,为了保密达成协议。这一切入点本应是恶的,孔乙己因为偷东西被“吊打”、“打断腿”,但有二伯偷东西在文中却没有任何物质上的惩罚,“我”偷东西被母亲知道了还会被打,但有二伯却例外。
笔者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是笔者之前提到的有二伯偷盗无物质惩罚,二是我们可以关注到小女孩“偷窃”的原因都是善的,有二伯的形象虽然是另类的、特殊的、不普遍的下层人民,但萧红是将他归类在下层人民这一范围里的,萧红对他不仅是有对呼兰人民的包容,还有萧红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爱,她总会把批判里更尖锐、更讽刺的点指向上层社会、绅乡阶层,有二伯在路上提到了石子、被鸟粪砸到的一系列滑稽的场景中,抱怨的内容都是带有“你们这些东西应该看好了去欺负上层社会的人,而不是我”。
这一点的原因除了萧红对整体社会认知上的情感倾向外,还夹杂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情感体验。在情感上反复受到的伤害和疼痛促使她将注意力从知识分子和上层阶层中转移,那情感的缺乏能在哪里获得补救?只有在生养自己的小城里找到,在祖父的爱中找到,即使回忆里也有母亲的不公平待遇,但祖父对她的爱足以成为一个情感上极度欠缺的女孩的生命支柱。她不舍得破坏自己对呼兰的爱,也就不舍得狠狠地批判自己笔下人物具有的缺点和劣根性,她所能做的顶多是停留在客观地叙述,让读者去体会别的意味。据以上来看,萧红的《呼兰河传》更像是她精神家园的重构。
三.从重构的精神家园里看坚韧与爱
呼兰河这座小城的故事是浪漫天真却也是凄凉绝望的,似乎是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萧红为文坛留下的最后一个脚印是沉重而深刻的。萧红的后花园在文中有多浪漫蒂克,在后记里变得也就多凄凉。
在她在生命的最后,她没有将自己的精神家园重构得更加美好,重点描写的人物几乎都是悲剧,无论是小团圆媳妇、有二伯,还是冯歪嘴子,从三个人物角色来说,她对小团圆媳妇的描写多出于“儿童视角”,使本该残忍的事件陌生化了,与读者拉开了距离。有二伯则是一个有自己价值、偷盗了却还能不受惩罚的底层人形象,冯歪嘴子也是一个在经历了多灾多难的人生后依旧没有放弃对生活希望活下去的下层人,萧红是在怜悯和爱下层人民的,他们所有人经历的苦难都没有让他们一蹶不振,他们在生活压迫下体现的坚韧在文中是一直存在的。
受到病痛折磨的萧红在似乎预知到自己生命尽头而创作的《呼兰河传》正是她精神的反映。没有规则限定可以获得无限自由的后花园里,萧红对精神世界的重构在荒凉中成功找到了“自由”,这种突破口在一点点人物和风俗的展开中读者能够体会得更加清楚,呼兰河是荒凉的城也是一直有坚韧生命力量的城。
《呼兰河传》里对于童年悲惨却又天真浪漫的重构中,萧红将她对于生活的最后一丝坚韧融了进去,将她在贫瘠的精神世界里找到的自由和对人民的爱融了进去。《呼兰河传》虽也有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但她写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家,是自己精神的栖息地,因此没有鲁迅的狠绝,多了一份萧红的坚韧和爱。
《呼兰河传》不仅仅只是批判国民性的小说,它更是萧红实现精神上长存自由、实现精神上的坚韧与爱的小说,她在此时已经跳出了鲁迅對国民性批判的路子,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汉语言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