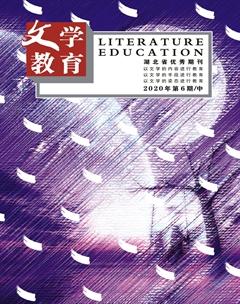《九歌》女神形象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杨晓翠

内容摘要:屈原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其代表作品《九歌》中塑造了湘夫人、少司命和山鬼三位女神形象,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女神形象,具有多重审美价值。她们地位相对较低,但重视内修外美;她们兼有神性和人性,并且充满悲剧性。这种形象特征的形成不仅与楚地的巫风、女神崇拜有联系,也与屈原的个人经历及其审美追求有关。
关键词:《九歌》 女神形象 悲剧性
《九歌》是一组祭歌。与《诗经》中单纯描写祭祀活动的祭祀诗不同,屈原在《九歌》中用充满诗意的笔触塑造了众多神灵形象,展现了一幅幅形象生动的神灵群像。其中,女神是爱和美的象征,其形象具有多重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下文将对《九歌》中的女神形象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作简要分析。
一.《九歌》女神形象特征
屈原在《九歌》中塑造了众多女神形象。这些女神形象各异,但总的来说她们的形象有以下特征。
(一)地位较低,重视内修外美
《九歌》中的男性神灵多被描写得很有气派。云中君来去一瞬,不可捕捉其身影,“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湘君“驾飞龙兮北征”。大司命“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洒尘”、“乘清气兮御阴阳”、“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东君“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河伯“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九歌》男神中除东皇太一外,都有龙这一文化图腾的存在。楚人受吴越的影响和自身的传统而尚龙。[1]《九歌》中描写神灵的升天场面均乘龙,正说明了这些男性神灵的地位较高。而相比于《九歌》中男神的威武气派,《九歌》中女神的排场就显得不那么盛大了,少司命“荪何以兮愁苦”、“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山鬼“被薜荔兮带女萝”、“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相比之下,她们更加注重内修外美。她们不仅容貌美丽,还往往都以芳草香花作为点缀。湘夫人所筑水室中有白玉与荷、荪、芳椒、桂、兰、辛夷、药房、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香草。少司命身姿绰约:“荷衣兮蕙带”。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又“善窈窕”,且“被薜荔”、“带女萝”、“被石兰”、“带杜衡”。这些香草的出现正凸显出女神的爱美之心与内心的高洁。
女神也具有香草一般的超尘脱俗的气质。她们在爱情面前没有功利心,追求的是情感的共鸣与满足。湘夫人久等无果,虽有失望之意,最后还是恢复了平静,她相信恋人对自己的感情。少司命深知自己的爱情没有结果,于是选择了离去。山鬼苦苦等待恋人,希望得到对方的回应。她们多情而不轻浮,坚守爱情最本真的模样,而不受世俗羁绊。
(二)神性与人性合一
《九歌》中的女神本质上是神,因此她们都拥有超自然力量,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湘夫人作为湘水之神,刚出场就降于北渚,后在水中筑室。少司命“登九天兮抚彗星”、“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她是生育之神,并庇護儿童。山鬼“乘赤豹”、“从文狸”,也符合山中之神的特征。
同时,女神不光具有人的躯体,也有人的情感和心理活动。她们像人间女子一样爱美,有喜怒哀乐,渴望爱情。湘夫人精心装饰水室,她“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但她也因为最后没有见到恋人而感到失落。少司命“荷衣兮蕙带”,在满堂美人中独与男巫“目成”,但他们无法相守。少司命在将要离开人间之时迟迟不愿离去:“君谁须兮云之际”,最后只能与对方分别。山鬼“被薜荔兮带女萝”、“被石兰兮带杜衡”。恋人未至,埋怨与思念接踵而至。她帮恋人找借口以安慰自己,但最终只能“思公子兮徒离忧”。
(三)充满悲剧性
《九歌》中描写女神的诸篇都带有哀伤怨慕的情感基调。湘夫人抱着殷切的思念:“思公子兮未敢言。”他们无法相见:“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少司命出场时便有巫者问道:“荪何以兮愁苦?”匆匆一面过后,只能是“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随着时间的流逝,山鬼的情绪由“怨公子兮怅忘归”变为“思公子兮徒离忧”。
湘夫人的爱情悲剧在于希望落空。她满心期待这次约会,精心建造并装饰了水中之室,但一切都是无谓的努力。少司命的爱情悲剧在于无法与爱人长相厮守,只能将爱意埋藏在心中。少司命与男巫一见钟情,一次相见便是永久的分别。山鬼的爱情悲剧在于无尽的等待。她伫立山巅,忘记时间流逝,思念之情与迟暮之哀交织在一起,使得山鬼的悲伤蒙上了一层更深的阴影。
湘夫人与山鬼的爱情结局是会合无期的等待,是一个追求到幻灭的过程。少司命的爱情结局是无法相守的分别。屈原赋予她们这种悲剧的气息,影射出诗人内心的悲伤。
从上述分析可知,《九歌》女神形象兼有神和人的特征,她们注重内修外美,追求爱情的自由与情感满足。但她们的爱情结局不遂人愿,充满悲剧色彩。
二.《九歌》女神形象形成原因
任何人物形象的形成,都会受到时代、作者个人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九歌》女神形象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下面将从巫风盛行、女神崇拜与屈原主观创造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巫风盛行
《九歌》一部分写于荆楚民间,其本质还是一组祭祀乐歌,带有楚地盛行的巫文化气息。研究《九歌》女神形象形成的原因,就不能不提到楚地巫风的影响。
既是“巫风”,必然与“巫”这一祭祀要素有重要关联。望山楚简中“巫”字写作“”,从构字法来看,此字为会意字,上体两横为天地,中二人,下体从口,以示歌唱。《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2](P100)因此,巫是在祭祀中以歌、乐、舞降神、娱神以沟通天地的人。在巫风祭祀中,巫者是人神交接的主要媒介。巫是神的代表,他们装扮成神灵的模样,展现神力,并抒发对百姓的关爱。同时,巫也代表人对神灵的迎送。
根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的描述,沅湘之地祭祀有歌舞娱神,且“词鄙陋”。[3](P55)保留了原始祭祀的重要特征。原始宗教祭祀与男女恋爱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中有姜嫄在郊禖仪式中怀孕生周稷的记载。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楚地祭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4](P185)因此,《九歌》祭祀中衍生出了人神恋爱的情节,女神也随之带有人间女子多情的特征。
《湘夫人》《少司命》和《山鬼》中的祭祀模式是以男巫迎神,女巫扮演女神。《湘夫人》中湘夫人与男巫对唱。男巫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湘夫人降临在北渚,那并非祭祀之地,因此男巫产生了忧愁的情绪。湘夫人则是“思公子兮未敢言”。而后男巫“闻佳人兮召予”,产生欣喜的情绪。湘夫人也精心装饰了水室,颇为悠闲自得,但最后他们还是未得相见,湘夫人在失落后平静的等待着恋人的到来。少司命与男巫互相爱慕。由女巫扮演的少司命在满堂美人中与男巫“目成”。男巫想象着他们在一起的场景:“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但少司命已然离去,最后男巫代表人民对少司命进行赞美颂歌:“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山鬼与男巫相互唱和,男巫开场夸赞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山鬼则“折芳馨兮遗所思”,但她因路途艰险未能准时赴约,于是独立山巅,最后只能“思公子兮徒离忧”。
(二)女神崇拜
女神崇拜是古老而又传统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存在一个盛行到衰落的过程。母系社会是女神宗教的现实基础,在原始时期人们对女神的崇拜远超过男神。叶舒宪先生在《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通过中外女神研究总结了女神信仰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根据“原母→地母→爱神→美神。”[5](P324)的规律演变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原母神创生了世间万物,母神是生育力的象征。随着农业的发展,土地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于是人们祭祀地母以祈祷丰收。《九歌》女神是爱和美的象征,是从原始女性宗教演变过来的。《九歌》中对女神的祭祀体现了楚人对原始女神崇拜的沿袭。
楚地一直以来都有敬拜女神的传统,如嫘祖、盐水女神等。嫘祖是黄帝之妻,《史记》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6](P10)她发明并推广了养蚕缫丝技术,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因此,民间乃至官方都有祭祀嫘祖的传统。据《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先蚕祭祀了,楚国民间各地也修建了众多嫘祖庙,以表达对嫘祖的崇敬与爱戴。对盐水女神的记载可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世本·氏姓篇》。当时处于母系社会的盐水女神部落盛产鱼盐。盐水女神对巴人祖先廪君一见倾心,最后被廪君所杀。巴楚二国相邻,交往密切,也经常发生战争,巴文化与楚文化也逐渐融合,盐水女神的传说也在这样的文化交汇中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嫘祖、盐水女神的神话传说建构了楚地的女神崇拜,也间接说明了楚人有女神崇拜,因此,楚地祭祀中女神的存在是非常合理的。
《九歌》女神是人们神灵信仰的体现,在某些方面也有楚人女神崇拜的影子。湘夫人是湘水神,对湘水神的记载可见《山海经·中山经》。帝之二女为湘水之神,活动范围在澧、沅、湘一带。这证明了或许在屈原之前,楚地就有类似的湘水女神了。少司命是生育之神,即高禖女神,她“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高禖神崇拜产生于母系社会,且经久不衰,各个时代、各个地区都有祭祀高禖神的传统。山鬼是山神,一说为巫山神女,有待考证。但山鬼“留灵修兮憺忘归”之事与巫山神女的主动献身有相似之处[7](P330)从这个角度看,山鬼与巫山神女也不无关系。
(三)屈原的个人经历与审美追求
文学形象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有意识地认识生活的结果,因此在文学形象中必然蕴含着作家的思想感情和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
屈原的个人经历为《九歌》女性形象的塑造形成了情感支撑。屈原出身楚国贵族,《离骚》中屈原自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自称是高阳氏的子孙。他博闻强识,早年身居要职,曾任左徒、三闾大夫。三闾大夫是主宗庙祭祀之职,王逸《楚辞章句》云:“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3](P1-2)这样的任职经历使得屈原有机会接触到祭祀内部,这也为《九歌》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为了振兴楚国,屈原试图变法改革,与顽固势力作斗争。但这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于是他被小人构陷,被流放到荒僻之地。在流放时期,民间的祭祀给他很大的启发,《湘夫人》《山鬼》就带有很明显民间祭祀特征。即使如此,屈原的爱国思想表现的更加强烈而深沉,但他却无法拯救这个国家的衰颓之势,这种苦闷彷徨的心情被带入人物形象中,与她们血肉相融。《九歌》女神对爱情的追求暗示了屈原在政治受挫后内心依然对君王抱有期待,他希望重新得到楚王的信任,以此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女神与恋人不得美满的爱情结局正是屈原与君王遇合的失败的间接反映,也影射出他内心中的无奈与悲伤。山鬼在等待过程中抒发了美人迟暮之悲:“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流露出屈原伤盛时易逝,恐无作为的心态。
特殊的审美追求又使得屈原所塑造的女神形象丰富多彩,又寓意深刻。屈原担忧国家前途,试图变法改革,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政治追求化为屈原独特的审美追求,使得屈原选择了女神作为符合自己理想的审美对象。女神是自己的化身,她们对爱情的苦苦追寻正是屈原追求“美政”理想的真实写照。屈原选择女神作为表达内心情感的媒介,用《九歌》中神女的爱情悲剧影射自己政治生涯的不得意,以神女们与恋人的聚合无常表现出他内心的隐忧。
综上所述,《九歌》中的女神形象,是在楚国巫风与女神崇拜的基础上,屈原内含个人经历与审美倾向的自觉创造。《九歌》女神形象以其獨特的审美意蕴为后世文学作品中的女神形象提供了最初的创作范式。自此,女神形象在后世文人士大夫的扩展中不断丰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瑰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刘玉堂,贾海燕.楚人的宗教信仰与四象空间观念——兼及对道教的影响[J].宗教学研究.2018(04).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