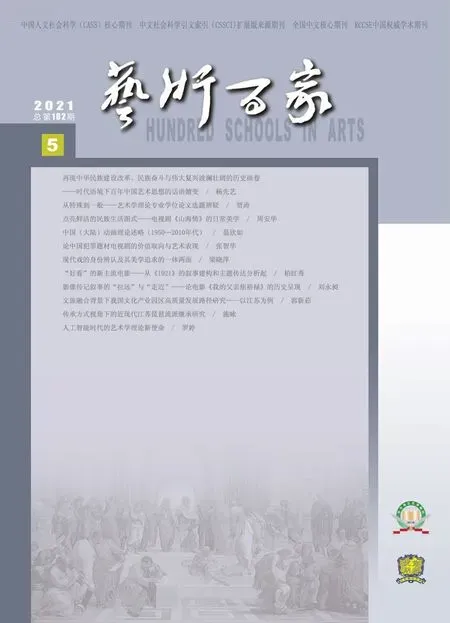求似·再创·意临:仇英摹古画风的三种进路*
常德强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0)
作为明四家中唯一的职业画家,仇英的摹古仿古画在其创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许多早已成为传世珍品,如《临宋元六景》《临宋元画册》《临萧照高宗中兴瑞应图》《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尽管如此,摹古与创新的关系似乎也是他绕不过的话题。一面是批评家对其妙手丹青能力的赞美——“精工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1],一面是对其摹古之作“寄兴”不足的叹息,如董其昌等仍沿用宋元以来形成的业余画家的理想标准认为其作“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也[2]66,李日华等也以传统趣味判其画“非高品也”。其实,当我们把仇英摹古画风放到明中叶艺术市场逐渐兴盛和古典文人画风仍为主流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考察时就会发现,仇英摹古画风中“求似”“再创”“意临”三者是并存的,它们共同构成其摹古画风的三种进路。“求似”,即大量模仿唐、宋、元画作,在摹“形”得“神”中汲取诸家之长;“再创”,即在结构内容的还原下,于细节处融入自己的体验和理解并进行创造性的仿古;“意临”,即融万家菁华,得其意而忘其形,区别于同时代文人画传统,复兴“晋唐样式”而独成大家。表现在仇英创作中的这三种进路的交集、并存、演进之态,也反射出明代中叶江南地区的艺术新需求和艺术新场景。
一、求似:在“摹形得神”中渐创
绘画领域的“求似”原指画家对现实之物的精确描绘;此处的“求似”概念,则是仇英临摹作品中忠实于原作的一种类型。这些临摹之作在绘制之时就有原作或粉本可供参考,仇英在临摹过程中以还原原作为目的,其临摹作品能反映原作绝大部分的特征。
一般来说,绘画领域的“求似”,只是画家的起点,当达到一定高度后,反而会成为画家攀登更高境界的障碍,也成为批评家品评画家品格高低的标准。但对仇英来说意义却不同,他一生绘制了大量“求似”的作品,不仅达到“求似”的巅峰,还极受热捧。检阅一下各家各派对仇英画作的议论,极少见在“似”与“不似”层面上的批评,对他的这种艺术选择和认同,显然与中国社会内部文化衍变,新的文化要素逐渐出现、形成有关。正如一般文化史描述的那样,明代中后期南方地区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繁荣的商业中心,如苏州、松江、南京、徽州、扬州等地,其中艺术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新兴艺术市场的形成,收藏、鉴赏、订制、交易在此进行,纯粹的艺术品第一次作为文化商品在这一制度化的舞台上流通起来。大批商人、官员、市民、职业交易人和中介均活跃于这一舞台,当然也产生了大量赝品和“苏州片”,那些具有顶级临摹能力的丹青妙手获得了巨大市场利润。
仇英中年以后,以“驻府画家”的身份先后在周凤仪、项元汴、陈官等收藏家家中居住近20年,这也是他大量观赏学习古代名画原作的黄金时期。清初吴升《大观录》记:“槜李项子京收藏甲天下,馆饬十余年,历代名迹,资其浸灌,遂与沈、唐、文称四大家。”[3]358仇英之所以备受收藏家青睐,是因为他精细入微的绘画技术。在没有彩色印刷复制品的年代,保护古画的重要方式是找画师临摹一个逼近原作的版本,用于日常观看赏玩。不同于收藏家项元汴或其友人那样只是偶尔短暂地欣赏古画,仇英受益于复制临摹古画的工作,有机会长时间接触和观摩,时时浸淫,细细揣摩。在临摹的过程中他既磨炼了画技,又能体会前代画家绘画的精微妙义,对于市井出身、文化修养不高的仇英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仇英临摹画作,不仅出于个人提升画技的需要,也是作为职业画家满足雇主要求的结果,“求似”不仅是仇英的个人艺术追求,也体现出赞助人的需求。
寄居项元汴家中[4]219-222是仇英广泛观摩唐、宋、元名迹最多的一段时间,也是他临摹古代作品最多、画技精进的一段时间。徐沁在《明画录》中称仇英“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5]16。姜绍书则在《无声诗史》中写道:“凡唐宋名画,无不临摹,皆有稿本,其规仿之迹,自能夺真。”[6]54仇英为项氏临摹了大量作品,每件摹品都用心揣摩,体现了对原作很强的理解能力和技巧掌控能力。大量摹古研习名画成就了仇英,博采众长的摹古活动使仇英超越周臣与文徵明对他的影响,虽在画中融入众家笔意,画风却毫无牵强拼凑之嫌。从文献记载来看,仇英的摹古之作见于著录者有45幅①,多数已散轶,现存《临宋人画册》《中兴瑞应图》便是这类摹古之作的典型代表。
《中兴瑞应图》现存有上海龙美术馆所藏十二段本、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四段本、天津博物馆所藏三段本、故宫博物院所藏仇英临四段本等多个版本,原作普遍认为是南宋萧照所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版本被认为是箫照存世代表之作的三段本《中兴瑞应图卷》。故宫博物院所藏仇英所作四段本《临萧照中兴瑞应图》(图1)被认为极好地还原了萧照原画风貌,董其昌赞其摹古之作与“真本”相差无几,“无不肖似”②。此图取宋高宗赵构即位前的种种瑞应传说为内容,张彦远说绘画有“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之功,此图正是这样一幅出于政治、道德需要,歌颂赵构重建王朝,宣扬其继承皇位合法性的作品。

图1 〔明〕仇英《临萧照中兴瑞应图》③,33cm×723cm,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箫照作品中赵构之母显仁皇后占卜和赵构城外军梦见御衣加身的情形都出现在仇本中。从这两段来看,画面的构图、情节布置完全一致。显仁皇后与仕女所处的抱厦,建筑的台基、梁柱、屋顶、屋檐上的细节、屋内的陈设,都被仇英精细地还原出来(图2)。原作中,占卜的方桌后面有一落地屏风,屏风上画着一处流行于南宋时期的水泊沿岸的边角之景,仇英的摹本同样保留了这一细节。从细微处可见仇英对原作的还原度。虽然由于时代欣赏趣味的变迁和颜料种类的丰富④,仇英使用的色彩较为艳丽,但是图中所画的建筑无论样式还是比例关系,甚至是细节部分的描绘均与原作保持高度一致。可以说仇英摹形得神,用笔粗拙,设色古雅浑然,极好地再现了箫照《中兴瑞应图》的精神风貌,一反通常惯有的清雅秀丽、“绢素之工,侯于叶玉”的本家面目,展现出古雅朴拙的宋人风度,达到“下真迹一等”的高超水平。

图2 显仁皇后占卜细节对比图,左图为箫照原作,右图为仇英故宫摹本
现存仇英的摹本没有年款。明代张丑:“项氏藏萧照《中兴瑞应图》,前后共六段,笔法原出李唐而沉著过之,品在晋文春秋上。”[7]651箫照原作曾藏于项元汴家,且仇英摹本上有项元汴多方收藏印,仇英很可能是在项家临摹的这幅作品。虽然失去两段,仅存四段,但依然表现出了原作中古拙的宋人风度。
另一本能说明仇英摹古功力的现存作品,便是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临宋人画册》。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一书中《仇英摹宋人画册》云:“实父为子京所摹宋人画册之一也。原有百幅,今所存止此矣。当是中年时所作,惜无款印耳。”[8]张珩先生当年看到的是珂罗版影印本而非原作,但他指出了该画册中所临摹的某些宋画原作的出处,比如《明妃出塞图》原为庞莱臣所藏,后流出海外;《松泉鸂鶒图》原为孙伯渊所藏,后归北京故宫博物院;《仕女对镜图》已流出海外;等等。从张珩的记载来看,他见过这套画册的宋代原作,虽然不是全部,但还是有部分作品保存到了现在。目前存世的一些作品,也能表明此本册页跟宋代绘画之间的联系。仇英画册中的《羲之小像图》与台北故宫所藏的《宋人人物》出自同一图式,男主人形象的表现方式为:背景屏风上挂的肖像和主人正面形象一一对应,主仆关系、家具布置、文房物件摆放都延续着同样的思路;另一幅《半闲秋光》中对镜梳妆的仕女图像,仅以侧脸的形式出现,而在镜面中描绘她的全貌(图3),借“对影自怜”来表现闺怨的主题,现存王诜《绣栊晓镜图》保存了这一图像的宋代版本。这些作品的对比可证明仇英在临摹时对原作的还原度之高。

图3 〔宋〕王诜《绣栊晓镜图》,24.2cm×25cm,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左);〔明〕仇英《临宋人画册之半闲秋光》,27.2cm×25.5cm,绢本设色,上海博物馆藏(右)
仇英以临仿唐宋名家稿本为多,这些临摹机会使仇英亲眼观看前代大师的原作,并且在临摹过程中学习他们精妙的构思、复杂的构图、院体风格的青绿画法等,并在此基础上练就了精湛的临摹功力:“凡唐宋名笔,无不临摹,皆有稿本。其规仿之迹,自能夺真。”[6]54
二、再创:在“摹古求变”中创造
仇英临摹仿古作品不仅能高度“形似”“夺真”,而且能在模仿整体构图和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经过早年的自我磨砺,名师周臣的指导,中年后对前代名画原作的广泛临写,使得仇英解决了临摹中的技术问题,克服了艺术媒介的障碍,正如施凤来题跋仇英《摹赵千里丹台春晓图卷》赞其“实父雅擅文藻,精于绘事,凡宋元名迹,靡不留心点染”[9]361,但仇英并没有停滞于此,他并不想仅仅做一些顶尖级的“苏州片”。仇英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充分利用自己独有的宝贵资源、超异的绘画技术,顺适时代审美趣味的若干变化,在传统主流文人审美和新兴市民需求的张力中,将传统题材转变为时代新兴趣、新审美。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画史最终遴选了他,时代遴选了他,他在摹古中求变的创造,让一向依傍于传统文人画标准的职业画家获得了更多合法的存在空间。
有幸留存下来的仇英临摹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见证了他的创造性。仇英原有两本《清明上河图》藏于清内府:一本是1950年清点故宫幸存文物时发现的[10]285-289,现存于辽宁博物馆;另一个版本连同清院本等七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此处论述以辽宁博物馆所藏本为蓝本。
在画幅尺寸方面,仇英本纵987厘米,比原作长近一倍,扩大的尺幅为仇英提供了更多挥洒笔墨的空间。仇英还创造性地将汴京替换成自己所熟知的城市——苏州,苏州城的繁华景象为仇英的画面提供更多新鲜的元素。仇英《清明上河图》中所呈现的不再是原作呈现的宋代都城,而是一个明代中期苏州城其乐融融的欢庆之日,仇英笔下的房屋更加高大齐整,沿街门面、楼阁深宅均显示出宏大的气场。明代经济繁荣衍生出的新兴行业在仇英的画中格外突出。贩夫走卒、店铺酒肆、街市交易、市民出行等场景细节,千姿百态,形象生动。
在建筑方面,仇英本中出现了带有时代烙印的细节变化。在仇英本中最为典型的圆拱形城门,是明代建筑样式,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城门呈方形,是典型的宋代建筑样式。虹桥呈半圆拱形是明代的造桥法,虹桥由条石砌成,桥面窄小陡峭,仅容行人通过,无车辆之干扰,行人可悠然自得拾阶而上。原作是全木结构的木拱桥,桥面宽阔平缓,可容车辆、牲畜、行人同行,甚至可以容纳摊贩于桥上摆摊叫卖。城墙由宋代质感粗犷的夯土城墙变成了明代清雅精致的包砖城墙。仇英画风与这种清雅精致的特点恰恰合拍。可见,仇英在临摹中并非亦步亦趋、一板一眼地摹写,而是在原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趣味进行创造性调整。
在画法方面,原作以灰色、褐色基调处理画面,仇英则对明末社会流行的青绿设色进行改造,在迎合主顾的同时,独出机杼的笔意和优雅富丽的气韵亦在画中自然流露出来。他沿袭唐宋青绿山水设色法,以赭色石绿敷染相互映衬,以淡墨勾勒,略加皴染,画面色彩斑斓又不失温润厚重。从画中人物可以看出,仇英学习唐宋人物画法,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新发展,他的线条细劲清雅,用色妍雅温润,容颜秀丽,相较于张择端原本中北宋都城人物的面貌,仇英所表现的则是繁华江南姑苏人物的形象。就连画面上的各种礼仪、活动、植物等也都一改原作中汴京都城的民俗风情,呈现出吴门地区的世貌风情。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流传到明代初年被苏州人陆完收藏。嘉靖五年(1526)陆完去世后,《清明上河图》被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走。仇英是否曾经见到过张择端本的原作,已经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仇英摹本既有对古典风格图式的历史继承,又有对艺术作品的重新塑造。他创作的具有时代烙印和独特风格的画作,与原作拉开不小的距离,正如郑振铎所言:“明代正大量流行着《清明上河图》,像仇英那样的大画家也摹仿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其实,却是自出心裁地画着一本浩瀚的明代社会生活的创作。”[11]231朱良志先生也曾说:“仇英是明代江南人,他在临摹这幅画时,改去了一些宋代旧制,而易以明代江南清明时候的社会景物。”倪元璐则谓:“张公择端为此图洵超前绝,后之作罕有与匹者。今见十洲摹本,形神俱妙,张君不能独擅其美矣,得者珍之。”[12]78
从仇英另一作品《春游晚归图》(图4右)也可看到他“仿中再创”的特点。此幅画作未见作者名款,仅在右下方钤有一枚“十洲”葫芦印,清代安岐《墨缘汇观》说:“每见十洲所作,凡临摹前人者,皆不书款。”[13]388本幅画作即可作为例证。从画题来看此作与浙派戴进的《春游晚归》同名,尽管具体细节的刻画不尽相同,但却有着秋游暮归、小桥流水、烂漫桃花等共同母题。鉴于此,可以推测仇英曾见过戴进的《春游晚归》,不过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完全照抄复制,而是以仇氏笔法精描细染,刻画有致又典雅清秀。整体看来,仇英把春游归来的文士、柳树掩映下的院落、岩石矮树等人物实景紧密安排在画幅下半部分,以淡墨没骨画法在画幅上半部分推出远山,整幅画面水气氤氲,一派温润清逸的江南气象。与之相比,戴进的《春游晚归》(图4左),则表现出另一种情调,松树、小桥、院落、叩门的高士以及远山等元素集中在画面右侧,左侧相对疏朗,这样的布局显然取法于南宋马远、夏珪的“一角”“半边”构图。从画面的布局看来,仇英《春游晚归图》比戴进之作显得平和稳重,笔墨含蓄服帖。特别是在暮色氛围的处理上,此图显示出极高明的绘画感受与技巧,比如院落远处树丛云烟遮掩,层层推远;画树木、远山以勾勒与晕淡为主,不用皴笔,仅以墨色把暮色迷濛、幽深杳霭的气氛烘染出来。因此无论从构图、笔墨、设色还是氛围营造来看,仇英均较戴进更重视对主题的精细表达、才情和技术的展现,体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图4 〔明〕戴进《春游晚归图》,绢本设色,167.9cm×83.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左);〔明〕仇英《春游晚归图》,绢本设色,145.5cm×76.5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右)
再看仇英的绢本设色册页《捉柳花》。此图系故宫博物院所藏《人物故事图册》中的第六开,图中文士心情闲逸,立于茅舍前观看孩童捉弄柳花,周围弱柳扶风、河水清且涟漪,三名童子于春风中扑捉柳絮。画面情境显然来自白居易的《别柳枝》绝句:“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飞向别人家。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此图又有宋代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之“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的诗意。此图笔致工整而不板滞,设色清丽典雅,为仇英的精心之作。将此册页与周臣的《画闲看儿童捉柳花句意》并置同观,尽管形制上一为册页,一为立轴,画面构图上仇英画布局饱满,周臣画主景安排于左侧,为马远、夏珪一派的“半边”格局,然而两画情境相同,兼具造型精谨、色调温润的特点,因此亦可推测出仇英师承周臣,仇英曾看到其师的同题画作,并能“仿中再创”、借题发挥。
统观仇英的传世作品,摹古仿古画作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摹古中“再创”的作品一定很多,惜今日可见此类真迹非常有限无法多加比较,然而从各种画论中可以看到相关信息。周天球称仇英在临摹古画时“盖非对临,以意仿佛为之,靡不神往,笔先似而不专以迹。……亦见其胸中博洽,故能随摹辄肖”,可见他的临摹作品能够“形神兼备”。顾复《平生壮观》云:“吾见其心师意匠,新新不穷,可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乎。”[14]384可见仇英的作品亦有独创之处,而并非只专注于摹古。
三、意临:在“得意忘形”中独创
除上述临摹之作外,仇英作品中也有部分“意临”的摹古之作。这些作品由仇英独创,但是在画面中某些情节的布置上,却可以明显看到师古痕迹,但仇英巧妙地将古代的图式、画法和自己的创作结合在一起。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汉宫春晓图》(图5)就属于这一类作品,该长卷以春日晨曦中的宫殿庭院为背景,描绘后宫佳丽的日常百态,用笔细谨,人物情态丰妍。画卷描绘了歌舞、赏荷、梳妆、观书、弈棋、扑蝶、婴戏、制衣、写像、捣练、拈花等多个场景,无不布局巧妙,全卷结构繁复,赋色沉厚绮丽,古木奇石与华丽宫殿掩映成趣,极尽精雅富丽之美。

图5 〔明〕仇英《汉宫春晓图》⑤,30.6cm×574.1cm,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仇英在《汉宫春晓图》中借用常见的仕女像,把她们置于一种富有贵族气息的宫廷环境中。胡应麟认为仇英在其作中运用了唐人的图式⑥,细观这幅作品,图中的熨烫情形可以在唐代张萱的《捣练图》中找到原型(图6)。张萱图卷中的一名妇女因为扯绢用力微微后倾以达到平衡,对面合作的妇女梳着高髻,背对画面,熨烫者神情专注,步态轻盈,熨斗自右往左徐徐推进,一女童自白练下方俯身钻进钻出,憨态可掬,画面充满生机。再看仇英《汉宫春晓图》中的熨烫场景,不再描绘白练下的女童,扯绢的两妇人位置对换,且后仰的女子回首目视临近聊天的妇女,鲜活生动,不似张萱版本那样端正。仇英画中人物细眼柳眉,削肩长身,仪态娴雅,人物的衣饰发髻也是明代典型的样式,而张萱本人物形象端庄丰腴,高贵雍容,设色柔丽,线条简劲流畅,颇具典型的大唐风韵。

图6 〔唐〕张萱《捣练图》(局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左);〔明〕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右)
从画卷中的弈棋场景可以看出仇英此作可能仿自唐代周昉的《内人双陆》(图7),在周昉的画面里,两名对弈的贵妇身着红绿色调的衫裙,头顶高髻,髻上缀以月形角梳,两位夫人看上去颇为淡定平和,甚至显得有些慵懒,身畔嫔妃小臂搭在侍婢肩上,神情专注,目视双陆棋戏。而仇英画中弈棋场景也描绘了相同角度的弈棋组合,却能别出心裁,自具新意。图画中对弈者身着朱红衫裙,簪钗环佩繁复,中间的棋盘改双陆盘为围棋棋盘,观棋者改站立为坐观,人物形象一改周昉的端庄丰腴而为明眸皓齿、潇洒俊美,其细入毫芒的笔致和妍雅温柔的情调亦与周昉笔致的闲散恬静大不相同。姜绍书《无声史诗》赞曰:“英之画秀雅纤丽,毫素之工,侔于叶玉,凡唐、宋名笔无所不临摹,皆有稿本,其规仿之蹟,自能夺真。尤工士女,神采生动,虽周昉复起,未能过也。”[15]41整个场景显得清新明快,气息欢悦,故其画雅俗共赏,怡神畅心。

图7 〔唐〕周昉《内人双陆》(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左);〔明〕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右)
此外,我们可以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挥扇仕女图》中找到刺绣的角色形态。图中婢女吹奏跳舞的情形与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极为神似,显然仇英在他的《汉宫春晓图》中借鉴了古代名家,并能把自己的绘画风格与前人的造型特点自然融合在一起,将精致繁复的汉宫生活很好地展现出来。这种不经意的挪用,是基于仇英人生经验中所储存的巨大古画图像库以及他所练就的高超绘画技巧,使临摹与创作结合得更加紧密自然。同时,《汉宫春晓》一半为室内景一半为室外景的巧妙穿插,显然又与唐、五代时期不画背景的宫中仕女图不同。南宋牟益的白描名作《捣衣图》虽然也描绘背景,但是《汉宫春晓图》的构图和细节却比《捣衣图》复杂很多。我们亦可注意到,仇英《汉宫春晓图》中所绘宫苑连绵的图景与现今可见的苏州园林更为接近。江南一带自然景观园林建筑的精致清秀正符合当时文人画传统和文学思潮的审美趣味,画家们自然也会把它们作为笔下的素材。
仇英的守正出新还表现在色彩的运用上。仇英效法“晋唐样式”,在山水画中复兴了以色彩为主体的传统,集中规模地使用了同一种语言样式的积色体山水。仇英的“集合式”积色勾染体山水可见于《桃村草堂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玉洞仙源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桃源仙境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等。仇英的积色勾染体山水,用浓墨勾画树石,不作皴,石青石绿压淡事先勾出的墨线,石青石绿上再以花青、汁绿等分染以突出岩石的立体效果,云为勾云或以白粉敷染等。[16]266-268董其昌说仇英的画“位置古雅,设色妍丽为近代高手第一”[17]94。
“设色妍丽”晋唐色彩得以复兴,我们不能仅仅将之看作仇英个人的擅长和趣味,而应视作他贴近和表现新市民审美所进行的有意识的调整,是时代和个人艺术的双向互动。对比宋明两本《清明上河图》的色彩变化,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宋本《清明上河图》基本上以墨笔为主,稍敷花青、淡赭,色调沉郁;而仇英本则借鉴青绿山水,用色明艳,色彩迎合大众的欢快明朗的审美趣味。
四、结语
清代画家、鉴藏家宋荦独喜仇英的摹古画品:“辛苦仇生学大李,画时鼓吹不闻喧,怪他小册临摹好,风致超超又宋元。”[18]727仇英“传移摹写”古画既严守法度,又“风致超超”,卓然成一格。一方面,这得益于他个人的优越机遇——他与吴地一流书画家、一流收藏家的密切交往,更长年成为几个重要收藏家的“坐馆”画家,守正出新,在“摹古”中“再创”,在“意临”中“独创”;另一方面,明中叶商业化艺术市场的形成,逐渐制度化的艺术生产机制,给他提供了最佳生长空间——收藏、鉴赏、订制、交易的艺术市场。所以,仇英摹古画风的三种并存进路,既满足了新兴艺术市场的需求,映射出明中叶文化艺术的历史场景,反过来此时期的文化艺术又为这种历史场景所塑造。
① 据福开森编《历代著录画目》所录仇英摹古之作及记载出处:《摹李思训海天落照图》《临李思训海天落照图二》录于《清河书画舫》,《摹董展道经变相图》《摹范长寿西域图》《摹李昭道明皇游月宫图》载于《清河书画舫》《书画见闻表》,《摹赵伯驹浮峦暖翠图》记于《清河书画舫》《清河书画表》《真迹日录初集》《佩文斋书画谱》,《摹松雪沙苑图》载于《清河书画舫》《珊瑚网画录》《佩文斋书画谱》《式古堂书画考》,《临西园雅集图》见于《书画跋又续三卷》《珊瑚网画录》《翕州山人稿》《佩文斋书画谱》《佩文斋书州山人稿》《佩文斋书画谱》《佩文斋书画谱》《式古堂书画考》,《摹西园雅集图》载于《佩文斋书画谱》,《临赵文敏山水四轴》《临苏汉臣仕女四轴》录于《珊瑚网画录》《佩文斋书画谱》《诸家藏画薄》《天水冰山录》,《摹四古图》载于《珊瑚网画录》《诸家藏画薄》,《临阎右伯李将军本三辅黄图》录于《珊瑚网画录》《诸家藏画薄》,《摹辋川图》见于《珊瑚网画录》《佩文斋书画谱》《翕州山人稿》《佩文斋书画谱》《佩文斋书画谱》《式古堂书画考》《诸家藏画薄》,《仿宋人花鸟山水画册一百幅》载于《珊瑚网画录》《式古堂书画考》《诸家藏画薄》,《临元人情仙花辇图》《临赵伯驹光武渡河图》《摹四古图》见于《佩文斋书画谱》,《摹四古图》录于《式古堂书画考》,《临贯休白描十六罗汉图》《摹冷起敬蓬莱仙奕图卷》载于《过眼云烟录》,《仿唐人驾车图一卷》《临崔白竹鸠图》《临宋元六景图》《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仿赵伯驹桃园图卷》《仿周昉太真上人图》《临阎立本文姬归汉图》见于《石渠宝笈再编》,《摹倪瓒小象图》录于《石渠宝笈三编》《西清札记》《觯斋书画录》,《摹驴图卷》载于《穰梨馆过眼录》,《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见于《穰梨馆过眼录》《眼福编初集》《眼福编三集》,《临九成宫图》录于《书画鉴影》,《临宋人山水界画人物画册》《临宋人花果翎毛画》载于《墨缘汇观》,《临李晞古山水卷》见于《虚斋名画录》,《临李公麟十八应真图》载于《秘殿珠林》,《临李唐文姬归汉图》录于《西清札记》,《摹李龙眠莲社图》《摹赵千里张公洞图》见于《红豆馆书画记》,《仿赵伯驹炼丹图》载于《盛京故宫书画录》《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十四卷》,《摹清明上河图》见于《平津馆书画记》《江村书画目》,《摹赵松雪卷》《临贯休罗汉图卷》载于《江村书画目》,《临四川雅集图》录于《诸家藏画薄》,《摹刘松年载酒图卷》见于《眼福编初集》。〔美〕福开森《历代著录画目》,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
② 在仇英所作四段本《临萧照瑞应图》拖尾上,董其昌的题跋为:“宋萧照瑞应图,曹勋每幅皆书其事,盖为高宗纪者,余曾见真本于冯祭酒家,今复为武林陈胄子生甫藏矣,照师李唐,仇实父临照,如师(狮)子捉象,用其全力,无不肖似。独少曹勋之题,勋亦学小米行书,不及照之学晞古也。”
③ 此卷共分四段画面,各画面之间均有墨线分隔。第四段画尾款以细楷“吴郡仇英实父董摹”,下钤“实父”长方白文印及“十洲”朱文葫芦印。引首董其昌题写“仇英临宋萧照瑞应图”,拖尾有董其昌、吴绳孙、许之渐、黄家舒、吴伟业诸人题跋。
④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苏州的手工业进步显著,当时苏州城手工业者有五万余人。由于外国商品的刺激,颜料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出现了柳芳绿、红白闪色、鸡冠紫、迎霜金、栀红、胭脂红等贵重色种。参见林家治、卢寿荣《仇英画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⑤ 此图卷尾有隶书署款“仇英实父堇制”,下有“实父”“仇英”二印,卷首有千字文“虑”字编号,拖尾有项元汴题“子孙永宝,价值二百金”。
⑥ 胡应麟曾在其《少室山房集》之《跋仇英汉宫春晓图》云:“右仇实父《汉宫春晓图》,文寿承其末以临宋李伯时笔,其于宫中景物纤悉具备。第所图嫔御皆丰妍而寡绰约。盖自唐周昉诸人传流。体法大槩尔尔。余尝于童子鸣处见《戏婴图》,王敬美处见《拨阮图》,文寿承处见《捣练图》,皆题昉作……岂尽画工传合哉。”胡应麟《少室山房文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