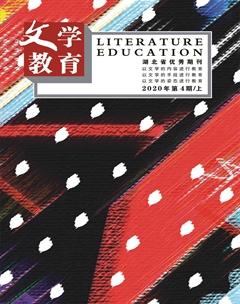文学经典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的互动共生
内容摘要:文学经典教育构成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途径。通过开展经典作家进校园活动、实行驻校作家制度、经常举办文学社团活动等多种形式,能够有效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同时,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也有利于文学经典的传播接受,二者具有互动共生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文学经典 校园文化 互动 共生
文学经典是指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经过不同时代读者反复阅读、阐释、评判之后,获得公认地位的文学精品,是一个国家、民族长期沉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学经典教育构成了校园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任务,是落实学校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有效载体。广大青年学子阅读文学经典不但能够增长科学知识,开阔文化视野,也可以提高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陶冶情操和砥砺品质,是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途径。因此,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利于文学经典的传播和接受,二者具有互动共生的内在关系。
一.开展经典作家进校园活动有利于营造良好的阅读文化氛围
一般来讲,经典作家都是被不同时代和读者遴选出来的佼佼者,其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具有深刻蕴涵,值得青年学子认真领悟和学习借鉴。经常开展经典作家进校园活动,不但能够开阔青年学子的文化视野,提升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能力,也可以增强其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兴趣,切实感知经典作家对国家、民族、时代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在中国古代,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重要观点,意在阐释家庭出身、时代背景、求学经历等对理解作家作品的价值意义。因此,除了认真研读作家个人传记、访谈录、作家评传、作家年谱、研究资料之外,与他们进行直接对话也是了解经典作家的基本途径。作为一种具有仪式性的“文学现场”,作家进校园活动通常会选在学校的学术报告厅、图书馆、会议室等重要场所,内部设施齐全,空间宽敞明亮,秩序分明,彼此之间进行对话交流和思想碰撞,这本身就构成了文学经典传播接受的别样形式。近年来,中国大陆高校举办过无数的经典作家进校园活动,比如,苏州大学的“小说家讲坛”和北京大学的“中国作家北大行”等等,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轰动效应,值得我们深度探究。
2001年10月,苏州大学在林建法、王尧等人共同倡导下,决定设立“小说家讲坛”,不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作家来校演讲,并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专栏刊载其在“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文稿。据初步统计,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邀请莫言、张炜、余华、李锐、贾平凹、韩少功、格非、阎连科、阿来、迟子建、王安忆、苏童、马原、陈忠实等国内一流作家进行文学交流,这就实现了广大师生与经典作家进行对话的基本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对话是发现和解释诸多问题的最好方式。因此,建立起凸现作家主体而又易于与学者、批评家、文学读者沟通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现场,是小说家讲坛的又一企图。在这样一个文学现场,作家的言说是自由的、朴素的,读者的质疑也是自由与朴素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对话。”[1]其中,作为“小说家讲坛”邀请的第四位作家,余华以《我的创作道路》为题,具体讲述自己是如何从一名牙科医生最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现实一种》《第七天》等都受到许多读者的高度评价,在中国当代文坛具有崇高声誉。实际上,余华之所以能够创作出风格独特的优秀文学作品,除了个人努力和写作天赋之外,主要在于他善于汲取中外经典作家的精神营养。在演讲过程中,余华首先谈到,自己早年受到汪曾祺《受戒》、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卡夫卡《乡村医生》、乔伊斯《尤利西斯》、福克纳《沃许》、司汤达《红与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等经典作品的深刻影响,是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源泉。之后,余华根据个人的创作体验,特别强调作家在观察能力、心理描写、细部呈现、人物对话等诸多方面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最后,余华和青年学子进行了深度的文学对话,回答了他们在阅读和创作过程中的疑难问题。2002年11月,史铁生以《宿命的写作》为主题,深刻阐述了个人对于写作作为一种职业、信仰、命运的认识看法。可以说,“命运的无常”和“心之家园”看似是一个矛盾体,但在史铁生的精神世界里,他却克服种种生理和心理障碍,在沉静、想象、玄思的心理状态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完成了自我超越。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写作已经成为史铁生寻找生命价值和宗教信仰的基本途径。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早已进入青年学子的阅读视野,成为他们锤炼品质和净化心灵的文学经典。可以说,余华、史铁生等著名作家在苏州大学“小說家讲坛”进行文学演讲,有利于青年学子和经典作家进行近距离对话,也肯定会增强他们阅读经典作家作品的浓厚兴趣,其现实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2009年3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明教授的呼吁下,“中国作家北大行”活动在北京大学拉开帷幕,先后邀请刘震云、苏童、王蒙、莫言、阎连科、张炜、格非、严歌苓等著名作家到北大开展文学交流活动。“作家走进校园,可以了解现在大学里的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和想法、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和看法,青年学生也可以了解中国最好的一批作家的思想和文学追求,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这对于文学应该是一项积极的有意义的活动。”[2]作为“中国作家北大行”系列活动之三的刘震云在《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的主题报告中,亲切回忆个人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学习的美好岁月,幸运地遇到王力、吴组缃、孙玉石、严家炎、袁行霈等资深教授。刘震云以讲故事方式再现袁行霈讲白居易《琵琶行》和吴组缃讲曹雪芹《红楼梦》的动人情景。之后,他具体阐述自己对《西游记》《水浒传》《论语》《鲁迅全集》《圣经》等中外文学经典的理解认识,可谓阐释视角独特,见解匠心独运。2010年5月14日,阎连科在《小说与因果——文学中的“小历史”思考》的演讲中,首先认为19世纪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以及屠格涅夫、契科夫、巴尔扎克等人的经典作品,基本都是从外部走向内部,从社会走向人,走向人物的内心。紧接着,阎连科进一步指出,与前者不同,20世纪西方经典文学的流行趋势则是由内部走向外部,小说的因果关系也发生显著变化。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等待戈多》《秃头歌女》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没有人写信给上校》等等经典作品,很多已经具有明显的荒诞色彩,也是全面阐释“内因果”含义的典型文本。这种小说创作内外视角的显著差异,表明西方经典作家对时代、社会、历史等问题的认识变化,也是我们理解思考西方文学经典的基本方式。
二.实行驻校作家制度有助于破解文学经典教育的现实难题
近年来,由于受到国外大学创意写作的深刻影响,上海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陆续开设创意写作专业,有效催生了驻校作家制度在中国大陆高校的落地生根。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聘任莫言、欧阳江河、苏童、西川、余华等为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延揽阎连科、刘震云、王家新等等为驻校作家,南京大学引进毕飞宇,复旦大学聘任王安忆,北京语言大学吸纳梁晓声等等。驻校作家制度在中国高校相继实施,许多专业作家有机会进驻大学校园,有助于破解文学教育改革的现实难题。实际上,文学教育的核心理念不仅是知识教育,还要培养人文主义情怀,写作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针对我国高校文学教育工作的真实现状,作为大学教育沟通互补、培养专门写作人才的一种创造性构想,驻校作家制度是一种柔性引进智力的全新探索模式,在繁荣校园文化和促进人文学科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来讲,国内大学驻校作家制度主要具有两种形式:一是长期聘任制,即高校把作家聘任为正式教师,作家的人事编制和档案也转到学校,平时正常开设课程讲学,或者招收研究生,需要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二是短期聘任制,就是高校聘请作家为兼职教授或指导教师,不定期进校讲课或开展与学生之间的文学交流活动。著名作家莫言说:“作家从封闭的书斋走出来,进入学校,设帐收徒,直接和年轻人打交道,会使自己年轻起来。在社会生活中,大学总是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端,与他们交往,肯定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保持锐气,必须不断地从外界汲取新鲜的东西。作家进入校园,对作家的写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学生的角度看,学生如果直接和作家打交道,听作家谈创作,也会获得许多从正儿八经的高校教师那里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作家进校园,对作家和对学生都是好事情。”[3]驻校作家制度不同于以往“作家讲堂”“文学论坛”之类的学术交流活动,而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活动内容更丰富、影响力较大的教育探索模式。“驻校作家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走形式,更不是让驻校作家为高校脸上贴金,而是要推动原有教育理念的变革、推动教育要素的结构性变化,使写作技能的培养成为一种习惯和机制,以此推动教育本身的变革。”[4]2013年5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正式成立,莫言担任中心主任。研究中心的重要职能是定期邀请国内重要作家或诗人担任驻校作家,具体从事文学交流、文学创作、文学教育、文学研究等多项工作。2012年,莫言获得世界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坛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一。作为一种国际性的荣誉奖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名副其实,也会带来诸多社会轰动效应。“我们慢慢汇集在莫言先生的精神感召下,在他这杆高高飘起的旗帜下面,已经吸收的十位驻校作家和诗人,他们都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大家的气息相聚在一起,生发出超越每一个个体的力量,最终生成了一种场域,一种氛围,一种精神。”[5]事实证明,驻校作家制度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落地生根,许多大学生的写作热情日益高涨,阅读兴趣逐渐增强,他们的文学作品集也相继出版问世。因此,驻校作家制度有利于活跃校园文化氛围,必然会对当下我国高校文学教育改革工作具有助推作用。
作为一所以理工科专业为主的高等院校,华中科技大学非常重视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教育,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关注。2012年3月31日,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并和湖北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喻家山文学论坛”,近年来,曾经邀请张炜、韩少功、苏童、贾平凹、毕飞宇、刘震云、王安忆、阿来、迟子建、格非、克莱齐奥等著名作家,以及张新颖、谢有顺、吴义勤、陈思和、张清华、丁帆、陈晓明等评论家进驻校园,主要采用授课、演讲、研讨、采风等交流方式。此时,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共同进驻高校,与广大师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交流,必将激活他们的研究兴趣和创作潜能,推动作家创作理念和创作方式的更新变化,也能够促进校园文化生态的整体提升。目前,华中科技大学“喻家山文学论坛”已经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文学批评盛宴。2015年4月12日,阿来和於可训、陈晓明、徐新建、王春林等评论家围绕着“秘闻与想象”主题展开互动交流,对阿来《空山三部曲》《格萨尔王》《瞻对》等作品进行研讨,认为“阿来的小说以特异而冷僻的题材、富有描述性的语言以及独特创造的文体吸引了众多读者”。作为“消散文明的打捞者”,无论是“土司制度的终结”,还是“终于融化的铁疙瘩”,阿来都以独特的跨文化视角为读者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旅行。我们知道,阿来早年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一举获得茅盾文学奖,在小说故事题材、语言风格、情节类型等方面都有独特贡献,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重要经典作家。2016年4月11日,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华中科技大学开始进行为期两周的驻校作家生活。期间,他不仅要给大学中文系学生上课,与广大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座谈,而且要在“喻家山文学论坛”进行文学演讲,之后,还将在武汉天地举行贾平凹作品朗诵和无主题对话。4月17日,贾平凹和著名评论家丁帆、吴义勤等共同参加“喻家山文学论坛”,他们以“浮躁与虚無”为题主要从三个层面对贾平凹小说展开研讨:一是关于贾平凹新世纪以来的创作成就、贾平凹的乡土写作、文体创新与传统文人文学之间的关系;二是关于当代文学创作和阅读出现的双重困境、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建构和当代文学叙事的深度论;三是关于贾平凹小说叙事伦理及其自觉的空间意识。《浮躁》《废都》《秦腔》《老生》《极花》《山本》等长篇小说,都是贾平凹贡献给中国当代文坛的代表性作品,具有地域性、民间性和民族性等鲜明特征,受到许多读者的共同赞誉。许多在校大学生和社会文艺青年热情高涨,积极参与研讨活动,他们不但亲自领略了经典作家的形象风采,也可以开阔文化视野,深入阅读经典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这就能够达到举办文学论坛的预期目标。
三.经常举办文学社团活动有利于文学经典的传播接受
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文人结社的优良传统,文人之间借助结社谈古论今,相互唱和,切磋学问,成为古代文人雅集的重要方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和“国故社”,清华大学的“游艺社”和“清华文学社”,南开大学的“新剧团”,西南联大的“南湖诗社”“新诗社”“南荒社”“冬青社”“文聚社”“文艺社”等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成为民国时期文学青年的精神家园。他们依靠文学社团广泛结交文友,相互交流心得体会,后来很多都成为声名显赫的文坛巨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北京大学的“五四”文学社、“我们”文学社、北大剧社、未名诗社,华东师大的“夏雨诗社”和“夏雨散文社”,复旦大学的复旦诗社,南开大学国学社、红学社、诗词楹联学会,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等等,都是影响深远的重要文学社团。2014年11月,为了在文学领域引领青年学生思想,服务青年学生成长,经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批准,决定成立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盟,并有全国学联秘书处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共同担任联盟指导单位。可以说,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盟在指导高校文学社团建设工作、培养文学新人、传递时代强音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
20世纪80年代,华东师大校园的文学社团林立,自由讨论的氛围浓厚,一大批大学生在文学社团活动中成就了青春梦想,比如,“夏雨诗社”“夏雨散文社”“散花社”“太阳河文学批评社”等等,都是深受华东师大学子青睐的文学社团。当时,华东师大中文系不仅汇聚着施蛰存、钱谷融、徐中玉等文学大家,而且赵丽宏、格非、陈丹燕、孙颙、王小鹰、宋琳、徐芳等一大批文学青年也在校学习。比如,在中文系读书期间,格非就积极参与“散花社”的文学社团活动,当时社团印有《散花》杂志专事刊发散文,格非担任杂志副主编,主要负责日常编辑工作。在平时阅读过程中,格非不但喜爱歌德、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托尔斯泰、福楼拜等西方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而且也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怀有浓厚兴趣,“在重读传统的过程中,他个人尤其喜爱明清之际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特别是《红楼梦》《金瓶梅》《镜花缘》《醒世姻缘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而对宋元以后的白话短篇小说并无太多好感。文言小说中他对《世说新语》,唐传奇中的《任氏传》《李娃传》,宋人的《错斩崔宁》以及《聊斋志异》”[6]之后,格非经常主动和文友们交流阅读体会,逐渐形成了志趣相投的文学圈子。“除在小组、座谈会、文人交往外,更多是朋友之间的清谈。清谈本来是华东师大的传统,《师大忆旧》的‘清谈篇中,忆及了与八十年代诸师友的交往。所谓‘清谈,不过是各路人马忙过了白昼的生计与写作之后,于夜晚幽灵般出没,找朋友聚会聊天,常常通宵达旦。却也大有龚自珍‘幽光狂慧复中宵的况味。陈村、姚霏、李劼、余华、苏童、北村、吴亮、程永新、孙甘露、宋琳、吴洪森等都是清谈的常客,这其中包括了很多在八十年代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所讨论的话题,除却文学之外,亦兼及哲学、宗教、音乐、思想史等等。”[7]可以说,正是这种自由开放和轻松愉快的文学氛围中,才成就了80年代“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显著成就。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华东师大作家群”可以说是文化环境和时代历史共同作用的结果,成为许多作家怀念和憧憬的光辉岁月。
总而言之,文学经典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文学经典作为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存在,凝聚着经典作家对时代历史、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等的独特思考,在培育人文精神素养和提升思想境界方面具有特殊价值。铁凝说:“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她却始终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复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8]因此,阅读文学经典是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自由宽松、平等开放的校园文化氛围对文学经典传播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提升青年学子的审美能力和精神品格,是他们实现茁壮健康成长的润滑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文学经典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具有互动共生关系,都是学校教育生活中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林建法、王尧:《小说家讲坛总序》,《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
[2]陈晓明、艾克拜尔·米吉提:《著名作家在北大的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3]莫言:《莫言对话新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4]舒晋瑜:《驻校作家制度能否推动大学教育变革》,《中华读书报》2017年5月10日.
[5]舒晋瑜:《驻校作家制度能否推动大学教育变革》,《中华读书报》2017年5月10日.
[6]褚云俠:《格非与华东师大——大学、读书与文人圈子》,《文艺争鸣》2019年第1期。
[7]褚云侠:《格非与华东师大——大学、读书与文人圈子》,《文艺争鸣》2019年第1期。
[8]赵艳:《文学·梦想·社会责任——铁凝自述》,《小说评论》2004年第1期。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G03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9M650936);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资助项目(2019GGJS156)
(作者介绍:禹权恒,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