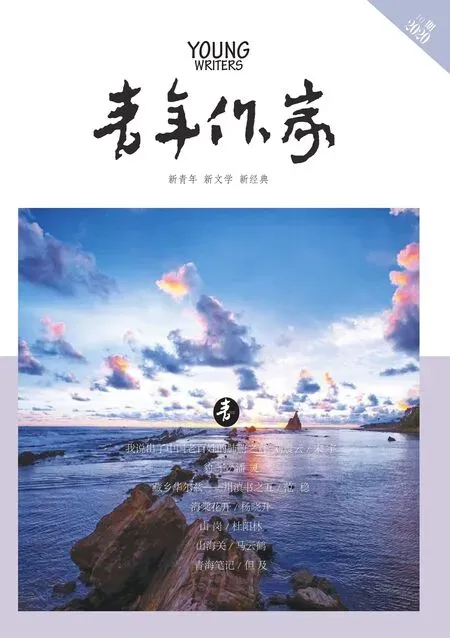让光开启暗夜和门扉
汗 漫
一
徐光启家宅周围的流水果实,汇聚成今天徐家汇的人流红灯。
四百年前,明文渊阁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在此地建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安葬在这里。后裔繁衍生息,周围渐成集镇,初名“徐家厍”,逐步成为上海市区中心。
早年的纵横河道,已被填充成密集道路——汽车、电车、行人、地铁这些事物,冒充浪花或深流,继续奔涌,安慰着长眠于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这个“睁开眼睛看西方的第一人”。“虹桥路”“漕溪路”“肇嘉浜路”“蒲汇塘路”“天钥桥路”等等路名,委婉泄露出这些道路与古代河流之间的裙带关系——明代小船上的裙子和衣带,已经隐含今天跑车内的薄袖春衫。对此,当代英雄与美妇不知不觉沉溺于徐家汇商圈现实主义的欢乐里。
徐光启当然没有来过徐家汇公园。
此地曾经为大中华橡胶厂,现在只保留下一个烟囱作为纪念标志——纪念工业时代的火焰与热息。公园周围道路上的汽车橡胶轮胎汹涌奔流,能不能使这个冷寂的烟囱,想起如烟往事?公园一角,有民国时期著名的百代公司小红楼,如红色大花朵,永远不会凋谢——它成为一座历史保护建筑。曾经出出进进小红楼灌制唱片的周璇、白光、李香兰们,已经演变成蜜蜂、花香、虫鸣?唱片般的月亮,升起在公园上空,试图重现三十年代的沙哑、委曲、柔情万端。
公园风景如画:人们练瑜伽,野餐,喂鱼,读书,接吻,拉手风琴,拍婚纱照,坐在婴儿车或轮椅里懵懵懂懂、昏昏欲睡……老少游客如画中人,自成一体,把明代徐光启的菜地、书房、后花园、河流,改变成悲喜交集之地。人生的起点、转折点、终点,隐秘交汇。草色、鸟叫、风、流水,尝试打破各种明确或隐性的边界,入耳入眼复入心。一个加速向晚年的中年人,需要练习在各种边界上探头探脑,而不遭到嘲笑、责备。那是一种对万事万物充满眷恋的探头探脑。
徐光启如果在墓地内失眠、醒来,应该对周围现代景象很欣慰——徐家汇教堂传递着福音,太平洋百货、汇金百货、东方商厦、港汇广场流通着中国制造的电视、电脑等等电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中学内讲授着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
在东西方之间左顾右盼,并决绝投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徐光启不是一个朽腐的抱残守缺者,对于用线香和沙漏计算光阴的流失,充满不安和痛感。他瞻前,在利玛窦的钟表所带来的西方蒸汽机般的广阔激动里,朝子孙、未知的方向焦虑、呼喊。
二
四百年前,大多数国人感觉身处中央之国,自己是完美的,异邦是荒芜的。
利玛窦历时八年,从葡萄牙出发,过好望角,经印度,于一五八三年来到中国。十八年后终于获准进入紫禁城。万历皇帝躲在垂放下来的帘子后,听完利玛窦唱的西洋歌曲,让他走了。留下一件作为礼物的钟表,在阴暗宫廷内滴滴答答奔走。
明朝推翻蒙古人的统治,依旧延续元朝创立的户口世袭制度:全国人口被划分成“军人”“农民”“工匠”三大类,再细分出若干类型。其中,工匠这一大类就细分出裁缝、木匠、船工、厨师……代代相传,不可更改,以此保持江山稳定感、人间秩序感。现在,钟表来了,万历皇帝开始考虑在“工匠”这一类人中,增加“钟表修理师”这一新称谓?
试图把中国皇帝改造为教徒的利玛窦失望了,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徐光启等等开明人士。
徐光启洗洗手上在漕溪或肇嘉浜附近菜地沾上的泥巴,推开几案上的四书五经:“中国自古不缺少闲散雅致之人,他们读经书,我就来做一个务实的俗人吧。”儒士打扮的利玛窦,每天来徐光启府邸,帮助他琢磨“角”“点”“线”“面”“平行线”“对角线”“相似形”“外切”等等西方概念的汉语对应词汇。汉语词汇表,在一天一天拓展、再造、丰富。
利玛窦怀疑,徐光启这个斯文白皙的中国文人是否有毅力有能力完成《几何原本》的翻译。一年后,清晰优美的汉字,在六卷本《几何原本》中实现了准确流畅的表达。利玛窦读后两眼满含泪水。“徐师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明史·徐光启传》)通过徐光启实现中国化的西方科学理论,散发出新光辉,照亮国人的世界观——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大海以外的地域,日新月异。
我们开始把时间看作三角直尺画出的射线、人类应当把握的射线、射向远方未知之地的光线。不再迷信于“无限轮回”的错觉,建立单行道一般的丧失感、紧迫感。“科学与工业技术,我们掌握物质世界的力量,以及这力量给予我们的自由,是古东方精英们之所以会对西方着迷的奥秘。人类,不再是星辰运转或业律的奴隶。”(帕斯《印度札记》)
正是徐光启,在中国确立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计时制度。也是他,反复尝试、琢磨工艺,把番薯引入江南地区,继而扩展向北方。在无穷晦暗的时代里,他用不息的爱意,负荷起一个知识者沉沉的责任:启蒙,图存,壮大华夏。
从徐光启开始,汉人们渐渐不再相信“天狗”一类虚无之物对天空、人心的占有,直起身来,看见并认清大海以外的世界。
三
徐光启身后约二百年,林则徐出现,被誉为第二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粗懂英语和葡萄牙语,组织翻译、印刷了大量西方著作。其核心思想,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师”与“制”,直到今天,仍是一个需要继续面对的问题。
出任江苏巡抚时,林则徐致力于疏浚太湖水系和运河,促进南方漕运业。徐家汇地区的漕溪、肇嘉浜、蒲汇塘,这三条溪流中挖出的淤泥,堆积成一方高地,被命名为“土山湾”。一八五〇年之后,此地逐渐建起教堂、孤儿院,前后有数千孤儿接受西式职业教育。中国近代工艺美术、建筑、雕刻、出版、印刷等领域,大都起步于土山湾。利玛窦们的著作,在这里被大量印刷,向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传播。
某一暮春下午,我进入徐家汇教堂。周围的漕溪、肇嘉浜、蒲汇塘,已成为红绿灯闪烁的道路。红灯冒充果实和花朵,绿灯向曾经的树叶致敬。教堂安静,一排排椅子上放有教徒常用的《圣经》,像学生们放学后留下课本的巨大教室。天窗上,彩色玻璃无比惊艳。玻璃上的天光与天使,像教具,在阐明天堂的壮丽。这些玻璃的制作工艺从法国引进,由土山湾孤儿们精心领会、磨制而成。天使高远,充满彩绘玻璃所赋予的美感和召唤力,俯瞰着我。
一九四七年秋,赵丹拍摄电影《丽人行》时,爱上影星黄宗英,多次进入这一教堂,祈祷那一个北平城里的女子早日来爱他。这一年冬,黄宗英坐轮船自天津出发,南下,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上岸。结婚后,风雨同舟三十载。赵丹似乎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需要一个载体寄托情怀,需要徐家汇教堂接受倾诉、分担心痛。
我也不是教徒,也非情种,于我而言,惟有写作能够安抚内心。低头面对白纸,与一个教徒、一个情种低头面对神灵祈祷,不论姿态与效果,都很相似。诗,就是语言之诗,就是祈祷词,并非只有物理形态的教堂与寺庙,才能让一个人获得信念和宁静。但徐家汇教堂天工与人工合作而成的壮丽景象,让我也感受到安慰和希望——
教堂尖顶处一抹光辉,酷似一艘沉船上方舷窗残余的天空。
四
漕溪路上有中餐馆“上海老站”。入内用餐,从壁上镜框中的旧照片,我认出这一清代保护建筑的前身:土山湾育婴堂。目前,天井里陈设有一节慈禧乘坐过的晚清火车,车厢和火车头,相互脱离,关系不好——几个花盆放在这两者之间掩饰尴尬。在晚清,一个中国女人向世界做出前进的姿态,却又原地不动。
当然,那节车厢,现在是一个小包房,可供四个食客垂帘用餐并谈天。
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一个事件:光绪皇帝准备学习英语。皇帝的这位老师,深感不安:“此何意也?”《纽约时报》知道这一事件的意义,登载消息并评价:“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希望未来大清国能立于世界强国之中,显示出的智慧和胆量令人钦佩。”
每隔一天,光绪皇帝就上一次英语课。此制度延续于末代皇帝溥仪。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使课堂上的英语诵读声日益局促、窘迫、游移不定。用英语向西方世界表达疑虑和拒绝?皇帝学英语、吃西餐,穿上西装让宫廷画师们描绘一种异域风情。公主们留洋学习交谊舞、芭蕾舞,回到紫禁城进行小范围演出。“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那些跳舞的人疯了”(尼采)。这是徐光启、利玛窦多年前没有预料到的景象。
在上海,清代末期兴起“洋泾浜英语”,其发明者是宁波少年穆炳元。定海陷入英国海军之手后,穆炳元接触英人、操习英语,自编教材以口诀形式传授于周围群众:“来是康母(come)去是狗(go),是叫噎死(yes)勿叫奴(no)……”后来,穆炳元成为上海滩宁波帮中第一个买办。懂外语的人,在当时被称为“通事”,他们游荡于商铺、酒家、茶楼、烟馆、妓院、剧场,促成华洋之间交易的洋泾浜通事,被称为“露天通事”。晚清,上海租界里的露天通事,从最初三十余人增加至二百余人,能掌握的单词约七百个。
一八六五年,江南制造局开设“广方言馆”,聘请数十位中外籍翻译员,采取“西译中述”方式工作。即,西人口译,华人再斟酌转化为文字,翻译出版《防海新论》《东方交涉记》《西国近事汇编》等等,深刻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广方言馆,“推广英语这一遥远的方言”,这一命名可见清廷之自大。此馆,亦可称为中国第一所外语专科学校,同时教授算学、代数、几何、重学、天文、地理、绘图等等课程,先后培养了六百余名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先后涌现出国务总理、驻外公使、实业家、报人、社会活动家等等时代翘楚。
语言史就是社会史、政治史、外交史、商贸史、经济史——就是人类史。
民国以后,通事或曰舌人,已经消失。
不知道徐光启的英文口语怎么样。
五
徐家汇商圈内淮海路、安顺路交叉口,原上海钢铁十厂的厂区,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之一。目前,此地转身成为“红坊”——一个艺术区。内涵上海雕塑艺术中心、民生美术馆、大地书店、乐泰咖啡馆、朵画廊……钢铁的腰身,在春风摇荡中剧变为杨柳腰,这是多么有难度的艺术。
新世纪以来,上海众多旧厂区纷纷摇身一变进入艺术领域,像商人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家。如上海第一服装厂(原荣氏面粉厂)成为“苏河现代艺术馆”,上海春明粗纺厂(最初的一信和纱厂、信和棉纺厂、上海第十二毛纺织厂)成为“莫干山路五十号”等等。一座以工业带动中国经济进步、文化更新的城市,在转型中让这些工厂摇身一变,冒充野外,但不可能也没必要回到徐光启所处的农业时代。
从梦想的工业化中国,进入后现代艺术之境,大约是徐光启那一代先行者所没有预料到的新现实。
在红坊,我看过英国雕塑家摩尔的雕塑作品展。露天陈列在厂房外的草地,那些铜黄、深灰、青绿的雕塑与环境相洽切,仿佛就是从这片工业废墟上生长出来的。摩尔,似乎就是这个钢铁厂的失业工人,转型成为雕塑家。那些雕塑作品中的人物,大都以斜卧姿态出现,仿佛是一脉斜卧的远山——女人乳房,男人膝盖,如同苍茫浑沌的丘陵,试图把这片厂区以及周围上海,恢复为节气分明的大自然?摩尔作品中的母子、国王、王后、战士,面孔模糊,姿态抽象。也许与野外经验有关——在野外,只能远远从一个人的身影而非面影,判断其身份与心境。他面向我们扬起双手,就是欢乐、激情四溢的人;他背对我们伏身,就是悲哀覆没的人。
在徐家汇,在上海,我对远处某人的扬手或伏身无动于衷。他可能是在扬手招呼出租车去约会,伏身拉动一个装满现金的旅行箱去交易。人体姿态的性质,与环境紧密相关。我学会不再关心街头的招手和俯身,密切关注红绿灯变幻和上司面部的阴晴。用艺术向野外致敬,用美来平衡上海的精神与资本,珍惜那些不断丧失、匮乏的万事万物。一代又一代人,永远处于追寻的旅途中,从徐光启到吾辈。所以痛苦,所以万象更新。
在红坊,上海钢铁十厂遗留的钢锭、齿轮、车床、铁锤等等工业废弃品,摆脱被遗弃而滋生出的重重锈迹与哀怨,再生为各种雕塑。那些异质斑驳的事物,在整合、拼贴中焕发出新能指、新所指。我,用西服领带附近皱纹重重的脸、手、躯体,隐秘表达中原泥土的气息和光辉?“将人体与风景交织在一起,正是我在雕塑中试图做到的。这暗示了人类与大地、山岭以及自然风光的内在关联。如果用诗意的语言描述,那么山峦的起伏正像羚羊那样轻快地一跃。雕塑,诗一样充满隐喻。”摩尔如是说。我也应该有能力与故乡风景交织在一起。
原上海钢铁十厂最大的一座厂房,被改造为民生美术馆,推出了一系列装置艺术展、摄影展、油画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诗歌来到美术馆”系列活动,策划者是诗人王寅。二〇一二年以来,相继有阿多尼斯、谷川俊太郎等诗人在这里交流、朗诵。王寅主持这一活动是合适的。我喜欢他《朗诵》一诗中的名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冬天里热爱一个诗人。”
二〇一四年霜降,冬天来临之前,朋友、新疆诗人沈苇来到上海,在这里朗诵了他的代表作《吐峪沟》——
峡谷中的村庄,山坡上是一片墓地
村庄一年年缩小,墓地一天天变大
村庄在低处,在浓荫中
墓地在高处,在烈日下
村民们在葡萄园中采摘、忙碌
当他们抬头时,就从死者那里获得
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
在艺术区、死去的工业区、仿生的野外,在一行诗面前,我也能获得俯视上海生活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从而目睹灵魂“像羚羊那样轻快地一跃”。
六
发轫于徐家汇的衡山路,向东北延展,穿越复兴西路、淮海西路、常熟路。一条著名的酒吧街。
我在衡山路一次又一次晃荡、唠叨,但不是衡山深处的僧人和大雁。没有诵经,也发不出雁叫。路边,咖啡馆、酒吧、时装店,假装是山中小寺或沙滩?一个以“生活在别处”为信条的上海人,如果想踮起脚尖向南飞,避寒取暖,参禅悟道,需要先还清当月银行贷款,再展开双臂,进入机场。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著名志士范仲淹怀抱士子之心,充满留意,不会逃避现实的冷峻。徐光启应该喜欢这一前辈,继承其著名的忧乐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所在的邓州,是我家乡一座小城。大学毕业后,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
徐家汇区域的道路呈密集射线状,像一盏灯,散发出射线状的光辉。光启公园一角,徐光启墓这一巨大圆形土丘,也酷似一盏灯,用坟墓上各种植物作为四季葱茏的光线,照亮无数从蒙昧中醒来的脸。这一个充满现代性的知识者,开启晚明尘封之门,让后来的中国得以看见那外部世界的光,正从门缝里使劲挤进来,迅猛扩张那光芒的领域——
光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