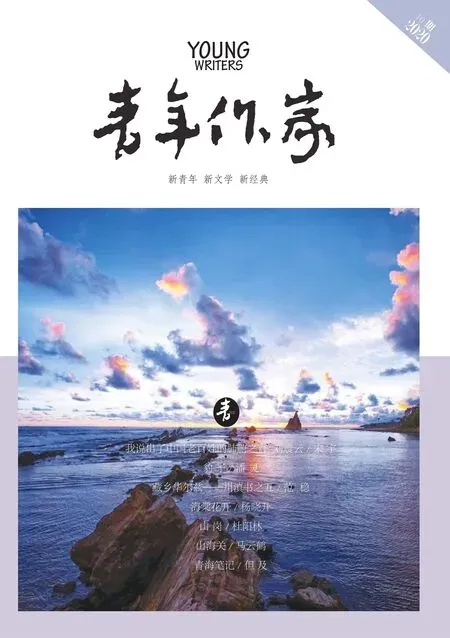园中葵
李 丽
落 葵
天响晴,一阵白雨后,天边垂下吸水虹,一头弯进山涧,一头悬着弯过山岗。晴天落白雨,光瀑倒泼,晴光潋滟好似有泠泠泻水声。群山鲜亮,惊得新雨蒸腾出一种茫茫远意。
木耳菜长得正盛,雨水一浇,清透干净,光看亦觉得饱,看来没少得母亲心思。木耳菜打了尖儿,矮叶贴着泥巴长,眼见长高指望不上,便琢磨往宽泛厚实里伸个自在。满叶漾着雨珠子,匀净又稳当,叶片湿泽,仿佛大雨打在池面拱起的水泡,那水泡却是悠然不破,一泡一泡铺陈开来。掐一叶菜,似乎便会动荡一池青水。
木耳菜,水灵且有朝气地长在《尔雅》中,里面说:“蔠葵,繁露也。一名承露,其叶最能承露,其子垂垂亦如缀露,故得露名。”掐尖儿后的木耳菜叶匹宽阔厚实,很能承接露水。晴天一早,朝阳没有照到的地方露水犹湿,叶子边缘起露朝叶心涓涓浸洇,白露青叶,只一眼便往葱郁里陷,满眼的水木清华。
木耳菜的叶和茎黏滑,嚼在嘴里打转,像盆里逮鱼,我不爱吃,但母亲喜欢。每回滚水煮挂面,总习惯掐几片丢锅里。面雪白,叶青秀,漂几星红油珠子,撒一撮绿葱花,泥巴里打滚的下里巴人,也要量裁着端一碗阳春白雪。
母亲从外婆手里接过菜园子,亦接过这样的吃法。外婆的生命得以分蘖,血脉从肉体延续到这片土地上,向死而生。
以往外婆叫它软浆叶,我也跟着叫。外婆扦立竹竿,牵引软浆叶抽出的藤蔓往白云高处攀。藤蔓不客气,叶片支棱,想蹿多高蹿多高,盘上架子逮着风头摇,颤一颤,颤两颤,实在够不着云朵,便憋着劲儿于青藤中梃出一串串籽实。藤蔓长壮,叶子才长得欢实而且多,外婆需要更多的叶子换来钱,填补苦日子。
我跟外婆傍着落日掐软浆叶,叶片阔大厚实,青心形。余晖从叶片上滑落,穿过叶隙滴在地上,洇开一团团柔黄。外婆掐一片摊在手心,再掐一片轻巧地往上盖,一叶一叶仔细叠摞,握满手心半卷了,挽上棕丝松松一系,青饺子似地排在竹筛里。高处够不着,外婆便倒扣背篼,我踩着背篼底儿掐。我够手掐高处,外婆低头掐矮地,茎叶间似有潺潺流水,一掐一汪水,一掐指尖一声脆响。余晖照着藤架,一墙的青。外婆叫我掐几叶便递给她,嫩叶娇气,攥不得多,也攥不得久,生怕汗手攥热叶片渍坏了青秀,失了卖相。外婆侍奉一菜一蔬皆是这样的小心翼翼,如同菩萨跟前供奉一香一烛的虔诚。
蝈蝈叫声潮起,远山远水地叫着。我和外婆只是掐,只是叠摞,面朝土地,谦恭地低下头来,拾捡起来的都是细嫩而滑溜的日子。
春菜,夏瓜,秋萝卜,一茬长一茬收。外婆一天到晚依附在锄头上,地里扯草、扶苗、搭瓜架、理瓜秧,掐叶摘瓜。菜地长菜蔬,也长草,长外婆的时间更多,一长就是好几十年。实际上地里的酢浆草、火炭草等杂草在外婆手里讨不着一口粮食,反倒把自己送进猪嘴,但它们依然喜欢往外婆的菜地里窜,如同我。夕阳斜过半山,外婆把影子丢给昨天,蛇蜕一般,蜕着蜕着就只剩得骨头。骨头也不安生歇几天,生怕草气盛,把自己给荒了。
乳瓜伏在瓜叶上好似初生,黄瓜刚落花蒂,红番茄,紫茄子,几刀细韭,一竹筛软浆叶搁在浅水边的石头上……山峦掐断光线,外婆在溪边淘洗各种瓜菜,溪流,人家,田野,远山,都在茶色烟霞里。菜蔬上的水滴溅湿石头上薄薄的暮色,恰如春水洇干土。临了,外婆淘洗塑料膜,清泉吸白纱那般,溪水里揉涮,斜晖里抖,一抖,彩霞满天。
远山上橘莹莹的暖色衬着暮霭,与人、与日色、与晚晴都有迟暮的归意,如淌在月光下的三五人家,有着实的安定。这份安定,生不起任何思远心思。黄昏衔着外婆,日子苍茫也具体,每每见着此景便生出亲蔼,这亲蔼娴静,抵得过世间一切动荡。
月亮瘦下来,像睡在窗台上的弯镰。秋阳下,万物都在柔情地老去,外婆日日料理菜园,仿佛不挪窝的老南瓜,直到身体长出暮气。软浆叶三月种,五月藤蔓延,八九月开珠花。珠花小巧细致,小小白花桃的模样。绛紫、雪青、桃粉,一串籽实上由老及嫩,次第变色,籽实串串累累,最上头一抹桃粉溶化在嫩梢,好似晚霞压黛山。乡下孩子有指甲花,还有软浆籽可以涂指甲。揪几粒紫珠果掐开肉瓣挤汁,把晚春的花事交付于一方窄窄的指甲。此后,缸里舀水尖着指头,喂猪喂鸡亦尖着,一整天便尖着十个指头不舍得洗衣淘米了。
渐渐起了露水,人声寂下去,独剩一目亮月。
落葵,是医书上的名字。里面说,落葵叶冷滑如葵,故得葵名。落葵花,落葵籽,全草叫落葵。
落葵籽不收。秋后的蚂蚱蹬腿就瘦二两肉,落葵青叶跟着败。回苗后,藤蔓日渐枯紧,外婆抽离竹竿褪下枯藤,收浆后的落葵籽如豆雨似地簌簌扑落,收都收不住。抽去的竹竿捆了,斜斜靠墙立着,避着风雨日头能使用好多年。
二年三月春信一送,外婆的锄头一口一口咬开泥巴,陈土一翻,新地气一咕嘟一咕嘟往上冒。好风好雨,来日锄头上挨着碰着的都是活泼的、水汪汪的一地新绿。
露 葵
外婆倒后,她的房子也疏了骨头,今年塌一匹椽,后年折一条檩。屋顶的瓦,承不住岁月薄凉,星月揭,霜雪蚀,三年五年,肋条把天都戳得漏雨。缺了瓦的房背,如同外婆豁牙的嘴,一齿一齿的黑洞静默向天,把风霜雨雪当做粮食来吞。也吞过路人的脚步声,只是这脚步声大多老了,轻得像猫,亦吃不饱,骨质越来越疏松。房屋一生顺从于外婆,安静地矗立,这借来的人世一程,流泪不是,言苦亦不是,都化作了垂暮中的摇摇晃晃。
外婆不见了,草开始寻她。起初只是翻过地坎,朝滴水檐沟蔓拢,尔后绕着房子踅摸,实在找不到便壮着肥胆爬房顶。楼上楼下空空落落,唯见荒凉坐在灶间,无火无烟。到底性子野,草有草的命力。巴地草破门潜入外婆生前的热土,试图讨要一把力量,即便仍是被撕拉离土,然而,没有然而……
菜也来寻,终是因为外婆一手一脚的豢养,菜们性子温软,跨不出菜地,就像一生走不出菜地的外婆。只一丛葵菜寻到墙根下,瘦得如同筷子,它倔强,执意不进屋。葵菜紫白的花朵亦皱亦舒,单层,单薄,花瓣娟娟,好似木槿蹙开,温柔得如同它和外婆的亲情。葵藿倾阳,葵菜守着外婆的遗泽,靠近外婆的房子就对了,没有其他想头。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我种在心地的葵菜拱出芽来。少年十五岁从军离乡,八十方回,如同眼下,剜心割肉。庭院长着野生的谷子,井坎上有野生的葵菜,野鸡乱飞,野兔也乱窜,少年动用六十五年的光阴换来一碗不知饴向谁的葵羹。旅谷、旅葵;少年、老者,蜷缩着,两千年前一指江山被压成薄薄的一页,不愿在历史中散去。历史的绳,那头系着老人,这头拴着我,中间千年山河的浩荡不减人世凄厉,百菜之王的语言都化成了这一株静默。
葵、藿、薤、韭、葱,古老的蔬菜,外婆都种。吃葵菜的人少,但仍种。外婆说,卖菜要有卖菜的样子,菜摊上多摆几样菜,青菜卖不得,萝卜总能卖几个。外婆种葵菜,大抵因为种一季能收好几茬。葵枝掐了发,发了掐,一茬一茬在日月里流转,好似岁月的无穷尽。外婆弯腰和葵菜细细商量,对话中的立春、雨水便从掐断的葵枝上叮当滚落。二茬三茬又把谷雨、小满青嫩地递到外婆手上,直到霜降后,薄霜下来,外婆和葵菜才暂时歇歇心。
葵园、薤垄、葱畦,一行一行,齐齐整整。我是独苗,单独划一块自留地,种在外婆屁股后头。外婆亦当我是种子,蔬菜和天气的谚语是我最早的养料。
“有露不掐葵,正午不翦韭。”“犁得深,耙得烂,一碗土,一碗面。”“人哄地皮,地皮就会哄你的肚皮。”外婆嘀咕给我听。
“蒜瓣栽进土,盖上干谷草。”外婆的话比蒜苗先在谷草间破土,“涝不死的葱,旱不死的蒜。”葱不怕水,蒜不怕干,外婆不怕苦。
家乡收割油菜籽、萝卜籽之类作物的过程特殊,名字亦好听——露。
油菜荚由青转黄,打上枇杷色便能割了。道上缝着人错身时,扛锄头的问,走哪里去?拿弯镰的答,李木坡的菜籽黄了,“露”菜籽去。菜籽秆割倒,不急着收籽往回背,就地一排一排顺序“露”在太阳下。油菜秆拽倒一笼笼打碗花藤,碗盏里的阳光全泼出来,混合油菜的金亮淌泻一山坡……镰刀饥饿,割破太阳,油菜秆一倒一大坡。汗珠子越落越密,滴在刀刃上溅出淬火的声音。
萝卜籽、白菜籽、葵菜籽,外婆皆如此收。连茎带秆割了,刀刃上听得见脆响,一排一排整齐“露”在地坎边,有时候倒挂在瓜架上。阳光正盛,地气朝天空云集,籽实在荚壳内收浆,干籽。大路上及人家户都静静的,有豆娘抿着翅落在荚壳上,尔后贴着青菜款款飞远。菜园安静,虫子皆噤了声响,太阳落落大方。日子好静,好长。
几个日头烤过,荚实一碰便会炸裂,外婆端簸箕揉葵籽。打油菜籽的木棍,打黄豆的连枷使不上,只能手揉,轻手轻脚地揉,即便揉碎葵秆,亦不觉得痛。饭粒沾到衣裳都得刨进嘴里的外婆,哪里舍得抛洒一颗种子,何况种子之后的无穷尽。外婆捧开荚壳碎秆,簸糠秕,簸稃皮儿,簸起半尺风,一场“夏雪”纷扬且轻巧地扑上了外婆乌黑的包头帕。簸干净的葵籽,如满心满意的日子,沉沉地攥在外婆手里。
芳菰精粺,霜蓄露葵,百菜、节气、秋水……外婆给我的种子。种子种在纸上,满记忆的阳光。它们出苗、打朵、结实……对比外婆一园子的瓜菜,我的文字亦是真真的葱绿可爱。这摸摸,那瞅瞅,也待他日生根出苗,也待他日放朵结实,只觉荚实日渐饱满,恰如外婆弯镰割葵籽,“露”在天地间。笔似镰刀,我亦割了,一排一排、一行一行“露”在纸上,随来的七月八月新好天气,新日头新亮月,便觉梦想不再水远山长。
向日葵
母亲端来葵花籽,年就在桌上。
喧阗在空气中炸裂如同葵花籽在舌尖嗑破,细碎、脆响,嗑出水煮和茶香。母亲说瓜子吃味多,但不如外婆自己晒的好。外婆的葵花籽里嗑得出太阳。
母亲拉拉杂杂絮叨着,外婆像一盘沉实饱满的向日葵,故事密挤,母亲抠下葵花籽,一一摊在我跟前,像晒簟上的谷子、玉米、葵花籽……
外婆种向日葵,但不吃。外婆不说葵花籽,亦不说瓜子,横竖说“舌儿粮”。“舌儿粮”——舌头尖上的口粮,不饱肚子,亦不饱胃,连打尖都算不上,只在年节下打发舌头使。“舌儿粮”同舌头上的长短话倒是喂饱了不少乡下农闲日子,这些日子散落在火炉边、树阴下,人们的心思变得缓慢。
霜,早于霜降之前落下来,浸透外婆的身体后,落成我生命里的雪。霜的白,是白雪的白,也是空白的白。
外婆将自己还原成葵花籽回归泥土的那年,地里空落落的。向日葵没人收,一片枯色,直到霜降,直到雪落。霜白铺开,肃杀之气贴地割倒一片青春。秫秆干巴紧瘦,葵饼低低鞠向地面,像失了主心骨。大片的霜白秋水似地荡开,葵饼、花萼、秆、叶子……三五十株皆是残荷色。
有葵盘断了,倒扣在地上,压倒一方茂草,葵秆单立,像一支支没有燃尽的香。外婆的骨头和体温已经被泥土分解,她的向日葵还骨立着。
我赶回来,伏在寿木沿上,外婆安静,屋子亦安静。寿木漆黑如葵花籽,装裹着外婆苍白的脸。一豆油灯点在脚后跟下,来世路上照亮的灯笼,一歪一歪地跳。我喊一声婆,外婆不应,想再喊,泪珠子先于喊声之前滚落。听说亲人的泪不可滴在亡人脸上,会成为下一世的泪痣。其实我知道,我们已经不再是亲人,外婆断舍这片土地后,便不肯再认我。地里未来得及收的向日葵、庄稼、菜园、河流山川、土地以及人世间,外婆都已不再相认。
黑衣裳、黑裤子,裹着黑色包头帕的外婆砍倒葵秆掰葵饼。地里,向日葵亦是低头,盘面向下。只觉外婆和向日葵是砖墙上贴旧了的画像,人物和背景如同民国。
这些留着,等过年给客吃。外婆的话随向日葵一同倾倒,雨点似的,刚落地,很快被泥巴抓吞。外婆嘴里的客,是她四处安家的子女。每年过年,那些远客洄游老屋,好似蒲公英从四处聚拢成伞塔。
我伸手掰葵饼,岁月的手也伸将过来往外婆身上压岁数,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岁数越是重,身体打桩似地越是往土里錾,外婆露在地面上的日子不及一截楔子长。气力都剥给了土地,剩一副枯槁架子的外婆,如同被抠净葵花籽的蜂窝状葵饼。土长庄稼,在奉送籽实后回苗,土地亦开始吞吃日渐枯萎的外婆。
外婆掰一饼抛给我。我坐在锄把儿上,一门心思对付。抠,刨,一粒一粒认真剥开捏了瓜仁递嘴里门牙切着吃。新鲜的葵花籽栽立于葵盘,皮软,仁是一泡浆汁。瓜仁嫩甜,清口。有时候连皮儿带仁扔嘴里“推磨”,吐渣。外婆便说,哪有这样的吃法,太糟踏,小人要爱惜粮食好生吃。我便好生剥了吃。外婆不吃葵花籽,不吃茶,亦不喊累。累得打鼓,也只是开水冲白砂糖,沉积在骨头上的苦和累,慢慢煨化于一盅糖开水中。外婆疏叶子,我抠葵花籽,阳光一绺一绺地穿过葵林……
外婆说,土吃进嘴巴,人就不中用了。
去年掰葵饼时外婆说,土埋到下巴了。前年外婆背一背篼葵饼往家走,一路走一路喘,像闷湿天气出水换气的池鱼,在歇气台上悠悠地嘘一口气后顿顿,说,土堆到心口了。
蛇床子凌晨三点开花。牵牛花凌晨四点开。清晨六点是龙葵……外婆瞥一眼向日葵朝向就能掐准时间的七寸。外婆活成植物,以植物开花来估摸时间,大致不差。晚饭花朝天吹喇叭,下午五点。月见草,夏夜八点开,外婆叫它“八点半”。月见草开花,单层,四瓣,柠檬黄,花瓣匀速旋开,地气上升舒平褶皱,抖落出一枚枚干净的月华。
外婆的向日葵年年挨着房子种,开门就望得见。七八月花开,一片灿然。外婆领我去向日葵地,路上有知了叫,新谷子新玉米,唯外婆是旧色,那旧里有一种贞亲和安宁。
太阳底下,葵花开势宏阔,花事烂漫到难管难收却依然简静。葵盘上缎黄的裙瓣翼动,面向南日追,如同我的小时候,追外婆的小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