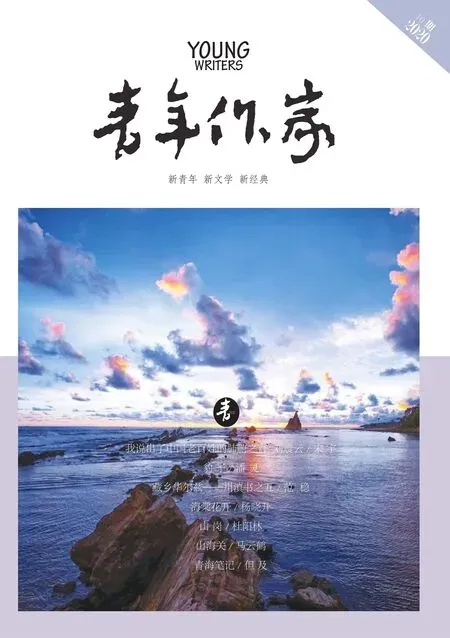藏乡华尔兹
—— 川滇书之五
范 稳
一
说到藏族歌舞,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最熟悉的莫过于那首《洗衣歌》。那欢快的旋律、鲜艳的藏族服装和带有浓郁藏族特色的舞蹈,至今犹在眼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可看的歌舞少得可怜,每当有文艺晚会,我们一帮小屁孩总会偷偷溜到后台看演员们化装、搬道具啥的。在不是穿红卫兵服装、灰色中山装就是穿阴丹蓝小翻领列宁装的演员中,忽然有一群身着白衣长袖、系五彩围裙、头上戴着色彩缤纷发带和五颜六色塑料珠子的姑娘飘然而至,整个后台顿时为之一亮。要跳《洗衣歌》了,大人们侧目而视,孩子们欢呼雀跃。节奏明快的旋律骤然响起——“呃,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姑娘们黑发飘荡、长袖翻飞,用彩纸粘在一块布上的围裙哗哗啦啦、色彩斑斓,直看得人眼花缭乱、心旌摇荡。在童年的印象中,藏族舞蹈就像外国舞蹈一样令人新鲜好奇,充满异域风情,尽管我们能看到的,不过是一些县级文工团甚至公社宣传队跳的《洗衣歌》。那年月,稍大一点的单位、学校都有宣传队,都可以跳《洗衣歌》,它似乎就是一台晚会的高潮,或者压轴。多年来《洗衣歌》就像一部老电影中的经典片段,在岁月的长河中闪闪烁烁,令人怀想。有一次,听韩红翻唱的《洗衣歌》,顿时就如喝到一杯老窖一样甘醇绵厚了。
或许,这就是藏传佛教所说的某种“缘起”吧。多年以后,我在广袤的藏区游荡,才发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凡有藏族人的地方就有歌舞,凡有歌舞的藏区就有藏族人。我曾经在我的作品《水乳大地》中借助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口说,藏族人把人生简化为三件事:干活、信教、娱乐。他们把身体的需要交给劳动,精神的需求交给信仰,其余空闲下来的时光,则全部交给了唱歌、跳舞、喝酒和谈情说爱。
我见识过最华美的藏族歌舞,从服饰、音乐、灯光、舞美、音响到演员阵容和编导创意,绝对堪称一流水准;我也欣赏过各种流派的藏族舞蹈,如弦子、锅庄、踢踏舞、热巴舞等,以及寺庙里祭祀性的宗教舞蹈“羌姆”,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跳神”。我曾在川滇接合部的一座宁玛派寺庙东旺寺参加过一次为时三天的“跳神”大法会,法会就在东旺寺措钦大殿前的广场举行,四乡八邻的藏族群众围满了广场四周,喇嘛们是当仁不让的舞者。他们戴着面具,身着法衣,击打着各式法器,跳着神灵凌空蹈虚的舞步,既仿佛神魂附体,又彰显人神共娱。如代表神灵降临的“法神舞”“凶神舞”“金刚神舞”,表现地狱中小精灵们与死神共舞的“骷髅舞”,为人间带来福禄的“鹿神舞”,宣扬乐善好施、长命富贵的“寿星舞”“仙鹤舞”,以及表演佛经经典故事的“舍身饲虎”“因果报应”等舞蹈。喇嘛们的舞蹈没有歌唱,只有钹、擦、法鼓等敲打得哐哐当当,大小法号吹奏得时而浑厚低沉,时而尖锐刺耳。人借神鬼舞蹈,神鬼则以拟人化身。整场跳神大法会既肃穆庄严,又让人心生敬畏,甚至不知今夕何夕、今世何世矣。
不过,若说到藏族歌舞中人与信仰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世俗生活的关系,最具吸引力的还是在藏民族中广为流传的民间自娱性舞蹈。它们就像漫山遍野盛开的野花,也灿若天上的繁星。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独树一帜的藏舞流派,每一户藏家,都有身怀绝技的舞者。
二
在迪庆藏区,我的生活基地汤满村所在的尼西乡是个歌舞之乡,有名的尼西情舞就源自于这一带。“情舞”在藏族舞蹈类别中比较小众,大体属于锅庄的一个分支。锅庄在藏语里称为“果卓”,是其汉语谐音。锅庄起源于古代藏民围绕篝火或室内火塘进行的一种自娱性的歌舞,进而延伸到普罗大众。我刚到汤满时,听人们说到尼西情舞,还以为这是一种关于爱情的舞蹈。民族地区,对爱情的表白大胆直白,无论是歌曲还是舞蹈,大多原始野性、简洁舒展,仿佛自然之子在舞蹈与歌唱,而尼西情舞,其实也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地人称情舞为“降鲁窗”或“卓昌”。“卓”一般泛指“表演性的圆圈歌舞”,即舞者围成一圈歌唱舞蹈。尼西情舞融合了锅庄和弦子舞的内容,但又有自己独特的舞蹈风格。它改变了锅庄中的弯腰动作,加入了许多腿部腾挪踢脚的舞步,使之比锅庄更欢快、奔放、野性,同时队形变化也更丰富。
以汤满村情舞为主要代表,尼西乡各村都有自成特色的情舞,歌词大体一样,但声调不同,汤满的声调大都拉得长一些,这需要更深厚的底气,更高亢的嗓子。不过这似乎并不成为一个难题,人们形容这里的人们“会说话的都能唱歌,会走路的都能跳舞。”从七八十岁的老者到十几岁的少男少女,都是情舞的乡间舞蹈者。
是谁最先发明了这种舞蹈现在已经无可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藏族人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人类一切艺术形式的起源莫不如是。在乡间,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一些伟大的民间艺术家。他们也许是秉天地之灵气,也许是受文化传统之浸染,他们是真正的民间艺人、是大地的舞者,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也舞蹈着歌唱着最底层的社会生活现实。因此它被整个社会大众所接受和喜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我们所受的教育和身处的文化背景使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认知仅限于象牙之塔里的某些艺术形式。我们可能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学钢琴、学小提琴,在学校的音乐课里学一些普通的乐理常识。可是乡村的孩子却是在大地上学习民间传承下来的舞蹈和歌曲,这是他们成长的一个过程,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在汤满村走访时随便碰上某个老人家,闲聊时问年轻时是否也跳过情舞,旁边的朋友便会说,他(她)么,是我们村里的情舞老师呢,我们从小都是跟着他们的舞步学会跳情舞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年纪越大的人,掌握的情舞曲调就越多,会跳的舞步也越丰富。
我在汤满村下属的一个叫汤浪顶的小自然村遇到一个叫七林培楚的中年人,人们介绍说他的尼西情舞跳得特别好,是汤满村的情舞王子。可我第一眼看到他时,怎么也不能把他和一个舞蹈者联系起来。他个子不高,身体粗壮,一脸朴实,是地道的庄稼汉,和一个“王子”的气质相差甚远。可是陪我去的朋友说他跳情舞厉害着哩,我们都跳不过他。说话这人是个长相英俊的康巴小伙子,身高一米八六左右,是我在汤满村的好兄弟,依我看来,这年轻人才更适合担当情舞王子的角色。他从前曾经开过大卡车,热情豪爽,嗓音嘹亮,高歌一曲时,让你真羡慕他那仿佛是神灵赐予的金嗓子,穿上节日盛装跳情舞那才叫一个帅呆了。巍峨的狐皮帽、镶豹皮的华丽楚巴、软皮高腰藏靴,再佩上各种胸饰和腰饰、漂亮的腰刀,潇洒得一塌糊涂,场上姑娘们的目光全被他夺走了。
但他却坚称自己还不能算是情舞王子。他说,七林培楚是。我想,“老王子”也许更练达,更炉火纯青。他们对王子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坐在七林培楚家的火塘边闲聊,请他介绍尼西情舞的特点。他一开始有些拘谨,但聊着聊着,话就多了起来。他说这里每到春节前后,人们都要唱歌跳舞。唱歌是峡谷两岸的三个村庄互相赛唱,一个村庄起了头,山对面的村庄立即应和,其他的村庄也跟上来唱,几个村庄隔着山谷轮流高唱,互相比赛,直唱得日月无光、山川失色。
我们知道汤满村位于一条山谷里,山谷的两边还有三个小自然村,隔一条汤满河遥遥相望,河南边的是汤浪顶村和布苏村,河北边的是肯古村和汤满村。山谷两边相距最近处少说也有三四华里地。人们唱歌要让对岸的人听明白,这山唱来那山应,没有一副高亢嘹亮的嗓子是不行的。在乡村里这样的金嗓子似乎浑然天成,不加雕琢。藏族汉子或姑娘放歌一曲,划破长空,响遏行云。当我第一次听李娜的《青藏高原》时,真为那嘹亮激越的嗓音所感动,认为那嗓子是上帝赐予的。可是我在藏区跑久了以后,发现能和李娜的嗓子媲美的人多的是,只是他们都隐没在乡间的大舞台上,历史没有给他们在城市的舞台追光灯下一展歌喉的机会。
山歌唱完了,便要跳舞啦。先是各村庄的人自己跳。大年初一的早上,汤浪顶村的人们开始跳锅庄。人们按自家房屋在村里所处的位置分为上下两个片区的舞蹈队,每一个舞蹈队的人都由各家各户出,有的一人,有的多人。上片的到下片的人家跳,下片的也到上片的人家跳,每家每户都要跳到,不论贫富,不分亲仇,人们在这一天尽情地娱乐高兴。到家里跳锅庄要把主人家客厅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唱到,从火塘开始唱,然后唱到铁锅、三角架、灶膛,再唱到经堂、佛像、中柱、地板等,见到什么吉祥的东西都要高歌一曲。都是溢美吉祥之词,极富文学色彩。主人家一般都煮有一大锅稀饭,里面有一个猪肚,以给来跳舞的人吃,当然还有其他零食,瓜子香烟、烙饼糖果等等。这样的锅庄一般要跳到天黑以后,村庄才会安静下来。
我想,这相似于一次集体拜年,只不过是以歌舞的形式。令人感叹的是,这种形式充满了人情味和艺术化,村庄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既欢度新年,又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曾经有过矛盾的人家,此刻互相走到一起,同唱一支歌,合跳一曲舞,还有什么恩怨在这浓浓的乡情中不能化解的呢?
我想起了我们的新年,——噢,在藏区我总是把所见到的和我们汉族人所经历的相比较,这就是文化差异使然吧。新年里我们到朋友亲戚家串门,也只能说几句“拜年了”之类毫无特色的话,然后给小孩子们散发压岁钱,对孩子们来说那是过年最让他们激动的事情。在这个网络化统领一切的时代,我们把传统的拜年简化得更彻底,在手机上发条微信,道一声“春节快乐”,我们便觉得该尽的情义完成了,压岁钱也通过微信红包的形式发。我们要恭贺的对象连我们的面甚至连我们的声音都见不到、听不到。
我们可否在新年里为主人唱一支歌、跳一曲舞?我们可否在新年的第一天,一大早起来就怀揣着一份美好的期盼,把火塘烧得旺旺的,准备好最醇香的美酒,恭候一村庄的朋友来家里做客?不,我们汉族人不擅长这个,我们也没有候客的火塘,或许我们早就忘了这些最人情化的东西。我们的热闹可能在别的地方,我们会驾车出门旅行,会和朋友一起“砌长城”,会找个地方去轻松休闲等等。可是它有多少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呢?我们能找到多少过年团圆的滋味,找到那份一年中家人和睦、朋友亲戚之间难得的温情呢?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过年没有年味了?因为我们的春节已然没有文化内涵了。
那天,我曾经诚恳地邀请七林培楚当场为我们表演一段情舞,我想见识一下这位情舞“老王子”的风采。但是遭到了七林培楚的婉拒,他总是扯三道四,就是不肯站到屋子中央一展舞技。我那时怀疑他是否老了,再也跳不出像风一样流畅自如的情舞了。从他家出来后,同去的人才告诉我说:“大哥你真会难为人家,培楚怎么可以在家里当着自己的儿子、儿媳妇跳情舞?我们藏族人跳情舞非常讲究辈分和长幼,同辈的人才邀请对方跳,不同辈的人是绝不可以跳情舞的。”甚至连同一个村庄的人都不能在一起跳情舞,因为村里到处都是自己的表姊表妹、叔伯兄长,情舞更不能当着自己的长辈跳,情舞的调子年轻人在家里连哼都不能哼。
这么多讲究,哪里还有什么浪漫可言?我把情舞理解得太庸俗了。这人说,情舞绝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随便。情舞分为三大类,分别叫做“擦沾”“擦中”和“擦喜”,前两类是在婚嫁时跳的,这种情舞男女老少都可参加,歌词内容多为祝福、恭喜之类的吉祥话语;“擦喜”才是年轻男女谈情说爱时跳的舞蹈,或者按我们的理解,是真正的有情而跳、有感而唱的爱情之舞。
他还告诉我说,藏族人其实是很内向、传统的,年轻人跳“擦喜”情舞时,人们要先唱一首歌《叶勒循儒》,意为请老人家和小孩进家去,我们年轻人要在一起跳情舞了。
到这时我才弄明白,尼西的情舞比我想象的要严肃规矩得多,甚至到了刻板的地步,人们要跳情舞一般都是到外村去邀约伙伴跳。大年初七,汤满各个村庄的年轻人会聚集在一个叫“臭水”的地方互相跳舞。那是几个村庄的年轻人新年里第一次聚会,那时真正的情舞才开场,许多年轻人在这个情舞聚会里将会找到自己的意中人,也有一些情舞高手,将在这一天奠定自己情舞王子的地位。
据说从前,年轻人打着火把,借着月亮和星光,走上一二十里路,然后跳个通宵达旦。他们以星星和月亮与大山的位置来看时间,主要以天上的六颗星和启明星为准。还有以鸡叫——此地鸡叫一般为三点——来掐算早晚。到启明星升起来了,鸡也叫了,跳情舞的姑娘小伙子们也该回家啦。他们悄悄地摸进家门,悄悄地钻进被窝,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其实他们的父母早就明白儿女们干的事儿啦,毕竟他们也曾经年轻过。年轻人也不愿意说给父母听。这是一种害羞心理呢还是一种习俗?我不明白。
这才是情舞里真正的浪漫,令人感动的纯朴和执着。走几十里山路,跳一曲舞,再走几十里地回来,你有这种勇气和浪漫吗?
年轻人在一起跳情舞肯定要跳出许多爱情故事出来,以前男女谈恋爱多以跳情舞为交际手段。如果“跳”回来的媳妇或女婿双方父母都满意那就皆大欢喜,要是遇到阻碍,年轻人自然也会有办法,没有爱情过不去的坎。
此地有过一种“偷媳妇”的风俗,男女双方在跳情舞时结下感情,假若女方的父母又不同意,小伙子便会将姑娘偷偷带回家里,藏在家中的青稞柜里,一直藏到女方家来找为止。为什么要藏在青稞柜里而不藏在其他地方呢?这有其象征意义,儿媳妇过了门,定然是要下厨房天天和青稞柜打交道的。藏族说法,儿媳已经进了我家的青稞柜了,她就是属于我家的人了。即便女方家硬要将女儿领回去,姑娘也会逃回来,因为她毕竟是进了人家青稞柜的人了啊。这就是我们汉族人说的生米煮成了熟饭,你能怎么办?
不过,我们不能完全以汉族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意义非凡的“青稞柜”。男女双方在未正式举办婚礼前,不能做出过分的事情。有的男女青年由于某一方的父母不首肯,双方在一起的时间太长,非但没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反而成了兄妹。既然不能结婚,大家还在一个屋檐下,就以兄妹相处也罢,这就挺让我费解了,可这就是村庄里的实事。
像和我一起的这样小伙子,长得仪表堂堂,高大魁梧,典型的康巴汉子气质,人又聪明活络,见多识广。城里人玩的时尚,没有他不会的。他用的手机比我的款式新,他穿的衣服大都很时尚,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没有人会认为他来自乡村。小伙子属于那种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地里的农活基本不做,或者不会做,交给家里人打理就够了,自己在外面做一点小生意,手中钱多时花钱如流水,钱少的时候也同样不少吃喝,日子过得好像比我还潇洒超前。我和他在一起喝酒聊天,常常在他劝你酒的时候,嘴里便会蹦出一句“名言”:“酒嘛,水嘛,粮食(做的)嘛,喝嘛;烟嘛,草嘛,烧嘛;钱嘛,纸嘛,花嘛。”这段“名言”我一听到就乐,头就大,就犯晕,就醉得一塌糊涂。他看上去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是一个和村庄里那些谨守本份、纯朴厚道的藏族人大相迥异的人。可是他的媳妇却不是情舞场上跳来的,是父母在他十四岁时就帮他订下的,他遵从父命,娶妻生子。尽管说到他家乡的情舞,他的那种自豪,他的那份热心,常常会令你感动。这位老弟还是汤满村情舞队的队长。他的爱情故事让我有些失望。
三
好了,关于情舞及它的过去我已讲了那么多,现在就让我们去亲身感受一次尼西情舞吧。
我参加的情舞是人们在婚礼上跳的,在这场为时三天的婚礼中,跳情舞也是仪式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跳情舞,来宾们怎么能尽兴呢?
婚礼的第一天,人们吃完晚饭后,身着节日盛装,纷纷来到村庄外面的一块空地上,在一块比较平缓的青稞地上燃起了几大堆篝火,这并不是一块平地,它是山脚下一块种青稞的斜坡地。冬天里这地闲着,离主人家也近,于是就成了婚礼上人们跳舞的地方。
跳舞之前仍然有一首歌作为前奏曲。人们围成一个大圆圈,来自两个村庄的男女各自排成队,男队在前,女队在后,围着篝火绕圈。人们从对歌开始,很自然地就进入一种竞技状态。第一支歌大多由男方家来的宾客主动唱,大意为邀请女方家来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一方唱两段,歌词不外乎是诚恳热情的邀请和谦虚礼貌的答谢。这时的舞蹈很舒缓,动作幅度不大。双方的男队都显得很矜持,女队也表现得很端庄。如果换个场景,假如是在哥特式建筑的大厅里,你会感到这是一群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们在跳华尔兹。此时跳的舞属于古典情舞,是“擦沾”和“擦中”类的情舞,歌词也很难翻译,相当于我们汉语中的文言文。我请我的藏族朋友帮我翻译,可是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抓耳挠腮了半天,只能遗憾地对我说,歌词太深啦,我们可以用藏语唱出来,但说成汉语,就说不好啦。我知道藏语里有一些古词汇是很艰深拗口的,只有寺庙里的那些高僧才能弄懂它们的含义。这有些像我们的古文,没有受过古汉语教育的人,面对那些方块字,也同样抓耳挠腮、一筹莫展。
一个在迪庆州歌舞团担任编导的藏族朋友告诉我,藏族舞蹈的基本动作可分为“颤”“开”“顺”“左”“绕”这五大元素,从而构成了它区别于其他兄弟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藏族舞蹈的步伐非常重要,且内容丰富,从脚部动作上可概括为“蹭” “拖”“踏”“蹉”“点”“掖”“踹” “刨”“踢”“吸”“跨”“扭”十二种基本步伐。藏族舞蹈的手势也很讲究,可归纳成“拉”“悠”“甩”“绕”“推”“升”“扬”七种变化。噢,这里面学问深着哩,哪有我们儿时看一曲《洗衣歌》那么简单!
需要说明的是,尼西情舞和藏族锅庄、弦子舞是有区别的。舞蹈步伐不一样,人们形容跳尼西情舞是“顺手顺脚”,即挥左手踢左脚,舞右手迈右脚。因此它比一般的锅庄要难学得多。我曾经试着学跳,但怎么跳怎么别扭,那笨手笨脚的模样引得周围的藏族朋友大笑不已。而他们跳起来却是那样流畅舒展,腾挪自如。况且我还不熟悉情舞的调子,老是踩不到节拍上,人家抬左脚了,我还高举起右脚,人家转圈了,我则傻站在那里找不着北。看藏族人跳舞是一种享受,而和他们共舞,我们就丑态百出了。
尼西情舞和锅庄、弦子舞的曲调歌词也各不相同,弦子舞还有人拉弦子,人们合着弦子的旋律跳。尼西情舞一般没有乐器,全靠人们现场演唱。而且它是一种对唱形式的舞蹈,具有一定的竞赛性质。跳情舞时人们分成两队,一唱一答,边唱边跳,若是某一方唱不下去了,或者跳不动了,则为输家,输的是个人的面子、村庄的荣誉,或者输的是某个心上人一颗暗恋的心。我们都知道,舞跳得最流畅舒展、歌唱得最嘹亮婉转的人,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明星,他(她)将被所有温热的目光所追逐,被所有温柔的心所疼爱。不论是在都市还是在乡村,人们对明星的感情和爱其实是一样的。
据说人们在跳情舞时为了不输给对方,有时除了吃饭的时间,一跳就是三天三夜,连觉都不睡。有的男人一直跳到尿血了,还不肯下场。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这些跳情舞的舞者,我想或许舞蹈在此时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愉悦自己和他人,舞蹈成了生命力量的一种证明。当一个真正的男人需要证明生命的价值时,他可以不怜惜生命。
我曾经有一次和小伙子一起在村庄里喝酒,大家都喝醉了。小伙子非要拉着我跳情舞,我们两人一边,和另外的几个小伙子对跳。可是由于我不会,又醉得步履踉跄,因此我们跳输了。这本来是一次醉酒的游戏——至少我是这样看的,可没有想到小伙子这家伙当真了,把我骂得狗血喷头。那晚上我们大干了一架,差点没有动刀子。我被小伙子骂得实在无地自容了,便仗着酒胆喊:“不就是跳曲舞吗?输了就输了,不服气你就来捅我一刀。”小伙子还在那边大叫大嚷,真的要去找刀子。好在那天还有几个家伙没喝够,他们把小伙子拉开了。
这事情过去好久了,小伙子提起来都还耿耿于怀,说我不中用,丢了他的面子。
因此,在情舞场上跳舞的人们与其说是在参加一场娱乐或游戏,不如说这是一个人生的竞技场,是人们证明自己才华与激情的大好时机。你想想吧,平常的日子里,大家都要为生计操劳,而且是辛苦异常地操劳——地里的庄稼要伺候,山上放养的牲畜要操心,家里的油盐柴米要谋划,活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现在你看看吧,欢乐的时刻到了,忘掉一切烦恼的时刻来临了,证明自己歌舞才华的机会来了。康巴的姑娘和小伙子站到了大地的舞台上,他们是在天地间表演自己的天赋。他们跳给神山看,跳给朋友们看,当然更是跳给心仪的姑娘看。
那天晚上,古典情舞跳了几圈后,已是十一点左右。这时人们唱起了《叶勒循儒》,刚才一直保持队形不变的那个大圆圈开始散开了,有性急的小伙子打起了欢快的口哨。我身边的藏族朋友说:“现在是我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我发现场上的老人纷纷撤了,新郎和新娘也收起行装,被他们的家人簇拥回家去了。按我们汉族的规矩,现在是人们闹洞房的时候。可在村庄里没有这一说,年轻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跳他们自己的情舞。一眨眼,场上就形成了三四个小圆圈,年轻人三五成团,男女分行对阵,开始跳“擦喜”情舞啦。这个时候,舞场上的情绪一下轻松活泼起来,舞蹈动作幅度也更大更快。唱出的曲调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婉转缠绵。跺脚,甩袖,转身,踢腿,人人都似舞林高手、情舞王子或情舞公主;人人的身姿都显得那样轻盈舒展,灵巧机敏。舞场上长袖飞舞,裙裾招展。舞步快到不能再快,身躯旋转有如陀螺。挥手踢脚之间,尘土飞扬,歌舞洞天。人人仿佛就要飘离大地,舞到星星月亮上去了。年轻人不再拘谨、刻板,欢声笑语融化了浓浓的夜色。遗憾的是,我听不懂藏语歌词,据介绍说一些歌词会很含蓄、寓意深刻;而一些胆大的年轻人会唱出些比较直截了当的歌词,具有很强的挑逗意味。浪漫的情调在歌舞声中愈发浓郁,以至于我都可以看到火光下姑娘们羞涩的笑脸和听到小伙子们爽朗的笑声。
这个时候是一场真正的乡村舞蹈大赛,每个小圈子里跳的舞步和唱的歌词都不一样,人们现编歌词现跳舞,使出浑身解数和对方一跳高低。一曲未了,一曲又起,天知道他们肚子里有多少支情舞调子,天知道他们一身的激情要什么时候才释放得完。
但是,我必须特别要说明的是:尽管情舞场上的年轻男女跳得激情四射,他们却连手都不会触碰到一下,更不用说身体其他部位的触碰了。
这些大地上的舞者让我忽然想起城里人跳的华尔滋,尽管两者间的舞姿是多么不一样,它们产生的土壤和代表的文化内涵也各不相同,可是我总觉得它们有着许多异曲同工的地方。来自于民间,却又典雅传统,普及于大众,却又高贵浪漫。华丽的服饰,奔放的激情,优雅的舞姿,考究的舞步,激烈的对抗。要是有人来操办像华尔滋大赛那样的情舞比赛,我相信尼西的情舞也可以为大众喜闻乐见,也可以走进大雅之堂,甚至还能走出国门。实际上,迪庆地区已经有好几支藏族民间舞蹈队,受东南亚几个国家的邀请,前去访问演出过了。
天上已是繁星满天,一些星星一眨一眨的,似乎它们也累了,可大地上的舞者一点也不累,他们跳得正欢呢。我呆到凌晨一点多钟,除了看热闹,什么都不会,但仅作为一个看客,我已经累不动了。到我回去时爬到一座山岗上,回首望去,山坡下的篝火在浓厚的夜空中闪耀,像黑夜之心在跳动。还有随风飘过来的歌声,穿透了夜色的帷幕,使这个夜晚不同寻常、浪漫四溢。那时我想起了红舞鞋的故事,舞者一旦穿上这鞋子,便会舞个不停。那些忘情地舞蹈的藏族人,他们的脚下也一定有一双红舞鞋吧?
神灵啊,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以你之名的舞蹈者,他们可以在天地间跳出飘逸华美的舞步,他们可以创造出超乎我们想象力的舞姿,他们可以舞得月亮满面羞涩,星星黯然无光,大地光彩重生。他们就是人间的舞神,是你派来的舞蹈天使。他们甚至可以仅凭一曲歌舞,就将生命摆渡到幸福的彼岸。万能慈悲的神灵啊,愿你赐福予他们,愿你保佑他们在舞蹈中找到自己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