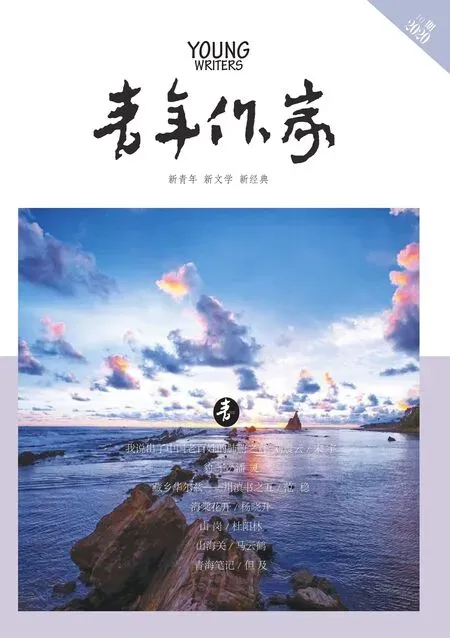鉴 池
王宗坤
他再次梦到了佳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
梦中的佳珍先是俯卧着漂浮在南水湾里,接着就昂扬地挺直身子,朝他游动而来。水面似乎倾斜着向下,跟她脚下的水湾底部形成了一个斜着的三角,那条最长的边就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她缓缓地向前蠕动,光滑平整的水面在她身后漾出了一溜儿绷直的波纹。三角被她的步伐逐渐蚕食。最后,她从水里升了上来,浑身上下挂着湿漉漉的水痕,衣服紧紧贴在高高凸起的肚腩上,就像一只刚刚上岸的水鸟,纷纷扬扬地往下溅落着水珠儿。她靠近了他,笑吟吟地挽住了他的手臂。而他本是满怀期待的,却突然之间有些胆怯了,比当年更甚,不安地向周围逡巡着,如同将要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的扒手,心里紧张得要命,身体也随之变得僵硬无比。
佳珍根本没在意他的情绪,仰着头柔柔地说,咱们回家吧。说着,就不由分说地拖着他离开了南水湾。他们转身向后,来到了北院老宅花园,旁边那破败的花房是他们的幽会之所,这也是被他们多次称为家的地方,可这次他们没急于往里钻。他此时应该已经放松下来,跟她一道徜徉在狭小的花园里。其实,这里早就不能称为花园了,树木都已被砍伐殆尽,那些巨大的树桩也被连根挖走,已成了周围乡邻炉灶里的灰烬,只留下裸露着黄土的树坑。鱼池也早已被填平,有陈旧的泥土浮在上面,中间还混杂着乱七八糟的石块,可以窥见当初那些操作者的随意与冲动。他和她是彼此的景致,也就忽视了眼前的荒芜,但她还是发现了惊喜,在一个角落里,竟然有一大丛白色的小花,挤挤歪歪的,长得很不整齐。她低头嗅了一下,然后很陶醉地对他说:真香!他被感染了,也俯下身趴在那丛弱小的花朵上,他没感受到任何味道,茫然回身,想问这是什么花,她却骤然消失了。他慌了,在花园里到处寻找,没有发现她的任何踪影,这让他更加疑惑,甚至开始怀疑她是否来过。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仔细回味,在自己的衣袖上他发现了水的印迹,手上也留有她的味道,还有那丛白色的花朵,以及她刚刚闪现出来的迷人神态。她确实来过了,可为什么又突然消失了?他急忙跑到街上,却不是藕池村那条弯弯曲曲的小巷,而是城市中惯常喧闹的街道。在汹涌的车流人流中,他奔跑着、搜寻着。找了好久才看到她急匆匆的背影。他终于找到她了,他欣喜若狂,可她好像变了一个人,衣服换成了一件白色长裙,头发散乱地披散在后背上,那原本凸起来的肚子也消失了。他不管不顾地往前追,一边还呼喊着她的名字,她似乎听到了,回身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满是哀怨,脸色也白惨惨得吓人。他被她如此凄凉的回眸所击倒,一下子就木在了那里。瞬间,那个白色的影子又旋转着奔跑起来,速度比刚才更快,很快就模糊了。他睁大眼睛,盯着那个逐渐消失的白点儿,绝望地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他被自己的哭声惊醒,艰难地睁开眼睛,有微弱的光亮从窗帘缝隙透进来。太阳此时应该就在不远处酝酿着情绪,已有了朦朦胧胧的痕迹,这是他平时醒来的时间。刚才的哭声犹在耳边,眼角还有残留着泪痕,他抬手伸向自己的脸颊,指尖触摸到了一片濡湿,在那片沟壑纵横的皱纹里,还有一些让他感到难堪的黏稠,他已年过古稀,泪水也已失却了早先的清亮。他已记不起自己上次流泪是什么时候了,五年?抑或是更早一些?五年前,他的结发妻子去世,他好像没有流泪,这并不是因为他心肠太硬,而是妻子之前已经瘫在床上多年,虽说有保姆照顾,但久病床榻的刻薄和乖戾一度让他不堪其忧,妻子那令人唏嘘的葬礼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解脱。真正流泪的那次应该在七八年前,参加最好朋友的葬礼,那次流泪不只是因为朋友的离开,更是被那个未亡人所感动。朋友的妻子,站在丈夫的遗体前,几乎悄然无声,只是默默望着那具仰面躺卧的躯体,不停地擦拭如溪水般汩汩流下来的泪水。他们是琴瑟和谐的一对,是周围所有朋友羡慕的对象。在当时的现场,他能明显感受到那位老妇人来自生命最深处的悲伤,他们是一个整体,倒下的虽然是一半,但失去的却是生活的全部。果然,不久之后那位老妇人也追随丈夫而去,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躺不下去了,心里总惦念着那张请柬,这应该是刚才梦境的起源。他忽然有些拿不准了,今天该不该去藕池村成了最大的问题。他穿着睡袍来到书房,书橱顶端的隔板上放着那张烫金的大红请柬。自退休以后,他已很少接到这样的请柬,因此它的存在就格外显眼。他没有开灯,从窗子里透进来的黛青色光芒已足够他确定所有物品的方位,更何况,此时他也不想再把请柬拿下来,请柬上的内容他已看了无数遍,不需要再次确认。
今年春节后不久,赵光带着藕池村新上任的支部书记来拜访他,书记很年轻也很客气,一进门就称呼他为袁老。
他虽离家多年,但跟藕池村前后几任支部书记都熟。第一次重新跟家乡建立联系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刚刚成为悦城一中的业务副校长,农村小学面临着合校定点,藕池村小学和附近的禹村小学竞争同一所完全小学的指标。当年的那位支书是造反派出身,并且亲自带人整过他。起初,客人坐在面前的时候是一脸拘谨和内疚,他往客人面前的白瓷杯里倒水,客人居然惊惧地站起来,胡乱地把手指伸向水杯,不想却被往下倾泻的热水浇了手指。这个小小的意外似乎减轻了客人内心的惶然,他终于壮着胆子把面临着的困境和诉求说了出来。
那次支书本没抱多少希望。他之前吃了多次闭门羹,带着侥幸心理前来,纯粹是有病乱投医,没指望他这个曾经被家乡深深伤害过的人会帮忙。但后来的事实跟支书之前的预料恰恰相反,他不但帮了,而且还帮得很圆满。作为悦城教育界的名师,再加上重点中学副校长的身份,他可以调动的资源很多。只需几个电话就把事情办妥了,藕池村小学不仅保住了完小的地位,他还把悦城实验小学拉了进来,和藕池小学结成了帮扶对子。
对于家乡人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此后,他们似乎丢弃了对他的内疚,这几十年来,村里几乎所有难题、所有大事都会来找他帮忙。他似乎也并没对家乡人的得寸进尺表现出应有的反感,每次都是在不超出原则的前提下尽力而为。随着职务的升迁,他为家乡谋取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完小的逸夫楼,村里的图书室,村内街道的路面硬化,村民用的自来水……几乎都是在他的关照下促成的。他成了全村人的救星,成了以德报怨的典范。
疑惑还是有的,但善于寻找托词的家乡人很快就从他祖上找到了渊源。袁家祖上本也是一介平民,无意间搭救了一位落魄书生,后来这位书生高中进士,很快擢升为当地巡抚,巡抚知恩图报,在藕池村最好的位置修了袁家北院,还从周围村庄购买了一百多顷田地送给袁家,后来又按照巡抚衙门的标准修建了气势恢宏的袁家南院,袁家由此成为方圆几百里内的大户。袁家从起初那件不经意的善事中开悟,多行善事、以德治家就成了袁家历代人的祖训。家乡人想当然地认为他就是这条祖训最好的实践者,认定他后来的所有行为都是在遵循这条祖训。正是基于此,家乡人也就不再忌讳他们当年施予他的那些磨难,反而对此津津乐道,把它们演变成了一个个最为动人的励志故事。
让家乡人更感到难能可贵的还有他的无私和低调,他为家乡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好像从来也没想得到过任何回报,家乡人想把他当成神来供,他却一直不肯走进神龛。这么多年来,他几乎很少回乡,即使非要回去也是来去匆匆,绝不会多作停留。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即使发源于良好的祖训,接受一下膜拜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更何况,有一段时间的藕池村应该是他的人间地狱,他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为黑暗的日子,现在扬眉吐气一番也应该并不为过。
赵光带来的支部书记也姓袁,论辈分要比他高,却一直毕恭毕敬地称呼他为袁老。袁支书此次前来是要请他题字的,藕池村一直是那一带的先进村,几任村干部都很有事业心。这几年,村容村貌有了很大变化,年前他们把南水湾也进行了整治,除了清淤加固之外,还修建了凉亭,布设了灯光,垒砌了水泥台阶,架设了木栈道,把昔日的臭水坑变成了村里的一大景观。
南水湾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个土气的名字显然已经跟现在的面貌不相匹配了。您是咱藕池村人,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又是威望非常高的老领导,所以想请您给赐个名字,也只有您才有这个资格……
年轻的支书很会说话,赵光也在旁边不时帮腔,显然他们对他的低调有着深入了解。尤其是赵光,跟随他多年,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外人都认为赵光是沾了跟他同为藕池人的光,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提携赵光,除了赵光本人聪明能干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佳珍,赵光是佳珍哥哥家的孩子。
听了支书和赵光的介绍,他半天没有言语,似乎沉浸在了某种往事之中,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向两位客人讲起了南水湾的来历:南水湾的地面原本是他们袁家的良田,在修袁家南院的时候挖土造成了这么一个大坑,历经几个雨季之后里面蓄满了水。当时袁家的掌门人担心会有人不慎落水,起初想把里面的水引导进附近的袁家河,由于工程太大,只好在周围修建了堤坝,还在进水口建了拦水渠,南水湾也就变成了方便周边村民的一个好去处。后来随着袁家的衰败,拦水渠和堤坝不断遭到破坏,渠坝上的石块都被拆走了,岸边的树木也被砍伐干净,致使污水泛滥而入,南水湾也就变成了臭水坑。
两位听众应该知道这段历史,但还是竖起耳朵做出津津有味的样子。他本来不是个拖泥带水的人,可眼下他愿意为南水湾破例一次。讲完南水湾的历史,他又沉吟了一下说:能再次把南水湾改造好,这是个大好事,我理应赞成和支持,也很乐意能为它想个名字。
那太好了!年轻的支书反应很快,急促而兴奋的回应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激动。赵光也有些意外,他没想到自己这位老乡党怎么会突然改变了风格。
之后他把两位客人撇在了客厅,自己去了书房。他关上门,书房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他的内心却变得烦躁无比,他不知道自己刚才为什么要那样表演!现在他有些鄙视自己,在潜意识里,他好像一直想要抹掉南水湾这个名字,很明显,村里的这次改造让他看到了机会,他这才避重就轻地讲起了南水湾的历史,这才痛快地把命名的事情答应下来。这完全是一种下意识行为,试图用一次浮皮潦草的缅怀来终结他心里的重负,用一个新的名字来淡去心里的阴影。既然已经脱胎换骨,已经改了名字,长久以来压在他心头的南水湾是不是也就可以消失?
他久久地站在书房的窗前,心中充满着愧意,对自己仍然怀有刚才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春天来了,楼下路边的法国梧桐已经冒出了嫩嫩的细芽,干枯的草地也有了些许绿意,这是一个真实的春天,他本不应为此而有太多伤怀。后来,他在铺着毛毡的案几前坐下来,他已彻底冷静下来,他知道他的内心一直在徒劳地逃避。南水湾之于他,显然不仅仅是个名字,应该是他心底永远也抹不去的伤痛,已经折磨了他大半个世纪,他已注定无法摆脱,这是他的宿命。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书房走出来,手里拿着两张四尺宣纸,上面有他的墨宝,都是他所擅长的行草,一张是两个大字:鉴池。另外一张是一首七言绝句:
清池一鉴朝天开
星辰云影共徘徊
鉴古证今明眸在
幸福时光向未来
两个客人一边读着一边不住地赞叹,他们都夸赞说不但字写得好,名字起得好,而且这首诗也写绝了,以史为鉴,清池朝天,简直就是神来之笔。面对这样的激赏,他心里反而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感伤。他实际上更想把南水湾改为忏悔湾,并像那位勇敢的法国人卢梭一样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
可他最终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仍然不敢敞开自己的心扉。外人也许永远不可能了解他的内心,鉴池没有替代南水湾,而是对南水湾进行了更深入的阐发,南水湾会永远以另外一种形式存于他的内心深处。以史为鉴,应该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课题,但之于他,似乎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那段只属于他个人的隐秘的“史”让他抱憾终身,让他的心灵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本来以为这事就这样完结了,不想过了几天,赵光又给他送来了那张大红请柬。赵光说,您给南水湾改的这个名字太好了,镇上区里的领导都觉得好。为此专门找来了一块巨大的山石,把“鉴池”两个大字和那首诗都刻了上去。区里主要领导提议就凭这两个字也要搞一个鉴池的启用仪式,请您务必光临。赵光说着,还把自己用手机拍的图片翻给他看。
他在照片上看到了那块立着的巨石,就在波光粼粼的水边。巨石上下两端尖耸,底下是一个水泥基座,立在那里就像是一枚放大了无数倍的枣核儿,鉴池两个字刻在了最顶端,下面是那首七言绝句,还有他袁慎之的署名。那天他就提议他不要署名,但他们还是把他的名字刻了上去。此时,他想再次把这个意见提出来,又怕引起赵光的误解,最终还是忍了下来。从照片上看,南水湾已被改造得面目一新,水清亮了起来,新修的木栈道在阳光下透着黄铜般的光泽,跟周围样式新颖的民居非常搭。
这是他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新上任的这个书记是大学生,准备依托这些新式民居发展乡村旅游,还计划着要恢复袁家南北两个大院,已经在着手开始论证,当然还要首先听取您老人家的意见。赵光翻动着照片继续介绍,在说到袁家大院的时候似乎分外小心,本来盯视着手机屏幕的目光转向了他。
这倒让他没有想到,袁家大院是他的出生地,现在似乎跟他的关系也不大了。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政府对他们孤儿寡母还是非常照顾的,虽然把土地都分走了,却把两个大院的地契重新还给了他们。在第一次挨批斗的时候,母亲为了减轻罪责,主动把地契交还给了政府,他们也被赶出了袁家大院,从那以后,他们娘俩住进了村西的场院屋子,袁家大院跟他们从此再无关系,变成了村里所有人都可以随意劫掠的肥肉。
他不会去参加鉴池的命名仪式,但当着赵光的面他不想把这个决定说出来。他了解赵光,这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不想跟他多费唇舌。赵光准备开列的那些他必须参加的理由,跟他内心沉重的记忆相比显然是太轻飘了。
上次的顺利显然给了赵光自信,赵光留下请柬就心满意足地走了。既然之前能欣然题名,赵光认定他没有理由拒绝。赵光不知道他内心所想,他拒绝的理由跟上次的“欣然”一样,只属于他一个人。现在他就能想象得出启用仪式那天的场面,纷乱而热烈,混杂而隆重。在家乡人的鼓掌和赞叹声中,他胸前戴着写着嘉宾的大红花,被人簇拥着坐在主席台正中,主持人还要请他做最重要的致辞,甚至还会有大红绸布编织出来的花朵让他亲手剪掉……他们认为他理应得到这样的尊重,理应享受这些光鲜。没有人知道他心里的痛苦,尤其是在南水湾,这里是佳珍的殒命之处,最为重要的是,他就是那个制造这起祸端的罪人。
搪塞赵光的理由非常好找,昨天早些时候他已给赵光打了电话,说省政协的一位老朋友要叫他过去品茶,他不好推脱,已去了省城,要两三天才能回来,参加仪式的事就回了吧。赵光在电话里照例着急地抱怨了一番,说家乡人都盼着他回去,区里镇上的主要领导都已做好了接待准备,致辞也已给他准备好了,还要请他作为主要嘉宾进行剪彩,您老怎么能釜底抽薪呢?他回答说,他这不叫釜底抽薪,剪彩致辞的任务任何人都可以代替他完成,而朋友之约却是唯一。
放下赵光的电话,他心里感到一阵轻松,这跟他之前所预料的一样,他庆幸自己还没老糊涂,明智地做出了拒绝的决定。
可当晚他就做了那个梦,梦到佳珍浑身湿漉漉地从南水湾里爬上来,然后又在茫茫人海中消失。在过去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佳珍时不时会在梦中造访他,但都没有这次这么清晰,这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惶然,佳珍一定又在怨他,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遵从佳珍的意愿,内心所有的假设都是以“佳珍若是还活着”作为前提。现在他不知道究竟哪里出现了纰漏?
一般早饭都是他自己来弄,请的阿姨只负责中饭和每周三次的卫生,他从来就是一个生活简朴的人,原本坚持不需要人来照顾,是赵光和政协办公厅主任非要给他找个保姆。吃过早饭,那个一早就萌生的念头在脑海中越来越清晰,他要回一次藕池村,请示一下佳珍,让她来告诉他究竟哪里做错了。
作为从市政协退下来的资深副主席,他本来可以随时从政协机关要车,可这次他却不想惊动任何人。
真正来到街上,他才发现一个人的回乡之旅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这让他感到羞愧无比。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他已经失去了普通人的感觉,即使退下来也在享受着一定级别的待遇,所有给予他的这些,他竟然都照单全收了,从来没有感到过不合适!尽管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
好在他还残存着一些自悟成分,从公交车站附近的银行兑换了零钱,在站牌前看明白了车次,他本来也可以打的,但还是选择了公交车,这种执念不是来自于一种想体验一把的矫情,而是此时他内心的一种需要。
公交车比他想象的干净,今天是星期天,天气也在逐渐暖和,出门的人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老年人,他们气喘吁吁地上车,理直气壮地刷老年乘车卡,然后嘴上虽然客气着,可还是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别人的让座。相比而言,他却落伍了很多,同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却要一块一块地往里面塞硬币,他表现得既不从容也不自信,由于没有那声老年卡的提醒,几乎没人把他当做老人,他站在挤挤挨挨的人堆里,显得极为尴尬。此时,他对那些坦然而坐的同龄人极为羡慕,他们的表情无拘而放松,想必内心也非常敞亮和充盈,看起来,要比他这个看似成功者不知要幸福多少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几乎都有家人陪伴,那些老人有很多是老两口一同出行,还有的带着自己的下一代,他不知道他们将去往何处,但却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踏实与满足,他们的行程有着别样的温馨,去往哪里似乎已变得不重要了。
在老汽车站他换乘了通往藕池的长途汽车,所谓长途也不过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大概有五十多公里的样子。这是一条家乡通往外面世界的桥梁,尽管有几番演变,但他却极为熟悉。当初,他的人生在藕池村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泥淖,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步走到了悦城,为此几乎付出了所有。
他悄无声息地在车厢后排找了一个座位,几乎没怎么说话,不是由于傲慢,而是不知道说什么,他感到自己已失去了这部分功能,起初他还想努力一下,主动跟邻座搭讪,可他很快就放弃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又担心别人笑话,就只好继续沉默着。
但纷乱的思绪并没有放过他,坐在回乡的大巴车里,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五十多年前的那次出逃,那是他第一次向自己的命运抗争。那年年初,藕池村革委会的人得到了确切消息,他已失踪多年的父兄逃到了台湾。他的母亲,那位出身大家闺秀的小脚女人,除了地主婆的称谓之外还成了匪婆子。刚刚成年的他也被冠以敌特分子称号。无休无止的批斗从此开启,他们把他和他母亲分别关押起来,然后用尽各种方法让他们交代发报机藏在哪里?发展了多少通匪成员?要在何时何地举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暴动?……这些子虚乌有的问题他当然无法回答,他们就把他吊在梁头上拷打,还用烧红的烙铁直接烫在他的皮肤上,他受不了这样的酷刑,胡乱招认起来,不想又换来更严厉的毒打。这年年底他的母亲不堪凌辱咬舌自尽,他的整个生命都陷入了黑暗之中,但他并不甘心,他感到自己还年轻,有很多想法还没有实现,不想让自己的生命就此完结。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他被关押在他们家南院原来的柴房里,看管他的民兵队员锁好门被人拉去喝酒了。他很早就注意到了那扇老式木门,那扇木门已经沿用了多年,门扇后面的立轴跟门台子沿窝儿有了很大的缝隙,他蹲下身子,抱住门扇的下方,用力往上一顶,门扇居然脱离了门台子。门扇被掀掉了,他迫不及待地往外张望,夜色下白晃晃的雪地晃了他的眼,他顾不上多想,见四周寂然无声,一下子就从柴房里蹦了出来。
他从藕池村逃了出来,朝着悦城的方向奔跑,这段路程他走了整整一天。按照他的计划,他要先去悦城火车站,然后再扒火车去厦门,他从广播里知道,厦门是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到了厦门再想办法去台湾找自己的父亲,尽管他已忘记了父亲的相貌,但他一直牢记着父亲的名字,他想当然地认为,有这就不愁找不到父亲。可他来到车站却根本不知道哪趟车是去往厦门的,他在火车站盘桓了两天,一直在寻找机会,可后来藕池村的人追了过来。
他被押解回去之后,本来应该面临更大的灾难,是佳珍出手解救了他。佳珍的大哥刚刚完成夺权,成为村里的民兵连长,佳珍央求自己的哥哥,然后在佳珍哥哥的暗示下,他坚决不承认自己这次出逃是想去台湾,而是要去北京。他出逃的性质就这样在反转的剧情之下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的整个生活也由此出现了转机。不久之后,他结束了羁押之旅,变成了可以改造的坏分子,继续在藕池村接受劳动改造,他和佳珍的爱情也在那时开始开花。
想来佳珍已经注意他好久了,他却一直没有留意这个长相清秀的小女孩,直到这次变故出现。佳珍跟他同岁,那年也应该是十九岁,他们很快就热烈地相爱了。那时,他禁锢而冰冷的内心太需要爱了,她似乎也一样,他的出身以及后来的遭遇给了她谜一般的诱惑,他们从彼此的身上汲取着营养,在幽暗的环境中进行着秘密交往,这种方式让他们的爱情焕发出更大的魅力,他们都不能控制自己,很快就在爱的泥潭里陷落了。
那时候,三里半长的藕池街是他的工作场所。他每天顶着星星拖着扫把去扫大街,佳珍就会在这个时候悄悄地出来陪他,也带着一把扫把,两人从东西两个方向齐头并进,然后在中间会合,而中间就是袁家北院的大门,他们早早完成每天的工作量,然后就溜进后花园的花房里幽会,那间花房已经坍塌,他们重新用残存的木料撑起来一个帐篷,又用一些烂树枝做好了伪装,里面狭窄的空间就变成了他们的新房,他们早已偷食了禁果,压抑着的青春在这个蜗居里得到了尽情释放。
他刚刚提拔为副校长那年,有一部叫《芙蓉镇》的电影当时非常流行,这也引起了他的好奇,但在听说了里面的故事以后他就不敢看了,因为他和佳珍就是里面的秦书田和胡玉音,所不同的是,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最后得到了圆满的结局,而他却辜负了佳珍。
开始是源于他自身的改变,爱情让他苍白的青春有了色彩,让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那几年,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又捡拾起了丢弃已久的书本,他一边接受着所谓的改造一边不断地汲取知识,后来在佳珍哥哥的举荐下他被抽调到了公社,成了公社革委会的宣讲员,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那个女人。
他的妻子当时刚刚从大学校门出来,是工农兵学员,接着就被任命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她是他的领导,他不过是公社革委会的临时成员,起初她并没有看上他,但几次交往下来她发现了他的才气,开始对他留意,渐渐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主动接近他。感到女领导对自己有了那层意思之后他是想要逃避的,佳珍对他有恩,更何况他也爱着佳珍,他觉得自己不能辜负佳珍,可后来他的内心就发生了摇摆。他已明显感到这位女上司会前途无量,她不但现在居于一个决定他未来的显要位置,而且还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他断定她能帮他彻底脱离苦海,达到一个他不可想象的人生境地。
他永远也忘不了跟佳珍最后相会的那个晚上,那也是一个春天,那晚的夜色昏沉黑暗,天空漆黑如墨,看不到一颗闪耀着的星星。花房里没有灯光,更没有鲜花,他和她静坐在他们自制的床榻上,他们都沉默着,一直过了好久,佳珍才缓缓地把身子偎过来,紧紧贴在他身上。当时,他没听到佳珍任何哽咽之声,但却在她面颊上触摸到了大片大片湿痕。他心里感到刀绞般难受,同时也在庆幸,他知道佳珍是善良的、是爱他的,为了他,她宁愿牺牲自己。正如他所料,佳珍爱他,希望他好,为此不惜隐瞒下自己已有了身孕的事实。
在后来的反思中,他曾经多次问过自己,假如当初知道佳珍已有身孕,他还会离开她吗?他一直不能确定答案。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并不了解自己,先前骨子里的自私与之后的宽容似乎都发自于内心,在很多的时候他根本就把握不了自己,这也是他为自己开脱当年罪责的唯一托词。
他成了女上司的未婚夫,当年就被推荐上了大学,几乎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佳珍的消息。那个年代,一个乡下女孩莫名其妙地怀孕,也就等于整个人生跌落进了谷底,家里人先是逼着她说出那个男人,遭到拒绝后又逼着她赶紧嫁掉,她同样进行了抗争。到了这年秋天,一个让他痛悔终身的消息传来,佳珍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悄悄把自己沉到了南水湾里。他后来听说,佳珍浮上来的时候虽然浑身肿大,但肚子却未见异常,有人就怀疑佳珍在投水之前已经把孩子生了下来。这种怀疑也并不是无凭无据,因为不久之后佳珍哥哥家就多了一个婴孩,这个孩子就是赵光。
本来大学毕业之后他是可以直接进机关的,但他却坚持要去教书,他的未婚妻有些不解。他不是一直想出人头地吗?仕途不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最佳途径吗?他的解释在当时也似乎合情合理:他感到自己对机关生活还是不太适应,想先在学校磨练一下。真正的原因他没有说出来,佳珍的离去给了他莫大打击,让他对自己那所谓的“雄心壮志”产生了根本性怀疑,他觉得愧对佳珍,不敢再沿着那条道路走下去,他想让自己踏实下来,而教师这个职业无疑能帮他安静下来。
可接下来生活并没有放过他,他很快就跟女上司结婚了。女上司跟佳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女人,他过得并不如意,有种仰人鼻息的感觉,女上司的仕途也并没有他之前所预料的那样顺畅,她站错了队,很快就被闲置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女上司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天南海北地找医生看,西医中医都用,但就是不见肚子里有动静。她由此变得更加暴躁而专横,后来突发脑溢血瘫在了床上,彻底成了他的负担。他的整个生活陷入了混乱,外面有一大摊子事情需要应付,回到家里还要忍受那位病人的辱骂和讥诮,他活得很累,沉重的生活无处可逃,外面的光鲜脆弱无比。
他把这看成了上天对他的惩罚,他为了所谓的前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爱人,埋葬了自己的孩子。上天对他已经失去了慈爱之心,再也不会眷顾于他这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了。此后的岁月里,他不敢再祈求上天的宽恕,一心扑在了事业上,好在教而优则仕,他后来的仕途还算顺畅,由一般教师到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再到校长、教育局局长,然后是副市长、政协副主席。这一路走来,纯粹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他似乎达成了最初的愿望,在外人看来也风光无限,但他自己,也只有自己知道,为这一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在藕池村下车的时候已经到了正午时分,司机每站必停,本来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竟然多走了将近一倍的时间。由此,他多少窥探到了人们平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愤怒!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的理由,而这种带有个人印记的理由难免就会侵害到别人的利益。
春日正午的藕池村有着难以名状的静寂。这跟他想象的不同,虽说这个时间启用仪式早就应该结束了,但也不至于这么安静。南水湾离此不远,仪式尾声的余脉应该还在。他有些茫然地踟躇于藕池村村头,再次想到了昨晚的那个梦境,忽然不想去鉴池了。
自佳珍走后,他曾无数次去过赵家的林地,但一直没有找到赵佳珍的墓碑。他也曾侧面向人打听过,甚至问过赵光,但没有人知道赵佳珍的墓地,赵光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姑姑。他知道赵家人在刻意回避着这个名字。起初他内心有些不平,想单独给赵光讲讲佳珍,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都不知道佳珍的下落也好,这样佳珍就会只属于他一个人,他就可以尽可能地展开想象了。所以,南水湾是他的痛,也是他心灵的栖息之地。佳珍借助这一湾水脉脱离了苦难的肉身,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了自由舒展,这也不失为一种归宿。从这个角度讲,他不想看到它的变化。
沿着梦境的指引,他来到了袁家北院的后花园,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这里竟然变化不大,只是花房的痕迹已无,那个位置叠加上了数不清的枯枝败叶,这是时光的碎片、岁月的尘垢。他再也找不到那个帐篷的入口了,斯人已逝,他也垂垂老去。这一切似乎都已成了过去式。
后来,他在西边的墙角下果然找到了那丛白花,细长的花瓣簇拥在一起,抖动着飘摇在细长的茎上,在茎的底部是狭长的豆荚般的嫩叶。他起初以为这是一丛雏菊,但雏菊怎么会在春天里开花?叶子也不像,他伸手掐了一片嫩叶,立刻有白色的浆汁冒出来,很快就汇聚成了一个白色的原点。他想起来了,这是苦菜花,当年他曾经和佳珍一起采过。他再次想起了梦中的情景,俯下身,趴在花朵上。“真香!”有个清脆的声音忽然传来,他急忙回身,发现佳珍就站在身后,跟五十多年前一样,穿着那件他曾经极其喜欢的水红上衣,正笑吟吟地看着他。他惊呆了,使劲揉了一下眼睛,没错,就是佳珍。他的眼泪流了下来,惊喜地跑过去,一下子把佳珍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