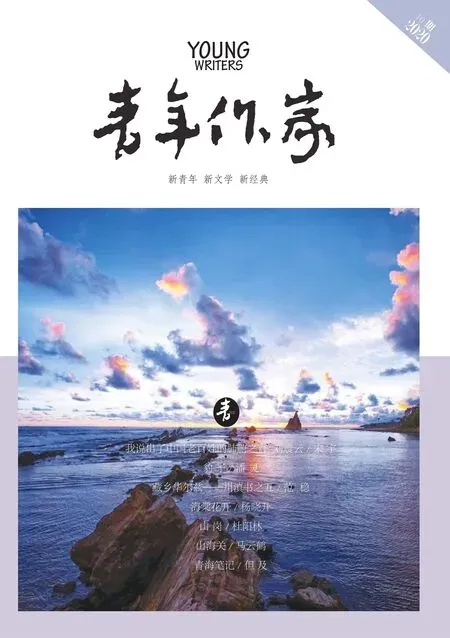天上的小学
陈 果
一
古路小学成了“网红”,校长申其军名震四方。如果知名度是一架天平,古路村几百口子打捆放一头,申其军单独扔一边,顿也不打往下沉的,准保是申其军。
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的古路村一切都是贫乏的,贫乏到给人取名字也缺乏想象力。举例来说,村上开大会,叫一声申其军,至少有两个人应声起立。一个是退位多年的老会计,另一个是古路小学前校长。
作为后者的申其军出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所位于四川省汉源县永利彝族乡万丈绝壁上的乡村小学校。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村里有了学堂。先生打山外面来,就着一间茅草房,拿肚子里不多的墨水换些洋芋、荞子糊口,这同后来来村里的补锅匠拿半生不熟的手艺换点粮食养家没多大区别。这是方块字进入古路村的最开始,在那之前,别说汉字,村里听到过汉话(直到现在,村里人还称汉语为汉话)的人也屈指可数。只可惜那时候能从口里腾出粮食来的人少,舍得拿比命金贵的粮食去换也不知有啥用处的汉字的人更少,没等到解放,学堂便解散了。
悬崖边再次响起读书声是1951 年。作为全乡第四个公办教学点,上面一次性派来两个老师。师资力量增长了一倍,生源却维持在原来水平——之前的私塾,最好的时候,学生也没超过八个。这样的局面却没能稳定下来,1958 年,随着刘成煜、伍元煜两位老师离开古路,公立学校重蹈了私塾覆辙。
1961 年,政府下了决心,非把学校办好不可。村小设在咕噜岩,古路村其余五个大队,每个队都建起校点,老师都是在永利乡招聘,以免学生登天梯走绝壁,以免公办老师离家远,安不下心。不能不说,不管是让学生就近入学,防止他们在每天来回两三个小时甚至五六个小时的悬崖路上出现意外,还是体察公办老师嫌远嫌苦嫌寂寞的人之常情,就地取“才”,当时的决策者找准了症结。可惜“疗效”并不理想,“全面开花”的局面只维持了几年。究其原因,读书无用的观念根深蒂固,有的校点招生比政府招商还难。再说,招来的都是民办教师,低待遇遇到高海拔,落差太大,招得来人,留不住心。至于来村里“镀金”的老师就更留不住了,只要一转正,人家身上某个零部件就不好用、不能用了,其实不想走可是不能留了。这样的情况一多,村民就有了议论,古路村没有小学,只有民办教师报到处、公办教师转正点。
到1982 年,除了村小,只有三队流星岩、五队马鞍山两个校点还在苦苦支撑。也是1982 年的秋天,古路村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姜腾全得了胃癌;另一件是除姜腾全外,全村读书最多的申其军从马托初中毕业。姜腾全是永利乡中心校校长,在老家养病的他见流星岩校点又没了老师,一边吃药一边给仅有的三个娃娃上课。一个月后,病情进一步加重,姜腾全住进医院。
这就到了申其军出场的时候。区教办主任李俊松找到申其军,姜老师一走,流星岩又得停课,你来顶一下如何?
姜腾全没教过申其军,教过申其军的老师早就在转正后远走高飞了。经验言说一切,申其军知道,说是让他代课,真正要让姜老师再把他替下来,那是摆聊斋。这也是他怦然心动的原因:如果先“代”后“民”,由“民”而“公”,不说是鲤鱼跳龙门,至少也能跳出“农门”,蜕了“农皮”——“农皮”包裹之下,只有面对黄土背朝天的日复一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复一年。凭良心讲,申其军爽快接招,另一个原因同样至关重要:满地跑的娃娃都沾亲带故,他不忍心看着他们成了“睁光瞎”。
第二年春季开学,上面做出决定,撤销流星岩、马鞍山校点,申其军和马鞍山校点代课老师向玉海调村小任教。后来才搞清楚,村小唯一的老师向开强调万家村去了,村小的“坑”得有人去填。
说到这里得补充一句,被撤销的流星岩校点第二年得以恢复,只因从流星岩到咕噜岩的路实在太远太险,让几岁的娃娃“两头黑”攀悬崖上学,没人放心得下。这个校点在后来的十年间一直处于停停办办、办办停停状态,仍然是因为老师走了又来、来了又走。1995 年春季开学,娃娃们坐在教室里,却没有等来他们的老师。流星岩校点不得已再次关门,直到后来连村小也关门大吉。
二
回到村小。两年后,向玉海也转正了、调走了,古路村小只剩下申其军一个老师——而且还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代民师”。
“代民师”还是“代校长”。用带了“长”的目光审视学校,申其军的心往下沉了又沉。全校只二十七个学生,却有四个年级。一个人给四个班上课,这个课怎么上,他希望有人先给他上一课。
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可靠,他相信,只要用心,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一二年级在一个教室,三四年级在另一个教室,给靠近讲台的一年级讲课时,他让教室后面的二年级做作业,另一个教室的两个年级自学。给二年级上课时,就让一年级做作业,三四年级继续自学。以此类推,二十分钟一节的课,他一天要上不下十节。等到放学,申其军又该批改作业了。改完作业,挤出时间,他又得去家访——甘友能来学校要走三个小时的路,鞋破得都快穿不稳了,他得提醒大人别把娃娃冻着;申其云上课时一副苦瓜脸,下课又偷偷躲到墙角里哭,一问才知道父亲喝酒后对母亲拳打脚踢,母亲死了心,去岩边寻了绝路,他得警告申绍兵,千万别再伤了娃娃的心;李友全一连几天没来学校了,他要当面给家长发出最后通牒:学校是学知识、讲规矩的地方,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放牛场,再这样下去,你家娃娃就别来了……
叫人别来了,只是吓人不咬人的把戏,真要有学生和家长铁了心回去念“农业大学”,吓得睡不着觉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是他申其军。道理明摆着的,一群娃娃都看不牢,村里人会说这个申其军读了那么多书也就这点本事,看来这书,他是读到了牛屁股上了。
当了一年代理校长,申其军心里想的东西跟以前有了一些不一样。由“代”转“民”、由“民”而“公”的目标之外,他又有了新目标——在我的手上,让学校变好。
怎样算好?村里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申其军说,入学率达不到九成,这个校长当着都没劲。他还真把自个儿当校长了。
苟向甫8 岁了还光着屁股满山跑。申其军找到苟树方:你家娃娃头脑灵光,一看就是读书的料,天天伙起牛耍,可惜了。
苟树方说:也没光放牛啊,挖洋芋,掰苞谷,他样样干起来都像模像样。
他脑壳这么够用,让他一辈子扛锄头,那是抵门杠作牙签——大材小用。
苟树方闻言笑了:莫非说,他还能从书本子上读得来二两出息?
依我看,这个娃娃只要进了学校,读出八两,只多不少!
苟树方的笑就从不信任变成了不自信:要想他读书读成公家人,再活三百年,我也长不了那么大个胆!
申其军笑着摇摇头,把目光停稳在苟树方脸上,无论如何,让他读几年书没坏处吧。至少,学来的汉字可以当拄路棍,可以陪他下山。申其军这句话有一个不言自明的背景,村里好多人都怕下山、怕进城,因为他们和大山以外的世界隔着一座更高更大的山——语言的山。
苟树方似乎有些动心了,但他的决心明显又被拖住了后腿:不怕申老师笑话,一学期学杂费要十多块,我家哪拿得出来。
古路人不爱“卖穷”,实在要“卖”,一定也是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知道这一点,申其军也就知道,苟树方是有心让儿子读书的,阻止娃娃进入学校的是四面漏风的这个家,是找不到来路的学杂费。申其军禁不住同情起目光比脸庞显得成熟的苟向甫来:如果有一根火柴,他也许会燃成一个火把。在你尚且无力选择命运的时候,命运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这样的现实,多让人心痛。没有条件上学,没有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机会,没有走出贫困的能力,这样的人生不就是一副石磨么?——无论时间如何流转,循环的轨道也一成不变。古路人要活得和从前不一样,要从贫穷落后的轨道上跳出来,必须走出这个怪圈,而跳出怪圈和走出大山一样,需要找到路口,需要一条路,学校就是那个路口,科学文化知识就是那条通往远方的路。申其军相信自己八年的书没有白读,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恰恰是这份自信,让他变得忧虑也变得焦灼:苟向甫这样好的苗子都不能招进学校,要把其他娃娃拽进来就更难了。入学率低位徘徊,他把学校办好的目标就要落空,目标落空就意味着自己没本事,读了八年书还是没本事,恰恰也说明读书无用,说明他的书读在了牛屁股上。
就从苟向甫这里打开缺口。决心下定,申其军又一次去了苟树方家。话没说上三句,苟树方又把话扯到了钱身上:要是手上宽裕,我早把娃娃送过来了,哪还等得到今天!
现在不说钱,你先把娃娃送过来再说。申其军直截了当。
苟树方听清了他的话,却觉得是听岔了:读书也可以赊账?
申其军笑了:不叫赊账,我先帮你垫着。
苟树方眼睛睁得大大的:申老师你要想清楚!听说你一个月代课工资只有二十二块五,我家这日子过得是顾得了身子顾不了屁股,哪天才能打翻身仗我不晓得,这个钱要垫到哪天,我也不晓得!
申其军顾左右而言他:只要发狠,苟向甫这个娃娃肯定有前途。
取下第一块砖后,拆除一堵墙变得顺利多了。申其军旁敲侧击,大人们的从众心理和面子观念推波助澜,古路村小学入学率一年一个台阶,到1986 年,全校已有84 个在校学生。申其军的工资涨到了二十九块五,拿在手上的钱却不如刚来时多——他先后为十余名学生垫付过学杂费,这当中有的后来归垫了,有的一垫就是二三十年,当年的学生家长都记不得了,或者想到物价今非昔比,都不好意思再提起还钱的事。
扩展生源只是办好学校的第一步。学生一多,桌凳就不够用了,别的地方画“三八线”,申其军的学生只能画“十字格”。四双小手放在一张课桌上,挤得一会儿这个的书掉下去了,一会儿另一个的本子起了拱,再一会儿就有人为“争地盘”吵得面红耳赤。申其军愧疚不已:学生像是学生,学校不像学校,这校长当得不及格啊!
为了让自己越过及格线,申其军不光拼,而且下了血本。
仗着人熟,他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百块钱,请村里木匠会树金做了8 套桌凳。再让人家做这没有赚头的活儿,他开不了口。桌子上的笔和书本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只有自己动手丰桌足凳了。他将批改作业延迟到晚上进行,腾出来的时间,将临时抱佛脚学来的一点木工手艺现学现用,热炒热卖。桌面是修建学校时用过的两副墙板裁切而成,桌腿和做凳子的材料,有的是他从申绍兵手上收购,有的是他从学校旁边人户里打的秋风。
桌椅差不多拼凑齐整,申其军又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是学校就该有个篮球场,对吧校长?还是就地取材,他把淘汰下来的一张黑板竖着锯掉五十厘米,篮板便有了雏形。篮球架是两根松木,虽是“材料”吃紧,看起来和篮板也还般配。巴掌大的操场,连篱笆也是后来才有的,篮球从坑坑洼洼的地上弹跳起来,方向全无规则,学生们因而拍球也和投篮一样小心翼翼——要是弹得一高,方向一偏,篮球出了操杨,只怕难以捡得回来。
孩子们激动万分又谨慎无比的样子让申其军心里有一种揪着扯着的疼,越是心疼,他越是发誓要对他们好,用他尽可能的付出,弥补老天制造的不公。
为学生垫付学杂费是好,亲手制作桌凳是好,熬夜批改作业是好,爬坡下坎家访是好,给生病的学生端水喂药是好,一丝不苟为他们上好每一堂课是好……
好字易写,好事难做。个中尤其艰难的,每期开学去中心校领取书本和教具可以算上一桩。从古路村到中心校要走六七个小时,往回走,背着百十来斤,路会显得更长一些。早上四点,申其军打着手电筒出发了。交完该交的取完该取的,已是下午四五点钟,见他背着书要往回走,中心校老师说,你这时候回去都几点了?山高路陡,黑灯瞎火,不如住一宿,明天早点出发。申其军说,提前没打招呼,娃娃们都会去学校,他们有的单边要走几个小时,我今天不赶回去,他们明天就得白跑一趟。
一个也不能少,一课也不能少。心窝里揣着这两句话,一个人走在路上,申其军也就忘记了孤寂劳累。老木孔的雪地上,流星岩的悬崖边,水井槽的泥浆里,申其军没少绊倒。每次倒下,他的第一反应都是将散落的书本收捡起来,像钞票般码放齐整,若是有书本沾了污泥浊水,就是把衣服脱下来,他也要给他们擦拭干净……
三
申其军的坚持感动了村民,也感动了区教办和永利中心校领导。他们给古路小学增派来两名老师。“单身”生涯这是要结束了吗?申其军心里起了一丝涟漪。谁知好景不长,新来的老师一个教了两学期,一个教了三学期,也都在“民转公”后调离古路。
他们想走,申其军理解。别说他们,他也想走。1988 年,他有了长子,1993 年有了二儿子申华刚, 1994 年又有了女儿申燕。除此之外,1994 年,娃的大舅在矿山上打工时丢了命,舅母跟人跑了,留下三个娃,大的三岁,小的一岁,也都跟着他们。虽说这时候申其军工资长到了每月55 元,但靠这点钱养活一大家子,太难了。和调走的老师来自村外不同,他自己就是古路村的,这些娃娃同他一样,都是呷哈后人,别人心一硬也就走了,他的心也硬过,可只要被那些柔嫩的沾着露珠的目光一碰,立刻就像吹到半大的气球漏了条缝,瞬间就瘪塌下来。除了心软,他想走未走还有一个原因——对于“转正”,他始终心存侥幸,这么多年都过来了,那么多人都转正了,就这样放弃,他不甘心。这几乎是他一生最大的理想,也是他唯一可以被视之为理想的目标。这个目标里藏着他对三尺讲台的热爱,藏着一个编外教师的自尊,藏着他对知识与命运辩证关系的理解,也藏着他希望家里的娃们有钱上中学、读大学的心心念念。
2005 年,县上出资二十余万元将古路小学改造为砖混结构。次年6 月,县政府专门就解决民办教师遗留问题下发文件,考试合格的民师可以正式入编,申其军离目标似乎又近了一步。申其军兴冲冲去教育局报名时才知道,要有中师以上文凭才可以报名考试。只顾埋头拉车,忘了抬头看路!申其军想,如果有时间,别说中师文凭,只怕成人大专的本本我都有一摞了,真要被这根硬杠子拦在外面,老天爷就太没有人情味了。他找乡政府和区教办出面帮他说话,请他们书面为他求情、争取变通,他们倒是痛快答应了,然而在县政府门前等了五天,申其军等来的答复仍是:这是上面的政策,我们也爱莫能助。
太阳火辣辣地晒在身上,申其军心里却像是结了一层冰。是时候兑现诺言了——自己在心里说过一百遍不干了,人无信不立,今天的结果,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否定。申其军想去山外换个活法,瞌睡遇到枕头,矿老板庆其华找到他说,以前叫你来,喊山一样你都不应。不过现在也不迟,给我当会计,每月保底一千块。
这时候,申其军每月工资只有195 元。看在钱的份上,他应了下来。
庆其华前脚刚走,永利乡党委书记苟国军后脚就进了屋。年轻的书记心事比申其军的还重:申老师,晓得你想不通,我也不想劝你……
谢谢书记不留之恩。申其军反应不慢。
苟国军尴尬地笑了笑:你一走,这个学校就又停了。这么多娃娃没人管,一夜回到解放前。
另外再请一个不就得了?顿了一下,申其军又说,真要重视,请上两个三个也不多。
苟国军说的也是大实话:就别说两个三个了,乡政府穷得叮当响——不瞒你说,我昨天亲自去莫朵动员过一个人,人家开口就是一千多!所以……
申其军赶紧截住他的话:这就是政府的事了。你们大会讲正义,小会讲公平,让我一个代民师操县政府的心,哪里来的正义,又哪里来的公平?何况说,我又不是不晓得我是个啥东西。假装是校长,打屁都不响!申其军越说越激动,口水星子差不多都溅到了苟国军脸上。
苟国军不光不生他的气,脸上反倒溢出了笑:要说不响,那是冤枉。这么多年来,你申老师教过的学生少说也有一两百个。这当中,苟向甫考上大学,石万民、张腾超考上中师,当了公办教师。没有你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他们响了就是你响了,他们给古路争光,归根结底,是你在给古路争光。
申其军早给自己讲过纪律,千万提高警惕,小心糖衣炮弹。戴在头上的高帽子还少吗?从教育局到中心校,张口闭口向你学习,大会小会向你致敬,然而结果呢?谁诚心诚意学黄牛叫过两声?让我把民师一当到底,就是你们口口声声的学习、漂漂亮亮的致敬?说白了,你们的高帽是圈套,再要当回事,这辈子也别想脱身。因此,苟国军听起来情真意切的一段话,申其军一点不剩地给他挡了回去:要不,你来?
……
出乎苟国军意料,甚至在申其军本人意料之外,一笔一画的“申其军”三个黑字,最后还是落在了《代课教师协议》白纸上。申其军选择留下,有月工资从195 元涨到720 元的因素,有苟国军再次重申“一有机会全力帮你转正”的因素,最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已经冻结成冰的心,没有经受住学生们泪水的冲刷。决定留下的那天晚上——更准确些,那个即将到来的黎明——申其军对自己说,他们已经把你抛弃了,你不能把他们也抛弃了。
四
如果没有过初恋的甜蜜,也就无所谓失恋的痛苦。这样看来,人生之树生发的很多枝节其实都是多余都是累赘,都是在给锯齿炮制伤疤制造机会。如果早一些悟到这个道理,也许,申其军无论如何也会在一开始就将包唐韬拒之门外。
2004 年2 月20 日,雅安日报第二版刊发了记者罗光德采写的新闻通讯《天梯人家》。6 天前,罗光德在金乌公路建设工地采访时意外听说了古路村和古路小学,情难自禁,他从同事那里借来相机,怀揣四个胶卷,孤身一人进村采访。天梯人家的贫苦、古路小学的简陋、代课老师的坚守和付出……眼前场景转换为文字和图片,再转换成报纸版面,罗光德闯了祸。有报社领导认为稿件没有体现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批评他没有全局意识,不善于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和捕捉亮点,反倒是泄气不鼓劲,添乱不帮忙。坐在火山口上的罗光德脱离困境,得益于同行无心插柳的遥相呼应。他的稿子连文带图被《成都商报》转载,时隔不久,《教育导报》记者杨绍伟采写的《挂在“天梯”上的学校》也见诸报端。
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古路村和古路小学成为了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而《华西都市报》的持续关注和记者杨涛命名的“天边小学”,更是极大地激发了外界对于古路的好奇。更多媒体聚焦申其军和他的学校,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爱心物资从四面八方涌向“天边”。
包唐韬是申其军接待过的若干外来者中与众不同的一个。2008 年7 月,毕业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包唐韬辞掉广告公司的工作来到汉源。那天,申其军在县里参加简笔画测试,接到包唐韬打来的电话,打摩的赶到一线天同他会合。听说这个没有手续的志愿者要到古路支教,申其军一口回绝了,他说我这个老师是“歪”(方言,不正规之意)的,你这个志愿者也是“歪”的,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歪”到家了。让申其军改了主意的不是包唐韬科班出身的背景,不是他坚决服从管理的表态,而是他画下的一个大大的饼:我有一些朋友很有实力,我会动员他们为古路捐资办完小、办初中。申其军正为学生升学不畅头疼,家里几个娃娃念中学的事也日益成为心病,包唐韬真要能把初中办起来,娃娃们就不愁升不了学了。这么想着,申其军答应让包唐韬试试。
包唐韬用三件事很快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一是当地中学教育资源紧张,包唐韬出面协调后,古路小学当年的12 个毕业生一度卡壳的升学问题顺利解决。二是村里虽有6 部手机,但因为不通电,电池耗尽只有下山去充,村民打电话,往往意思还没说完整就着急忙慌地掐了。“5.12”地震后湖北省对口援建汉源县,申其军在县城正巧碰到湖北作家采风团。听明原由,采风团共同捐资4000 元为村里买了一台小功率发电机。此后,“我们爱读书”社团还为学校捐款、捐书。三是一个多月后,包唐韬的师妹杨菲也从湖北来到古路,不光课程变得生动,就连学校和村子似乎也变得更有活力起来。
包唐韬和杨菲来村里支教,对申其军来说,好处显而易见,课程压力没那么大了,精神上没那么孤单了,更大的好处是完小、初中,包唐韬画过的饼,远远闻着都来劲。想着村里、学校和自己得到和可望得到的好处,申其军就有些难过起来。他难过的是两个大学生放着好好的前程不奔,背井离乡来同他一起受罪。觉出了别人的好,就要用自己的好来回报别人的好。这句绕口令一样的话申其军没有张嘴说过,却是他的处世哲学。两个新老师刚来时不会做饭,申其军就抽时间帮他们煮饭炒菜,或者把他们叫到自己渊曲的家里“打牙祭”。
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2008 年11 月,由于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持续报道,新浪网广大网友极力推举,申其军成为当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当时村里一台电视机也没有,申其军也就不知道“感动中国”是怎么回事,他只是从“央视”和“中国”里隐约掂量出了“候选人”的分量,进而乐滋滋地想:真要评上了,想不转正,只怕也难了!
申其军人生里的高光时刻,却是“天边小学”从天边消失前的落日余晖。
申其军同包唐韬的矛盾没过多久就显露出来。他正嫌包唐韬和杨菲音乐课上得多了些,他们又自作主张开了地理课、自然课。课还经常拉到外面上,惹得申其军班上的娃娃人在教室心却满山遍野地跑。申其军说,语文和数学是教学重点,你们主次不分,学生学不到真东西。包唐韬说这叫快乐学习,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促进他们全面发展也很重要。申其军说快乐是快乐了,学习却荒废了。《学习大纲》总不能不要吧?期末考试总不能画鸭蛋吧?包唐韬说,我们两个大学生还教不好这几个娃娃,你是门缝里看人。申其军说,地震后,我连夜搭棚子都要给娃娃娃们上课,就怕误了他们学习。我辛苦抢出来的时间,你们耍耍闹闹就给浪费掉了。包唐韬说学习不是死记硬背,学习讲究质量讲究效率。申其军说,那就说质量吧,前段时间测试,你班上考几分十几分的都有,我教的起码也是六七十分。包唐韬说,这些学生基础太差,有的到毕业还不会乘法口诀,既然他们不能成龙成凤,倒不如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只要把自信建立起来,即使有一天不读书了,他们还可以面对自己和人生……
都觉得自己是为学生好,又都说服不了对方,天长日久,两个人的隔阂就加重了。申其军想,作为校长,再任你们这样乱来是我的失职。于是,他代表学校作出决定,包唐韬和杨菲教低年级,自己教高年级。包唐韬找申其军理论,我们好歹也是正规大学毕业,你不能瞎指挥,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苍蝇。申其军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让你们教低年级就是信任你们。包唐韬说既然打基础这么重要,你教了几十年,比我们有经验,这么重要的任务最好还是你亲自完成。不得已,申其军实话实说:眼看就要考试,再这样卖白亮晃(方言,混日子之意),这拨学生就没搞头(方言,前途之意)了。包唐韬说,都没试过你咋知道呢?我带他们,我比谁都有信心!
双方的争执起了头就没有尾。有一次,申其军受邀去湖北培训,回学校发现有学生在教室里打架,包唐韬不仅坐视不管,还说这不算打架,只要不头破血流,只要不是男生欺负女生,任他们去玩。盛怒之下,申其军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对涉事学生严厉批评。包唐韬认为申其军不光小题大作,而且指桑骂槐,当着学生的面,年轻气盛的他和申其军吵了一架……
不管是这些事情中的哪一件,不管当时自己再委曲、难堪,再出离愤怒,申其军后来都选择了遗忘、选择了谅解。他信奉君子和而不同,他相信这些只是教育观念的分歧,他觉得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天之骄子能以实际行动支持古路,能为穷乡僻壤带来活力,能为这些娃娃带来快乐并赋予他们一些自己所不具备的能力,无论如何,总是好的。觉出了别人的好,就要用自己的好来回报别人的好——对他们和他的冲突加以过滤,也算与人为善,也是投桃报李。如果就这样保持平衡也是好的,至少学校还在,至少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至少,他拿了二三十年的教鞭不会被淡出讲台,被铃声抛弃,像那些阴暗角落里随处可见的木棍般被岁月蒙上风尘。
事发突然。2009 年5 月,22 名学生离开古路小学,把学籍转到了永利乡中心校。学校是包唐韬联系的,转学是包唐韬组织的。为说服家长,包唐韬搬动了远在北京的“I Do”基金。基金许诺,事后也兑现,转学到中心校的孩子,每人每月给予250 元生活补贴,直到初中毕业。
申其军大光其火,问包唐韬为何要背后搞小动作,偷偷摸摸摸挖我辛辛苦苦砌的墙脚!当初你咋说的?你说你来是要建立完小,还要开办初中!
说他搞“阴谋”,包唐韬才不承认。小学撤点并校是政策方向,把学生转出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个思路,他也曾向申其军提起,只是关系僵成那样,多一言不如少一语,申其军没当回事,他也懒得多说。在申其军追问之下,他说树挪死人挪活,古路小学各方面条件都太简陋了,只有让学生到山下读书,同外面接轨,他们才有希望,古路才有希望。
申其军找区教办和县教育局领导讲理。他没想到的是,他们和包唐韬是同一个立场。2010 年9 月,又有32 名孩子迁离古路小学。随着这批孩子的离开,包唐韬也结束支教生涯回了湖北。他的师妹杨菲,则于一年之前告别古路。
古路小学重新回到“一师一校”时代,“朗朗书声云中荡”的旧日时光,却似乎是再也回不去了。28年间,申其军教了接近三百学生,这时只留下来五个孩子。树还没倒,猢狲却先散了,申其军心里被打翻的五味瓶搅得一片狼藉。
申其军没想到,就连“最后的果实”,他也没有保住。
2009 年11 月4 日,县教育局局长康克君来村里告诉申其军,为了让古路村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县上计划撤销古路小学,在校学生转校到乌斯河镇上由铁路部门与地方联办的“路地小学”,县政府已经做了研究,每月发给每个学生300 元生活补贴。
好好的学校,说不要就不要了?申其军想不通。
申其军对古路小学割舍不下,其实也是难以同自己泼洒在校园里的心血挥手告别,康克君知道,也理解。但是他说,边远山区教育的欠账,现在是到了必须偿还的时候了。教育不跨越,娃娃们接受的教育不充分,古路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又会产生新的欠账。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欠账过日子,一个地方、一所学校,也是这样。
五
2011 年11 月20 日下午4 点,申其军和剩下的几个学生一起举行了古路小学最后一次升旗仪式。看着孩子们蹦蹦跳跳地出校门,他知道,一切过去都已过去,“天边小学”即将从天边消失,又或者——正在消失。
曾经的代理校长申其军最终没有“感动中国”,也没有转正。如今的他在“路地小学”负责住校生卫生和伙食团管理,每月工资860 元,年底考核合格,每月另有340 元补贴。2019 年10 月里的一天,在“路地小学”促狭的宿舍里,申其军告诉我,这份工作,他是要干到退休了。申其军生于1963 年,能守着自己最后一批学生读书直到退休,他将之视为缘分。
“路地小学”坐落在乌斯河镇一台坡地上,抬起头来,大峡谷两岸像是默默注视着学校的另一双眼睛。尽管这里离曾经的古路小学很远,远到再怎么用力也不能看见,申其军还是习惯了在闲暇时举目凝望,在想象中,让一座山峰或者山峰背后的世界成为他的学校。这个时候的他看起来那么平静,而他平静的表情下,内心从来都不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