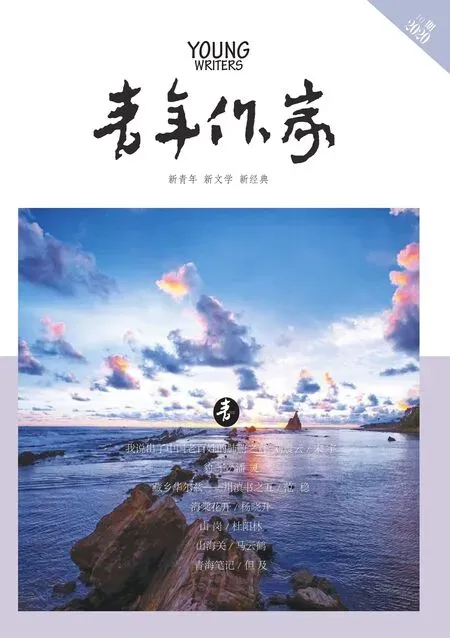青海笔记
但 及
年宝湖的夜晚
天暗了,雨也一阵阵地来了。顿时,风变冷,也变锐了。
前面,还有阳光呢。阳光千辛万苦,从云缝里挣扎出来,与我们会了个面。它高高地挂在蓝色的湖面上,朝我们抛媚眼,让我们拍照、嬉戏。没想到,性子竟这么短暂,一晃就闪失了、逃掉了。
我坐在湖边的草地上。满地开着碎小的花,金色,一大片,又是一大片。花骨朵像一把把小伞,撑着,散开着,铺满了大地。风一吹,花在瑟瑟地抖,又好像在无声地叫。湖上顿时有了雾,雾像纸张一样能卷起来,它涌着,越铺越大。前面就是雪山,刚才还醒目的雪尖,渐渐迷糊起来。更大的雾起来了,压迫着,围堵着。看上去,又好像不是雾,更像云。但那不是云,应该是雾。
年宝湖像一面长长的镜子,闪着光,展开着。雨,洒了下来,我舍不得走。我把冲锋衣裹紧,躲到一块岩石后。岩石挡住了风,但挡不住雨,雨落在脸上。我蜷缩着。雾气深重,在湖面上转悠,雨滴在湖上溅了起来,一波又一波,像麻花点一样。寒冷挟裹着雨往我身子里钻,连后背都感到了阴冷。
年宝湖是一个奇怪的湖。草甸一样的青山,在湖水前突然来了个变脸,青山戛然而止,突变成了雪山。这中间没有过渡。一脉青山绵延过来,草就没了,变光了,然后就有了雪,雪越来越多,爬满整个山峦。山,清冷,寂寞,默不作声。这样的景观我从没见过。
湖边有桑烟,那是下午藏人做煨桑仪式留下的。烟,还在袅袅地盘旋着,伸到了雨幕里,与天化成一个颜色。湖边没有一个人,只有雨打在草地上的沙沙声,像雪珠在树叶上弹跳。湖面上,雾气在变厚、变大,风起云涌,没多久就罩住了雪山的一角。雪山躲藏起来,成了雾的一个影子,带着某种诡谲和灵异。
年宝湖,当地人叫海子。据说,年宝湖的后面还有一千多个这样的海子。这里海拔有4200 米,如果这个天真的被雨水笼罩,那明天的骑马穿越就要泡汤。我想进入这一片片海子,到里面去探一探、望一望。在一个个海子的旁边,轻轻走过,用目光抚摸,当一个过路的行者。这一千多个诱惑,在眼前跳跃,让我又痒又不安。
雨大了,稀里哗啦地响,我往回逃。后面有三间帐篷,那是我们过夜的地方。那是三个固定的帐篷。顶是一个布篷,四周却有钢架,安了一扇扇玻璃窗。同伴们在准备晚餐,他们用随身汽炉烧香肠米饭。香味在帐篷边沿弥漫开来。
香味进鼻,却没有激起我的食欲。我的肠胃一直在咕咕地唱,不适一阵阵袭来。昨天的烤羊肉,让我经历了一场折磨,此刻还没全消。蓝色的炉火在丝丝地叫,同伴在说笑。窗外正在变黑,夜已迫近,就在眼睛前面。冷雨在飘,吹起像风筝一样彩色的经幡,对面山坡上一群牦牛在移动,前面有人在引路,正在赶往回家的路上。人和牦牛都走在夹着雨的暮色里。
旁边有溪,水在流,野花围着溪在摇,四周静谧极了。透过帐篷,能远眺年宝湖,雾气已完全遮住了山,只露出单调幽冷的湖面。桑烟还在雨中,在为孤独燃烧。牦牛正在过溪,它们蹚水,半个腿浸在溪里和草里。一个同伴呼啦啦地奔跑出去,像遇上火烧一样,原来他要去拍牦牛。
天完全黑了,因为雨,我们被锁定在了帐篷里。计划的湖边篝火,又唱又跳,都消失了。夜,围住了我们的三间帐篷。四周是黑色的草甸和无边的大山,荒无人烟。没有水,没有电,只有越来越大的雨声紧紧捂着我们。雨帘,像个大罩子,而帐篷就像个小罩子,大罩子套着小罩子。
我吃了两口饭,就回了自己的帐篷。这里有一排低矮的床,今晚将有四人挤在一起。地上有一块地毯,已经湿了。旁边还有一个老鼠洞,敞开着,好像随时有老鼠会进来。窗下,青草顽强地插进来,潮气和无边的黑暗从四面八方涌来。
看不到雨,但能听到声音。雨落在厚厚的草甸上,哗哗地响,单调中仿佛又有节奏。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其实,真的是什么也不能做。我就坐在属于自己的床位上,床位很窄,间距不到一米。就这样,坐在黑暗中,听雨。雨,一阵大,一阵小。同伴都在另一个帐篷,电瓶灯亮着,单薄的光线穿越过来,落在我床前。男男女女在一起,就有欢乐,声音不时传来。
司机们闯了进来。是金师傅和大雄,拿来了酒和食物。他们邀我加入,但我没食欲,肚子一阵热一阵冷。于是,他们两人摸黑吃着,但你能感觉到他们嚼得很香,像在啃鸡翅,又像在吃花生。他们话很多,滔滔不绝,声音里还会带来酒的香味。上路时,他们没声音,现在话匣子开了,竟很会说。金师傅叫我老哥,一个劲地老哥长老哥短。我只能模糊看到他们的轮廓,觉得他们十分可爱。
终于,钻进了睡袋。屋子里还留有酒香。四个人挤着,动弹不得。不久,便有了呼噜声。大家都累了。
迷迷糊糊到了半夜,听到嗒嗒的声音从头后响起。一摸,有一摊水,原来是窗子破了,漏雨了。赶紧起来,打开头灯,慌乱封窗。窗外,景物糊成一团。雨在喧哗,好像比白天还强劲。夜更深地包裹着我们,隔着窗子,也能感到外面的空荡和凉意。
肠胃依然在折磨我。我起来,摸黑掏着药瓶,再放进嘴里。每回出门都好好的,这回,冒险不带药,结果却中了招。药是金师傅给的,霍香正气水,不完全对路,但只能将就。黑暗中,我把那浓浓的中药味吞进肚去,然后木然地坐着。床上,有人在翻身,还有人问几点钟,就像在说梦话。
雨好像轻了,出去走走的愿望竟紧紧地抓住了我。
我打开头灯,一束光亮照亮脚前。胡乱裹上冲锋衣,走到了野外。巨大的夜如黑洞,深不可测,缥缈深远,头灯的光细微如丝。我把冲锋帽翻起,踏入浸饱雨水的草甸上。空气寒冷,但又清新得仿佛走进森林。我张开嘴,用最大的劲吸入肺里。我知道湖的方向,但此刻根本看不到湖。黑,密密实实,又无边无际。我知道,自己离湖很近,我能感受那股洪大的水汽。
夜气裹着,我继续走,更大的黑暗像门一样敞开着。
头灯在照耀,刺破飘来的雨丝,但在这片空旷里,它仿佛就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山与湖化成了一团,密不可分,大地山川正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接纳我。更广阔的幽暗在前方,它是那样的新鲜又刺激,带着神秘与莫测。
我继续向前,心头竟升腾起了一道柔和的光芒,并化成喜悦。我成了夜的一部分。
冰川与花朵
站在阿尼玛卿面前,有种晕旋感。可能来自高度,也可能来自灵异。
阿尼玛卿主峰由三个海拔6000 米以上的峰尖组成,“阿尼”是安多藏语,含有美丽、幸福或博大无畏的意思。“玛卿”的意思是黄河源头最大的山,也有雄伟壮观之意。此刻,我站在主峰的下面,这里的海拔也有5000 多米。云层灰且厚,沉沉的,好像山也透不过气来。领队沮丧地说,他来这里三次了,从来没见过阳光。我说,不要灰心,弄不好今天会有。领队对我的话置之不理。
风很烈,伴着呼啸声,每走一步,仿佛后面有人在推。风托着我在走。
跟前是一片山丘,碎石满地,高低不平,我沿着荒地而上。海拔太高,脚有些飘,人也有些悬空感,好像踩在一片不真实的土地上。如此荒芜的景色从未遇过,这里寸草不生,全是乱石。乱石堆满了整个山谷,这些石头大小不一,自由地散落着。风一个劲地往衣服里钻,寒冷冲击着面颊。此刻,竟下起了雪,雪花末子一片片地在乱石缝里起舞。
一座硕大的冰川耀眼地展现在眼前,浑然又壮观。以前,在江孜,目睹过卡若拉冰川,但那是在冰川的脚下,有着距离,远远地观望。今天可不同,冰川就在面前,触手可及。一大坨的冰从雪山的缝隙里钻出来,流水突然凝固,冰封在大地上。现在,你仿佛还能看到水流的印子,看到昨日奔腾的模样。
云层更低了,挤压着雪山之巅。雪末子在飞舞,但不大,若有若无。我在乱石上爬,想靠近这冰川,登上这冰川。诱惑鼓动着我。
心,在怦怦地跳,好像要蹿到空中。路,是没有的,我只能手脚并用。回头一望,只有两个人跟着。同伴像大多数游客一样,在雪山面前摆了个姿势,合了一个影,就消失了。此刻,估计正躲进车里,避风去了。
终于,在大风的陪伴下,我靠近了冰川。
眼前是一块巨大的冰,一块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冰块。它傲慢地横在面前,展示出它的不可一世和恢宏气势。冰看起来不像冰,反倒像是大理石,布满了纹路,有横的,也有竖的。冰川并不干净,上面满是污垢,像是雪后被踩过的大地。有那么几处,甚至很脏,上面被黑色覆盖,黑的占比多,白的占比少。
我静静地靠近它,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水流声就在这时出现,那是冰川在融化。嘀答嘀答,嘀答嘀答,声音清晰。在冰川的最末端,高耸的冰突然被掏空了一截,形成一道沟壑。大地仿佛伸出了一只无形的手,在一点点地挤榨眼前的冰川。水,在一滴滴地流,汇成水流,蜿蜒而下。这些水滴最终会变成汹涌的激流,变成江河和大海。站在冰川面前,就仿佛站在时间面前,听水滴声就好像在看时光的流转与变幻。
我在沟壑间穿行。
同行的两个人开始翻上冰川,一男一女,他们在冰川上行走。我也从沟壑里出来,紧随其后。巨大的冰就在脚下,踩在上面还能听到吱吱的响声。在冰川与沙石的接缝处,融化的冰水顺着沙石往地下默默地渗透……
听领队说,他前年来的时候,冰川还在前面,两年后,冰川又退后了许多。我不敢设想,照这样的速度,眼前这个冰川离它的毁灭还有多久。悲哀之情油然而生。冰川,由于年代的久远,里面记录着地球的秘密,解剖冰川就能目睹地球的变化,然而眼前这巨大的冰川正在一点点倒塌与消融。
从冰川撤下,回到车旁,我已精疲力竭。就在此时,奇迹发生了。一缕阳光拉开一道口子,冲出了厚厚的云层。阳光如一道垂直的瀑布,一下子照亮了阿尼玛卿的主峰,也照在我们身上。我既惊讶又紧张。“神显灵了。”我对着领队大叫。
我展开四肢,跑向乱石丛,躺倒在地。现在我变成了仰视,用一种最低矮的姿势看着这山这冰川以及这阳光。阳光直逼而来,抚摸冰川,冰闪耀出白色的光,与阳光交融到了一起。就在这时,在乱石丛中,我看到了一片苔癣。
苔癣之上竟然有几朵黄色的小花。
我抬起头来,被这庄严的小生命吸引。此时,小花骨朵也在阳光里展开了肢体,生命在如此贫瘠之地依然怒放。它带给我的惊叹与冰川同样巨大。
阳光很吝啬,不到一分钟又溜走了。云层又复原了,重新压住了群山。
越野车发动了,载着我们离开阿尼玛卿。我有些不舍,不时回头,喃喃自语。我与那巨大的冰川和那微不足道的小花朵做着告别。
禅画师
大伙们都进了寺院。塔尔寺,数年前我来过。我不想再跟随导游重复一遍,只想清静地逛逛,看看寺院的外围。
同行的司机坐在小店前喝茶小憩,吞云吐雾地抽烟,他们劝我到对面的山上,换一个角度去看看这座寺庙。
山不高,一会儿就登上去了。从高处远眺,寺院尽在眼底,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风是热的,从寺院那边吹来,经幡几乎都把山包裹了,在我耳边响亮地翻动。我看见寺内的人流,他们如蚯蚓般蠕动。一拨拨虔诚的人们,在叩头和上香,在传递着敬意。寺院里飘出来的香味,若有若无地在鼻前闪烁。
从山上下来,还有许多时间。同伴们还在寺院里。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各种小摊热闹、拥挤,藏地的刀子、牛角、珍珠、虫草、衣裳,拥堵了我的眼睛。还有音乐,藏地粗犷的声音,从店铺里蹦出来。我喜欢这样的音乐,乐声里有一种辽阔与原始。这对我是陌生的。
街,太闹腾了。有人在推销牛角木梳。有人提着珠子在叫卖,恨不得马上塞到我怀里。我一一躲开。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间冷清的店面,门开着,没人进出。它与其他的店铺形成反差。
转入门径,我看到了画。墙上都是画。唐卡,我心里一惊。满眼都是唐卡,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唐卡,以前只在画册、电视上看到过。我有一种期待已久的陌生感。
画是繁复的。藏地的景象,宗教的仪式,还有一种我道不清的缥缈存在感。每个空间都画满了,没有留空。我有点看不懂这样的画。
主人出现了,很轻的脚步,带着一种憨厚的笑。我们寒暄,他向我介绍画。墙上大部分是他的作品,也有他兄弟的,也有其他人的。我看不出区别,但他很清楚。他还跟我讲故事,说画里面的宗教故事。
店外很热闹,人来人往。还有他的孩子,大约三岁,不时从门口窜进来,又窜出去。屋里只有我和他,还有唐卡,我们被唐卡包围。他说这张三千,他画了两个月。另一张一万,他画了一年。我以为听错了,一年?我问。是的,他肯定地说。一张画要花一年时间,我难以想象,惊讶写在脸上。
然后,他给我看两者的不同。作为一个初阅者,的确分不清里面的区别。他介绍用笔和层次。我跟随他的手势,第一次进入了唐卡的细部。一点点,一点点,我进入了画作。我的心就停留在他的指尖上,在指尖的引导下,在繁复和细腻中穿梭。我进入了藏地的山水、寺庙、花卉、庭院。我在多彩的画布上跳跃、翻腾,甚至好像闻到了里面的气味。
我惊讶开了。我读懂了,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与汉地的画不同,它们需要用心去读。
过后,他坐下,继续他那张晾在门口的画。我站在他后面。他拿起笔,一支很细的笔,然后屏住了呼吸。
他的神态是安宁的,就好像我不在身边。笔尖,开始在画布上行走,很慢,很细致。我看着,看这支笔是怎样游走。就像绣花一样,在一针一线地走。笔很轻,画时就像在撩头发丝。这让我惊愕。我第一次看到唐卡是这样一点点被“绣”出来的。我明白了他需要画一年的道理。
再看他的手,我发现是弯的。手指已经变形,呈弯钩状。
他的孩子在门口奔跳,有时还摔倒,但他似乎都没看见。他甚至忽略了我的存在,专心在画布上。没有说话,凝神在了画上面。画是安静的,他这人也是安静的。外面的街头依然嘈杂,但没有人进来。
我的内心渐渐升起了几分敬意。我看到他好像不是在作画,而是走进了画中。他成了画的一部分,在里面的山川河流里,在寺院里,在云端里。
离别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张名片。青海热贡吾屯艺术中心,加扬华旦,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背后还有这样一行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神情依然安详,递名片时还有谦卑的动作。
离开这间小屋,再度走在浑浊、喧哗的街上,仿佛经历了一次沐浴。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感。人头满满,密布大街。还有一辆辆的旅游车,带来一张张中国脸和外国脸。同伴们依然没有露脸,我独自在走,心里却装在了唐卡的世界里。
我想,有时,寺里和寺外是一样的。修行的方式是多样的。塔尔寺里有香火,对面的山上有香火,一张张薄薄的唐卡里依然也有香火。我目中无人地走着,仿佛走进了藏地的神秘与斑斓里。
塔尔寺外阳光正明媚。
山顶上的节日
快到久治时,滂沱大雨扑面而来。大雨,洗去了越野车上积满的灰尘,我们在疲惫与困顿中,踏进了久治县城。
一到久治,就有消息传来,因为煨桑节,城里住满人了。城里的旅馆都让藏民住上了,我们预订的县府招待所被迫取消。于是,我们只能去住更小的招待所,没有水,没有卫生间。 一夜是偎着雨声度过的。
天透亮时,雨还在下,稠密又急迫。远处是山,坡上的草经过雨水的洗刷,绿得像毯子。山坡上有影子在晃,还有五颜六色的旗子。我看不清,于是就取出相机,把长焦对上。一拉,吓了我一跳。是人,确切地说是坐在马背上的人,他们在雨中扛着旗,朝着山顶走。我想起来了,今天是煨桑节。然而,在这样的雨中,他们照常举行,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山坡上,人越来越多了,都骑着马往山上赶。许多人没带雨披,身上背着沉沉的东西,手里举着幡旗。彩色的经幡张开着,鲜艳夺目。
来到街头,更热闹了。男人及男孩们占领了马路,盛装打扮,满脸笑意。雨,在他们眼里仿佛消失了,他们不畏惧,好像就盼着这节日的到来,无暇顾及这眼前的雨了。不时,有马队、摩托车队经过,浩浩荡荡,神采飞扬。
这真是一种久违的场面。小时候过年,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这种快意和期盼,而现在,我在久治重拾了这种记忆。甚至,从情感而言,可能更强烈更炽热。面前的藏人,强壮,黝黑,然而我好像能揣摸到他们的心,他们在期盼赶快融入到节日中。
大批的人还在往山那边拥。千条路,万条路,汇成一条路。十点钟,煨桑法会就要开幕,连我这个汉人也都知道了。我的心跳得更鲜活了,我也想跟着上山。
雨,此刻,竟停了。太阳毛毛的,躲在云层后面。我与同伴在一起吃早饭,我就忽悠他们一起参与,但他们态度犹豫,拖拖拉拉。直到十点多了,一行人才出发。下了雨的草地,又让马儿践踏了一番,变得泥泞。好在有高帮登山鞋,不怕泥泞,在湿地里照样自如。藏人已不见踪影,山坡上,只有我们几个外地人在吃力地行走。
久治的海拔3800多米,还要再爬一座山,难度系数有点大了。原先以为,转过一个山坳就到,结果不是。转到山的背面,才发现煨桑大会竟是在另一座山的山顶,一看,高得吓人。山顶,已站满了人,几千人,在呜呜地叫,一阵又一阵。离奇的是,山顶上覆盖了一层白色,我不明白那是什么。
半山腰间,停满了摩托。藏人都是骑马或骑摩托上山的。
天已彻底放晴,山顶还在遥远处。这里是高海拔,畏惧心理不时升起。但上面却又像是在施放魔法,尤其是一阵阵原始又粗犷的喊声,紧紧地抓住了我。无论如何,我得上去,毕竟这样的机会难得。我奋力徒步。
高原登山与平原不同,每走几步,就会气喘。但那阵阵海浪般涌来的声音,好像在给我鼓劲,让我脚下生出几倍的力来。同伴拉开了,分散了,到最后一个人影也不见了。我催着脚步在走,不时停下,喘上几口,补充新鲜氧气。此时,山顶有人下撤,仪式似乎就要完成,我急了,竟奔跑起来。在高海拔奔跑是十分危险的,会缺氧、晕厥,但一种无形之力在后面驱使。有一阵子,感觉自己虚脱了,动弹不得。
我只能在山地上躺下,调整自己,身后有个声音一直在鼓动:上去,再上去。
快接近山顶时,遇上了最先下撤的人群,一大群,像长龙一样。藏人的微笑是迷人的。这是一种朴实的笑,灿烂又天真。每个经过我身边的藏人,都朝我投来微笑。“快结束了,你来晚了。”有人对我这样说。我开始最后的冲刺。
终于,登顶了。
眼前是一缕长烟,正腾空而起,扶摇直上。那是桑烟,煨桑节的主角。几百个男人骑在马上,围着幡旗和桑烟在奔腾、盘旋。呼叫声和马蹄声扭成一团。马的热气和力道扑面而来,男人的昂扬气也布满空间。
我湮没在了奔腾的马群里。马群在快速飞旋、转圈,做着逆时针大回环。马蹄声震得山顶也在发颤。经幡在风中翻动,发出响亮的击打声。一支支扛上来的幡旗,现在已围成硕大的一堆,高高地插在山的正中央。人们在祈祷,僧人在诵经,山顶热闹极了。
地上成了白色,像下了一场厚厚的雪。我一看,竟然是纸片。拾起一看,纸上还有图案和经文,人们正在抛撒纸片。一声未落,另一声又起,此起彼伏。
这真是生动的一幕:叠叠纸片拿在手里,随着口里的叫喊,纸片抛到高空,随风飘开,然后像花瓣一样纷纷落下。这个纸片就叫龙达,是祈福的纸片,上面有真言,也有咒语。原来,我在山脚听到的喊声就是抛龙达发出的。
呜——呜——
太阳也来了,缕缕阳光从云缝里钻出。龙达已变成地毯,厚达数厘米,掩去了原来的绿色草甸。我置身于一片陌生的海洋里,声音是陌生的,人群是陌生的,连山顶那片开阔也是陌生的。这里在塑造热情、奔放和豪迈。
每张脸上都写满了自信和骄傲。他们在喊、在叫,声音融到了大自然中。眼皮底下,能看到久治县城,声音正朝着县城方向传去。
我不会骑马,也不会抛龙达,但我好像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内心一直在澎湃,就像眼前的马蹄一样,在疾速地奔腾。
呜——
终于,我也喊了一声。尽管这声音很不像我自己,但我还是喊了出来,对着这片辽阔而又陌生的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