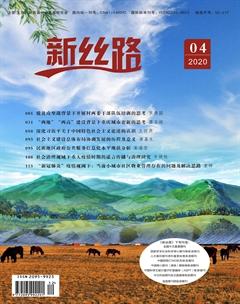建设我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思考
摘 要:随着世界范围内频发严重的生物事件,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也非常严峻,需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构建新型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筑牢“防火墙”,意义重大。
关键词:生物安全;生物威胁;治理体系
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一、我国生物安全的现实境遇
1.顶层设计生物安全规划日趋完善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非传统安全的战略视野,将大规模传染病等领域纳入关注视角,并制定各种生物安全战略或规划,如《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相关部委也提出了《“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十三五”健康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为生物安全研发提供了相关技术支撑和平台建设资源保障。
与此同时,国家先后颁布了与生物安全有关的如下法律和条例:《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2017年第二次修订)、《国境卫生检疫法》(1986年,2018年第三次修正)、《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2013年第二次修正)、《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主席令第53号,1991年,2009年修正)、《动物防疫法》(1997年,2007年修订)、《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2002年)、《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4年,2018年修订)、《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2019年)。《刑法》中涉及生物安全的条文共有17条,对传染病、生物恐怖、外來生物入侵和生物资源保护等进行了规定,但有关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和生物技术谬用防控的条款尚属空白。2019年10月23日,我国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
2.生物安全科技工作有所突破
(1)我国在重大传染病防控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对新突发病原体的发生、传播、致病机理、防治和预警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如发现了蝙蝠源冠状病毒、丝状病毒等烈性病病原体的起源、中间宿主、病原体与中间宿主的共进化关系以及跨物种传播感染机制等,并分析了H7N9、H5N6、EAH1N1等新发突发病原体的发生、重组、播散、损伤机制;成功研发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并研究发现了1600多种新病毒,另建立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数据库、鸟类迁徙数据库、野生动物疫病样本库及预警示范基地,为未来野生动物源性新发突发传染病监测预警奠定了基础。
(2)生物安全实验室为国家生物安全提供有效装备支撑。我国现已形成初步覆盖全国、功能较为齐全、作用发挥较为充分、管理较为规范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截至目前,已建成近80个三级生物安全P3(BSL-3)实验室和3个四级生物安全P4(BSL-4)实验室,覆盖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3)外来物种入侵甄别与防控初步形成体系支撑。在外来生物入侵防控基础研究及其防治技术与产品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入侵生物学学科框架体系初步形成。建立了上千种外来有害生物的DNA条形码识别或种特异分子检测等快速检测技术与产品,开发了多物种智能图像识别APP平台系统,实现了重大入侵物种的远程在线识别和实时诊断。
(4)生物安全特种资源库初步建立。我国陆续建成囊括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微生物资源、入侵生物标本资源、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信息资源等生物安全特种资源库。如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亚洲最大的医学昆虫标本馆、入侵生物标本资源库,以及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中国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兽医系统菌毒种保藏中心、中国烈性病毒资源保藏库等。
3.生物安全防御的短板和弱项
(1)顶层设计针对性不强。虽然我们出台了各种《纲要》、《规划》和一些规范标准,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生物安全法》,《刑法》里面仅有17条涉及生物安全。2004年我们出台的《传染病防治法》,在传染病应急事件和响应管理上规定的不够完善[1]。另外,相对于美国的盾牌计划、生物监测计划、生物传感计划和“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以及《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我们国家缺少具有国防和军事意图的科技项目。
(2)生物研发投入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国际重视生物安全并向大生物安全观——健康安全观转变的趋势下,全球各国都积极关注生物安全领域的研究。如美国,直到2019年底,美国管理机构共资助与生物安全相关的项目9893项,资助经费高达1592亿美元[2]。法国科研署共资助生物安全相关项目31项,累计经费约1060万欧元。日本自 2015年起,文部科学省拨付特别领域研究补助金资助开展“全球传染病等生物威胁的新冲突领域研究”项目。
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研发,我国虽然也对生物安全有关项目进行了立项,但项目数少,资助资金也比较少,以国家社科基金“公共卫生”为主题进行搜索,从1994年到2019年25年间,只有802项项目立项。
(3)生物安全防御联动机制不健全。在这次举国“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CDC(疾控中心)、军队CDC和地方CDC以及各级床染病医院,仍存在条块分割严重、隶属关系复杂、部门机构各自为政、协调机制不畅等问题,面对疫情,还存在短板、漏洞和弱项,远没达到对疾病的“可溯、可诊、可防、可治、可控方面合力攻关”,不能真正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信息共享和体系的健全完备。
二、对策和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领域
生物威胁已经从偶发风险向现实持久威胁转变,威胁来源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威胁边界从局限于少数区域向多区域甚至全球化转变,突发生物事件影响范围已经从民众健康拓展为影响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因此,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应从战略上重视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
2.推动科技创新,加强科研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科技不仅是打赢当前这场战争“最有力的武器”,而且还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国之重器”。他在3月2日的考察中说,“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为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倚仗“国之重器”。我们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要健全国家重大疫情监控网络,要研究建立疫情蔓延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科研攻关等方面指挥、行动、保障体系,平时准备好应急行动指南,紧急情况下迅速启动。
3.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以“法”的强有力手段恢复秩序、安定人心,处理常规和特殊变通亦大体有章可循,在非常时期、应急情况下从容镇定,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加快生物安全立法工作,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从法律制度上筑牢生物安全的“坚实底线”。
4.健全生物安全的联动机制
虽然维持一定力度的生物安全公共投入,但在政策协调、组织人事、物资供应方面存在薄弱环节,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存在短板,难于有效抵御网络生物安全等新型生物威胁。因而,在防控突发事件时,应建立央地、军地联动机制,解决应急措施短板等瓶颈问题,让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真正起到可防、可治的作用。
注释:
[1]徐缓.美国公共卫生应急法制化建设新动向及启示.中国应急管理,2009年第3期第50-54页
[2]李爱花、杨仁科、唐小利.美英法生物安全领域基金资助布局.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9年第28卷第1期
作者简介:
刘龙(1964--)男,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生物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