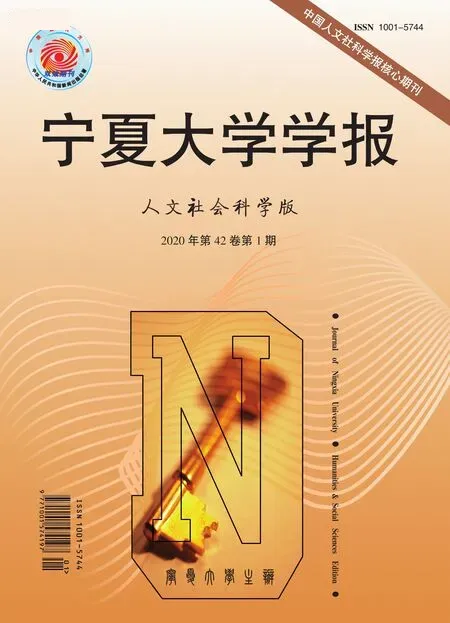描写翻译学视角下支谦译经的特色
——以《大明度经》为例
范晓露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图里(Gideon Toury)将规范性翻译理论改进为描写性翻译理论,并将研究方法具体化,对翻译作品 进 行 “ 全 面 历 时 性 描 述” (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ription),即从翻译的结果出发,去探寻对翻译产生了影响的社会历史因素, 从而定位、分析翻译作品在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功能。 对翻译作品采取历时性描述的这一视角,正好符合了汉译佛经跨越上千年、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时期经由不同的译师创作出不同译本的历史传播特征。 描写翻译学理论能够有效规避带有局限性的当下审美干扰,深度挖掘佛经译师的翻译特色以及其所翻译作品的特征和价值。 从描写翻译学理论的视角,我们尝试探讨在佛经汉译的进程中支谦的译经特色,以及他的代表作《大明度经》在创作过程中的历史背景、价值体现等。
一 关于支谦及其所译《大明度经》
在佛经汉译的进程中,三国吴支谦可谓是贡献最大的译师之一。 支谦,月支人,从黄武元年到建兴中(223—252 年)的三十年间,译经数十部,与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并称为早期佛经汉译的四大译师。 支谦在所撰写的《法句经序》中阐述了他译经的心得,成为我国有记载以来最早的翻译理论文章。
关于支谦,东晋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有如下记载:
越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 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
在早期译经史上取得成就最高的“三支”之一的支谦可以说是我国翻译史上当之无愧的“意译派”的祖师[1]。支谦主张的意译主要是为了便于读者更好理解经文意思,同时达到译文的简洁,兼顾文体的典雅。 支谦还擅长使用老庄的思想来解释佛教晦涩的义理,其所译般若经意义深远。
在支谦所译经典中,《大明度经》最能体现他个人的翻译风采,尤其是当中大量的意译词汇。 可以说《大明度经》是支谦的代表译作,并能为其他疑似支谦作品的鉴定提供重要参考依据[2]。 《大明度经》是汉代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的同经异译平行文本,原文本为梵文《八千颂般若》。 《八千颂般若》在各个时期为不同的佛经译师所翻译,前后共有七种汉译本,分别译于2 世纪至10 世纪之间,是考察中古时期汉语发展的最好证据。 但严格来说,各个汉译本被翻译时所据的《八千颂般若》具体样貌是什么,其究竟有多少个系统、每个系统多少文本,目前还无法确切考证。 正如辛嶋静志指出,这些不同的译本并非直接来自唯一的某一部原典。 换言之,不同时期的汉译本以及藏译本中的新旧语言共存现象,恰恰反映了其“原文”也处在一种发展变化的过程,而非一对一的关系[3]。这正好提出了我们在看待佛经平行译本时要如何摆脱佛经翻译中的 “原文”观念。
二 从目标语的角度窥视《大明度经》原文本的面目
佛经汉译是十分特殊的翻译行为。 首先,初译距今久远,重译次数多、年代跨度大。 在佛经翻译活动中,所谓的原文本,除了梵文、巴利文之外,还有其他西域的“胡语”,甚至可能是一个原文本中同时掺杂了梵语和中世纪时期印度语、方言。 并且,这些原文本多数已经无法保留最初的样貌,所以要想还原当初的翻译行为实为困难。 加之梵文语法构造与汉语差异尤大,深奥晦涩的佛教哲学词汇转换为汉语时又更加深了难度。 孔慧怡指出,由于佛经原文本的失传,加上年代之久远,能流传下来可以用于做文本对照的“原文”并不多。 而且作为口传文献,一部佛经拥有多个系统也是常有的[4]。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原文本、目标语文本在佛经汉译过程中的作用呢?
图里将翻译定义为目标语社会文化活动,提出了用 “发现—证明” 的过程来检验 “假定的翻译”(assumed translation)说,并使用以原文本条件为首的三个条件来推演[5]。 从这一点足以可见原文本在构成翻译时的重要性。 同时,图里也明确提出,原文本不会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就呈现于面前,所以我们必须先从目标语的角度切入去了解整个翻译活动。也就意味着对译本展开的研究工作变为最首要的任务。 所谓的译本研究则包括了不同时期、不同译者的平行译本对比。
《大明度经》的平行汉译本中,最早的是后汉支娄迦谶译的 《道行般若经》, 三国时期支谦重译之后,分别有前秦竺佛念译《摩诃般若钞经》、后秦鸠摩罗什译 《小品般若波罗蜜经》、 唐玄奘的两次重译:《大般若波罗蜜经》第四会、第五会(下简称玄奘第四会、玄奘第五会)、宋施护译《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 又有藏译本。
关于支谦译《大明度经》的原文本——梵文《八千颂般若》和各个汉译本、藏译本之间的传承关系,辛嶋通过对各传本的语言特色进行考据后分成了如下四组:
(1)支娄迦谶、支谦、竺佛念所译文本与犍陀罗语写本为最古老传本;
(2)鸠摩罗什、玄奘第五会所译文本为较古老传本;
(3)玄奘第四会为较新传本;
(4)梵文本、施护、藏译本为最新传本。
这当中,最古老传本和较古老传本之间并非存在一个明确的界限。 辛嶋认为较古传本包括了支娄迦谶、支谦、竺佛念、鸠摩罗什译本,以及部分鸠摩罗什、玄奘第五会的文本;较新传本除了玄奘第四会之外还包括了部分的梵文本、施护、藏文本[6]。 可见,新旧之间是既有交叉重叠又有先后继承的关系。 例如,玄奘第五会的译本就处于从较古老传本到较新传本的转换过程。 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所谓的原文本——梵文本,是始于11 世纪的梵语残卷,显然和最古老时期的样貌相比发生过极大的变化。 而完成于2 至6 世纪之间的汉译平行本显然更能为语言研究提供更多线索
辛嶋通过对支娄迦谶译 《道行般若经》 中的“呵”和“诃”进行了考察,发现正好反映了梵文源语中bh-和h 的发展,如ap(r)amānasuha<apramānasubha(诃波摩首诃(呵)天),从而推定支娄迦谶译出的汉语经典所依据的原文本中包含了中世纪印度语形式[7]。因此,我们在使用佛经的梵文原文本与汉译平行本进行校勘研究时,需要注意的是先从目标语文本出发去考察支谦的翻译行为,而非错综复杂的原文本。 尤其是像佛经,其原文本来源和途径都尤为复杂,甚至还有同一个文本内掺杂其他种语言的情况。
在《大明度经》中,支谦意译的词汇“水行天”,是其把原文本的ābhā(光)误译为“水”。 他把ābhā(光)与犍陀罗语ava(水,梵语āpas)相混淆[8]。 对比其他汉译本, 支娄迦谶、 竺佛念均音译作 “天”(“”应作“廅”);鸠摩罗什意译为“光天”。 鸠摩罗什的译本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前面的推想,支谦于此处确实是混淆了原文本中的犍陀罗语。 因此,我们在从事佛经语言研究活动的时候,为了了解原文本的面貌,需要充分重视目标语平行文本。 通过结合梵文原文本、汉译平行文本对勘的方式来解读汉译佛典,让原文本和目标语互相验证,使得佛经语言研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 从译者的翻译规范准则看支谦的翻译策略
既然翻译是一种以目标语为最终目的的社会文化活动, 那么肯定会受到历史文化等因素制约。规范准则处于绝对准则和个人风格之间。 规范准则被定义为:“将社会整体认可的如对待正确与错误,恰当与不恰当的看法等价值观念,转换为适用于某种特定情形的准则”。 在翻译过程中发生 “初始规范”(initial norm),指的是译者的总体选择。 这时译者或是以目标语系统又或是以源语系统来规范自己,则分别可能产生的是“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或“充分性”(adequacy)的特征。“可接受性不单是读起来像目标语言的文本”,而且“读来像翻译成目标语言的文本”[9]。翻译文本就处在充分性(面向源文)与可接受性(面向目标语言)之间的某个点,对这个点的定位便是翻译研究的目标。
支娄迦谶最早译了《道行般若经》,从文本的语言特色来看,虽然流畅却难免质直,音译词汇多。 不同于支娄迦谶偏爱直译、 把梵文的顺序逐句排列,支谦主要擅长意译,大量借用道儒教术语,删除重复的句子和段落,让“可接受性”在翻译中占上风。到了佛教开始渗透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之后,再后来译者们或者开始创立佛教专用名词,或者沿袭部分已经为受众所熟知的术语,从而又使得“充分性”的重要性达到了高峰。 当然充分性提高了之后,读者的负担也随之增加。 我们通过对支谦译经活动的描写,分析他是如何权衡“可接受性”和“充分性”,又是采取了怎样的翻译策略,从而影响了后世的佛经译师。
(一)意译
所谓的意译指的是译者的文化观、 翻译技巧,我们需要抛弃传统的“意译”框架,转而关注译本的实际功能。 在图里理论体系下,“初始规范”主要描写的是译文所呈现的语言内容,其中的篇章语言规范(testual-linguistic norms)便关系着包括用词、文体在内的译文语言素材的选择[10]。 支谦译《大明度经》时倾向于意译风格,主张经文应该通俗易解,所谓的“数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指的是虽然采用了更为简洁的意译手段, 使得译文长度被压缩、字数减少,但是仍然大体保持了内容与原文本一一对应的特征。 例如,在《大明度经》中的这一组佛教术语的翻译:
相对于早先支娄迦谶的音译手法, 支谦大胆采用意译,译为“重戒”“忍辱”“精进”“弃定”,简洁易懂,语义突出,并影响到后期施护的翻译。
通过对支谦译经进行比较,勝崎裕彦认为《大明度经》中下列这些意译词为支谦所创(括号内为支娄迦谶之对应音译词):
1.善业(须菩提);2.明度无极(般若波罗蜜);3.秋露子(舍利弗);4.无上正真道(阿惟越致);5.缘一觉地(辟支佛法);6.一切智(萨云若);7.闿士(菩萨);8.沟港道、频来道、不还道、应义道(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9.锭光如来(提和竭罗佛);10.除馑众、除馑女、清信士、清信女(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11.高士(善男子善女人);12.六度(六波罗蜜);13.地狱、恶鬼、禽兽(泥梨、禽兽、薜荔);14.转轮圣王(遮迦越王);15.慈氏闿士(弥勒菩萨);16.无怒佛(阿閦佛)[11]
例如“阿閦佛”,是梵文“aksobhya”的音译。意思是“不动”,菩萨心之不可动摇即无嗔恚,故支谦意译为“无怒佛”。 类似的译法在《大明度经》中比比皆是。 而像“一切智”这类佛教义理概念已经彻底通过意译成为固定词汇。 这类已经被确切考证为支谦特色的意译术语可以有助于我们研究标志为支谦译的部分疑似伪经。
图里在讨论规范研究时指出,有一些只是“可容许”(tolerated) 的行为, 可称为 “征兆性手法”(symptomatic device),就算出现的频率不高,也能反映某种规范,而这类行为从不出现则反映其他类型的规范[12]。 在译经中出现的增补、删减就属于“征兆性手法”。
佛经的论述往往将同一事件、同一句子反复阐明。 译者要想在不影响文采的同时,又将梵语佛经的原本样貌传达出来,确实“传实不易”。 因此译者的主动性的充分发挥就很重要了。 据初步统计,支娄迦谶所译的《道行般若经》约有八万余字,而支谦译《大明度经》则精简到了约49800 字,缩短了将近一半的字数。 例如下面这段支娄迦谶的译文:

表1
须陀洹不当于中住,斯陀含不当于中住,阿那含不当于中住,阿罗汉不当于中住,辟支佛不当于中住,佛不当于中住。 有色、无色不当于中住。 有痛痒、思想、生死、识、无痛痒、思想、生死、识,不当于中住。 有须陀洹、无须陀洹不当于中住。 有斯陀含、 无斯陀含不当于中住,有阿那含、无阿那含不当于中住,有阿罗汉、无阿罗汉不当于中住,有辟支佛、无辟支佛不当于中住,有佛、无佛不当于中住。 色无、无常,不当于中住,痛痒思想生死识无无常不当于中住。 色若苦,若乐,不当于中住,色若好,若丑,不当于中住。 痛痒思想生死识若苦若乐不当于中住。 痛痒思想生死识若好若丑不当于中住,色我所,非我所,不当于中住。 痛痒思想生死,识我所,非我所,不当于中住。 须陀洹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须陀洹道成已,不当于中住。何以故?须陀洹道七死七生,便度去。是故,须陀洹道不当于中住。斯陀含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 斯陀含道成已,不当于中住。 何以故? 斯陀含道一死一生,便度去。 是故,斯陀含道不当于中住。阿那含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 阿那含道成已,不当于中住。 何以故? 阿那含道成已,便于天上般泥洹。 是故阿那含道不当于中住。 阿罗汉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 阿罗汉道成已,不当于中住。 何以故? 阿罗汉道成已,便尽是间,无处所,于泥洹中般泥洹。 是故阿罗汉道不当于中住。辟支佛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何以故?辟支佛道成已,过阿罗汉道,不能及佛道,便中道般泥洹。 是故辟支佛道不当于中住。 佛道不当于中住。 何以故? 用不可计阿僧祇人故,作功德。 (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卷一)
对比之下,同样的内容,支谦译文则大大缩短:
沟港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 何以故? 七死七生便度去。 频来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 何以故? 一死一生便度去。 不还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 何以故?于上灭度。 应仪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 何以故? 应仪道成已,便尽于灭度中而灭讫。 缘一觉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 何以故? 不能逮佛道便灭讫。 是故不当于中住。 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 (支谦译《大明度经》卷二)
除了支谦独具特色的意译词汇“沟港道”“频来道”“不还道”“应义道”(分别对应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之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译文的简练、流畅、易懂。 支娄迦谶所译虽然忠于原文本,但是却导致了无谓的反复,行文枯燥、无趣。
但是,吕澂也曾指出,支谦尽可能地删除繁复的梵文以取得简便的效果,又将音译减少到最低程度,甚至连保留原音的陀罗尼也意译了,不免令人反感。 但同时也必须承认,从佛经翻译的历程来看,由质趋文是必然的趋势,支谦首开风气之贡献是不能否认的[13]。
(二)偈诵与梵呗
偈诵,梵文“gāthā”,最早在安世高的《七处三观经》中被译作“绝”、《道地经》中译作“缚束”。 安世高早先所译的“gāthā”字数参差不一。而支娄迦谶是最早将“gāthā”音译为“偈”的。
隋吉藏《百论疏》中有一段关于“偈”的记载:
问斯论既是长行。何故云论有百偈从偈立名。答偈有二种。 一者通偈二者别偈。 言别偈者,谓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皆以四句而成,目之为偈,谓别偈也。 二者通偈,谓首卢偈。释道安云,盖是胡人数经法也。莫问长行与偈,但令三十二字满,即便名偈,谓通偈也。 中论、十二门即是别偈,斯论谓通偈也。 婆沙列四种偈……所言偈者,外国称为祇夜,亦云竭夜。今略其烦故但云偈。此土翻之句也颂也。有人言,偈是此门之名,训之为竭。以其明义竭尽,故称为偈。
根据吉藏的这段记载,偈又分为“伽陀”和“祇夜”, 传到中国汉译之后便皆无区别, 统一称为“偈”。 “偈颂”是后世造出来的梵汉合成语。 汉译的偈颂部分,句子长度划一,字数规整,形式上尽量与中华韵文保持一致。 后汉的汉译偈颂形式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 到了三国两晋时代,受建安文学的影响变为以五言为主,南北朝末期的时候则七言增加,而由于受到隋唐诗歌形式的影响,宋代的译经中,偈的五言格式的势头又盖过了七言[14]。
据《出三藏记集》之《支谦传》载:
所出维摩诘、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二十七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 又依无量寿、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 注了本生死经。 皆行于世。
又,《高僧传》则提道:
其后居士支谦。 亦传梵呗三契。 皆湮没而不存。 世有共议一章。 恐或谦之余则也。
可见支谦除了译经之外,还会“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虽然这些作品皆已“湮没而不存”。 支谦根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等自制了梵呗。 后来,以支谦译《维摩诘经》《太子瑞应本起经》《般泥洹经》等有韵偈颂为基础,经师篇立传的僧(释僧并、释慧忍)和曹植、康僧会等人制作梵呗,又作了敦煌本《众经别录》的《咏瑞应偈》一卷,乃受支谦所作有韵偈颂之影响。 支谦在译经事业上充分发挥了其韵律天赋。
关于梵呗见《法苑珠林·呗赞篇》记载:
寻西方之有呗,犹东国之有赞。 赞者,从文以结音。呗者,短偈以流颂。 比其事义,名异实同,是故经言。 以微妙音声歌赞于佛德斯之谓也。
又《高僧传》:
若然可谓梵音,深妙令人乐闻者也。 然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 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 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绾。 五众既与俗违。 故宜以声曲为妙。
《释氏要览》卷上“梵音”条目:
梵音梵云呗匿,华言止断也。 由是外事已止已断。尔时寂静,任为法事。 又云诸天闻呗,心则欢喜……其梵声有五种,一其音正直,二和雅,三清彻,四深满,五周遍远闻。法苑云:夫呗者赞咏之音也,当使清而不弱,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滞。 远听则汪洋以峻雅,近属则从容以和肃,此其大致也。昔魏陈思王曹子建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音,清响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乃摹其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音兹为始也。
“呗”和“赞”一样,指用文字进行咏赞。 在印度凡是歌咏法言都称作“呗”。 主要形式为短偈。 汤用彤:“转读止依经文加以歌颂, 梵呗则制短偈流颂,并佐以管弦。 前者虽有高下抑扬,而后者则以妙声讽新制之歌赞,非颇通音律擅长文学者不办。 支谦依《无量寿》、《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 可见其深通汉文”[15]。
偈颂和制梵呗都是支谦擅长文辞的证据。 支谦在译经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梵语的音韵特点,兼结合汉文学中的四言、 五言或七言诗的形式,以迎合中土人士的阅读习惯, 更好地普及佛教教义。 这同时也证明到了支谦时代,译经事业在不断地发展成熟。
(三)合本(会译)
支谦对译经史的贡献还包括了他所首创合本,即“会译”的翻译体裁。“合本”指的是提取出佛经的各种译本中的精华, 删除累赘晦涩内容, 重新翻译、整合为新的内容。 陈寅恪曾指出:“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 ‘合本’与‘格义’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经典之方法。 自其形式言之,其所重俱在文句之比较拟配,颇有近似之处,实则性质迥异,不可不辨也”[16]。
《出三藏记集》卷七记载了支谦是如何“合”微密持经的。 支谦将所译《无量微密持经》《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邻尼经》《无端底总持经》三本(后两种为失译)合为《合微密持经》。 后来支敏度、道安皆模仿支谦合本的做法。 “合本”从文字上的校对慢慢发展为语义对勘。 如《出三藏记集》卷八记载,支敏度合《维摩诘经》,是因为他认为支谦、法护、叔兰三位译者“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 ”既不能“偏执一经”,也不能“广披其三”,因此将其合在一起校勘。 《首楞严经》最早为支娄迦谶所出,支谦将支娄迦谶等译的“异者删而定之,其所同者述而不改”,参照其他三种译本进行改定,谢敷做了合注。
(四)道教词汇
译经事业初始,译师们都难免受到道儒教的影响。 从道家经典中寻找可以匹配的词汇,可以更清晰地描述佛教中的哲学概念,例如“清静无为”[17]。像佛教这种外来的哲学思想初次传播进来借用了本土相似的概念来解释其哲学概念、术语,便是陈寅恪提出的“格义”。
而依据图里提出的“翻译的普遍法则”,首先,第一点是标准化法则,在这个法则之下原文本的特征会被忽略,去附和目标语文化模式的倾向。 当佛经刚传入中土时, 必然处于比较弱小和边缘的地位,套用汉地民众更为熟悉的道儒教术语来翻译佛教教义则成为译者的一种习惯性选择。 其次,是干涉法则,指的是默认原文对译文的干涉,将原文中的语言特征复制到目标语中,特别是当佛教越来越为人民所熟知,声望渐长,变成一种重要的文化组成之时,干涉的宽容度就会变高[18]。
支谦所译《大明度经》与支娄迦谶、鸠摩罗什的风格大有不同。 例如:
善业言:“如世尊教,乐说菩萨明度无极,欲行大道当由此始。 夫体道为菩萨是空虚也,斯道为菩萨亦空虚也。 何等法貌为菩萨者? 不见佛法有法,为菩萨也。 吾于斯道,无见无得。 其如菩萨不可见,明度无极亦不可见。彼不可见,何有菩萨当说明度无极?若如是说,菩萨意志不移不舍、不惊不怛,不以恐受、不疲不息,不恶难此微妙明度,与之相应而以发行,则是可谓随教者也。(吴支谦译《大明度经》卷一)
汤用彤认为:“系援用中国玄谈之所谓道,以与般若波罗蜜相比附”[19]。 “道为菩萨是空虚”与道教宣传的虚无、无为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牟子《理惑论》释“佛”就提到了“佛”与“道”存在共通,为“无形”“无声”等。 支谦与牟子一样深谙《老子》之说。“道”也被称为“本无”,虚无之意,最早见于晋裴頠《崇有论》。 但在佛经中,汉代就常见了。 佛经中的“本无”指的是一切现象本性空寂[20]。
《大明度经》第十四品,梵文为tathatā,在各个时期被不同的译者分别译作:
1.《本无品》(支娄迦谶、支谦、秦竺佛念译)
2.《大如品》(鸠摩罗什译)
3.《真如品》《如来品》(玄奘译)4.《真如品》(施护译)
支娄迦谶、支谦均译为“本无”,后又译作“真如”。 “真如”即“体”,就是《老子》提的“道”。道为虚无,“真如”亦“本无”。
善业言:如来是随如来教。 何谓随教? 如法无所从生为随教,是为本无,无来原亦无去迹。 诸法本无,如来亦本无无异。随本无,是为随如来本无。如来本无立,为随如来教。与诸法不异,无异本无。无作者,一切皆本无,亦复无本无,等无异。于真法中本无,诸法本无,无过去当来今现在,如来亦尔,是为真本无。 (吴支谦译《大明度经》卷四)
支谦认为一切皆本无, 如来亦本无。 “佛”与“道”同样、“本无”与“如来”亦同样。
支谦所译经典中,但凡重要佛教概念几乎都受到《老子》的影响。 但是过度使用道教词汇翻译佛教术语难免会造成佛道概念的混淆。 正如孔慧怡说的,在佛经翻译漫长的900 余年时间里,佛教思想这一外来文化跨越了两种文化(主体文化是中国文化)进行传播。 佛教扎根于传统中国文化中,建立并维持了自己的参照系;作为外来文化产品,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各种规范产生的对抗和融合,就显示出翻译在进行文化协商时产生的各种现象[21]。
四 小结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断地在“可接受性”和“充分性”中间进行选择或妥协。 而我们在研究支谦的译经特色时,恰好可以通过分析充分性和可接受性去描写其从事译经活动时所面临的抉择。 不论是对佛教词汇的音译或意译、借用道儒教术语,还是大面积删减累赘句子段落、开创梵呗等,都可以让我们在外观上更深入地了解支谦的译经风格及魅力。 但过分追求美巧、适合汉人的阅读口味,不免会造成脱离原文本、影响到译文的忠实性,例如支谦将“须菩提”“舍利弗”等常见人名也意译为“善业”“秋露子”。 不管怎么说,这种不忠实原文本的作风也是支谦独具一格的翻译思想。 他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译经手段折射出佛教在汉地是如何得到传播的,从这方面而言支谦所译佛经当之无愧是佛教在中国的流行的重要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