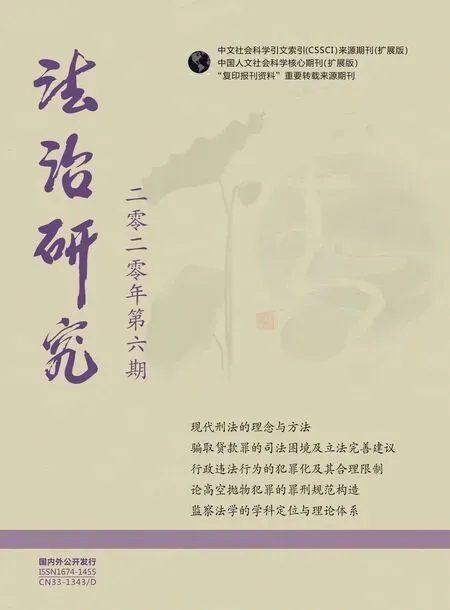公司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的体系解构*
——兼论《民法典》第70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的适用关系
赵 吟
公司解散清算是公司终结法人人格,清理现存财产以及债权债务关系,事关债权人、股东、董监高等各方主体利益的重要程序,分为破产清算与非破产清算。在非破产清算程序中,公司的各方主体利益一般都能得到较好的满足。但现实中存在许多公司在解散后不对公司进行清算,甚至未经清算就注销的情形,导致公司债权债务久拖不决,严重损害债权人及中小股东的利益。2017年通过的《民法典》总则部分第70条①2020年5月《民法典》出台后,将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吸收为总则部分,其中第70条内容没有任何变动,本文中除论及法院判决书原文内容外,统一表述为《民法典》第70条。《民法典》第70条规定:“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针对法人解散清算问题作出规定,其中关于清算义务主体范围及其侵权构成的规定较为笼统,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表述存在差异,致使如何协调二者的适用来确定清算义务人的具体侵权责任观点不一。在我国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明确清算义务人制度规则,厘清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解决《民法典》第70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的适用关系问题,是健全公司非破产清算制度,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保护相关利益者权利,形成良好的优胜劣汰之营商环境的有效手段。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清算义务人责任的分析和判定存在诸多问题。从法律依据的角度来说,作为认定公司清算义务主体范围的裁判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对此实践中部分法院已经有所认识,故而转向直接援引《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致使裁判出现分歧。②司法实践中,法院大部分仍选择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来圈定清算义务人主体范围,但也有小部分法院会选择以《民法总则》第70条为依据。如在方自炎诉长沙市岳麓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清算责任纠纷案(2020)湘01民终632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引用《民法总则》第70条排除案涉公司股东的清算义务人身份。同时,法官在裁判主文进行说理论证时,对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的分析也较为模糊,既难以将清算义务人独有的不作为侵权责任与一般主体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作为侵权责任区分开来,又在真正的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分析过程中大而化之地解析侵权构成要件,对细节但关键之处模糊处理,导致裁判中说理不充分,当事人难以服判。
事实上,司法实践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法律规定的不合理以及当前理论与实践对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要件系统梳理的不足。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一)恶意处置公司财产、骗取注销登记之侵权行为的误读
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债权人主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至第20条针对清算义务人规定了几种侵权责任类型:包括怠于履行清算义务造成公司财产贬损的赔偿责任、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清算不能的连带清偿责任、恶意处置公司财产或利用虚假清算报告骗取注销登记的赔偿责任以及未经清算即注销公司的清偿责任。有学者统一将其归为公司清算义务人的侵权责任,并将其划分为清算赔偿责任、连带清偿责任与清偿责任进行讨论。④参见段卫华:《论股东在公司解散清算中的义务与责任》,载《河北法学》2016年第1期。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将《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⑤《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认定为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的情形。例如(2020)鄂08民终453号判决中,法院将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注销登记论证为对股东清算义务的违反。⑥参见王秀峰诉唐平、王英翔清算责任纠纷案(2020)鄂08民终453号民事判决书:“现已查明,满鑫公司提交的清算报告是虚假的,由此可认定满鑫公司未经依法清算,仅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法人注销登记,导致王秀峰的债权落空,依据上述规定,王秀峰有权向公司股东唐平、王英翔主张赔偿责任……唐平、王英翔为满鑫公司登记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其在满鑫公司注销前负有法定清算义务,其不履行该义务即已存在违反法律规定之过错。其是否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是否参与清算,对于赔偿责任的承担,均不构成影响。”事实上,第19条的内容不同于另外两条,规定的是作为侵权责任。错误认识该条所规定的侵权行为性质,无疑会导致法院在审理恶意处置公司财产、骗取注销登记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案件时,将负有清算义务作为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遗漏不负有清算义务而实施了该类侵权行为的其他责任人。
(二)清算义务内容模糊导致过错分析有偏差
公司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适用的是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过错的判断多体现于对被告清算义务履行与否的评价之中。如(2016)鲁0203民初4584号判决中,法院未对被告股东主观认识的过错有特别说明,而是以具体清算义务的不作为为标识推定其存在过错。⑦参见李本祥诉青岛第四印染厂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案(2016)鲁0203民初4584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法院认定被告股东在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在强制清算程序中不能提交公司账册等重要文件,导致公司不能清算,客观上造成债权人的损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在过错判断中,若不能明确清算义务的具体内容,则容易将其他责任人之义务混入清算义务之中,从而扩大清算义务人的主观可归责性。因此,清算义务是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判定的核心要素,对清算义务内容的厘清,是判断清算义务人过错的前提。然而《民法典》第70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中均未对清算义务的具体内容进行准确定义或者列举,这便加大了法官裁判说理的难度。在司法实践中,除了启动清算程序这一应有之义务内容外,法院通常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将对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的保管义务认定为全体清算义务人之义务。与此相类似的案例还有(2019)沪0107民初14755号判决,⑧参见徐陈兰诉王春海、韩林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2019)沪0107民初14755号民事判决书。二者法院皆未对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的灭失时间和真正原因进行调查,径直将保管义务认定为所有清算义务人在公司整个运营、清算期间的义务,实则属于未将公司清算义务人之义务与直接责任人之保管义务区分开来的错误。也正是因为对清算义务内容认识不足,在(2020)浙民再103号判决中,法院在结合案情认定该案清算义务人不存在清算义务后,又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为依据判定其应对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的灭失承担侵权责任。⑨参见江苏海福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诉孙虹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2020)浙民再103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法院查明案涉公司未经解散直接由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因此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没有触发的条件,后法院又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认为其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实属自相矛盾。
(三)债权人以外利益受损者侵权赔偿请求支持依据不足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股东、公司诉请要求清算义务人承担相应责任的情况。⑩参见翟道远、伍冬睿诉仲晓东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2020)鄂01民终6073号民事判决书;无锡阿博华科技有限公司诉黄欢利、王文军清算责任纠纷案(2020)沪民申613号民事裁定书。然而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来看,债权人利益是清算义务人侵权行为的唯一客体。只有债权人可请求怠于履行义务的清算义务人承担相应侵权责任,这就导致了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法院对因清算义务人侵权行为而利益受损的公司、股东的权利保护大多持肯定观点。[11]虽然查阅到的股东、公司诉请要求清算义务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案例较少,但法院基本都肯定了有关权益属于清算义务人侵权行为客体的观点。参见卢晓云诉周旭光、宁波兴泰管业制造有限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2017)浙02民终1621号民事判决书;章永远诉李新方、赵晓春、钟菊方清算责任纠纷案(2015)台温商初字第3689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市新和诚食品有限公司诉李飞、叶映丽清算责任纠纷案(2020)粤0303民初12498号判决书。但在现有裁判中,法院证成其观点的思路基本上仍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为法律依据,佐以学理观点或引用《公司法》中有关股东权利的规定对其进行当然解释,来扩充清算义务人侵权行为的客体范围。如(2019)苏13民终821号判决中,法院说理阐述认为,即使《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并未规定中小股东的利益可成为清算义务人侵权行为的客体,但不能以此否定中小股东在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行为中受损害的事实,同时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享有对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请求权,清算义务人的侵权行为侵害其权利,就应对其承担相应侵权责任。[12]参见万松超诉金福斌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2019)苏13民终821号民事判决书。由此可见,股东、公司的利益是否能够成为清算义务人侵权行为的客体尚待讨论,即使在该条件成立前提下,法院在判决中也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如何对现有法律进行解释适用,以加强法院裁判说理的科学性,亦需明确。
(四)消极事实证明标准不一
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判定的要件之一。法院在分析因果关系要件时,需要双方当事人对各要件事实进行证明,以形成法官的内心确信。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明债务人已不能清算的证据之证明力的认定却不统一。对于债权人的举证,许多法院在其请求怠于履行义务的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时,往往要求其对仍未清算的公司申请强制清算以证明公司确实无法清算。[13]参见天津江城工贸有限公司诉青岛新永安实业有限公司货款纠纷案(2015)民抗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国电河南燃料有限公司诉濮阳市达源商贸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2856号民事裁定书;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诉陈秀英、吴成林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申2293号民事裁定书。然而在(2018)最高法民申5325号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债权人所主张的“公司无法清算”属于消极事实,不需要以公司必须完成清算程序为前提,债权人只要能提供证据使得法官产生公司不能清算的内心确信,即已完成其举证。[14]参见鹰潭金良汇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5325号民事裁定书。裁判的矛盾表面上体现的是法院对公司强制清算程序是否为审理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案件的前置性程序的观点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部分法院对清算义务人侵权要件中消极事实证明的认识错误。这种认识错误将导致清算义务人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证明规则设置发生偏差,难以保证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公正。
二、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范围界定
公司清算义务人的侵权责任作为一种不作为侵权责任,其责任的承担源于清算义务的违反。由于清算义务具有特殊性,谁应当作为义务的主体则至关重要。在我国,清算义务主体的确立虽然经历了从司法实践提出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间接规定,再到第9号指导性案例正式引入“清算义务人”概念,直至《民法典》第70条直接规定清算义务人之主体范围的历史进程,[15]参见梁上上《:有限公司股东清算义务人地位质疑》,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但在学界和实务界仍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因此在讨论具体的侵权构成要件之前,首先需要厘清公司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以避免在构成要件分析中混入对非清算义务主体清算义务履行与否的讨论。
(一)清算义务人相关概念辨析
与清算义务人常常同时出现的其他概念还有清算人、清算责任人以及配合清算义务人等。首先对于清算义务人的内涵,目前学界基本形成一致观点,即依法启动清算程序之主体。[16]参见张俊勇、翟如意《: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主体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19期。亦有学者将其更为准确地定义为:“基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的特定法律关系,在公司解散时负有在法定期限内启动清算程序,成立清算组织,并在公司未及时清算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失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的民事主体。”[17]王欣新:《清算义务人的义务及其与破产程序的关系》,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12期。而清算人则为公司解散启动清算程序后,实际上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理的主体,在我国《公司法》中相对应的为清算组[18]参见冯果:《公司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亦可用于指代清算组成员。[19]参见李建伟《:公司清算义务人基本问题研究》,载《北方法学》2010年第2期。因此,清算义务人与清算人存在于清算程序的不同阶段,清算义务人在启动清算程序后也可能进入清算组成为其中一员,二者在实质个体上可能有身份重合,但绝非同一概念,义务内容更是大相径庭。
清算责任人的概念出现在《企业破产法》第7条中,其规定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主体在公司解散后出现资不抵债情形时负有向法院申请破产的义务。[20]《企业破产法》第7条第3款规定“: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在对《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一》进行规定背景和目的解读时认为,清算责任人包括“未清算完毕情形下已经成立的清算组”和“应清算未清算情形下依法负有启动清算程序的清算义务人”。[2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答记者问,载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https://www.pkulaw.com/lawexplanation/3d855e5312f84971bb704d8550e7605dbdfb.html,2020年9月2日访问。由此可见,清算责任人是用于指代破产法上对已解散的资不抵债公司负有申请破产义务之主体概念,在不同的公司清算阶段指向不同的义务主体。
配合清算义务人为学者在其文章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实质为《企业破产法》第15条规定的对公司财产、印章、账册、文书等重要资料有保管义务的有关人员,[22]同注⑰。亦是后文论及的“直接责任人”。[23]关于直接责任人之义务与清算义务人之义务的区别与关联,以及二者义务违反与侵权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等方面的辨析,将在后文相应部分阐明,此处不再赘述。
(二)公司真正清算义务人辨明
1.《民法典》第70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对比解读
《民法典》第70条将清算义务人主体范围表述为“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有观点认为,该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对公司清算义务人主体范围的认定存在矛盾,《民法典》第70条明文规定的清算义务人仅限于公司董事,并未列举股东为清算义务人。[24]参见王长华:《论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的界定——以我国〈民法总则〉第70条的适用为分析视角》,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8期。这一观点属于对法条的误读,虽然我国《公司法》将股东会称为“权力机构”,但并不能否认股东会在公司的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董事选举、公司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上的决策功能,因此将股东会表述为“决策机构”未尝不可。并且,参考立法机关编写的释义书可以看出,立法者在规定清算义务人制度时已考虑到《民法典》第70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衔接问题,并没有否认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的地位。[25]参见王成《:〈民法典〉与法官自由裁量的规范》,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若仅对《民法典》第70条进行文义解释,清算义务人为公司董事或者股东,规定的是一个非限定性的主体范围。这意味着立法者为清算义务主体的认定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在对该条进行解释适用时可以在两类主体之间进行选择或组合。而就《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来说,其虽分别明确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主体,但并没有超出《民法典》第70条的规定范围,实质是根据两类公司不同的特性对清算义务人范围进行限缩的结果。因此《民法典》第70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之间就清算义务人范围问题并不存在冲突。
2.《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清算义务主体范围与现实脱节
关于《民法典》第70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之间的适用关系,原则上来说,《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作为《公司法》内容的深化理解和延伸,[26]参见陈春龙《:中国司法解释的地位与功能》,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应当属于《民法典》第70条“但书”适用范围,清算义务主体的认定仍应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为准。[27]对此,也有学者认为,清算义务主体认定应当适用《民法典》,《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内容早已超出《公司法》第183条规定的范围,不属于《民法典》第70条第2款但书部分的“法律”。参见钱玉林《: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适用关系论》,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但该规定中有关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主体范围的内容并不合理,既忽略了董事在公司经营管理直至清算阶段的重要性,又未能对属于清算义务人的股东之范围做合理限缩。虽然目前理论上大多数观点支持董事也应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只是就股东是否属于清算义务人以及具体哪些股东应当负担相应义务的问题尚存在分歧。[28]参见梁上上《:有限公司股东清算义务人地位质疑》,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张俊勇、翟如意《: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主体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19期;李建伟《:公司清算义务人基本问题研究》,载《北方法学》2010年第2期。但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在判决时仍直接将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认定为清算义务人,且通常不要求董事承担清算责任。[29]参见唐平诉王秀峰清算责任纠纷案(2020)鄂08民终453号民事判决书;范东斌诉王英翔、唐平清算责任纠纷案(2020)鄂08民终451号民事判决书;徐陈兰诉王春海、韩林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2019)沪0107民初14755号民事判决书;张明高诉魏由禹、丁祥惠等清算责任纠纷案(2018)闽01民终703号民事判决书。以上案件的裁判均直接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默认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另外,也存在一些法院在审理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侵权案件时,会有意识地考量是否不参与公司经营的某些中小股东对债权人的利益损失不应该承担赔偿或连带清偿责任,但因《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不合理的规定,只能另辟蹊径,将对部分公司股东的免责分析纳入侵权构成要件说明之中,而这事实上是案件在进入实质侵权构成要件审理之前就应该处理的主体范围问题。[30]参见北京凯奇新技术开发总公司诉西安高新区西工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清算责任纠纷案(2020)陕民终34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被告为案涉公司持股仅有5%的小股东,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证据显示其参与过公司经营或者选派人员担任该公司机关成员,事实上其根本就不具有清算义务人主体资格,然而因为法律适用困难,法院只能在构成要件分析中,证明其不履行或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公司不能清算造成债权人损失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
3.董事与对公司有控制力的股东作为公司清算义务人的理由
一方面,清算义务来源于公司执行、决策机构人员的信义义务。信义义务源于英美法,其具体义务内容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忠实、勤勉义务相同。[31]参见刘凯《: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及违信责任》,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对于董事来说,其忠实、勤勉义务延续至清算组接管公司财产并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理分配之时。就基于控股关系、投资协议等原因事实上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控制力的股东来说,其也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但这里的信义义务不是因为出资关系而产生的不得滥用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利益的消极义务,[32]参见刘怿《: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清算责任》,载《中国商论》2019年第10期。而是在公司解散这一特殊阶段与董事相同的积极作为义务,即清算义务。
另一方面,从债权人与公司股东利益保护平衡的角度来说,即使清算责任规则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受损害的债权人利益,但也不能过于忽视部分中小股东未参与公司经营,实质也属于“受害者”的事实。[33]参见李清池《:公司清算义务人民事责任辨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号》,载《北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15卷,第67页。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9号指导性案例中,利益保护的天平可谓是全然偏向债权人一方。[3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第9号指导性案例: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而(2016)最高法民再37号判决中,虽有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意识,但仍以债权人利益为先,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中小股东负有更高的举证责任。[35]参见上海丰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诉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案涉公司的财务皆由另一股东公司的财务科管理,被告股东实际上并未参与案涉公司的经营管理。在此前提下仍以负有清算义务为前提要求其证明自身不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侵权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实际上加重了被告股东的证明责任。由于案中的被告股东是具备相当证据收集能力与应诉能力的公司,可以承担繁重的诉讼成本,而对于更多类似案件中的中小股东尤其是自然人股东来说,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法律意识和应诉能力,难以自证。鉴于此,在清算义务主体范围中排除对公司经营管理没有控制力的股东,要求其仅需对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将能更好地平衡中小股东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清算责任的滥用。
4.清算义务人的认定应当回归《民法典》第70条
以上从应然层面解释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和对公司有控制力的股东是真正的清算义务人,但在实然层面,若坚持单独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需要解决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主体规定不合理的问题。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尚待修改,实践却急需合理解决路径的现实情况下,《民法典》第70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之间的柔性选择适用事实上更为合理、高效、便捷。不难发现,虽然《民法典》第70条对清算义务人主体范围的规定并不具体明确,但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解释余地和自由裁量空间,通过对第70条进行目的性缩限解释,可在将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纳入清算义务人范围的同时,把对公司没有控制力的中小股东排除在清算义务人范围之外,以使义务主体的认定更符合立法意旨。[36]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因此在涉及清算义务主体认定时,鉴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而《民法典》作为民商事法律的一般法具有适用的正当性,且通过合理解释能够修正《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的不足,故《民法典》第70条应当具有优先适用性。[3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一部分第3条指出,就同一事项,民法总则制定时有意修正公司法有关条款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与此同时,法院在对《民法典》第70条未详细说明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有较全面规定的清算义务人侵权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时,仍然可以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以发挥司法解释强大的漏洞填补和细化规则之作用。[38]参见陆青《:民法典与司法解释的体系整合——以买卖合同为例的思考》,载《法治研究》2020年第5期。
三、公司清算义务人的侵权行为与主观过错判断
在清算义务人不作为侵权的构成要件分析中,侵权行为、过错的判断与清算义务紧密相连,因此需要借助清算义务的性质与内容来剖析该类不作为侵权的行为要件与主观要件。
(一)公司清算义务人的侵权行为厘定
公司清算义务人的侵权责任本身属于不作为侵权责任,其来源于清算义务的规定,是对作为义务的违反。在我国侵权法上,作为义务通常表现为三种类型的法律规定:显性规定即明确作为义务之具体内容、具体隐性规定即虽未言明作为义务之内容但是配备了特别的责任或者法律后果,以及一般隐性规定即法律的基本原则或所遵从的习惯。[39]参见张东玉《:论我国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认定机制》,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4期。但无论何种规定,其共有的特征是不需要义务主体的作为行为,且正是因为义务主体的不作为才构成侵权的前提。《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所规定之恶意处置公司财产以及骗取注销登记的侵权责任并未设定任何显性或隐性之义务,明显强调的是行为人的积极行为,若无行为则不发生侵权后果。实施了该积极行为,导致公司出现不能清算的后果,侵害债权人利益,就需要承担有关作为的侵权责任,承担该责任不以主体负有特别作为义务为前提。因此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必考量行为主体是否存在清算义务,亦不需要考虑《民法典》第70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的适用关系,可直接依据第19条进行裁判。而第18条、第20条的规定才真正属于公司清算义务人侵权行为规范,在判断是否要承担侵权责任前需要明确行为主体负有清算义务,这是不作为侵权责任的归入门槛。由此,得以将第19条规定的“恶意处置公司财产”以及“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剔除出清算义务人侵权行为的范围。
(二)公司清算义务人的主观过错认定
1.对清算义务的不履行即推定为过错
侵权责任主观要件的实质就是过错,过错意味着主观的可归责性,只有当客观上存在应当负责的情形,才有主观可归责性的可能。[40]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页。在作为侵权中,是当事人以自己行为招致的责任,探求行为人内心真实意思方能知晓其过错。而不作为侵权中,是因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其他先行行为、特殊职业要求等义务设置,使得当事人在未为任何积极行为之下就可能承担侵权责任,能够纳入评价范围的主体是小部分。其过错的判断标准就在于是否履行了作为义务,若未履行,则当然推定其存在故意或过失,而不必去探求其是否真实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由此可见,作为义务是过错构成的前提,亦是不作为侵权责任成立的核心。在清算义务人不作为侵权中,过错应当仅限于对清算义务的不履行,因此清算义务的内容、义务履行的方式和程度,是主观要件中必须厘清的一个问题,如此才能清楚地判断义务主体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积极义务的行为是否存在可归责性。
2.过错仅限于对清算义务的不履行
关于清算义务的具体内容,学者们多有讨论,目前基本达成共识的是启动清算程序、选任清算组这两种具体义务是清算义务的应有之义,但对于是否还包含监督清算、协助配合后续清算以及对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的保管义务存在较多分歧。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1款规定的是清算义务人侵权的一般赔偿责任,也是清算义务违反的最低归责标准,义务内容为“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说,当清算义务人没有履行法定期限内启动清算决议、选任清算组成员的义务时,就构成对清算义务的违反,具备了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观可归责性。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清算义务人在清算程序启动后极有可能又进入清算组执行清算事务,因此产生的妥善管理清算财产、清理公司债权债务等义务则不属于清算义务范围。[41]参见王德山:《公司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比较而言,《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第20条规定的是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和清偿责任,属于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加重赔偿责任。在此类造成公司不能清算最为严重后果的情形中,清算义务人不仅违反了及时启动清算程序这一作为义务,还存在对其他特别作为义务的违反。
首先是对公司财产、账册等重要清算文件的保管义务。清算义务人的保管义务并非从公司解散之时即负有,而是存在一定的合理“豁免期”。这涉及在公司解散后直接责任人对公司财产、账册等重要清算文件负有的保管义务与清算义务人之保管义务的衔接问题。《公司法》第183条规定,清算组应当在公司作出解散决议15日之内组建完成,这15日即为清算义务人的义务履行宽限期。在此期间,公司财产、账册等重要文件仍然掌握在直接责任人手中,若在宽限期截止前发生重要文件的丢失,则属于直接责任人而非清算义务人的过错,追究的也应是直接责任人的侵权责任。实践中,掌握公司财产、账册等重要文件的人员通常都是对公司有控制力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与清算义务主体存在大部分重合,因此容易误将宽限期内甚至公司未解散之前直接责任人的不作为侵权责任判定为全体清算义务人的清算责任。[42]参见张明高诉魏由禹、丁祥惠等清算责任纠纷案(2018)闽01民终703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法院将公司经营期间妥善制作、保管公司账册等文件的义务认定为清算义务人的义务。自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理论上清算义务人应当已经成功启动清算程序并组建清算组,相关账册等重要文件也应掌握并移交清算组。若此时清算义务人仍未积极掌握并移交这些清算资料,即违反清算义务,主观上存在可归责性。
其次是协助配合清算的义务。该义务与前述中对这些清算资料的保管义务相衔接。协助配合清算的义务内容是指清算义务人在清算程序开始时,应当将其掌握的公司财产、账册等重要文件及时移交清算组,不得无故扣留、隐瞒公司的会计账簿、原始凭证等重要清算资料。[43]参见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6页。因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对公司账册、重要文件等负有的清算义务实质上包括启动清算程序宽限期届满后的保管义务与启动清算程序后对公司账册、重要文件等的配合移交义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注意两种义务的发生时点,避免将直接责任人与清算义务人的义务混淆,以防止不恰当地向前延伸清算义务人之义务履行期,扩大其归责范围。
再次是监督清算的义务。有观点认为,清算义务人在清算过程中还应当有监督清算的义务。[44]参见刘敏《:公司解散清算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这实际上是以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为清算义务人的错误认识前提下对清算义务的误判。对公司清算过程进行监督,需要审阅清算组的清算报告等文件,这在自行清算程序中是股东会的职权。[45]《公司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应当制定清算方案,并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清算义务人并不因为没有对后续清算进行监督而存在过错。
四、公司清算义务人侵权的损害结果判断
清算义务人违反清算义务造成的损害结果不仅限于债权人利益受损,事实上还关涉公司财产所有权和其他非清算义务人股东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问题。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司财产毁损灭失,属于侵犯公司物权的范畴。对债权人利益承担侵权责任则来源于债权侵权理论,债权作为民事主体的法定权利可成为侵权的客体已为我国理论和实务界的共识。[46]参见周华《:侵权法中债权损害的确立及发展》,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第8期。公司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债务人财产受损,间接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就股东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来说,权利的本质为基于出资比例或者所持股份而享有的,对公司在缴付完各种费用以及清偿债务后剩余财产的给付请求权。虽然在权利实现的顺序上次于债权,但同样可能因清算义务人的不作为受到损害,故不可忽视。
(一)非清算义务人股东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亦是侵权行为的客体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0条仅规定了清算义务人应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公司和非清算义务人股东是否也可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呢?
就公司而言,其财产所有权不是清算义务人侵权行为的客体,因为清算义务人承担侵权责任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若公司已解散还未注销,此时公司虽仍有主体资格,但已失去经营能力和目的,其本身对资本维持不再有需求,即使诉请要求清算义务人赔偿补足因其不作为而导致的财产损失,其也不再是最终的受益者,最后仍需完成清算并将财产分配给债权人及股东。若公司未经清算即被注销,此时公司主体资格不再,也就没有公司利益一说。因此将公司损失与债权人损失等同视之,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徒增诉累。
但公司股东是可以在公司正常清算程序中获得财产分配的受益者,《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虽然只考虑到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却也没有明文禁止股东行使赔偿请求权。并且参考请求法院对公司强制清算的主体变化来看,《公司法》第183条只赋予了债权人申请法院对公司强制清算的请求权,但《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7条将主体范围扩大至公司股东。[47]《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7条第3款规定“:具有本条第二款所列情形,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进行解读的文章中认为,公司解散而不清算对股东也会造成严重损害,仅赋予债权人申请强制清算的请求权而置股东需求于不顾,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48]参见宋晓明、张勇健、刘敏《:〈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1期。同样,在债权人通过侵权之诉获得利益的保护之后,应当允许能够证明自身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受损的股东向清算义务人追责,如此才能在公司解散清算制度中贯彻一致、公平的权益保护理念。
不过,并非所有的股东都能够诉请清算义务人对其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受损承担侵权责任。[49]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公司设立、治理及终止相关疑难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2期。当部分股东与清算义务人身份重合时,其自身的不作为就是损害结果的发生源,应对义务不履行造成的后果与其他清算义务人一同承担责任,在一致对外完成清偿之前,不得要求其他清算义务人对其进行赔偿。
(二)《民法典》第70条第3款可成为裁判的直接依据
通常情形下,特别法应比一般法对法律关系的规定更为清晰具体,但当出现特别法没有规定而理论上又应当成立的情形时,就需要从一般法中寻找最能支持裁判观点的法律依据。据此,在非清算义务人股东请求清算义务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案件中,法官在寻找法律依据时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中。当其中没有对非清算义务人股东权利保护的直接依据时,应当将目光放回规定清算义务人制度的一般法即《民法典》第70条。《民法典》第70条第3款规定,清算义务人不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民事责任。该条对清算义务人侵权行为的客体未作限定,规定的仅是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与结果要件,存在非常大的解释空间。所以,与其参照适用明确规定侵权行为客体为债权人利益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再佐之以理论或其他间接规定进行当然解释,不如以《民法典》第70条第3款为直接裁判依据并对其进行适用解释更为便捷及合理。
五、公司清算义务人侵权的因果关系判断
在讨论公司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证明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在清算义务人侵权案件中,债权人、非清算义务人股东的损失并不能当然地归因于清算义务的不作为,其客观因果关系需要进行具体的判断。倘若只要二者权利受损就要求清算义务人担责,将造成清算义务人责任过重,很可能产生打击股东投资积极性的负面效果。[50]参见叶林、徐佩菱:《关于我国公司清算制度的评述》,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1期。
(一)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关于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的判断,目前我国通说采用的是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即行为并不要求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达到必然、精确引起的程度,只要能够使得损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变得更高,就可以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51]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228页。这种因果关系认识在不作为侵权关系中尤为突显。不同于作为侵权,不作为侵权中的因果关系链不是平行的,其成立往往是义务人的不作为与其他原因介入的结果,[52]参见李小光、王曙华《:论侵权法中的不作为因果关系》,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5期。在清算义务人侵权案件中常表现为清算义务的违反与其他责任人行为的结合。如在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的同时,还可能存在导致公司财产、账册等重要文件灭失的其他直接责任人行为,以及未经清算擅自将公司进行注销登记的行为。因此如何把握清算义务的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存在一定难度。
实践中,对清算义务人侵权因果关系要件成立的判断,通常会比较清算义务人之义务产生时点与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情形出现时点的先后顺序。当公司出现法定的解散原因时,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开始产生,在公司财产的损毁、灭失发生于公司解散之前的情形下,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与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公司财产的损毁、灭失发生在公司解散之后,债权人、非清算义务人股东的损失才与清算义务人的不作为存在因果关系。[53]参见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诉上海滨海实业发展总公司、上海市自来水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387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法院认为二被告股东清算义务产生时,债务人的动产及不动产早已被冲抵债务或强制拍卖,其剩余债务亦被相关法院以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而裁定中止执行。债权人不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的情形发生在公司清算义务产生之后,法院可以推定两被告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原告的债权未得到清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类似案件还可参见北京北鹰吉成科技有限公司诉王倩倩清算责任纠纷案(2013)一中民终字第6082号民事判决书;柯晓燕诉衷汉春、熊国铭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2018)闽0782民初987号民事判决书。这种以损害发生时间为锚点的判断方法具有标准化、易识别的特点,有利于法院在后续各方当事人的举证中,形成对侵权因果关系成立于否的心证,且不需要排除其他直接责任人行为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影响,也正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相契合。
(二)因果关系证明规则中消极事实的认定与证明
关于因果关系的证明,我国原则上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故债权人等原告应对其主张清算义务人侵权行为与自身损害之间因果关系成立的相关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由于清算义务人侵权系不作为侵权,待证事实中存在诸多消极事实[54]消极事实为当事人在举证过程中提出的某种事实不存在,或某法律上的评价结果不存在的待证事实。参见陈贤贵《:论消极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以〈民诉法解释〉第91条为中心》,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5期。,这类事实对于提出一方来说通常举证难度较大。原告若要举证义务人没有履行作为义务,往往需要搜集大量的证明材料,且很难达到直接证明的效果;而被告只需提出自身已为履行义务做出了努力的证据,相对简单得多。鉴于此,在公司清算义务人承担侵权责任情形中,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规则。[55]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院民二庭课题组《:不当履行清算义务案件审判实务若干问题探析——以常州市两级法院的审理情况为研究基础》,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7期。由清算义务人对侵权要件中的消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此前提下,法院在审判中需要明确清算义务人侵权中哪些属于待证消极事实,以及债权人对于消极事实的证明是否完全不需提供任何证据。
一方面,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不能清算应当属于要件事实中的消极事实。公司能否清算之事实的查明,有赖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存在与否,而这些都是债权人和非清算义务人股东不可掌握的清算资料,若要求二者对其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则基本不可能。[56]参见陈旭《:怠于清算股东清偿责任之诉中消极事实主张的查明》,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20期。对此,该消极事实应当转化为清算义务人可举证的积极事实,由清算义务人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仍然存在,公司可以清算,以完成其举证责任。[57]参见中国印刷物资总公司等诉刘金龙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2013)一中民再终字第10728号民事判决。该案中,法院认为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已灭失是消极事实,根据司法常识,消极事实无需举证,如若清算义务人认为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没有灭失,对于此积极事实有举证义务。在具体案件中,当债权人等原告已经提供能够证明债务人不能清算的初步证据时,如若仍然要求其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进行强制清算作为诉讼进行的前置程序,事实上是要求原告对债务人已清算不能之消极事实的证明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违反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规则。并且就向法院申请债务人强制清算这一前置性程序来说,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债权人诉请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中证明自身的具体损失数额。因为在赔偿责任中,清算义务人起到的只是补足债权人损失的作用,仍需以公司正常清算分配所得的清偿为先;而在债权人诉请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中,则没有这一清偿顺位要求。所以要求债权人申请法院对债务人强制清算以证明公司无法清算,既是消极事实证明规则的配置错误,又是对该证明手段作用的误解。
另一方面,举证责任的倒置并不意味着原告对其提出的消极事实完全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在起诉之时仍需对债务人不能清算的事实存在提供必要的初步证据。例如,原告可以提供其在工商部门查询到的债务人已被注销或已解散但仍未组织清算的工商资料和法院因债务人已无财产可执行作出的终结执行裁定。[58]参见吴庆宝《:公司无法清算之举证责任分配》,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10月9日。又或者,原告在身份上同时属于公司股东和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债权经法院长期执行仍然不能实现。[59]参见鹰潭金良汇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5325号民事裁定书。清算义务人如要否定该消极事实的存在,就需要提供更为充足的证据,使得法官的内心确信达到高度盖然性,而不仅仅是使法官内心产生合理怀疑、令该消极事实变成真伪不明的状态。[60]参见杨剑、窦玉梅《:论消极要件事实的证明——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7期。
六、结语
在《民法典》生效后,实务中审理公司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案件首先需要明确《民法典》第70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0条的适用关系,准确判断公司清算义务人主体范围,方能将适格主体带入侵权构成要件的具体分析中。《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不是清算义务人不作为侵权的适用规则;清算义务人的过错应区别于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过错;同时要注意除债权人的利益外,非清算义务人股东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受损亦可成为违反清算义务的损害结果,不能忽视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在因果关系要件的判断中,要合理把握清算义务的不作为与侵权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相当性,明确要件事实中消极事实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避免错误地提高债权人初步举证的证明标准。
公司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的系统化分析,有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清算义务人主体范围不清、构成要件分析不明的困境,通过统一裁判标准,助力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不过,正确的法律适用始终以科学合理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对清算义务主体及要件的规定已在实践中表现出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建议新一轮的《公司法》修改将公司清算义务人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纳入其中,一定程度上明晰清算义务人范围、清算义务内容以及侵权责任核心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