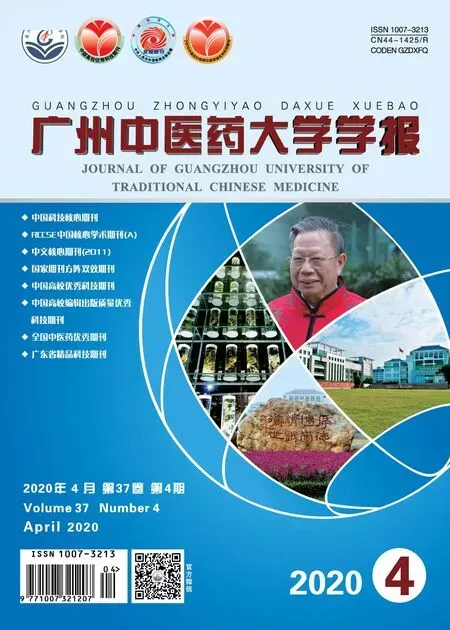从《广州近代老中医医案医话选编》和《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赠诊医草》论近代广东中医之学术风貌
林振坤, 宋文集, 李乙根, 卢巧毅
(1.广州市中医医院同德围分院内一科,广东广州 510130;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广州 510360;3.广州市中医医院同德围分院妇科,广东广州 510130)
近代广东频繁的中外交流,一方面导致鼠疫、霍乱等外来传染病进入广东,并频频流行,给社会经济和民众健康带来极大损失[1];另一方面西学东渐,社会崇洋风尚盛行,西医传入并迅速发展,使中医面临强劲的竞争对手,而民国政府又屡屡给中医的发展设置障碍,使中医陷入困境[2]16-19。这些纷然涌现的来自疾病、社会、学术、政府等方面的挑战,给近代的广东中医带来强大的冲击。广东中医实践者们由此开始反思传统中医理论体系,探索与西医学、近代科学的对话方式,以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在这纷纭的时代与激辩的哗声中,广东中医日常的临床诊疗是什么样的?哪些才是他们真正关注的话题?在西医东渐的浪潮里,他们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学术风貌?这对于增进对那个时代广东中医学术史之认识与理解,具有一定的意义。以下以《广州近代老中医医案医话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赠诊医草》(以下简称《赠诊医草》)为例,试作一探讨。
1 《选编》与《赠诊医草》
《广州近代老中医医案医话选编》(简称《选编》)由广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在文革前编纂,后由广东省医药卫生研究所中医研究室于1977 年和1979 年两次改编出版。1979 年版的《选编》在1977 年版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内容,以下所论以1979年版为据。
《选编》中收录了近代广州8 位老中医即程康圃、潘兰坪、易巨荪、陈伯坛、黎庇留、吕楚白、吕安卿、杨鹤龄的医案与医话。程康圃,名德恒,广东高明人,生活于清代道光、光绪年间(1821-1908),程氏为业医世家,尤精儿科,所著《儿科秘要》 为其毕生行医与祖传经验之结晶[3]168,[4]点校说明1。潘兰坪(1807-约1886),名名熊,兰坪为其字,广东番禺人,精研叶天士的理法,著有《评琴书屋医略》《叶案括要》,为清末岭南“叶派”代表性医家[3]168-169,[5]影印说明1。易巨荪(?-1913),名庆棠,巨荪乃其号,广东鹤山人,著有《集思医编》,未见存,另有《集思医案》[3]168,[6]。陈伯坛(1863-1938),名文炜,字英畦,广东新会人,光绪20 年(1894)举人,著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卷十九〉》《麻痘蠡言》等[3]168,[7]。黎庇留,名天佑,庇留为其字,广东顺德人,著有《伤寒论崇正编》,其子黎少庇建国后整理父亲医案,编成《黎庇留医案》[3]168-169。当时易、陈、黎,与谭彤辉(号星缘,又作星沅,南海人)以专研经方著名,在清末广州医界颇负盛名,时人称其为“四大金刚”[8]。吕楚白(1869-1942,名绍珩)[2]404、吕安卿(1876-1950)[9]为广东鹤山人,同一祖辈,世代业医,为民国时期广州妇儿科名医[4]167。“二吕”曾为广州医学卫生社社员,吕楚白历任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师,著有《妇科纂要讲义》《幼科纂要讲义》与《内科纂要讲义》等[2]404,410;吕安卿则未见有专著存世,《选编》所录医案出自门人雷仁生[4]167。杨鹤龄(1875-1954),广东大埔人,近代广州著名儿科医家,著有《儿科经验述要》[4]点校说明1。医史学者吴粤昌(1915-1989)曾将吕楚白、吕安卿、杨鹤龄与郭梅峰(1879-1970)并称近代“岭南四大家”,认为此四家为“岭南医派的奠基人”,其持论和治绩“开创了岭南医家的新风气”[10]。《选编》收录8 家医案208则,医话41则(见表1),多从各家医著摘编而成,病种丰富,门类齐全,有些医家的医著如今已难以获见,故此《选编》为研究岭南医家学术思想与诊疗特色的极佳文本。

表1 《广州近代老中医医案医话选编》载录医家医案与医话数目Table 1 The amount of medical cases and medical notes recorded in the Selections of Guangzhou Modern Veter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Medical Cases and Notes n/则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赠诊医草》(简称《赠诊医草》)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赠医处初期的病案记录,载录卢朋著、陈惠言、冯瑞鎏、陈任枚、梁翰芬、陈颂冕6位医家的应诊医案,曾连载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辑的《中医杂志》1927年第3、4、5 期,郑洪等对之进行整理,附录于《南天医薮——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史》[11]155-175。
卢朋著(1876-1939),名雄飞,广东新会人,时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药物学、方剂学教员”,编有《方剂学讲义》《药物学讲义》《医学史讲义》 和《四圣心源提要》[11]26,135-136。陈惠言(1869-?),名汝来,广东南海人,时为“全体生理学教员”,著有《生理学讲义》《形体生理学》《内科杂病讲义》等[11]26,136。冯瑞鎏,广东南海人,为“伤寒、温病教授”,著有《伤寒论商榷》[11]26。陈任枚(1870-1945),广东南海人,为“病理学教员”,1927 年至1936 年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 著有《温病学讲义》(与刘赤选合著)[11]26,42-44,127-128。梁翰芬(1876-1960),广东番禺人,为“诊断学、疗治学教员”,兼赠医处主任,著有《诊断学讲义》《治疗学讲义》等多种[11]136。陈颂冕事迹不详,当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早期教员。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是当时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中医学府,《赠诊医草》之6位应诊大夫既是中医专校之教员,也是当时广州中医国手[12],故《赠诊医草》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东中医临床之基本风貌。
2 《赠诊医草》与《选编》里近代广东中医之日常
《赠诊医草》共载录55位患者的医案,病案患者多为一病数诊,最多者达6诊。当时大概实行医师轮班制,故患者首诊与复诊常由不同医师接治,体现出不同医家对同一病患的不同诊治特点。从病种来看,《赠诊医草》中诊治疾病最多的是外感发热,占56.4%(31/55),其他的是咳嗽、泄泻、眩晕、风湿骨痛、胸膈疼等,以内科常见病、多发病为主,与今日中医日常门诊无异。《赠诊医草》医案行文都较为简洁。从《中医杂志》原文来看,其时当有使用统一印制的处方笺,所以医案格式相同,首言舌色,次脉象,次证候及说明,最后是处方明细及医家签名。“证候”和“说明”两项是病案的主干内容。“证候”主要叙述主诉及其他各种症状、病史,复诊时则会简述病情的变化,记录多较简略,有时只有两个字,如“腹痛”“发热”等,记录较为详尽的会提及既往史,多数只列述几个主要的症状,体现了当时广东中医日常病案记录简洁扼要的特点。“说明”则是对“证候”的辨证论治,包括病机判断与立法两部分,有些医案则只言病机判断或者立法,二者仅及一。从“证候”与“说明”两项,可以看到当时中医日常临床“以证括病,执证驭繁”的特点。
虽然中医也强调“辨病”,但从《赠诊医草》来看,当时中医对于“证”的记录与重视,显然甚于“病”。这并非指《赠诊医草》的大夫们不辨病,而是他们常常将辨病“隐括”于辨证之中,如第6 案之陆氏[11]157-158,陈惠言首诊认为该患者“由中气虚弱不能消化而成痰饮”,可见陈氏认为是痰饮病,其表述的重点则在于“中气虚弱不能消化”这个病机上;冯瑞鎏二诊时未言何病,仅说明是“里有寒滞而气虚”;卢朋著三诊时“自胸至心腹胀痛”,认为是“下焦虚寒,浊气上升,但上焦有微热”;此后陈任枚四诊、卢朋著五诊、陈惠言六诊,均是据证而立法、处方、用药,“病”的概念消隐于对“证”的思辨与阐述中。
这样的现象在《选编》中也随处可见。虽然《选编》的医案均列于特定的病名下,如温病、风温、咳嗽、咳喘、哮喘、肺胀等,但这样的归类是后来的编辑者所为,其准确性、病名概念的清晰性本身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在这些医案里,一样可感受到当时医家日常诊疗中“以证括病”的思维方式。如杨鹤龄有一个很精彩的医案,治1例三龄小儿半载久热不退,前医或谓湿温,或谓疳积,而杨鹤龄则未言是何病,从其神态焦躁,不肯就医,按腹部与额灼手而腹不胀,舌绛脉数等,认为这是“热在肝经,乃肝火郁结也”[3]14-15。“热在肝经,肝火郁结”显然是病机判断,是“证”而不是“病”,虽然从交代的背景可将此案归入中医“久热不退”一病,这一点杨鹤龄应该也很清楚,中医对于“久热不退”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与对应的方药,但这个医案的重点显然在于突出杨氏的识证精准与用药精到。另外,当时医家会诊时的争论,也常常在“证”而不在“病”,如黎庇留治罗某案[3]8:“六月间患发热,口苦,大渴,请某医诊治,用大剂小柴胡汤去法夏加栝楼根、白茅根与服。次早,发热如前,且加鼻衄颇多,某医认为热迫阳络,于前方加犀角、竹茹等与服,亦复如故,且增加辛苦。请余往诊……余认为此悍热乃阳明急下证发热汗多者,即瞩其家人速煎大承气汤与服”。
这种“以证括病,执证驭繁”的思维方式,体现出“证”为广东中医日常临证的最基本元素。虽然辨证的方法在中医学术发展中不断丰富,但“证”一直是一以贯之的“公式”,正如卢朋著评论黄元御《四圣心源》所言:“算数之推算也,数数而算之,无一公式以通之也。唯代数则有公式以通之,不必数数而算之也。黄氏之医术,一以贯之,殆犹代数式欤”[13]。正是这一公式,在面对“遍考医书,鲜有说及”的烈性传染病“大癍症”时,杨鹤龄从传统的“癍者……胃经热盛之故”的病机与证候出发,认为“此症乃因热毒重极而致”,“痧癍症”与“毛癍症”则是“感染暑湿热毒而成”,从而制定对应的治疗方药[3]117-120。也正是基于疫毒毒极的认识,在西医束手无策时,易巨荪、黎庇留等从仲景《金匮要略》“阴阳毒”得到启发,以升麻鳖甲汤化裁治疗鼠疫[3]121-127。
可见,虽然面对西医的竞争、大规模新发传染病的挑战,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近代广东中医或许在思想上出现过各种时代涟漪,但日常诊疗仍然秉持传统中医基本理论,以证括病,执证驭繁,故能从传统理论中汲取经验,以中医学术特有的能动性,应对时代的纷纭。
另外,当时报刊上充斥着关于中西医的激烈论辩,而在日常的学术探究中,传统经典内的命题实际上依然是近代广东中医热切关注的话题。《选编》医话部分收录了程康圃《儿科秘要》与杨鹤龄《儿科经验述要》的主要内容。此两书于儿科诊法与疾病辨治均有精彩的发挥,代表了清代中叶以来岭南儿科的学术成就。从篇章话题的设置看,程康圃、杨鹤龄关切的仍然是中医儿科传统的话题,比如小儿手纹诊法,小儿脉法,以及小儿风热症、急慢惊风、咳嗽、疳积等的辨治,内容范围不出300 多年前明代《万密斋医学全书》。当程康圃、杨鹤龄详尽地阐述小儿手纹浮沉、纹色、纹状的主病,小儿分经用药及隔一隔二治疗方法,以及为小儿急慢惊风、慢脾风、暑湿热泄泻、湿温、疳积等提供富有岭南特色的论述与方药时,其呈现的是中医学术理论体系内在的发展,只是时代与岭南风土赋予了程、杨新的经验与认识。
3 《赠诊医草》与《选编》呈现的近代广东中医之学术风貌
从《赠诊医草》与《选编》来看,近代广东中医至少呈现出以下3个方面的学术风貌。
一是仲景学说始终是近代广东中医日常临证的基石。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在广东中医心中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清末岭南士人出身的中医均以通晓仲景之书为时尚[8]。而仲景学说在岭南的传播,最为炫目的便是以精研经方闻名广州医林的“四大金刚”——易巨荪、黎庇留、陈伯坛、谭彤辉的出现。这四位医家在日常临证中积极应用经方,这在历来被视为高温多湿的“瘴疠之地”的岭南,在视温热为正途的岭南医林,引起了莫大的震撼,对经方在岭南的应用具有垂范的效应,对后世岭南医家有着深远的影响。《选编》所录易、黎、陈医案,多是危重、疑难坏症,均多方三家采用经方力挽狂澜。1924 年陈伯坛于广州开设中医夜学馆,从学者四五十人,座无虚席,多为其时在广州的执业名医[14],可见当时中医界对仲景学说之热衷。《赠诊医草》中也有两位精通仲景学说的医家——冯瑞鎏与陈惠言。冯瑞鎏为“伤寒温病教授”,“在当时学校教习伤寒颇有名气”[2]241,其《伤寒论商榷》字析句释,鞭辟入里;《伤寒论讲义》汇集历代各家注析,足见其对《伤寒论》一书与仲景学说钻研之深邃。《赠诊医草》中其处方用药也每每可见经方家笔意。陈惠言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主讲《生理学》《形体生理学》等,中医基础理论涵养精深,对《黄帝内经》《难经》等经典原文娴熟,“许多卷篇均可一字不漏背诵”[2]326-327。同时其对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研究也极为深刻,常在报刊发表关于仲景学说的研究论文,其《内科杂病学讲义》即是以《金匮要略》为蓝本分章编述。在日常临证中亦每用仲景方,如所著《星聚草堂医案》,以及《赠诊医草》中均可见大量经方医案,实岭南一经方大家。而《选编》与《赠诊医草》中的吕楚白、吕安卿、卢朋著、梁翰芬等虽不以研究仲景学说闻名,但其临证用药亦常以经方化裁,如吕楚白以葶苈大枣泻肺汤合旋覆代赭汤化裁治哮喘[3]24,吕安卿以麻杏石甘汤加味治奶哮[3]25、卢朋著以小柴胡汤化裁治风热类疟[11]168、梁翰芬以甘麦大枣汤加味治肝热生风之眩晕[11]162等,可见发展到近代,仲景学说已内化为中医学术的基因,在“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的岭南,亦复如此。而近代岭南医家传承仲景学术注重实用,不事玄谈,与清初以来伤寒学研究注重仲景辨证论治的思想方法的学风一脉相承。
清代初期与中叶,以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的江南温病学派兴起,温病学派约在清代中叶传入岭南后,虽然作为岭南伤寒“四大金刚”之一的易巨荪曾有“《温病条辨》,陋书也;银翘散,陋方也”[8]的批评,但很显然,在多湿多热的岭南,至少外感热病的诊治仍以叶、吴温病学派理法为主流,就如陈惠言这样的经方大家亦不能免俗,如《赠诊医草》第46 治周棉案,陈氏认为是“外感而兼有伏暑”,处方以土忍冬、连翘、赤芍、莲梗、芦根、桔梗等[11]171,其辨证处方显然与叶派无异。而易巨荪、黎庇留最为得意的以仲景升麻鳖甲汤治疗鼠疫案,其于升麻鳖甲汤中也只是取其中的升麻、鳖甲、当归、甘草四味,宗仲景重用升麻以升透疫邪,“人感毒气……病从外而入,亦当使之由外而出,故升麻一味为此病要药”[3]126,应用时加入其他解毒凉血之品,黎庇留常用犀角[3]121-124,易巨荪案中则“用当归四逆汤,以苏梗易桂枝,加紫草、忍冬、竹茹、枳实……入升麻鳖甲汤散”[3]126-127,可见其方虽取诸仲景,但用药与理法则已入于叶、吴温病畛域。生活于嘉庆至光绪年间的潘兰坪,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在岭南引介、传承叶天士学说的医家,其在《叶案括要》自序中言:“叶氏医案一书,诚学医者暗室明灯,患病者孽河宝筏也。余生平遵先生治法,疗病罔不奏效,故每举是书以勉同道”[5]7。《选编》中潘氏医案皆选自《叶案括要》,为“生平遵叶氏法治验之案”[5]7,其中议病处方,充分展示出潘兰坪对叶氏理法的熟稔。这些医案不仅包括温病,还有内科、妇科医案,使叶天士学说在岭南的传播早期便呈现全面性、系统化的特点。潘氏之后研究叶、吴温病学术的岭南医家日众[4]124,特别是在应对近代岭南频发的瘟疫时,常被视为“临证指南”,并在实践中结合岭南风土民情,逐渐将其“岭南化”。如林庆铨《时疫辨》言:“疫病……余历考方书,唯叶氏天士、吴氏鞠通二家论辨最为精详”[15]7;同书联元之序言亦云:“今之鼠疫,即以叶、吴之法治之不验,然而离叶吴之谱复又不可”[16]3。卢朋著、梁翰芬等均对叶、吴温病学术有所推崇,吕楚白、吕安卿、杨鹤龄三家亦深受叶、吴影响。陈任枚在《温病学讲义》中则基于叶、吴温病学术理论体系,结合岭南医家经验构建了一套新的温病辨治体系,是叶、吴温病学术“岭南化”的理论化,代表着岭南温病理论水平新的高度。是故清中叶后的叶、吴温病学术在岭南的传播与在近代的盛行,为近代广东中医学术风貌之另一体现。
近代广东中医学术风貌之最大特点是本土经验不断地被熟稔经典文本的主流医家吸纳,与经典文本理论汇于一炉,应用于日常临症之中,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岭南中医临症风格。而这一风格的形成,意味着岭南医学流派核心内涵的成熟。本来中医学理论就是在融合地域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丰富而发展起来的。岭南医家于经典之外吸收本土经验的现象,在岭南历史上是持续存在的,到了清代,特别是近代,岭南本土医学著作大量出版,逐渐建构起特色鲜明的岭南医学体系,而本土经验正是推动这一过程持续、强劲的力量。
所谓“本土经验”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对疾病的认识与诊疗经验。如陈任枚《温病学讲义》中阐述温病病因时,将伏气列为首因,认为其为“人身阳热之气郁伏于人身之内而不得外泄者也”,“其伏匿深沉,郁极而发,或为外邪激刺而发,或为饮食嗜欲逗引而发。其发也,多致内外合邪,势成燎原,不可向迩,此即所谓温病也”[16]。这是基于岭南人阳热体质特点,一有外感,易于从阳化热的认识而提出的富有岭南特色的温病病因观。又如吕安卿认为温病用药,当以松、通、清为原则[3]117,“比方热水在保暖壶中,一定要拔其栓塞,使热有出路,热水才可以徐徐转冷”[3]8。本土经验的另一方面体现在用药方面。近代岭南医家独具特色的用药风格一直是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医史学家吴粤昌将吕楚白、吕安卿、杨鹤龄、郭梅峰列为近代岭南四大家,其缘由即是认为此四家最能体现岭南医家对药物功效的独特认识及其独具一格的用药习惯。如吕楚白、吕安卿喜用素馨花舒肝解郁、调畅气机,而少用柴胡;吕楚白对于咳嗽气逆,喜用柿蒂、竹蜂,治肿胀喜用蒟叶、黑白丑(牵牛子)等。吕安卿用苍耳子、蒺藜、甘菊、蜂房、天麻治阴虚阳亢或肝阳偏盛之头痛,用锦地罗、天香炉治痢疾,以及对柚树寄生、松树寄生、杉寄生、桑寄生等几种寄生药材的应用等。杨鹤龄更是以善用花类和广东土药闻名,据说其用药不过百种,常用者三至数十种,而花类竟占22 种之多,其用素馨花舒肝,白莲花清暑,腊梅花解毒透疹,扁豆花健脾祛湿以及象牙丝退热、竹卷心清心等[4]111,皆属地域特色用药。梁翰芬、卢朋著等也十分重视民间方药。梁翰芬曾言:“久在民间流行之方药,每有实效,医者宜搜集,验之临床,切不可忽视,医圣张仲景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想伤寒金匮之方,大多是当时已在民间流行之方。广州及邻近各县流行之方,如五核汤治疝气,七星茶治小儿外感,苦瓜干、鬼羽箭、榕树须、鸭脚皮治夹色伤寒,昆布、海藻、生地、犀牛皮治血热暗疮等,均有一定效验,对症可加减用之,不必强求处方要‘有书为证’也”[17]。卢朋著在《中医杂志》第1 ~6 期连续刊载其采录的《验方》。医史学家梁其姿指出:“医学知识的建构不纯粹基于经典,贸易、移民、政治、宗教、基层社会的生活经验,自然生态与疫疾环境等均深远影响着医学知识的建构,人群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是创造知识的重要动力”[18]。正是这种对于本土经验的重视与吸纳,使岭南医学流派成为祖国医学体系中光彩夺目的地域性医学流派。
4 结语
观近代广东中医之学术风貌,无论是其日常临症中的以证括病、执证驭繁,对传统经典命题始终热切的兴趣,亦或是对仲景学说的探索,对叶、吴温病学术的发展,以及对本土经验持续的重视与吸纳,都体现了中医学术体系的灵活性与稳定性。处激变之时代,中医学术之灵活性使其在面对纷纭的挑战时,能以固有的理论,消弭各种挑战多变的锋芒,而于过程中获得其自身学术规律与恪守传统的稳定的发展,展示出了中医学术强大的生命力。王夫之《周易外传》云:“圣人于常治变,于变有常,夫乃于时偕行,以待忧患”,可为注脚。而反观今日,面对近数十年来“中医科学化”“轻医重药”“以现代科学语言解构中医”等强势话语,我们对于中医学术理论体系本身是不是应该有别样的思考与基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