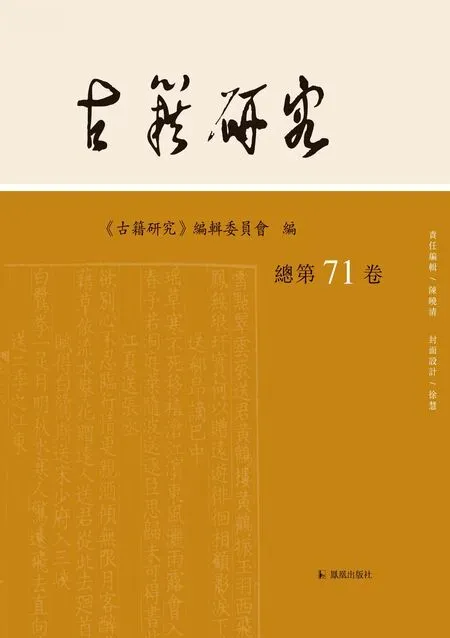《建康實録·魏虜傳》对《南齊書》的校勘價值*
郭 碩
關鍵詞:建康實録;魏虜傳;南齊書;校勘
長期以來,對《建康實録》史料價值的研究主要關注其補史的作用,强調其保存了諸多六朝諸史所不載或今已不存的史料。由於其書對原始史料删省過多而導致史事支離破碎,流傳過程中也出現不少錯誤,因而其校勘價值較少爲人注意。《建康實録》南齊部分是全書最爲簡略的部分,且基本没有超出《南齊書》和《南史》的史料範圍,其史料價值向來不被重視,校勘價值更是難以得到正確認識。不過,由於該書成書于唐代,且存有南宋紹興刊本,該版本的時間在現存各種正史版本之前,在文獻校勘方面自有不可忽視的價值。某些特定的卷次校勘意義尤爲重要,《魏虜傳》可謂典型。今就該書校勘方面的一些問題作一梳理,以便重新認識其文獻價值。
一、 史家正統觀念與《建康實録·魏虜傳》的他校價值
由於以《魏書》爲代表的北魏史書記載頗多隱晦不實之處,因而《宋書·索虜傳》和《南齊書·魏虜傳》所記北魏史事的史料價值非常高(1)代表性論著可參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劄記》“崔浩國史之獄”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42—350頁。。不過,《索虜傳》和《魏虜傳》獨特的史料價值却是20世紀以來才逐漸被史家所認識的。自隋唐以來,由於史家觀念的變化,《索虜傳》和《魏虜傳》分别是《宋書》和《南齊書》最受詬病的部分,少有史家認識到其史料價值,甚至極少引述其中的文字。
隋唐之際的李大師對南北朝各自所修史書的一段著名批評説:“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2)《北史》卷一《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343頁。隋唐以降,“索虜”與“島夷”這類侮辱性的稱謂自然很難爲統一國家史家的歷史觀所接受,因而李大師所謂“書别國並不能備”的情况針對的内容,南朝史書中首當其衝的便是《索虜傳》和《魏虜傳》。在其子李延壽所作的《北史》中,曾對其不取《魏書·島夷傳》有過解釋:“至如晋、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魏書》命曰《島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蕭詧雖云帝號,附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爲《僭僞附庸傳》云爾。”(3)《北史》卷九三《僭僞附庸列傳》序,第3061—3062頁。《南史》雖不見有類似的説明文字,但從文本來看,其處理方式也大體相類。正因爲如此,在《南史》中不僅《索虜傳》和《魏虜傳》篇目無存,甚至連此二卷中成句的内容也少見引用。至於《北史》中所記的北魏事,與二傳記載相關的内容雖多有涉及,但李延壽也基本未予采信,是否有參考引用或據以考訂也值得懷疑。
與李大師父子類似的歷史觀也影響到了唐宋之際類書的編纂。經筆者搜集檢索,就《南齊書·魏虜傳》的文字而言,幾部類書中,《太平御覽》所引者僅2條,不到70字;《册府元龜》則僅有卷二一五《閏位部·和好》以及卷二一七《閏位部·交侵》各引數條,只有總計不到300字的内容。除此以外,今存的唐宋以來各種類書甚至都找不到直接引用該卷内容成段乃至成句的具體例證了。
與《南史》和各種類書不同,《資治通鑒》及其《考異》是采信《魏虜傳》較多的一種史著。從《資治通鑒》的體例來説,由於司馬光等人下過很深的考證功夫,對史料進行細緻的判斷選擇之外,更多的是對史料的重新梳理和剪接。這種態度對於史事的梳理當然是極具價值的,但就史料校勘層面而言,《通鑒》所引用的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史料的本來面目,則不得不仔細加以分辨。具體到《魏虜傳》這類記載,司馬光也堅持貶斥“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爲南爲島夷”(4)《資治通鑒》卷六九魏文帝黄初二年“臣光曰”,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186頁。的歷史觀,對其記載更是抱着極爲謹慎的態度。由此,《通鑒》采信《魏虜傳》的材料往往都經過了考辨和改寫,所引内容往往都與《魏書》以及其他材料錯出,基本找不到完整引用的段落。最常見的情况是前一句來自《魏虜傳》,後一句便來自《魏書》,即便能够判斷其出於《魏虜傳》,字句之間也很少有完全相同的。除去個别《考異》有對原文的引用和相關説明以外,對《通鑒》與今本《魏虜傳》文字的大多數相異之處,今人已經很難判斷哪些是引自原文,那些來自于司馬光的改寫。因此,就《南齊書》的文本校勘而言,《通鑒》這部分材料的價值可能要大打折扣。
在今存唐宋以來的史書中,只有《建康實録》秉持一種與主流正統觀念不相符契的歷史觀,延續了《宋書》、《南齊史》等南朝史書的正統觀,以定都建康的政權作爲歷史叙事的正統王朝。南朝史書以北朝政權爲僭僞的做法,也加以沿用。或許正因爲如此,《建康實録》爲《魏虜傳》保留了一個專傳的位置,而且是在南齊部分諸傳中篇幅最長的一篇。許嵩雖對《南齊書·魏虜傳》的材料也有不少的删節,但仍舊保留一千二百餘字,是《南齊書》成書以後今存諸種史書中承襲該傳内容篇幅最長的一種,其字數比各種類書和《通鑒》所引的總數還要多。與《通鑒》等後世史書支離破碎的引用相比,《建康實録·魏虜傳》首尾完具,段落次序也基本能與《南齊書》對應,是《南齊書》成書以後承襲該卷内容最完整的一種。更爲重要的是,《建康實録》對《魏虜傳》文字較爲完整的承襲,在今存各種史書乃至類書中都是唯一的。
另一方面,《建康實録》對南齊部分的史事考辨極爲粗疏,對原始材料的處理在大段删芟之外基本上都是原文照抄,少有潤色和改寫之處。或許是和蕭子顯所秉持的歷史觀接近,許嵩對《南齊書》中的諸多侮辱性成爲如“索虜”“魏虜”“虜”一類稱謂都予以保留。不過,從《建康實録》全書的情况看,若是所引材料來自《南史》等史料,亦是沿用李延壽將“虜”易爲“魏”“魏軍”,將“北討”易爲“北侵”“北略”等稱謂,並不回改。這在唐代以後的史書中是極罕見的。這一點早已爲宋代以來的史家所注意,但除了招致“至於名號稱謂,又絶無法”(5)晃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六《實録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5頁。的批評以外,却很少有學者注意到許嵩保留原始稱謂的做法,其實在最大的程度上保留了原始材料的本來面目。雖然由於删略不當産生了很多不必要的錯誤,成書後在流傳過程中又衍生了某些錯誤,但從保留史書原貌的角度來説,《建康實録》仍舊是其他史書所無法比擬的。《魏虜傳》由於全文皆不見於《南史》等史書,許嵩缺乏更多的材料以供參考,更是做到了最大限度上忠實於《南齊書》的本來面貌。
《魏虜傳》在《南齊書》中可算作最爲獨特的一卷,存世文獻對其承襲和參考的情况也與其他卷次極爲不同。由於《建康實録·魏虜傳》是今存唐宋史料中獨一無二的相對完整地襲用《南齊書·魏虜傳》的文獻,因此將其列爲《南齊書·魏虜傳》最重要的他校文獻應當不爲過分。
二、 校勘舉例
如果拋開史法等層面而單就校勘而言,《建康實録·魏虜傳》的意義顯然是不容忽視的。可惜的是這並未引起足够的重視。如校勘《南齊書》最重要的成果即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南齊書》,於《魏虜傳》列校勘記47條,無一條涉及《建康實録》者;其後陸續出現的補正著作,如朱季海《南齊書校議》和丁福林《南齊書校議》,二書校勘《魏虜傳》的篇幅都是各傳中最長的,但都没有一條引用《建康實録·魏虜傳》的内容。筆者在修訂點校本《南齊書》的過程中,僅《魏虜傳》一卷據《建康實録·魏虜傳》新出或補充校勘記就達11條之多(6)參見《南齊書》點校本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因限於體例,校勘記對相關内容均未作詳細説明。今結合點校本修訂的成果,以具體實例對《建康實録·魏虜傳》的校勘價值進行重新檢討,分四類情况略具校例如下:
1. 直接校正史文之例
(1) “佛狸破梁州、黄龍”條(點校本第984頁,修訂本第1090頁):“梁州”《建康實録·魏虜傳》作“凉州”,點校本、朱季海《校議》、丁福林《校議》均失校。按嚴耕望《正史脱譌小記》云:“按梁州指北凉沮渠氏,黄龍指北燕馮氏,此“梁”當作“凉”,中古史書往往有此音誤”(7)嚴耕望:《正史脱訛小記》,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89頁。;田馀慶《拓跋史探》亦有兩處注釋指出此“梁”當是“凉”之譌(8)田餘慶:《拓跋史探(修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63頁注釋〔4〕、第242頁注釋〔1〕。。拓跋燾統一北方攻滅的最後兩個政權是北燕和北凉,北凉在凉州,北燕都城被稱爲黄龍。梁州之地則主要在宋、齊控制之下。此當從《建康實録》作“凉州”爲是,諸家考校皆未注意到《建康實録》的他校依據。
(2) “宏西郊,即前祠天壇處也”條(點校本第991頁,修訂本第1097頁):“祠”字《南齊書》宋元遞修本、南監本、北監本、汲本、殿本、局本等傳世版本皆作“相”,點校本逕改作“祠”而未出校。《建康實録·魏虜傳》作“祠”。北魏郊天之處《水經注》、《通典》皆寫作“郊天壇”(9)《水經注》卷一三云“城周西郭外有郊天壇”,參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42頁;《通典》卷四四《吉禮三》云後魏“至孝文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於郊天壇”,參《通典(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222頁。,不過《南齊書》前文有“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云云,與“即前祠天壇處”文意照應,作“祠”是。由《建康實録》可知,《南齊書》較早的本子可能正是寫作“祠”,是唯一的他校依據,今修訂本據以補充校勘記。
2. 異文文意兩通,而《建康實録》更優之例
(1) “皆使通虜漢語,以爲傳驛”條(點校本第985頁,修訂本第1091頁):“傳驛”《建康實録·魏虜傳》作“傳譯”,點校本、朱季海《校議》、丁福林《校議》均失校。“傳驛”與”傳譯”雖形近,但文意全然不同。前句云“皆使通虜漢語”,則《建康實録》作“傳譯”文意似乎更貼近前後文意。此異文很有出校之必要。
(2) “南門外立二土門”條(點校本第984頁,修訂本第1090頁):“土門”《建康實録·魏虜傳》作“土闕”,點校本、朱季海《校議》、丁福林《校議》均失校。按照當時都城修建的慣例,南門是宫城的正門,門外立雙闕是符合當時制度的。按《正德大同府志·古跡·後魏宫垣》條云“在府城北門外,有土台東西對峙,蓋雙闕也”(10)(明)張欽:《〔正德〕大同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全書第186册影印明正德刻嘉靖增修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261頁。,可見北魏平城宫城雙闕遺跡明代尚存。據陳連洛、郝臨山所考,雙闕位置大致在今大同市操場城範圍内之北魏宫垣南門口(11)陳連洛、郝臨山:《大同北魏平城形制與建城年代探析》,《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第37頁。。從雙闕之遺跡與所處位置看,皆與《建康實録》所記吻合。以此來看,今本《南齊書》中的“門”很可能是“闕”字筆劃缺損而譌。如果采用較謹慎的處理方式,也有保留這一異文的必要。
(3) “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界,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號爲索干都”條(點校本第990頁,修訂本第1096頁):《建康實録·魏虜傳》“干”上有“索”字,原點校本、朱季海《校議》、丁福林《校議》均未校。按《水經注》卷一三“水”條云:“水自南出山,謂之清泉河,俗亦謂之曰千泉,非也。”“千泉”明萬曆朱刻本作“干水”。熊會貞云:“《寰宇記》薊縣下引《隋圖經》云,出山謂之清泉河,亦曰千泉,非也。本酈氏説,酈氏蓋以千與清音近字别,故駁之。足證今本干爲千之誤,水亦泉之誤”(12)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第1191—1192頁。。陳橋驛回改作“千水”(13)陳橋驛:《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24頁。,不過未出校辨析。即算作“干水”不誤,亦是水東流至薊縣之地才稱此名,而非“平城南”,今本《南齊書》之文仍頗存疑問。又,水流經平城時又稱桑乾水,楊守敬云“水上源爲桑乾水,其下流爲水,非桑乾水與水爲二也。”(14)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第1133頁。《三國志·任城威王彰傳》裴注云:“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15)《三國志》卷一九《任城威王彰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556頁。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二五云:“索干即桑乾之轉”(16)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卷二五《南齊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35頁。。又按《水經注》亦云“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縣西北上下。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溹涫水者也。”(17)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第1128—1129頁。此“溹涫”亦“索干”音轉。以上諸例可證《建康實録》作“索干水”不誤。從《南齊書》前後文看,下文云“世號爲索干都”,前作“索干水”,文意方有着落。因此,《建康實録》“索干水”之異文很有可能是正確的,有保留之必要。
3.補充原校勘之例
(1) “魏、晋匡輔”條(點校本第988頁,修訂本第1094頁):“輔”字宋元遞修本、南監本、北監本、汲本、殿本、局本皆作“戰”,點校本依據《通鑒》改爲“輔”。今按《建康實録·魏虜傳》亦作“輔”,較《通鑒》更早,可資補充。
(2) “皇師雷舉”條(點校本第993頁,修訂本第1099頁):底本“雷舉”文義不通,汲本、殿本、局本作“電舉”,點校本據以出異文校,然“電舉”似亦不通。按,《建康實録·魏虜傳》作“電擊”,用以指稱軍隊長驅直入,前人用例頗多,如《漢書》卷一《叙傳》稱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長驅六舉,電繫雷震”,《文選》卷四七陸士衡《漢高祖功臣訟》稱曹參“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卷六陸士衡《吊魏武帝文》稱“摧群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等。三者相較,以“電擊”最優。今修訂本以此補充出校。
4. 補正原書脱譌之例
(1) “佛狸討羯胡于長安,殺道人且盡”條(點校本第990頁,修訂本第1096頁):此條有兩處校勘點。其一,“羯”字宋元遞修本作“及”,而南監本、北監本、汲本、殿本、局本改作“羯”,《建康實録·魏虜傳》作“反”, 點校本以“及胡”不通,據諸本改爲“羯”。按此條所記之事,乃北魏史上著名的蓋吴之亂。《宋書》卷九五《索虜傳》云“二十三年,北地瀘水人蓋吴,年二十九,於杏城天臺舉兵反虜”(18)《宋書》卷九五《索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339頁。,史料均指明蓋吴爲盧水胡,並非羯胡。一般而言,盧水胡主要是分佈於關中以西的胡族,羯胡則指分佈于河北的并州雜胡後代(19)參見陳勇:《後趙羯胡爲流寓河北之并州雜胡説》,《漢趙史論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89—211頁。,二者有一定區别,在南北朝的文獻中也有明確區分。今存魏晋南北朝時期的“羯胡”“胡羯”“羯”用例,或確指石趙一族的雜胡,或用作北方雜胡的貶稱,没有一例用以指代盧水胡的。今按“及”“反”形近,史書中二字相譌者極多,但“及”與“羯”只是音近,《建康實録》作“反胡”説明在唐人所見的文獻中並不是作“羯胡”的,因此南監本等作“羯胡”當出自明人臆改。據此,此處當從《建康實録》作“反”,而不應從後出的版本改作“羯”。
其二,《建康實録·魏虜傳》在“于長安”下多“有道人射殺虜三郎將斛洛真佛狸大怒悉毁浮屠”二十字(20)按“斛洛真”張校本、孟校本《建康實録》誤作“斛浴真”,係形近而訛。四庫本不訛,今從之。。今本《南齊書》此前後文意不接,對“討羯(反)胡于長安”與拓跋燾屠殺僧人二事之間有何聯繫全無交代。從《建康實録》補入此二十字後,文意方才顯明。核諸《建康實録》南齊部分,溢出《南齊書》和《南史》的史料而有字數連續達二十字者,這是唯一一例。又按《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云:“會蓋吴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内,御騶牧馬于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聞”(21)《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點校本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3296頁。,《魏書》對蓋吴之亂的記載細節方面完全不同,許嵩也不大可能依據北魏方面的史料對此細節進行補充。引文中稱北魏爲“虜”、稱拓跋燾爲“佛狸”,也都是南朝方面史書中的寫法。更重要的是,此二十字中出現了“三郎將斛洛真”一詞,不見於傳世文獻。但在上世紀出土的《文成帝南巡碑》碑陰題名中,出現了“三郎”“三郎幢將”“斛洛真”“斛洛真軍將”諸名號,皆北魏直宿禁中之武官(22)參見靈丘縣文管所:《山西靈丘縣發現北魏“南巡御射碑”》,《考古》,1987年第3期,第281—282頁;張慶捷:《北魏文成帝〈皇帝南巡碑〉的内涵與價值》,《民族匯聚與文明互動:北朝社會的考古學觀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48頁。。按《南齊書·魏虜傳》前文記“帶杖人爲‘胡洛真’”,後文又稱“輦邊皆三郎曷剌真”,朱季海《校議》云:“鮮卑語‘曷剌真’即幢將之屬,魏收從漢名書之,子顯特存代北舊名耳。”(23)朱季海:《南齊書校議》,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31頁。從《南齊書》的用例來看,蕭子顯對北魏的人名、官名,往往隨音翻譯,所取之字往往不同,常見同一人、同一職官在《南齊書》中有多種譯名者。實際上,“斛洛真”與“曷剌真”“胡洛真”應該都是“帶杖人”同音異譯,與《南齊書》對人名、官名的寫法非常吻合。綜合以上情况,此二十字很有可能是《南齊書》流傳過程中的脱文,賴《建康實録》得以保存。
總之,《南齊書》在流傳過程中産生的問題,能够通過《建康實録》他校解决的問題雖然只是少數,但已極具意義。儘管《建康實録》本身存在諸多錯譌之處,但對其他南朝史書的校勘價值是不應該忽略的。如《魏虜傳》這類特殊卷次,《建康實録》的他校價值要比其他卷末更爲突出。